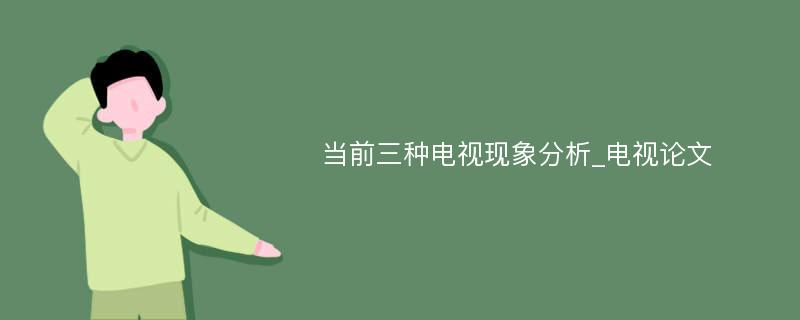
当前三种电视现象之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现象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电视业以迅猛的改革步伐,震动着中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方方面面,也引起了社会的瞩目,而且近期步伐迈得更为急促,提出了诸如建立世界一流电视大台,推行产业化、集团化等观念思路,这些愿望或许设想非常美好,作为目标、旗帜、口号是振奋人心的,但由此而带来的电视业普遍的求快、求新、求变、求加速增长等趋向和局面,不论是从中国国情,还是中国电视业目前的条件和基础来看,却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愿以当前流行的三种电视现象为切入点,进行一些分析批判,可能不够成熟甚至不够正确,还望得到业内外同仁的批评斧正。
一、关于“技术崇拜”与“形式崇拜”
当前中国电视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每家电视媒体都在探索生存之路,发展之路,突破之路,这对推动中国电视的整体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突破点在哪里,出路在哪里?许多电视媒体把眼光放在了“技术”和“形式”的突破上。
从技术突破方面来看,又包含了传输技术和制作技术两个部分。许多电视媒体根据自己的实力铺设先进的传输网络,引进新技术(如数字压缩技术),以备增加未来的电视传输能力。在制作上也努力更新设备,引入新的编辑系统、制作系统,以创造新鲜别致的屏幕形象。
应当指出,追求技术上的突破是电视发展必需也必然的环节。电视发展历史上由于技术突破带来的电视传输能力、电视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带来的电视屏幕形象的重大改造和变革,是有目共睹的。电视作为现代高科技与高文化的结晶,技术突破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应当否定。
但当下的确出现了盲目追求技术突破的现象,不少电视媒体把自身生存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技术突破上,形成了“技术崇拜”的取向。
我认为在国家整体上还处于发展中水平的国情条件下,盲目追求技术突破是不可取的。而事实上,技术突破所带来的也未必是立竿见影的效益。如果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观念滞后,再好的技术也不可能带来电视媒体发展的突破。对于电视的“上帝”——观众而言,电视节目好看是第一位的。技术突破如果带不来节目的好看,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技术崇拜”是值得业内人士警醒的。
与“技术崇拜”相关相联的是“形式崇拜”。由于中国电视的本体建设尤其是形式的开发建设起步较晚,最近十年来形式突破力度较大,电视媒体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于是许多电视从业者陷入了“形式崇拜”之中。一个节目、一档栏目,首先考虑的是形式突破的各种“招”、“术”,如考虑节目串联方式、叙述方式、演播室设计方式、观众参与方式、主持人与观众的交流方式、声画结合方式等如何才能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最好是产生令人惊诧的效果。电视从业者们开始迷醉于对各种“形式”、各种“招”、“术”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某家电视媒体屏幕上出现什么较为新鲜的形式或“招”、“术”时,不久便会被无数家电视媒体群起而“克隆”、仿效,形式的变革便这样风风火火地演进着。
客观地讲,形式的无限丰富是电视屏幕丰富多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的变革演化对电视节目的发展繁荣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将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寄托于形式本身的变革改造上,也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取向。“形式崇拜”可能带来的弊端或后果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造成电视屏幕“浮化”、“浮躁”的景观。一些花里胡哨的“形式”充斥着电视荧屏,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疲惫不堪,只好关机以找回宁静和放松。第二,造成电视屏幕新的千篇一律的景观。事实上,电视节目的形式万变不离其宗,大的类型和方式是离不开其基本要素的,如果只求形式上的变革或与众不同,结果还是避免不了“撞车”、“雷同”或“似曾相识”,结果还是“千篇一律”。第三,造成形式大于内容、媒体观点缺失的局面。的确当下有不少电视节目,过于注重形式的变化和视觉、听觉的冲击力,而把其传承的内容忽略了,更缺乏电视媒体主体观点的选择、整理、判断。久而久之,还如何塑造媒体的独立形象呢?第四,造成从业者自我炫耀、自我表现而脱离观众需要的局面。当下许多电视从业者常常不去投入很大精力了解观众、社会需要,而只按自己的一己的思路,局限于苦思冥想“形式”的突破上,最终很可能导致自己“创造”的那些“形式”只成为自我炫耀、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对象,而无法让社会、让观众得到满足的局面。
所以,“技术崇拜”和“形式崇拜”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电视媒体生存、发展之路,其突破点并不是“技术”本身(尽管技术非常重要),而在于节目;节目丰富繁荣、好看的突破点也不在于“形式”(尽管形式同样非常重要),而在操纵节目的“人”——电视的记者、编导、主持人等从业者那里。
说到底,最关键的突破点(要素)不是“技术”、“形式”,而是“人”。因此造就、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教养、高水平的电视从业者队伍,是中国电视大发展的永远的目标。
二、关于“改版”与“创新”
自1995年以来,以电视栏目“改版”和电视节目“创新”为号召的“改版”与“创新”的潮流在中国电视界不断涌动,最近一两年一浪高过一浪,演化为全行业的整体性行动。
“改版”和“创新”都意味着葺旧更新,破旧立新,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改版”和“创新”是为了提高电视节目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日益提高着的精神需要。从电视传播自身的规律来看,根据时代、社会诸方面条件的变化,对已有电视节目、栏目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革也是有必要的。但“改版”与“创新”的实质是什么?目前“改版”与“创新”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到底应当怎样进行“改版”与“创新 “?这些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几个问题,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实际的问题。
什么是“改版”与“创新”?当下许多人把“改版”与“创新”理解为彻底改变或从未有过的“全新”的改变,有人就宣传自己推出的节目或栏目是“绝对全新”、“从未见过”的样式和面貌。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任何“改版”或“创新”都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基础或前提条件:第一,同类电视节目或栏目此前的积累;第二,电视媒体自身的能力;第三,社会、观众可能的接受、承受能力。
而目前普遍火热的“改版”与“创新”浪潮中出现的许多总是电视媒体或电视从业人员对上述三个基础、前提条件考虑不够,盲目上马所致。
怎样进行电视的“改版”与“创新”呢?当下常规的思路是求“变”、求“动”、求“新”,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个人更倾向于到那些相对“不变”、相对“稳定”甚至相对“旧”的素材中进行开掘,这种思路、方式我把它叫做“素材增殖”。
所谓“素材增殖”,意味着将电视栏目、节目已有的“旧”的影像资料作为素材,按照新的思路、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在新的背景、条件、时机中,进行行政机关的组织、处理、编辑、加工、改造,使之产生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如果一种素材被使用多次,那就意味着它“衍生”、“繁殖”了多次,素材使用的频率越高,其增殖的能力越强,其开发的效益越高。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组毛泽东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影像资料作为素材,可以说达到了“素材增殖”的最大效益。
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充分使用已有素材(包括自己拍摄制作的,也包括了从外部购买进来的),只是变换角度、思路与方式,而且考虑不同的背景、条件和时机,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
我们还可以看到,《动物世界》、《东芝动物园》购入的节目,经过我们自己的编辑、处理、整合,同样达到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素材增殖”是一个“改版”、“创新”的很好的思路与方式(当然并非是唯一的思路与方式)。之所以我特别强调“素材增殖”,我认为这是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契合的。不可讳言,许多电视媒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改版”、“创新”,许多电视栏目、节目动辄斥资千万百万,做一档或一个“一次性”播出的栏目、节目,这种浪费是巨大的,也是可怕的。
强调“素材增殖”,同时也符合电视生产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因为“素材增殖”并非否定全新的电视生产与制作,而是对“改版”、“创新”思路的一种调整——已有的“旧”的素材同样蕴含了丰富巨大的资源有待我们去开掘。因此,电视媒体建立自己的“节目库”,以收购、储存大量节目素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海外许多电视媒体在“节目库”建设上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三、关于“收视率迷信”
当下许多电视媒体“把关人”及各类电视从业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有关媒体调查机构提供的收视率当作检验自己工作业绩的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尺,依据收视率的高低进行电视栏目播出频道、时段的安排,甚至依据收视率高低来决定一档电视栏目、一个电视节目的生死存亡。这无疑是一种“收视率迷信”。
将电视节目收视率放置在这么高的地位,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电视现实运作的必要。因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电视媒体仅仅当作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而忽略了电视媒体的其它功能的发挥,至于电视的社会传播效果到底如何,更不去注意。因此对电视收视率调查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我们的电视媒体对其市场效应、社会效应的综合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对其客观传播效果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收视率的重视是一种进步。
另外从电视的现实运作来看,以收视率作为最为重要乃至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尺恐怕也是不得已,如同以一次性的高考来决定考生胜负一样。因为相比较而言,也许收视率是最客观、最让方方面面无言以对的标尺,的确,舍弃收视率的标尺,又有什么别种的标尺可以替代呢?
但历史与现实的必然与合理性,不能表明其正确性。盲目地追求高收视率,陷于“收视率迷信”的弊端显而易见。
第一,引发“收视率”调查的“暗箱操作”,失去收视率调查的客观公正和权威性。既然各电视媒体的“把关人”们如此重视收视率,为了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数据,出于利益考虑,“收视率”调查机构和电视从业者有可能达成某种默契,通过“暗箱操作”,对“收视率”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适当调整和修饰,这是无法避免的一种结果。如果普遍采用“暗箱操作”来做出收视率调查数据,那收视率调查的客观、公正和权威性无疑将丧失。
第二,不能区分“绝对收视率”与“有效收视率”,导致决策的失误。当下大家普遍只看取“绝对收视率”,即最终收视率的数据,但却不去看取“相对收视率”即“有效收视率”,即不去分析判断收视群体的实质性收视行为和收视的关注程度。假如有一万人来看某电视节目。而这一万人却是消费水平、投资电视的意愿和能力较低的收视群体,那么就算收视率较高,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假如只有10人来看某电视节目,而这10人却是消费水平、投资电视的意愿和能力都很高的收视群体,那么就算是收视率很低,对于电视业自身来讲,是不是比上述高收视率来得更有意义呢?答案是显然的。如果不能区分“绝对收视率”与“有效收视率”的话,只看表面的收视率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势必导致决策失误。
第三,盲目地追求高收视率,将影响电视媒体社会效益的发挥。收视率的情况与电视的市场效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高收视率往往意味着电视传播较大的市场份额占有(当然也要对相对的“有效收视率”作一分析)。追求高收视率,以获得电视媒体更大的市场份额的占有,这无可厚非。但中国电视媒体毕竟担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担负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等重任,如果仅仅考虑高收视率,势必将具有较大社会效益但也许收视率不高、收视群体相对少的电视节目挤出关注视野,任其自生自灭,从长远利益考虑,这将导致两个文明建设的不平衡局面(至少从电视传播来看),影响电视媒体巨大社会效益的发挥,对于民族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的教育、培养、塑造也非常不利。当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出现这种局面,但防微杜渐是必要的。
“技术崇拜”与“形式崇拜”、追求“改版”与“创新”及“收视率迷信”,成为当前中国电视业普遍存在、广泛流行的三种现象。任何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这三种电视现象的发生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浮躁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阶段,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在“转型期”过程中,人们传统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等发生着巨大变化,种种社会问题接踵出现,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种社会情状下,由失落、不平衡、找不到自己的准确社会定位等带来的必然是浮躁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心态,电视传媒作为社会情状敏感的反映者,自然逃脱不了其深刻影响,自身也出现种种浮躁,而电视浮躁又倒过来反作用于社会,加剧了这种浮躁的力度。
第二,媒体竞争的日渐剧烈,电视生存危机意识的产生。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各大传播媒介也同时进入了其“转型期”,报业集团、电影集团、出版集团的纷纷建立,使得电视以往的独特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数千家各类电视媒体自身的竞争也日渐剧烈。传统的行政垄断不再奏效,要在众多电视媒体竞争中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受动摇,也越来越显得艰辛困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各种电视媒体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匆匆出台各自的谋略与招术。
第三,受众的严重分流。受众(读者、听众、观众等)是媒体剧烈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媒体的剧烈竞争,意味着他们可能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媒体的自由度。对于电视媒体来说,至少有两个系统的竞争造成了其受众的严重分流:一是信息传播系统。除各种电视媒体外,日益活跃、丰富的各类报纸、杂志、读物及因特网等传播了多种多样的信息,许多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被诸多传播媒体所分化。二是娱乐系统。除各种电视媒体外,各种健身场所、游艺场所、休闲场所及因特网等同样提供了为不同类型受众所喜欢的娱乐服务,它们也从电视媒体这里夺走了一大批受众。
在这样的情境中,电视媒体想方设法施展自己的独特魅力,其初衷和设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技术崇拜”与“形式崇拜”、追求“改版”与“创新”和“收视率迷信”恰如一把把“双刃剑”,同时具有正面与负面双重的意义与价值。本文的主旨并非彻底否定它们的存在,而是意在警醒大家,在关注其积极正面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谨防或遏制其消极负面的意义与价值的膨胀与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