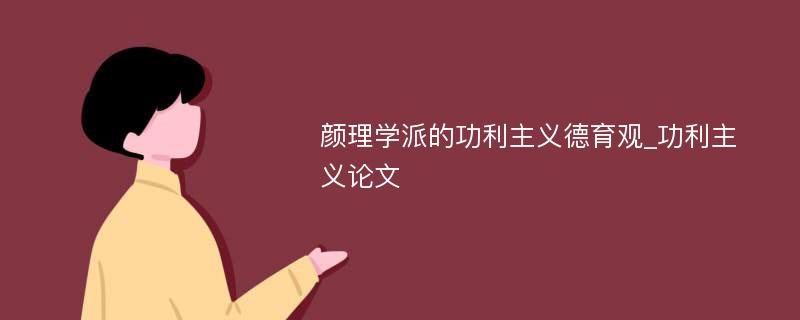
颜李学派的功利主义德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主义论文,德育论文,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颜李学派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作为其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在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道德、鄙弃实事实功之风的基础上,提出了“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观,主张不是从个人道德完善而是从济世救民的实际功业完成方面来论圣贤;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求学者既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又必须具有济世救民的真正本领,而对后者尤为重视,认为德性只有在济世救民的实际才能和活动中才能真正体现。颜李学派德育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对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否定。
关键词 颜李学派;义;利;实事实功;圣贤
颜李学派是清初著名的学术流派。学派代表人物有颜元、李塨等。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李塨(公元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颜元弟子。颜元是学派的创造人,李塨则大力宣传颜元学说,畅发颜学旨趣。颜元学说因李塨而得以广泛传播,名震一时,故当时人们称之为“颜李学”。颜李学派以富国强兵、民安物阜为宗旨,崇尚艺能,讲求经世致用,以彻底的毫无保留的态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在德育思想方面,颜李学派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他们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实事实物”的品德教育原则与方法以及“习动贵行”的修养论,表现出浓厚的近代启蒙特色,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就颜李学派德育思想的核心——功利主义的德育观作一简要论述。
一、颜李学派德育观的理论基础:“以义为利”
明清之际,风雷激荡,天崩地坼,变革与启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时进步的思想家适应时代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义利观上,颜李学派也冲破了宋明理学樊篱,提出了“以义为利”的义利关系说,从而为其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义利关系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创始人孔子强调“以义制利”,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重义轻利思想,反对言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就确立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基本价值取向。到汉代,董仲舒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把这一价值取向推向极端。宋明以来,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反对功利,将义利之辨视为“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颜李学派则于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义为利”的观点。颜元说:
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习斋言行录》卷下)自古以来,圣贤的“正德”之事就是和“利用”、“厚生”之事紧密联系起来的,“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习斋言行录》卷下)。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必须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见”、“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而理学家却讳言功利、不求效用,这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颜元批判说:
宋家老头中群天下人才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秘,指办干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祀庙廷之典。……是世间之德乃乱矣。(《朱子语类评》)
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高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所造就的必然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存学编》卷一)的无用于世的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无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朱子语类评》)。为了扭转这种空疏的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颜元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存学编》卷四)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动机和效果的一致,必须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把“功”作为道德评价中必不可缺的因素。颜元还特别强调以“用”来判断、评价道德。他说:
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习斋年谱》卷上)
德性的醇驳、学问的得失,都离不开用的检验,必须要通过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才能判断。这样,德性就不是什么空洞抽象、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与事功联系着,在实事实功中表现出来,对人物道德价值的评判也有了一定的客观标准。无疑,颜李学派的这一卓见是对崇尚空疏而鄙弃经济生民实际功效的宋明理学超功利主义的根本否定。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就必然会有相应的德育目标和理想人格。颜李学派的德育观正是建立在这种“以义为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之上的。
二、“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观
颜李学派十分重视人才,视人才为治国安民之本。颜元在谈到人才的重要性时说:
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习斋记余》卷一)
在颜元看来,人才无疑是完成政事、治平、民命的最关键、最为根本的因素。因此在谈到实现自己“安天下”的政治理想时,颜元把“举人才”作为首要措施,“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可谓对人才寄予厚户。那么,颜李学派所期望的人才究竟是怎样的呢?颜元在谈到自己的人才理想时说:
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虽矫语性天,真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习斋言行录》卷上)
吾儒自有真才真器,隐足以型俗开后,见足以致君泽民。(《习斋记余》卷四)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才是圣贤。圣贤是儒家的传统范畴,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颜李学派沿用了儒家的这一范畴,但是其内涵却已发生了变化。儒家传统的圣贤多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偏重于内心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而并没有包含对事功的要求,即所谓的“内圣”。而颜李学派的圣贤范畴则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从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事功的要求,而对于事功则尤为注重。因此,颜李学派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有“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所提出的是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的圣贤观。
对人才的要求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明朝灭亡、清兵入主、天下残破的惨痛事实,促使颜李学派思想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学学风的空疏无用,人才的柔弱无能,并且认为这正是导致亡国之祸的重要原因。颜元揭露宋明理学静坐读书教育培养的人才的柔脆无用:
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材,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腔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习斋记余》卷一)
这种毫无实际本领、百无一用的人才充塞朝廷,则必然导致民生凋蔽、社会腐败,其结果必然是误国害民。李塨揭露道:
至于明末,万卷经史、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矢。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社墟、生民熸矣!祸尚忍言哉!(《平书订》卷一)
明亡的历史事实仍相去不远,因此颜李学派对于宋明理学教育所造就的人才的这种揭露和批判就显得相当深刻而切中肯綮,其痛恨之情,跃然纸上。在颜李学派看来,宋明理学学者,沉溺于静坐空谈、讲学著述而不谙世事,根本算不上什么人才,更谈不上是什么圣贤。颜元说:
世岂有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存学编》卷二)
按照颜李学派的圣贤标准,入仕20多年而“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朱子语类评》)的朱熹只不过是无用的腐儒。而与此同时,王安石、陈亮等谈求经济生民、注重事功的思想家却备受推崇。颜元称赞王安石为“宋朝第一有用之宰相”、“三代后第一人”(《习斋记余》卷六)。在颜元看来,王安石建功立业、造福生民,是历史的功臣,是三代后第一大圣人,却被理学家斥为小人,而空谈性理、无益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被尊为圣贤,这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有宋一代人的不幸。正是这种道德评价标准的颠倒,圣贤观念的倒错,葬送了大宋江山。因此,重新审视、评价历史人物,在圣贤观上正本清源,是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问题。这是颜元所不能不辨、不得不辩的。对于那些迂腐无用却自命为或被吹捧为圣贤的理学学者,颜元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他说:
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而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存学编》卷二)
在这里,颜元以古讽今,揭露了静坐著述、空谈性理的理学人才误国祸民的实质。为此,颜元慨叹道:“坏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习斋年谱》卷下)正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沉痛反思、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社会风气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李学派提出了其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习斋记余》卷三)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的目标。
三、颜李学派德育观的具体要求
“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是颜李学派的人才理想,也是他们提出的品德修养和教育的目标。颜李学派鼓励人们立志用功,学作圣人。“学者,学作圣人也”、“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习斋言行录》卷下)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颜李学派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作圣的具体要求。
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往直前、变革现实的勇气。明清之际的历史动荡,使颜李学派已经预感到了重大的社会转机正在孕育发展。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文盛之极必衰”的转机关头。这种转机存在着两种前途:或者“返文于实”,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于野”,使“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为了使社会转变朝有利于生民百姓的方向发展,颜李学派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留意世事、关心民瘼,要求学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圣道,扭转乾坤。他们说:
天下事皆吾儒份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存学编》卷二)
卓然奋立,以我为天下万世必不可少之人。(《恕谷后集·留别长安诸子》)
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
在这里,颜李学派所倡导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为天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他们认为,作为儒者,就必须“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习斋记余》卷三《寄桐乡钱生晓城书》)。对于宋明理学学者天崩地解而落然无与、“不做费力事”(《存学编》卷二)的种种表现,颜李学派深表痛恶。同时,有感于宋明理学教育的空疏和当时学者不救困穷而徒论危微精一的流风恶习,颜李学派更强调勇往直前、奋力变革,决不能同流合污,随俗沉浮。他们说:
但抱书入学,便是做转世人,不是做世转人。(《存学编》卷四)
勇往直前,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朱子语类评》)
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恕合年谱》上)
颜李学派强调变革现实,积极干预世事,建功立业,造福天下。他们对于学者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感和卓然奋立、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其次,必须具备济世救民的实际本领。他们认为,“德行之实事俱在六艺,艺失则德行俱失”(《大学辨业》卷二),德性要在济世救民的实际活动中习成并且通过实事实功的完成来体现,因此,只有有能有艺、立足附众、武足威敌、艺足成事,才能造福生民、建立功业,成为圣人。否则,徒言高论,终究只是镜花水月。明末学者“愧元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存学编》卷二)的现实表现更使他们体会到:学者不仅应当有学为圣人的远大志向,更应该具备治国理民的实在学问和经世致用的实际能力,能够身任天下大事。因此他们对六艺之学特别推重,主张“学从六艺入”,从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学入手进行学习,在习艺中涵濡性情,在运用中体现德行。颜元说:
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存学编》卷一)
所谓“通儒”,实际上就是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才,与“圣贤”意思一样,指的是具有“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的实学,能够历难危、任繁难的通才。同时,在颜李学派看来,通儒固然是圣贤,而偏胜偏至之才也同样可称之为圣贤,“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存性编》卷二),甚至可以只精通一德一艺,或数人合精一艺,仍不失为圣贤。颜元说:
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如一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如习礼者某冠昏、某丧祭、某宗庙、某会同,亦可也。(《存学编》卷一)总之,颜李学派认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习斋言行录》卷下),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真才实学,能够以己之所长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生民,就具备了作圣贤的条件。圣贤就必须具有实学、能有用于世。他们以此评判宋明理学学者,将那些鄙弃六艺实学,崇尚性理空谈,没有扶危济难的真正本领、不可相不可将而于社稷生民无用的理学人才,斥为“将就冒认标榜”的假圣人。颜元说:
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存学编》卷三)
颜李学派呼唤真学真圣。他们的圣贤是能够“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具实学有实用的人才。他们对于作圣贤的具体要求,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德、才两个方面,只不过颜李学派是把有“才”作为“德”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方面来要求并且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其理想人才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来谈的。而对于实际才能与事功则尤为重视。这与传统儒家专从个人心性修养、品德完善方面来要求的观点,无疑是有根本区别的,具有功利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其具体内容和要求都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可以说,颜李学派的德育观是功利主义的德育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范围,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济苍生”、“担荷圣道”等传统范围,但是,颜李学派的功利主义德育观是对宋明理学超功利主义德育观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学教育的衰颓,是中国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声。在崇尚空疏、鄙弃事功的“文盛之极”的时代,其历史意义尤其不可低估。
本文于1994年12月18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