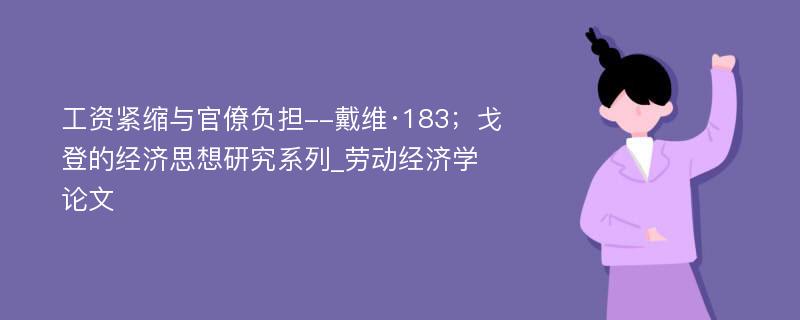
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大卫#183;戈登经济思想研究系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卫论文,官僚论文,戈登论文,负担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11—0096—09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的研究热潮,然而作为该学派主要创始人大卫·戈登教授的著作并没有引起应有的理论关注,呈现出了“去戈登化”的研究现状,笔者将以系列研究性评论文章持续发力,着力刻画戈登的经济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大卫·戈登(David M.Gordon,1944-1996)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在1971年以《阶级、生产率和贫民区》(Class,Productivity,and the Ghetto:A Study of Labor Market Stratification)为题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73年加入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直到1996年因心脏衰竭病逝。戈登去世之前,任新学院经济学教授,也是经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戈登出生于经济学世家:他的父亲,罗伯特·亚伦·戈登(Robert Aaron Gordon)是杰出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美国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关键人物,1975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戈登(Margaret S.Gordon)因其对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经济学研究而闻名,两人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并任经济学教授;他的哥哥,罗伯特·J·戈登(Robert J.Gordon)是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妻子,戴安娜·戈登(Diana Gordon)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2] 纵观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四大特点:一是,自始至终都把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研究作为核心命题;二是,构建和贯彻具有历史性、制度性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三是,大规模使用定量分析,娴熟运用计量经济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四是,戈登的学术研究和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饱含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这和他与美国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工人工作生活的细致考察密切相关,这在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努力寻求更具民主特点的经济学中有充分体现。具体而言,其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在哈佛大学研究生时代,戈登已经开始关注贫困、就业、劳动市场等经济社会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是在皮特·多林格(Peter Doeringer,当时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后来任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在其论文中,戈登证明了纽约和底特律城市内部“劳动市场的二重性”(duality of labor markets)。他发现,在根据工资、福利、保障和工作条件对职业(jobs)进行的排序中,存在显著的“双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在详细地实证分析下,这一结论成了他最初的“学术符号”;他通过“二重劳动市场因素”很好地解释了在这些市场中职业的不同性质。[2]戈登把自己的一些发现,结合与其他人的合作,撰写了一本关于城市贫困、影响颇广的书——《贫困和不充分就业理论》。[3] 在1970年代,戈登与曾经同为哈佛大学研究生的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和里奇(Michael Reich)围绕劳动市场问题持续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了深受历史影响塑造而成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分化,挑战了传统的“单一劳动市场假设”,提出了“劳动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拒绝了那种把分割劳动市场的因素视作外生变量的见解,[4]主张对工人进行“三重劳动市场分析”来取代以往的“两重劳动市场分析”。[5]9这三人合作研究的最终成果,以1982年出版的《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为标志,这本书的一个理论目的就在于回应主流经济学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给出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鲜明特点在于忽视社会整体利益,忽略工人的存在。这三个学者认为,工人阶级对于经济调整的方向和有效性而言是最为重要的群体,是不应该被忽略掉的。工会力量为什么会被弱化,美国工人为什么没能组建劳工主导的政党?要理解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的分化,必须追溯工人营生所凭借的职业和劳动市场所具有的结构上的本质差别,即必须追溯劳动分割的特点和影响。三人通过分析美国劳动管理结构和劳动市场制度变迁的历史动态,根据美国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三次经济危机,认为危机的化解在于工作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work)和劳动市场结构的三次重大结构性变革,具体为:最初的无产阶级化(1820年代—1890年代)、同质化(1870年代—二战爆发)以及分割阶段(1920年代—现在)。[5]2-3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确定,在于化解经济危机、重新开启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制度结构的出现,这里充分体现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是继戈登1978、1980年两篇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文章之后对该理论的系统运用和发展。① 第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经济危机的爆发通常会促进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创新。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讲,美国197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推动了理论界对“长经济周期”(长波)的研究。②戈登认为,各种围绕长周期的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逻辑一贯的理论基础,致使很多问题悬而未决。③为此,戈登尝试借鉴、修改已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④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的阶段理论”来给长经济周期构建理论基础,其特点在于协调了“塑造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和矛盾”与“通过长周期进行自我展示的纯粹经济动态”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7]94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依次呈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系列阶段。[7]108可以说,戈登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构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开启了他的重要学术篇章。 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来讲,这场经济危机及其严重程度,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外部冲击(例如: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因素)所造成;但是,主流经济学为里根政府开具了各种挽救美国经济的药方,其本质则是根植于“零和”(zero-sum)思维逻辑以及“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思想,里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拥抱资本和富人、弱化劳动和工会组织的政策主张,其结果是强化了美国私人公司的利益,打压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在上述背景下,戈登邀请鲍尔斯(Samuel Bowles)、威斯考普夫(Thomas E.Weisskopf)共同合作:一是,借助“公司权力费用模型”(costs of corporate power model)剖析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这源自二战后美国公司制度以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僵硬的、等级化的私人特权结构,这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负担”,⑤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堪重负;[8]6二是,寻求一种能够替代主流经济学,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消除经济浪费、更好地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民主经济学”(democratic economics),进而提出经济复兴的民主纲领来推动制度转型。[8]5,11,14这三人十多年的合作沿着上述方向,并对诸如:停滞动态、生产率增长放缓、决定盈利能力和投资的因素展开了深入地分析。这些共同努力,集中表现在两本合著的出版:《超越荒原:经济衰退的民主替代》(1983),[8]以及《荒原之后:2000年的民主经济学》(1990)。[9] 第三,SSM模型与“官僚负担”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非正统宏观经济学(heterodox macroeconomics)呈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所提供的多种观点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戈登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非正统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优劣比较。由于这些模型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在他看来将它们进行一个新的综合并纳入到社会结构主义框架之中是可行的,戈登将其命名为“社会结构主义宏观计量经济”(Social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etric,简称SSM)模型。戈登此项研究计划分为两步,先把SSM模型与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卡莱茨基主义派生模型(Kaleckian variant)进行比对,然后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发起挑战。戈登认为这项工作充满希望,但也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完成。[7]400SSM模型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它试图综合凯恩斯主义对需求决定的重视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冲突的强调,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兼有两者的基本特征;二是,该模型高度重视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和调节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因为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积累和增长的逻辑和动态的不同,是由制度结构或体制来限定的。[7]364 除了上述SSM模型构建,戈登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针对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观点——是美国公司的“官僚负担”造成了工人的“工资挤压”。在他去世的那个月,出版了《臃肿与卑劣:对美国工人的公司压榨和管理“精简”的神话》(1996)。[10]国内学者在评介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没有足够重视戈登本人的著作,特别是他后期的理论研究。⑥为此,本文余下内容将详细阐述戈登《臃肿与卑劣》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并没有真正分享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及其家庭正在遭受工资挤压及其后果,戈登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众多美国公司延续了膨胀臃肿、头重脚轻的官僚结构,并以错误的方式对待工人。美国公司在劳动管理过程中所采用的“大棒策略”(Stick Strategy)是“公司膨胀”(corporate bloat)和“工资下降”两个问题的共同基础,戈登把二者界定为“官僚负担”(bureaucratic burden)和“工资挤压”(wage squeeze),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10]4学术界对工资挤压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官僚负担的研究则是戈登的独特贡献。 (一)工资挤压。自大萧条以来,美国劳工统计局曾定期发布用以衡量美国工人平均生活标准的“可支配收入”(spendable earnings)数据——工人每周的税后净薪,通过这一数据可以考察工人的有效购买力。但是,里根时代的劳工统计局在1981年终止了这一工作,转而用服务公司利益的“就业成本指数”(employment cost indices)来替代,只要公司们打个电话就可查阅行业的用工成本及其变动情况。[10]17-18⑦为化解没有官方数据支持的困境,戈登曾与鲍尔斯、威斯考普夫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指数——“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real spendable hourly earnings)——来分析工人收入的变动情况。[10]18[8]24-25。该指数衡量了“生产和非监管”(production and nonsupervisory)工人的平均税后净薪的实际价值,这些人员构成了1994年美国总就业规模的82%,这个群体主要依赖于薪资收入,其成员包括:体力劳动者、机工、书记员、程序员以及教师。由于自1980年代以来高级管理人员(其规模约占总就业的20%)报酬的激增,为避免数据的扭曲,这个群体被排除在上述指数的测度之外,戈登借用劳工统计局“生产和非监管”类别的数据作为分析“生产工人”(production workers)的数据依据,其余的类别统称为“监管人员”(supervisory employees)。⑧ 据此,戈登给出了在私人非农部门中,生产和非监管人员(即“生产工人”)的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的历史纵向变动情况(1948-1994年,以1994年美元计算):⑨该数值从1948年(约6.4美元)至1972年(约10.6美元)总体显著上升并达到峰值,之后伴随短暂周期性波动,该数值显著加速下滑至1994年的约9.4美元。从年均变化率来看:1948-1966年,年均增长2.1%;1966-1973年,年均增长下降为1.4%;1973-1989年,年均负增长接近1%;1989-1994年,年均负增长0.6%。其中,1994年的数值比1972年峰值降低了10.4%,并低于1967年的水平。戈登认为,与其把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的工资下降趋势称作“工资挤压”,不如称作“工资崩溃”更为贴切。[10]19-20 从横向视角来讲,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戈登分析了12个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中所有就业人员的实际小时报酬(real hourly compensation)年均变化率(1973-1993):⑩美国制造业所有员工的实际小时报酬是12个发达经济体中增长最少的,年均增长0.3%,由于该类员工包括了“非生产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s),进而没有表现为负增长;其余11个国家作为整体年均增长2.1%,其中德国3.1%,日本2.2%。[10]26-28 和大多数围绕工资挤压的研究略有不同,戈登强调了遭受工资挤压的人群是广泛的:不仅仅局限于低技能工人,而是包括了广大工人阶级;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底层民众,而是包括了广大中产阶级。从美国社会总体来看工资挤压的波及幅度,它呈现出大众化的显著倾向。[10]23依据家庭调查数据,戈登给出了在私人非农部门中,根据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进行群组划分的劳动人口(work force)的实际小时收入(real hourly earnings)变动情况比较(1979-1993,以1993年美元计算):总体来看,处于底层80%的劳动人口降低了3.4%至1993年的8.59美元,处于顶层20%的劳动人口提高了10.04%至1993年的24.66美元,后者为前者的三倍左右;处于底层80%的白人工人降低2.9%,黑人工人降低3.6%,西班牙裔工人降低7.9%;处于底层80%的男性工人降低9.0%,女性工人提高2.8%;高中辍学的工人降低20.6%,高中毕业的工人降低9.5%,接受一定高等教育的工人降低15.9%,大学毕业生提高3.5%,研究生提高8.8%。[10]23-25 总之,工资挤压对美国工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不仅工人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直接遭受侵蚀,其影响终将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并影响其结构的稳定性,所谓“美国梦”正日渐消散。 (二)官僚负担。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美国私人公司出现的种种管理问题,特别是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但把症结明确归结为美国公司日益膨胀的、头重脚轻的管理和监督的官僚机构,并揭穿“管理精简”的神话,(11)却是戈登的学术贡献。戈登把美国公司管理和监督人员机构的巨大规模和费用界定为“官僚负担”,它是美国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10]33 要对美国官僚负担进行量的考察,面临的首要难题仍然是对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能人员规模的确定,戈登把美国官方两种数据(商业机构调查数据和劳工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与埃里克·俄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所提供的“阶级结构调查数据”(截止到1991年)进行了比对,(12)进而提出把官方数据作为对美国官僚负担规模进行测算的最小估计是可靠的。[10]37-39 从纵向视角来讲,戈登以监管人员就业规模占私人非农部门总就业规模的比重变动情况来衡量美国官僚负担的历史演变(1948-1994):1948年,监管人员只有470万,占私人非农总就业比重12%;1994年,监管人员1700多万人,占比高于18%;整个1980年代,占比均值达到19%。美国官僚负担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8-1973):此阶段给现代美国公司管理结构提供了基础,可细分为官僚负担快速上升期(1948-1966)和放缓期(1966-1973)两个时期,官僚负担在前一时期年均增长1.8%,在后一时期年均增长0.4%。[10]47-49与此同时,美国公司的新管理结构——自上而下的、头重脚轻的公司权力控制结构——在前一时期出现并迅速成长,在后一时期开始稳定发挥其职能;尽管工人被排除在投资和生产的决策过程之外,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经济繁荣的好处(此阶段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上涨的),进而默认了这种新的控制结构。第二阶段(1973-1989):此阶段亦可细分为较快增长期(1973-1979)和放缓期(1979-1989)两个时期,官僚负担在前一时期年均增长1.0%,在后一时期年均增长0.4%。[10]49第二阶段,恰恰是制造业中“非生产工人”规模快速扩张的时期,此类人员占制造业就业规模比重几乎增长了25%。[10]49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资挤压”和“官僚负担”两个方面交相互动,美国公司对待工人日益采取强硬立场,雇佣更多“监管军团”来“挥舞大棒”。 为了进行横向国际比较,戈登借助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所提供的“行政与管理”(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职业类别的国际数据,并与美国劳工统计局家庭调查的“管理人员”数据进行比对,(13)以“行政与管理”类就业规模占非农部门总就业的比重,来刻画官僚负担的具体程度,9个发达经济体的官僚负担情况如下(1989年):(14)美国的官僚负担最为严重,达到13.0%(是德国或日本的三倍),意味着美国非农总就业中有13%的人员(1500万人)从事“行政与管理”类事务;加拿大官僚负担数值也高达12.9%;德国为3.9%,日本为4.2%,瑞典为2.6%;其余国家的数值在4.3%—6.8%之间。[10]42-45官僚负担数值越高的国家,其公司组织和劳动关系越具有对抗性;官僚负担数值越低的国家,其公司组织和劳动关系越具有合作性。[10]44 如果劳动管理系统依赖于等级原则,进而对车间或办公场所的一线员工进行管理和监督,没有人会被信任,所有人都需要“被盯着”,就会形成层层监管的金字塔结构,需要越来越多的监管人员,其规模和代价是巨大的:从规模来讲,美国非农就业的15%—20%是监管人员,在1994年已达1700多万人;从代价来讲,在1994年美国为监管人员支付了1.3万亿美元的薪资和福利,接近美国当年GDP的1/5,恰好等于联邦政府的收入规模。[10]4-5,36如果美国把官僚负担水平降低到德国或日本的水平,完全可以释放巨大的“公司官僚红利”(corporate bureaucratic dividend),定会极大地促进社会性生产活动。[10]46 (三)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的相互依赖。作为美国经济两大关键特征的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来源于美国公司在劳动管理和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大棒策略”。一方面,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资挤压诱发了对一线员工强化监管的需要,由于工人无法获得以往稳定的工资增长和职业安全等好处,工人努力工作的动力就会不足,公司需要强化监管或惩罚来迫使工人努力工作,大规模的“监管军团”最终挥舞起大棒来监督工人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公司官僚结构形成以后,存在自我膨胀和利益强化的内生动力,维持“监管军团”的巨额费用只能来自一线员工的报酬,进而强化工资挤压。[10]5 这里需要指出,上述官僚负担历史演变的两个阶段伴随着不同的工人实际工资表现:第一阶段中(1948-1973),官僚负担快速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上涨;第二阶段中(1973-1989),官僚负担较快上升,工人实际工资遭受挤压。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的相互依赖关系只有在第二阶段才有显著表现,在第一阶段似乎并不存在。戈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美国战后繁荣时期公司有稳定的利润、生产率上涨,实际工资上涨有充分的条件,工人分享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监管军团”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挥舞起来的不是“大棒”(Big Stick),而只是“小木棍”(Little Stick)。[10]68,70相反,1970年代后公司利润下降,它们没有进行制度结构调整,而是充分利用了二战后业已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劳动管理控制系统,“监管军团”从“预备役”转向“正规军”,而且其规模不断壮大。 二、劳动管理的两种类型及其后果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用于管理生产工人和提高工作绩效的“劳动管理系统”存在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更具“合作性”(cooperative)的劳动管理关系,包括相当程度的就业保障、正向的工资激励,通常伴随实质性的员工参与,以及强大的工会组织;另一种类型则是更具“冲突性”(conflictual)的劳动管理关系,包括程度较低的就业保障、把“解雇”作为驱使工人努力工作的手段、低工资激励,通常伴随软弱的工会组织。[10]63前一类型的经济体,依赖于“胡萝卜策略”,如德国、日本和瑞典是这种劳动管理系统的代表;后一类型的经济体,依赖于“大棒策略”,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其典型代表。前一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一种“高端道路”(high road);后一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则是一种“低端道路”(low road)。[10]144“合作型”劳动管理系统更有利于宏观经济表现,呈现出更为快速的生产率提高,更活跃的投资表现,以及在通胀、失业和贸易竞争方面,均优于“冲突型”劳动管理系统的经济体。 劳动管理系统的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僚负担。戈登通过美国的经验发现,如果工资增长和职业安全无法给工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冲突型”劳动管理系统将呈现出头重脚轻的官僚控制结构,这意味着:劳动管理系统的不同类型和公司官僚负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戈登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数——合作指数(Index of Cooperation)——来衡量劳动管理系统在“冲突型”与“合作型”之间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他再次使用“行政与管理”类别的国际数据来衡量官僚负担情况。最后发现,“合作指数”与“官僚负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官僚负担越小,合作程度越高;官僚负担越大,合作程度越低,冲突性越强。例如,美国合作指数为-3.18;瑞典合作指数为+1.85。[10]73-75 在“合作型”劳动管理系统经济体中,工人抱有实际工资稳定增长的预期,他们和企业所有者共同分享生产率快速提高带来的红利,就业安全也得以保障,这些正向激励措施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进而降低了公司监管的需要程度。与之相反,作为“冲突型”劳动管理系统典型的美国,随着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结束,这种维持“监管大军”巨额费用的旧有条件也一并丧失,公司转而把监管人员报酬持续增长的来源锁定在生产工人身上,进而出现了从“生产工人”到“监管人员”之间巨大收入转移问题。为衡量这一再分配过程,戈登给出了美国私人非农部门中的“生产工人”和“监管人员”各自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1973-1993):1973年,生产工人的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40.4%,监管人员的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16.2%;1993年,前者为34.5%,后者为24.1%;私人非农部门总报酬(生产工人与监管人员报酬合计)占国民收入比重,1973年为56.6%,1993年为58.6%,几乎没有变化。[10]81-83这意味着,处于车间和办公场所一线员工的一部分报酬,转移到了监管人员手中。戈登强调,“收入转移”是美国经济鲜为人知的秘密之一,众多经济学家善于论证要素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例如总员工报酬和利润各自占国民收入比重相对长期不变,却忽略了总员工报酬内部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三、助推美国经济制度转型的五步改革建议 工资挤压与官僚负担反映了美国公司对“大棒策略”的严重依赖,美国公司陷入“低端道路”的泥潭,不仅工人及其家庭付出巨大代价,整个美国的宏观经济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为了助推美国经济走向“高端道路”,戈登提出了围绕美国公司管理和劳动关系转型的五步改革建议。 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1994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是4.25美元一小时,制造业生产工人平均工资是12.06美元一小时,占比为35%;然而,这一比值在美国战后经济繁荣时期为45%—50%。戈登建议,分若干步骤把最低工资由4.25美元一小时,提高到2000年的6.50美元一小时(以1994年美元计算)。其基本原则是,联邦最低工资应该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相绑定,进而保证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在未来不会遭受损失。[10]241 第二,提高工人的话语权。通过立法改革,增强工人获得工作场所有效代表权的能力,进而提高工人的话语权。一是,清除工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建议授权工会代表权的自动认证,凭借55%以上工会成员签名即可自动获得工会代表权,这样可以提高选举工会代表的效率。二是,扩大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的辐射范围,把处于中低职级水平的管理人员也纳入到该法案的管辖之中,他们也可以参加工会组织,进而给美国公司头重脚轻的官僚结构施加压力。三是,授权那些25个员工以上的工作场所组建“员工参与委员会”(employee participation councils),这类委员会有权对那些影响工作场所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各项决策进行管理,目的在于扩大工人的参与权和话语权。[10]245在戈登看来,有效的“员工参与委员会”和强大的工会,会有利于推动美国公司迈向“高端道路”。 第三,要弹性就业,不要“一次性”就业。美国出现的各种弹性就业形式,有演变为“一次性”(disposable)就业的不良态势,从而丧失了弹性就业的固有好处。[10]246要扭转这种局面,可以通过改变医疗保险和工资税等制度,消除“正式就业”和“临时就业”之间的差别,让企业放心用工。建议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一是,禁止强制性加班;二是,把补休时间作为自愿加班的替代性补偿,扩大工人对工作时间安排的灵活性;三是,扩大该法案对薪资员工工作时间的调节范围;四是,经过一段过渡时间,把所有薪资员工的三周假期普遍提高到四周假期。[10]247 第四,激励企业向“合作型”转变。美国公司在由依赖“大棒策略”向“胡萝卜策略”的转型过程中,也需要激励和帮助,戈登建议组建“国家合作性投资银行”(National Cooperative Investment Bank),用于给那些更多采用合作化和民主化组织结构的企业提供投资信用以及补贴。[10]248 第五,“合作型”经济发展需要培训和辅助。美国公司的管理者和工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往的劳动管理系统类型和结构,他们也需要被教会如何迈向“高端道路”,改掉这些旧有的习惯是需要代价的。戈登建议组建“国家合作性培训辅助机构”(National Cooperative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Agency),来帮助工人和管理人员获得适应合作型劳动关系的习惯和能力。[10]249 四、对罗斯多尔斯基“呐喊”的回应 罗斯多尔斯基在1967年9月(他去世前一个月)提交给“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法兰克福讨论会”的论文——《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中强烈呼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极其丰富的方法,只有借助马克思的方法论才能够发现连接《资本论》中的抽象理论和当代具体现实的那些“过渡环节”。否则,将会陷入一种不幸的境地,它类似于十九世纪正统李嘉图主义者的困境。那些理论家们试图把李嘉图的抽象教义,这些内容缺乏任何“中介环节”,直接运用到直观世界的表象。其结果,他们或者武断地把经济现象直接归结到抽象原理之下,或者直接拒绝经济现象的存在。[12]也就是说,必须构筑“中间层次”的范畴体系,来连接抽象原理和处在不断变迁中的现实经济矛盾。 与均衡经济学所提供的美好图景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由不同寻常的周期性危机所打断;与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期望也相反,资本主义并没有直接陷入永久性的萧条或停滞状态。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相对活跃的稳定增长和持续积累。SSA理论尝试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停滞的“显著性长周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周期”相联系。[13]1在一定意义上,由戈登所创建的SSA学派恰恰提供了“中间层次”的分析,这种分析比那种针对资本主义历史细节的分析要一般和抽象,但比资本主义抽象理论分析要明确和具体。“中间层次”的研究,相比抽象理论更容易接受实证检验,相比具体的历史研究则更容易进行推论。[14]如果把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抽象层次的概念组合,SSA学派所提供的“资本积累—积累的社会结构”则是该概念组合的具体化,构成了中间层次的基本概念组合。 ①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在介绍SSA学派的时候有的误以为戈登在1982年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当然,也有学者进行了准确介绍。[6]实际上戈登本人在1987年《权力、积累和危机: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兴衰》文章中,明确指出自己最初是在1978年《长期坐过山车般的上升与下降》(David M.Gordon.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In,U.S.Capitalism in Crisis,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ed.).New York: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pp.22-35.)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在1980年《积累阶段与长经济周期》(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In,Processes of the World-System,T.Hopkins and I.Wallerstein(ed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0,9-45.)中对其进一步发展和运用,接着才是1982年《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的出版。[7]280 ②戈登主张采用“长经济周期”(long economic cycles)概念,来描述那种可以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收缩的周期交替现象,这相当于持续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s)或曰“长波”(long waves);他同时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持续15至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与“长周期”(long cycle)的混淆。[7]119 ③戈登给出了在长周期研究中四个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是,长周期为何能够重复发生;二是,为何它持续50年左右的时间;三是,是什么因素决定它的振幅;四是,一个周期中造成经济停滞的原因,与下一个周期中刺激复苏和新积累的创新或事件之间是什么关系。[7]94 ④戈登高度评价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宇野弘藏(Kozo Uno)的“阶段理论”和“三层次”分析方法;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指出宇野对不同发展阶段能够衔接的原因并未给予分析。[7]120 ⑤需要指出,这里的“浪费负担”(waste burden)提法,与他在《臃肿与卑劣》中的“官僚负担”(bureaucratic burden)提法具有直接的联系。 ⑥当然,也有学者谈及戈登的最后著作,并译作《富有而吝啬》。[11] ⑦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率m’=(m/v),而利润率p’=(m/C),分母的变化是有政治含义的,立场不同,结论当然不同。同样道理,戈登所讲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变换亦如此。 ⑧戈登对“工资挤压”和“官僚负担”进行定量分析时,把私人非农部门从业人员进行了“两分法”划分:把“生产和非监管人员”统称为“生产工人”,把“非生产和监管人员”统称为“监管人员”。[10]19,35 ⑨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生产工人的小时薪资收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费)的平均。[10]19 ⑩“实际小时报酬”包括薪资和福利两个部分,只扣除通胀因素,并不进行税费扣除;“实际小时收入”,只是进行通胀因素扣除;“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则不仅扣除通胀因素,而且进行税费扣除。 (11)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开始流行“管理精简”的说法。戈登指出,“管理人员”占私人非农总就业比重,从1989年的12.6%增加到1995年2季度的13.6%,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精简。[10]52-53 (12)赖特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2012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13)戈登所统称的“监管人员”是由“管理人员”(managers)和“监督人员”(supervisors)两个部分构成,这里的国际比较只是针对“管理人员”。[10]43 (14)戈登打算测算12个发达国家的官僚负担,但英国、意大利和法国1989年相关数据欠缺。[10]43标签:劳动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戈登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模型公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