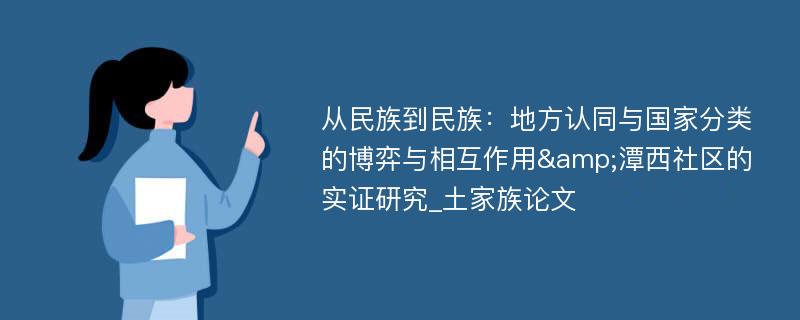
从族群到民族:地方认同与国家分类的博弈与互惠——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互惠论文,民族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10)06-0038-05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各级民族工作者和民族研究者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伟大创举,也是迄今为止民族学在中国最重要的应用,具有突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与强调。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反思,其中既有切中肯綮的独到之见,也不乏罔顾历史、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泛批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对个案的实证研究作出回应,通过分析潭溪土家族民族识别的历程,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族群”和“民族”的关系。
一、土、苗、客:地方性的族群分类
本文田野调查点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潭溪镇。潭溪镇是目前土家语南部方言唯一的保留区,也是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最集中的聚居区之一。在潭溪地区,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以前的三大族群土、苗、客,或土家、苗家、客家,先后成为祖国民族大家族中正式的成员,即土家族、苗族、汉族。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本地的实行,潭溪地区的族群格局和族群认同也发生了变迁。
按照我国的民族分类体系,目前潭溪地区的主体民族包括土家族、苗族和汉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识别的结果。事实上,民众更习惯于沿用另外一种地方性的族群分类体系,即土家、苗家、客家,或土、苗、客,至今犹然。
自明代以来,与土家族地区相关的文献中大量出现土、苗、客并举的记载,表明土家族地区三大主体族群之间的族群边界已基本确立,各自的身份认同也基本形成。较早的如明代嘉靖年间《思南府志》记曰“腹里边方,风俗各异……苗僚土客,人民各异。”[1]33清代乾隆时,湘西永顺、保靖、龙山三县岁科两考,童生“俱已遵照填明土、客、苗三籍”[2]。光绪《古丈坪厅志》在记述古丈坪民族状况时,专门分为土族、客族、苗族[3]卷九·民族上。综合文献记载,苗与土、客的区别主要在风俗民性上,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如“苗民犷猂轻生,服食起居与内地齐民迵殊。其间若永顺之土蛮、泸溪之犵狫,似苗非苗,种类既分,风俗亦异……涵濡礼教非卉服鸟语者可比矣。”[4]而土客之间则尽管亦有文化上的区别,但似乎融合较早、程度较深,故文献中区别土、客多以籍贯、先来后到甚至职业为依据。李星星先生罗列了文献材料中对土、客的解释,土家大概指“前代土著”、“前朝(明)入籍者为土”、“旧土司治者曰土籍”、“土家者土司之裔”等等。客家所指包括“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也。”“本朝(清)入籍者为客”、“自外县迁移来者曰客籍”、“外来民人附居落籍者为客家”等等[5]43-44。
研究者一般认为,土家族地区的“客家”即汉族,但传统上,土家族地区的汉族又可分为“民”和“客”,两者的区别在于入籍与否,如方志所记:“民籍中又有一种客民,多江西之商贩斯土及辰、永一带为工杂技于此者,或年久仍未入籍。”[3]卷十·民族下这种区别至今还有影响,笔者在湘西地区调查时得知,地方上一般对附近乡镇上的汉族习称为“客家”,而认为城市里面或外来的汉族不是客家,这显然是与客家过去未曾入籍、散布乡里的状况有关。苗族以前被分为“生苗”、“熟苗”,两者的区别在于汉化的程度、是否顺从官府的抚绥;自明代苗疆设边墙以来,更以其内外区别熟苗、生苗,如方志记曰:“苗疆边墙……以外者为生苗,在内者与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纳赋当差,与内地民人无异,则为熟苗。”[3]卷九·民族上潭溪土家族现在仍把相邻丹青、排吼的苗族称为熟苗,认为他们语言易懂,习俗相近;而把远处吉首、凤凰等地苗族一概指称为生苗,尽管与他们并无实际往来,但仍认为他们语言生拗,风俗怪诞①。这应该也是受传统的影响。
目前,潭溪土家族仍主要以土家自称,而以苗家、客家分指苗族和汉族。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差异,即讲土话的是土家,讲苗话的是苗家,讲客话的是客家。但是,现在潭溪地区大多数的民众以汉语为交际语言,因而使“闻声知族”的办法很难奏效,如一位报道人所言:
现在都搞乱了,都讲起客话了,特别是那些从学堂出来的学生,到广东打工转来的年轻人,一势客话,还讲个么事普通话,你哪里分得清他是个什么族?政府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自己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宁卖祖先田,不卖祖先言”,老人讲的,现在也顾不得了。(报道者,铺锄村人,男,土家族,1940年出生,文盲)②
现在民众多根据姓氏、村寨来区分族群,因为传统上不同姓氏、不同村寨的人讲的“话”是不同的,比如向、覃二姓是讲土话最多的,陈姓则是讲苗话最多的,李、刘等地方上的杂姓则一般讲客话。以村寨分,则峒河两岸的以讲土话居多,后山上、“溪里面”的以讲苗话为众,而墟场上做生意的则主要是讲客话。在调查中,报道者常常由姓氏、居住地来确定某人的族群身份,甚至包括自己的母亲、祖母等人的族群身份。
二、土家族、苗族、汉族:“民族”身份的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苗族是首批被确认的民族之一,“苗”也成为泸溪县第一个获得合法“民族”身份的土著族群。但由于少数族群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不愿或不敢报出自己的“民族”身份。泸溪也是如此,“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泸溪境内只有苗族9320人,仅占当时总人口的7.4%”③。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加大了民族工作的力度。1951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了“湘西苗族慰问团”来泸溪访问,深入苗区调查、采访,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赠发《告湘西各兄弟民族同胞书》,对一些苗族困难户进行了救济,使苗族群众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意识也日益高涨。随着湘西地区苗族识别工作的深入开展,苗族的数量不断上升,区域自治的要求也逐渐高涨。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泸溪县也从沅陵专区划出,划归湘西苗族自治区管辖④。
泸溪县土家族的确认虽然晚于苗族,但在苗族确认之后,土家人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在某些场合视同少数民族对待,如“1952年10月,泸溪县召开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评选出一等劳模5人,其中有2人是少数民族,即说土家话农民向文产、苗族妇女杨玉翠。”[6]512
随着“湘西苗族自治区”的成立,苗族——这个在本地区一直处于劣势的族群——却逐渐取得了在社会上尤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加之国家给予苗族的种种优惠政策,这些都刺激了世代与苗族比邻而居、既共存又竞争的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如一位大陂流土家老人讲到:
解放前我们这里不分族,看你讲什么话,土话啦,苗话啦。解放后才有民族,苗族还是先承认的,他们抢了先。我们起先没觉得,想,总不是做田吃饭,要那个“族”干什么?后来不行,成立了自治区,把我们划归苗族人管,他们还有优待,少完粮啦,多发布票啦,代表多啦。我们就也坐不住了,土家、苗家,从来都坐(方言,有“居住”之意)一起的,就是话不同,讲“少数民族”,我们人还少些。我们就向区里反映。(报道者,大陂流村人,男,土家族,1924年出生,文盲)
潘光旦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土家族地区调查时也注意到类似的现象:“1952年与(苗族)自治州成立的同时,还有一件富有刺激性的事:‘土家’人也曾暂时被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看待,减免过一次农业税。但只此一次,1953年至今,便没有再减免,原因是他们的民族成分还没有确定下来。……1952年,为了减免,政府曾要求他们填‘土家’,1953年及以后,凡遇登记或填表,在有的县区级政府,却又教他们不要填‘土家’,而改填‘汉人’!这更是具体加强刺激的一个因素”[7]536-537。
当时,“土家”人中流传着这样两首民歌,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想法:“苗族土家一家人,犹如同胞同奶生。过去走的排排路,土家成了掉队人。”“民族团结是一家,客家土家分明它。客家土家分明了,土家人民好当家。”[7]534
1956年下半年,由中央、中南区和湖南省有关专家、负责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湘西地区调查土家族的民族识别与确认问题,但调查组的结论并不利于土家人的民族识别:“土家成为一个民族,除语言确实不同外,其他条件似尚难据以肯定。”[8]24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土家汉化程度很深,除语言还有一定的保留外,其他如服饰、习俗、经济生活等均与汉族差别不大,在当时“民族识别”以文化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情况下,便显得条件不充分了。二是解放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本着“解放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指导思想的,这也是与1949年以后中国持续高涨的革命意识形态相一致。然而,土家族在其聚居区内一直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诚如调查组的工作报告所言:“土家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它不是作为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而存在。”[8]3不仅是作为外来者的调查人员,即便是本地土家人中的代表也有否定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例子,“(土家)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如宣传部田大礼同志(土家)说:‘我们不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汉族一样,是汉族。’”[9]
在这种背景之下,潭溪土家人争取“民族”身份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较大的作用。一位是当时的一名南下干部。一位报道人回忆说:
刚解放不久,成立了农协会,主任是县上派下来的,姓皮,名字记不到了,是南下干部,每顿都要吃馒头的,好像是陕西还是河北的,记不清了。有一回,我们为什么事争起来了,她赶来解交(“调解”之意),她听不懂我们的话,别人说我们在打土话。她就说,那你们这个话是少数民族的,要减公粮。这不做了一件好事?刚刚搞了半年,她一走,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新来的干部就不给我们减了。(报道者,婆落寨村人,男,土家族,1929年出生,文盲)
这位仍留在民众记忆中的姓皮的干部所做的“好事”,必定极大地刺激了地方上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另一位是当地的土家精英,一位当事者回忆到:
苗族承认了,我们也要求,不光我们这里,自治州别处地方,龙山啦,永顺啦,那里也有土家,也要求承认。我们就向区里反映,当时区里干部苗子多,区长姓符,符家坪的,对我们的事不是那么热心,我们是土家嘛,讲的话都没同。我们就到县里头去,我们也有人,找向仁贤县长,是我们大陂流人,论辈分还是我孙子。仁贤就了解情况,向县里头、州里头打报告,就把我们承认了。(报道者,大陂流村人,男,土家族,1924年出生,文盲)
这位老人所说的向仁贤,已故,是大陂流寨上人,现在其房屋还在,还有后人在大陂流。向仁贤1920年出生,读过私塾,解放前以务农为生,他身材高大,办事果断,能主持公道,又粗知文字,在地方上较有威望。潭溪解放后,他即担任地方上农会的负责人,并在剿匪斗争中有过很好的表现,1950年即进入县政府工作,1954年被任命为副县长,至今仍是峒河两岸土家人中出过的“最大的官”,常为一些中老年人提起。现在已无法弄清楚向仁贤在潭溪土家族民族确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可以想见的是,向仁贤作为一位从土家聚居区出来的地方领导人,又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机关工作,他对于土家人取得“民族”身份的意义,无论是从土家族群还是他个人的立场上,应该有超出一般民众的认识。1957年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在此之前,地方上即已获悉这个消息,并采取了相应举措:“(泸溪)县印发《喜报》和《祝贺信》。县委书记常克良、副县长向仁贤(土家族)率领10名干部,随省、州人民政府委派以龙再宇副州长为首的慰问团,深入土家族聚居的潭溪、下都、土麻寨、大陂流、且已等地访问。”[6]517
三、恢复与更改民族成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贯彻落实了中央《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为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尊重一切少数民族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的自由”,对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情况,提出了几条操作性较强的原则[10]。总的看来,这几条原则强调了两点: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要求;突出了民族身份通过血缘的代际传承性。这与建国初期“民族识别”时强调民族的文化特征和集体性显然有较大不同。由于此后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要求更改或恢复为土家族的情况,国家民委于1982年4月邀集了四省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要求恢复土家族成分问题的会议,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纪要》,即国家民委(82)民政字第240号文件。《纪要》要求,在恢复部分群众土家族成分时,要注意两点:(1)申报恢复土家族成分者,须有一定的文化特征,如土家语、过赶年、跳摆手舞等;本人具有民族意识,要求恢复土家族成分。(2)土家族同其他民族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成分,可随父系或母系而定,但追溯血缘关系不能过久,最远以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限[11]。
泸溪县民族成分的更改与恢复工作也基本上是按照相关政策、规定进行的。2005年7月12日,笔者在泸溪县民宗局查阅资料时,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在80年代民族恢复过程中,我们县主要是依据他们的语言、来龙去脉、姓氏、风俗习惯。以前“两棉赊销”,实际上是物资扶贫,不是少数民族的不能享受,这样更改民族成分的就很多,80年代以前更改族别的很少。(报道者,泸溪县民宗局干部,男,汉族)
从这位民族工作者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利益驱动是当地群众要求更改或恢复民族成分的主要动力。在潭溪地区,几乎所有此前登记为汉族的人都逐渐设法改成了土家族或苗族成分,如一位地方干部所言:
今天我们潭溪没有汉族了,因为民族可以随父、随母,对少数民族有些照顾,像娃儿升学考试,少数民族可以优惠10分;计划生育,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两胎。通过前几年搞户口整理都成了少数民族。(报道者,潭溪镇政府干部,男,土家族,1955年出生,高中文化)
唐胡浩对鄂西来凤土家族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近的案例,据统计,来凤县每年约有600人要求更改民族成分,其中95%以上是在校学生,无一例外都是考虑到高考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加20分的优待政策。来凤土家族的民族认同主要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资源[12]。
由于相关政策过于宽松,使得具体的民族成分认定工作缺乏规范,极具操作性,如菅志翔所言:“国家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为人们根据既存族群关系的格局和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需要进行群体重塑,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操作空间。”[13]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更改为少数民族,使得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急剧增加⑤,以致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国家民委1986年发文指出:“近期,有些地区又有部分人要求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其中有的有正当理由,而有的民族特征已消失,却不恰当地追踪溯源,以谱牒、姓氏等为依据,要求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更改民族成分。出现的这些倾向和错误做法,不利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影响民族团结。”[14]
四、讨论与结论
以上简要回顾了潭溪土家族“民族”身份确认的历程,下面结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对其特点以及我国“族群”和“民族”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国外研究中国族群的学者以及多数国内研究者,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我国目前的“民族”体系是1949年以后在前苏联“民族”管理体制的影响下、由政府组织行政和学术力量自上而下对我国人群分类体系的一种建构。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郝瑞先生(Steven Harrell)认为:“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15]268他还以彝族为例指出:“彝族这一范畴不是由彝族人自己创造的,而是由管理他们,与他们争斗又与他们往来的汉族人创造的,是由中国和西方研究他们的学者们创造的。”[15]59又如台湾学者谢世忠认为:“中共统治下的非汉族群,除极少数未被识别属于何族的人之外,每一个成员都被安排进某一官定的族类范畴之内,这个属性是不能怀疑或改变的,而一个人属于哪一族的最后决定权,则在拥有‘科学’证据的专家干部手中,当事者本身往往是被动的。”[16]就土家族而言,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甚至认为,土家族“与汉族已经非常接近”,“它被界定为一种少数民族,就是把区别重新界定了一下。”[17]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突出强调我国民族识别的建构性,认为民族身份是由政府主导划定并强加于民众的。
对潭溪土家族民族确认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1949年以后在政府主导下确立的“民族”分类与地方性的族群分类并非是截然分开、彼此对立的,民族身份也并非全然是由政府划定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的“民族”分类是地方性的族群分类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潭溪地区历来就存在土、客、苗的人群分类范畴,1949年以后的“民族”分类正是基于此之上形成的。所以,在潭溪民众中,人们都能自然地把如今的“土家族、汉族、苗族”与过去的“土家、客家、苗家”对应起来,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或权利关系的共谋。第二,“民族”认同已经内化为民众的主位知识。经过半个多世纪“民族”认同的实践,潭溪土家人已很自然地以“土家族”作为自己的族群身份,表明原本处于客位的“民族”分类已经成为民众的主位认同,或者说国家的“民族”分类取代了地方性的族群分类;而且,这个“取代”的过程是在国家政策因势利导之下平稳实现的,并非国家强制性的划定。第三,“民族”认同并非完全是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也对之有着重要的影响。1949年以后,面对国家的“民族”分类规则,潭溪土家人没有单纯地听之任之或加以抗拒,而是审时度势,根据周围族群关系的变化,积极地作出响应。因而,从国家立场来看,推行“民族”体制的确是出于治理的需要。从民众立场来看,接受“民族”认同则体现了他们在变动着的社会情景中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在潭溪土家族的民族确认过程中,除了国家力量的关键作用之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族群自身的能动作用,比如族群精英的影响与运作,族群对文化的采借与创造以适应新的“民族格局”等。
当然,国家语境中的“民族”和地方语境中的“族群”还是有着相当的差异,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前者以制度性的分类取代了后者文化性的区分,使民间流动、开放的族群边界被官方固化、封闭的“民族”身份所取代。在潭溪地区,族群身份的传承在以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濡化来实现,族群身份的转换也主要是基于族群文化同化之上的。而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身份的获得主要是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制约,只要是政策能够确认或无法否认的,个体就能争取到相应的“民族”身份,使得潭溪土家人在族群文化迅速消失的同时,“土家族”规模却在急剧扩张。民族身份之上的利益成为民族认同主要的凝聚点,民族身份的工具性彰显无遗,也造成了我国民族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在此,我们透过潭溪土家族民族确认历程所观察到的地方性的族群认同与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分类之间的关系并非彼此冲突与新旧交替,而是彼此之间的博弈和互惠。
收稿日期:2010-04-28
注释:
① 对于潭溪土家族的这种族群偏见,笔者有专文探讨,见陈心林《族群偏见与消极认同——以潭溪社区为例》,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6).
② 本文引用的报道材料直接引自调查时的录音,只加上必要的连缀,使意思基本畅通。本文遵循人类学的惯例隐去了报道人的姓名,只列出年龄、文化程度等背景资料;但文中的地名均是真实的,以方便后续的研究。
③ 泸溪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泸溪民族志(审定稿)》,2000年,第334页。
④ 泸溪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泸溪民族志(审定稿)》,2000年第334页。
⑤ 就以土家族而言,其人口从1964年的52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802万,36年间增加了约14倍,显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