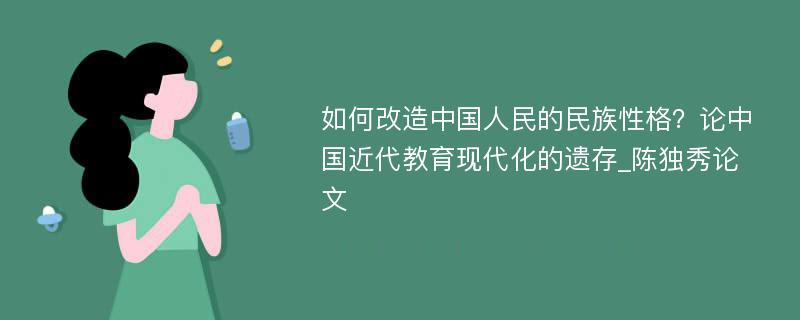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遗存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教育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10-0119-09 一、近代中国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 自1840年始,近代中国除了到处弥漫着“抵御外侮”、“救国救民”和“革命”这一时代的民族与国家主义主旋律,还面对着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在传统中国曾经是很清楚的问题(“学做圣贤”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近代中国则是一片混乱。 1.变化着的生活秩序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导致民众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人生观、秩序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瓦解的困境,同时又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一位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① 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清朝统治的长辫子,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变。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自近代传入,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人生礼俗发生变化。例如,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行“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等,表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 新社交礼仪渐趋流行。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消解。 2.对西方新文明的崇拜 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字构成了一连串新词汇的组合,借此来界定新文明。“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②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对新文明的崇拜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类新特征:第一是“新秩序”,用“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新学”等;第二是“新时代”,“时代”与“新时代”这两个新概念的流行,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三是“新文明”,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③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崇拜西洋文明、西方文化的思想性标志。 3.安身立命的意义危机 社会大动荡既引发了秩序瓦解的社会危机,也导致了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意义危机。意义危机首先发轫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④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尤其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中,很多读书人投身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是“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⑤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价值取向变得无所适从,对人生意义迷茫造成的。 4.“迷乱之人心”与自杀行为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是“迷乱之人心”。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不知廉耻、不顾他人死活地赚取不义之财;有人茫然失措,形成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致“自杀”或“出家”在民国前后成了一个突出的、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⑥ 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⑦ 对这些社会失范现象,当时的人们作出过解释。例如,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说:“念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而下”⑧。梁漱溟在解释很多人为什么走上出世之路时说:“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⑨陈独秀在分析厌世自杀的精神原因时指出:“以前的信仰都失了威权”、“青年的理想受到社会的压迫”、“佛教‘空观说’的危害”等因素,故而尤其倡导揭示“人生真相”的新教育方针。⑩ 5.崇拜美国新生活的风气渐成 五四前后,社会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股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崇洋风气。学习英语成为时尚。在大学联考中,英语的比重最大,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原文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学,有90%的教材是用英语编撰的(不包括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有英文演讲社,《北京大学学生日刊》经常有英文作文比赛的报道,社会上自然也以英文水平为判断教师的标准。(11)1919年11月10日,一位赴美留学的黄森生在致书尚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友人信中说:“新舞台、新思想、新生活,恐怕除了美国以外再难他求了”。他说:“美国是我唯一的亲友,唯一的兄弟园,唯一的自由的、博大的、大同的国家,凡学术技艺,不问国界都可以供他人研究”。(12) 6.老走运的孔圣人不再走运 中国长期以来傲视邻国,向有自大心理,如此崇洋风气,刺激了大国之民的自尊心,反弹的力量十分强烈,以传统权威抗衡崇洋风气的莫过于抬出孔子。这便是陈独秀所谓的“孔圣人为什么老走运”的道理。1912年孔教会在上海成立,翌年创办了《孔教会杂志》,提倡孔教为国教。1913-1915年间,许多省份都有孔教会与帝制运动的团体。袁世凯去世后,康有为向新任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上书,要求以宪法确定孔教为国教。他说:“如果不读孔子的经典,人们就不懂得立身处世”,“无孔教,即无中国”。(13)“今将欲救四万万之民,大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今尽灭之,而还其旧”。(14)有人甚至指斥崇洋风气“直与猩红热、梅毒等输入无疑!”(15)1918年9月30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校长布告”:“10月1日即旧历8月27日为孔子诞期,本校照章放假一日,此布。”北京大学日刊也循此例停刊一天。(16)尽管有这样的反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仍实现了“打倒孔家店”与“孔子已死”的传统瓦解工程。 近代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蔑视传统、解构权威、瓦解秩序、崇尚西学、重建人生、寻求意义的无序时代;同时一场更为广泛而剧烈的社会运动在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声中急剧展开。 二、改造中国与改造国民性并行的道路选择 晚清政府留给国人的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残局,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渊源于此。在这种社会大变局中,近代中国人遭遇到旷世未遇的“中国问题”:近代化道路如何选择?究竟是先有了开明的政府或说君主再来提携国民素质,还是先有了高素质的国民反过来限制专制的君主或政府?但是,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难产的答案,在现实中,近代先贤作出了既要教育改造也要社会革命的双重回答。 1.近代中国的出路选择 1905年,西学第一大家严复与威震四海的大革命家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会晤,就中国出路问题,严复对孙中山的回答是:“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以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对此孙中山的回应是:“埃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17)两者对中国出路的选择取向显然充满区别。 其实,这次对话不止是两人之间的私人谈话,它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观念碰撞。它所反映的事实是中国大地在一度充满了各种声音: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实业救国、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之后,我们的第一选择究竟是什么?为此,1905-1907年,主张“新民或改良”的《新民丛报》(以梁启超为代表)与主张“革命”的《民报》(以汪兆铭、朱执信为代表)围绕“革命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被近代史家称为“改良与革命”的持久论战。 从历史现实看,先贤们最终既选择了革命,也选择了教育改造。辛亥革命及此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可以说是时代主旋律。毛泽东因此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评价孙中山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18)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启蒙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则在思想上弥补了辛亥革命。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于近代中国人为使国家强盛而进行的艰苦奋斗过程作出了概括:“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9) 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正确地说明了近代中国人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可见,教育改造是与“革命”这一主旋律并行前进的近代画面。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轫也正是在这样迷乱的场景中孕育发展的。 2.国民性改造的启动及其内容 自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就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全方位的文化反思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中,聚焦到了一个问题:对“国民性”的批判、反思、建构与改造。 号称“新民第一人”的梁启超首先是从反思传统以来的中国人缺失“国民资格”开始的:“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交一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可以使之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民之资格。”(20)从“家天下”到“国家”、从“乡族”到“国民”,家国关系自此有了全新的含义,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渐次演变为新时代的新意识。 翻开20世纪早期的报纸杂志,无论是《清议抱》、《新民丛报》、《国民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或者是街头小报如《大陆》、《湖北学生界》、《扬子江》等,“国民”的使用频率都几乎都是最高的。1903年,《江苏》杂志上一篇题为《国民新灵魂》的文章更是一个极好佐证。作者“壮游”强烈诉求“五种国民魂”:“一曰山海魂,二曰军人魂,三曰游侠魂,四曰社会魂,五曰魔鬼魂。”因为“吾国民具此五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士驱除异族,生则立憬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如成功焉。”(21) 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业已成为国民性改造的宗旨。《国民歌》、《军国民歌》、《女国民歌》一时充斥大街小巷,报纸杂志,成为20世纪前后中华民族崛起的渴望,令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这样一种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带来的是一大批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革命事业。革命成为其时最具号召力的思想动力。革命不仅体现于救国运动,更见于日常生活,举凡“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伦理革命”、“文字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等,还有如胡适的“反对‘处女迷信’”、“‘无后’宣言”、“《李超传》(1919)”,陈独秀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梁漱溟的“慎重婚姻观”以及此期影响极大的“科玄论战”等,成为近代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渊薮与行动的直接动力。 20世纪初“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精神。1903年仅18岁的邹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发表《革命军》一书,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全书2万字,颂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号召推翻卖国的清政府,模拟美国独立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革命军》振聋发聩,喊出了时代最强音,所以印刷20多次,发行了100多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之首。1912年,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因此追认邹容为“大将军”。 但是,辛亥革命之后还有过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的原因。与此同时,复辟的事实还表明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仅仅依赖于革命是否成功,还需要更为广泛的国民基础和群众基础。陈独秀注意到了“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2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就此进入了更为深入与广泛的观念变革历程。 三、国民性改造与新人观的设计 五四前后,革命面临低潮、人生与信仰世界充满迷茫,什么样的人能够担当起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这一问题便自然进入了先进中国人的头脑中。他们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与改造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与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教”密切相关;与对国民性的反思及批判密切相关;与倡导“新人学说”紧密相关。以下笔者主要选取三位代表人物:陈独秀、毛泽东与鲁迅的“新人观”进行分析。 1.陈独秀的“新青年” 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有梁启超发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的呼声,倡导重塑中国人形象,重建中国人生之道,但是这种呼声很快被淹没于革命的浪潮中而未及深化。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推出的“新青年”,为迷茫中的近代中国人提供了现代人“理想人格”的系统阐述,也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改造与兴盛的新希望。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呐喊着“自觉奋斗”、“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出现。这样的新青年具有六种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3)这种新青年的实质就是“生命、活力、创造”。(刘长林,2001)陈独秀的“新青年”论很快得到了李大钊的响应。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及之后的“青春”等文中,将青年的使命定位于“青春中华”或“少年中国”之创造。 为了培养这样的“新青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10-15)一文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方针尤其突显了“个人解放”的价值,而且是“尚文”又“尚武”的,目的是培养文武双全的“新青年”。由此可见,陈独秀是带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双重使命创办《新青年》,所以他的文学成了社会革命的工具,他的教育思想也成了社会革命的手段。陈独秀的“新青年”具有明显的斗争使命,他的教育思想中尽管不乏“个人解放”或“个性自由”的价值追求,但“社会改造”或“国家改造”的时代意识仍占据主导地位。 2.毛泽东的“新人说” 毛泽东对于“理想人格”的求诉贯穿于他的一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一贯反对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但他也同样强调个人对社会和集体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五四前后,毛泽东所提倡的“新人”无疑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影响,这可以从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的那次谈话中得到佐证。(24)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1917)中关于“德智体”三育思想的初步阐发,以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之身心发达、互补并立、相辅相成的观点,乃是陈独秀“教育方针”的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他那“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的理论观点,正适合于“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之理想。(25)显然,毛泽东此期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文武双全、人格健全、改造社会的“新人”。 3.鲁迅先生的改革国民性 鲁迅先生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26)具有“最硬骨头”的鲁迅始终把“人”的问题置于根本位置(汪晖语)(27)。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为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充分张扬的现代示范。鲁迅先生之所以抱定文学这一“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28)不放,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深有感触和体悟的认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29) 鲁迅先生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0)可见,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根本上是在精神上下工夫,心灵的觉悟占据了全局。直到1933年在谈起“我怎么做小说来”时,他仍然带有那股一意孤行的韧劲:“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1) 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精神因此在现代中国便有了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32)鲁迅精神也就此成为指引近现代中国人思想、精神、人格和行为等方面进入“现代性”的思想象征。概言之,近代中国人在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终于找到了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想人格”。 四、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国民性改造归根结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必须依靠新教育、新社会教化手段来达成。这种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根本点就在于“个体解放”、“个性自由”,所以必须重视个人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目的,他们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与民主主义。 1.国民性改造与个性主义 近代启蒙的根本点是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个性主义”便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核心。19世纪末中国开始的启蒙运动(戊戌启蒙)并没有抓住这个主题。那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的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政治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而对个性解放并不十分关注。 因此,尽管“天赋人权”、“新民”的口号源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但是却被淹没在政治论战、武装革命的潮流中。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把“唤醒国民之自觉”作为根本任务。所谓“国民之自觉”,就是陈独秀所指出的促使大多数国民“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之人格”,是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33)到胡适在“自由主义”和“容忍与自由”两文中倡导“自由人格”,以及他与人合译的《娜拉》中“还要争取做一个‘人’的出走的娜拉”,(34)都表达了追求独立人格的新价值观。无疑,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是充满了强大的号召力的。这种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喊,我们还可以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妇女解放的潮流、“我怎样想就怎样写”的白话文运动,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感受。 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的鲁迅,尽管以一个“先觉者”的现代人,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深刻地体验着“独战的‘悲哀’”(鲁迅语)。但是,鲁迅先生那种“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意志,号召“个人的自大”、“独异”、“向庸众宣战”、“前赴后继的战斗的‘中国的脊梁’”(鲁迅语),则不仅充分表达了他对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视和对愚昧专制的反叛,而且为近现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化示范以及现代精神的指导力量。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先生《伤逝》小说中出自恋爱中的少女口中的句子,“这样一个短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它却赢得中国人如此的激动”(汪晖语)。在鲁迅自己所描述的小说中,它也具有无比的威力。鲁迅描述道:“这几句话很震动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光的。”(35) 在一个被宗法制度所覆盖的社会里,独立人格、个人自由、法律平等、人生权利等是被禁锢、剥夺与压制的。所以,一旦个人的能量被释放,“个性主义”自然就成为倡导与培植现代人的强大思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个体、个人、自我、人格、自由等新概念便成了这个时代新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源泉。 2.国民性改造与科学主义、民主主义 科学与民主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提出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才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高举起“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两面大旗,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23年的“科玄大论战”是一次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与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在传统价值系统和人生观念动摇甚至崩溃的情况下,中国近代思想家希望按照现代科学的价值观,从理论上重构现代人生观的比较深入和系统的大辩论。 “科学万能论”自此日益浮出水面。科学逐渐凌驾于“人”之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胡适所评论的:“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6)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并步发展。在整个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过程中,尽管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不断辩护,但是,时代潮流还在不断地把传统文化推向对立面。 3.对西方的信仰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恰好发生在欧洲动乱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却发现了西方文化固有的弊端,从而失去了对西方文化的敬仰。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西方问题”的产生,不仅因为西方大国失之于正义的维护与条约的遵守,不仅因为当中国处于日本人蹂躏时西方人所持的冷漠,当近代中国人看到了欧洲人是如何对待欧洲人自己时,他们也发现了西方文化自身的严重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到欧洲游历一遍之后,指出欧洲文明并不像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那么完美。他们的说法对今天大多数仍然觉得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国人不止是一个清醒剂。辜鸿铭是近代中国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早年留学英国得硕士学位,遍游欧洲,他就认为以欧美政学变中国,实质上是乱中国。 对西方的信仰危机催生了近代中国人开始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陈独秀、李大钊、杨贤江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意义深远的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37)于是,在学西方学了几十年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 五、国民性改造的遗留难题 曾经自视为唯一的文明和唯一的生活方式(林语堂语)的中国人,在面对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精美器械、科学进步之后,开始了艰难又痛苦的思考:如何改造国家、如何改造国民?当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于古老文明中时,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和思想的冲突也就成为必然。所有这些冲突都体现为一个事实:传统性的不断瓦解与现代性的逐渐产生,并在思想层面凝聚为一个主题:中国如何步入世界化的进程?国民性改造便是这一思想主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的“近代化变局”(包括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无论是“外源性”的刺激,或者“内源性”的激发,实则上都是被动应对的产物。这就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发动,由此呈现出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文化与思想论战画面。范围宽泛的论战所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体”与“用”、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东西文化论战、革命与改良、社会性质之争等;在相对狭义的教育领域,则涉及教育目的、学校与科举、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文言与白话以及多种类型的学制之争等。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从未间断。这些论战的结果,往往演变为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际的革命、变革或改良。如此,一幅充满渴望与激情、躁动与困惑、希望与追求、幻想与理想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将它纳入改造国民性的内容中。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适者生存说”,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在传入中国后,却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它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外是“自由学说”,在西方是指基于个人财产基础上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经过近代中国人改造则转变为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其主因就是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事实所决定。因而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很淡薄。尽管五四时期的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很强,但最终也很快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第三是“科学民主学说”,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目标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着眼于富国强兵及社会改造,其二是为了配合新国民的培养,必须通过使中国人树立科学与民主的态度,才能形成新国民的文化与心理素质。 然而,尽管近代中国业已完成了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发动、观念变革和理论准备,却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爆发、国内革命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社会主义运动,国民性改造的任务并没有得以实质性的完成。这种情况也直接反映在中国“教育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断裂。 近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突显首先附属于“图强”目标的追求,因而对科举制的批判与新式教育的倡导几乎是同步的。伴随着“学习西方”的思想变革,科举制的废弃,新式教育渐次形成。但是,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的诉求缘于被动应对,同样经历了“病急乱投医”的纷乱采撷,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教育思想。舒新城先生将1862年至20世纪初中国教育思想的演变概括为“模仿期”,而将辛亥革命后十多年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称为“自觉期”。(38)陆有铨先生则将这两者分别称为“西化”与“现代化”的追求期。结果,近代中国至少流行着超过18种之多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模仿”或“自觉”,或者被动“西化”与主动“现代化”;无论是停留于观念层面或者已经体现为教育实践,这些教育思想的实质可以简化为两类:百年强国梦与现代国民性的追求。 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在这两者关系中,“百年强国梦”的追求又常常盖过了“现代国民性”的求诉。或者说,教育的任务服从于革命的需要。这可以从孙中山先生前后两次演讲中找到佐证。孙中山在“民国教育家之任务”讲演(1912年)中说:“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今日破坏已完,建设伊始”,要变破坏之学问为建设之学问。此后的求学方针,是“为全国人民负责,非为一己攘利权”,“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从而我国之价值也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瓜分之说,自消灭于无形了。到了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青年会演说中则指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成功虽然已经八年,但政治腐败依然,造成“官僚、武人、政客政治之局面”,甚至比清政府还要贪婪与专制,因此立国的要素首先不是“教育、实业和民主自治”,而是革命。(39) 总之,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两条思想主线紧密相关的:第一是“百年强国梦”的追求,第二是“现代国民性”的诉求。但是,这一进程是一个纷乱的诉求过程。尽管“救国”的重任常常盖过了“救民”的责任,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性”仍然在双重困境中艰难发展,并成为现代中国许多教育思想、观念以及教育改革的渊薮。同时,近代教育思想的复杂变局也给我们另一个结论:在尚未找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之前,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想本身是杂乱无序的,这也同时表明,学校教育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主阵地至少在近代中国是处于混乱与失范状态的。概言之,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并没有走完的历程,仍需要当代中国人和中国教育改革继续探索前行! 注释: 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 ②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③[美]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④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59。 ⑤⑩(34)刘长林:《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68、291-295页。 ⑥对自杀问题的议论,也能佐证此类现象。例如,陈独秀1920年初发表了《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李大钊此期写有“厌世心与自杀心”、“新自杀季节”、“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罗志希著有“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也与此期首次翻译成中文。 ⑦齐卫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9期。 ⑧原文见《十力语要》卷四,第59页,1947年湖北印本,转引自(刘长林,2001)。 ⑨《梁漱溟全集》第1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33页。 (11)寿勉成:《我国大学之教材问题》,《教育杂志》17卷3号(1925-03)。 (12)《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1920-02-27)。 (13)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不忍》杂志第3期(1913-04)。 (14)康有为:《中国还魂论》,《不忍》杂志第8期(1913-11)。 (15)怆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14号(1918)。 (16)案例二与案例三,均见沈寂先生为《中国人生哲学重建》所作“序三”(刘长林,2001)。 (17)转引自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页。 (18)转引自范忠程:《毛泽东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9)(3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1359、1359页。 (20)梁启超:《新民说,解新民之义》。 (21)《江苏》第5期,1903年8月。 (2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1卷,第54页。 (2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4页。 (24)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见周溯源编《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下),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535页。 (25)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 (2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 (27)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8)(29)(3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417、417页。 (30)《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32)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讲,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页。 (3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35)鲁迅:《伤逝》,转引自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36)《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卷3,第152页。 (38)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21—112页。 (3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