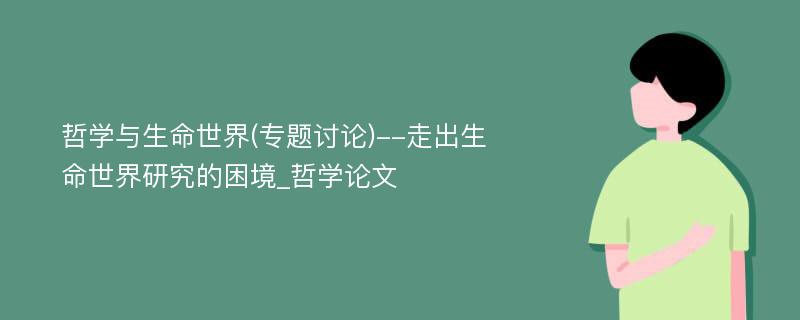
哲学与生活世界(专题讨论)——走出生活世界“研究之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世界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杨学功
[主持人语]如果仿效文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而,曾几何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远离”生活的“学院派”倾向;与此同时,20世纪为众多西方学者所阐扬的“生活世界”理论,却未能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深入的研究。有感于此,我们几位青年学人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策划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试图把对当前哲学研究现状的评论和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当代西方学术资源的开掘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专长,从互不相同而又彼此相关的角度,共同切入“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一主题。
有人说,哲学本来就是“贵族化”的学问,不必也不能“迎合”生活世界的旨趣,而应尽量与生活保持间距。但是,在这个“平民化”的时代,假如哲学只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它还会受到欢迎吗?李文阁博士显然对当前哲学研究的状况极为“不满”。在他看来,面对“SARS”之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语表明:哲学研究远离了生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缺乏现实意识和价值关怀,而是由于现实意识的政治化、功利化、非哲学化、方法论和整体化所致。他提出了“生活哲学”的概念,力图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一种哲学化的回答。
邹诗鹏教授似乎对问题抱着“留有余地”的态度。他肯定了“生活世界转向”的意义,认为它是当代哲学主题从抽象的理念世界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显示了当代哲学理性及信仰状况的双重转变;但同时又对生活世界问题的过分“课题化”表达了一种忧虑,认为这可能会模糊甚至遮蔽当代哲学的生活关怀,以至于越是强调生活世界,就越是缺乏生活气息。哲学有待于确立自觉的生活意识,但生活意识不能代替全部的哲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哲学界,“世界观”无疑是人们最熟知的概念之一。然而,正是这一概念反思的缺席,制约着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杨学功博士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世界观”概念作了辨析,认为世界观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一个人们借以“打量”和“观照”世界的不同于知识结构的独特精神世界。以此为视界,基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重新解读,作者阐发了马克思“现实生活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指出这种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
与之呼应并互为补充,唐正东教授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了对比性分析;又从理论源起、具体内容及方法论意义等角度,阐明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最大区别——能否剥开生活世界的表面现象,深入到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层面解读生活世界本身。依他之见,马克思在“生活过程”问题上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晏辉博士独辟蹊径,从元理论层次以及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视角,对“生活世界”作了带有明显个性化风格的拷问。他认为,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实存,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物理空间或边界。但是,生活世界更是一种意义世界。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不同,人的意义世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意义世界的过程是人的生命的展开形式,人的生命的量与质即表现为其生命的显现方式和显现业绩。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作为对象化活动之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世界就是人的生命的丰富性本身。由意义世界向人的生命的丰富性的回归尚有诸多环节,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认同—反观—确认;对意义的感悟需求与感悟能力。人不只是存在者,更是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哲学揭示生活世界真谛总是悲情的,它以揭示当下生活世界之无意义的方式而指向一个更有意义的可能的生活世界。
邹兴明和李芳英博士似乎对这一话题不以为然。据他们说,目前“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已步入“困境”,即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研究方式的怪圈。“生活世界”之哲学研究要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克服概念化的研究“困境”。
很明显,上述各方论者在同一语题下并未形成相同的理论立场,而是展示了一个相互商谈和对话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我们策划和组织这次专题讨论的初衷。
[中图分类号]B0;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027-28
生活世界本身是先于一切理论研究之世界。但是,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则是自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后才正式出现的。当然,这里所指的“研究”是专指以“生活世界”概念的名义而把“生活世界”作为“课题”来研究之理论研究。其实,就生活世界的实质内容而言,胡塞尔并非是最早对生活世界进行关注的哲学家。应当说,马克思才是真正将人们的关注焦点聚焦到生活世界的最早的哲学家。中国学术界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距今也有二十余年,期间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不可低估的。遗憾的只是,“返回生活世界”、“回归生活世界”到目前为止似乎已成了一句空喊的口号,犹如一个游子有了“回归故里”的念头却在归途中迷误了目标与方向。
之所以说学术界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已陷入了困境,是因为学术界已逐渐暴露出对生活世界“无话可说”。所谓“无话可说”,一是指“无新意可言”,说不出新东西来了;二是对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还有悖于前辈哲学大师提出“生活世界”之本意,即把哲学前辈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或“回归”变成了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关注”。因为学术界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已经陷入了围绕哲学前辈之生活世界“概念”兜圈子而难于自拔的境地,似乎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离开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我们就再无别的话可说了。导致对生活世界理论研究之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其实,就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而言,“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具有双层内涵。一是相对于科学世界等主题化世界而言的“日常生活世界”,这是源于胡塞尔对实践和现实的关注;二是作为“基底世界”且先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始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这是一个本质直观的世界,这是源于胡塞尔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其先验现象学的需要。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首先意味着朝向我们涌现、发生的直观对象的总体,是所谓“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朴素的、无问题意识的、自然呈现的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朴素性是指它是一个原初的领域,具有最直接经验特性。它没有任何反思和判断,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态度。或者说,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性,就是指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平凡的、被给予的、非创造的和非理想化的。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中生活,人们不会有任何的惊异之感。人们原本就是生活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经验到这个世界,感知和体悟到这个世界,但并不追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也不追问这个世界何以如此。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在其中的普遍世界,即人们在日常经验中直接面对和经验到的“周围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对现实的直接在场,是人们与其感知到的生活环境之间互动的场所,是实现人的现实意义及价值的最原始和最根本的世界,同时也是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整体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优先于任何外在的抽象理论预设的概念世界。作为奠基性、直观性和前反思性的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广博的包容性,包括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人际活动关系等等,它们构成人的生命存在的总体世界 。这样的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 验到的世界”[1](P58)。就此意义来说,“生活世界”是与知觉同在的且能被直观到的 世界,是能随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的世界,因而是必然具有某种历时性 结构的世界。用胡塞尔的话说,“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 的有效世界,但这种有效不是出于某个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每 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就连那种企图在科学真实性中认识生活世界的普遍目的也 以生活世界为前提”[2](P131)。也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世界层面的意蕴来说,胡塞尔 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前反思的、非主题化的、为科学和人的其他活动提供价值与意义的、 奠基性的、人们日常能够经验到的世界。
作为“基底世界”且先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始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生活世界又是一个超验的世界。胡塞尔甚至认为,就此意蕴的生活世界才是真正的、更为根本的奠基性世界。可以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之先验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原始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的界说上。
继胡塞尔之后,“回归生活世界”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一个重要转向。许多哲学家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聚焦到生活世界上来,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理论。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作为人们语言交往或游戏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赫勒的“日常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 行动为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之“生活世界”;罗蒂以种 族为中心的人群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布迪厄的作为一个关系的、开放的“游戏空间”的 生活世界,等等,看出20世纪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重要转向。这些哲学家对生活 世界的理解虽然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有别,但他们却仍有一些共同点。在他们看来, 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单一的科学世界、物理世界或心理世界,而是一个未经科学专业术语 泛化的日常语言和日常意识中的世界;不是观念意识世界或本体世界,而是一个主客统 一的生活经验世界;不是由各种符号建构的文化世界,而是传统与理想、历史与现实浑 然一体的多样化世界。
虽然同为生活世界观,但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眼里,他们所说的生活只是指人的日常的精神生活,其生活世界最终仍然是一个抽象世界;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生活世界则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统一,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生活世界是由实践活动创造和生成的人与世界功能性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指人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或前提的现实生活过程,生活世界本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生活世界本身是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世界,因为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不断翻新的涌流。在人的生活世界里,没有什么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东西,一切都处于无限的 生成过程中。理论研究永远跟不上生活世界自身的生成变化,如果理论研究要真正回归 到生活世界,理论研究就必须走出“经院哲学研究”之怪圈,这样才能走出生活世界“ 研究之困境”。要走出对生活世界“经院哲学研究”之怪圈,理论研究就必须对生活世 界做到“实践性回归”。所谓“实践性回归”,就是要摒弃从外在的、抽象的东西出发 规定世界、考察人的思维,走向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走近人们每时每刻都能经验到的生 活;就是要将理论的视角聚焦到人们现实的生活过程当中,去研究现实生活世界中存在 的刻不容缓的现实的实际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 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 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P58—59)正是由于对生活世界 的“实践性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产生,并进而发展成为无国界的具有世界性 和革命性的伟大理论。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根据说明,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关注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
早在1836年,即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在从事法学研究时就针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存在的缺陷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4](P651—652)因为康德与费希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批判“现有”、用理想批判现实,而不注意研究“现有”和现实本身。这种方法导致的结果,使马克思的法学研究脱离了实际的法和法的实际形式,只研究内容空洞的原则、思维和定义,因而走入了死胡同。1842年,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之职后,新的岗位使马克思跳出了纯理论问题研究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直接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马克思投身现实斗争,首先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1842年1月,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实质。在1842年10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1843年1月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触及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使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正是由于对现实尘世生活和市民社会的热切关注,马克思才得以最终走上历史唯物主义之路。正是由于对《莱茵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得以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并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深化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即转向从市民社会探究政治国家的根源,从而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生活世界所走的是一条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回归的生活世界才是我们应当要回归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从来不谈论与人无关的自然、世界或存在,而只讲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由此,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即从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或绝对理念出发来考察人,而他的哲学则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说明以往哲学中的那个抽象世界的产生。以往哲学的内核是抽象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它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从而导致了哲学对人的失落。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变革就是使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从而形成了以现实的、总体的和历史的人为特征的全新思维,哲学由此才得以成为服务于人类解放的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3](P73)由此可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
就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之说,衣俊卿主张的“文化回归”颇具特色。他指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应用哲学所代表的对生活世界的外在审视或外在规范的方式,一是文化哲学所代表的对生活世界内在启蒙或内在教化的方式。相比之下,后者更为深刻。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途径是促使对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同实证的文化批判的统一、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整合。”[5]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回归路径”,与其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衣俊卿认为:“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物体组成的冰冷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创作的世界。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存在领域中,文化无所不在。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历史地凝结成的、自发地左右人的各种活动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就是文化。因此,当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时,就是回归人本身,就是回归文化。”[5]显然,衣俊卿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然 而,哲学的使命却是要在现实中实现自身,从而使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哲学要在 现实中实现自身,或者说,要实现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因 此,“回归人本身”或“回归文化”之根本途径依然是实践,只有走“实践性回归之路 ”,哲学理论才能真正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实践性回归”是走出生活世界“研究 之困境”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引领哲学转向的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生活世界”,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生活世界”,其共同之点说明,我们所要回归且能回归的生活世界是先于一切理论,或者说,无须理论界说而普通民众可以直接顿悟和经验的世界,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之世界整体。因此,哲学研究要“回归生活世界”,就是要回归人们现实地生活在其中的本真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使理论能引导人们实际地解决问题。由于生活世界本身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研究它的哲学理论也应当不断关注生活世界在生成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研究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论才能不断地生成自身,才能始终充满活力,并始终扎根于生活世界。
收稿日期:2004-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