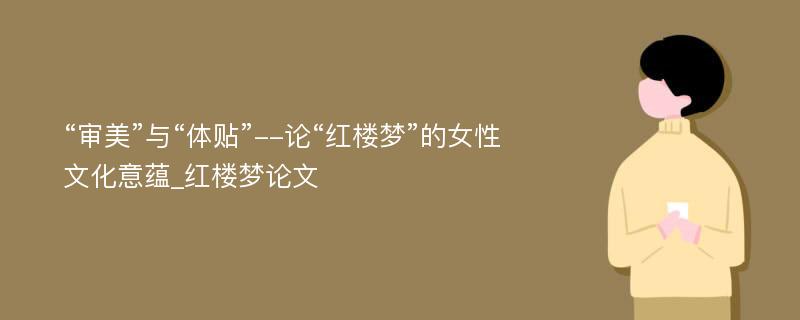
“审美性”与“体贴”——论《红楼梦》的女性文化意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体贴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3-0093-11
当性别文化的议题日益被重视的今天,我们除了了解与参考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转而从性别的向度去检视我们的文化现象,以及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文本(text),以便能从中有着更为丰富的发掘与诠释,并进而可与西方的性别理论进行对话。综观在中国的文本中,《红楼梦》可说是最具性别反省意义的一部作品,它的小说艺术成就,以及对文化与性别的反省性都相当高。小说中创构了一个独特的女儿天地——大观园,而在此大观园中,则有着与园子外面迥然不同的价值世界(注:余英时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该文即特别标举出那是“乾净与污浊”,“理想与现实”对比的两个世界。这篇文章刊载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1974年6月,也同时转载在台北的《幼狮月刊》第42卷第4期,后收于余氏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根据该书所录,这篇文章还曾译为英文稿。由于发表地之故,这篇文章较为港台学者与英语界学者所熟知,相较之下,大陆红学界对此文便较不重视。因此,几部重要的红学史的回顾,如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以及欧阳健等著《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均未提及此文。),小说在此呈现了一个相当具有特色的“女性文化”(注:本文所说的“女性文化”,即是feminine gender,它是性别文化的概念,因此,所指涉的重点并不在“生理”性别的层面,而小说中,也藉由生理上为男性的贾宝玉来作为女性文化的代表之一,他认同女性种种,鄙斥由来已久的儒家主流文化所造成的一些糟粕现象,小说刻意以此两个文化价值来对比出女性文化的特殊性含意,本文限於篇幅,将重点放在女性文化中的“审美”与“体贴”这两大重点上,至於这和男性文化的对比之处,文中仅点到为止,并不作更详尽的论证。)以对应园子外面的父权的价值文化。本文着眼于此,拟针对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女性文化的“审美性”与“体贴”关系这两个层面来作探究,以见出女性文化的独特性意义。
一、以“女清男浊”价值为准的审美性
在大观园女儿国所呈现的女性文化中,是以“女清男浊”为准的价值面向的开展,它也是对由来已久以“男性为清”、以“阳刚为清”的一种反动(注:由于易经的“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以及魏晋男性文人品评“清”的理想标准,曹雪芹的“女清男浊”论,其实也可说是对由来已久的以男性为清的一种“反动”,或者说是转为女性文化世界的一种“置换”。关于此,孙康宜特别就女性作品的品评标准为“清”,提出了看法:以为是女性的“文人化”再加上后天影响,方造就了女性作品为“清”的结果,孙氏意见正可作为女性文化世界为“清”的旁证。参见孙氏著“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性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一文,收于孙氏著《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他不仅转而以“女儿为清,男子为浊”的价值观来替代,更以此来开展女性文化的生命面向。小说藉由女儿国中的重要主角贾宝玉提出了这样的价值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先天上便认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所以,在“女清男浊”的认知前提下,他对从自来以男性为主所建构的、以儒家道德伦常价值为核心所带来的为人所歌颂的价值,如“世道人情”(第五回)“文死谏”“武死战”(第三十六回)等均深不以为然,而认为只有透过清爽的女儿,方能展现“天地精秀所钟”的“理想”。因此,“清”“浊”不仅是从男女的性别上来说,它的背後,更指涉着从宝玉身上体现的女性文化价值,与由来已久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男性文化价值的一种对比。
首先,就“清”“浊”的意涵而言,他们原来所指涉的均是自然现象(注:《说文解字》解“清”为:“清,朖也,澂水之貌”段玉裁注曰:“朖眼者,明也。澂而后明,故云澂水之貌。”《玉篇·水部》:“清,澄也,洁也。”《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漪”另《说文解字》解“浊”为:“浊”水。出齐郡厉妫山,东北入钜定。”《释名·释言语》:“浊,渎也,汁滓演渎也。”《诗·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凡此均说明了清与浊原是个自然现象的叙述。),而后又被赋予了价值高低的评断(注:如《楚辞·渔父》即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王逸注:“浊,众贪鄙也。”又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赌大体。”均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被赋予了美、丑之意义,而演变成一组具体的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清”更用来作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概念(注:《世说新语》中,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赏誉篇)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容止篇)),此“清”的形象是十分“男性化”的,它意味着脱俗、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典雅气质。除此,“清”也意味着天性本质的自然流露的美。以“清”来指涉文人雅士的美好、高尚、尊贵等;而以“浊”来指涉丑恶、卑劣和低下等,特别是从曹丕《典论·论文》引“清”“浊”这一组范畴入文学理论的实践中时,更把“清”和“浊”的内涵扩大了,使得“清”不仅指的是个人的人格气质,又指的是作品中的神韵等(而“浊”则是有着与“清”相反的意思),曹丕更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有着“清”的人格品质,才能创作出“清雅”的作品来。关于此,孙康宜以为:因为女性作家她们不必在意现实的考虑以及诗歌的派别,所以反而能保持诗的感性,又由于他们在社会经验的局限性,使得她们有着更为丰富的想像力。而这使她们更为接近“清”的气质。而能创作出“清”的诗歌作品。(注:孙康宜还进一步说明了:从明清以降的文人,把“清”的美学推广到才女的身上,他们更倾向于把“清”等同于女性诗歌的品质。而女性被说成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孙氏的见解,可参见“从文学批评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收于孙氏著《文学的声音》,台北三民书局,2001。)因此,吾人可注意到在女儿国的意义世界中,她们便是以创作“诗”的活动来相互辉映他们清丽的品质。
除此,“清”“浊”还与“美”“丑”(注:中国最早从美学意义上提出“丑”这个概念,并对“丑”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庄子,他认为现象界的丑与美在本质上是没有什麽差别的,都是绝对美的外化,所以,现象界的美、丑的存在便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例如他在“秋水篇”中,便以北海之水的大与河川之水的小,来说明美、丑的相对性。所以,尔后美、丑作为一相对的比较范畴,往往可以产生丰富的讨论。关于此,可参彭修银《美学范畴论》第221-225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此审美准则相参,也就是说“清”是“美”,而“浊”是“丑”的。依循这个角度,我们方可进一步理解在小说中所叙述的“皮肤滥淫”的呈现,其实是一个“丑”的、“不美”的存在,而不是以儒家道德伦理的角度所批判的“秽德败行”的存在。此由警幻仙姑的话语可窥出端倪,警幻在第五回中所批判的“皮肤淫滥”,其后面紧接着的受词是“蠢物耳”(注:原段落是“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另外在第一回中亦出现此词,藉由一僧一道的对话,以超脱人世的角度及嘲谐性的语气,呢称那央求下世的“石头”以及还泪的风情月债的一干人等为“蠢物”。),此“蠢物”用词充满了一种“嘲谐性”,而不是“谴责性”(注:谴责性与嘲谐性之分,正说明了一为道德角度,一为审美角度,此观点参考自周义“《红楼梦》中的‘意淫’解”一文,《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吾人可见在小说中,凡对这些皮肤滥淫者的描绘,其嘴脸都确实是滑稽而又可笑的(注:无论是贾琏与多姑娘的放浪的模样(第二十一回),或者是薛蟠唱的“哼哼”女儿歌(第二十八回)以及他调戏柳湘莲不成后的反被设计(第四十七回),均充满了令人忍俊不住的好笑的效果。)。所以,此词并非指其性质邪恶,败德不堪;而是指其“不美”;“美”正是皮肤滥淫之流所最缺乏的。警幻口中“绿窗风月,绣阁烟霞,悉被‘玷辱’”(第五回),此“玷辱”正可说明了对“美”的清净特质的玷污与唐突。而这也可说明了为何当宝玉思及香菱的慧质兰心,便觉得是被薛蟠这个“霸王”玷污,而觉得“可惜”的原因了(第六十二回)。
清、浊是以性别作出发的一个充满了“审美”的面向,就外在的形象美而言,如写黛玉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第三回)写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第三回),都着重在其姿态神韵的美感上,甚至连湘云的睡态,都是一幅美丽的形象:“一把青丝拖於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第二十一回),女性文化的世界中,除了对一个个的女儿有着不同的形象神韵之美的呈现外,更以自然界美丽的“花”来强化此清净之纯美形象。让女儿们是分属不同的花神(注:例如:在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群芳开夜宴”时,女儿们以掷点抽花名签子,以各自不同的花,来暗示他们的特质与命运。又透过一个小丫鬟的口,说晴雯已升天作了花神(第七十八回),凡此,均说明了花与女儿的关系。),以此标准,我们也可见在大观园外面的一些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如北静王水溶、蒋玉菡、秦钟、柳湘莲等,他们也都有着女性化的鲜明特质,他们虽生理上是男性。但都天生禀性好静、恬淡温柔、光彩照人、秀美袅娜,因此,除了宝玉之外,相对而言,他们是小说中,较为“清洁”的男子形象,也就是较为倾向女性文化的男子,小说以此对比如皮肤滥淫之流的贾赦、贾琏、贾珍、贾蓉,与迂腐刻板的贾政等人的污浊形象。
清、浊从外在的“形象美”的指涉,更进一步地用以对比一个“干净”与“肮脏”的价值世界,这个干净的世界也就是指涉着女性文化的世界,那个世界由黛玉为首作表徵,她对于一个非女性文化世界的态度,是更为绝对而彻底的,无论是生理上的男性或是父权文化,黛玉都是视之为脏的臭的,例如:当宝玉兴冲冲地将北静王给他的珍贵鸽香串送给黛玉时,她便马上掷而不取:“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第十六回)。除此,并以美好的花的意象来代表一个干净的纯美的世界,黛玉在葬花时,便以她的理念和宝玉产生了共鸣:
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第二十三回)
小说不断以“干净”来与“葬花”此美丽的意象作紧密连结,此即在透过干净纯美的花,流出园外便会受到沾染,来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天地灵气之所钟的女儿,出了嫁,被父权体制收编时,即意味着被浊物“沾污”了,那么原来的纯美便会变得污秽,没有色泽。宝玉以“珠”的变化来说明此间的差异: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珠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在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透过丫鬟春燕的口转述,第五十九回)。
又如当他思及邢岫烟已被择定夫婿时,仍不免伤感:“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第五十八回),以及当他得知迎春出嫁,要陪四个丫头过去,更是跌足叹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第七十九回),凡此均说明了小说透过宝玉的感受,传达了对女儿们纯美理想特质失落的感伤。除此之外,倘若闺中女儿在认知上“浸染”了父权价值系统的色彩时,也变得“不美”了,当宝钗劝他时,他便生气地说道: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第三十大回)
而和宝玉一起长大的史湘云,一次忍不住劝他要去会一些为官作宰的人,谈讲些世途经济的学问,以便将来有个朋友好应酬世务之类的话时,宝玉听了更是厌烦地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视此为“混帐话”(第三十二回)。
因此,清净的美,不仅只停留在外在的女儿样貌上,还要加上内在的价值认知以及纯洁柔美的情性,所以,“清”“浊”的意涵在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便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从清净洁白的女性形象、神韵到背后指涉的未被污染的价值世界,都说明了她的审美的、理想的特性,而这个审美的、理想的特性,是完全迥异於小说中所另外呈现的儒家文化的种种面貌的,不仅如此,小说还刻意以美丑的价值来加以对比。以女清男浊为准的价值出发,女性文化所开展的生命面向,充满了相当浓厚的审美特性。
二、审美主体之艺术性活动
审美的经验世界是透过有着自由情性的主体,以感性、丰富的想像感受与真挚的心去展现的,这可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主体在对事物感受上的审美心理,一方面就其所从事的活动而言,带有一种审美特质。而就心理层面而言,这种心理体验是人的内在心理生活与审美对象之间交流或相互作用後的结果。(注:参考自李泽厚主编、滕守尧著《审美心理描述》第1页,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7。)所以,他是审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当下的交流互通,就女性文化的世界而言,这种当下的交流互通,充满着美感与意趣,此中展现了一种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的审美观照,著名哲学家康德便曾提出了“审美无利害关系”(注:在18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中,这种性质和特性即已提出,但把他们提到哲学高度来论述,并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则首推康德。参考自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的观点,以为这是一种充满了想像力与非逻辑性的审美特性(注:参考自朱光潜编译《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第196页,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4。)。所以,女性文化中的人以各自具特色的主体情性,或者以个人对外在美感之物所迸发的艺术形象,或者,他们共同从事的活动,都可见出其中有别于男性世界的艺术活动特色。此中,无论是小姐的角色,亦或是丫鬟的角色,带发修行的女尼(妙玉)角色、亦或是社会上地位较低下的戏子角色等,都可因着自己的特性长才参与进来,而彼此之间也以审美的心理相互观照着,织就了一幅美丽的艺术图像(注:其实,就他们所处的大观园,本身就具有一种艺术造境的美,此中每人所居之地,有着寓情于景,景中有情的总体效果。其中造景的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诗情画意,便使人置身其中,而进入一种超尘脱俗的清淡谐和之境。)。
首先,就他们群聚的活动而言,他们的活动很多,如过生日、行令、宴饮以及猜灯谜等,然而此中,他们认真看待并投入心力热情的便是主要活动“作诗”(注:作诗确实是他们最常表现的审美活动,除了诗社的作诗活动,他们彼此的乘兴联诗,都是大展其才华之时。)了。他们透过作诗的活动,意味着对于外在物象或者是内心的感怀,有着自我主体发声的满足,不同于男性文人的应和酬祚的社会性(注:《红楼梦》中女儿们的“诗社”活动,并非独创,就中国诗社传统的建立和形成,虽清袁枚曾提出起于明末的推测,但事实上早在宋哲宗元佑年间传统诗社便正式出现,综合诗社的构成要素及运作,大约要有发起人和组织者,称为“主盟”或“社首”,一般多为在文学和政治上有成就的人,而参加者,必须自觉地对其有尊崇的和服膺的意识,他们透过诗社的聚集,进行或唱和或品第标榜等活动,以达至诗艺的交流与对外发挥影响力。虽然,女儿们的“诗社”大体形式与男性文人结社相差无几,但男性诗社藉由评诗所要达成的内部评诗准则,以及对外产生的在文坛上及社会上所要发挥的影响力的企图是不同的,女儿们的聚集所强调的个体性与趣味性,要较男性文人诗社的较具社会性的色彩不同。有关诗社的成立溯源,可参见黄志民《明代诗社之研究》第一章第一节“诗社渊源考”,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2。),他们是以嬉戏相互品评欣赏的方式来创作,诚如朱崇仪所说:“使用诗的语言此一文学能力,就成了尽情享受女性奇幻世界(female fantastic world)的先决条件。”(注:引自朱崇仪“大观园做为女性空间的兴衰”一文,中外文学第22卷,第2期,1993。)而在此当下,他们又以“起义”“意趣”的审美态度灌注了他们全部的热情。延续着前面的以“女清男浊”为准的审美性为出发点,吾人可见,他们起初成立诗社的原因便是“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第三十七回),以“脂粉不让须眉”的方式来说明女性优异的才情展现。果然在探春的登高一呼之下,宝玉与众女子莫不欣喜附和。值得注意的是,诗社成立之初的第一件事,便是他们从伦理序列中脱离出来,重新为各自命名,也就是因应着黛玉的提议:“先把这些姊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大家分别就看待彼此最有特色之处,相互为对方取名,例如探春以“湘妃竹”的典故,加上黛玉流泪的形象,取了个“潇湘妃子”的雅号,而宝玉在大家的玩笑之下,也被取了个“无事忙”“富贵闲人”之类的和其平日予人的印象相符的封号。
诗社的成立和作诗等活动的进行,都充满了一种偶然的、当下的、兴起的、意趣的审美特性。成立之初,便是因“一时之兴”而起,探春说的:“偶然起个念头”而後又正巧有贾芸送进的两盆白海棠,就这样,他们便以白海棠来作诗,并以海棠为诗社之名。此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贾芸送花,是为拿花孝敬宝玉,认宝玉为父,拿花为进身之法的,这原本是人情往来,具功利性色彩的行为,但却为女儿们转作了风雅的吟咏。如此的偶兴也出现在后来他们把海棠诗社改为“桃花社”时,便是偶因黛玉的一首“桃花行”的缘故,众人都说:“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一个人‘作兴作兴’”(第七十回)而后他们的因柳絮填词,也是因着“时值暮春之际,史湘云无聊,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令”(第七十回)这样的因缘,当湘云写完,拿给宝钗黛玉看,黛玉赞着:“新鲜有趣”,便“偶然兴动”地邀着大家以柳絮为题。这种偶发的、不为特定目的的行动,有着随机而有的无意中的惊喜与欢欣,再如也是在他们咏柳絮完后,听到窗外竹子上的一声响,见一个别人家放的蝴蝶风筝,落在自家竹稍上,于是黛玉便一提:“把咱们的拿出来”,于是大家(小姐丫鬟)又开心笑闹地一块儿放风筝了。
这些女儿们均是以“清雅”“有趣”来看待起诗社这件事,所以,当诗社成立后,并不用严格的社规,来限制彼此,也没有约定必得要几日一会,只大抵有个准头即可,诚如探春说的:“若只管会的多,又‘没趣’了。”(第三十七回)而宝钗也附和着,除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岂不活泼‘有趣’”(第三十七回),这种随机、当下的“兴致”,常是触发他们行动的原因。诗社成立的第二天,史湘云得知此事,也巴巴地要加入,众人“见他这般‘有趣’”,便欢喜他也成为诗社一员,而湘云更是“一心兴头”,等不及的在和众人边说话边构思的情形下,便成就了两首“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的好诗。当下随机的诗社活动,在尔后无论是咏菊或咏红梅,都展现了众人一贯的“趣味性”及全心投入的热情。例如在咏菊时,他们将与菊相关的题目誊好,贴在墙上,也不限韵,叫每人勾选,这时他们的状态是:
林黛玉自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掷向水面引的游鱼浮上来唼喋。湘云出一回神,……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一回又俯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第三十八回)
他们沈吟在自己的诗兴中,一个个全心专注地在美好的景物上,所以,不仅成就了一首首的好诗,他们自己与美景混融一片,更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们作菊花诗时,以“主意清新”为宗旨,以菊为主,以人为宾的咏菊,果然写了十二首有着不同气象新意的好诗。
他们以充满着“意趣”的审美心态,来从事他们看重的活动,“趣味性”“有趣”是他们群聚兴发的一个心理触动,诚如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以为的:
趣味是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一种专门欣赏美的器官,每当我们采取一种非功利的态度去注意事物时,这种感官便开始工作。(注:引自李泽厚主编、滕守尧著《审美心理描述》第14页,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7。)
当人们用这种“趣味性”“非功利性”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和艺术创作中的美时,便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愉快的心情,这正可说明当这些女子群聚作诗时,都充满了天真欢乐活泼的气氛,因为他们在其中,除了忘却自己的原本的身份角色,而以自己的才情以“当下的”“起兴的”以及“有趣的”方式及心态来从事这群体的活动。他们作诗的欢快,以及无目的的存在状态,对比贾母所说:“有作诗的,不如作些灯谜,大家正月里好顽的。”(第五十回)更可见出他们行为背后的审美价值倾向。
这种审美的欣赏,也展现在众人相互的看待对方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六十二回所叙述的“憨湘云醉眠芍药裀”了,当湘云酒力不支、离了众人时,才被小丫头发现他在山后头的青板石凳上睡着了。小说这样叙述着:
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於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沈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
湘云不胜酒力地醉卧在芍药引,她那酣饮沈睡的自在闲逸,以及和花瓣、蜂蝶等外在景物交融的自然和谐,洋溢着无限的天机盎然,也形成一幅有趣而又美丽的画面,众人以审美的心境观照着这幅画面,于是“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此处没有对湘云醉卧“当与不当”的责备与价值判断,而是个个审美主体们均表现了对美的姿态的一种直观的感受。除此,又如晴雯(宝玉丫鬟)的“撕扇”情节(第三十一回),也是因着撕扇本身的“好听”“有趣”,引得宝玉也大加赞同。以及莺儿(宝钗丫鬟)的巧手编柳(第五十九回):莺儿便是因见了“构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便对着同行的蕊官(原为戏子),说柳叶儿“什么东西编不得?顽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个花篮儿,采了各色花放在里头,才是‘好顽’呢。”于是他“一行走一行编花篮,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枚,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将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如此新鲜的别致的花篮,也得到了黛玉的赞赏,小说在此对比着老婆子的以为糟蹋了花儿柳儿,不得卖钱的“心内不受用”,也着实在此区分出女性文化世界的非功利与非目的性的审美趣味。
三、女性文化中的“体贴”关系——平面网络关系的建立
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是一审美面向的开展,此中的人们,他们群聚的当下本身,充满了一种偶然的、趣味性的特性。观察此中的人们,他们的关系也有着与园子外面迥然不同的关系形式,那就是“体贴”关系。女性文化中的体贴关系,是一种超越身份名位的一种“彼此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是以各自的主体情性为准,而以当下的纯粹心意作出发的互通方式,此间没有人情利益的考量,而是以对方的处境与心情作为心意发出贴近的对象,使得心意互通的双方能感受到情意流通的体贴与温暖。
在女性文化中的存在主体,他们可以不必从名位序列的关系人情上,去拿捏考量自己的心意与利益间的传达合宜,而是能一本初心地,将自己真挚的心意发散出去。在男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人们往来的关系认知上,虽然也有着真心诚意的流通,但是,重点却不在此,而是在於对往来双方的社会角色,有一“相称”“妥贴”的心意传达。女性文化的审美面向,正是需要审美主体以真心诚意去感受人与外在事物的美,此中的“真心”,主要指的是一种无功利性的、不受名位之心所蒙蔽的“绝假纯真”(注:此颇能从明李挚的“童心说”得到证明:“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明李挚《焚书》卷三“杂述童心说”第98页,台北汉京文化公司,四部刊要子部法家类,1984。)的心意,而这正是清净洁白女儿的一项特质。
由于女性与社会价值系统的密切性,不若男性为高,相较之下,闺中女儿亦受父权价值系统的洗礼较少。所以,他们的“童心”便较容易维持着。事实上,他们也常被视为是较自然的、较天然的,较不具文化与文明性的(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西苏(Cixous,Helene)在他一篇题为《突围》(Sorties)的论文中,便曾列举出像太阳/月亮、文化/自然、高/低、男/女等这样的二元对立,在这二元对立中,男人是被联系住一切属于文化层面的、光明的和高的属正面的事物,而女人则是被联系住一切属于自然的黑暗的低的属负面的事物。参考自罗思玛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华译《女性主义思潮》第395-396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就像孩童一般较未受到污染。在中国文化中,即常见将女性与婴儿孩童化为同一类的说法,例如:“孺”字,原本是指幼儿、乳儿的意思(注:《说文解字·子部》:“孺,乳子也”。),但《礼记·曲礼下》则说:“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此“孺人”便指的是大夫的“妻子”,另外又如“孥”字,也是指的“幼子”,或者是“妻与子”合称(注:《小尔雅·广言》:“孥,子也。”《孟子·梁惠王下》:“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赵岐注:“孥,妻、子也。罪人不孥,恶恶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凡此,均说明了将女人与儿童归为同一类的看法。去除了道德伦理价值判断所可能造成的对本心的蒙蔽,以及剥落掉名位序列所带来的好名之心与位阶高低的价值,女人就可像孩童那般地天真自然。以此立场发而为女儿们的创作观,他们便强调了以“真心真意”出发的重要性。例如:黛玉的教香菱作诗,便特别强调:“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第四十八回),妙玉也同样提及此“以真为准”的价值:“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第七十六回)“纯真”的特性,发而为真情真事,而这便是“闺阁本色”了。
在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人们,他们可在自己纯真自然的心意之发散下,来构成一个较平等、较充满了真心情意的网络关系。这个网络关系,是以“关怀”(care)对方为纯真心意发出的基础,这个“关怀”,诚如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注:关怀伦理学是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而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参见萧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第26页,北京出版社,1999。)中的诺丁斯(Nel Noddings)所以为的:是包括了对他人的感觉、感受,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种“化他为我,他就是我”的状态(注:这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基本主张,美国的关怀伦理学健将诺丁斯(Nel Noddings)将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主张更为系统化的说明。而认为:在关怀的过程中,自我和他人是完全地融为一体的,这和儒家所说的以己取璧,推己及人的先突出了我与他人的区别,在思考顺位上不同。参考自萧巍《女性主义关怀理论学》第132页,北京出版社,1999。)以“纯真心意”加上关怀对方的处境心境的过程,可以在一个彼此平等的前提下,和他人建立起一个“平面”的关系结构,而这是有别于父权位阶系统下的“纵向的”“等级式”的关系的。此诚如吉利根(Carol Gilligan)所说:
女性的道德就是一种网络性的关系结构,他们的道德发展就是网络关系的不断扩展,这就使父权制下的等级制的道德关系变成了人与人相互平等的平面关系。(注:参考自萧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第129页,北京出版社,1999。另外,在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代表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也提及关怀伦理学的贡献,是为人类的联系,提供了一个非等级制的视角,他以为:“尽管存在着力量差异,但仍有着自我和他人将被同等对待的憧憬,一切都将是公平的憧憬;每个人都应当被反映和包括进来,没有一个人将被孤立出去或者受到伤害。”引自该书第64-65页。萧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此平面的网络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四方发散,网络的范围越大,自我在其中也就越有价值,以主角宝玉来看即是如此,他对清净女儿的关怀,从大观园内的女儿,扩展到园外的女儿,如平儿、鸳鸯,更扩展到不相识的女儿,如傅试家的小姐,甚或画里的女子等,当他在女儿跟前尽心时,便深以为幸,他自己的价值意义也才更得到满足。宝玉由于身为男性,但性别价值认同却为女性,所以,更能在较女儿行动来得自由的前提下,能更多机会地“在女儿面前尽心”来形成他的网络关系。
相较之下,其他的女儿,通常则是藉由所处环境的允许,藉着彼此的关怀,来形成网络关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小姐与丫鬟的关系了,他们超越了身份,同样也是经由“关怀”的过程,方建立起一个平面的网络关系,例如:黛玉的丫鬟紫鹃,他原不是跟随黛玉来贾府的丫鬟,但他却因处处以黛玉为主的关怀,而有了“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第五十七回)的精彩情节,也才会有“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第五十七回)的对黛玉剖心的建议,所以,当宝黛二人生气闹了一日后,紫鹃也才敢于以“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之语相劝,更是不听黛玉而自作主张地开门让宝玉进来(第三十回),如此昧于份际的情形,便可从其原与黛玉是一种平面的网络关系中见出了。
四、以对方处境与心情为主体的贴近
女性文化世界中以绝假纯真的心意出发,而建立了平面网络关系,人们于此中,是以“体贴”的方式来彼此相交,前面已提及,此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所标举的“关怀”理念——“全身心的投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小说中,直接以“体贴”来形容之人物,便是宝玉了。第九回说宝玉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而脂批于第三回与第五回中,也以“体贴”来注解宝玉和黛玉(注:第三回在黛玉见宝玉摔玉而哭说:“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的段落,脂砚斋批曰:“所谓宝玉知己,全用‘体贴’工夫。”另第五回叙述到警幻仙姑推宝玉为“意淫”是“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部分,脂批为:“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这两处文字分别引自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第89、135页。)。就小说整体而言,吾人可知,透过宝玉与黛玉所发明之“体贴”,其意思便是:以对方处境与心情为主体的贴近。而这也是此中人与人往来的行为方式与价值。
“体贴”一词,并未在过去的中国哲学范畴中形成一系统的说明与讨论,不过,“体”字倒是曾被用作为君王者的对待臣下与百姓所应具有的心态。《中庸》有言:“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朱熹便注曰:“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晋鲍照亦曾在“代客坐吟篇”中,叙及:“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注:《汉语大字典》第七册,第4220页。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从“体”字的用意,可说明了它“察别人心意”的意思,因为“意”本身,就有和“体”类似的意思,《说文解字》便说“意”是:“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而《易·系辞上》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凡此都在表明一种用心去体察别人心意的意思。
在《红楼梦》中,“体贴”二字则有了最丰富的展现,因为,它除了说明它原来的意思之外,更强调了两个重点,那就是:全心的投入到对象上以及将观看对象的女性转客体为主体。当“体贴”用到女儿身上时,对体贴一词便有了新的突破的意义,这意味着原处于从属的客体位置的女性,转而成为主体的存在。在小说中,便是藉由身为男性的宝玉来呈现女性反转位置的这个变化。以女儿为尊的宝玉,常常是怀抱着对女儿的欣赏、对其处境的悲悯与同情,而“忘我的凝视”(注:陈维昭说:宝玉是“在对众女儿的凝视中忘却自我”确实如此。引自陈氏著《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第2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并将心思挹注在那些尊贵的女儿身上;在体贴的过程中,当重心转到了对象主体的身上时,此中,“我”便从主体的位置消失,而反转为客体,小说中的李嬷嬷所说颇为传神:“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第十九回)此对象女儿便会在宝玉体贴的当下,瞬时转变为主体,而他原有的身份地位也会消失,转而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主体情性的自由展现。
在宝玉“体贴”的映照下,原来在社会上卑微的女儿,如丫鬟和戏子,便会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惊喜的经验。第五十八回中,便叙述到宝玉让原是戏子,而后分派当丫鬟的芳官,尝了原要给自己喝的汤,芳官“只当是顽话”,而后在晴雯的示范下,才大着胆子喝了,也正因如此,芳官忘却了他的身份,接下来便写他“满面含笑”地解答了宝玉对藕官烧纸的疑问。另外,玉钏儿的“亲尝莲叶羹”也是一例,在第三十五回中叙述到玉钏儿奉王夫人之命,为挨父亲打的宝玉送莲叶羹,玉钏儿因姊姊金钏儿为宝玉之故被撵出而自杀,所以心中含怒,但又碍於自己丫鬟身份,只好哭丧着脸尽责任地只回答宝玉的问话,而后才慢慢地发现“只管见宝玉一些性子没有,凭他怎麽丧谤,他还是温存和气”,于是他“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脸上方有三分喜色。”玉钏儿开始感受到宝玉的善意,接着拿汤时,却不小心把汤泼了宝玉手上,“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的,却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钏儿和众人都笑了…‘你自己烫了,只管问我。’”玉钏儿终于因着宝玉的体贴而转怒为笑。从玉钏儿在宝玉面前的从含怒隐忍到开怀而笑的转变过程,说明了玉钏儿在宝玉体贴关怀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卑下的丫鬟身份。
“体贴”透过宝玉的实践,正说明了那正是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价值,因为,在无意中,当被体贴的女儿,都会有种那正是“我辈中人”之感。例如:第五十八回叙述到,扮演生角的戏子藕官因祭拜死去的旦角菂官,在园中烧纸钱,而被老婆子严责,恶狠狠地准备拉去管家处处罚,宝玉体贴丫鬟烧纸必有悲情,便当场编以自己之故来护庇藕官,且看藕官的内心变化:
藕官正没了主意,见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忽听他反掩饰,心内转忧成喜,…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
在同为此中人的感通下,藕官透露了心中的秘密。尔后藉由芳官所言,知道藕官难以对外人道的心事时,果然宝玉是“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第五十八回)另外又如第六十二回叙及香菱的“情解石榴裙”,由于香菱把宝琴给了石榴裙污脏了,当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宝玉的话,完全从体贴他的处境出发:
若你们家,一日遭塌这一百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姊姊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样,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遭塌东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
宝玉的话让香菱是“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了”。宝玉的体贴,完全从对方的处境、心情与需要上出发,所以,常让对方有正合心意的惊喜与感动,而后宝玉出主意让袭人的裙给他换了完了此事。宝玉在女儿跟前的尽心,就属香菱与平儿是“意外”中事了,因为他们侍妾的身份,以及不常单独与宝玉相处,所以,宝玉不得机会对他们尽心体贴,然而,一当有这机会时,连平日颇知世道人情往来的平儿,也都不禁讶然,第四十四回这么叙述道:
平儿素习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儿们接交;…平儿今见他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的周到。
宝玉的体贴,让女儿们感受到惊喜与温暖。凡也是此女性文化中人,必能感受到他实是“闺中良友”(第五回警幻仙姑之语)。园外有着特殊性情的女子尤三姐,便曾当着尤二姐与小厮的面,这样细腻地为宝玉分辩着:
咱们也不是见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若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脏,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说:“我吃脏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样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第六十六回)
宝玉这种全心只为体贴女儿的“不大合外人的式”,只有在深知女性文化价值的人身上,方能得到共鸣,这也说明了,女性文化世界有着与外人不同的人际运作逻辑。
在此女性文化的世界中,以对方处境和心情为主体的贴近,藉由宝玉与黛玉这两位主角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说是表现得至为透彻(注:小说随处可见两人对对方的了解与体贴,如宝玉被贾环用腊油给烫伤了脸,黛玉忙着赶来探望,宝玉则是“忙把脸遮着,摇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洁,见不得这些东西。”而黛玉知道宝玉心内怕她嫌脏,但仍“强搬着脖子瞧了一瞧,问他疼得怎么样。”(第二十五回)又如宝玉的诗才远不及黛玉,当大家作菊花诗时,宝玉得意地作了“螃蟹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呢?”黛玉忍不住地笑道:“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并立刻提笔挥就,宝玉看了全心喝采,黛玉体贴他的勉力成诗,马上一把将自己的螃蟹诗给撕了,并说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第三十八回)又如在风雨之夕,只有宝玉冒雨来探望黛玉,满心以黛玉的身体为念:“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你想什么吃,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而黛玉则是一心挂念宝玉回去不便,所以,一边催促:“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一边把连宝玉都不舍得用的玻璃绣球灯拿来(宝玉说他原有一个,怕失脚滑倒打破,所以没点来),给宝玉用,并说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宝黛相互的体贴,可说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自然表现。)。在二人尚未定情之前,由于代表世上价值的“金玉良缘”之说,始终横梗在两人之间,所以,体贴之情往往藉由迂曲的方式表达。第二十九回二人心中所想,颇能说明全心挹注在对方身上的体贴之情: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
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
这种全心挹注在对方身上的体贴,正可从“只要你随意,我便…也情愿”以及“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的真心真意得到充分的说明。所以,当宝玉后来遭贾政狠狠的毒打时,黛玉是“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而宝玉则是见了他便说道:“你又做什么跑来!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的馀热未散,走两趟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你不可认真”(均见于第三十四回)这两位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代表,用他们无时不体贴的方式,最后终于相互走进了对方的心灵世界。
在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体贴”方式,可说超越了现实的利益与人我之间的份际拿捏的。因为,此中人一心只在对方的处境与需要上用心,付上自己的关怀,此中是不计利害得失的,黛玉的教香菱作诗即是一很好的说明。第四十八回便叙述香菱学作诗的过程。当黛玉面对香菱向她求作诗之法时,便展现了她对对方需要的完全尽心,此中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的,而黛玉却是极有耐心地一一从对方学作诗的不同阶段来教导:先是以“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来去香菱心中之怯,而后再指点他作诗以“立意”为上之理,再借之以大家之诗集,使其玩味揣摩,而后再不厌其烦地与之讨论,黛玉说:“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最后再鼓励他试作诗:“只管放开胆子去作”。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香菱学作诗的这件事情上,小说另有着耐人寻味的对比。那就是诗才其实与黛玉不分轩轾的宝钗,才是就近教导香菱的最好人选,因为,香菱是进园来与他作伴的。当香菱央求道:“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工夫,教给我作诗罢。”宝钗的一句:“我说你‘得陇望蜀’呢。”便拒绝了她,宝钗在意的是要她“先出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第四十八回)而这正是宝钗与黛玉的最大分别。宝钗看重的是如何“合宜地”经营她在所处环境的人际,所以,与此并无直接相关的事,宝钗是没有兴趣的,反观黛玉,她则只单纯着眼在他人的需要上。这两种价值的对比,也可在宝钗的收服黛玉上,见出分别。对宝钗这位大得贾府上下人心的人而言,她对黛玉从间隙到收服的过程,可说明了二人价值倾向的不同,宝钗藉由私下规谏,以免黛玉出糗,以及以送燕窝来稳固彼此的关系,换得了黛玉对宝钗的剖心告白: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第四十五回)
宝钗以经营人际的关系来妥贴地收服了黛玉的心,但对黛玉而言,她所感受到的却是宝钗的“体贴”之情,所以黛玉方会说出“东西事小,难得你多情如此”(第四十五回)的话来。
同样的对比,也可以丫头身份的晴雯与袭人来说,晴雯可说是和黛玉一流的人物(注:说在人物的设计上,将宝钗与袭人归属较具世道人情价值的人,而黛玉与晴雯则是同属自尊心强,较不合世道规范的女子,所以,让黛玉与晴雯在外貌上有些神似,如王夫人口中的“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第七十四回)即指晴雯。举凡宝黛关系中的重要发展,都和晴雯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就黛玉的含泪葬花事件的误会,使得二人关系更进一步,以及宝玉对黛玉的定情之帕,刻意支开袭人而让晴雯去传达等,甚至后来的晴雯死,宝玉为他作的“芙蓉女儿诔”,黛玉听了,亦以其对象彷佛自己而心中悄然变色。),所以第五十二回叙述到,当他仍在病中,而宝玉的孔雀金裘又烧了一个洞时,他把全心都放在宝玉的需要上——“明儿是正日子呢,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她那挣扎着坐起补裘的过程是:
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著。…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第五十二回)
一旁的宝玉全心放在晴雯生病滚烫的身体,所以,体贴地边嚷着歇歇,又递茶拿枕的,而晴雯则是全心在宝玉身上,所以急得他体贴地央求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此二人对对方的体贴,可说是一片纯真心意,但袭人却有了“目的论”的解读,且见她后来拿话取笑道:
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枯,竖线不动。…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别只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第六十二回)
对照这两个例子,颇能见出女性文化世界的体贴,是展现在当下对方的需要上的,这是一种体贴者以对方为主体的全心挹注与付出,而这是超越人情份际、审估对方需要、付出的时机与要达成的果效等的层面的。
由于女性文化的“体贴”和男性文化所强调的世道人情智慧的“拿捏份际”不同,所以,此中人所可能产生的挫败也源于此,特别是有着男儿身的宝玉,当他以真心真意的体贴之情发送出去时,若此对象女儿顾忌着社会上男女授受不亲的价值标准时,宝玉的体贴之情便容易受伤了。例如,他见紫鹃在风口里坐着,穿着单薄,便一面说一面向他身上摸了摸:“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看天风馋,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他的真心意,换来紫鹃的喝叱:“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所以,宝玉是“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以上均是第五十七回)女儿的防他,让他觉得被排除在女儿世界之外,对于恨不能为尊贵品格女儿的宝玉来说,那是最委屈的事了,同理,他觉得最幸福不虚此生的时刻便是真已身为女儿国中之人,而得姊妹们的关怀、怜惜,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第三十四回)。
基本上,在女性文化的世界中,体贴与关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通交往方式,所以,此中人常常会感受到网络关系相连的美好与温暖。这份体贴与关怀,并不是所谓的得到此中人推崇的一种“德行”,而是自然而然以纯真心意出发,彼此互为主体的相濡以沫。丫鬟之间,或小姐之间倒不足为奇,而是它最难得地在不同社会等级,甚或原男尊女卑的性别阶层上被实践着。
五、结语
《红楼梦》的“女性文化”呈现了一个“审美”的生命面向,他们的存在或者是从事的活动,都带着一种当下的、偶兴的,以及充满意趣的审美性。他们也用这样的美感来观照自己与他人,所以,群聚本身并不明显地通向一个具有如传统儒家价值的目标意义。而也在这样的审美特质上,他们彼此之间也发展了一种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的“体贴”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他们构作了一个平面网络关系,彼此互为主体,当他们以对方为主体而全心挹注在对方身上时,温暖的情谊便在其中流动。
《红楼梦》的大观园所呈现的女性文化是和园子外面的父权价值是成对比的,当然此中亦有着内化父权价值较多的女儿,所以,小说在此鲜活地呈现了一个存在于父权结构现实之下的女儿文化状态,也就是说,在大观园内的女儿,并不是每一位都呈现了绝对的女性文化特色,如小姐身份的宝钗,或者是丫鬟身份的袭人,就是个例子,他们的生命价值倾向,是较接近父权名位序列层面的。但无论如何,红楼梦以宝玉、黛玉为准的女儿国所呈现的女性文化,对比着男性文化总带有较多的理想色彩,因为那是一个超越了名位阶级的人人为主体的平等关系,以及不带功利与道德价值判定的审判世界。自然,我们也可从中解读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于女性文化的向往。
收稿日期:2003-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