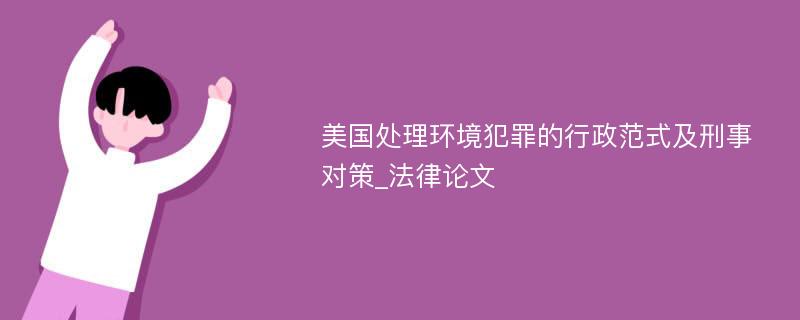
美国应对环境犯罪的行政范式与刑事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美国论文,对策论文,行政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85(2009)02-0070-07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旨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法规的行为。为了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采取法律行动却由来已久。在英格兰,《1876年迪斯莱利河流法》及美国《1899年废弃物法》,标志着以全国性立法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的开始。在20世纪最后数十年,各国立法机构均在立法中扩大环境犯罪的范围,增设罪名。在美国,1963年《清洁空气法》、《1979年资源保护与恢复法》、《1972年清洁水法》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立法,将更多有害环境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畴。
在对环境犯罪进行的多方位理论研究中,刑事法学家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犯罪是犯罪人的理性选择这一理论假设之上。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理论前提是:如果一种行政规制方案的经济成本超出预期收益,这一方案便无效率可言。尽管研究成果视角各异,但这些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环境犯罪造成经济损失,危害人类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危害达到何等程度,迄今为止尚无法确知。第二,环境犯罪的总发案率以及自然人和公司所实施的环境犯罪的比率,在各项研究中均有很大差异。相关理论和研究已经指出对环境犯罪总发案率可能产生影响的一系列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如经济状况、产业的竞争程度、违反环境法规是否会受到社会的普遍谴责以及控制环境犯罪的模式。第三,尽管世界各国针对环境犯罪所采取的措施千差万别,但在那些政令畅通、政治力量持续性要求政府打击环境犯罪的国家,对环境犯罪的控制更加有效。第四,对环境行为予以干预的最重要的机构是行政管理机构,被提起刑事起诉的案件很少。尽管对环境犯罪人施以更严厉的刑罚是总趋势,但尚无证据表明这种举措已有明显成效。第五,在对环境犯罪采取应对措施的过程中,决策者最关心的,仍然是某一区域、某一地区、某一产业的经济良性运行态势。第六,虽然对环境犯罪有加重处罚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影响范围有限。发生明显变化的,是行政管理范式,即以威慑为导向的管理范式已让位于强调教育、具有灵活性并侧重合作的针对型管理范式,而后者更能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第七,对国际环境问题予以密切关注,显有必要,它会加深我们对环境犯罪的社会背景和意义的理解,拓展我们对环境犯罪行政管理范式的比较研究,并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
一、环境犯罪的类型
以环境犯罪的特征及其造成的危害作为分类基础,可将环境犯罪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如乱扔废弃物、非法处置放射性物质、在非法狩猎期狩猎或在非法捕渔期捕鱼、故意向泄洪渠或下水道排放有害物质、盗窃动物、植物和自然资源。有些环境犯罪的被害人较少,也容易识别。如工厂排放有毒化学品,污染了邻近居民的水井,从而使水质有害健康。有些环境犯罪的被害人则多得不计其数,危害的地区广泛,危害的时间多达数年。如将有毒物质排放到空气中,并随大气流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而引发呼吸道疾病暴发,并损害地球上空的空气质量。还有一些环境犯罪可能会立即导致灾难性后果。如1984年联合卡比德公司在其位于印度博帕尔的分厂,由于工人操作疏忽致使含有甲基氰化物和氰化氢的致命性气体泄漏到大气中,导致3329人死亡,2万多人重伤。为了禁止和限制对环境有潜在危害的行为,世界各国已签署多个国际公约,如1973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7年《蒙特利尔损害臭氧层物质议定书》、2001年《斯德哥尔摩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等。
二、环境犯罪的危害及被害人
环境犯罪表现各异,危害巨大,没有人能估算出环境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多大。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失包括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失、人身伤亡及被害人心理上的创伤。环境犯罪不仅对个人和组织造成严重伤害,还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很多被归责为环境犯罪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白领犯罪,但与典型白领犯罪不同的是,环境犯罪的被害人常常不仅有人,还有野生动植物或濒危物种,而其价值是立法判断出来的。像清洁的空气或国家森林一类的公共所属物,很难判断其价值。环境犯罪的非物质性损害包括痛苦、煎熬以及生活质量下降。这类被害人或许有成千上万。有的环境犯罪行为致使整个社区的居民流离失所。环境行为危害或危及的主要是那些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社区及居民。方兴未艾的环境正义运动,便以探讨和公布环境危害的不公平分布为己任。贫穷的少数族裔居民居住的地区常常受到危险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危害。
三、环境犯罪的分布和趋势(略)
四、环境犯罪人
克林纳德与伊格对1975年和1976年由美国25家联邦机构针对477家美国最大的公有制造公司提起或审结的联邦行政、民事、刑事诉讼案件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这些公司实施的所有违法行为中,环境违法行为占29.4%,每个公司平均实施3.9起环境违法行为。有些公司多次实施环境违法行为,有些公司在这两年间却未发现一起环境违法行为。另一项针对1984至1990年间美国78家犯有联邦犯罪的公有制公司进行的研究发现,这些犯罪中有21%是环境犯罪。
(一)特征
对环境犯罪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犯罪动机与行为特征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发生在美国南部林区的纵火案件开展的研究表明,“潜在纵火者”,即那些背离乡村社区关于焚烧林木的乡俗乡规的人,他们对防火与森林保护不屑一顾,并与所在社区以外的人很少来往,难以融合到社区中。研究人员还发现,潜在的纵火者年岁较大,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性格孤僻。美国量刑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数据报告,公布了被美国地区法院定罪的环境犯罪人及危害野生动植物犯罪人的特征。这些犯罪人与违反联邦刑法的犯罪人特征迥异。表1(本文略)说明,环境犯罪人比抢劫犯、夜盗犯与盗窃犯的平均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白人数量多于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且身为美国公民者居多。在环境犯罪人中,女性仅占5.2%;但因违反联邦刑法而被定罪的抢劫犯、夜盗犯和盗窃犯中,女性占22%。由于已被定罪的环境犯罪人与未受逮捕、未被起诉的环境犯罪人的数据特征缺失,因此,两者无法比较。与其他类型的犯罪人一样,环境犯罪人在犯罪的严重程度及实施犯罪的数量上差异很大。有的研究人员将犯罪人区分为情境犯、惯犯与公司犯罪人。
有数据表明,因违反联邦环境法而被提起刑事起诉的公司的数量,多于被判犯有联邦经济犯罪的公司数量;在1988年因环境犯罪而被判刑的公司中,有42%的公司位列标准普尔指数榜,而同年因经济犯罪被判刑的公司中仅有20%位列该榜。凡世通公司对1990年至1997年间环保局325个刑事、民事及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分析,其中,被判刑的公司有53家,占16%。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都很容易成为执法目标,但却很少成为刑事起诉的对象。另外,小公司占被查处的公司违法者总数的近40%,但在被查处的刑事犯罪中,小公司占60%强。比较而言,自然人犯罪数据更加充分、可信度更高。而公司犯罪的数据则比较缺乏、可信度较低。
(二)决策
理性选择理论有助于把握环境犯罪人的决策过程。一般而言,白领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比街头犯罪人更加理智,他们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犯罪可以供其享乐,也不是因为吸毒后丧失对犯罪得失的判断和计算能力,更没有在那些青年男性聚集的场所作出犯罪决策。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提倡、实施并褒奖理性决策。白领犯罪人及其决策都受到限制,而大多数白领犯罪人都能从其有限的决策范围内自得其乐。组织中的白领犯罪人决策时比街头犯罪人更加慎重。
自然人实施的环境犯罪一般比较轻微、简单。对偷猎麋鹿和龙虾的人进行的研究,对违反捕鲻禁令的渔民及对马来西亚渔民进行的研究都表明,环境犯罪自然人通过账目和技术的使用规避法律,并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将其行为合法化的借口。在一些组织和地区,这样的账目记录和技术被广泛分享,人们对其使用持赞赏态度,认为这些行为是合法的,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过去,在美国南部一些乡村地区,人们将森林纵火行为视作对私敌的报复,或者对那些不公平对待土地拥有者和猎人的林木公司的报复。对那些遵守环境管理制度的公司决策进行的研究表明,守法成本高、市场压力大、公众压力大,以及惧怕承担环境责任是公司守法的原因。
五、民间对环境犯罪的回应
(一)公民
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影响下,人们对环境犯罪严重性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很多公民倾向于认为有些环境犯罪与某些类型的街头犯罪一样严重。1994年美国量刑委员会资助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全美公民中进行抽样调查,就多种类型犯罪的适当刑罚征求被调查者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公众一般认为那些对被害人人身实施的预谋犯罪具有更严重的危害性,并且“如果危害后果方面的证据导致最终量刑高于量刑中线,则取决于危害后果的类型”。公众认为那些故意实施的造成人身伤亡的环境犯罪属于特别严重的犯罪。
在发达国家,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另一个回应,便是侧重环境保护的政党的出现,这一现象与工业生产有关。这些政党被称为“绿党”。究竟这些“绿党”的政党组织及其组织的社会运动对环境法律、环境控制及环境守法有多大影响,尚不得而知。旨在控制和改善林木制品产业造成的环境问题的民间团体已经出现,其主要行动目标便指向实施犯罪的公司,并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联邦和多个州政府推出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环境保护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硕果。信息披露制度还可以促使政治活动家在议事日程中提高对污染的重视,间接减少污染。
《美国清洁水法》容许公民个人对污染者提起民事诉讼,从而敦促人们遵守该法的规定。对《有毒物质排放清单》中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拥有满足公民知悉权项目并为之提供雄厚资金支持的州,以及在立法上赋予公民起诉权的州,有毒物质排放率特别低。另外,癌症发病率高的社区中的居民,起诉违反《清洁水法》的公司能够成功胜诉,信息披露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二)商业组织
环保运动的成功开展及环保立法数量的增长,受到既得商业利益者的抵制。商业组织试图影响公共政策,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立法。企业对犯罪化运动的回应,便是推出“环境友好型”商业活动形式,这一“绿色管理”包括贴上生态标签,进行生态审计、生态营销、环境质量生命周期分析,改进加工工艺,重视研发以环境保护为重心的产品和工艺等。绿色企业还尽量少用自然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以便减少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在决策中将经济目标与环保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六、应对环境犯罪的行政管理范式和刑事对策
限制企业行为的各种活动均遭到贸易组织及行业组织的反对,这些组织声称,限制企业行为的法律草案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危害合法的商业利益,是大政府过分干预企业活动的不良典范。旨在保护商业利益的活动,目的是使企业的自主性免受干预。当然,政府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大多都是对大多数类型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小额民事罚款。公民与民间组织所期待的立法,最终兑现的很少,相反,与公民及民间组织的倡议相左的法律法规数量却很多。企业利益及其代表人在左右其行为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一)行政管理机构
行政管理机构构成环境守法监督的前哨,因此,这些监督官员及其工作受到公众广泛关注。而实际中执行的法律与立法者的立法初衷很可能相去甚远。对31名负责执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的渔猎法执法官进行的访谈表明,经验老到的偷猎者比执法官更加灵敏,他们对偷猎区域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对动物出没踪迹也非常熟悉。由于渔猎法执法官执法主要依靠线人举报,因此,那些不与他人谈论其行为踪迹的偷猎惯犯,比偷猎偶犯更具有隐蔽性,容易成功避开执法官的逮捕。如果能够找到行为人故意严重违法的证据,或者发现某种类型的违法行为常发,大多数司法辖区内的执法官都会将这些违法者交付刑事侦查和起诉。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的环保机构在将环境违法行为交付刑事侦查和起诉时都十分审慎。
行政执法的内容和强度因地因时而不同。例如,美国环保局下属十个辖区,将环境违法行为交付刑事侦查和起诉的比率均有差异。执法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受法律规制的企业数量的多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拥有资本集中的大型产业的地区与拥有大量小型、进行潜在流动性运营的企业的地区,就存在较大差异。行政监督的力度也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尤其受制于当地保持就业率稳定的需要。各地的检察官也同样存在执法差异。有时,由于担心可能损害该地的经济发展与就业状况,检察官对当地企业实施的环境犯罪并不积极提起刑事起诉。如果某区域失业率上升,对该区域工厂的巡查监督频次就会减少。违法工厂及周围社区的经济状况变坏时,自我报告的数量会减少,处罚的严重性则会有所减缓。
州和联邦行政执法官员进行例行的行政督查,发布违法报告,对有可能处以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的行为转交给相关机构。每年美国行政督查的到查比率都有很大波动,例如,美国环保局1998年进行行政督查23000次,创九年间新高。但到2002年,督察次数下降到17668次。大多数违法行为违反的是《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及国家污染排放消除制度设立的限制。在被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交付司法部提起刑事起诉。每年,美国环保局将环境违法行为交给检察官提起民事起诉的案件比率,均高于交付刑事起诉的案件比率。2002年,环保局交付民事起诉的案件是342起,而交付刑事起诉的案件只有250起。
对美国33个州发放国家污染排放消除制度规定的排放许可证执法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行政机构对纸浆与造纸厂富有针对性的执法活动,在整体上提高了自我报告的数量。而且,造成环境危害的石油泄漏事件数量和频次,与港口执法官的执法时间长短成反比,并与港口执法监督的类型、执法行动的可预知性及对目标违法者的执法方法有关系。研究还发现,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与执法监督的频次有关。
根据联邦环境制定法,公司、公司管理者及雇员均可承担法律责任。1991年,违反联邦环境法的被告人中,有80%是公司。到1995年,公司仅占联邦环境犯罪被告人总数的20%。对行政执法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表明,违法者的违法程度及其政治地位的高低,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环保局对小型公司的处罚有轻有重,处罚轻重程度的依据,主要是犯罪人从违法行为中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的大小及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行政监督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政治力量对违法者有更大的影响力,这表明社会需要联邦执法者的存在,也表明联邦执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调查机构
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法的执法职责由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分担。除最简单的环境犯罪以外,地方警察和检察官通常不具有处理和调查环境犯罪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资金支持。复杂、繁琐、疑难的环境犯罪需要州或国家委派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帮助处理。很多环境犯罪都很复杂,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机构及法律执行机构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执法人员共同组成特别工作组来进行调查与处理。
在美国,联邦环保局与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法律执行机构联手协作,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在联邦一级,对环境犯罪的调查,主要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的环境犯罪类型包括有害废物的非法处置、将污染物非法排放到水体里、将法律限制或禁止的化学品非法进口到美国境内、擅自篡改饮用水供给线路、邮件诈骗、电话诈骗、共谋及与环境犯罪有关的洗钱行为。
除了警察与行政执法官转交的环境犯罪案件以外,关注环境污染破坏情况的公民,也可以向侦查人员举报环境犯罪案件。在有环境违法行为的公司中工作的雇员也可以成为秘密举报人。2002年,一艘丹麦油轮上的船员将油轮漏油一事,向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根据他们的报告,美国海岸警卫队不仅发现油轮漏油,而且发现该运输公司的管理人员命令手下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风声。根据联邦制定法,秘密举报的两个船员得到奖励,奖金数额为该案被判刑事罚金总额(25万美元)的一半。2003年1月,美国量刑委员会发布新的量刑指南,进一步加强对内部举报人的保护。
当侦查人员对各种来源的举报进行调查时,他们面对的常常是多种多样的行为,有简单易处理的行为,也有涉及很多人的复杂疑难案件。由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具有隐蔽性,因此侦查人员在判断谁是责任人、谁是参与人、犯罪如何发生时,很困难,因此,抗制犯罪的一般执法手段用处不大,用于侦破有组织犯罪的措施则用处很大。秘密侦查、线人举报、警察圈套等都能派上用场。至于在调查犯罪如何发生、哪些人参与犯罪过程中,为了从知晓内情的参与者那里获知案情,侦查人员也会使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因此,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人很可能不会被处以重罚,他们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及其提供的案情,使他们在与行政执法官及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时常常处于有利地位。
(三)检察官
对环境犯罪人提起刑事起诉的数量很小。美国1899年《废弃物法》禁止人们在可航水域处置废料。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检察官总共起诉了25起违反《废弃物法》的案件。在1981年,美国环保局和司法部均成立了环境犯罪处,在随后的30年中,刑事起诉的数量有所增加。2002年共有484起环境犯罪案件受到刑事起诉,每年受到刑事起诉的环境犯罪案件均不超过636起。
检察官查处公司犯罪案件时,尤其关注该罪对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及其程度,关注是否有实施多起犯罪的证据,该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在受到行政警告与罚款后该公司是否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起诉的因素有:犯罪人是否自愿坦白其违法行为、犯罪人与执法官员合作的时间及程度等。另外,公司是否已制定预防措施、是否存在守法计划、是否业已形成违法氛围及此前是否有过因违法行为而受到处罚的记录,也在考虑之列。原来,受到起诉的多为公司雇主,近来多起诉公司管理人员,或者将雇主与管理人员一并提起刑事起诉。1983年至1990年间,联邦执法机共对703起环境犯罪提起刑事指控,其中有70%指控的是公司中的自然人,而对自然人提起的刑事指控中,有52%指控的是公司总裁、公司雇主、公司副总裁、总监及其他管理人员。
1983年至1991年间,共有571家公司被判犯有环境犯罪,其中多数案件发生在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公司被告人与自然人被告人的年度分布差异很大,例如,在1991年,被告人中有80%是公司,而1995年,只有20%是公司。其中缘由尚不清楚。在英国,从1984年至1990年间,因环境犯罪而被提起刑事起诉的被告人,有10%至15%为公司,其中,有88%的案件以公司作有罪答辩而和解结案。
(四)法院与法官
执法机构查处的环境犯罪,很少进入到刑事审判程序中。根据《美国量刑指南》,环境违法行为依其严重程度分为四种类型:明知危及人身安全、非法处置有害或有毒物质、非法处置其他污染物及危害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环境犯罪人尤其是实施环境犯罪的公司,可以以所受多项指控中的少量犯罪为代表进行有罪答辩。
1988年至1996年间因触犯联邦刑法而被判刑的公有公司的数据表明,在所有案件中,环境犯罪约占20%。《美国量刑指南》于1991年被修订以后,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加重了。例如,1998年至2001年间因故意犯罪而被判刑的公司中约有25%实施的是环境犯罪,但所判之刑多为罚金或赔偿经济损失,而其被处财产刑的数额,比实施经济犯罪的白领犯罪人所受财产刑数额少得多。
尽管近年来惩罚的力度有所加大,但对刑罚的威慑效果持续进行的微积分学研究表明,对刑罚确定性的畏惧比对刑罚严厉性的畏惧更强烈,前者的威慑效果更好。但查获和惩处环境犯罪的确定性程度,迄今尚无法了解。究竟近年来对环境犯罪的关注不断升温是否会受到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对环境犯罪的密切关注是否会长期持续下去,尚不清楚。但联邦政府因忙于反击恐怖主义而大大减少了此前用于控制环境犯罪的各种资源。
与行政处罚及民事处罚相比,违反环境法的自然人更容易受到刑事处罚。小公司受到行政处罚及民事处罚的数量,是大公司的7倍。受处罚的犯罪人多数为中层管理人员,仅有少数为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触犯联邦刑法的自然人被判处的刑罚有罚金、缓刑或监禁刑。1983年至1989年间,自然人因触犯联邦环境刑法而被判处的平均罚金额均未超过5000美元,被判处的监禁刑平均刑期从5天到11个月不等。
七、变革中的环境犯罪控制范式及环境守法行为
研究人员依据犯罪控制理念的差异将用于控制公司行为的方式和策略即“控制范式”划分为不同类型。控制理念是指人们对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特征、公司实施环境犯罪的原因及尽量减少环境犯罪发生的适当策略的总体认识。
(一)威慑型控制范式
威慑型控制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认为公司行为人具有自治性,他们精于算计,但对公众福利无动于衷。由于他们仅关心公司利润和个人权势,因此需要使用权力对他们施加限制,而这种权力通常就是国家的强制力。要使公司在运营中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就需要对其施加严格、严密、具有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在威慑型控制范式之下,占主导地位的法规是命令控制式法规,主要方式是威慑、监督,对违法行为施以机械性处罚。
命令控制式法规所具有的对抗性特征,在某些产业、某些部门已引起执法对象的不满,使执法对象丧失对执法者的信任,激起他们对执法的抗拒,从而提高了监督成本,削弱了执法成效。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执法权力的联邦法律,使得“威慑型控制范式”得到支持并占据支配地位。
(二)灵活执法与针对型控制范式
20世纪80年代,“威慑型控制范式”不再得到官方支持,迅速衰落。里根政府拒绝采纳威慑思想,大量减少各行政管理机构中执法官的数量。联邦职能受到削弱的同时,行政管理职能被大量转移给州级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公司的自我管理。
针对型控制范式“是指针对管制对象的不同动机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控制,在提高公司守法程度的执法活动中采取灵活的执法措施”。针对型控制机制侧重对行为人违法行为背后的问题、动机和背景情况进行考量。大量违法行为的发生是因为行为人忽视了法律的要求,而非故意为之。针对型控制范式的基本理论前提在于认为多数公司都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和控制,外部监督越少越好。政府管理官员对这些公司应公平对待,在他们守法出现困难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执法重点放在对公司进行法律培训上,帮助公司努力守法。而那些主要依靠威慑和机械化施加处罚的执法策略便不再受到重用。如果企业在接受培训并得到帮助以后仍然实施违法行为,执法官员便对其予以严重警告,并给以相应处罚。尽管施以重罚的使用率非常低,但执法官在必要之时一定会动用重罚、会对实施严重犯罪或屡次犯罪的公司施以重罚,促使企业尽量守法。针对型控制范式使执法官在执法方法上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可以自愿协助公司守法,也可以处罚违法公司,两者都是合法的执法行为。
很多管控手段都与针对型控制范式具有制度上的可容性,如寻找违法目标、对目标公司进行检查、处以罚金、执法重点是私营公司等。美国海岸警卫队为防止发生漏油事件而进行的巡逻,比为缩小漏油范围而进行的随机船只抽查更见成效。执法官员在执行环境法时采取与企业合作的举措也受到批评,有人担心这种执法举措会为公司在其必须接受的监督的性质和力度上施加更多影响而大开方便之门。
八、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技术变革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环境犯罪可能危及的被害人群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新技术和跨国公司的增多,还加大了环境犯罪的控制难度。到境外投资建厂的公司在经营管理中规避所在国法律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犯罪控制的难度。很多国家之所以能够大量引进外资,就因为外国投资者看中了这些国家具有劳动力廉价及行政管制松弛的资源。跨国公司对所在国规定环境标准的法律制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使该国法律中环境标准的确定有利于跨国公司。
环境犯罪控制领域中最突出的变革,是从威慑型控制范式转向其他控制范式,即合作型、灵活型执法模式。对公司进行非政府的环境守法控制是目前不断发展的趋势。“公司自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积极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当然,威慑型控制范式与灵活执法范式究竟孰优孰劣,争论还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