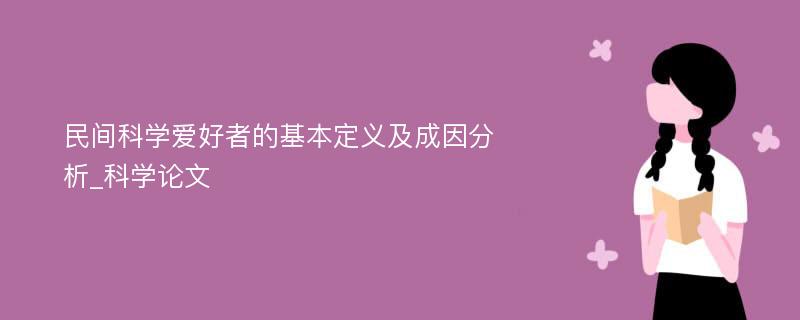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爱好者论文,民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专业科研的补充,予以鼓励和支持;有人认为他们行为无益,但精神可嘉;有人认为他们精神不正常,表示同情;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伪科学,予以批判。专业科研人员普遍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工作毫无价值,他们的来信来访对于专业机构的正常工作是一种干扰。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什么会有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在中国出现?涉及到公众、科学与社会的诸多关系。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科学社会学问题,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
1 什么是民间科学爱好者(注:民间科学爱好者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建立在以下资料之上:a.大众传媒的公开报道;b.笔者收集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自己印制的材料。c.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直接或间接交往。)
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注:对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相对于科学共同体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作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给出结论,不作具体讨论。)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注: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具体人数难以估计。根据中科院数学所的估计,单是哥迷就有几千人之多。),几乎所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话语地位的科学领域都有他们的存在。在数学领域,他们热衷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等等尖端问题——这也是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1],直到今天,中科院数学所每年还能收到几麻袋声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和文章。在物理学领域,他们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注: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宋正海研究员组织的“天地生人”系列讲座上,曾做过“相对论争鸣”系列讨论,并于2000年7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研讨会,还出版了论文集《相对论再思考》(宋正海等主编,地震出版社,2002年7月)。)、量子论,或者提出新的宇宙论体系,还有一些人研究永动机。在生物学领域,有人试图提出新的进化论体系(注:其中最知名的是提出人类体质进化新说的朱海军,他认为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人类的祖先采取了面对面的性交体位。)。此外,在地学、心理学等科学领域都不乏其人。有些人的理论庞大无比,从宇宙起源到阴阳五行,从饮食起居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包,已无法归入具体学科。
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心理特征、行为方式、文本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共性。归纳起来,他们最核心的心理特征是偏执。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与世俗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生活在幻想的情境中,比如他们不能平实地理解他人的言论,会忽视对其不利的部分,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比作布鲁诺和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他们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成为一代大师,这种信念使其困苦的生活镀上了一层光辉。
民间科学爱好者推广其“学术成果”的方式大体如下:①写信、上访(对象可能是学术机构、学术杂志、大众传媒、各级官员);②直接演讲(通常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场地);③自费出书;④自建研究所(注:如提出地球抛月学说的冯宜全,就在唐山自建了一个地学哲学研究所。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的一版刘学斤文章《冯宜权,一个人的“学说”》。);⑤上网。
他们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些共性:①新名词极多,且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体系没有多少关系;②逻辑混乱,不知所云;③常常夸大结论的意义;④喜欢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⑤常常把结论建立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建立在现有科学不成立的可能性上,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可能被自己引发的未来的科学革命上。
此外,从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
由于民间科学爱好者所具有的共性,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
目前学者及大众媒体对这个群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有人称之为“民间科学家”或“业余科学家”,他们也愿意如此自称。本文作者称之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这个命名自1999年开始见诸媒体[2],已被部分学者和媒体接受。最近,刘华杰博士发明了一种新的称呼,“江湖科学爱好者”,有更多讥讽的意味,但也凸显了他们的某些特征。
一般而言,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工作不属于伪科学,顶多属于“科学向度的伪科学”[3],或者郝柏林院士所说的赝科学[4]。因为伪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也有学科范式,甚至有“学术刊物”。而民间科学爱好者都各自为战。另外,通常所说的伪科学都是产生了严重社会影响的以经济或者政治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这也与之不同。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成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有干部、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普通农民、工人,甚至有社会高层人士(注:级别最高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大概是政协委员黄维,他一直热衷于设计永动机。参见:金源,《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年龄范围也比较宽泛,年龄最长的哥迷有七十多岁,但是大体上有一个下限,一般不小于三十岁。
2 民间科学爱好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差异
命名也是出于区分的需要。表面上看,民间科学爱好者(science fans)与另外一个人群有很多相似。这些人也不是专业科学工作者,也喜欢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活动,甚至有些人也很固执,但是他们接受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能够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并能够做出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这些人可命名为“业余科学爱好者”(science amateur),他们才是真正的业余科学家(amateur scientists)(注:关于两种科学爱好者的英译,曾在“虹桥科教论坛(www.rainbow.erg)上有过讨论,致远,离乡俗、微结构、PHpig、二蒙、烁泯、XYPS、老五等网友提供了可贵的建议和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从字面上看,“业余科学爱好者”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词义有很多交叉,甚至难以区分。这里不准备把它作为一个语文问题详细辨析,而是直接命名。
业余科学爱好者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所从事的学科范围也很广。比如有很多天文爱好者,他们用业余时间观测天象,也能够发现新的天体(注:2002年2月3日,国际天文学会小行星彗星中心就把一颗由中日两国的业余天文爱好者张大庆和池谷熏分别独立发现的新慧星命名为“池谷—张”。张大庆是河南开封的一位普通工人,这颗彗星他是用一台自制的20公分口径光学望远镜发现的。),但他们并不想推翻现有的天文理论,也不期望创建一个全新的宇宙论体系。
业余科学爱好者并没有成为特殊人群,而是社会的普通成员。
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业余科学家好者与科学共同体有着正常的交流,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有时也十分频繁,这和业余棋手与专业棋手的关系非常相似。而民间科学爱好者不但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交流,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同样是“哥迷”,每个人都构建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读懂他的体系,而不愿也不能读懂别人的体系。所以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一个集体,只是一个集合。
3 1980年代的社会氛围:苦行、牺牲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
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其他国家也有存在,拉德纳所说的科学狂想者[5]就属此类。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规模则属罕见。如果我们把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别产生归结为其个人原因,则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大规模出现必有其社会原因,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令人困惑。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几乎没有物质追求,常被视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们这种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苦行和牺牲精神从何而来?需要从他们受教育的年代寻找答案。
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化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比如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等等),为此,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并且应该牺牲的,是谓献身。不单邱少云、黄继光这些战时英雄,和平年代的英雄如向秀丽、欧阳海、罗盛教等也大多与牺牲有关。当不足以牺牲生命时,就强调对物质生活的牺牲——“苦行”。所以有对大庆人的先生产,后生活的赞颂。在这种语境中,苦行与牺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识形态价值。反过来,苦行与牺牲的决心与程度,又成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纯粹的标志。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姿态与这种语境正相一致。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孟子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民间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并无二致。因而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表观下,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
苦行本来是达成理想的手段,但是,当理想遥遥无期,苦行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为其依然拥有理想、拥有崇高精神的证明。这使他们能够在生存艰难的状态下,保持着强烈的精神优越感。
然而,为什么是科学,具体而言,为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科学领域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献身的对象?
从五四运动开始,科学的地位日渐提高。1949年之后,唯科学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科学常用作形容词,代表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6]。投身科学事业一度是广大青年的美好选择。然而在文革期间,虽然“科学”这个词仍然具有意识形态价值,但具体的科学工作和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负的意识形态价值。这时,科学已经不能作为实现“争光理想”的手段。
1976年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科普类杂志、期刊有了将近十年的繁荣,其中一种现已停刊的杂志的刊名很能体现当时的时尚——《我们爱科学》。甚至在1980年前后高中文理分科时,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视——只有理科学不好的人才会去学文科。
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哥迷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数学本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有史以来都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然而,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背景的纯粹的科学家成为传主,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陈景润立即成为公众人物,直到逝世,都是传媒关注的对象。然而,“使徐迟、陈景润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难以数计的中国人加入了证明这一猜想的行列。他们都想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7]如:
今年53岁的刘平危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了,但因喜欢数学,便到处找书看,1970年,因风湿病加重不能上班,便投入到数学研究中。1978年,他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萌发了要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8]
又如:庄严是辽阳市1968年初中毕业的下乡青年,1976年返城后当过多年的装卸工。1978年,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冲击,完成了“1+2”,震撼了世界。庄严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染,时年27岁从小也特别喜欢数学的他顿时热血沸腾,剩下这一步之遥,他也要试试,为国争光,把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摘下来![9]
长期以来,对哥迷及其他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正面报道在大众传媒上时有出现,上面所引只是其中之二。对这些文本可以做多重分析,从中不仅可以获得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信息,还可以看到作者和受访者是以何种方式理解科学活动的。因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夸张、改写,这又为我们分析其中深层心理留下了线索。
陈景润的一夜成名,哥德巴赫猜想的简单表述,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崇尚,都使很多具有争光理想的人开始了摘珠之梦。当然,最后成为铁杆哥迷的大多是那些有偏执倾向的人。
那么,为什么只有初中文化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会认为自己有可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唯科学语境是在公众科学素养很低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形成的,因而公众对于科学活动并没有基本的了解。文革期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的口号充斥大众传媒,贬损科技专家的故事层出不穷。甚至卫星上天这样的科技成就也被宣扬成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传媒上的功臣更多的是劳动模范,科技专家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现。长此以往,科学研究便不被认为是一项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才能从事的事情。
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言谈和文本中,可以看到他们思想中的时代烙印。一位哥迷在2002年3月给本文作者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民间是科技的源泉,大从(众)是科技的主体,小人物是可有所作为的,可以弥补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发挥小人物的优势作用而不能抑制他们的创造性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所必需。”从这些话语可以联想到很多当年的口号,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干快上。”等等。下节还要说道,很多人的确认为,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方式来完成。
如上所引,很多对哥迷的报道都有这样的叙事模式:某某人看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被陈景润的精神所感染,决心为国增光,不顾自己只有初中毕业,也要去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种模式使我们看到,哥迷等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目的首先为国争光,摘取明珠不过是实现其争光理想的手段。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问题在数学上具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关心。
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
综上所述,民间科学爱好应该满足两个条件:①受过理想主义教育,有牺牲与苦行的精神动力;②经历过1980年代中国科学的春天,能够把科学作为献身的对象。由于最后一批受过理想主义教育的一代出生在1970年以前,1968年出生的朱海军基本上是民间科学爱好者年龄的下限。
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导致①大众语境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日益淡化;②经济、法律、管理等人文学科以及某些实用类工科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理科则大幅度下降。这时,民间科学家爱好者大批产生的社会氛围已不复存在。即使仍有兼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献身的对象也不再是科学了。
出于类似的原因,1980年代曾产生规模更大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又在1990年代迅速减少,现在只留下一个已经带有讽刺性的称谓:文学青年。
4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知识背景及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
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他们是如何了解所研究的领域的?他们的科学知识来自何处?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又来自何处?
根据大众传媒的报道及其自述,他们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中小学教育;自学;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由于文化革命,很多四十岁以上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连中学教育都不完整,这样的知识基础使他们的自学也有很大的局限。因而,民间科学爱好者理解科学、了解科学的最重要途径其实是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
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很少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偶有涉及,也常和大众传媒一样,给出某些模式化的描述。比如,科学家的经典形象是身穿白大褂、秃顶、戴眼镜、和和气气、全知全能的老爷爷,他们德高望重,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科学献身,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这种模式已经具有了某种原型的特征(注:原型,荣格心理学的概念,指某种类型化的无意识的思维方式。),成为传媒及受众潜意识中思维方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徐迟所描述的陈景润也是这类形象的变形。当然,它与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同样表现了对苦行与牺牲的尊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民间科学爱好者正是按照大众传媒和科普书刊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自我塑造的!
在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中,也存在类似的原型。“灵机一动”和“铁杵成针”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
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有很多科学天才灵机一动或者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比较著名的有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浴缸、瓦特的水壶,还有凯库勒的梦。与此相对的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类的故事,最常说的是“六六六”,说发明人经过了665次失败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故以此名之。(注:实际上,六六六的名字取自其化学分子式,与实验次数无关。)居里夫人从沥青中百炼成镭的故事也被归入此类,这类故事符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民间格言,也与苦行和牺牲的精神相吻合。
前一类故事把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与机遇,简化为拍脑门出点子。后一类故事强调了培根式的归纳法发现模式,因其忽视了深层的在先的理念,使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这两类故事都含有对科学活动的某些误读,甚至其个案也为科学史学者所质疑[10]。但这种叙事模式或因其富有戏剧性,或因其符合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这类故事不断产生,不断流传,已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种大众语境之中,民间科学爱好者激起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传媒工作人员在一篇支持哥迷的文章中写道:
数学家陆柱家说得好,陈景润去世后,哥氏猜想在采用新方法之前,是不可能被证明的。那么,有些复杂问题换一个方式思考,也许就变得简单。所谓“新方法”,不就是改变思路吗?我们至少应该关心有没有人试图利用“新方法”证明这个问题。”[11]
这正是铁杵成针、灵光一现的模式。作者相信哥迷的“思路”具有科学价值,所以大批哥迷就有可能碰上正确答案。仿佛哥德巴赫猜想是埋在山上的一个宝藏,只要有海底捞针、铁杵成针的精神,就可以找到。又仿佛是一项寻宝竞赛,所以要赶在外国人的前面先挖出来——为国争光。而在媒体的描述中,科学活动有时的确很像是体育比赛——一场在很短时间内决出胜负的具有可观赏性的活动。
这样,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与某种意识形态背景结合起来,就造就了轰轰烈烈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苦行与牺牲为其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的价值,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之类的叙事原型为其行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合理性。民间科学爱好者一面年复一年地打磨铁杵,一面期待灵光降临。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科普同样接受了,甚至强化了这种误读。
时至今日,这种语境依然存在,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肯定,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使得民间科学爱好者常被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很多人即使在表示批评时也要强调,他们的精神是好的。科研机构也不愿直接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委婉地推托。相反,民间科学爱好者及其同情者则常常理直气壮地指责科学共同体在打击人民群众爱科学搞科学的积极性。
5 结语
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科学与公众的沟通出现了某些障碍,意味着传统的科学传播出现了某些问题。尽管大规模产生新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总体社会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大众传媒以及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仍在继续。因而,对这一人群进行研究,既有利于解决与之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也能够为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某些借鉴。
收稿日期:2002-03-03
标签:科学论文; 哥德巴赫猜想论文; 大众传媒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数学论文; 陈景润论文; 苦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