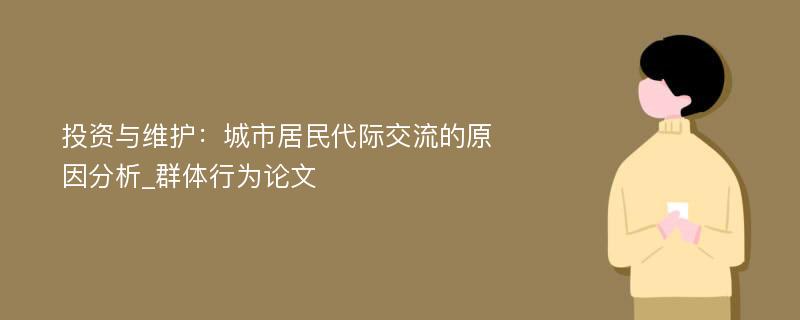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果论文,城市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长者特别是男性长者所居地位之显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家庭内部以年龄和辈分为标准的严格的等级划分,男性家长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直接干预,子女对母亲强烈的感情依附,对赡养老年父母的尽心尽责,以及人们对扩大家庭的偏好,所有这些主题都曾被用来描述长久而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体系,亦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长者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参见Fairbank,1986;Yang,1945;Yang,1959;Fei,1939;费,1985)。
传统家庭中长者权力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家庭财产的控制,以及绝大多数家庭在以往既是消费亦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由于奉养和服从父母的孝道被赋予最高的道德意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扬,加之数千年间国家科层体制各层机构的全力支持,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对成年子女拥有强有力的支配权。此外,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宗族组织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深受儒家道德观念熏陶的绅士阶层手中,这种情况也起到了维护长辈权威的作用(胡,1988)。与此相对应,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能够向“长老统治”(费,1985)之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价值系统。正如C.K.Yang所言:“在传统社会秩序下,(人们)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想像力才能成为不孝之子”(Yang,1959:89)。
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生活。延续上千年的皇权帝制被推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由此失去其统治地位。在城市中,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大降低了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而也去除了长者所赖以运用权力的物质基础(Whyte and Parish,1984)。换言之,产生以及维持以“长老统治”为特点的旧式家庭秩序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结果则是家庭中长者的权力和权威被大大削弱了。
但是,家庭内部长辈权威的减弱似乎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大量的个案性研究认为,老年父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无论是住在一起或是分开居住, 仍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见 Davis-Friedmann,1991;Unger 1993,袁,1987;潘、林;1987)。近期大规模的定量性社会调查表明,尽管在城市里大多数老年人有他们自己的收入,但半数以上的人仍然获得来自儿女的帮助(CRCA,1994)。此外,城市各个年龄组的绝大部分人仍旧认为照顾老人是最重要的家庭职责之一(Wang and Chen,1996)。换言之, 尽管城市中大部分老人有维持经济独立的能力,但成年子女的帮助仍然是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家庭中长者权威的削弱对子女抚养老人这种养老方式几乎没有影响。这便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怎样的一种社会机制使得两代人之间能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家庭养老的模式得以延续?在老年父母所拥有的经济权力、道德权威以及国家予以的政治支持与其前辈相比都大大降低的今天,为什么大部分老人仍能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亦即老人们以何种方式保持与其子女持续的交往,从而在整体效果上产生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家庭养老模式?
本文试图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所提供经济和服务上的帮助的关系,并据此对上述问题做出部分回答。此外,根据对在河北省保定市所做的一项抽样社会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本文还试图就当代中国都市的家庭养老机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二、养老的家庭策略有助于维持家庭养老制度的结构条件
虽然中国在20世纪的政治与社会再组织,迅速的工业化,以及政府为使大众建立公民意识所做的努力,在客观上打破了传统家庭生活的旧秩序,但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经历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中国家庭行为的效果。例如,以“文革”为代表的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使得大多数人退回家中寻求安宁与信任(见Chan et al.,1984)。在经济改革之前, 面对体现为诸如基本生活物品的定量供应,严格的户口制度,以及人们对工作单位的高度依附的城市科层制对市民生活的严格控制,许多人学会了利用家庭和亲戚联系来对付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小至购买供应定量之外的日常用品,大至将下乡的子女从农村调回城市。因此,在城市生活中,家庭仍旧是一个高度团结的,其成员据此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社会群体(见Whyte and Parish,1984;Whyte,1995)。此外, 大大改善的公共卫生条件,对迁徙的严格限制,以及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住房紧张情况,也为大量以三代同堂为特征的扩大家庭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和人口条件。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反而帮助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意识的延续(Davis and Harrel,1993)。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与亲子关系在家庭中的界定和维持紧密相连。因此,巩固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联系和强化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可以用来解释家庭养老制度的延续。但是,这种结构性解释对家庭养老制度的延续仅做了一个不完整的回答,即它只对老人继续依赖子女以求晚年安定的倾向做了解释,而对老年父母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的,以及子女何以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仍然乐于照顾自己的父母,未能直接的回答。
在父母权威由于子女的经济独立和孝道意识弱化而大大减弱的情况下,父母将不得不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成年子女交往。那么,父母采取何种策略实现子女养老的目的呢?
老人的三种策略
从父母的角度讲,为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有三种可使用的策略:(1)以远期的利益,例如财产继承权,把孩子吸引到自己身边;(2)与子女交换服务;(3)强调代际间家庭利益的统一性(Lee et al., 1994)。因此,从理论上讲,子女赡养父母这种资源转移的实现,可以是因为子女从长远角度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回报;或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使父母和子女双方均受益的等价交换;或者是因为子女出于家庭责任感,而并不希图任何经济上的补偿。
这三种解释皆有其道理。而本研究所关心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老人们最有可能采取何种方式以确保晚年的安定。可以想像,对丰厚遗产的期待可能会促使成年子女对其老年父母倍加关怀。但这种解释对中国城市的代际关系基本不适用。因为绝大部分城镇老年居民没有很多的财产可作为与子女讨价还价的资本。
关于第二种以交换获取经济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父母与子女相互支持的调查证据。如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1年至1992年对天津、杭州、无锡所做的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老人帮助过子女照顾孩子(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90—91)。如果我们假定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有助于子女照顾老年父母,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子女住在属于父母名下的住房,以及当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时往往是母亲在操持家务这些事实, 说明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也从父母处得到了大量的好处( Davis-Friedmann,1991)。因此,就实际的帮助而论,在扩大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帮助,而这种相互帮助从表面上看类似于一种等价交换。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相互帮助是否真正意味着父母与子女间在进行等价交换,或者说中国的老年人是否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作为养老的保证。首先,父母和子女的相互帮助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它说明即使在短时间内,代际之间的资源转移可以是双向的。换言之,看起来似乎是等价交换的相互帮助,在性质上并非等同于市场中所出现的交换。再者,短期性交换行为意味着交换双方均拥有一定价值的物品以从对方换取好处。而对老年人来讲,他们恰恰是在最缺乏回报能力的时候最需要子女的帮助。如果代际之间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高龄或羸弱的老人则几乎不可能从子女那里获得帮助。因而,等价交换的策略,即通过即时服务以换取儿女的帮助,对大多数老人来讲,其前景是十分黯淡的。
因此,无论养老提供者是国家、地方福利机构还是以子女为代表的家庭,老人在晚年得以保障的关键在于确保老人在失去回报能力时仍能得到养老提供者的无偿服务。就家庭养老而言,如果我们假定父母和子女关于养老有不成文的“协约”(Lee et al.,1994),那么,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子女在老人晚年时能忠实履行这一“协约”。
父母投资、群体团结与一般性互惠
父母所能采用的第三种策略是强调代际间家庭利益的统一性。那么,父母是怎样通过这种策略以确保“协约”的长久有效性呢?
有两种观点,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一种视家庭为自愿性的社会群体,另一种强调连续性的社会关系对资源交换的制约和影响。自愿性群体能够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群体内部有足够的共同生产的产品以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在这种群体里,人们为生产共同产品所进行的活动在规范层次上体现为他们对该群体的义务;为分担生产共同产品的费用,履行所规定的群体义务便成为能否享用共同产品的条件。根据Hechter的观点, 群体团结的一个操作化定义是群体成员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能自觉完成自己的群体义务(Hechter,1987)。 换言之,当一个群体对其成员有广泛的义务要求,而用于直接补偿的费用又很低时,这个群体是一个团结的群体。另外,如果我们假定每一个群体成员都具有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那么,当其成员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仍能自愿完成他们的义务时,即说明他们所享用的群体共同产品的价值超过了承担义务所花费的费用。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要使群体成员在没有直接补偿的情况下履行他们的义务,也就是说,要增强一个群体的团结,则其成员所享用的共同产品的价值必需要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以使他们在群体中的受益高于所承担的义务。
家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愿群体。例如,子女在家庭中最初的成员身分的获得显然不能用自愿来描述。但就成年人能够放弃其家庭成员身分的意义上讲,家庭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愿群体。这一点就有关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来讲,尤其适用。当父母把赡养老人作为子女的一项重要家庭职责这一信息,通过多年对子女的教育和训导,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子女之后,无偿地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便成为子女在家庭这一群体中的义务。而为保证家庭义务的履行,重要的一点便是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及子女对父母家庭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依此推理,当子女年幼,父母仍扮演抚养者的角色时,家庭团结或凝聚力的形成和保持则取决于父母对整个家庭的奉献。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的这种奉献具体化为他们对子女的投资。
至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群体义务这一概念的作用。在视家庭为自愿群体的概念框架中,群体义务起到了联系投资和养老两个概念的中介作用。换言之,父母的投资对以后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群体义务观念的建立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当赡养老人不再是明确规定的家庭义务时,投资与养老之间的可能的因果联系便不复存在。现代西方家庭的家庭行为可为其佐证(费,1988;潘,1985;Goode,1963;Hajnal,1982;Shorter,1975)。反之, 如果父母希望在自己年老时能够得到子女的帮助,那么驱使父母为子女奉献的动力,除了普遍存在的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情以及责任感外,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功利的因素。
根据这些讨论,并考虑到养老为家庭职责的观念仍在中国家庭中广为流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此外,假定养老的责任在子女间并非完全的平均分布,那么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也会有所不同。
另一种观点以父母与子女的社会关系为讨论起点。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抑或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均涉及资源在代际间的转移。而依此种观点,双方之间的某次物质交换通常是连续性社会关系的一个短暂的插曲。物品流动的性质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Sahlins,1972)。但是,物品交换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又是双向的:不仅社会关系决定了物品交换的特点, 资源的转移也反过来认定、 强化或者改变社会关系(Blau,1986:112—114)。因而,与连续性社会关系相伴随的,是双方之间持续的社会交换过程。根据古德诺的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有回报趋向的看法(Gouldner,1960),此交换过程在一般情况下由互惠原则所支配。
但是,互惠并不一定总是平衡的,即一对一的即时交换。 Sahlins认为互惠的交换过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由所谓“一般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原则所指导。根据Sahlins的定义,一般性互惠行为指目的不在于即时报偿,而是为了帮助受惠者的物品交换。此外, Sahlins 认为交换的模式是由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所限定的:社会距离愈近, 物品交换则愈有可能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所指导(Sahlins,1972)。因此, 由于资源流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亲密的社会关系意味着资源流动是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所指导;而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支配的资源转移也会使社会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很显然,我们难以将父母和子女间的资源流动描述为平衡的交换。父母和子女间的年龄差别这一生物学事实,决定了子女在年幼时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回报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当成年的子女在为已进入老年的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时,父母与子女在几十年间的资源交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交换。而由于这种交换在时间上跨越了几十年,它便只能是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所支配。勿庸赘言,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子女作出大量的感情以及物质资源上的奉献,而那些希望在晚年得到子女照顾的父母为子女奉献并从而保持与子女亲密和持久联系的动机力量则会更强。故我们可以推测,表现在经验事实上,父母的投资和子女赡养老人的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至此,通过从以上两种不同思路的讨论,我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所遵奉的家庭养老的传统,以及目前有助于增强家庭团结的结构条件的影响,可以想见,在老年父母心目中,以子女赡养老年父母为特征的家庭养老,即便不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可行并且可靠的方案。那么,要提高这种方案的可靠性,父母除了增强家庭的团结,建立与子女坚固的感情联系以强化养老责任的道德约束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具体努力,就是为包括子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做出尽心尽力的服务。
三、数据与变量数据
本文的经验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94年对保定市老龄化及代际关系的社会调查。这项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及美国密执安大学合作完成。老龄化和代际关系是此项研究的两大主题。调查的基本计划是,首先根据多阶段、等机率的抽样设计,对保定市50岁以上的居民作访问调查;然后根据简单随机抽样选出每个被访人的一个居住在保定市的子女,再作访问调查。具体访问调查完成于1994年夏季。调查后所得有效父母样本为1002人,子女样本为753人。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拒访或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访问,未能对子女样本中的22人的父母进行访问。下面的分析只采用了父母也被访问的子女样本的数据。因此,此项研究使用的实际子女样本为731人。
变量
在访问中,被访子女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对父母提供各类帮助的问题。这些帮助包括个人照料、做家务以及现金和实物上的帮助。关于个人照料和做家务(其中包括帮助父母购物、做饭、乘车以及安排家庭财政),被访人被问及是否正在为父母提供这一类的帮助。关于现金帮助,被访人被问及是否定期给父母钱。关于实物上的帮助,被访人被问及是否在前一年给父母送过礼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下面所叙述的统计分析中的因变量。以年龄分组的对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给出。
表1. 子女为老人提供的养老帮助(平均值和百分数)
被访问的老人的年龄
总样本
50-59 60-70 70+
为老人提供的养老帮助
个人照料(%)
18.5 29.4 42.6 25.9
家务(%)
57.6 55.0 72.2 58.6
现金(%)
37.8 43.7 53.1 42.1
每月所给予的钱数(元) 109.9 67.7 56.2 84.8
(91.9)(68.7)
(47.1)
(80.6)
前一年的实物帮助(%)
54.2 71.8 73.3 63.3
实物的现金价值(元)
337.4 399.2391.7372.7
(327.5)
(429.0) (492.8) (402.2)
个案数(n) 358
269 104 731
资料来源:1994年保定调查子女样本。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方差。
父母投资指父母为子女所做的各种帮助。在这里用来测量父母投资的变量可大致分为3组:(1)早期家庭帮助;(2)较近期的帮助; (3)至访问调查时仍然予以的帮助(见表2)。
表2. 解释变量的平均值或百分比分布
被访问的老人的年龄
50-5960-70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1.19 1.13
(0.87)
(1.04)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元) 3 860.7 2 458.8
(5 864.6)(3 811.0)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23.7 43.1
高中或同等学历(%) 57.2 38.6
大专及大学以上(%) 19.0 18.2
婚后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 31.6 43.5
未与父母同住(%)68.4 56.5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42.2 70.6
做家务(%) 68.7 61.7
提供经济上的援助(%)73.2 64.7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25.7 26.0
做家务(%) 22.3 12.6
提供经济上的援助(%)19.0 8.9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身体状况 0.54 0.99
父母的家庭月收入(元) 896.8762.5
(402.45) (534.0)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96.6 85.1
离婚或丧偶(%) 3.4 14.9
子女的个人月收入(元) 296.8342.3
(223.9) (233.7)
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52.5 36.1
未与父母同住(%) 47.5 63.9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50.6 15.6
有孩子(%)49.4 84.4
性别:
女(%)43.3 47.2
男(%)56.7 52.8
个案数(n) 358 269
被访问的老人的年龄
总样本
70+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1.04 1.15
(1.00)
(1.00)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元) 2 114.8 3 096.5
(9 146.5)(5 876.1)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42.3 33.5
高中或同等学历(%) 42.3 48.3
大专及大学以上(%) 15.4 18.2
婚后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 59.6 39.9
未与父母同住(%)40.4 60.1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83.7 58.5
做家务(%) 63.1 65.3
提供经济上的援助(%)61.5 68.1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17.3 24.6
做家务(%) 11.5 17.2
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9.6 14.0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身体状况 1.38 0.82
父母的家庭月收入(元) 678.5818.0
(504.2) (475.6)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69.2 88.5
离婚或丧偶(%)30.8 11.5
子女的个人月收入(元) 497.0341.9
(719.8) (349.6)
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35.6 44.0
未与父母同住(%) 64.4 56.0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3.8 31.1
有孩子(%)96.2 68.9
性别:
女(%)41.3 44.5
男(%)58.7 55.5
个案数(n) 104 731
资料来源:1994年保定调查子女样本。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方差。
早期家庭帮助包括:(1 )测量被访人早期对家庭帮助的依赖的指标;(2)父母为子女结婚所花费的费用;(3)被访人的教育水平;(4)婚后的居住情况。在具体调查访问中, 被访人被问及过去是否在做家庭作业、升学、就业、换工作以及分配住房方面得到过家庭的帮助。早期对家庭依赖指标记录了子女对此类帮助的依赖的频数。为减少此变量分布的不对称性(skewness),所有大于3以上的频数编码为3。因此,此变量的变化区间为0至3,这一变量在使用过程中仍被视为连续性变量。
父母为子女结婚所花费的费用的变量记录了实际费用。在有些研究中,子女教育水平被视为一个测量父母投资的变量(见Lee et al., 1994),即子女教育水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父母对子女的投资程度。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费用很低,但父母至少在子女受教育期间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因而代表了一种投资。婚后的居住情况指被访人是否在结婚后与父母同住。考虑到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住房紧张情况,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往往代表着一种父母对子女的帮助,而不是相反。
父母帮助成年子女的最通常的方式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做家务以及给他们经济方面的帮助。1994年保定调查询问了被访人是否在过去和现在接受过这些帮助。父母对子女过去和现在的帮助构成3 个“较近期的帮助”和3个“当前给予的帮助”的变量。 所有这些解释变量均编码为二分变量:1代表给予帮助,0代表其它。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分布也在表2中给出(见表2)。
在我们的分析中还包括一些作为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的测量。许多理论讨论和实际研究认为老人的需要,或者说老人的物质资源或自立能力的缺乏,是决定亲子间资源流动的一个因素(Hermalin,1995;Lee et al.,1994)。因此,只有在分析中引进测量老人健康和经济状况之后,我们才能检验父母投资是否在控制了老人的需要之后仍然对养老存在影响。由于老人年龄既可用于描述养老的基本模式,也可理解为测量其健康状况的一个代理变量,控制变量中也包括被访人的父母的年龄。此外,分析中还使用了一个用来测量被访问的父母身体状况的变量。在对父母的问卷中,列出了8 个需要一定体力才能完成的日常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购买个人用品,自己上楼,一次走二三百米的路,等等,我们的问题是询问被访父母是否有能力进行这些活动。这一变量根据被访父母对这8个问题的回答综合而成。 此变量具体编码如下:0—被访父母完成所有这些活动时毫无困难;1—被访父母完成某些活动时有一些困难;2—被访父母完成其中一两项活动有很大困难;3—被访父母完成其中三项以上的活动有很大困难。因此,变量值愈高,说明被访父母的身体愈差。
其它一些控制变量包括父母的月家庭收入,父母的婚姻状况(1 =在婚;0=离婚或丧偶),被访人的个人月收入,是否有孩子(1=有孩子;0=没有孩子),是否与父母同住(1=同住;0=未同住), 以及被访人的性别(1=男;0=女)。父母的月家庭收入在这里可理解为父母经济需要的一个指标。父母的婚姻状况在这里用以测量被访问的父母是否有配偶为其提供帮助。被访人的个人月收入描述了子女的经济能力。是否有自己的孩子测量了被访人对自己小家庭所承担的义务。
对居住方式变量的解释比较复杂,在此仅将其作为一个结构性变量,测量目前居住方式的影响。同理,被访人的性别在这里用来测量儿子和女儿在提供养老上的差别。
所有控制变量的基本统计分布也在表2中给出(见表2)。
四、分析结果
基本模式
表1中的数字表明, 有半数以上的被访人为父母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其基本模式是父母年龄越大,子女向他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也越大。给父母提供实物上的帮助似乎是最常见的养老方式。此外,父母的年龄越大,子女提供实物的现金价值越高。在给父母的现金数量方面,其基本模式是子女给钱的数量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高而减少。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购物不便,年迈的老人更希望得到实物的帮助。
就代际间向下的资源流动来讲,子女也同时接受着父母的广泛帮助(见表2)。子女早期对家庭的依赖,子女教育水平, 父母为子女结构所花费的费用,以及子女婚后的居住情况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一般性帮助。除此之外,表2中的数字说明,即使在子女长大成人后, 代际间向下的资源流动仍在继续。例如,半数以上的被访人在近期内接受过父母在照看孩子(58%)、做家务(65%)或经济上(68%)的帮助。与之相比,正在接受这些帮助的子女的百分比较低。但表2 中的数字也清楚地表明,一些老人即使在过了70岁以后仍在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帮助。例如,在70岁以上的老人中,仍有17%的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孩子。考虑到80%的70岁以上老人在近期为子女照看过孩子,照顾孩子似为居住在城市中的老年父母帮助已婚子女最常见的方式。
因此,将表1和表2的数字综合考虑,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1)代际间的物资和服务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2 )这种交流在父母年迈后仍在继续;(3)当父母年事渐高时,向上流动的资源逐渐增加, 而向下流动的资源逐渐减少。
那么,这两种资源流动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表3 给出了对父母投资和子女养老的二元分析的结果。在对父母的个人照料方面,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中,有30%提供了这种服务,而婚后未与父母同住的子女中,只有 23%提供了这种服务。此外,这种差别在统计上呈显著性(p<0.05)。这说明在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比婚后未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更有可能提供个人照料方面的帮助。与之相类似,那些在近期接受过父母在照看孩子、做家务和经济方面帮助的子女比那些未接受过此类帮助的子女更有可能为其父母提供个人照料方面的帮助。
表3. 子女为父母提供的养老帮助与父母投资的交互分布
子女提供的养老帮助
个人照料 家务
父母投资的变量
百分比
F比
概率 百分比
F比
概率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
025.98
51.23
124.66
61.51
227.33
61.07
327.16
0.15
0.92762.50
2.15
0.092
结婚时父母所作
经济贡献:
0-1 000元[a]
28.25
59.70
1 001元以上22.94
2.65
0.10457.36
0.40
0.526
小学或初中 23.77
54.73
高中或同等学历 25.36
59.20
大专及大学以上 31.06
1.23
0.29364.39
1.69
0.186
婚后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 30.34
63.67
未与父母同住
22.88
5.08
0.02555.30
5.03
0.025
父母是否在近期
帮助照看孩子:
是 29.65
59.76
否 20.53
7.71
0.00657.05
0.53
0.466
父母是否在近期
帮助做家务:
是 30.87
66.10
否 16.73 17.40
0.00044.76
31.83
0.000
父母是否在近期
提供经济帮助:
是 30.18
65.73
否 16.52 15.59
0.00043.17 34.11
0.000
父母是否正在
帮助照看孩子:
是 21.67
56.11
否 27.24
2.19
0.13959.48
0.63
0.427
父母是否正在
帮助做家务:
是 28.00
63.71
否 25.42
0.36
0.54957.60
1.58
0.209
父母是否正在
提供经济帮助:
是 26.47
69.61
否 25.76
0.02
0.87956.84
5.92
0.015
子女提供的养老帮助
现金实物
父母投资的变量
百分比
F比
概率 百分比
F比
概率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
040.91
68.47
143.25
59.66
239.86
62.67
347.74
0.26
0.85265.00
1.37
0.249
结婚时父母所作
经济贡献:
0-1 000元[a]
44.73
62.63
1 001元以上38.82
2.53
0.11264.22
0.20
0.658
小学或初中 44.77
64.61
高中或同等学历 42.86
63.25
大专及大学以上 34.88
1.77
0.17161.24
0.21
0.813
婚后居住情况:
与父母同住 47.52
70.93
未与父母同住
38.46
5.76
0.01758.28 12.10
0.001
父母是否在近期
帮助照看孩子:
是 45.17
70.19
否 37.71
3.96
0.04753.54 21.47
0.000
父母是否在近期
帮助做家务:
是 47.72
68.79
否 31.58 17.57
0.00053.41 16.96
0.000
父母是否在近期
提供经济帮助:
是 44.49
68.76
否 36.96
3.63
0.05751.74 20.06
0.000
父母是否正在
帮助照看孩子:
是 48.00
66.67
否 40.11
3.38
0.06762.25
1.14
0.287
父母是否正在
帮助做家务:
是 44.63
65.32
否 41.53
0.40
0.52962.94
0.25
0.616
父母是否正在
提供经济帮助:
是 31.63
54.46
否 43.72
5.09
0.02464.79
4.01
0.046
a 1 000元是父母在子女结婚时所作贡献的变量的中值。
我们可以就表现为替父母做家务、给父母现金和实物的养老行为和那些代表父母投资的变量的二元关系做类似的解释。就替父母做家务来讲,婚后居住方式,父母近期在家务和经济上的帮助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此外,婚后居住方式, 父母近期在照看孩子、家务和经济上给子女的帮助,父母正在提供的照看孩子以及经济上的帮助,都是影响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现金和实物上的帮助的显著因素。
通过对养老变量和父母投资变量的一元分布的检验以及对这两组变量的二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在中国城市中,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仍然保持着广泛和持久的物资和服务上的交流;一般地讲,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多元分析
由于所研究的因变量(个人照料、家务、现金和实物帮助)均为二分变量(dichotomous variables), 因而不满足古典多元回归模型规定的关于因变量必须是连续变量这一基本条件(Amemiya,1985; 方,1989)。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模型有probit回归和逻辑司提回归(the logistic regression)。 虽然这两种模型的数学假设颇有不同之处,但二者在实际应用中差别很小(见Maddala,1983)。 下面的分析采用逻辑司提回归统计模型。
服务性养老 表4 中列出了以父母投资为解释性变量对服务性养老进行回归的逻辑司提回归分析的结果。服务性养老的操作化定义在这里为子女为父母提供的个人照料和家务上的帮助。解释变量有代表父母投资的变量以及一些控制变量(见表4)。
表4. 父母投资对服务性养老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个人照料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B)(S.E.)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 0.0480.104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对数值) -0.0020.024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 0.2070.214
大专及大学以上 0.3910.270
婚后居住情况:
[未与父母同住]
与父母同住 0.3120.231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 0.3020.341
做家务:
[否]
是 0.675[**]0.241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 0.678[**]0.234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0.537[*] 0.253
做家务:
[否]
是 0.0460.261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0.0680.277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年龄:
[50-59岁]
60-69岁0.628[**]0.224
70岁以上
1.237[***]
0.307
被访问的父母的身体状况
0.1230.089
父母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在婚
0.5110.313
居住情况:
[现未与父母同住]
现与父母同住 -0.0850.247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有孩子-0.0470.418
性别:
[女]
男-0.710[***]
0.193
回归常数(constant)
-2.990[***]
0.482
模型卡方检验值(model X square) 83.01
做家务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B)(S.E.)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 0.0370.095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对数值)
0.059[**]0.023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 0.1680.190
大专及大学以上 0.3070.251
婚后居住情况:
[未与父母同住]
与父母同住 0.1780.210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 0.4790.289
做家务:
[否]
是 0.465[*] 0.204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 0.693[***]
0.195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0.2290.224
做家务:
[否]
是-0.2340.244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 0.2900.262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年龄:
[50-59岁]
60-69岁0.0530.195
70岁以上
0.928[**]0.303
被访问的父母的身体状况
0.0750.084
父母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在婚 -0.1200.288
居住情况:
[现未与父母同住]
现与父母同住
0.696[**]0.235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有孩子-0.785[*] 0.355
性别:
[女]
男-0.773[***]
0.177
回归常数(constant)0.5500.417
模型卡方检验值(model X square) 97.03
*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1994年保定调查子女样本。
注:表中数字为逻辑司提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方括号里的项目为缺省参考项目(omitted reference categories)。
根据对个人照料回归分析的结果, 在父母投资中有3个因素影响子女为父母提供此类帮助的可能性。即,如果父母近期在为子女做家务或经济上提供了帮助,子女更有可能为父母提供个人照料上的帮助(0.675和0.678)。换言之,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 获得这种帮助的子女与未获此类帮助的子女相比,其为父母提供个人照料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但是,父母正在帮助照看孩子的效果正好相反(-0.537)。 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老人还能够为子女照看孩子,说明他们的身体状况尚好,不需要别人的随身照料。
另外,此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年龄是预测子女是否提供个人照料的最强有力的变量。在60—69岁年龄组的父母获得子女这方面的帮助的可能性,大约是60岁以下父母的1.9倍(e[0.628]=1.87)。 同理,70岁以上的父母获得随身照料的可能性,与60岁以下父母相比,其差别比(odds ratio)大约为3.5(e[1.237]=3.45)。
最后,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710。这说明, 儿子为父母提供个人照料上的帮助的可能性比女儿要小得多。
关于做家务的回归模型中所展示的养老模式与上述的结果大致相同。也就是说,那些在近期接受过父母在家务和经济上的帮助的子女,与那些未接受过此类帮助的子女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帮助父母做家务。此外,父母为子女结婚所做的贡献的变量也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这意味着,父母在子女结婚时贡献愈大, 子女在以后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的可能性愈大。
就控制变量来讲,子女帮助70岁以上的父母料理家务的可能性比帮助较年轻的父母的可能性要大(0.928)。 如果子女在目前与父母同住,他们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的可能性也有所提高(0.696)。另外, 如子女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为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则有所降低(-0.785 )。
最后,与个人照料相似,儿子为父母做家务的可能性比女儿要小得多(- 0.773)。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城市由儿子负责为父母提供养老的传统已基本被打破。至少在服务性养老方面,女儿为父母所作的奉献比儿子要多。
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庭早期的帮助和父母正在予以的帮助对子女的养老行为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正在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父母在服务上获取帮助的可能性反而较小。在早期家庭帮助的变量中,只有父母在子女结婚时的经济贡献起到一些作用。子女教育水平的效果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原因或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几十年以前,子女教育的完成并不需要父母大量的经济上的贡献。此外,那些父母在60岁以上的子女,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文革”动荡时代教育体制的变动弱化了父母的努力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即使对于同年龄组的人,教育水平之高低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个人能力和家庭文化熏陶的影响,而并不体现父母的直接努力。
因此,在体现父母投资的诸变量中,有助于促使子女为父母提供服务性养老的,既不是父母早期的帮助,也不是正在予以的帮助,而是父母在近期给予子女的种种帮助。据此,我们可以推断:(1 )那些希望在年老时获得子女帮助的父母,倾向于以给予子女各种各样的帮助来维持与子女长久而紧密的联系;(2)子女在为父母提供各种帮助时, 并非为了获取即时的经济补偿。
经济性养老 经济性养老在这里指子女给予父母现金和实物上的帮助。对经济性养老进行回归的逻辑司提回归的计算结果,在表5中给出。基于前面已经提到的考虑,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有关于父母投资的变量以及一些控制变量(见表5)。
表5. 父母投资对经济性养老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现金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B)(S.E.)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0.1140.100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对数值)
0.0220.023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0.0580.197
大专及大学以上-0.5110.263
婚后居住情况:
[未与父母同住]
与父母同住 0.1090.221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 0.3460.316
做家务:
[否]
是 0.649[**]0.219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 0.3460.208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 0.3590.230
做家务:
[否]
是-0.0810.251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0.535[*] 0.276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年龄:
[50-59岁]
60-69岁0.2140.202
70岁以上
0.590[*] 0.299
父母的家庭月收入(对数值)-0.444[**]0.152
父母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在婚 -0.1440.306
被访人的个人月收入(对数值)
0.349[***]
0.099
居住情况:
[现未与父母同住]
现与父母同住
0.2420.240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有孩子-1.008[**]0.377
性别:
[女]
男-0.0470.180
回归常数(constant)0.4681.071
模型卡方检验值(model X square)
88.6
实物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B)(S.E.)
(1)早期家庭帮助:
对家庭依赖的指标-0.0580.105
结婚时父母所作经济贡献(对数值)
0.0230.024
教育水平:
[小学或初中]
高中或同等学历 0.0800.208
大专及大学以上-0.1450.274
婚后居住情况:
[未与父母同住]
与父母同住 0.499[*] 0.240
(2)父母在近期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 0.0060.315
做家务:
[否]
是 0.603[**]0.228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 1.121[***]
0.218
(3)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
照看孩子:
[否]
是-0.0260.249
做家务:
[否]
是 0.2740.267
经济上的援助:
[否]
是-0.657[*] 0.272
(4)其它:
被访问的父母的年龄:
[50-59岁]
60-69岁0.642[***]
0.214
70岁以上
0.636[*] 0.324
父母的家庭月收入(对数值)-0.0590.143
父母婚姻状况:
[离婚或丧偶]
在婚 -0.5470.356
被访人的个人月收入(对数值)
0.139[**]0.045
居住情况:
[现未与父母同住]
现与父母同住 -0.581[*] 0.265
是否有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有孩子-0.1580.375
性别:
[女]
男-0.710[***]
0.193
回归常数(constant)0.1100.957
模型卡方检验值(model X square) 125.9
*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1994年保定调查子女样本。
注:表中数字为逻辑司提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方括号里的项目为缺省参考项目。
回归分析所展示的子女给予父母现金帮助的机制比较简单。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父母在近期给予子女家务上的帮助有助于促使子女为父母提供现金上的帮助(0.649)。但是, 父母正在提供的经济帮助降低了子女为父母提供现金帮助的可能性(-0.535)。 代表父母正在提供的经济帮助的变量的负效果说明,正在接受经济帮助的子女不会对父母作经济上的回报。这种情况再一次说明,子女照顾老人并非为了即时的回报。
再者,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父母的年龄在这里影响变小。此外,如所预期的,父母家庭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0.444)。 这表明,父母收入愈高,其获得子女现金帮助的可能性愈小;此外子女收入对因变量有正影响(0.349)。换言之,子女的收入愈高, 他们为父母提供现金帮助的可能性愈大。最后,如果子女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给父母钱的可能性降低很多。儿子和女儿在这方面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与现金帮助相比,影响子女给予父母实物帮助的因素稍有不同。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除了父母近期在家务和经济上的帮助的正效果(0.603,1.121)以及父母正在提供的经济帮助的负效果外(-0.657),子女在婚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0.499)。
此外,父母的年龄在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父母年龄越大,他们获得子女实物帮助的可能性越大。虽然子女个人收入的作用仍具有统计显著性(0.139),父母家庭收入的统计效果则基本消失。 再者,不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更有可能为父母提供实物上的帮助。最后,被访人性别变量的系数(-0.710 )再次具有统计显著性:儿子提供实物帮助的可能性与女儿相比,大约仅为一半(e[-0.710]=0.49)。
关于父母投资对经济性养老的影响,回归分析所揭示的格局可总结为以下两点:(1 )正如我们在讨论父母投资对服务性养老时所发现的,对经济性养老有影响的变量主要为父母在近期为子女所提供的家务和经济上的帮助;(2 )父母正在给予的经济帮助降低了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
五、总结和讨论
关于现代中国城市家庭养老的格局和代际关系的特点,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老年人的晚年安定仍然被普遍认为是子女的重要责任,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也仍然保持着持久和密切的联系(见费, 1988 ; 袁,1987;Davis-Friedmann,1991;Unger,1993)。本文的主旨是探讨在中国城市中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服务(个人照料和做家务)和经济帮助(现金和实物)作为代际养老的主要指标,此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检验父母投资和代际养老间存在有因果关系这一假设。总的来讲,我们的分析结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
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在中国城市中,父母与子女间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服务和物质性资源的交换。无论是否与其成年子女同住,大部分父母继续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其中以照看孙子女最为普遍,而子女也继续为进入老年的父母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2.在父母投资的诸变量中,最重要的促进子女养老可能性的因素是父母在近期给子女的帮助。父母早期帮助的效果并不明显。父母正在给予的帮助也没有正影响。此外,这种模式适用于对所有4 种养老类型(个人照料、做家务、给钱和实物帮助)的解释。因此,这些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间长久的联系,以及父母给予子女的持续的帮助,促使了子女尽心地赡养父母。而且,子女的尽心并不是为了从父母那里获取即时的回报。这说明真正促使子女为赡养父母作贡献的不是父母的投资本身,而是体现在父母投资中并由此强化的长久和密切的代际关系。
3.一般地讲,在其它例如父母的年龄、身体状况、收入、子女的收入和居住方式等与养老相关的变量的影响被控制之后,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的关系仍然存在。
4.同时,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净效果也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有很清楚的统计证据表明,除了父母投资以外,其它一些因素也对养老行为有影响。换言之,这里所提出的父母投资与养老的因果关系可能仅仅是形成中国城市家庭养老制度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中的一个社会过程。
因此,以代际间的联系以及资源交换为讨论主题,此项研究的结果也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网络家庭”的概念,即父母家庭和子女家庭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依赖的想法,十分吻合(见Unger,1993:40 —43)。再者,通过分析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行为的联系,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所谓“网络家庭”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实际上可能是在因果上相互关联的代际间资源流动的具体体现。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子女的持续的帮助,促使子女在赡养年迈父母时能够尽心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代际向上和向下的资源流动不应视为父母和子女间的等价交换。因为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即时交换,而代际交流的资源也往往不是等价的。在概念意义上,代际间的相互帮助代表了一种代际间相互履行责任、资源流动由“一般性互惠”原则所指导的这样一个社会过程。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想,由于家庭养老对大多数中国老人仍然是保证晚年生活安定的一个重要选择,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子女的各种帮助便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只有如此,代际间隐含的“协约”才能得以履行。这样,驱动父母为子女提供物质和服务资源的动力不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感,或对子女纯粹的感情依附(Macfarlane,1 986;Aries,1962),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功利性的考虑。但是, 由于养老只能在父母晚年才能实现,届时父母可能不再拥有足够的经济或社会资源以补偿子女的服务,养老的圆满实现在客观上又要求父母压制或去除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和感情因素的一致性,大部分父母能够全心地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以达到巩固与子女的关系和增进家庭团结的目的。如进一步推论,也可能正是由于家庭养老制度的长期实行,中国家庭长久以来才得以保持了惊人的社会凝聚力(Madge,1974)。
此项研究通过对一项社会调查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父母的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子女赡养老人的可能性。因此,除非有一个全面和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出现以减轻老人对子女的依赖(战,1992),代际间广泛的资源交流将继续成为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家庭养老制度也将继续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
谨向参加“保定市老龄化及代际关系调查”的研究人员, 尤其是Martin K.Whyte、杨善华、萧振禹、王丰和鄢盛明等人表示感谢。 此外,在文章撰写过程中,买向平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