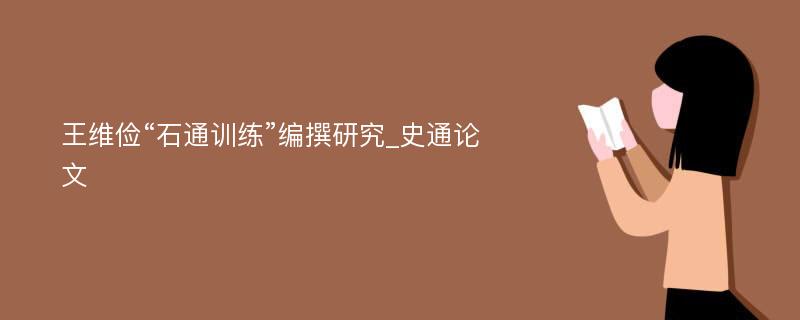
王惟俭《史通训故》编纂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惟俭论文,史通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4)01-0052-06
王惟俭字损仲,明代后期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以博通经史百家、书画古玩,被当世称为“博物君子”[1],其史学代表著作即《史通训故》。从表面形式上看,此书是一部注释唐代史家刘知幾《史通》之作,书首自序也主要是谈注释的问题,因而从问世迄今,学者们都认为他是为注释《史通》而写作此书。但综合考察所见资料即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惜学界至今无人探讨。此外,其书与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关系及二者优劣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些未发之覆,有必要进行专文析论。
一、《史通训故》的撰述宗旨与撰述经过
王惟俭在自序《史通训故序》中说明了其书写作缘起及相关情况,其文云:
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黄庭坚)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张林宗(张民表)年兄以江右郭氏(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读之,与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注焉,历八月迄功。然此二书讹处甚多。嗣从信阳王思延(王延世)得华亭张玄超(张之象)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故此书之校,视《文心》为愈。往见李济翁《资暇录》,云李善注《文选》,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苏子由(苏辙)注《老子》,亦自言晚年于旧注多所改定。今余此书,曷敢以为尽是?聊以备遗忘,为他日削稿之资耳。[2]247-248
此序简明扼要,分四层交代了作者注释《史通》的基本情况。一是撰作缘起。王惟俭在刊刻《文心雕龙训故》后,想到宋人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的话,遂欲取《史通》注之。但从他所引黄氏之语可知,他是转引自明代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或《丹铅总录》卷二六《琐语类》、《升庵集》卷四七《老泉评史通》,而非黄庭坚本人之《山谷外集》卷十《与王立之四帖》(之二),黄氏原话并非如此。二是注释体例及写作时间。在王惟俭决定注释《史通》之后,其好友张民表将郭孔延《史通评释》相示,他发现郭注与自己的想法“多不合”,这更加促使他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撰写一部《史通》注释之作,于是他就以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并于八个月后完成《史通训故》初稿。三是校勘修订。王惟俭以郭孔延刻本为工作底本完成初稿后,文字讹处仍较多,恰好他从友人王延世处得到张之象刻本,感觉此本“大善”,于是就以之续校刊定。四是对己书的期盼。作者最后以李善注《文选》和苏辙注《老子》都曾反复修订的情况为譬喻,说明其注释绝非“尽是”,只是“聊以备遗忘”,以为后人他日“削稿之资”,这表现了王惟俭的谦虚精神。
在王惟俭刊刻《史通训故》的过程中,其好友纷纷为此书写作序跋,为后人提供了更多有关此书撰作的信息,可惜学界一直未予注意,因而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其中张民表在序中说,王惟俭以《史通》“世无善本,学者不传”,遂“既训刘氏《文心》成,复训是书”,最后署为“万历辛亥岁春三月己未”[3]。这一是说明,王惟俭写作《史通训故》,也有整理出令世人可读之《史通》“善本”之意。二是告诉我们,该书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己未之前已经完成。王惟俭自序中只说他是在八个月内完成初稿,后来又有修订,但并没有明白说出具体的工作起讫时间。查其《文心雕龙训故》,卷首自序所署日期是“万历己酉夏日”,书末有其手书“识语”一则,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三日”,则全书刊刻完成,必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二十三日之前。由此可知,王氏《史通训故》始撰时间最早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历时八月完成初稿,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己未之前完成定稿。
此外,张民表序中还谈到了他对刘知幾的认识,“刘子玄目洞千秋,手裁万化,决断无疑,于义进退,各厌其心,虽证事少乖、制词多靡,乃得失自在,取舍由人。信史家之砥砺,述者之夷庚也”。王惟俭在自序中并没有对《史通》直接发表个人评论,但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既然是为自己撰史而先从《史通》取鉴(详见下文),又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曾与张民表“商订”[2]251,因而张民表对《史通》的这一评论,或许也可以代表王惟俭的观点。
王惟俭同年陈九职的跋语,从宏观方面对其注释工作进行了说明和评价,其文云:
小司马损仲以颖异成其该博,……既取《文心雕龙》注之,兹复有《史通》之纂述。校雠璠摩,发凡立例,删赝订讹,旁援互证,抉秘补漏,提要括繁。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用力斯已勤矣。[4]
所谓“校雠璠摩”,是指王惟俭对《史通》文字的校勘。“发凡立例”,是说王惟俭注释《史通》有自己的体例。“删赝订讹”,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史通评释》中的一些错误,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卷首《例言》第二则也有类似说法[5]435。“旁援互证”,是说王惟俭在注释过程中采择史料比较广泛。“抉秘补漏,提要括繁”,是说王惟俭的具体注释方法。“事详而核,辞赡而雅,条分而贯”,这是评价王惟俭的工作成效。陈氏的评论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他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因而其所述基本上反映了王惟俭的工作实际。至于称王书使“上下数千百年理乱兴衰之迹、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诸掌”,则显然过于虚夸而有失真实。
对于考察王惟俭注释《史通》工作的内在宗旨,更重要的还是自署“年弟”的薛永宁的跋语:
明兴以来,载笔不乏,至于纪传之体,独郑端简公(郑晓)《吾学编》耳。吾友王损仲思欲删润一代之大典,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其训注该博,信史家之龟鉴也。损仲渊雅卓荦,异日著述,必将与龙门(指司马迁)、兰台(指班固)分镳共驰。此无俟余言。[6]427
这告诉我们,王惟俭之所以训释《史通》,不只是王氏自序中所说的注释《文心雕龙》之后,想到黄庭坚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相提并论,遂取《史通》而注之;其更深层的原因,乃是王惟俭欲撰著一部纪传体明史,“故于《史通》一书深所究心”,也就是要以《史通》中所讲的史学理论为自己写史的指导原则,以便写好自己欲图撰著的这部明朝当代史。薛永宁认为,有了《史通》的理论指导,加上王惟俭个人“渊雅卓荦”,则其日后所成纪传体明史一定可与《史记》、《汉书》“分镳共驰”。前述张民表序言,也曾称扬王惟俭“他季著述必有可观,且将方驾龙门,联镳长广”,与薛永宁推崇之意正同。无论二人对王惟俭的推重是否属实,但薛永宁作为其好友,并也曾参与《史通训故》的“商订”[2]251,则他所说的王惟俭之所以写作该书的缘由,应该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王惟俭是为了从《史通》中借鉴修史的原则和方法,才要撰著《史通训故》的,“既注《文心》,因念黄太史”云云,虽然也是缘由之一,但更多的只是表面上的虚词客套之语,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从《史通》中寻求理论借鉴。
综上所述,全面考察王惟俭自序及其与修诸友序跋可知,他主要是为了撰著一部明代纪传体史书而进行《史通训故》的编撰的,目的是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仅仅是为了注释《史通》。其最早写作时间是在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后,八个月完成初稿,此后又有修订,到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完成定稿。他在开始工作之前拟定了撰写凡例,工作内容包括对《史通》的校勘和注释,同时还有针对性地纠正了此前郭孔延注释的一些错误。
二、《史通训故》的体例、内容与学术成就
(一)《史通训故》的体例
《史通训故》二十卷,逐篇对《史通》全书进行注释和文字校勘。按其自序,王惟俭是以自己过去注释《文心雕龙》的体例来注释《史通》的,因而《文心雕龙训故·凡例》也就是《史通训故》的体例。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者至今无人对此进行梳理。
《文心雕龙训故》共有凡例七条[7],除第五条是专门针对《文心雕龙》者外,其余各条都适用于《史通训故》的写作。
第一条:“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即有粤语伟字,如‘鸟迹’、‘鱼网’之隐,‘玄驹’、‘丹鸟’之奇,既读斯书,未应河汉,姑不置论。”是知其工作宗旨仅在“讨求故实”。具体到《史通》一书,就是对其中的人名、书名、史实、典故等作出注释,说明《史通》各篇引事用典之出处所本,以便顺利读懂原书;至于其他在理解上不会有较大出入的词语,则不加注释。
第二条:“故实虽烦”,但世所共知、耳熟能详者,如“舜、禹、周、孔之圣”以及子游、子夏等人之贤,“世所共晓,无劳训什”,不再加注释。
第三条文字较多,但意旨只有一个,就是讲注释时按照避繁从简的原则来处理具体内容。作者指出,如果注释时“人详其事,事详其篇,则杀青难竟,摘铅益劳。故人止字里之概,文止篇什之要,势难备也”。这与郭孔延在《史通评释·凡例》中所说的“注书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注人序其爵里”[8]表面上相同,但在实际注释时,郭孔延往往有非常详细之处,有时还在注释文字之后紧接着加以“延按”性的考证评论,以致显得有些繁琐枝蔓,而王惟俭则始终坚持避繁从简的原则,因此相对郭孔延来说,王惟俭确实简略有余,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伤于太简,未免遗脱”[5]435的现象。不过,王惟俭的目的即在从《史通》中为自己撰写史书寻求理论借鉴,并非是专门为《史通》做一部注释之作,因此他为避免“杀青难竟”而采取简注速成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正是这一撰述宗旨决定了他避繁从简以速成其书的写作原则。
第四条:“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见,或一事而累出,止于首见注之。其或人虽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为训什。”某人某事,只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注释。后面其人再次出现时,只有与前注事件不同,才会再加注释。这是避免重复的正确做法。
第六条:“训释总居每篇之末,则原文便于读诵。至于直载引证之书,而不复更题原文者,省词也。”在《史通训故》中,大部分篇章的注释“总居每篇之末”,少数篇长者则分成多个内容单元,在各单元之后紧接着写出本单元的有关注释。但他为了“省词”,竟也和郭孔延一样,直接写出注释文字,而无该注释的名称性标题(“不复更题原文”),这对阅读和检索都不方便。
第七条:“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十四处。其标疑者,即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在七条“凡例”中,只有这最后一条是讲文字校勘问题,可知其全书内容是以注释为主,而以校勘为辅。在《史通训故》中,王惟俭是用张之象本《史通》来核校郭孔延评释本《史通》的,其中校字千余,比《文心雕龙训故》多些;有疑问者则“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这是客观求实的缺疑态度,值得肯定。
(二)《史通训故》的内容与学术成就
1.校勘
王惟俭在《史通训故》卷首写有如下一则文字校勘识语:“此书除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显然,这是王惟俭对自己校勘总成绩的简单概述,既交待了他对《史通》篇章整理校勘的贡献,又交待了他对全书中零散性文字校勘的总数量。
我们先看王惟俭特别提出的“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王惟俭在自序中曾说:他感觉郭孔延评释本《史通》讹处甚多,而张之象刻本《史通》则“大善,有数处极快人者”,于是就用张本加以校勘。联系上面校勘识语,所谓“数处极快人者”,当即是指“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事情。
但清代四库馆臣将王惟俭《史通训故》与郭孔延《史通评释》比对相校,发现事实并非如王氏所自称的那样。他们在《史通训故》提要中写到:此书“惟《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无增入之语,不知何以云然”[9]。现代史家蒙文通等人也曾将二书比对勘校,指出:“实则《补注》、《因习》二篇之增补,自郭而不自王,《曲笔篇》一百九十九字之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损仲之说不审,《提要》之语亦失于检核”[10]。蒙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郭孔延在根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完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刻本《史通》,特别是得到了其中卷五《补注》、《因习》两篇全文,遂据而补入,并以张本校补全书,形成《史通评释》修订再刻本。既然郭孔延也是依据张之象本校补,则王书出现“《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曲笔篇》文字增入“亦自郭而不自王”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是则,《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王惟俭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皆为他个人所得。
但如此一来,王惟俭岂不成了掠他人成果为己有而又大言不惭的欺世盗名之徒?如果仅看二人校勘成果,自然会得出这一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惟俭以博学著称一时,其友人刘不息在《史通训故跋》中也曾明称该书为“注悉”、“博奥”[11];之后,著名文史学家钱谦益对当时文士“独许”王惟俭为“博雅”[12],杰出诗人、博学家王士祯在告诫儿孙时,称《文心雕龙训故》、《史通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所当宝惜”[13]。这些高度评价,说明博奥、博雅之王惟俭“精于文献整理注释”,而从《文心雕龙训故》看来,他也没有“攘窃”先前各家成果,“是其独立完成”[14]。那么,他依《文心雕龙训故》来写作《史通训故》,应该也不会攘窃他人成果。王惟俭的性格是爱憎分明、原则性强,“于臧否处太分明”[6]427,由这一点来说,他也应该不会做出剽窃之事。更何况,人们只要拿来《因习》、《直书》、《曲笔》三篇文字,将其与郭书两相对读,即可轻而易举地发现全是直接继承了郭孔延的校勘整理成果,如此,他还要大肆渲染自己“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岂非拙劣、愚蠢到极点?
考虑及此,笔者以为,王惟俭自称“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的贡献,应该是符合他的真实情况的,他没有抄袭郭孔延的校勘成果。但他的这三篇校勘成果却又真的给人一种源自郭氏的感觉,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就涉及到郭书有初刻本与修订再刻本之别的问题了。王惟俭从友人处得到的郭氏《史通评释》,乃是郭氏尚未与张之象本《史通》相校勘的初刻本,因此,他在得到张本后,感到张本这三篇“大善”,“极快人”,遂据而“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但他不曾料到的是,早在他开始写作《史通训故》之前,郭孔延已经得到了张本《史通》,并据以补校其书,形成修订再刻本。可惜郭氏这一修订再刻本虽然行世,但王惟俭始终未曾得见,于是他这三篇的校勘成果虽然与郭氏再刻本相同,但他却总以为是自己独得之成绩,沾沾自喜之余,遂不免在全书卷首单独提出。蒙文通依照郭书修订再刻本,称王惟俭此说“不审”,确实如此,但王惟俭此说却符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欺世盗名。换言之,王惟俭与郭孔延对《因习》等三篇是各自独立进行校勘工作的,虽然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都是依据张之象本《史通》来校勘的,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校勘成果相同的现象;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后来之王书暗合了先前之郭书。
再看第二个方面,王惟俭说,除上述三篇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具体到《史通训故》四十九篇文章之中,他或在全篇文章之后,或在篇内每个内容单元之后,注明校字情况。如卷一《六家》分成六个内容单元,在“尚书家”之后注云“校八字”、“春秋家”之后注云“校二字”等等,而卷二《二体》只在全篇之后注云“校六字”。根据这些自注,总计四十九篇校字之和,共校一千零七十九字,比王惟俭在卷首所言“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少六十三字。联系上述卷首“校阅姓氏”也与正文所记校者姓名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许可以推断,这两处卷首所记都是王惟俭书稿初成时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王惟俭又对正文有所改动,校阅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忘记了在卷首作出相应调整,于是出现了卷首与正文不相符合的现象。
2.注释
《史通训故》以注释为主要内容。由于其工作有自己一定的体例,因此下面就以其书卷一《六家》的第一个内容单元“尚书家”的有关注释为例,并通过与郭孔延《史通评释》同一条目之注释做对比,既以见二人各自之注释,亦以见二人注释之异同,因为王对郭进行过“删赝订讹”的工作。
对刘知幾提到的孔安国与《尚书》的关系,是王、郭二书各自第一个注释的内容。王云:“《前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起家为汉武帝博士。”郭云:“孔安国,汉武时人。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王惟俭写明了释文出处,这是其长处,但真正释文内容只有一句“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而且末句“起家为汉武帝博士”也并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应该是整合了《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孔子世家》中“安国为今皇帝博士”一语而成,直接说成是出于《汉书·儒林传》无疑属于伪注;郭孔延未注出处,这是其短处,但全部释文除首七字外皆出自《汉书·儒林传》,资料可靠,其中孔安国整理和传授《古文尚书》的情况也都得到了全面反映,即使其传授都尉朝和司马迁的情况可以不写,但其整理之功则不能不写。因此,在这个注释问题上,王惟俭伤于太简,并存在伪注问题;郭孔延全书大都没有注明释文出处,属于全书体例之失,但此处引文并不难查到其原始出处,而且资料准确,内容全面。两者相较,笔者更倾向于郭孔延的做法。
第三个注释,二书都是对说过“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的“王肃”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注释。王惟俭认为是指三国时期魏国的经学家王肃,遂引《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之,释文内容将其学术著述情况介绍得也很全面,超出了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的范围,这是可取的。郭孔延认为是指南北朝时期的王肃,遂引《魏书·王肃传》注之,但既没有注明出处,释文亦“误”[15],应该是指三国时期的王肃。也就是说,王惟俭纠正了郭孔延的错误,做到了后来居上。
二书第四个注释都是关于《逸周书》的。王注云:“《前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郭注云:“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陈氏云:文体与古文不相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李仁父曰: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余,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耶?篇目比汉多同,但缺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显然,郭注详尽,王注则如其凡例所说“文止篇什之要”。这种不同当然是由二书的不同旨趣决定的,但王注伤于太简的弊病也很明显。
王书第七个注释是关于孔衍的:“《晋书》: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补中书郎,王敦恶之,出为广陵相。”这符合其凡例中所说的“人止字里之概”。郭书第二个注释为:“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也。晋中兴,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撰述百余万言。”郭注也是来于《晋书·孔衍传》,但未注明;其内容比后来的王注多了一句“撰述百余万言”,王注则比他多了被贬出的缘由,即“王敦恶之”。那么,两个注释哪个更好呢?这只能由考察《史通》原文来决断。《史通》说:“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显然,郭注“撰述百余万言”很是切题,而王注则没有这一内容,王注所增“王敦恶之”虽属实,但在这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更直白点说,王注是减所不该减、增所不该增,属于两失之误,这可能是他主观上故意标新立异造成的缺失。
郭书第六个注释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如下:“王劭字君懋,北齐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问劭,劭具论所出,一无舛误。入隋,迁秘书少监。劭在著作,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词义繁杂,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堙灭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文词鄙野。然其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李延寿曰:劭究极群书,雅好著述,崇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经营符瑞,杂以妖讹,为河朔清流而干没荣利,颓其家声,惜矣!”这段注释仍不注明出处,但可容易查知,它是截取《北史》卷三五《王慧龙传》所附王劭传及该卷末史论文字所成,其内容之丰富,对于读者了解王劭其人,可谓详之又详。与之相应,王书第八个注释也是关于“王劭”的,其全文是:“《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齐待诏文林馆。隋文受禅,迁秘书少监。”这完全符合作者“人止字里之概”的凡例,相对郭注来说,则更是简之又简,但王劭“迁秘书少监”乃在隋炀帝继位之后,并非隋文帝时,这既可能是过于求简造成的疏失,也可能是直接删取郭注而稍加修饰造成的。在这条注释上,虽然二者一繁一简都是按照各自体例而来,很难简单论定孰优孰劣,但笔者个人更倾向于郭注。
以上就是笔者对王、郭二书第一篇的部分注释所作的简略比较。笔者无意将二者分出高下优劣,事实上,由于作者与读者的旨趣、知识底蕴等各不相同,也很难简单论定二者高下,因此也就不再多加举例。从上述各例看来,二者注释是各有优劣短长的。王惟俭作为后起之秀,确实纠正了郭孔延的一些错误之处,并明注释文出处,工作更加规范严谨,但他为速成其书而追求简略注释的方式,却也使他的一些注释伤于太简,有时还出现为了表明与郭注不同而删所不该删的情况。郭孔延所作注释,内容比较丰富,往往还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考证评论,但也有过于繁细之处,而且还存在一些错误,又不注明释文出处,因此,郭注不为后人满意是正常的,王惟俭要继之而写成具有自己一家言的注释之作,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其工作确实颇有成绩,这毋庸讳言。但如果仅从注释内容繁简的角度说,笔者更倾向于内容详细的注释方式,而从清代以来注释《史通》的情况看,浦起龙《史通通释》、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张振珮《史通笺注》等著作,基本上都是采取了详细注释的方式,并没有采用王惟俭的简注方式,浦起龙、张振珮还在许多注释之后写有考证评论性的“按”语,这也是采用了郭孔延的做法。此无他,详细注释对普通读者阅读《史通》来说,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
清代学者对王、郭二书也多有评论,有些内容颇能补充笔者上文简略讨论之不足,因此也引述于下,并稍作分析。
黄叔琳在乾隆十二年(1747)刊刻《史通训故补》,他在自序中说:《史通》“综练渊博,其中琐词僻事,非注不显,注家王损仲本为善”[5]430。既指出了为《史通》作注的必要性,也肯定了王惟俭《史通训故》的价值,而对郭孔延《史通评释》则根本不提。在其书卷首六则《例言》中,黄叔琳对王、郭二书多有比较性评论,其中第一则从文字校勘的角度指出二书都有讹误;第二则从注释的角度对二书进行了评论,认为郭注“援引蹖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后损仲更注《史通》,名曰《训故》,依据正史,选择精严,远胜郭书,然伤于太简,未免遗脱”;第三则、第四则是列举王注失误。总之,黄叔琳之书正是为了“增补王氏所未备”[5]435,但他对王惟俭的工作尚能优劣并举,对郭孔延则只有批评而看不到些许长处,未免有失公正。
比黄著晚五年,浦起龙主要根据王惟俭注释本《史通》完成并刊刻《史通通释》,他在卷首自序中说:“(《史通》)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辞衅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大梁王损仲粪除(郭孔延)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16]。浦起龙对王、郭二书都有评价,但显然更轻视郭孔延对《史通》的评论,虽然他本人也对《史通》多所评论。对于“世称佳本”的王惟俭《史通训故》,浦起龙明确指出了其缺点所在。不过,浦起龙是专门对《史通》进行注释和评论工作的,因此他必须对《史通》中“蒙焉”、“讹焉”、“脱焉”的内容进行“别彻”的工作,但王惟俭并非是专为注释《史通》而写作其书的,因而采取了简注而速成其书的方式,自然也就难以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别彻”工作,这与浦起龙是绝然不同的。
黄、浦之后,四库馆臣也对王、郭二书有所评论,他们先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九《史通评释》中说:“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故王维[惟]俭以下注《史通》者数家,皆嫌其未惬,多所纠正焉”,继又在同卷《史通训故》中说:“是编因郭孔延所释,重为厘正,又以华亭张之象藏本参校刊定。……孔延注本,漏略实甚。维[惟]俭所补,引证较详,然黄叔琳、浦起龙续注是书,尚多所驳正。盖刘知幾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后人捃摭残剩,比附推求,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固亦势所必然耳”。他们对王、郭二书持各有优劣短长之评价,虽然并不具体,但符合二书的实际情况,比径直否定郭书成绩的观点要公正得多。他们还说,《史通》一书“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想要以一己之力为《史通》作出完善之注释,绝非易事,需要众多学者“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并认为这是“势所必然”。揆之以浦起龙《史通通释》之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吕思勉《史通评》、程千帆《史通笺记》、张舜徽《史通平议》、张振珮《史通笺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等多部互相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的研究力作,则四库馆臣“辗转相承,乃能赅备”之言,确属不易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