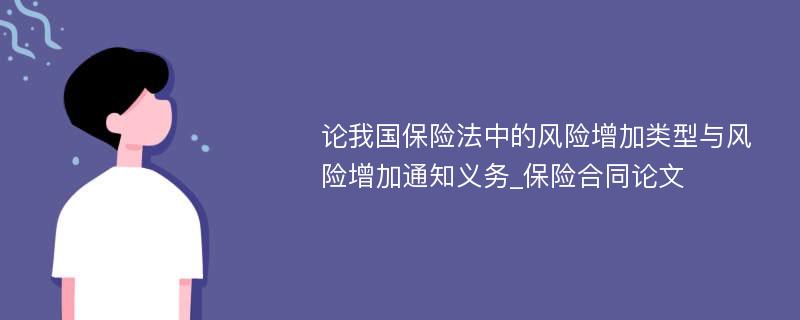
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险论文,保险法论文,化与论文,义务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2)02-0069-07
一、关于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法分析
保险合同的中心内容在于投保人以给付保险费为代价换得保险人承担约定的风险,从 而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实现风险的转移,而在与保险人具有合同关系的全体投保人之 间则形成风险的分散。因此,保险合同在保险精算的科学基础上,要求保险人承担的风 险与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关系,必须遵循对价平衡原则。由于保险人所承担 的保险标的物的风险处于无体不确定的状态,不能转移占有,因此,“保险人无论于缔 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1](P140)保险 标的物风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保险合同缔结之初其承担的风险与合同履行中的风险可 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而保险合同又是继续性合同,若危险严重超出缔约时保险合同所 承保的程度,则势必会提高保险事故发生的几率,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义务,破坏原有的 对价平衡。为此,当保险标的情况的变化严重增加了保险合同缔结之初所承保的风险, 保险法课以相对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使保险人有机会对危险增加的事实重新作出 正确估量,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风险。各国 保险法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但其具体内容却不尽相同。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36条用两款加以规定:第一款:在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 或者解除合同;第二款: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而 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纵观其规定,简单有余而涵盖性不足。危险增加有时可归责于当事人,有时则不可归 责于当事人,是否应不分情况规定为相同的结果;按现行法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下 保险人有合同解除权与保险费增加权,其间的关系若何,是否可任意选择……凡此种种 ,皆须明了。现行保险法第36条的内容未涵盖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不同情况而在法律上 异其效果。因此,有对之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必要,以在法律运行中明其意义,定其权利 义务,理顺其责任,祛除对当事人造成的不公及由此而致的纠纷。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之后,面临外国发达保险业的竞争之际,尤须基于后发展之地位,借鉴他国先进保险立 法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规则,在投保人与保险人间达成利益的平衡,以完善我 国保险现行法,加强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
二、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法学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类型化研究的本旨不是为类 型化而类型化,其目的在于通过类型化而达到区别法律事物的性质、法律上的权利、义 务与法律后果的不同,以明了其法律规则的适用。
(一)根据重要危险增加①(注: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的危险增加,有其特定 的构成要件。我们认为,该危险增加须是重要危险增加才符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危 险增加”。我国保险法对此规则亦有缺失。)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将之分为约定 危险增加与非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经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危险增加 ,后者是保险合同上虽未约定,但在客观上足以提高危险发生率,符合重要危险增加构 成要件的危险增加。在实务中,是否在合同中约定负通知义务的危险增加都是重要危险 增加,从而皆须负通知义务,关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他们代表着需要获 得保险保障的社会大众,显有澄明的必要。有学者认为,凡是在合同中约定的须通知的 危险增加情形皆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纵使客观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亦在其内。[2]( P133)按此,若保险合同中载有危险增加应负通知义务的情形,义务人都必须在情形发 生后通知保险人,如违反此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其实质上是否具有 重要性。此观点的合理性不无疑问,实质上涉及保险合同中对危险增加的约定的效力问 题。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特定事项应负通知义务,包括:一是该特定事项从实际上来 说确已致重要危险增加的标准,同时双方又在合同中约定明示,既反映了合同自由原则 ,亦符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没有问题。二是合同中虽约定该事项发生须负危险 增加的通知义务,但该危险增加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此时,令当事人对此负担危险增 加的通知义务,不合该义务设定的本旨,更使对方为通知义务所累,反给保险人推卸责 任提供了理由,使义务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不能赋予合同中对特定事项须负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约定以绝对效力。解决的办法一是在保险业监督机关审查保险合同 条款时加以限制,二是司法中由法官来认定该条款与实质危险增加是否相合。无论如何 应在立法上明定该种条款的效力或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应赋予该种条款为 推定非重要危险增加的效力,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由其负举证责任。义务人可以举证证 明该约定的事项不是重要危险增加而不必履行通知义务。而不能赋予其视为重要危险增 加的效力。在保险合同未约定的场合,则需按实质标准判断是否因该危险增加而使保险 人在合同缔结之初绝不会以相同的条件承保。发生争议时,由法官根据保险合同的种类 及保险标的的特性作个案判断。
(二)根据危险增加的原因事实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这 是各国保险法理论中的通常分类,实质上立法并未如此表现。日本商法第656条规定为 “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者”,同法第657条则 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 加者”。即日本法以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德 国保险契约法第23条将主客观危险增加分别表述为“与要保人意思有关……”,第27条 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与要保人之意思无关……”。可见,德国保险法将是否与要保 人的意思有关作为区分主客观危险的标准。据此,若危险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则 不论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均为主观危险增加。反之,若与要保人意思无关,则为客观 危险增加。[2](P133)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9条第二项将主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危险 增加由于要保人或由于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第三项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不由 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致者”。即将是否由义务人行为所致为判断标准。但在台湾 保险法中,该处“行为”系指行为人于主观上是否应有认识并有意使之发生,在客观上 系在该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作为与不作为,即过错行为。[3](P203)
综观各立法例,皆在保险法上将危险增加区分为主客观不同的情形,但主客观危险增 加的区分标准并非完全相同。德国法中的“意思”与法律上评价是否有可归责性的“过 错”并非一致。因此,德国保险契约法在适用中,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须在“意思”基 础上再考虑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过错)而异其法律后果,显得烦琐而无必要。[4](P133, P202)按台湾现行保险法以是否为义务人行为所致为标准,则须对其行为的主观因素作 出适当解释方能实现划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本旨。反观日本法上关于主客观危险增加以 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可谓一举中的,既能明确将两者进行区分,又与各自情况下 当事人保险法上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认定和法条适用紧密关联。所以,不妨采此标准为 法律上的划分。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重要危险增加进行主客观区分的类型化,而对两种 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却作相同的规定。该种立法形式不能体现出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 的法律理念,无法公平而效率地实现对通知义务人的保护和对保险人的救济。
三、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36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义务人及时通知,保险 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二是怠于通知,依当然解释,保险人当然可以要求 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并且无论是要求增加保险费还是解除合同,保险人对因危险增 加而致保险事故发生皆不负赔偿责任。从立法技术上来说,前款规定了危险增加通知义 务人履行义务后对保险人的法律后果,第二款则是对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关于 此条规定的其他缺漏之处前已述及,在此仅对法律后果的妥当性进行讨论。
(一)义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保险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1.关于保险费增加权和选择权
无论主观或客观危险增加,皆破坏了投保人与保险人间固有的对价平衡。对价平衡被 破坏的结果表面上不利于保险人,而实质上有害于由其他投保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因此 在主客观危险增加情况下,保险人若于通知后经重新估价风险后,认为可以继续承保, 则理应根据对价平衡原则对危险增加的部分加收保险费,以回复对价平衡。增加保险费 的权利旨在救济保险人承担风险增加所受不利益。只是根据该条规定,此时保险人享有 选择权,而如何选择法律上并未明示。因此,从字面意思来说,保险人既可选择加收保 险费以维持合同,亦可解除合同。理论上存在着一经危险增加的通知,保险人即可解除 合同的可能,解除合同亦不失实证法上的根据。若作此理解,该条显然对保险人利益保 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设置本旨 在于因客观情事的变化而破坏了保险合同对价平衡,而该危险增加的状况又属于承保风 险性质允许的范围之内。保险人不能在缔约之初对其评价,因此,通知义务旨在使保险 人对于变更了的风险重新评估,以决定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 收保险费即可继续承保回复对价平衡的情形下,应首先选择增加保险费,而在加收保险 费亦不能符合承保条件,危险增加致事故发生几率超出保险风险性质所允许的程度,保 险人才能选择他种权利进行救济。因此,保险法立法应限制选择权的行使或通过法律解 释来加以解决。
2.保险人解除权的效力
现行保险法第16条、第27条、第35条、第36条、第53条和第58条分别规定了不同情况 下的解除权,在这些规定中,有的涉及了解除权的效力,有的则未为明确。从保险法上 关于解除权效力的现有规定来看,解除权的效力并非完全相同。实务中遇到相应的情形 ,难免出现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保险人的解除权的性质和效力 进行讨论。
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自身有特别规定者应适用自身的规定, 无规定者自应回于民法。按民法理论,解除权为形成权,以单方意思表示而无须经他方 意思表示配合即发生法律效力。危险增加情形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属于履行合同中的 解除权,可以在合同履行的范畴讨论。一般认为一时性合同解除权原则上具有溯及力, 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权原则上无溯及力。[5](P439,P441)至于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有 溯及力的问题,学者们持溯及力肯定说、否定说与折衷说三种观点。按肯定说,保险合 同解除权原则上有溯及力,发生双方对待给付恢复原状的效果,保险人对其解除前的保 险事故发生不负给付责任,投保人应返还受领的保险费。按否定说,保险合同解除无溯 及力,只向将来发生效力。解除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履行的给付依然有效存在。折衷说区 别不同情况考虑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认为保险费返还的情形下,解除权有溯及 力,不返还保险费情形下则无溯及力。[6](P34-P37)我们认为,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 有溯及力,首先应看解除权的性质,其次要保护守约方,三应考虑保险合同的特性不仅 在于对价性,更在团体互助性。由于解约对保险人并无实益,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 一方交付保险费后,保险人即已承担了风险,在精神上使他方减少忧虑,在物质上于保 险事故发生时负给付保险金义务使其获得物质补偿。无论事故发生与否,解除前,一方 都已享有合同利益,因此,继续性合同原则上要维持其效力。解除权的本旨在于使合同 关系消灭并回复致如以前未曾缔结合同的状态。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亦不能违反其本旨, 原则上应有溯及力。
3.解除权的行使
危险增加使保险人具备解除权条件后,只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我国并不采取“当 然解除主义”,因此,保险合同具备解除条件时并不当然解除。若使合同溯及的消灭, 还须解除行为。解除行为以意思表示为之,并发生合同关系溯及既往的消灭的后果,因 此,是法律行为。同时,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决定解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无须 意思合致,保险人一方只须将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于相对人,无须对方的同意即发 生合同解除的效果。解除权的行使为法律行为,且为单方法律行为,则不能不涉及向何 人为意思表示,以何种方式为意思表示,在何种期限内为该形成权的意思表示。
关于以何种方式为解除的意思表示,保险法无明定。实务中常由保险人以书面通知方 式作出。但该通知除双方约定之外,既然保险法未为明定,则为非要式行为,保险人未 为书面通知,只是承担举证的不利,并非未为书面通知而生未通知的效果。
4.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解除权的比较法分析
参诸各国立法例,日本商法典第656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因不可归责于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的事由,致使危险显著变化或增加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契约,但该契约只对将来 发生效力。韩国商法于第652条第二项规定,保险人从接到第一款之危险变更、增加的 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请求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规定, 凡危险增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者,保险人于危险增加后不但得终止契约,且该 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与其到达时或为对方了解时立即生效,在危险增加不可归责于要 保人时,保险人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于要保人接到保险人所为终止契约之表示一个月后 生效。在第27条规定,保险人须在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之一个月前先通知要保人。即在 一个月期间内,契约不失其效力,要保人于此期间可另觅保险人订立契约,以免失其保 障,并且因归责于要保人所致之主观危险增加,虽未经保险人终止契约,于危险增加发 生事故后,保险人亦不负理赔之责。
从各国规定来看,日本法将危险增加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分主观危险增加与 客观危险增加。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契约丧失其效力,无论通知义务履行与否, 简洁利落。在客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只向将来发生效力,实质上类 似合同终止的效力。同时亦严格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行使时间,规定保险人自接到通知 之日起应尽快行使解除权,否则视为承认该契约(日本保险法第657条第三项)。而德国 保险契约法在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保险人自知悉后立即通知,不得迟延。其不同点 在于,保险人行使终止权时,其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根据危险增加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 而发生效力的时间不同。因可归责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保险人接到通知后得立 即进行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并且契约自为对方理解和到达时立即生效。而因不可归责 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则均于危险增加通知后一个月期满时,保险人的终止权才 生效力,最为周到温和。但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1)规定,在因义务人过失致主观危 险增加场合,在其行使解除权前发生的因该危险增加所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免除给付 义务。韩国保险法亦于此场合规定保险人仅得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我们认为,我国 现行保险法不仅对此情形下保险人解除权规定显有缺失,而且其本身是否妥当亦不无疑 问。保险合同为继续性合同,其性质要求尽量促使其维持合同,而不是放纵其解除合同 。纵使解除合同亦不能如一时性合同那样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同时,基于保险的团体 互助共济性质,投保人本是弱势群体,其订立保险合同旨在分散风险于其群体,只因自 己无力组织该风险群体而借助保险人之中介。因此保险合同不能象一般民事双务合同那 样具有对等性,因危险增加不问归责于义务人与否皆解除合同。我国保险法解除合同的 规定对投保人过于严苛,在此情形,令义务人对因主观危险增加所致事故产生的损害不 负给付义务已足,再令其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险保障,对于双方皆非有利。在怠于通知 时,我国保险法由于不分主客观危险增加,因此,既可增加保险费又可解除合同,但对 因危险增加所致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从我国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规定来看,未区分主客观危险增加而异其效 果。在履行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但在第二款规定若怠于 通知时,保险人对于因危险增加所致事故发生不负给付义务。按立法技术来看,怠于通 知的法律后果显然重于适当通知时的后果,因此,可将前款理解为及时通知的法律后果 ,后者为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但第一款的后果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对因危险增 加导致事故发生是否负给付义务未为明定。在增加保险费情况下,保险人继续承保自应 承担事故发生的给付义务,没有问题。但在解除合同场合,若有溯及力则自不负给付义 务,只是现行保险法对此未予明示。因此,若采解除权溯及力说,则在怠于通知下,法 律后果显比及时通知情形下为重,前者解除下尚有溯及力,不负给付义务,怠于通知时 则更不必作此画蛇添足之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法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方面应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 为标准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前者因具可归责性而规定较重的后果,在此 情形,因可归责于义务人的事由使以缔约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估计的风险发生几率严重增 大,且义务人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违反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据此,可赋予保险 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或合同终止权。这时因终止权为形成权,自其生效之时起仅向将来 发生效力。而在生效之前,因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所致的损失显然不应由保险人 承担,因此在立法上不妨规定,在保险期间内,终止权生效前,因危险增加而致保险事 故发生,保险人不负给付义务。此时,不负给付义务非因终止权为形成权的效力使然, 而因系惩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归责性所致。我国保险法应一并规定终止权的效力、 行使方式与除斥期间。而在客观危险增加情形,相较于主观危险增加而言,因其客观上 虽改变了对价平衡,对保险人不利,但主观上并无可归责性,实情非得已。保险合同不 能因为提供保障而限制义务人正常的生活自由。此种情形,只违反对价平衡,并未违反 诚实信用。基于保险的团体互助性与继续性合同的特点,应尽量维持其合同效力,以免 被保险人失其保障,德国的立法不妨参考。
(二)义务人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行保险法在第36条第二款规定了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对因该危险增 加而致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依当然解释,自得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这对保 险人较为有利。在危险增加怠于通知时,由于危险增加使合同双方的对价平衡状态破坏 ,而又应通知而未通知,同时破坏了诚信原则。因此,法律自可赋予义务人比适当履行 通知义务情形为重的后果。鉴于此种情况与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形皆违反对价平衡与诚实 信用,各国立法例多规定此时与主观危险增加相同的效果。我国不妨在未来保险法立法 时斟酌参考。
收稿日期:2001-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