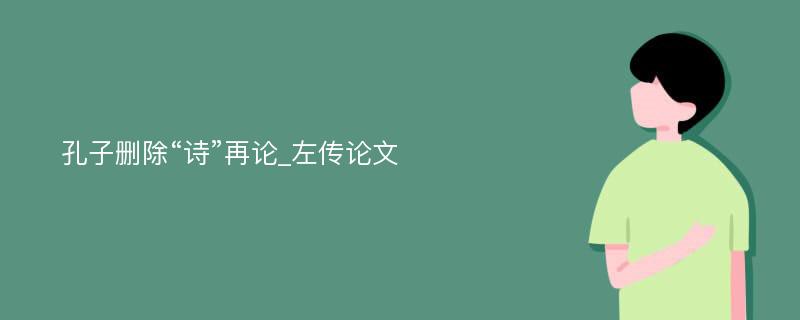
再议孔子删《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再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春秋中期至孔子时代约一百五十年间,《国风》作品产生的数量也许不少,但被编入诗文本而保存下来的,却仅有寥寥可数的十篇。这十篇作品包括《秦风》五篇:《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陈风》三篇:《株林》、《月出》、《泽陂》,《曹风》两篇:《鸤鸠》、《下泉》。从总体上来看,这十篇作品表现了与春秋前期诗歌明显不同的思想特点:春秋前期的各国风诗,尽管《诗序》均以“美”“刺”为说,但以男女风情之歌为主体的内容则多与《诗序》之美刺不相吻合。而这十首作品,除《陈风》中的《月出》与《泽陂》,因其所抒写的思念之情由于所思对象与性质的不确定性而难以评判之外,其余诸诗均表现了相当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诗序》与诗义基本吻合。这种情况说明,《国风》的编辑在经历了“乡乐唯欲”的声色追求之后,出现了一种向政治伦理回归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上述诸诗中时代最晚的《曹风·下泉》产生于公元前510年前后,其时为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岁。因此,我们不能不把这些诗歌被编入诗文本的事件与《诗经》学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孔子“删诗”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 一、孔子是否删《诗》 在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之后,汉儒多笃信不疑,至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始对《史记》之说提出怀疑,之后异说不断,孔子是否删《诗》遂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否定孔子删《诗》的种种论述,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古诗三千不可信。第二,孔子仅说“正乐”,未说“删诗”;“正乐”与“删诗”不同。第三,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已观乐于鲁,所奏乐次已与今本《诗经》次第相去不多。第四,孔子无位于王朝,以其影响不足以删《诗》。第五,孔子若“删诗”,不当存“淫诗”。第六,孔子若删《诗》,不当删其盛、存其衰。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因为不了解《诗》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不了解孔子时代《诗》文本存在的基本状态才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与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诗乐”一体,“诗”就是以“乐”的方式存在和传播的。因此,以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为理想的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术精神,把整理《诗》的行为称之为“正乐”,正表达了他对周代礼乐精神的坚持与守望①。 除了通过反驳前人的质疑来论证孔子删《诗》一说的真实性之外,“诗三百”这一名称的特殊性也能为孔子删《诗》一说的成立提供支持。在先秦典籍当中,人们在指称诗文本时,最习惯使用的称名方式是《诗》,除此之外,还有直接称其类名,如《大雅》、《周颂》或直引篇名的。但是,在《论语》所载孔子的言语中,却出现了两次称《诗》为“诗三百”的情况: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 《礼记·礼器》中也出现过一例相似的用例:“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④这些材料中的“诗三百”,前人多读为“《诗》三百”,释之为“《诗经》三百篇”。不可否认,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理解《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这句话时。但是,仔细分析这三条材料,其中“诗三百”却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的叙述中,“三百”明显是作为一个表现数量之多的定语出现的,作为一个虚指《诗》之篇数的概念,这里的“诵诗三百”,实际上表达的是“诵《诗》很多篇”的意思,因此后文才有“虽多,亦奚以为”的反问。而孔子以“思无邪”来评价的“诗三百”以及与“一献”、“大飨”、“大旅”之礼相对而言的“诗三百”,则更适合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专用名称来看待。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句评价来看,这个“诗三百”,很可能就是孔子自己修订的、与当时通称为《诗》的“先王之书”略有区别的诗文本。由此而言,“诗三百”这一名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聘问歌咏仍然盛行的鲁襄公、昭公时代,它只是一个虚指《诗》之篇数的概念,《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叙述即发生在这一时期。至孔子删定《诗》文本之后,“诗三百”一名,经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使用与评价之后,始具有了特指孔子所定《诗》文本的意义。 先秦史籍中提及“诗三百”的,除了上述三条材料之外,还有《墨子·公孟》: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⑤ 综观《墨子》全书可知,《诗》、《书》也是墨子所推崇的“先王之典”,曾被多次正面地称引⑥。可是,他为什么对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行为要进行激烈地批评呢?这除了与墨家一贯反对儒者“繁饰礼乐”的思想有关之外,儒家诵弦歌舞的“诗三百”与墨子所推崇的《诗》并不相同,应当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对待《诗》与《诗三百》的不同态度,为《诗三百》是经过孔子删定的《诗》提供了旁证。 二、孔子删《诗》的时间 确认孔子删《诗》一事的真实性之后,孔子删《诗》发生的时间随之成为问题。历史上赞成孔子删《诗》的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持早期说,即认为孔子删《诗》活动发生在其周游列国之前。其中翟相君《孔子删诗辨》一文⑦,直接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记述,将这一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⑧,则以孔子晚年聘问歌咏之风早已消歇,且“删诗”与“正乐”无关为由,提出孔子的删诗活动一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即孔子四十六岁之前。与“早期说”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依据《论语·子罕》孔子的自述之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把删《诗》的时间确定在孔子晚年反鲁之后。 实际上,被翟相君《孔子删诗辨》引以为据的《史记·孔子世家》之文,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就提出过怀疑:“时为定公五年,恐未曾修《诗》、《书》、《礼》、《乐》也,疑衍。”⑨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则云:“此但言孔子不仕,隐居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耳。唯既未尝仕,便不当云‘退’。当删‘退而’二字。”⑩那么,孔子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完成删《诗》这项工作的呢?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时代《诗》文本的流传情况,再结合孔子一生的经历来确定删《诗》行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 首先来看孔子时代《诗》的流传情况。春秋时代最负盛名的文化活动,无疑是风行于各诸侯国的聘问歌咏、赋诗言志。而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就是有一个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诗》文本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经详细记载过吴季札聘鲁时请观“周乐”的情况: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11) 因为周公的缘故,鲁国一直享有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的特权。至春秋中后期,在周王室因王位之争而动荡不安之际,“周乐”得以在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密的鲁国保存下来。根据《左传》的记载来看,其时鲁国所存的“周乐”体系(即音乐形态的“诗”),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结构已与今本《诗经》相去不远。这一结构的《诗》文本,是春秋中前期齐桓公“尊王攘夷”所带来的周礼复兴的产物。在此之前,人们引以为据的《诗》,则是东周初年平王恢复周礼、重修礼乐的成果。这两种《诗》在结构上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颂》是否被纳入《诗》中。《左传》所载“周乐”形态的《诗》,以风、雅、颂合集为主要特征;而形成于东周初年周平王时代的《诗》文本,则只是风、雅合集的《诗》,《颂》仍然是以独立的形式流传的(12)。从传播的角度而言,在“《左传》周乐”版的《诗》流传之初,这两种形态的《诗》必然在一定的时间段落中发生交集。尤其是传播方式单一、传播途径很不发达,而且周王室已没有足够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的春秋中期。《国语》、《左传》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国语·晋语四》:“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13)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前句出自《小雅·小曼》,后句出自《周颂·敬之》) 《左传·文公十五年》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 《左传·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引文出自《周颂·赉》) 《左传·成公二年》齐宾媚人云:“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引文出自《商颂·长发》) 《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引文出自《周颂·敬之》)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对曰:‘……《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14) 上引材料中,《晋语四》公孙固与郑叔詹之引《商颂》、《周颂》,发生在公元前642年,《左传》臧文仲引《周颂》而称“《诗》曰”,在公元前638年;季文子引《周颂》而称“《诗》曰”,在公元前612年;晋邵成子引《周颂》、齐宾媚人引《商颂》俱称“《诗》曰”,分别发生在公元前598年、前589年;而楚声子之并引《诗》与《商颂》,则发生在公元前547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诗》并未以统一的形式在诸侯各国流传。更进一步而言,从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鲁国人最先引《周颂》称之为“《诗》”开始,晋人、齐人也先后跟进,说明到公元前6世纪初,《风》、《雅》、《颂》合集的《诗》已在以鲁、晋、齐等与周王室关系亲密的诸侯国开始流传,而与此同时,迟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楚国流行的却仍然是与《颂》分立的《诗》。 楚声子并引《诗》与《商颂》的公元前547年,孔子四岁。也就是说,到孔子时代,尽管《风》、《雅》、《颂》合集的《诗》已在齐鲁等地流传,但从整体上看,《诗》的传播实际上步入了一个杂乱无序的历史阶段。 再来看孔子的一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幼年贫贱,“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岁前后始任委吏;三十而立,齐景公适鲁,问孔子秦穆何由称霸;三十四岁,孟僖子将卒,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三十五岁,“三桓”攻昭公,孔子带弟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景公”;三十七岁,因齐景公弗能用孔子,孔子自齐返鲁。其时鲁国“三桓”专权,昭公失位,之后更发生了季氏家臣阳虎囚季桓子而专鲁政的事情。所谓“陪臣执国政”,“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于是,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孔子未求出仕,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授徒讲学、培养弟子之上,“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至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出任中都宰,继而升任司空、大司寇;相传适周问礼事也发在生这一时期(15);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而摄行相事,诛少正卯。鲁用孔子而齐人惧,是年,齐人遗桓子女乐,孔子怨而去鲁,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活(16)。十三年中,他游走于卫、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国之间,甚至一度打算西行见赵简子,但窦鸣犊、舜华之死让他临河而返。“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失败,不断地打击着孔子干政的热情。至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此后,鲁哀公虽亦问政于孔子,“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鲁定公四年(前506),秦哀公为申包胥赋《无衣》,这是《左传》所记载的最后一次赋诗活动发生的时间,其时孔子四十六岁。也就是说,孔子四十六岁之前,适逢赋引风气最为盛行的襄、昭时代,其时鲁国仍然保留着完整的“周乐”,而孔子的行踪也未超出《风》、《雅》、《颂》合集的《诗》广为流传的齐鲁之境。尽管其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但整个礼乐系统尚在维持与运转。就孔子而言,还未发生“礼乐废,《诗》、《书》缺”的事情。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们都找不到这一时期需要孔子来删《诗》正乐的理由。 时至孔子晚年,则景况大不相同。鲁定公四年之后赋诗活动彻底走向沉寂,这缘于整个社会礼乐制度的加速崩坏。我们知道,在鲁昭公后期,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出居狄泉长达十年之久,后在以晋国为首的诸侯国的帮助下得以入居成周。当周敬王再次向晋国提出了“城成周”的要求时,“勤王”已成为晋国沉重的负担。《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了晋范献子对于此事的看法:“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作为霸主的晋国抛弃王室,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之后,鲁定公四年召陵之会,晋失诸侯;同年,吴国败楚。“竞于道德”的时代开始向“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过渡。这一系列颠覆周礼、使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事件,直接导致了赋诗、引诗之风在刚刚经历襄、昭时代的高潮之后陡然衰落。当《诗》、《书》、《礼》、《乐》失去了现实的功能和需要时,散亡就成为其必然的命运。至鲁哀公时,乐人纷纷去鲁,“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17),曾经完整地保存于鲁国音乐机关的“周乐”,随着乐人的离散而残缺散佚遂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在整个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孔子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出仕,之后由中都宰一再升任而至大司寇摄行相事;从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因不满鲁君、季氏接受齐国女乐而去鲁,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自卫反鲁,长达十三年的时间,他游走于卫、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国之间。在此期间,以“好古,敏以求之”自评的孔子,对于《诗》在诸侯各国流传的混乱情况必然有所了解与掌握。至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面对乐人离散、《诗》《书》残缺的现状,对于“不求仕”的孔子来说,无论从教授弟子的需要还是保存周礼文化的责任感出发,正乐删《诗》都成为迫切的问题。 如果以孔子对求仕的态度为标准,我们可以把孔子的一生以“自卫反鲁”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孔子积极“求用”。两度适齐,多次去卫,以及欲西见赵简子等等,都是为了能被任用,企图通过求用来实现“从周”的政治理想。与此相应,早期的孔子在培养弟子时,十分注重其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等,表达的正是这一时期孔子对于《诗》的看法。《论语》记载的“孔门十哲”中,分别以“德行”、“言语”、“政事”而见称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等人,与孔子的年龄差距多在三十岁左右,其中子路与孔子更是只差九岁。在孔子周游列国之时,众弟子的事迹也多见载于史籍。他们无疑都是在孔子去鲁之前即归于门下的弟子。而其中以“文学”闻名的子游与子夏,与孔子的年龄差距分别是四十五、四十四岁。即使如一些学者所言,“陈蔡相从,子夏与焉”,把子夏与子游作为孔子晚年所授弟子的代表人物来看也是合适的。从颜渊、子贡、子路等人以“德行”、“言语”、“政事”闻名到子夏、子游以“文学”而见称,正好反映了孔子人生理想与学术重心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在司马迁的记述中也得到了反映。《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8)经过前文的分析,以及紧随其后的“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叙述可知,司马迁所说的因“礼乐废,《诗》、《书》缺”而发生的“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一样,均发生在孔子自卫反鲁之后。除此之外,“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叙述,也进一步证明了孔子晚年着力于古代文献整理的事实。 纵观孔子一生,“自卫反鲁”实质上宣告了孔子政治生涯的终结,此后的孔子真正地变成了一位“教授老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0),应是孔子对其晚年讲学生涯的自我总结。当通过干政来恢复周道的愿望在现实的打击下最终破灭之后,聚徒讲学、整理文献不仅成为孔子晚年的职业,也成为他传承周代礼乐文化的唯一途径与选择。也只有立足于此,我们也才能理解孔子自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1)的真正内涵。 三、孔子对《诗三百》的删定 澄清了孔子删《诗》的真实性以及删《诗》的时间等问题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诗经》中属于春秋中后期的十首作品整体地表现出了与春秋中前期诗歌不同的政治伦理倾向?它们有没有可能经孔子之手被编入《诗》中? 通过研究《诗》文本的形成史我们发现,诗文本的每一次编辑,都是在前代所传文本的基础上,通过采集当世或稍前时代创作和流传的诗歌作品加以编定的方式完成的。伴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被累次编辑的《诗》,除了辑录专门为仪式创作的诗歌之外,主要来源于“献诗”与“采诗”两途(22)。那么,当删《诗》正乐作为孔子的私人行为发生时,失去了礼乐制度保障的孔子有没有条件搜集到这些作品呢? 《秦风》五篇,是这十首作品中时代较早的作品,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距离孔子时代大约一个世纪。尽管孔子一生未能至秦,但百年之间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频繁发生的会盟、聘问乃至战争,仍然让孔子十分了解秦国的史事。《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齐景公问孔子秦穆公称霸的原因,孔子答道:“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23)而且,在孔子所教授的弟子中,不乏来自秦国的秦祖、壤驷赤、石作蜀等人,他们也可能带来关于秦国的种种知识。孔子既然称赞秦穆公“其志大”、“行中正”、“虽王可也”,他必然也会思考秦国“霸小”乃至后来“诸侯卑秦”的原因。在他最终删《诗》正乐时,把讽刺秦穆公“死而弃民”的《秦风·黄鸟》,讽刺秦康公忘父之业、弃其贤臣的《晨风》、《权舆》等诗纳入《诗》中,与歌颂秦仲、秦襄公的《车邻》、《驷驖》并列,表达了孔子对政治兴衰的思考。 而陈、曹两国,则是孔子周游时亲历之地。在一个崇尚“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时代,对于“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24)的孔子来说,通过歌谣俗谚来了解民情政事,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陈风》三篇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陈灵公时代,距离孔子出生约五十年。其中《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均与在位者好色相关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孔子到达陈国,居陈三年之前,卫灵公是唯一一位礼遇孔子的国君。但是,“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孔子遂至陈”(25)。卫灵公之“好色”是促使孔子再次去卫的直接原因。那么,在孔子居陈之后,讽刺陈灵公君臣“好色”的《月出》、《株林》、《泽陂》等不能不对孔子有所触动。将“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合观,诸诗之入《诗》,也在情理之中。 《曹风》两首,一为赞美君子“其仪不忒,正是国人”的《鸤鸠》,产生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期;一为歌颂郇伯(晋臣荀跞)能“念彼周京”,“四国有王”的《下泉》,产生于公元前510年前后,其时孔子已经四十二岁。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6),所谓“君君”,即《鸤鸠》“其仪不忒,正是国人”之义;而诸侯“勤王”更是周礼精神之所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样两首契合周代礼乐精神的诗歌,很难不被孔子采入《诗》中。而且,作为《诗》中时代最晚的一首诗,《下泉》的入《诗》,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自是以后,诸侯不复勤王,故列《国风》,《诗》亦终于此。”(27) 孔子周游列国时途经的卫、曹、宋、郑、陈、蒲、蔡、楚等国中,其风被列入“周乐”的还有卫、郑两国,为什么只有陈、曹之风补入《诗》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前文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十首作品会整体地表现出与春秋中前期诗歌不同的政治伦理倾向——共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孔子的思想倾向。在春秋时代,由于地处殷商旧地,久承殷商文化重声传统的浸淫,加之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推动,郑、卫两地成为当时新声靡乐最为兴盛发达的区域。周代礼乐制度下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它与献诗“补察时政”的政治目的基本相同。但是,东周以后,“采诗观风”的行为背后包含了更多满足声色享受的欲望追求,这是春秋中前期以郑、卫两国诗歌为代表的,并无讽刺内容的《国风》作品大量汇集宫廷的根本原因。这部分作品被编入《诗》中,成为备受后世理学家诟病的“淫诗”。“淫诗”的出现反映了美刺名义下“乡乐唯欲”的实质。至孔子时代,新声靡乐更加发达,执政者耽于女乐而怠慢朝政的事情时有发生。季桓子接受齐人女乐,三日不朝一事,更是导致孔子去鲁周游的直接原因。因此,孔子不仅十分明确地表达对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兴音乐的反感:“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8)同时,他甚至把“放郑声”提升到了治国安邦之法的高度:“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29)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卫之地的靡靡之音自然不会被孔子采入《诗》中。正是由于孔子的选择,《诗经》中春秋中后期的诗歌才表现出了与中前期明显不同的政治伦理倾向。 孔子对《诗》的删定,除了增入上述诗篇,《鲁颂》之入《诗》也是孔子所为。除此之外,他还进行了删削诗篇、调整乐次、雅化语言等一系列的工作。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在《两周诗史》一书第七章第二节“孔子对《诗三百》的删定”中已做过详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注释: ①在《两周诗史》第七章,笔者对孔子删《诗》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针对否定孔子删《诗》者的质疑所做的论证,本文不再赘述(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页。 ③刘宝楠《论语正义》,第525页。 ④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8页。 ⑤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6页。 ⑥参见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⑦参见翟相君《孔子删诗辨》,载《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⑧承蒙徐正英先生厚意,使我能够在他的新作《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未刊之前有幸拜读,在此衷心感谢! ⑨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9页。 ⑩蒋伯潜《诸子通考》,中正书局1948年版,第54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1—1164页。 (12)相关论述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第四章“两周之交的诗歌创作及周平王时代对诗的整理”及第六章“春秋前期风诗创作的勃然俱兴与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 (13)《国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6册,第100—101页。 (14)上述《左传》引文,分别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95、614、713、798—799、818、1120页。 (15)《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十七岁适周问礼,《史记索引》云:“《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盖系家亦依此为说而不究其旨,遂俱误也。……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语也,乃既仕之后言耳。”(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册,第1909页) (16)《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为“十四岁”;司马贞《索引》云:“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计至此十三年。”(第6册,第1935页) (17)刘宝楠《论语正义》,第730页。 (18)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6册,第1935—1936页。 (19)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54页。 (20)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70页。 (21)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51页。 (22)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绪论》第二节“《诗经》中的歌与诗”。 (23)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6册,第1910页。 (24)子禽问子贡语。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4页。 (25)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6册,第1921页。 (26)刘宝楠《论语正义》,第499页。 (27)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页。 (28)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97页。 (29)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21—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