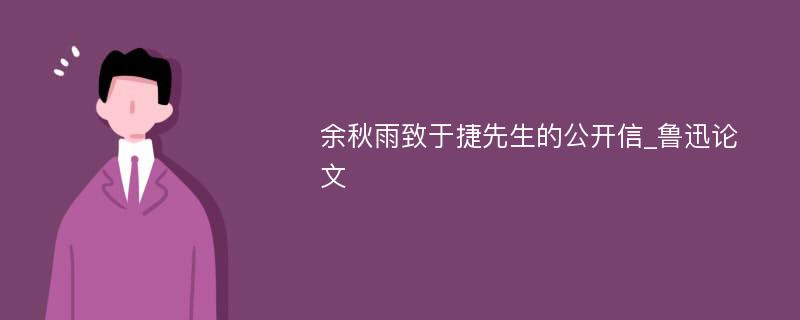
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雨论文,一封公开信论文,余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余杰先生:您好!
我还在“千禧之旅”途中。回国后接到的电话多数都提到大作《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今天又有一位记者远道送来了复印件,拜读了。大作的标题是第二人称的问句,我理应作个回答,也感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
细读大作,您要我忏悔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石一歌”,二是《胡适传》,然后归结到整体表现。略作说明如下:
一、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
也是事出有因。林彪事件爆发,我们从军垦农场回城,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被逮捕,毛主席下令复课,教师回到工作岗位,全面编写教材,我这个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人也被学院军宣队分配到一个各校联合的教材编写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的103、104室。当时这幢楼里同样的教材编写组有二三十个,我去的那个组编鲁迅教材,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教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吴教授,都刚刚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来。又有一个核心组,除他们两位外还有新入学的一些工农兵学员,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改造学校、领导学校”。我们几个被领导的组员都是各个学校的教师。教材组属中文系总支领导,但在市里都归市写作组管,统称“写作组系统”,这个系统很大,可能把现在的宣传部、教委、社科院、出版局、文联全都包罗进去了。真正的写作组很小,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老人马,加上后来的一些工农兵。曾有一个联络员到过我们的教材编写组,但他也不是写作成员,借调来的。教材编写组人员变动很大,吴教授很早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
到我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离开,这个教材编写组编印了《鲁迅小说选》和《鲁迅杂文选》各一本,署名是“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我参加注释《祝福》;写了半本《鲁迅传》的草稿,还没有印,我参加了其中鲁迅在广州一段。这个教材组里的几个工农兵学员和他们的同班同学写过一本给小学生看的《鲁迅的故事》,署名“石一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署名。
我离开后的经历因与这个教材组无关,留得以后在自传中细说。只是后来听到,在我一九七五年生肝炎养病之后,署名“石一歌”的应时文章不少,不知是谁写的,写了些什么。我因多数在故乡山间,无缘读到。估计会写两个方面,响应“批林批孔”和“评水浒”,这都可牵涉鲁迅。这些文章在“四人帮”垮台后当然都受到过清查,什么结论不清楚,据我判断不会太严重,因为在写作组系统它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外围的笔名。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我倒是喜剧性地用过一次“石一歌”的名号。在那最紧张的十月,有一个鲁迅代表团要去日本访问,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也在里边,原定的团长是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但他问题严重,照理不能去了,却一时无法向日本解释。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少将临时掌管上海大局,派了两位先生来找我,说从一些干部子弟那里知道我的思想倾向,要我随团出去起“阻止”作用,一是阻止朱离队出走,二是阻止朱离开讲稿发言,并规定代表团一切讲稿都由我起草。但我以什么身份参加?一不是写作组成员,二不能在办手续时用上海戏剧学院的证件又号称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教材编写组,两位先生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用暧昧的“石一歌成员”的说法。出去了十二天,回来接受我汇报的已是新上任的宣传部长车文仪先生。
总之,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是不对的。没想到这两年因我的关系,“石一歌”居然逐渐提升到与“梁效”、“丁学雷”、“罗思鼎”并列的地步,我不知说什么好。
二、《胡适传》为何只有一个头?
作为鲁迅著作教材的参考资料,需要整理几个有关人物的“生平小记”,分配我和另外一位先生整理胡适。当时读不到胡适的任何书,无法写生平,只有一套解放后胡适批判运动中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集》一至八集,郭沫若先生题签,里边是几乎所有留在中国大陆的文史专家们写的批评文章,因此所谓生平小记全是从里边摘抄的。这份东西后来怎么拉长,由谁修改,为什么作为文章发表,发表时为什么用了我的名字,完全不知道。曾问过一个姓邓的老编辑,他说:“毛主席号召大学要恢复学报,又要求学报上用一些真名。我们缺少稿件,这一篇主要是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的一些教师修改的,但他们互相之间关系太复杂,用你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吧,可惜你的名字也像笔名。”我说:“我没有任何条件研究胡适,这篇是抄的,我不会再写了。”因此,这个所谓的“传”,只有一个头,再也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写到共产党最不喜欢胡适的那些事情。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至少没有读者来问为什么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如果说这篇文章被上面看中过,那他们为什么不下令继续写下去?
另一篇您提到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轶文》倒是我看了《中山大学学报》上的讨论文章主动写的,因为我查核《鲁迅日记》等材料可考定这篇未见于《鲁迅全集》的文章确实出于鲁迅手笔。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
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
从您的批判中我看到一种有趣的时代性隔膜,您用现代的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定稿权概念,寻找文句与署名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其实在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特例,是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的,所以才要花几年时间仔细清查。清查结果证明,大量需要真正负责的人,没有一个署过真名。
三、提点异议
看到大作中建立起来的“余秋雨=石一歌=写作组=一朝红人=“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一个快速推进逻辑,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了。恕我直言,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大行其时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转眼出了那么多叛徒、工贼、特务、内奸?我参与过后来的平反工作,反复思考过大量“专案组”所建立的逻辑思路,以及这种思路对所谓“材料”的运用。当时的“专案组”要被害人按照这个思路来忏悔,但我相信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获得通过。我在“文革”中代父亲写的忏悔至少长达五十万字,深知其间滋味。
“文革”中是不准指出这种逻辑思路的漏洞的,但我信任你的文化道义和理性能力,因此想略略探讨几句,请勿见怪。
您的这个逻辑长链在第一个扣子上就遇到了障碍,全部证据只是据称是我“当年同事”的人对你说,我是“石一歌”中最年轻的人。但这句话已足以证明这位“同事”的所疑,因为我说过,我见过的那本署名“石一歌”的著作全部是工农兵学员所写,即便硬把我推进去,年龄上也是最老。可见那个夸夸其谈的人完全不知道“石一歌”是什么。
那位“同事”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是,我受到过当时身居中央要职的一批人的“青睐”,第一个是康生。但略知“文革史”的人都知道,林彪爆炸之后,康生去了哪里?进一步的问题是,他们看上了我什么?当然是文章,那么是哪一篇?总不见得是那篇一看即知抄自别人、又只开了一个头的《胡适传》吧?于是说我还有“几十篇文章”。这就来了大问题,“文革”中有几十篇被康生等人看中的文章,至今逍遥法外、无人认领!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这个“同事”就犯了大罪,因为他明知这些文章的炮制者却隐瞒了二十几年没有揭发。
这只是一条逻辑长链上的一个漏洞,大作中其他几条逻辑长链我也不敢苟同,例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追叙自己与同一班级的造反派同学在“文革”初期的不同心理经验,就被上升到为全国的造反派辩护,为所有的红卫兵辩护,为他们的血腥辩护,再上升到辩护的目的是为自己开脱,开脱的原因呢?再上升一层,因为我是参与者。余杰先生,用这种批评方式就没办法研究文章了,因为这是几亿人参加的事,总要允许不同的人谈不同的体验。我至今认为,你所说的残酷是存在的,必须永远谴责,但大多数当年参加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人并不都是坏人,责任不应该由他们个人来承担。我说这番话并不是因为我是参与者,恰恰相反,我是我当时所在的高校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批判造反派的人,造反派掌权后受尽磨难;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多年致使我们全家八口人几近乞丐;唯一有可能救助我家的叔叔也死在造反派的批斗之下。当年,我如果稍稍巴结一下造反派,让他们与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打个招呼,说不定能多发几元生活费,改变全家的惨状,但我从来没有做过。然而到文革结束之后,我深感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应该经仇恨和惩罚提高一步;开始用比较平静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对头”。在我担任院长期间,对于因当初造反受到处分的在外地工作的毕业生,一再希望当地组织对他们不要歧视。我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最雄辩的身份:我是他们当年的对立面。
四、一个建议
您的文章很犀利,思路也很敏捷,这是优点,但这种优点也容易失控,尤其是在很多读者高呼“痛快”的喝彩声中。作为一个比您年长一辈的同行,我想提个建议,供您参考。
犀利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上面几段话也体现了这个意思,但我又不希望你在考证、调查中忙碌,而且事实证明,很多细节真实也会组合成一个大不真实。我只建议您固守两点:辨轻重、合常理。这比细节真实重要。
以我们已经展开的话题为例,要判断一个文化人在文革中的基本表现,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如:有没有在文革初期造反、打人、抄家、诬陷、罗织别人的罪名并进行大批判?有没有在文革后期明知邓小平整治有功却昧着良心批邓、批四五运动?有没有借运动之名迫害同行、老师、领导、朋友?与这一切相比之下,一个教师有没有参加过哪个教材编写组,这个教材组受什么部门领导等等,就比较次要了。在重要的地方犀利,刀笔生风,道义卓著;钻在次要角落,虽有抉隐发微的乐趣,却总也觉得暧昧甚多,难于透彻爽利,容易造成误伤。
至于合常理,也就是在犀利之前先作一些常识判断。不要,把犀利误解成对常识的颠覆,恰恰相反,它以常识为基座,又回归常识。如果真有常识妄颠覆,那便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文化研究了,外部形态反而犀利不得。又以我的事为例,其实稍作常识推断就可以明白事情大概的,例如我是在上海经历整整三年文革大清查后担任高校领导干部的,而且大家知道,又是一连几次本单位民意测验都名列首位的结果,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文革余孽”吗?还有,不管分析得多高,在如此灾难中有一篇谈胡适或读鲁迅轶文的文章,哪怕都是我写的,会成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吗?因此,常识会产生一种堤岸般的作用。
又说自己了,但我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请原谅。另外,大作说我参加“千禧之旅”是大言不惭地把一位记者的创意占为己有,这肯定说错了,可看看我已发表的文章。三个月前的事已颠倒,三十年前的事更应谨慎。请原谅我直言。
此致
敬礼!
余秋雨
2000年1月21日于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