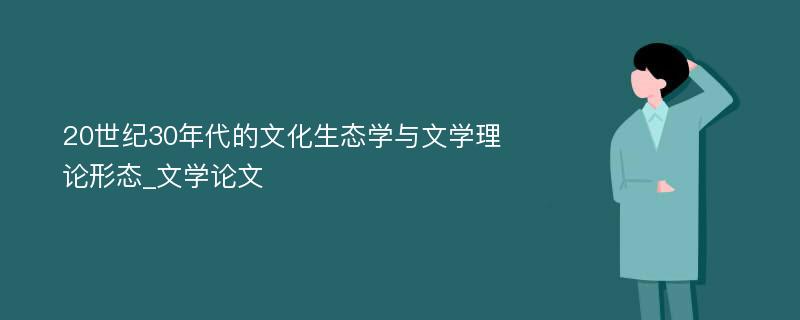
1930年代的文化生态与文学理论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形态论文,生态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文学不能离开文化,因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①,而文化则是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最为核心的“环境”,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部门”②。
文学理论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即被人视为与“经济”、“军备”并列的国家“势力”。③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活动方式,也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既包括客体之自然、社会的世界,也包括主体之情感、心理的世界,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世界,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客体、物质世界)”、“世界2(主体情感和心理世界)”、“世界3(主体创造的精神世界)”。文学及其理论世界自然属于“世界3”,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世界。作为由文学主体即文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3”,其存在形态为前两个世界的社会生态状况所决定,亦即由社会客观因素(经济、政治、教育、历史等)和主体经验因素(艺术素养、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所决定。
一
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其主流文化形态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因为广大农村教育出奇的落后,民众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文艺的创作、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在城市区域内进行。该时期(1938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是上海、南京、北平(现在的北京)三座城市。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因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城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北平虽然在政治上比不了南京,在经济上比不了上海,但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上却远远高于南京,也高于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经济、政治、学术的三分格局,在19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形态表现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个鲜明的理论印记表征就是南京文学与学术的乏弱以及上海“海派”与北平“京派”的对立。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文学与学术何以乏弱?这与政治中心环境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限制过多有关。在这样的区域,文人自然不敢放肆,理论领域里的探索不敢乱越政治的雷池。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由于军事强人掌权,其政治模式还基本上停留在“军政”阶段,蒋介石本人又十分崇信法西斯主义,在他直接掌控下的京畿之区,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意识形态管制较严,言论自由十分受限;即使在文艺领域,官方也给文人们制定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紧箍。这种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不甘受约束的文人都选择了政治意识形态大逃亡: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文人跑向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北上北平,南京所剩的也就是一些想吃官饭的平庸文人。在此情形下,南京文学界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什么作为。自古以来,凡政治意识形态管辖过严、政治标准第一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时代和国度,精神领域必然萎缩,各种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上海和北平的文坛出现“京派”和“海派”的对立;主要是因两地各自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两地不同的文化生态,陶铸着两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气,从而导致两地文人在创作文体、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北京的文人群体追求高雅、纯正、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旨趣;受殖民主义统治影响下的商业投机习气影响,上海的文人群体追求“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当然,这只是就地域文化的整体精神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京派”与“海派”概念的提出者沈从文对此说得也十分清楚:“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京,也已经有了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④ 因此,“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文人禀有的艺术价值观。
抗战以前,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集聚区域主要是北平和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文艺精英大批南迁,桂林、昆明、重庆都曾经成为193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文艺中心城市。战时的中国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偶有的理论争鸣与批评也都与战时政治有关,因此,谈及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时间上以抗战以前为主,地域上以上海和北平为主。事实上,1930年代文学领域的批评、论争和知识探讨,也主要发生在抗战以前的上海和北平。
先看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态状况。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与众不同。
从自然位置上说,上海地处长江口,交通便利,航运发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抗战以前,上海在行政区域毗邻国民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以后,南京陷落,成为汪伪政权的首府所在地。上海又成为日伪统治区的一个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主权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区域。“租界”享有独立的政治和司法权,成为国民政府治下区域的政治飞地。无论是“共产党”、“第三党”还是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只要逃到租界内,就可以安然无事。以法租界为例:“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此,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⑤ 多重政治空间给多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的上海因此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政治、文艺的博弈中心:它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集结地。
从经济状况上说,上海因其特殊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西方资本家在远东投资的最佳场所。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贸易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娱乐和消遣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这里是花花世界、销金之窟;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从发展历史上说,上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受西方人价值观的影响,上海人在经济上喜欢投机,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在商业活动中喜欢冒险投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放纵和刺激。西方殖民统治影响下的铜臭飘飞、人欲横流,上海人早已司空见惯。受此影响,上海形成了注重实用、势利的精神传统。在这个十里洋场,很少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见金钱而不眼开,也很少有人能够不趋时媚俗、追新逐奇。
1930年代的上海,其政治与生活上的多元、混杂特征必然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上海的商业环境给许多那里漂泊的文艺青年提供了谋生之路,以至于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气息十分反感的沈从文也一度说:“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⑥
左翼文学家正是“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随之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作品,想方设法加以推销。”⑦ 同样,那些留学归国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秉持的先锋文学意识,在上海找到了现代派文艺的试验场域。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商业化、政治化、前卫化、通俗化等数重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而“海派文学”的滋生,正是以此为文化背景。
再看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状况。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平是另外一番文化光景。该时期北平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⑧ 程度与上海相去甚远:“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是,30年代的北平经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除了电车以外,大部分北平人几乎没见过现代机器和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该城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大部分是一些分布在该市各处的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小工厂车间。”⑨ 以1933年的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12个主要城市之中,“北京工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⑩。到1935年时,北平的“工业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商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据1935年统计,在全市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到5.62%,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94.38%,其中商业资本占到50.58%。依然是以消费商品为主,而且其中粮食和副食品还是占主要部分”。(11)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绝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为社会现代化的硬指标之一就是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的政治中枢位置自然失去。然而,经济、政治的边缘化并没有导致北平文化发展中的边缘化。抗战之前的北平,其文化综合实力堪称中国的中心。
北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现实原因。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因其政权不稳,它一时还顾不上文化建设,许多重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留在北平,这就使北平的文化生产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二是历史原因。从明清两个朝代再到初期的民国,北平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已历数代,积淀已久,底蕴丰厚,其精神地位一时还难以动摇。三是文化自身的原因。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规律并不一样;在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实验器具马上就能投入使用,高楼大厦马上就能建造成功。文化的发展过程较之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它需要薪火相传,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其成也缓,其败也慢,不会随政治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也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就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文化大城;北平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同样,也不会因首都的迁徙,大厦将倾,成为精神领域里的破落户,此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然,京派和海派文学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受制于京沪两地文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文学理论生产的主体世界差异,这种主体世界的差异隐然折射出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重影响。从文学理论生产主体的教育背景来说,京派的自由主义者留学背景多为英美。英美国民价值理念奉行独立、自由、平等,政治变革喜改良而不喜暴力革命,尽管美国是以暴力革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但这个国家与英国文化渊源关系毕竟太深,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多与英国趋同。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部分留学日俄,俄国政治革命当时是“正在进行时”,日俄两国虽有宿仇,却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人在政治理念上多受俄人熏染,苏俄革命思潮对日本影响极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苏俄政治与文艺思想多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从政治出身来说,留学英美者多出身大户人家,而留学日本者多出身草根阶层。大户人家多是“被革命者”,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而草根出身的文化英雄则深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自然极力主张革命。
二
上海、北平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物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学生产主体世界的差异,这两者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状态,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形态的?客观的文化生态是如何通过主体情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生成造成影响的?弄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1930年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文化生态根基及其互相关系至关重要。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尽管从口头上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往往不敢对意识的作用展开分析,生怕被人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文化创造的实际情形来看,主体在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吾心就是宇宙”、“意之所在便是物”,从精神创造的角度来说,这些命题确能成立。如果不是站在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站在实践论的角度考虑,在文学领域里,意识的确能创生“物质”: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文学理论的设计模式,一旦通过相关手段物化出来,就能成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在1930年代,上海、北平的文化生态通过影响文学主体的下述成分,从而形成相应形态的文学理论:
一、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集居状态。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商业、金融、贸易城市,又有租界这样的特殊政治——地理空间,它既能给政治受迫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能给普通人提供较多的生活和就业机会。所以,早在19世纪末,四面八方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虽“沪上开销之大……而四方之人犹源源而来者,以上海所谋之事多也”。(12) 如果“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13) 这虽是小说家语,却也是19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之众生真实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金融冒险家、商业投机者的乐园,也是下野高官、失意政客的寓居之所、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空间;是先锋艺术家的实验之地,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谋生之所。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曾一度漂泊上海,尽管沈氏对沪上文坛的政治性质和商业气味极为反感,但他对上海本身的生活环境却十分怀恋,他在给友人的通信中强调:“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14) 为什么年青的沈从文只有在上海“才能够混下去”?因为上海数百万人口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贫民阶层,上海娱乐场所虽多,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大报、小报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文艺副刊等,成为底层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对象。写稿件、赚稿费成为有文字写作一技之长的青年们的主要谋生方式,沈从文、曹聚仁、徐懋庸、谢六逸等不同理论倾向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文坛上都十分活跃,报上曾有专文称沈氏为“多产的沈从文”(15)。文学市场拉动文学消费,文学消费推动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文艺之士走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良与不良现象,必然诱发相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反思,这是文学领域必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经验形态。两朝古都与现代新城、慢条斯理与行色匆匆、余韵悠长与机器轰鸣:这就是1930年代北平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文化生态图景。两种文化生态图景的差异实质上是传统手工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生活经验状态的差异,“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状态下文人经验形态的对立。借用德国现代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传统手工文化的特点是“闲适”,现代工业文化的特点是“震惊”。手工文化属于“经验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属于“体验文化”。“经验”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基础的淳朴生存状态,“体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遭到破坏,信息取代感觉与想象、冲突与对立取代和谐、机器支配人的生活状况。“经验”与“体验”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两种文化的对立意识集中在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文化心态中。谈到“乡下人”或“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说法,一般人都熟知沈从文的“乡下人”宣言(16),其实在1930年代,京派作家中作出这种思想表述的不止沈从文一人。李广田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件吧。”(17) 李健吾在评论李广田的诗文时则说:“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接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18) 京派文人普遍存在的“乡下人”心态,实际上是京派文人的生活经验形态在创作或批评上的一种理论折射,一种美学层面的理论还乡意识,这种理论还乡意识的表现,就是京派文人在批评与理论上的诗化风格的追求。(19)
三、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创造心态。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的影响,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洞察到这一点:“‘京派’与‘海派’,……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20) 鲁迅所说的“居处”,其实也就是地域文化环境,而他所说的“作家的神情”,则是指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心态。上海的文人大多生存比较窘困,许多人都有过居住狭小、昏暗、通风差、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经历,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文人没有条件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那个殖民化、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是文人的第一法则;而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走向反抗。大部分文艺青年走向了政治激进之途,他们深知:“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21),更为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一心为生活抗争奋斗的文艺家只顾得了当下,当然没法“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自然,那种深入细致、富有学理的学术论文在上海文坛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上海文坛所能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只能是一些零零碎碎,难见系统。北平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花花世界的喧嚣与骚动;虽然其商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但影响不了文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北平的文人都是生活处境优裕的教授、学者,他们没有上海穷文人的生活窘境,能够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学问;他们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多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考虑,其理论设想大都建立在人类生活常态这一暗含的假定之上,政治意识不强,很少从时局出发去考虑问题。他们谈天说地,谈生活,谈文化,“什么都谈,只除了政治”(22)。“纯正”(23) 的审美趣味、高蹈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事实上也只能在这种文化情态下才能生成。
三
与平、沪两地的文化生态、文人情态相对应,京派与海派两个地域文化派别所生产的文学理论也表现为文体与逻辑两个种类的差异。
理论文体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海派文人中的左翼文艺家因贴近政治、立场左倾、心态浮躁、情绪偏激等原因,坐不住冷板凳,其理论见解常常是以杂感、小品、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左翼批评家的理论文章虽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都近长篇文艺政论;京派文人大都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上面提到的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他们大都在高等学府供职,远离政治与商业,远离杀戮和恐怖,商业领域里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里的腥风血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于自己的象牙塔内,谈审美,论距离,讲象征,说趣味,构制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即使批评文章,往往也洋洋洒洒,钩深致远;至于专门的学术论文,更是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立论沉实,理足服人。
“京派”与“海派”文人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形态建构方面,其精神差异更大。
海派中的商业主义者,如张资平、叶灵凤之类的人物,其写作目标就是生活目标——赚钱享乐,而不是艺术,这类文人在文学理论上毫无建树,因为他们深知:高头讲章的理论文章根本卖不出去,换不成金币。
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在上海那样的商业环境里,他们从事写作一方面也要顾及挣钱,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因而,其写作的根本目标是政治而非金钱,那当然也不是艺术。左翼文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特质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和斗争性,因此,左翼文学理论一般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即使与纯文艺知识相应的讨论,也往往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成为思潮形态。
京派文人大都幽闭于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堂和自己家庭的书斋,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艺术领域中的商业主义者那样为金钱而奔波,自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24),他们也没有左翼文艺家的革命冲动。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活动,京派文人都比较讲究秩序,追求典雅和厚重,讲求趣味和水平。他们关注的是艺术自身的存在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他们对相关文学的探讨往往出于纯粹的知识与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深深的迷恋,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较深层次的知识形态。
当然,在纷然芜杂而又丰富无比的事实面前,任何逻辑概括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所谓“京派”与“海派”之说,也只是从两个地域的文学精神与理论形态的总体状况概括而言,理论上的实际存在情况却常常是“斩不断,理还乱”。以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而论,左翼文人穆木天与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可谓标准的“海派”,然而,他们在探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时,十分严肃认真,李金发的诗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商业主义市侩之气,穆木天的诗论也没有左翼理论家常有的机械左倾之弊。
注释:
① [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② 江流:《从本位文化说到本位文学》,《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
③ 王云五:《出版与国势》,《广播周报》第36期,1935年5月25日。
④ 沈从文:《论“海派”》,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
⑤ 薛耕莘:《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一)》,《史林》2000年第3期。
⑥ 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⑦ 沈从文:《“文艺政策”探讨》,《文艺先锋》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10日。
⑧ 近代以来,国人所说的“现代化”,如果不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其实就是指“西方化”的程度和水平。因此,著者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也主要以生活的技术条件与思想、艺术观念的西方化程度为标准。
⑨ [美]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⑩ 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11) 齐大芝、任安泰:《北京商业纪事》,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12) 1896年7月14日《申报》。
(13) 蘧园著《负曝闲谈》、颐琐著《黄绣球》合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4) 沈从文:《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15) 平凡:《多产的沈从文》,《社会日报》1932年7月31日。
(16) 沈从文:“我是个乡下人”(《水云》,《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萧乾小说集题记》,《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2月15日。
(17) 李广田:《〈画廊集〉题记》,《益世报》1935年3月20日。
(18) 李健吾:《画廊集·李广田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9) 在1930年代京派文人的理论文章中,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批评论文都有浓厚的诗化色彩。
(20) 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
(21)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2) 西谛:《“随笔”前言》,《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10日。
(23) 这是京派文人朱光潜在1930年代反复强调的一个文学标准。
(24) 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标签:文学论文; 沈从文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1930年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南京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海派风格论文; 文艺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