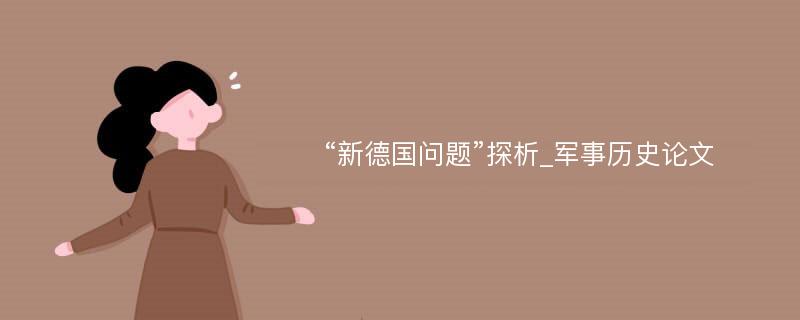
“新德国问题”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新德国问题”?它在“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分析和评价它们? 这些是本文尝试进行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新德国问题”的产生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德国是1871年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在这年“普法战争”的胜 利之中,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镜宫宣告成立。从1871年德国 第一次统一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两次以赤裸裸的战争政策向世界发难, 给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1949年,德国在统一了七十八年之后再 度分裂,固然是以美、苏为首的西东方“冷战”造成的;然而,德国的不少有识之士指 出:德国分裂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是他的侵略战争使德国再次陷入国家分裂的困 境。
1949年两个德国先后成立之时,德国人没有想到:这次分裂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1 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德国人又没有想到,国家统一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就实现了 。在老的德国分裂问题解决以后,新的德国问题又出现了。对此,德国国际政治学教授 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在他2000年出版的名为《贸易国家德国——新国际体 系中的德国外交政策》的长达五百多页巨著中指出: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解决了‘德国问题’以后不久,一个‘新德国问题’便展现 在世人面前:统一德国将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之中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围绕这个主题, 国内外学术界、政治—新闻界又在论争中提出一系列其它问题:德国外交政策的内、外 框架条件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对德国外交活动空间带来哪些影响?哪些因 素可以扩大、哪些因素可以限制德国的行动能力?德国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规范其根本方 向吗,抑或只需对迄今为止的根本方向逐步作些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变化要求?德国 外交政策的根本利益、目标、结构模式和行为准则变化了吗?其外交风格更新了吗?德国 能够、想要和将会在全欧洲、欧洲联盟或(只在)东欧承担霸权领导责任吗?德国将如何 看待其全球作用,会使其迄今为止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转为以全球为导向吗?民主制度 和西方一体化的价值取向在扩大了的德国中根深蒂固了吗?德国重蹈‘特殊道路’覆辙 从而导致内政、外交灾难的可能性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吗?(注:Michael Staack,Handels staat Deutschland.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 em,Paderborn 2000,S.18.)”
“新德国问题”的出现是很自然的。本来,大多数人都没料到德国会统一,也都不愿 看到8千万德国人统一的前景,这是美国前驻德大使弗农·A·沃尔特斯(Vernon A.Walt ers)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的场景(注:Vernon A.Walters,Die Vereinigung wa r voraussehbar,Berlin 1994,S.89.)。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看到德国统一。1990 年3月24日,她曾召集高级专家座谈德国统一问题,还让其外事顾问整理出一份绝密级 座谈纪要,集中表达了英国对德国人的负面看法与疑虑(注: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法国总统密特朗也不情愿 将来只同一个德国打交道。1989年12月20日,他在“柏林墙”倒塌以后不久就作为西方 三个战胜国第一位国家元首正式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注:详见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苏联 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先是坚持统一德国要保持中立,后在1990年7月1 6日德国联邦总理科尔访苏时表示统一德国有权自由决定其联盟归属,从而放弃了原来 反对统一德国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立场(注:Werner Weidenfeld/Karl-Rudolf Korte (Hrsg.),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Bonn 1993,S.137—138.)。苏联变化的动 因这里暂且不谈,上述国家领导人的对德态度都发出一个信号:他们担心统一德国会改 变迄今为止奉行的外交政策,重新威胁本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这是 “新德国问题”的要旨之所在。
如今,德国统一已经10年有余了,德国外交政策发生人们所担心的变化了吗?
二 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
(一)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实现
进入21世纪以后重新审视上述问题,应该说,德国外交政策已在军事安全领域发生重 大改变,即结束原来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辖区以外世界范 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对此变化,德国政治精英和学界人士的解释是:德国外交政 策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正常化”(注: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较为令人信服 的阐述,我认为是德国“时代”周刊总编和发行人特奥·桑默新近发表的一篇论德国外 交政策新作用的文章,详见Theo Sommer,“Geopolitik-Deutschlands neue Rolle”,i n:Deutschland,Dezember 2001/Januar 2002,hrsg.vom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Berlin,S.10—13.)。
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在1990年德国统一以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在世界范围 总共参加过120多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然而,联合国授权的军事救援行动却从未参加 过,理由是:德国的“基本法”禁止这样做(注: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较为 令人信服的阐述,我认为是德国“时代”周刊总编和发行人特奥·桑默新近发表的一篇 论德国外交政策新作用的文章,详见Theo Sommer,“Geopolitik-Deutschlands neue R olle”,in:Deutschland,Dezember 2001/Januar 2002,hrsg.vom Presse-und Informat 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Berlin,S.12页。)。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后,已 经实现国家统一的德国仍然恪守“军事克制文化”,没有派兵参战,科尔政府履行德国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是支付了100亿美元巨额军费。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欧 洲局势的急剧变化以及西方盟国的不断敦促,德国开始逐步承担起愈来愈多的国际责任 :1992—1993年间,联邦国防军卫生兵在柬埔寨设立了一所野外医院;1991—1996年, 联邦国防军直升机多次将联合国裁军督察员送往伊拉克执行督察使命;1992—1996年, 海军部队参与监督对南斯拉夫实施的贸易和武器禁运;1993—1995年,空军士兵在北约 负责监督南斯拉夫领空禁飞令的阿帕奇飞机中值勤;1992—1994年,约1800名联邦国防 军士兵部署在索马里,为当地联合国军队提供后勤服务;1992—1996年,空军出动近20 00架次,将13000吨援助物资运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1994年7月12日,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就联邦国防军在北约辖区范围以外派兵的问题作出判决。此后,德国参与海外军 事行动逐步升级:1995年底,联邦国防军出动一支约3600名士兵的部队,赴克罗地亚参 与国际维和行动(Ifor);1996年底以后,这支部队成为在波黑监督“代顿协定”实施的 多国维和部队Sfor(Stabilization Force)一部分;1999年3—6月,德国空军出动14架 托纳德飞机,参与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中打击,此后便作为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一部 分,负责科索沃某一地区的管理工作;2001年夏天,联邦国防军在旨在帮助斯拉夫人和 阿尔巴尼亚人和平共处的马其顿“红狐”行动中,承担了“领导国”(lead nation)角 色;1994年以后,联邦国防军约有10万名士兵驻扎在巴尔干地区(注:数字与事实均引 自Theo Sommer文章,Theo Sommer,“Geopolitik-Deutschlands neue Rolle”,in:Deu tschland,Dezember 2001/Januar 2002,hrsg.vom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 undesregierung,Berlin,S.12页。)。
本来,德国联邦国防军对他们在巴尔干的使命还没完全驾驭,2001年又发生了“9·11 ”事件!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战争迫使他们承担前所未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事重 任:既要投入国际反恐战争,同时又要(在欧洲大陆以外的中国边界线上!)参加阿富汗 维和行动。施罗德总理置别人指责他追随美国战争政策于不顾,明确表示要完全与美国 站在一起,支持国际军事反恐行动:向美国提供3900人的兵力,部署在阿富汗周围具有 地缘战略意义地区,用以防御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攻击;保障海事交通;撤离伤员和 进行空中运输(注:数字与事实均引自Theo Sommer文章,Theo Sommer,“Geopolitik-D eutschlands neue Rolle”,in:Deutschland,Dezember 2001/Januar 2002,hrsg.vom P 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Berlin,S.12页。)。德国甚至还派 出特种部队直接参与在阿富汗前线作战(注:这是2002年3月4日,美国军方一位发言人 在介绍美国最新对东部阿富汗地区的地面军事行动时,不经意间透露的消息。“秘密” 一经捅出,立即在德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对媒体赋予他的“战争总理”称谓,施 罗德总理直言不讳道:国家的正常化目标也包括军事行动(注:Sueddeutsche Zeitung,9.November 2001.)。
(二)德国国内对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的讨论(注:国际上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问 题的评论,详见“德国‘克制文化’的国际认同”一节。)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问题就已提出。以后,随着国际形 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不断飞速变化,德国国内对有关“正常化”问题的探讨也在不断延 续和深入。1990年10月3日是德国统一日。这天,德国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在柏林音乐堂举行的国家庆典讲话中指出:在欧洲历史上,德国第一次不 再构成争执的焦点;德国统一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和平实现的,是旨在争取人民自由和 欧洲新秩序的全欧进程一部分;德国愿为这一目标服务(注:转引自Helmut Hubel/Bern hard May,“Ein‘normales’Deutschland?Die souveraene Bundesre-publik in der auslaendischen Wahrnehmung”,Arbeitspapiere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92,B onn 1995,S.3.)。
1994年9月1日是俄国军队完成从德国撤军的日子。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彼德·施 瓦茨(Hans-Peter Schwarz)教授将这一天作为他一本新书的发端,着重分析“德国重返 世界舞台”的问题。他的核心命题与结论是:“重新统一”(注:德国历史学家与国际 政治学家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看法不同。Hans-Peter Schwarz是德国历史学家,他从历史 角度使用“重新统一”的概念。国际政治学家Karl Kaiser对此提法持有异议,认为: 德国不是重新实现统一,而是在民主制度的新条件下实现统一。KarlKaiser/Hanns W.M aull(Hrsg.),“Deutschlands neue Aussenpolitik”,Schriften des Forschungsinst ituts der DGAP,Muenchen 1994,S.1-14.)的德国无论是否愿意都将在欧洲发挥中心作 用;欧洲未来的塑造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态度。为此,他呼吁德国必须在 态度上作出改变,特别是要告别“冷战梦魇”;德国的处事态度必须“象其它欧洲民主 制国家一样正常”(注:转引自Helmut Hubel/Bernhard May,第4页。)。这里已经提出 了“正常化”这一中心概念。对战胜国从德国彻底撤军和德国获得完全主权,德国联邦 国防军总监克劳斯·诺曼(Klaus Naumann)也不无感触地说:自黎塞留(Richelieu 1585 —1642法国政治家)时代已经300多年过去了,德国第一次不再成为来自东方或来自西方 的外部压力对象,“我们从而有可能在政治上行动而不是反应,在北约与欧盟既有联系 的坚实基础上参与塑造国际关系。德国的责任上升了(注:转引自Helmut Hubel/Bernha rd May,第5页。)。”
显然,1994年是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讨论的关键年头,各派意见纷争不断。总体 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两大阵营。保守派的代表之一、基民盟头面人物沃 尔夫冈·朔依普勒(Wolfgang Schaeuble)指出:“摆脱了冷战桎梏,实现了国家统一, 不再为寻求民族统一的特殊问题所困扰以后,德国现在是一个正常国家了(注:Helmut Hubel/Bernhard May,第130页。)。”德国慕尼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哥特弗里德—卡 尔·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定义是:“不 能让对12年纳粹专制的回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注:这是2001年夏天我在德国学术考察 访问他时,他对我发表的看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左派营垒包括左翼自由党人、“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以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士 。他们的看法是:即使德国统一也未改变德国应继续在国际上发挥“特殊作用”的事实 ,因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12年,要求德国必须在国际政治中从根本上保持克制态度 。学术界一些人士如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教授还提出:德国应在世界上发挥 “文明国家”(Zivilmacht)的独特作用;除了自卫目的以外,德国应原则上放弃使用武 装力量(注:参见Helmut Hubel/Bernhard May,第130页。)。
显然,“正常化”争论的焦点是德国要不要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要不要也可以使 用军事力量。这些问题在1994年时还不可能获得明确答案。然而,此后国际关系中的一 系列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促使德国对有关外交政策“正常化”实现的探讨逐步明朗化 。概括起来看,三个事件以及德国学术精英对它们的评论,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正常 化”问题的彻底解决。首先是国际政治学者施特凡·彼尔凌(Stephan Bierling)的评论 。他在一部有关德国外交政策教科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1997年2月5日是一个划时代日 子,它标志着二战以后德国外交政策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因为,自1945年5 月8日第三帝国投降以后,德国军人第一次完全参加了一场军事行动。两个日子的区别 是巨大的:前者是德国单独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后的失败投降日,后者是联邦国防军作为 多国维和部队一部分在波黑监督“代顿协定”实施行动的开始(注:Stephan Bierling,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Normen,Akteure,Entscheidung en,Muenchen 1999,S.1.)。
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再次引发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方 面,国际政治学教授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科索沃冲 突是向施罗德/菲舍尔联邦政府提出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挑战。且不谈德国参战的政 治、国际法或战略意义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联邦共和国也在军事力量使用方面恢 复了‘正常状态’,与联合国其它成员国不再具有区别。德国参加科索沃战争可以被视 为德国对国际体系新的框架条件适应阶段的结束(注:Michael Staack,第13—14页。) 。”
2001年突发的“9·11事件”震撼了全世界!它也使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实现时 间的划定又从1999年向后推迟了两年。2001年岁末,德国“时代”周刊总编和发行人特 奥·桑默(Theo Sommer)撰文论述“德国的新作用”,将德国1949年以后五十年走过的 外交政策历程比喻为一场“通往正常化的长征”;这场长征,从阿登纳政府开始,历经 勃兰特政府(1969年上台)、科尔政府(1982年开始执政)和施罗德政府(1998年入主联邦 总理府)持续不断,“直到世纪更迭以后,德国才完完全全实现了正常化。这个正常化 国家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但却已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注:Theo Sommer,第10 页。)。”
总之,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不是以1990年德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为标志, 也不是指1994年战胜国彻底撤军和德国获得完全主权,而是指德国要再次融入国际共同 体、拥有全部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拥有“一种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仰人鼻息的崛起民族的 自信心”(注:这是施罗德总理在1998年11月10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的话。引自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Hrsg.):“Die Regierungserklaerung vo 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oeder vom 10.11.1998”,Bonn 1998,S.34.)。鉴于194 9年以后德国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军事克制传统,所谓外交政策“正常化”,主要是指 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期”,逐步突破原来政策藩篱,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 与北约辖区以外世界范围维和军事行动视为禁区。那么,“正常化”的改变是否与“连 续性”的坚持背道而驰呢?
三 德国外交政策的平等目标
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问题与“连续性”问题不是相互矛盾和截然对立的。恰恰 相反,它们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
首先,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与“连续性”进程是同步发生的。如前所述,德国 外交政策“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一场“长征”,始于1949年。而在这一 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位,用一种伙伴关 系、和平合作和自我克制的新政策、新传统,取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军国主 义、扩张主义、统制和镇压的老政策、老传统。这是反思历史、吸取教训所必须,也是 战胜国和德国的其它欧洲邻国所要求的(注:参见莱蒙德·谢德曼(Reimund Seidelmann ):“德国和欧洲:完善民族国家,地区一体化和多边合作”,载于梁守德主编《中国 的发展与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2页。)。这 一新政策、新传统自5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度连续性。所以说,两个进程是同步发生的。 不过,两个进程可以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因为,到了20 01年,“正常化”问题已经盖棺论定矣,而“连续性”问题仍还叫人寝食不安!
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与“连续性”问题的根本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正常化”的 实质内容,即争取平等目标的实现上。在这方面,德国外交政策从未中断过它的追求, 1990年德国统一和1998年德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都未动摇这一外交政策目标。
德国外交政策的平等问题,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它与所谓“迟到的民族”(注:Helm uth Plessner,Die verspaetete Nation,Ueber die politische Verfuehrbarkeit bue rgerlichen Geistes(1935 bzw.1959),Frankfurt a.M.1974.)这一概念紧密相连。本来 ,“迟到的民族”是在论及精神、文化与宗教问题时使用的概念。后来,它被运用到国 际政治领域,以说明下述问题: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与其它世界大国比起来, 它在国家发展与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它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比别国晚,成为 大国、工业国、殖民帝国或世界大国以及成为共和国或代议制民主国家也都迟于其它国 家,因此,一种不再想“异”于他人的需求格外迫切与强烈(注:Gregor Schoellgen,D 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n den Anfaengen bis zur Ge genwart,Muenchen 1999,S.223—224.)。
这种需求表现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就是德国要在欧洲或世界上争取平等地位。在19 世纪上半期,争取平等的含义是要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以后 ,争取平等就意味着要向其它殖民主义大国抢占“阳光下的地盘”。1919年,“凡尔赛 和约”使德国的平等要求又转向摆脱遭人歧视的战败国地位上,这也是后来希特勒利用 的一个借口和掩护,以推行他的战争和种族灭绝政策;这时,平等地位已不是目的,纳 粹德国是要奴役欧洲乃至全世界!(注:Gregor Schoellgen,Die Aussenpolitik der Bu 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n den Anfaengen bis zur Gegenwart,Muenchen 1999,S 224页。对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疯狂,Schoellgen教授还指出:即使大多数过去德国的 受害者和反对者也都认为:它是普鲁士德国历史的断裂,而不是连续性的表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平等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具体外交政策目标 上:争取主权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因为,1949年“德国和德国人民”所处的状况,正 如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其第一个政府声明中所描述的, 是“还不自由,还未与其它国家人民处于平等地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还被分裂 成两个部分”(注:Ausgangslage der Bundesrepublik.Erste Regierungserklaerung des Bundeskanzlers Konrad Adenauer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vom 20.Septem ber 1949(Auszuege),in:Auswaertiges Amt(Hrsg.):“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 blik Deutschland.Vom Kalten Krieg zum Frieden in Europa.Dokumente von 1949-1 989”,Muenchen 1990,S.126.)。
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两个具体的平等目标,经过1955年5月5日(西德获得主权独立, 同时加入北约组织)、1975年9月18日(加入联合国)、1990年9月12日(“2 + 4条约”签 定)和1994年8月31日(俄国从德国彻底撤军)这些重要日子发生的重要事件,已经彻底实 现了。那么,为什么前面提到的以争取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进程 ,到世纪更迭以后的2001年才宣告结束呢?这与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目标实现的条 件具有直接关系。
众所周知,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两次战败的结果却根本不同:一战以后 德国军事上失败,但政治上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仍然存在;而二战以后德国是总体性 失败、无条件投降,连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国际法主体地位也丧失殆尽,必须完全听命于 战胜国的控制与安排。有鉴于此,不仅可以说:德国的分裂是国际关系“冷战”的产物 ,而且还应该加上一句:德国从分裂,经过维持现状,到最终实现统一,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国际关系演变的结果(注:结合中国的台湾问题,我曾于2000年和2001年多次为 北京大学和其它院校学生做过专题讲座“统一问题与德国模式”,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参见北大在线主编:《2001北大最佳讲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2页 。)。
前已有述,德国对分裂与统一问题曾有两个没想到:没有想到1949年以后德国分裂长 达40多载,也没有想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一年,德国统一就大功告成了。20 00年11月9日,在“柏林墙”倒塌11周年纪念日,我有幸在柏林听过一场由赛弗特(Seif fert)教授主讲的题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的一系 列观点我至今难忘:1989年时,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预料到德国会统一,更别说有所准 备了;德国统一是一个国际进程,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进程;统一的开端是在苏联 和东欧发生的变化,东德居民是用自己的双脚造成了国家的崩溃;还在“柏林墙”开放 以前,德国统一列车就已经启动了,科尔总理不过是及时跳上已经启动了的统一列车。
对德国统一没有充分准备导致了对国际环境的适应困难:统一德国将如何在国际关系 中自处和相处,如何设计和塑造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新地位和新角色。这些困难与问题 集中反映在对“克制文化”的反思上。换句话说:1990年德国统一仅仅意味着德国平等 目标在客观意义上的实现;在主观意义上,平等目标还远未实现。
四 德国外交政策的“克制文化”
(一)德国外交政策“克制文化”的涵义
历史地看,“克制文化”(Kultur der Zurueckhaltung)是1949年成立的西德外交政策 新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人所熟知的、邓小平1989年提出的“韬光养晦” 外交方针具有根本区别。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后受到列强欺凌、压迫,因此视国家独立 、民族尊严为外交政策最高准则,并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目标昭告世界;“韬光养晦”主要是在特定条件下,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时采取的一 种外交方略。德国国情则根本不同。作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必须进 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权力国家、实力政策、 德意志特殊道路等,都是具有负面意义或必须摒弃的东西,因为它们使人立即联想到威 廉二世的军国主义、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政策。有鉴于此, 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克制态度,特别是在高层政治的军事安全领域进行自我约束,如将联 邦国防军完全纳入北约一体化,不设立德国参谋部,自愿放弃制造、拥有和控制核武器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建立武装是为了不必使用武装等,就是西德外交政策所要遵循 的新的原则了。它给西德带来了国际信任与安全、内部繁荣与稳定。这一历时40多年的 正面经历,使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不愿意轻易放弃它、改变它。难怪有人形容德国这种军 事克制政策是从“权力狂暴”(Machtbesessenheit)到“权力忘却”(Machtvergessenhe it)!
(二)德国外交政策“克制文化”的国际认同
德国外交政策“克制文化”的国际认同十分重要。在历时几十年之久的“冷战”时期 ,德国的“克制文化”或曰“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是得到国际认可的,美国人 满意它,法国人欢喜它。然而,在“后冷战时期”,德国“克制文化”的国际认同出现 了问题。首先是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伊拉克、南斯拉夫、索马里、柬埔寨、科索沃、 阿富汗,这里只需列举一下这些国名或地名,就足以将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至20 01年进行的国际反恐战争这十年“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形势的急剧变化, 一一鲜活地拉回到人们的记忆中。
形势的变化要求国际体系的主体之一、西方联盟重要成员国的德国必须作出反应。显 然,在“海湾战争”时期,德国尽管已经统一,但“克制文化”仍占主导地位,德国还 没有做好参与战争的心理准备(注:2001年11月2日,德国“时代”周刊记者Jan Ross和 德国柏林广播电台记者Dieter Jepsen-Foege采访了德国前外长根舍,谈到德国在“海 湾战争”中的“特殊角色”,即所谓“支票外交”,光出钱不出人。对此,根舍进行了 反驳,指出:当时的情况与今天完全不同:首先,联邦国防军对出兵海湾地区在装备和 训练上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即使驻军盟国土耳其,也必须要从苏联租用运输机才行。 另外,1991年1月时,有关德国统一的“2 + 4条约”还没有完成批准手续,最高苏维埃 直到3月份才批准了条约。“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政府的政策无可辩驳, 我已屡次公开表示:政府在反恐斗争中的表现是正确的。”)。德国的态度在其西方盟 国中引来非议。譬如,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就曾激怒道:是不是德国的非军事化搞得太过 分了?!纽约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也愤然指责8千万德国人是:只谈 道德,不作军事贡献!(注:Sueddeutsche Zeitung,9.November 2001.)
又要回到德国要不要也在军事领域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对此,国际上不乏反对之 声,如“一个无聊的德国是对世界的祝福”;若德国象法国、英国一样发展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则显然是一个倒退(注:这是荷兰前驻德大使Jan van der Tas说过的话, 转引自Hubel/May,第7—14页。)。尤其是那些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德国侵略扩张和迫害 之苦的国家和人民,对德国仍怀有深深的疑虑与成见。以色列、美国和德国犹太人就明 确表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正常化不了,历史也不可能完结;1993年,美国犹太人 在华盛顿建立的大屠杀纪念馆开幕,再次强调历史的记忆不容抹杀(注:这是荷兰前驻 德大使Jan van der Tas说过的话,转引自Hubel/May,第131—132页。)。
应当指出:“正常化”的概念比较笼统,不可能涵盖统一德国国际作用的方方面面。 然而,针对德国几十年形成的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的“克制文化”,德国的主要盟 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政治精英是主张德国发挥正常作用的,包括德国参与北约和西欧联 盟军事行动。譬如,美国的德国问题专家菲利普·H·哥登(Philip H.Gorden)指出:“ 完全正常化”或许是不可能的……,但德国在四十五年当中在欧洲显示了负责态度,所 以德国现在值得信任(注:这是荷兰前驻德大使Jan van der Tas说过的话,转引自Hube l/May,第65页。)。另一位德国问题专家罗纳德·阿斯穆斯(Ronald Asmus)认为:统一 德国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承担起旨在维护国际秩序的“正常与适当的部分责 任”;只有当德国“正常化”以后,才能成为美国的“真正伙伴”(注:这是荷兰前驻 德大使Jan van der Tas说过的话,转引自Hubel/May,第64页。)。
1994年,曾为美国驻德大使、后在外交部欧洲司任司长的霍尔布鲁克(Holbrooke)担任 特别顾问的丹尼尔·S·汉密尔顿(Daniel S.Hamilton)出版了一部有关美德关系和统一 德国世界作用的书(注:Daniel S.Hamilton,Beyond Bonn.American and the Berlin R epubli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1994(Jense its von Bonn.Amerika und die“Berliner Republik”,Frankfurt a.M.1994).这本书 是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小组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克林顿政 府外交决策施加影响。),引起轰动。人们惊讶地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美国人这 么明确地呼吁德国人要在外交政策上转变思想,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与其增长了的地位相 适应的更大作用。该书的中心命题简言之就是“柏林不是魏玛,但也不是波恩了”;“ 柏林共和国”必须首先从外交政策上重新作出解释。1994年7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他 首次对德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发表讲话的基调,就是这本书中奠 定的。
克林顿在讲话中倡导美、德两国在稳定和引导中、东欧国家方面建立“真正独特”的 伙伴关系,号召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承担更大责任,认为德国在东欧国家一体化方面具有 举足轻重的领导作用(注:转引自Hubel/May,第66—67页。)。问题是,早在1989年5月 ,布什总统就已把德国称为“美国的领导伙伴”,然而,当时的德国对这种角色尚感到 手足无措;到了1994年,当克林顿以11年前肯尼迪总统在柏林演讲时的风格再次向柏林 人发表讲话,呼吁德国承担起新的世界领导责任时,德国的“克制文化”仍然占据主导 地位,德国对承担新的世界政治角色仍然还不成熟。
(三)德国外交政策“克制文化”的演变
是1998年上台执政的德国新一代政治精英施罗德总理和菲舍尔外长领导的红绿联合政 府,对德国“克制文化”的禁区作出了重大突破。
关于人事因素对政治的影响问题,德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阿登纳总理到科尔总理 ,历史情结和不要战争的强烈愿望左右着他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德国的欧洲政策(注 :譬如Habermas在他新近撰写的一篇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这一因素。 详见Juergen Habermas,“Warum braucht Europa eine Verfassung?”In:Deutschland ,Dezember 2001/Januar 2002,S.62.)。施罗德总理则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新 一代领导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其前任的出身和经历。因此,德国知名国际政治学者魏尔 纳·韦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指出:“1998年9月27日的大选结果,不仅意味着 一次人事更迭,它还昭示着德国历史上在连续性表象下面发生的一次尚不为人所注意的 深刻的划时代转折(注:详见“Werner Weidenfeld,Wende,Wechsel und Europa”,in:A lexander Siedschlag(Hrsg.):Realistische Perspektiven internationaler Politik ,Festschrift fuer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zum 75.Geburtstag,Opladen 2001,S .137。对人事因素影响外交政策的问题,德国外交部官员Eckhard Luebckmeier持有异 议。2001年9月4日我在柏林访问他时,他认为:形势比人强;从根本上来说,是形势的 变化、而不是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导致了德国外交政策风格的变化。)。”德国 慕尼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金德曼曾对笔者说过:“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恰恰是红 绿联合政府将德国引向了参与战争的方向(注:2001年7月,我在德国学术考察时访问了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教授。他的这番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已有述 ,施罗德对媒体赋予他的“战争总理”称谓曾直言不讳道:国家的正常化目标也包括军 事行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为了争取本党和执政联盟伙伴绿党的稳定多数支 持,施罗德总理创造性地运用了“基本法”规定的“信任投票”机制。本来,联邦总理 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案问题是为了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施罗德却将信任问题同他领导实 施的一个政府具体政策,即派德国联邦国防军参加阿富汗战争的问题联系了起来,这不 啻在向议会施加压力,真是前所未有!
五 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几点思考
总之,德国在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不仅在客观层面上,而且也在主观层面上实现了 外交政策“正常化”,以平等目标为实质内容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长征”遂告终 结,德国在“后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阶段也因之宣告结束。
“新德国问题”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课题,在21世纪需要继续进行探索。本文集中分 析了“后冷战时期”的“新德国问题”,认为:德国在国际组织授权下使用军事力量方 面改变原来基于特殊地位而形成的克制态度,决不意味着统一德国将重行军事大国实力 政策,而是适应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正常状态。这种变化是对本国外交政策 因国际局势演变而作出的调整,并未改变原有政策的性质、目标和根本的国际取向,因 而得到德国的西方主要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认同与支持。
将德国在“后冷战时期”一改过去近半个世纪非军事化外交政策的常规作法问题,纳 入德国外交政策实质目标即平等地位(“平等”这时与“正常化”同义!)的范畴去理解 ,是本文提出的主要论点。相信也希望它会引起争论!在21世纪世界历史新时期,特别 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国际局势新的发展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平等 地位的德国将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应是探索“新德国问题”另一篇论文分析和 解决的问题。尽管有画蛇添足之嫌,对此问题还想论说几句:
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继续同美国 实行旨在建构国际新秩序的紧密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继续深化和扩大欧洲一体化;致 力于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合作机制发展,使危机和冲突处理法制化、文明化;以信奉民 主和宽容、开放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回击原教旨 主义挑战。尽管还有国际、国内等诸方面困难与问题,如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洲一 体化的障碍、德国“内部统一”的压力和统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等,德国仍将是西方 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