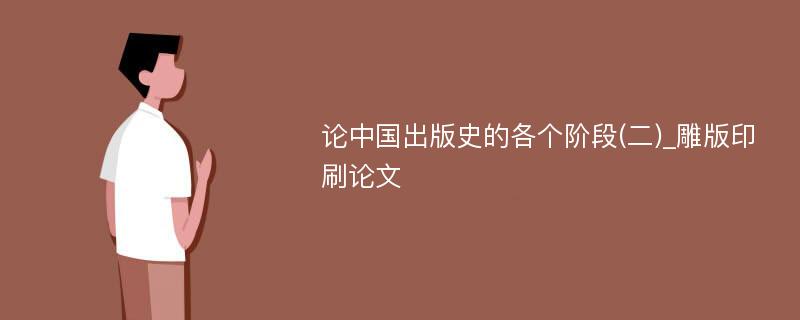
论中国出版史分期(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4-0047-07
在古代史上,唐宋两代是秦汉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大都肇始于隋唐,完善于两宋。从经济方面看,唐代经济空前繁荣,促使胡人大批到内地经商,其中有专营书画的胡商。内地人因为害怕“市籍”,不敢经商。到北宋,废除“市籍”,取消宵禁,开放市场。宋代市场比唐代繁荣得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唐以后,影响出版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二:其一,五代时将雕版印刷成功引入出版;其二,“市籍”废除之后士人开始下海经商,而宋代士人以做书商为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雕版出版取代抄本出版大踏步走上历史舞台。今天称之为雕版出版的原因是,复制方式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刷在出版中不居重要地位。
推广雕版印刷,以印刷取代手抄的结果,促使出版业内部随之发生一系列重要变革。印刷术大概发明于隋唐之际。纸张的发明是在汉官府主导下,最后完成于蔡伦领导的尚方令作坊,因此史籍记载明确。印刷是民间能工巧匠发明的;发明后长期不受主流文化与士大夫的重视,故而文献记载阙如。最早的印刷品旨在满足善男信女祈福消灾的需要,属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不为士人所重。刻印书籍以唐代书商为早。擅长经营旧书的书商,不谙书籍制作,不熟悉出版业务,靠书商无法将印刷引入出版而获社会认同。制作书籍与使用书籍的,一直是士大夫。唐代士大夫遵循传统,往往将自己所藏书卷,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士人心爱抄本卷轴,即使知道民间有印刷品,在尚未发现印刷复制的潜能与魅力之前,不会轻易利用印刷术。在出版活动中,士大夫是真正的主角,书商不过是配角。成也士人,不成也士人,这在古代出版史上是常见的现象。
到五代,以冯道(882-954)为首的一批学者,第一次将印刷用于《九经》出版而大获成功。唐代书商没有做到的事,他们终于做到了。原因主要是冯道等人刻印《九经》时,自觉继承抄本出版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印刷取代手抄后的诸多实际问题。首先,建立以国子祭酒田敏为首的校书队伍。选择公众认可的开成石经作为底本,又补上开成石经没有的注文。经注合一,加精心校雠,读者称善。其次,革新装帧,改卷轴为册页。以前抄本都是卷轴装。《九经》凡一百三十册,宋人所见为册页装。册页利于印刷与制作,又可降低成本,方便读者使用。以册页取代卷轴,这是书籍装帧史上一大进步。其三,版面设计美观大方。《九经》的书版文字由书家李鹗等人书写。南宋洪迈说:“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1](P233)王国维说:“其书每半页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与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1](P235)《九经》版式继承卷轴的行款,注重字体与书法,富有书卷美。其四,《九经》刊印后售卖,开我国官府“刻版印卖”之先河。以上四点说明,冯道等一批学者是在继承抄本出版的重校雠、重卷面版式、重装潢等传统的基础上,吸取书商经验,创造性地将印刷用于出版,因而获得成功。五代印行《九经》成为雕版出版已臻成熟的历史性标志。
印刷出版滥觞于隋唐之际,孕育于唐,成熟于五代,推广于两宋,鼎盛于明清,结束于清代末年的现代出版诞生之前。鉴于雕版出版成熟于五代,出版史分期应将五代下属于宋,不应上属于唐。雕版出版的基本过程是:先校书,次复制,后发行。从这一过程看,它比抄本出版更接近现代出版,然而与现代出版仍有区别。兹略述于下。
一、新古典书商崛起
北宋废除“市籍”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使宋代士人下海经商,改变了书商的知识结构与经营作风,进而成为产生新型书商的重要原因。与前代相比,宋代社会上轻商观念有所转变,士商对立有所缓解。在这样变革了的社会中,诞生了与汉唐书商不同的新型书商。
将宋代出现的新型书商,与宋以前的古典书商做比较,至少有两方面不同。首先,以前的古典书商是“入籍”的贱民,文化水平低;宋代出现的新型书商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化人。像杭州书商陈起,“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2](P14)。福建建阳书商余仁仲自称“国学进士”[2](P58)。像陈起、余仁仲这样有功名的士人做书商,宋以前是没有的。书商由“入籍”贱民变为中下层士人,对书商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明清书商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水平,比宋代又有提高。因此,宋以来的书商逐渐可能与作者、读者平等相处,进而可能在出版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中介作用。第二,以前古典书商的业务特征是经营旧书;宋代新型书商的业务特征是自刻自售。宋及宋以后的书商,依旧是经营旧书的能手。在经营旧书的同时,他们又在各地建立了书籍作坊,前店后坊,自刻自售。书商自营作坊,个别出现于晚唐,大批出现于宋代。从书籍牌记看,有实力的宋代书商刻书,多有校雠。像书商余仁仲刻印的“建阳余氏九经”,校雠颇佳,为宋版中精品。自宋至清的新型书商,纷纷建立起校书、印刷、发行三者合一的出版机构,充分显示新型书商与唐以前书商迥然不同的业务内容与经营作风。我们据此可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新型书商为新古典书商。
在出版活动中,新古典书商富有创造性与进取精神。他们的从业条件最差,发展速度却最快,迅速成为出版界一支生力军。书商为了避免在经典文献与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与士大夫争雄,于是独辟蹊径,进军士人轻视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结果,书商创造了异彩纷呈的大众文化出版物,在这个出版领域独领风骚数百年,为中国出版的发展进步,也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世界上,中国的市民阶层最早享有属于自己的多种多样出版物;坚持为市民阶层提供各种出版物的,就是中国书商。到明清,书商在全国出版业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可谓今非昔比。但是,一直到晚清以前,书商并没有成为全国出版业的领导者或主导力量。社会上轻商观念逐步有所减轻,却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新古典书商在出版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现代书商仍有不小区别。从历史上看,书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汉至唐的古典书商;自宋至清末的新古典书商;清末以后的现代书商。这样区分书商发展三个阶段,旨在便于区别性研究。
二、朝气蓬勃的多元化出版
自宋代开始出现的上千年多元化出版,在世界古代出版史上独树一帜。多元化,是相对于垄断一元化而说的。北宋官府曾试图禁止民间刻印书籍,这种禁令很快废止了。中国官府不想垄断出版,相反是敢于向民间开放,包括向书商开放,向不同宗教开放,在社会上形成了出版多元化。
在我国雕版出版时期,谁出资刻书,谁就是出版者;出版行为与出版过程,由出资刻书的出版者主持。官府与民间都可以出资刻书,因而都可以成为出版者。出资刻书的官府,包括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出资刻书的民间,包括不同的阶层、群体、宗教。叶德辉《书林清话》最早把古代刻书,区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我们从资金来源与出资目的做区分,大体也区分为官府出版、民间出版、书商出版三大类。书商也属民间,为何区分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需知轻商观念与士商对立这两大问题,宋以来与以前相比是大为缓解,并未完全消除。因为大为缓解,新古典书商才可能产生并发展;因为并未完全消除,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只能分道扬镳,不可能合而为一。将书商出版从民间出版中区别出来,有利于识别出版多元化。官府对出版的管制并非没有。禁书令宋代就有,大概元与清更多些。另外,刻书还有一些禁忌,像民间不准刊刻天文书,不准刊刻当代“实录”等。总的看,官府的管制较为宽松,不算严厉。与欧洲中世纪的少数僧侣垄断书籍上千年,不准民间染指相比较,中国古代刻书是自由的。刻书比较自由与出版多元化,两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两宋以来,尽管书商队伍迅速壮大,对出版影响最大的社会力量依然是士大夫。我国经历了先秦上千年的官方垄断文化以后,到汉代建立了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士人因酷爱自由而酷爱多元文化。社会上长期存在为士人酷爱的多元文化,是出版走向多元化的最重要因素。此外,出版多元化与士商矛盾也不无关系。民间出版不论集体出资或个人出资,大都靠士人兼做出版而发展起来。宋以来,一部分士人直接做了书商,多数士人轻商观念犹存,热心出版又不肯做书商,于是纷纷兼做出版。士人为何兼做出版?因为可以不做书商,保持士人身份不变。书商出版的优势是善于经营;士人出版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出版资源包括藏书、版本、新作、校雠、资金等,这些大都掌握在藏书家、学者、作家、士绅、官员这些士人手里。可是,多数士人仍旧视商人为低人一等,因此士人的出版资源与书商的善于经营,两者无法结合起来形成更大优势。只要轻商观念犹存,士人与书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或全面的合作,只能各走各的路。于是,不谙经营的士人利用自己的丰富资源从事出版活动,常常耗尽家财而不惜,不断做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业绩。书商为了避免与士人竞争,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宋以后大都选择出版畅销书。于是,书商的大众文化出版成为古代多层次出版的重要方面,而书商出版也成为我国多元化出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出版多元化,最能体现出版领域的禁区较少,自由度较高。自由度高,所以低级庸俗或陈腐的出版物,屡见不鲜。官府的禁书令常有,往往禁而不止。看上去乱糟糟,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实际是在碰撞与竞争中,不断走向有序,走向互补。官府出版以政治导向为重,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经、史为多,一般校勘精审,镌刻上乘,纸墨考究。官府利用自己资源刊刻大部头书籍如宋之《册府元龟》、清之《古今图书集成》等,最能体现官府出版的优势。民间出版多以文化与学术为重,不求牟利而崇尚后世扬名,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子、集为多。像寺院刊刻《大藏经》与明清刊刻“丛书”等,最能表现民间出版的巨大能量与高超水平。古代新作无不靠民间刊刻才得以问世;学术著作包括学术经典大都靠民间刊刻才得以传承至今。在明清两代出版物中,品种与数量以民间为最多,精品也以民间为最多。书商出版以赢利为尚,出版物涵盖四部而以大众文化或通俗文艺类读物为多,包括小说戏曲、歌谣唱词、科举应试、日用百科、版画年画等。宋以后大众文化长盛不衰,书商功不可没。我国的通俗文艺,原来多为口头艺术。书商将口头艺术变成印刷读物之后,才产生了可供阅读的小说、唱词、戏文等。像明清文人小说的兴起,就是直接受了书商刊行话本的影响。书商刊行的小说戏曲,数百年风靡全国,流布东亚各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出版引发的通俗文艺热。总之,出版多元化像是永不衰竭的发动机,它为出版繁荣不断提供动力。没有出版多元化,就不会有五代以后上千年出版的全面繁荣与持续繁荣。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出现合流之势。常熟士人毛晋的出版作风,亦儒亦商,颇具以经营为尚的书商特色;南京书商汪廷讷、胡正言,亦商亦儒,颇具以文化为尚的士人作风。这种现象,代表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不过从全局看,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仍旧保持不小的距离。只要将著名书商如容与堂、富春堂等的出版风格,与士人出版家如士礼居黄丕烈、知不足斋鲍廷博、文选楼阮元等的出版风格做比较,就知书商出版与民间出版的界限,仍旧判然有别。只要社会上士商对立没有完全消除,两者的界限就不能完全消除。晚清以降到1902年,具有进士、翰林身份的张元济毅然加入书商夏瑞芳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成为士人与书商全面合作的历史性标志。这样的合作,也是产生现代书商与现代出版的必要条件。
三、以出版者为中心,建立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
在抄本出版时期,虽有校雠,但多数读者在抄写前不做校雠工作。雕版印刷用于出版以后在出版业内部引发的重要变革之一,就是必须重视复制以前的校书,以校雠为主的编辑工作遂成为复制以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这里需说明,雕版出版的编辑工作为何以校雠为主?原因主要是,雕版出版时期的公私出版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刊行古籍与前代名著,不受理社会上作者的新作问世;新作问世,概由作者或其亲友出资刊刻。这也是雕版出版与现代出版的一个重要区别。
新作问世由作者或其亲友出资刊刻,它与抄本出版时新作由作者或其亲友定稿问世,前后一脉相承,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习尚。宋以来,作品由作者自己出资刊印,此为天经地义,从无疑异。像明代袁宏道(1568-1610)为刊印自己两个文集而筹措资金,差一点卖掉湖北公安县家中一处田产①。闻名全国的大作家袁宏道刊印作品也要自己出资,遑论他人?像南京芥子园书铺屡次刊行其主人李渔(1611-约1670)的作品,这与袁宏道自己出资的性质是一样的。有的官员往往利用公费刊刻作品。此外,更常见的是亲友资助刊刻。例如,李时珍(1518-1593)名著《本草纲目》完稿后,作者自己无力出资,书商拒绝刊刻,最后得到南京绅士胡承龙的资助,才得以刊刻问世。明清时常有坊间代人刻书之事,汲古阁也代人刻书。这种代刻,出资者仍是作者或其亲友。自宋至清,书商刊行社会作者的新作,如南宋陈起刊行《江湖集》,还有明代书商约请冯梦龙编辑并刊刻《三言》等,总的看这类事例很少,未成风气,不可视为常规。明清书商往往翻刻当代名著以牟利。像李渔的作品在自己出资刊行之后,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在李渔生前就被书商多次翻刻。这种翻刻,未经作者同意,现在看有盗版之嫌。今天不可将书商这类翻刻,与受理新作问世,视为等同。
从出版工作本身看,将手抄改为印刷之后,出版业加强编辑工作,是迟早必然要做的事。印刷与手抄的不同之处是,印刷为批量复制。因为是批量复制,所以印刷出现问题后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手抄大,不良后果比手抄严重。为防止印刷复制出现问题,办法主要是强化刻印之前的编辑工作。当时,谁出资刻书谁就是出版者。刻什么书由出版者自己决定。换言之,选题的决定权在出版者手里;官府刻书的选题决定权在主事的官员手里。因为选题的决定权在出版者手里,再加公私出版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刊行古籍与前代名著,在这种情况下,公私出版机构的编辑工作大致有三项:一,书籍校雠;二,书籍编撰;三,版式设计。其中编撰这一项,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出版机构才有,多数没有。这样,公私出版机构中的编辑工作必然以校雠为主,也就是以校书为主。对古籍出版来说,校雠是第一位的大事,古今皆如此。校雠,也称校勘,是古代“治书之学”的总称。如今有人把古代校雠,与今天校对视为一样,大谬不然。
随着雕版出版不断发展,印刷复制之前的校雠(校勘)这个环节,越来越受重视。出版者出资刻书时,除了可以自己校雠外,为了保证复制质量,往往延聘专家学者从事校书。在此同时,又雇佣刻工建立自己的书籍作坊。于是,以出资刻书的出版者为中心,使校书、印刷、销售三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官府出版是如此,民间出版与书商出版也是如此。这样三者合一的出版机构,在冯道以前尚未正式形成。冯道刊行《九经》第一次成功实现校书、印刷、销售三者合一,它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三者合一而言,印刷与发行将在下面介绍,这里仅说明以校雠为主的编辑工作。五代以后,官民出版机构为了加强编辑工作,纷纷设置校书部门,延聘校书人员。书商出版中的校雠并非完全没有,只是大多水平较低。一般说,士人比书商重视校雠。士人兼做出版时,或亲自校书,或聘请专家校书。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出版《九经》,校书者达“百余人”。明代毛晋汲古阁,曾谋划“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宋以来的书籍牌记与序跋,除记出资刻书者为谁,又记校书者为谁,这是业界对编辑工作重视的表现。印刷书籍的版式,宋代已经奠定良好基础。到明代,因为创造了版画、套印等新技术,书籍版式又取得宋以后的一次重大革新。
明清出版中的校书成就,总的看比宋代更大;而清代校书之风,比明代更盛。校雠是一种专门学问,称校雠学或校勘学,它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历史文化、版本知识等关系密切。出版业校书水平的提高,不仅要靠出版机构的重视,还须依赖校勘学本身的进步。清代得益于乾嘉之学,故而清代校勘学比前代进步最大。校勘学的进步,是清代校书比前代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清人做出版,最讲究精校精刻。精校,是加强编辑工作;精刻,是重视刻印复制,包括装帧。学者临时刻一部书,自己不校书而延聘专家校书,足以代表清人对校书的高度重视。例如,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聘张文虎校书;蒋凤藻刻《铁华馆丛书》,聘叶昌炽校书;黎庶昌刻《古逸丛书》,聘杨守敬校书。上面这些出资刻书的人都是学者,他们自己不校书而延聘校勘家校书,说明知识界认同出版中的校书是一种专门学问。同时,这也体现了出版者与编辑者的专业分工。出版者是出资者,他们决定刻什么书,另聘专家校书;一部书校完,出版者与编辑(校书者)之间的临时关系便结束了。
四、刻工作坊与刻工市场为多元化出版提供自由灵活的服务
从10世纪开始,中国跨入雕版出版的时代,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印刷出版强国。出版史关注的重点,并非印刷技术本身,而是印刷业如何成为出版业的组成部分。活字印刷在11世纪中叶发明后,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未能推广,我国出版业在20世纪以前,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雕版印刷是以刻工为主的手工印刷。刻工,既代表印刷技术,又是劳动力。所以,刻工及其劳动制度构成印刷业的基本内容。我国古代印刷业的巨大活力,主要源于自由而成熟的刻工制度。
五代以来,以刻工为主的手工作坊逐渐遍布全国各地,以小型作坊最多。印刷作坊的规模,一般以朝廷作坊最大。清代武英殿分为书作与刷印作两大部门,其中又有书写、镌刻、刷印、装订等分工。历代朝廷作坊,唯武英殿在雕版作坊外,另有活字作坊。武英殿是古代最大的印刷作坊。民间作坊之规模大小,视出版规模而定。汲古阁的出版规模很大,有人估计它的“印书作”员工可能有二百来人。[3](P130)明代吴兴闵氏、凌氏也设有印刷作坊,据说规模不小。不过,古代公私出版机构的规模,多数较小或很小。古人做出版,刻一部书板可以刷印数十年,或一二百年;书板有损坏,修补后仍可使用。从出版经济学看,一部书板可以长期使用,就是一次性投资完成后,可以在长时期内不断实现增值。换言之,刻一部书板作为投资,可以为子孙后代不断增值。这一点,也是建阳或南京的许多书铺可以传承一二百年的秘密所在。因为是刻工的手工作业,大型作坊在降低成本方面并不比小型作坊具有多少优势。书商为谋利,不必建立大型作坊,以扩大经营规模。书商牟利的关键是,刊刻长期畅销的作品,与雇请技艺高超的刻工。一次刻书不宜多,大都刻一部两部,尽快刻完,尽快赢利。这样,既可以利用现有资金迅速实现增值与不断增值,又可以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大,避免刊刻时间过长,占用资金过多。因此,书商云集的出版中心,必以小型作坊为多。至于官府出版或民间出版,多数是临时有书需刻,临时雇佣刻工,有常设机构者其实很少。所以自宋至清的雕版出版中,印刷作坊的规模多数不大,小而分散,有些作坊还是临时性的。
五代以来,谁出资刻书,谁就主宰出版过程,一般是如此。出版业的核心是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凡刻书要靠刻工。出版者通过市场,雇佣刻工为自己刻书。出版者与刻工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与以前抄本出版中的佣书,前后一脉相承。出版者的作坊有长年与临时之区别,刻工的受雇方式也有长年与临时之不同。社会上,不论有无刻书的堂号或铺号,都可以刻书。当有作品需要刊刻,一般不需官方审批(元代有些例外),只需备齐物料,雇佣刻工就行。与此相适应,社会上不能没有雇佣刻工的自由市场。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出版业最发达,刻工市场也最发达。农闲时,刻工往往自带工具,走门串户,自由招揽活计。从出版业内部关系看,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居于核心地位,刻工与作坊隶属于出版者,校书者也隶属于出版者。
刻工制度,简单说是自由雇佣制度。刻工是手工业工人。先秦的手工业者多是官府或贵族的工奴。出版业的刻工不是工奴,不存在奴婢与主人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刻工的社会地位较低,然而都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己选择雇主。而刻工市场是一种自由市场。出版者通过市场选择刻工,刻工也通过市场选择出版者。刻工到出版者的作坊工作,并非服劳役,是为自己谋生,所以积极性较高。明代山西五台山刊印《方册藏》时,数百刻工从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等地受雇来到五台山。[4]可见,刻工通过雇佣市场在全国流动,不受地域限制,相当自由。中国自唐代开始逐步解放奴婢,因此身怀技艺的工奴与演唱艺人(唐代称音声人)逐渐从奴婢转变为自由人。中国的刻工自由市场,是唐以来社会改革的成果。宋元以后,安徽籍刻工最早掌握套色与版画等新技术,印刷技艺在全国遥遥领先。因此,南京、苏州、杭州、湖州等出版重镇纷纷雇请徽籍刻工;后来,北方地区也雇请徽籍刻工。从出版学看,刻工自由流动,就是印刷技术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相当于印刷厂的自由流动。再进一步看,自由流动的印刷技术与劳动力,与当地出版者的刻书任务、资金、物料等结合,就在当地形成了出版业。这也是各地出版中心得以迅速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原因。刻工自由流动必然加剧市场竞争,进而促使出版技术不断进步。明代的刻书价格比宋代便宜,[5](P154)也是刻工市场竞争的结果之一。刻工的自由雇佣制度是雕版出版得以不断发展,多元化出版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保证。
五、书籍发行业迅速发展,然而发行始终是古代出版业中最薄弱的环节
书籍发行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印刷引入出版以后,在出版业内部引发的另一重要变革。印刷复制所需一次性投入资金的数量,远比手抄要多;而印刷复制的单位成本,又与印制书籍的数量成反比例。印制数量越多,单位成本越低;印制数量越少,单位成本越高。因此从经济利益考虑,印刷复制不能不追求印制书籍的数量,进而迫使书籍生产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目的,不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利用手抄复制的书籍生产者,不妨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利用印刷复制的书籍生产者,再继续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就变得很困难了。所以推广印刷复制的结果,必然促进书籍生产走向市场,促使书籍成为商品。书籍发行随之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五代宋以来,决非仅仅是书商刻书以后售书。官府或士人所刻之书,品种、数量都比书商多。他们手中这么多书,无法都留下自己使用,不能不拿到社会上去交换;而交换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市场的商品交换。五代时,冯道刻《九经》就向公众出售,这是中国朝廷第一次向公众售书。到宋代,国子监的书库官是中国最早的售书官员。士人售书留下的资料很少,原因是士人售书而又讳言售书。社会上的轻商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与轻商贱商、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始终是束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也是束缚书籍发行的枷锁。
官府刻了书,除了赠送,多数要向公众出售。鉴于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官府借刻书赚钱,所以一般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宋代国子监的刊本,常用代客刷印的方式,只收成本费。官府出版的有些书籍,只求保本微利,再加出版条件优越,因而质量高而价格低,性价之比最优。宋代官府刻书尤其舍得花钱,镌版精良,版式美观,纸墨考究。后来,宋官刻成为藏书家与版本家之最爱。官刻有时价廉,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而甘愿赔钱,不属于市场行为。有些官府出版物,靠“颁行”而销量很大。“颁行”,是利用行政权力发行书籍,与商业发行有区别。坊间书商不具备官府刻书那些特殊有利条件,将官府出版与书商出版做简单类比,评论高下,未必公允。一般说,书商最善销售,最重发行。为了扩大销售,书商常常采取的方法有:降低原材料成本,力求书价低廉;通过上门推销等灵活方式扩大销售;利用牌记等加强书籍宣传;靠诚信建设百年书铺等。明代有福建建阳书商在南京设立代理机构,清代有江苏苏州书商在北京设立代理机构。书商在外地设立代理机构,扩大销售业务,虽属个别现象,然而最能代表书商开拓市场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士人出版所不及。
民间士人刻印自己文集,赠而不售是常有的事。赠书,本是古人交往的方式,也是书籍流通的方式之一。但是,书籍流通的最佳方式,是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让读者到市场去自由选择。不断刻书的士人,如果都是赠而不售,实际上行不通。都赠而不售,从经济学看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种情况除非有资金不断注入,否则谁也无法继续刻书。为实现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刻书以后的售书是必要的。因此,士人做出版迟早也要售书,只是士人讳言售书,所以很少留下售书的文字记录。清代版本学家黄丕烈(1763-1825),江苏吴县人,珍藏宋本百余种,一生刊行《士礼居丛书》19种,另附4种,多为罕见珍本。如今,见有一份清代苏州“滂喜斋书籍铺”印的《士礼居刊行书目》,上面记载19种书的书名、册数、定价与刻印年份。例如:“《国语》,五册,一两二钱,庚申。”在黄丕烈“书目题跋”或他的其它著作中,找不到他售书的记载,可是这份《书目》表明,黄丕烈所刻书当时在苏州书铺标价出售。士人售书,可能委托销售与直接销售都有,具体不易弄清。士人售书做得好的,首推秀才出身的毛晋(1599-1659)。毛晋因科举不第而经营出版。他以汲古阁名义刊书并售书,据说云南人不远万里到江苏常熟汲古阁购书,“毛氏之书走天下”[6],汲古阁成为名噪全国的书业品牌。毛晋刻书数十年,镌书板十万多块,刊书六百多种,事业做得这样大,销售做得好是重要原因。
雕版出版时期,新书发行的基本方式是自产自销。善于经营的书商,大都是前店后坊,自刻自售,并没有完全脱离自产自销这个模式。官府或士人做出版,更不能完全脱离自产自销的模式。在书籍销售方面,官府与士人总是远远落在书商的后面。不过,书商始终没有能建立完善的新书发行制度。福建等地个别书商在外地设立代理机构,或许是建立发行制度的一种可贵尝试。在儒学主导的古代社会上,书商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完善的新书发行制度,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士人做出版所拥有的出版资源最丰富,出版物不仅品种多,数量多,传世的精品也多。士人为出版而无私奉献,可是,士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乏商业进取精神。士人出版家中,像毛晋那样重视销售的人,少之又少。在观念上,士人多视售书为重利轻义,又视利润最大化为不道德。因此士人刻书之后,一方面是不得不售书,另一方面又因轻商而羞于售书,束手束脚,顾虑重重。这样的矛盾心态等于是自己套上了精神枷锁,根本无法做好售书,更不能建立新书发行制度。总的看,官府出版与民间出版在观念上都是重刻而轻售。重刻,是重视编辑(校书),重视复制(印刷);轻售,是轻视销售发行。书商重发行的作风,可以影响但不能完全改变士人与官府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作风。一直到晚清以前,我国在书籍销售方面,迟迟未能建立批发零售、代销经销、连锁经营,广告宣传以及读者服务、售后服务等的书籍发行制度。
受自产自销这种发行模式的限制,新书的流通主要限于某个地区的范围。自宋以来,全国各地的出版中心与次出版中心,虽有兴衰更替,总的趋势是数量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全国书籍市场以东南地区最发达,但各省都有分布,几乎应有尽有。再从另一面看,宋以来迅速繁荣的书籍市场,主要是围绕出版中心出现的区域性市场,或以区域为主的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书籍市场,实际上非常困难。这方面的政治障碍并非一点没有,但主要是缺乏现代发行制度。历代监本能流通全国,官府“颁行”起了很大作用。宋元期间,建阳的闽籍书商将自己出版物,大量销售到文化发达的江浙皖地区。明清两代,江浙书商刊行的小说、戏曲等风靡全国,占领市场数百年。在书商努力奋斗下,部分地建立了全国性书籍市场。但是,靠长途贩运或靠官府“颁行”,没有完善的发行制度,很难建立健全的全国统一市场。考察宋以来目录学著作可以发现,同一种书在全国各地被不同出版者同时刊行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重复出版现象无处不在,主要是因为区域性市场发达,全国统一市场薄弱的缘故。
从流通对出版的影响看。首先,出版的自身价值必须通过流通,进而通过读者的接受才能实现。流通不畅,直接妨碍读者对出版物的选择与接受,进而妨碍出版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流通不畅必然影响书籍生产的发展。区域性市场不能不限制书籍生产的规模,束缚出版者的手脚。为与区域性市场相适应,出版者适宜搞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各地的旧书买卖,总是比新书销售更兴旺。自产自销的新书,或赠而不售的新书,不管出版者为谁,迟早可能流入旧书店。旧书店林立,旧书交易繁荣,是古代书籍流通一大特点,所以旧书业很值得研究。但是,旧书业再兴旺,直接的受益者是经销商,不是出资刻书的出版者,因此对出版者扩大生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并不大。总之,由于全国统一市场薄弱,出版者不能从全国性大市场中汲取力量,谁也没有办法把出版做大做强,暂时做大了也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结果是,出现大市场、小生产的局面。说是大市场,是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教育发达,书籍市场非常大。说是小生产,是从具体的出版者看,书籍生产大都维持小规模,而且很分散。晚清以前,我国出版业没有走上产业化的道路,落后的书籍发行是一大原因。建立现代发行体制,以及引进西方先进机械等,成为建立现代出版业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2008-04-22
注释:
①袁宏道《与苏潜夫书》:“近日刻《瓶花》《潇碧》二集,几卖却柳湖庄。计月内可成帙,然不能寄远,以大费楮墨也。”见《袁中郎随笔》,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