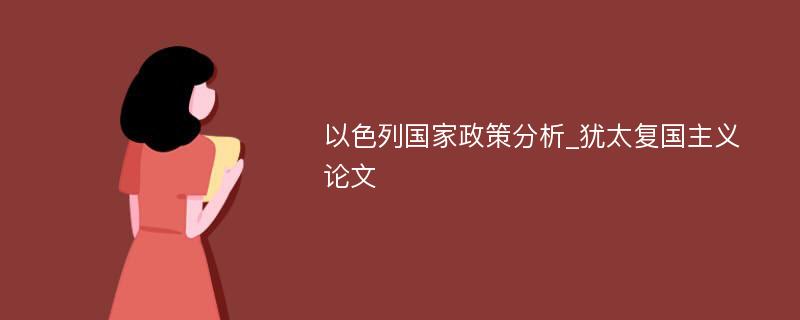
以色列民族政策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民族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阿拉伯两大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截至2003年底,以色列总人口为674.84万人,其中,犹太人口为516.54万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76.54%,与1949年相比净增长415.15万人;阿拉伯人口为158.3万人(不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占以总人口的23.46%,与1949年相比净增长142.39万人。① 由于阿拉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犹太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甚多,且从海外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口总体上日益减少,因此预计未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的数目和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15年阿拉伯人口将达到181.4万人,到2025年将达到232万人”。② 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而言,在犹太人的数量及其在以色列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③ 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宗教、语言来说,无疑是少数民族,并在国家权力、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劣势地位。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独立宣言》中声称:“以色列国……将尽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于所有的居民;将以以色列先知所梦想的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充分享受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④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色列政府是否实践了它在《独立宣言》中的庄严承诺呢?是否执行了平等的民族政策呢?以下将通过对以色列民族政策的由来、基本特点及后果和影响的分析来加以阐述。
一、以色列民族政策的由来和实质
以色列是由犹太人、阿拉伯人及少量的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政府从未制订过任何明确的民族政策。本文所说的“民族政策”是指以色列政府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的原则性、指导性措施,即主要指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政策以及处理犹、阿两族关系的政策。这些措施主要来源于以色列的法律、法令和相关政策,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1950年的《回归法》、1952年的《国籍法》、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1984年的《基本法·议会》修正案等。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以色列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一种民族解放运动和意识形态,⑤ 正如1968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27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所声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包括:“犹太民族团聚并以以色列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犹太人从世界各国返回其历史家园;通过犹太和希伯来教育以及犹太精神和价值观念保持犹太认同。”⑥ 可以说,以色列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法律、文化和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⑦
由于以色列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实施其民族政策的,因此,其民族政策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早在1931年,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就在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声称:“我们发誓,我们永远不会赞同巴勒斯坦的一个民族集团统治另一个民族集团。”⑧ 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建国时,本—古里安又在《独立宣言》中声称以色列将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平等对待其所有居民。“将阿拉伯人整合(integration)到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以色列)政府所宣称和实践的政策。”⑨ 确实,从表面上看,以色列阿拉伯人有着与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地位。例如:阿拉伯语被定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阿拉伯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阿拉伯儿童享受与犹太儿童同等的义务教育权利;阿拉伯人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甚至在以色列政府中还专门设立了阿拉伯人事务司,并且其各级职位也主要由阿拉伯人担任,例如,在拉宾政府(1992—1995年)中就有阿拉伯人担任副部长和驻芬兰大使。
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的建国、存在和崛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194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为2亿美元,到1998年已经增长到900亿美元,⑩ 半个世纪里翻了450倍!到2000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8万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1) 与此同时,其教育、科技、文化也步入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列。因此,以色列官方公开宣称,其境内的阿拉伯人是中东地区最为富裕、享受最多民主权利的阿拉伯人。有阿拉伯学者甚至写道:“与中东地区的大部分阿拉伯人相比,以色列阿拉伯人有着相当高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准……阿拉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社会和文化活动自由,大大超过中东地区其他群体所享受的自由。”(12) 这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人均寿命上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以其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为例,1999年至2000年,以色列阿拉伯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4.6岁,超过黎巴嫩(71.3岁)、沙特阿拉伯(70.3岁)、叙利亚(69.8岁)、约旦(68.9岁)、利比亚(68.6岁)和埃及(65.3岁)等阿拉伯国家的人均寿命。(13) 无疑,身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尽管无法与以色列犹太人比肩,甚至在近20年中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但在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们并未与以色列政府处于直接对立之中,流血冲突更是很少发生的事情。
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了提升,并不等于以色列执行了平等的民族政策。“以色列当局所追求的整合(integration)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控制手段,用以防止阿拉伯人将制度上的分离(institutional separation)作为提升民族自治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坚固堡垒。”(14) 为了确保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性和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权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色列政府自始至终奉行犹太大民族主义政策。早在110年前,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兹尔就在他的《犹太国》中明确指出:多数党(the majority)将决定谁是“异己的”(the alien);在民族关系中,这一问题与其他所有问题都是权力问题(a matter of power)。(15) 他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以色列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平等口号下的不平等”,即在犹太国家以色列,犹太民族是多数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阿拉伯人是“异己的”,处于“二等公民”地位。
二、以色列民族政策的特征:剥夺与压迫、歧视、隔离与分化
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宣布:“……根据我们天然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宣布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16) 尽管以色列宣称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犹太教和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纳达夫·萨弗兰在《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的开篇写道:“以色列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物。”(17)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时至今日,以色列仍然没有一部宪法。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更主要的是一份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宣言,而不是一部法律,它不具备法律所特有的约束力。而“以色列《独立宣言》所体现的宗教、民族色彩,对阿拉伯人来说意味着排斥和歧视”。(18) 宪法的缺乏,使得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种族平等地对待和保证全体公民的权利缺乏法律上的最终保障。“对阿拉伯人来说,法律平等的缺失和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根本特性诱发了对阿拉伯人的结构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19) 因此,以色列具有双重国格:犹太国家(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一特性决定了以色列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即表面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剥夺与压迫、歧视、隔离与分化。
1.剥夺与压迫。建国以后,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在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全部120名议员中仅有3名是阿拉伯人,占议会总人数的2.5%。这与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人口中所占比例是不相称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色列国家涉及到阿拉伯人权利的政策、法律和法令的一个重要特征——剥夺与压迫。以色列“建国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滞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约有15万人,其中约1/4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成为以色列的国内难民。(20) 而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夺取了大片巴勒斯坦领土。这些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大多数沦为国际难民,其总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房屋、土地、家具、家畜等财产绝大部分落入犹太人手中。“如果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不能返回家园,仅财产损失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根据现行的标准计算,按照当年的价格折算……金额约为920亿至1470亿美元。”(21) 此后,以色列政府又先后通过一系列法令,如1948年的《开发闲置土地条例》、1949年的《紧急土地获取法》、1950年的《不在者地产法》和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夺取了原来属于阿拉伯人的大量土地。以色列政府的第十五届议会一致通过《公共土地法:侵入者的迁移》(The Public Land Law:Removal of Intruders),以色列“政府的目的是把传统上游牧的贝都因人集中在内格夫沙漠固定的定居点中,为新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来”。(22) 除了通过法令强行剥夺阿拉伯人的土地之外,为了兴建新的犹太移民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使尽各种手段,例如没收阿拉伯人的居住证、强征土地等,夺取了阿拉伯人的大量耕地和牧场。“1947年,犹太人只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不到7%,而到1993年,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拥有量已经下降到4.5%。”(23)
如前文所述,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以色列民族政策的重要来源,一些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甚至直接对以色列的民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不久,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办事处,(24) 在以色列政府内被赋予特殊地位,(它们)分派其代表到政府的许多部门,尤其是农业和土地部门……这些组织在农业和土地政策的形成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阿拉伯人再也无法建立新的村庄或农业定居点。”(25) 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本质特性带来的后果是很清楚的:犹太人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占有绝对优势;而阿拉伯人则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被犹太人掌控的历届以色列政府边缘化。2001年,“阿拉伯人口占总人口的将近19%,而以色列政府各个部门一般只把不到7%的预算拨付给阿拉伯人。福利部拨付给阿拉伯人的预算为9.8%,教育部拨付的预算为3.1%。”(26)
以色列是一个“举国皆兵”的国家,目前主要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根据该国1959年颁布实行的《兵役法》,服义务兵役仅限于犹太人和德鲁兹人,但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可志愿服役。也就是说,实际上该国境内的大多数阿拉伯人不能参军。问题是,在以色列,许多社会福利是与兵役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就业、居住地点的选择、医疗保险、减免学费、住房贷款等,都与兵役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以色列境内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就无法享受许多社会福利,造成了阿拉伯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无疑,这是对以色列国内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正当权益的剥夺。
以色列国家犹太本质的排斥性也反映在1984年通过的《基本法·议会》修正案中。该基本法规定:若某政党否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则该政党无权参加议会选举。该基本法再一次突出了以色列国的犹太本质特性。(27) 问题的关键便在这里:若有政党试图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与以色列犹太人同等的权利,则该政党就是否认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本质特性——犹太国家,那么该政党就丧失了参加议会选举的权力。也就是说,阿拉伯人政党永远无法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争取同等权利,阿拉伯人永远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2.歧视。尽管以色列宣称其境内的阿拉伯公民享有完全的、平等的权利——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拥有投票权,事实上,许多法律和政策将阿拉伯人降为二等公民。(28) “作为以色列公民,阿拉伯人并未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歧视。”(29)
以色列建国后,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英国政府于1939年5月发布的《麦克唐纳白皮书》,该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是控制犹太移民活动,并严格限制土地的转让。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以色列是所有流散犹太人的“祖国”,所有犹太人都有权到以色列定居。由此,新生的以色列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移民潮,“这次移民潮从1948年5月持续到1951年底,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以色列共接受了大约68万新移民,这一数字超过了建国时以色列本国的人口,使以色列总人口达到了130万”。(30) 1952年4月1日,以色列第二届议会通过了《国籍法》。这部法律规定,每一个回归以色列的犹太移民都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除非他(她)声明不愿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但是,放弃以色列公民身份并不影响他们移居以色列的权利。与此同时,该《国籍法》对非犹太人(主要针对阿拉伯人)获得公民权却采取了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阿拉伯人要想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她)是在以色列出生的,否则他们既不能回归自己原来的居住地,也无法获得以色列国籍。而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大约有65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以色列实际占领区(包括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以色列的地区和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其他地区)。这些人无权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和故园,更不可能获得以色列国籍和公民身份。因此,1952年《国籍法》“不但扩大了《回归法》的影响,也使其实施更为方便”。(31)
以色列建国初期颁布和实施的1950年《回归法》和1952年《国籍法》为歧视阿拉伯少数民族奠定了法律基础。通过这两部法律的实施,以色列得以严格控制阿拉伯人移居以色列和杜绝阿拉伯人难民回流,从根本上保证了以色列的犹太特性。以色列高等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公然写道:“作为犹太人,作为犹太国家的本质,就是要赋予犹太人优先权。任何人若以民主的名义要求赋予以色列全体公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的权利,必将被拒。因为他(她)否定了以色列国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32)
3.隔离与分化。除了压迫和歧视之外,以色列民族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隔离与分化。自从建国以来,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其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问题。正如纳达夫·萨弗兰所指出的:“在以往十三年期间(指从以色列建国到1961年——引者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分布,这是政府作了周密的、花费了很大的努力的结果。”(33) 以色列建国后,立即通过《紧急状态条例》将阿拉伯人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直到1966年才解除。在将近20年的军事管制期间,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拥有权和政治权利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34) 例如,阿拉伯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各个村庄或部族、部落之间彼此隔绝,甚至连到相邻的村庄也要事先获得管制当局的许可。1956年,以色列边境警察以违反宵禁为由,枪杀了49名阿拉伯居民,而这些居民只是在天黑以后才从自己的耕地上返回村庄,事先没有获得军事管制当局的许可。这样,阿拉伯人被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如“大三角”地区(加利利西部和中部地区)、内格夫沙漠北部、“小三角”地区(约旦河西岸一狭长地带)等,与犹太人的居住地隔离开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阿拉伯公民参与以色列有限资源的分配,便利了对阿拉伯人资源的利用,同时限制了流动及社会政治活动,从而巩固了犹太人的统治地位。”(35)
除了在居住地域上对阿拉伯人实行隔离与分化之外,以色列历届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从两个层面上隔离、分化阿拉伯民族。第一个层面是将犹、阿两大民族隔离开来。无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族际联系上,以色列政府都设置各种障碍,千方百计地分化两大民族。以族际通婚为例,“尽管不算非法,族际通婚在以色列非常罕见并且几乎无法维持。族际通婚的稀罕,表明阿、犹两族就主体而言是非同化(non-assimilating)的”。(36) 2002年,由海法大学巴蒂·胡赛斯(Badi Husseisi)和阿米·帕多泽(Ami Podhozer)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多达90%的犹太人不愿自己的子女与阿拉伯人发生恋爱关系。(37) 因此,社会与文化多元化在以色列是一种稀罕的自发现象,欠缺相应的引导与鼓励机制。另一个层面的分化就是不遗余力地离间阿拉伯族群内部的关系。首先,以色列政府否认阿拉伯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将其国内的阿拉伯人称为“少数民族”、“非犹太人”,割裂他们与其他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并为“离间”其内部不同族群奠定基础。其次,鼓励阿拉伯人在宗教、教派等方面的分化。例如,以色列政府1956年即允许德鲁兹人参军,后来又于1962年首先解除了对德鲁兹人的军事管制。这些举措更进一步突出了德鲁兹人这一族群与阿拉伯人族群之间的差异。以色列政府还刻意将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德鲁兹人、贝都因人与其他阿拉伯人的穆斯林主体区分开来。例如,德鲁兹人、贝都因人先后被允许参军,而大多数阿拉伯人却不能参军。又如,德鲁兹人获得了相对更多的政府经济援助。再次,拉拢和收买阿拉伯知识分子。例如,通过在大学设立奖学金、组织学生会等社团,将阿拉伯裔学生中的佼佼者吸收到学生会中担任职务,毕业后再吸收他们进入政府机构,让他们负责阿拉伯人事务的处理。
“政府可以——在过去确实是这样做的——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族际间的敌对情绪。它可以利用某种手段,影响、加剧或消弭族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38) 以色列政府的目的有二:一是便于当局管理和镇压阿拉伯人可能的反抗,保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二是切断犹、阿两族间的联系,故意制造和加强他们之间的隔阂和敌意,阻碍族际交流和取得理解,从根本上杜绝阿拉伯人地位被提升的可能性。“犹太人反对阿拉伯人迁入上拿撒勒(Upper Nazareth),以保持这一地区的犹太特性。”(39) 以色列政府长期以来的隔离、分化政策,造成了犹、阿两族间深刻的隔膜、怀疑,甚至敌对。2003年,在军事管制被解除之后将近40年的时候,一项以以色列犹太人为询问对象的调查表明,仍然有53%的以色列犹太人坚持认为不应该赋予以色列阿拉伯人完全公民权,有77%的人认为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应该由犹太人作主,只有不到31%的人支持阿拉伯政党进入政府,有57%的人认为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移出以色列。(40)
三、以色列民族政策的后果及影响
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民族政策,造成了以色列犹、阿两族在人口分布上的严重失衡和社会分层上的巨大差异。2001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在综合分析人口分布、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政府资助获得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前提下,将整个以色列的212个居民点划分为10个层次,其中“1”代表最低层,“10”代表最高层,数字越大,层次越高。在1—4层的108个居民点中,只有32个是犹太人居民点,所占比例仅为29.63%;而在5—7层中,犹太人居民点有63个,占67个该类居民点的94.03%,至于最高的三个层次即8—10层共37个居民点,犹太人“一家独揽”!(41) 这就是说,在以色列,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要远远优于阿拉伯人。犹、阿两族间的巨大差异,给以色列带来了重大影响。
首先,以色列犹、阿两族人口地理分布上高度“隔离”的情况不容乐观。周星先生在《民族政治学》中指出:“几乎在一切情形下,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都可能成为民族问题的潜在影响因素乃至显在的表现形式。”(42) 以色列犹、阿两族人口在地理分布上的“隔离”,在未来可能成为其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潜在诱因。事实上,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人一直在为其平等地位而抗争,只是他们采取的基本上是集会、游行抗议等合法而且温和的斗争形式。
其次,以色列国家构建中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的错位或严重不同步。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这两个原则的本质区别对于理解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是至关重要的。”(43) 就以色列而言,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的矛盾。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国家统辖之下的地域基础上的语言、宗教、文化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是尚未完全消除的“历史”遗存。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政治整合,要求由已经统一的国家政权来推动文化整合进程,确保这些“历史”遗存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奇格蒙特·鲍曼指出:“在国家的政治统一中,共同的民族性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作用。”(44) 这样,现代多民族国家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政治整合通常要求其每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共同体和民族特性,推动民族宗教个人化,逐步使少数族民族文化和传统边缘化。这就为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产生制造了很好的理由。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一般可以概括为对本民族存在的宪法承认、语言平等、民族文化保护和政治权力的分享等几个方面,其核心要求是多民族国家政权对本民族在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倾斜,并据此要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由于民族利益所指向的多是那些具有“拥挤性”或“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族际纷争。一旦这种族际纷争失去“动态均衡”,“受害”民族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和屈辱感;由于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因而那些“受害”民族理所当然地会对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在民族精英系统化说教的引导下往往会得到加强。(45) 民族矛盾的出现既导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族群认同的强化,同时也使得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陷入危机。由此,以色列犹、阿两族“文化”上巨大的天然差别,导致了以色列政治(国家或政权)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分裂。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种族和宗教集团……许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裂运动。”(46) 显然,以色列的民族、文化状况恰恰符合塞缪尔·亨廷顿描述的这种情形。
再次,犹、阿两族间总体上的互不信任、怀疑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敌视,对以色列的民主政治构成了潜在威胁。这种威胁是由民族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造成的。民族是特定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有相异甚至大相径庭的文化认同(犹、阿两族的文化认同即是如此)。就民族与民主的关系而言,任何国家政权的存在,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继而上升到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民主政治的大众参与、公开选举、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都极大地提高了它对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的要求。因此,民族与民主的冲突在于多民族社会的文化异质性与民主社会所要求的较高文化认同程度之间的矛盾。宁骚教授指出:“民族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既表现在理念的层面,又表现在制度的层面,既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内部,又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层面之间。诸如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与各民族的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等等。”(47) 以色列的阿拉伯亚文化随其人口的快速增长而日益崛起,从而对以犹太主流文化为支柱的以色列民主政治构成了潜在的冲击和威胁。
最后,以剥夺与压迫、歧视、隔离与分化为特征的以色列民族政策,造成以色列犹、阿两族长期相互怀疑和敌视,削弱了以色列的国家凝聚力,降低了其民族士气,从而损害了以色列的国家权力。社会心理学认为,一个社会群体(例如部落、族群、民族等)对于另一个社会群体越陌生,两个群体间的不信任和怀疑程度越高。相反,两个社会群体间的相互联系越密切,它们越能够相互适应和理解。以色列的民族情况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是否允许阿拉伯人参军这一问题上,61.5%的犹太人持反对态度,而持反对态度的阿拉伯人更是高达到80.7%。(48) 原因很简单:在犹太国家以色列,“犹太人将阿拉伯人视为以色列潜在的安全威胁,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人的专有家园”。(49) 犹、阿两族间的怀疑和敌视,影响了以色列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士气,而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士气都是构成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犹太民族的杰出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谈到国家权力的构成时指出:“就其对国家权利的关系而言,所谓民族士气则比其它一切因素都更难捉摸、更不稳定,但却同样重要。民族士气是指一国民众不论在平时或战时,支持本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决心所达到的程度。它渗透在一个民族的各种活动之中,如渗透在其工农业生产、军事机构和外交工作之中。表现在公众舆论方面,它虽然是一个无形因素,但是没有它的支持,任何政府,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执行其政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效果。”(50)
注释:
① 参见“Israeli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n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No.55,2004。此人口数目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人口以及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口。
② “Israeli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n The Arab Population of Israel 2003,2004.
③ 本文中的“阿拉伯人”指的是具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不包括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属于无国籍人口),但包括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阿拉伯人。以色列通过1967年的“六五战争”夺取了耶路撒冷旧城并于1980年通过一项基本法,将该城(包括东、西耶路撒冷)确定为其永久首都。截至2000年,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已经从1967年的7.1万人(其中穆斯林5.81万人,基督徒1.29万人)增长到21.11万人(其中穆斯林19.69万人,基督徒1.42万人),占该城总人口的33.141%。在“六五战争”中,以色列还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面积约为700平方公里的戈兰高地,当时该地人口约为6000人,大多数是德鲁兹人。按照国内学界的一般看法,本文将德鲁兹人视为阿拉伯人内部的一个次群体(sub-group)。但也有学者认为德鲁兹人是一个区别于阿拉伯人的少数民族。1981年底,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关于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法令,事实上吞并了该地区。1981年底,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关于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的法令,事实上吞并了该地区。
④ 转引自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2页。
⑤ 参见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Greenheaven Press,Inc.,San Diego,1994,p.51。
⑥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71.
⑦ 同上,第51页。
⑧ David Ben-Gurion,“Palestine is the Jewish Birthright”,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36.
⑨ 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Westview Press,Boulder,U.S.A.,1992,p.88.
(10) 参见Business Weekly,Feb.2,1997。
(11) 参见赵伟明:《科学技术——以色列经济腾飞的翅膀》,载《国际观察》,1996年第6期,第48页。
(12) Moshe Ma' oz,Middle Eastern Minorities:Between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Washington D.C.,1999,p.38.
(13) 参见Israeli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The Arab Population in Israel,Statistilite No.27,November,2002,p.6。
(14) 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p.88.
(15) 参见Theodor Herzl,“A Separate Jewish State is Necessary”,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18。
(16) 转引自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32—133页。
(17) [美]纳达夫·萨弗兰著、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页。
(18) 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Israel Violates Palestinian Civil Rights”,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199.
(19) 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Mossawa Center,Haifa,Israel,November 2003,p.25.
(20) 参见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7。
(21) Rashid Khalidi,“Toward a Solution”,in Palestinian Refugees(ed.),Their Problem and Future,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on Palestine,Washingtong,D.C.,1994,p.24.
(22) 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28.
(23) 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Israel Violates Palestinian Civil Rights”,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199.
(24) “犹太办事处”是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组织,成立于1929年,总部设在以色列,在美国、俄罗斯、法国等犹太人较为集中的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目前,犹太办事处的活动主要是加强全球犹太人之间尤其是加强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联系。
(25) 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Israel Violates Palestinian Civil Rights”,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201.
(26) 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13—14.
(27) 参见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Israel Violates Palestinian Civil Rights”,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199。
(28) 同上。
(29) 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55.
(30)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52页。
(31) 同上,第155页。
(32) Anne Mary Baylouny,“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Support an Oppressive Israel”,in Charles P.Cozic(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p.239.
(33) [美]纳达夫·萨弗兰著、北京大学历史系翻译小组译:《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第146页。
(34) 参见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8。
(35) 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4页。
(36) 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p.89.
(37) 参见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p.50—51。
(38)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39) 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p.88.
(40) 参见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p.29。
(41) 参见Amin Fares,Ranking of the Arab Local Council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载http://www.mossawacenter.org。
(42) 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43) 转引自[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第28页。
(44) [英]奇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45) 参见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载http://www,sis,pku.edu.cn/wanglian/mzzhy/readings/chenjy.htm。
(4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47)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48) 参见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pp.92—93。
(49) Sammy Smooha,Arabs and Jews in Israel:Change and Community in Mutual Intolerance,vol.2,p.94.
(50) [美]汉斯·J·摩根索著、杨歧鸣等译:《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