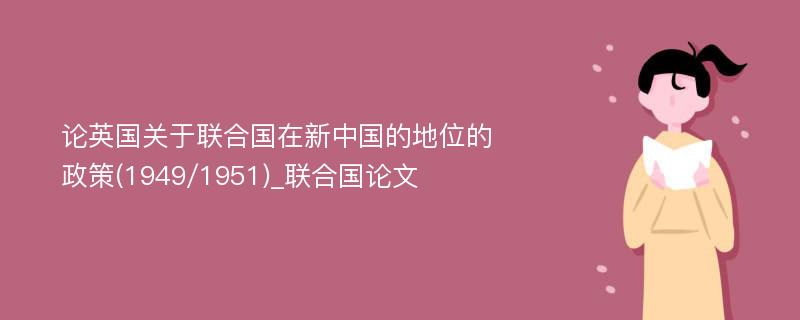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英国论文,席位论文,新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87-09
新中国成立前后,尽管中英站在两大阵营的对立面,但中英关系中亦有若干特殊因素。首先,在远东,英美有利益竞争。随着英国势力的衰落,美国影响上升,但英国在东南亚、中国香港都有难以舍弃的特殊利益。其次,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援助使其难以从“沉船”上抽身,而英国并没有因中国政权更替而产生失落与沮丧。英国工党执政后,其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于内政外交上均有表现,这使英国想同新中国打交道的心情远比美国迫切,因此,1950年1月6日,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英国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本文从英国内阁决策、对美国的游说活动、议院辩论、利益集团与公众舆论影响等角度,探讨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政策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
一、英国投票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已考虑其对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应持的态度。在英国看来,承认新中国就意味着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投赞成票,但考虑到美苏可能各执一端,而这个问题需要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意见,英国希望等到多数成员国赞成时再表态。[1]因此,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间,英国的态度是以弃权票等待多数赞成票。
自1949年11月下旬,苏联代表即在联合国提出新中国席位问题。在1950年1月13日安理会投票中,苏联代表呼吁应将国民党代表逐出联合国。美国代表认为,这只是程序问题而非实质问题。英国方面认为,因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为数不多,苏联的提议不成熟。英国投了弃权票。[2]苏联以退出会议的方式作为抗议。
英国投弃权票的态度,加上英国扣留香港机场的两航飞机拒绝转交新中国,致使两国协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未果。1950年3月,在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同英国代办的交涉中,英方表示,英国会在适当的时候投赞成票,同时也提请中方,“集体多数决定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法,通过协商最能达到目的。”[3]
香港防卫地位的脆弱及英国在华商业集团的利益,使英国政府急于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一方面考虑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说服美国,“即使在中国席位问题上不能够投赞成票,也应该向安理会成员国表示愿意接受席位改变”,另一方面考虑向中国施加压力,“如果中国要消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话,英国就没有兴趣帮助中国争取联合国席位并游说美国采取更友好的政策了”。[4]
不过,这种想讨价还价的念头很快被寻求打破中英关系僵局的建议取代。5月11日,外交部国务大臣扬格建议外交大臣贝文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关系。扬格认为,目前投弃权票的做法不明智,不过是一种骑墙的姿态。[5]首相艾德礼也倾向于改投赞成票。6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从7月3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投票起,改投赞成票。同时,英国也改变在安理会做工作的方法,在各联合国下属组织的投票中,逐一帮助中国争取多数票。
新投票政策一经提出,旋即面临严峻考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贝文表示,苏联可能以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为条件,以保证不介入朝鲜战争。这样,英国决策层中有了继续投弃权票的想法。
鉴于美国的压力,新中国席位问题遂成为8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的焦点,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政策是,在同意改变中国代表团席位获得多数票之前,避免在联合国的任何组织中采取绝对的立场”,而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我们应该避免用无效的赞成票去触怒美国人”。另外,由于美国表示受多数票的约束,“我们的责任在于,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国提出,我们要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6]由此,内阁会议决定,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国会议提出,英国代表应征询政府的指令,由英国外交大臣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与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这样,对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到底投弃权票还是投赞成票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决定权恰好落到贝文手中。①在8月11日致各驻外大使的电报中,贝文相当坚定地表达了投赞成票的决心:“西方国家没有权利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阻挡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拒绝文明世界的行事标准以前,不应使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7]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后,英国决定投赞成票。1950年9月19日,新中国席位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英国首次投票赞成由印度提出的呼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议案,但该议案只获得16票赞成,未能获得多数票。稍后加拿大代表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考虑新中国席位、在此期间国民党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内的提议获得通过。美国对此投了赞成票。英国认为,美国投票赞成至少表明美国承认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英国打算劝说美国不要再游说其他国家投反对票。然而,鉴于美国的反对,英国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游说努力均告失败。
在投票问题上,英国政府一度坚持独立的对华政策,主要基于其对新中国前途的判断。英国自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远比美国悠久,更能理解中国事务。与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自由势力将导致共产党政权崩溃的预期相反,英国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起源与组织方式上受苏联的影响,但根本上仍是本土化的,中国不会甘心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相反,中国将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确立其大国地位有助于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以任何行动或态度,将中国增添为我们的敌人”。[8]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英国一度积极推动帮助新中国进入安理会。
二、对美国政府的游说
展开对美国的游说活动,是英国实施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英国曾努力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但均以失败告终。
1950年5月,英法美三国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展开了首次游说,但对法美的游说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表示,接受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决定,但无意采取主动争取多数票来改变现状,这意味着可望美国不在安理会投否决票。法国对新中国承认胡志明政权表示不满,也无意投赞成票。不过,英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中国永远隔绝于西方世界,因此,英国继续推行其主动接触的对华政策不至于受到美国的猜忌。[9]同时,英国认为“关于对华对日问题,美国没有政策。对于中国,他们看起来连想法也没有”。[10]
同年9月中旬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再次强调除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外别无选择,因为不能无视亚洲人民的意愿,必须避免新中国完全依赖苏联。艾奇逊表示,准许新政权加入联合国的标准应该仔细研究,这样做或许能让中国人感到正在经受考验而不敢进入朝鲜或台湾。在新中国席位问题提出之前,应由全权证书委员会提出一个事实报告,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类事项。一旦新中国席位问题提出来,美国将表示反对,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这样做。[11]显然,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希望以联合国席位作为筹码,以防止新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或借机收复台湾。
因美国的反对,在1950年9~11月的投票中,英国所有的外交努力均告失败。英国意识到,在美国改变态度前,它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英方认为,在11月大选之前,美国政府必然十分在意公众意见。大选之后可望不至于受公众意见的牵制。英国遂决定在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游说美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联合国席位问题再度变得敏感。在此之前,英国舆论多倾向于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连保守党也支持工党政府的政策。之后,英国舆论出现分歧。一些保守党议员表示,在这时允许新中国参加联合国会被认为是软弱的妥协。而一些左翼人士则更加坚定了支持立场,认为如果早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新中国就不一定入朝参战了。
12月,英美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会晤,英国再次同美国交涉。艾德礼向杜鲁门提议就朝鲜停战问题与新中国展开谈判,为此应该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以这一国际组织的名义要求其遵守联合国宪章。英国驻美大使也表示,英国视新中国为联合国成员,仅仅是承认一项事实,这不该成为谈判的障碍。而艾奇逊认为,同新中国谈判就等于妥协,让步政策不会奏效,杜鲁门则强调,新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使美国公众很难接受让中国进入联合国”。[12]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使战线很快推到三八线以南。美国感到颜面大失,力图利用苏联缺席的机会,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新中国为侵略者。英国认为,这样的谴责对新中国而言是不公正的,美国的做法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且将损害其他成员国的利益,难免激起一场反对新中国的有限战争。为此,英国竭力劝阻美国放弃谴责申明,同时策划为双方接受的停战方案。英国建议,组织有中国人参加的停战委员会,划分所有非朝鲜军队必须撤离的安全区,准许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在英国方面看来,形势越是危急,越需要同新中国沟通,通过国际社会施加影响,但中美两国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
1951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新中国为侵略者的决定。英国内阁会议对投票进行了反复讨论,虽然否决的意见占了上风,②但英国仍决定附和美国的意见。英国决策层很无奈:“事实上除与他们合作外,我们别无选择。对我们而言,加入苏联集团不可想象,一直反复考虑建立一个中立或独立的欧洲集团协调于苏美之间,但这方案也常常被放弃——我们的责任在不分裂统一阵线的前提下,避免美国人的不明智或危险举动”。[13]显然,英国无法冒与美国决裂的危险。
1951年3月,贝文因病辞职,4月,这位亲华政策的推行者去世。同月,三位工党内阁成员因反对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削减社会福利辞职,这被美方视为对美国以军备拱卫集体安全政策的公然挑战。美国公众的反英情绪抬头,对英国反共不力甚至亲共的指责加剧。5月,联合国大会宣布了对新中国的战略禁运令。6月,英国宣布对新中国的出口管制,新任外交大臣宣布停止投票赞成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1951年11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保守党执政,英国放弃了在“第三条道路”与“美国道路”之间的反复选择。
对于美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态度,英国认为美国没有将之视为基于国际法的问题,而视为美国的防务问题,这势必将联合国变成一个反共联盟。尽管“犯了大错”、“情绪化”、“非理性”、“不负责”等批评从英国内部转向公开,甚至对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与政治判断力表示怀疑,但英国自身利益决定其必须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曾希望以欧洲为基础,走第三条道路,形成欧洲第三种势力,但随着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西欧复兴计划的提出,英国转而放弃独立的国际路线,接受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仅在远东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在欧洲复兴、西欧防务系统方面,英国完全依赖美国。同时,英国也认识到,倘若坚持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势必要重新检讨在欧洲与美国结盟的反苏战略。显然,英国并不打算走这么远。
三、议院辩论与舆论意见
英国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度的国家。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间,英国两院多次进行对华政策的辩论。有议员提出,中英两国建交未果损害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形象,英国承认新中国的时间与方式都有问题,是“不成熟的”。在对华外交上英国应与英联邦成员国、美国保持一致。如果英国在海上的商业利益继续遭遇困难,英国政府应考虑撤销对新政权的承认。[14]1950年5月24日,贝文出席下议院辩论,为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作辩护。他谈到民族主义在中国且在远东兴起的事实,指出处理问题不仅要考虑美国的意愿,而且要考虑亚洲国家的意见。英国承认新中国的时机是对的,不应用短期效果来判断国际事务中的行动。不应让俄国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能帮助中国的唯一国家。[15]
11~12月间,新中国抗美援朝引发了上下院连续的对华政策辩论。支持意见强调联合国的性质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有益于其运转,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塞缪尔认为,问题在于联合国是“反共国家的联盟”还是“人类的议院”?如果苏联现在正式退出联合国而新中国又被拒之门外,这将是对世界的极端危害。[16]西尔弗曼认为,某些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将联合国当成是冷战的武器或扩散民主的工具,建立联合国是为了维护和平,防止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体制、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危害世界与人类文明。尽管中国是共产党政权,原则上它也应加入联合国,如果苏联退出联合国将是人类文明的倒退。[17]支持意见肯定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及安理会成员的资格,国民党政权已经丧失资格。西尔弗曼认为,“基本的事实是,联合国是力量的代表与反映,当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排斥在外时,联合国是不完整的,缺乏权威的”。[18]塞缪尔认为,“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世界人民的代表’,蒋政权的代表连这第一句话都不够格,除事实上占据台湾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19]帕吉特认为,英国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明确台湾当局不能再在联合国或安理会拥有代表,这是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先决条件。事实是中国已经发生了政权转换,台湾应该交还给新中国。[20]支持意见主张,不能无条件地与美国合作,美国也应考虑英国公众的感受。西尔金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要有勇气,不必害怕与美国意见不一致,必要时要和对手握手言欢。[21]斯坦斯盖特称,美国必须考虑英国公众的意见,必须把英联邦也当成一个压力集团,同美国合作的条件应该是公正对待中国。[22]支持意见还强调苏联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不真诚,因为这不利于新中国成为其卫星国。鲍尔称,苏联不想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希望通过排斥新中国使其长久保持对西方的怨恨。如果继续让苏联有机可乘实在是愚蠢之至。[23]这种想法在英国决策层颇为普遍,是英国推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意见则批评英国外交政策没有与美国和其他盟国保持一致。纳丁回顾了英国外交传统:与美国一致、与英联邦成员国一致、与西欧一致。他批评了外交大臣近五年来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在这三大集团中丧失了领导地位,并将其归咎于外交大臣的三大情结:在面对国内本党与反对党的批评时的“优越情结”、在处理英美关系时的“自卑情结”、在处理欧洲事务时的“孤立情结”。[24]同美国的公开分歧尤其引起反对党议员的不满。麦克莱恩表示,朝鲜战争对联合国是一场考验,是对集体安全理论的考验,“如果敌人知道我们不会开战,如果他们怀疑我们和盟友意见分歧,他们将利用这一事实,从中获取最大好处”。[25]反对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强调英美统一战线是避免战争的根本,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早该与美国合作,承认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从长远看并不值得,将破坏英美的合作关系。[26]反对意见还强调新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违反联合国宪章,此时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会被视为对侵略行为的妥协与让步。艾登认为,不能邀请一个在国际事务领域犯了“毫无借口与不可原谅”行为的国家一起来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27]
自新中国抗美援朝后,英国外交官员更频繁地出席议院辩论。11月29日,贝文在议院发言说,影响亚洲人生活的是新亚洲的崛起,英国外交代表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是有价值的。虽然目前并不清楚中国入朝参战的动因,如果有在国际组织中相互交换意见与看法的机会,或许就不会有目前所面临的困难。[28]出席议院辩论的外交副大臣戴维斯也表示,当一个国家是国际组织的合法成员时,我们不能根据其行为来判断谁该来代表它。中国的真正代表应该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以便于协商、谈判。目前应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保存自由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29]
综观英国议院辩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反对派的声音有所加强,但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张仍然占上风。
英国议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显示出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传统的均势观念使英国主张以国际组织协调国际关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即成为国际联盟的发起国之一。且英国受两次世界大战之害,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以保障集体安全在英国政界已达成共识。英国人认为,联合国是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组织,各国有自身利益与传统,不能强迫一个主权国家违背其意愿行事。作为世界议会政治之母,英国富有长期议会政治的经验与传统,这也使他们倾向于将英国政治经验投射到国际事务中,将联合国视为“人类的议院”而不是“反共国家的联盟”,希望新中国到世界上发出声音。在他们看来,利益争端从战场移向会场,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样的场合不应该排斥任何国家。在冷战加剧时,联合国已经成为不同阵营国家唯一接触的机会,这样的场合不能缺少新中国。
利益集团与公共舆论是西方国家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利益集团在对华外交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党左翼与商业集团。
工党左翼主要指工党内持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大学教授、记者为主,一部分人也活跃在议会。他们经常在《新政治家》、《经济学家》、《当代社会主义者》等报刊上著文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比如,拉斯基曾认为工党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将在罗斯福新政停止的地方起步。[30]1947年4月,一本《向左转》的小册子出版,主要作者是工党议员,宣传“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自工党执政后,一些党内左翼政治家及知识分子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主张英国外交“向左转”,走“第三条道路”,组建美苏之外的“第三势力”。1948年1月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1月初,英国工党还打算与法国社会党共同组织“世界第三方面的势力”,以促进美苏和好。1月22日,贝文宣布建立西欧联盟,与东欧集团抗衡,向“杜鲁门主义”靠拢。英国的转向令当时主张中国外交追随英国走“第三条道路”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发出哀号:“实在太令人悲愤,太令人悲愤呵!”[31]
美国一度对英国的内政外交调整十分敏感,对英国国内出现的社会主义宣传十分不安。在美国看来,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援助不能用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英国成为冷战伙伴的可靠性值得怀疑。[32]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治学者就注意到英国工党左翼对于英国外交的影响,将英国工党左翼视为“苏联的政治同情者”,“对苏联的温和态度已经深入到政治潜意识,一般的社会科学家难以揣测”。[33]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没有出现像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潮,对新中国抱有一定的同情。前卫生部大臣比万曾说:“绝大多数英国工人如出身在中国的话,也会成为共产党”。[34]基尔特社会主义③者科尔说:“如果英国被美国人拖下水同中国作战,我将站在中国一边。”[35]一些英国左翼人士、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1951年1月成立的“中国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的强权外交,反对将战火引向中国。他们提出五项呼吁,其中第二项是“英国应该联合英联邦成员国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坚持允许中国进入安理会”。[36]该会在全英各地建立分会,在1951年1~3月间举行了200多次集会。
商业集团则从功利性的角度鼓吹对华友好。英国重商主义的传统和岛国的现实使得其从事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的愿望十分强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贸易大大超过英国。英国力图重新恢复战前的对华贸易份额,对国民党政府把生意交给美商经营、拖欠英方贷款等均表示不满。与美国在华投资主要在贸易领域不同,英国除3000万英镑的对华贷款外,还拥有3亿英镑的固定资产与对华投资。在英国看来,即使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为实现工业化也不得不发展对外贸易,在远洋贸易中将借重英国。这一切使英国商界希望承认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商界的代表是成立于1889年的中华会社④,他们强调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早在1948年就建议与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区域打交道。1950年8月该会主席走访外交部,抗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会使新中国敌视英国。即使在朝鲜战争中,该会仍设法往中国运送非禁运物资。中英两国外交接触一度停止后,该会仍设法通过东欧同中国做生意。
上述利益集团对英国公众关于中国的看法的影响与美国援蒋集团相似,但方向相反。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⑤显示,1950年6月中旬,美国公众同意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只占11%,反对者占58%,不知道者占31%。1951年2月,英国公众支持者占40%,反对者占35%,不知道者占25%。到1954年6~7月间,美国支持者占7%,反对者占78%,不知道者占15%。而英国公众支持者61%,反对者20%,不知道者19%。[37]显然,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公众的反华情绪空前高涨,而英国公众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同意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主持民意测验的盖洛普也对结果感到惊讶,因该项测验已在英美两国作抽样调查近20年,但从来没有一个问题像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样引起争议,两国人民的想法完全不同。
总之,英国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态度,是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缩影,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政治文化传统、外交战略以及英国对中国革命及新政权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治中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使其对所谓的“共产国家”持温和态度。正是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即使保守党执政(因为有反对党声音的存在),英国也难以成为美国政策的忠实追随者。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1953-1954年间,工党议员在议院重提赞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1954年6月,中英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自1961年起,英国重新开始投票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注释:
①贝文是英国工党温和的社会主义者,1917-1918年间曾领导罢工抵制运输用于镇压苏俄革命的武器。他深受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主张通过国际组织的协商解决争端,认为联合国是走向世界政府的第一步。贝文在英国外交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当内阁会议决定由他权宜决定投票的时候。贝文的坚定态度,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英国政府内部的摇摆。
②"Extract from the Conclusions of a Meeting of the Cabinet held in the Prime Minister's Room,House of Commons,on Thursday,25,January 1951,at 5 p.m.",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Ⅱ,Volume Ⅳ,p.333.根据扬格在日记中的记载,本来主张投赞成票3人,投弃权票包括首相本人2人,主张投否决票的有8人。
③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行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是介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是改良主义的一种,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其代表人物有彭迪、霍布生、科尔。
④中华会社由一批英国洋行、银行组成,如汇丰银行、英美烟草公司等,1949年时有团体会员197家公司,个人会员230人。“Some Interest and Pressure Groups”,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appendix I,p.153.
⑤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美国舆论研究所进行的调查项目之一。因1935年由G.盖洛普创办该所而得名。总部设在普林斯顿。民意测验每年举行20~25次,总统大选年略多。调查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各州按比例选择测验对象,派调查员面访,然后统计调查结果,分析并作出说明,提供给用户。其特点是用简单的随机取样法并且试图把偏差度保持在最低。盖洛普民意测验是一种观点的民意测验,它常常被各大媒体用于代表民意的一种表现方式。
标签:联合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苏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