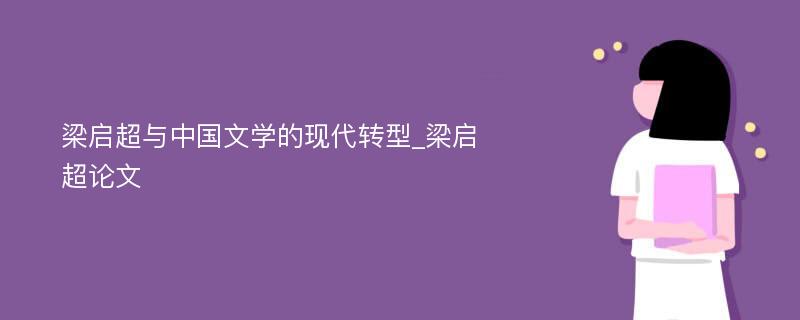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2—0013—09
梁启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他不仅以其意气勃发、文辞滂沛的文字鼓动起一代有识之士的改革思变之心,而且更以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并非与事实相符。
在几为定论的历史与文学研究中,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必自五四“文学革命”起,且必定置设于与前此的一切主张的对抗格局中运思。在这一格局对认识的框定中,梁启超很自然地就成了“改良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属于“新”字号历史时期的“旧派”。近些年来,人们眼界大张,观念亦有较大调整,学界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无奈因成见既深,一时又难以改变固有的选取与评价的尺度,如《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虽属一部视野开扩的创辟之作,但在其列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一编中,却是由“‘五四’‘革命文学’思潮”讲起的。 至于梁启超的种种主张, 虽然更富实质性的倡导多发生于20世纪之初,但却统统被纳入了19世纪。而对于新建构面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该书把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视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有些学者更是难以接受,立即著文予以质疑,坚持认为“中国真正的新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即以中国近世文学而论,在文艺思潮上起了巨大变化的,也不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有人还“进一步看问题”,指出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之说赞成与否,“两者之间根本性的分歧意见,其实在于是否承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其旗帜鲜明的倡导‘文学革命’(本质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
笔者倒是想向质疑者且发一问:为什么一些“五四文学革命”的亲历者对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态度反而与近世论者不同呢?不妨举几例。如,钱玄同可谓在“文学革命”时态度最激烈者之一,可他在“文学改良”(注意:胡适旗帜初张,讲的倒是“改良”,足见“文学革命”初倡时与历史思路的承接)、“文学革命”刚提出之时,旋即致信陈独秀云:“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3〕(P98)又如,郭沫若虽属情绪激烈而善变的人,但在回顾“文学革命”时却并未忘记梁启超,而且称赞他是在那一时代局限中“充分地发挥尽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4〕(P88)。再如,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也说梁氏之“新文体”,“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而且还指出:“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按:指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5〕(卷6,P393)很显然, 这些亲历者都在“现代文学之革新”的意义上热情肯定了梁启超的第一人与先导的作用,赞扬了他对其“个性”与“自由”的充分发挥。那么,为什么到了近几十年来,作为并非亲历者的后辈学者们,倒是另执一言,特别着意于强调本属同一转型过程的前后两段之间的异质性与对抗性呢?质而言之,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分依附于这几十年来对历史所作的政治分期,因此拘牵于以“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为界分的所谓“近代”与“现代”的历史判断,以致形成的迄难有改的思维惯性。故而闻异而动,生怕错乱了被仍然奉为圭臬的“历史秩序”。
这种担心非为治“现代文学”者所仅有,治“近代文学”的人也已给予密切关注了。据报道,1995年6月18 日“第五届上海近代文学研究者联谊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发言者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甚明晰的概念,表面上看,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视界前移的结果,实际上这一说法,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向作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显然会对(中国)文学进程的研究和阐述造成逻辑上的困难。”〔6 〕近代文学研究界出现这种反应的原因,与前者实出一辙,并无二致。
海外的研究自然有所不同。由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述到维新变法的失败时,表示了这样的识见:“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20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找思想的新方向。”〔7〕(下卷P382)这种见解无疑是十分精到的。 但有一点又不能不令我们感到遗憾,那就是当其对维新运动作如是观时,却没有发现恰恰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才使得“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的实现真正成为可能,即梁启超在其时所发挥的独到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忽略。证之于由费正清独立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则更足以见出此说不谬:“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7〕(上卷P358)可见,把1898 年的改良运动及其在文化上的观念变动笼统视为一物,而与“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分列、连缀,为其基本的认识。
由以上情况可知,海内外学者在评价该段历史时各有其见,也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的独特意义有所忽略,没有看到历史在这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此,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价梁启超及其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首要的一点,即是吹拂掉遮盖历史绉折的烟尘,明察以维新变政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
见之于历史的事实是,维新变政失败后,梁启超亡命东瀛,但却得了机会在一个他看来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深刻的反思。他自陈:“既旅日数月,肄业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8〕(文集4P80)。并因此而“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 与前者若出两人。”〔8〕(专集22P186)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间, 梁启超在学习与反思中观念大有改变,在政治与文化上都与原曾为其主帅的康有为发生了分歧,并走出康有为的笼罩。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州。……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既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9〕其态度于此可见大概。对于“新法”, 以及前此的种种变革努力,梁启超皆作了痛心疾首的深刻反思,并从两个方面力陈其弊:第一,没有抓住根本。他认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8〕(文集3P61 )而已历之诸种努力,“至叩其术,最初则外交也,练兵也,购械也;稍进焉则商务也,开矿也,铁路也;进而至于最近,则练也,警察也,教育也。此荦荦诸大端者,是非当今文明国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虽然,枝枝节节而行焉,步步趋趋而摹仿焉,其遂可以进于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国家于不败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什么原因呢?他打比方说:“披绮罗于嫫母,只增其丑;施金鞍于驽骀,只重其负;刻山龙于朽木,只驅其腐;筑高楼于松壤,只速其倾,未有济者也。”〔8〕(专集4,P63)在梁启超看来,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乃积久而成的文化痼疾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民素质的低劣,不触及此,“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也”。所以他断言:“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8〕(专集4,P2)
第二,缺乏破坏力。梁启超列举教育、商务等方面的事例,力证不触动根本症结问题的变革行为的无效,然后说:“推诸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谓新法者必无效也。何也?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者也。”〔8〕(专集4,P64)他指示的“进步之道”则为“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8〕(专集4,P64、65)。
正是在这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转折,原有的维新运动已易帜换将,即已由原来以变革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变法运动一变而为以“新民”为标志的文化启蒙运动,主将也已由康有为而转换为梁启超了。此时,君主立宪式的政治变革已被历史的巨浪推涌到了历史之河的边缘,而代表新的政治革命力量的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尚处于萌动之时,恰恰在两者之间,可谓应运而生,由梁启超大力鼓动和代表的20世纪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入主历史中心,并有幸成了20世纪启蒙运动的开端。倡导变法时期,开启民智的主张虽然已经提出,但它只是被作为变法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次要方面来对待的,所以那时康梁等人虽也看到了文学独特的施教作用,但却不可能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而到此时,文化启蒙已成为主要的责任承当,情况自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考之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似乎可以归纳出一个基本规律:几度“文学革命”的提出或发生,均发生于文化启蒙运动构成为历史主要潮流之时。梁启超倡导“新民”运动时如此,陈独秀、胡适等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如此,新时期80年代中前期“人道主义”涌动时又是如此。其实这也不难索解,因为只有在这种启蒙思潮中,促成文学革命的思想基础和构成文学革命的基本观念内涵,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提供,并使之成为活跃在历史中心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性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后两者自不必说,而作为前者的以梁启超为主将的启蒙运动,是否也具备了与后两者在基本性质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它是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上也有资格被纳入这一过程。笔者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对此问题作如何结论,应该有一个测试的尺度。为取得这一尺度的共识性,不妨就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的进行一个基本的归纳。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进化论为内涵的历史观念,与相伴而生的青春朝气;第二,在对历史症结问题的探索上,历史的思考已由政治转移到文化方面,并在价值观念与价值判定模式上表现出明显的颠覆性重构;第三,对西方式“人权”与“民主”的大力提倡,及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高度重视;第四,激烈的历史态度及对批判力度的强调;第五,对“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提倡。倘若以上概括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笔者则要指出,梁启超时期的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虽然具有不同于后者的阶段性内涵和创辟时期不可避免的初级性特征,但就上述基本规定性而言,它不仅条条具备而且应该说是为后世之启蒙立下创辟与奠基之功的。对历史稍加翻检,便可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的许多基本命题,在此时均有触及或明确提出,而且不难找到它们之间前后的对应及衔接之处。
的确,在梁启超发动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之前,包括他自己在内,人们对许多问题已有触及。再说,某一重要历史行为的出现,再怎么突兀,也需要有必要的历史铺垫。但有一点是必须明察的,那就是此前对这些问题的触及,都只是在政治性变革的总目的的笼罩中出现的,还不可能超越这一历史层面而形成服从于文化启蒙目的的统一与基本整合,因此,它们是散在的,有局限的,甚至在一人身上,也难以取得统一。较之以往的自己和朋辈而言,梁启超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先觉者,他已能够率先立于新的历史进境之中,实现了对各种观念意识的综合性整合,尽管这种整合常常亦难以避免其粗疏及自相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只有到这时,原本散在的而目的又另有所属的各种关涉到历史、文化及文学的主张,才以新的目标环绕统合起来,使历史真正进入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的“新的思想意识时代”,“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不妨依据前文所概括的几个方面,逐条予以具论。第一,“五四”时期为人们时时标榜的“进化论”,实则正是此时予以奠基的。梁启超言必称“进化”,把“进化论”即“天演学”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视为立论的原则依据即“公例”,把“竞争”看作“进化之母”,并认为“此议殆既成铁案矣”〔8〕(专集4,P56)。梁启超的贡献,并不在于单言“进化”,而是将这“进化”之理引向民族痼疾之根本处,并由此而倡言文学革命。基于对历史进化的坚信和力促其进化的满腔热情,梁启超竭力鼓吹“少年中国说”,并作了这样的比较:“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8〕(文集5,P7 )梁启超这种取譬比较的方式,其实也内蕴着一个新旧文化之间的比照,这种方式与内蕴,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人物的思路与表述。由陈独秀向旧文化发难的《敬告青年》一文,就足以见出其承袭的痕迹。而梁启超所谓的“造成今日之老大帝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8〕(文集5,P11),也直接影响到了鲁迅等一代代人的观念倾向。为其所热情营造的蓬勃青春之气,也绵延而为笼罩于整个世纪的历史氛围。
第二,梁启超此时已将思考的重心由政治转向了思想文化,明确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8〕(专集4,P1), 并对传统文化的积累结果表示了明确的批判态度。他指出:“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源也。”〔8〕(专集4,P6 )他还指出,由于世界风潮的簸荡冲激,已能使我国一变其千年来之旧状,但是,“所变者外界也,非内界也。内界不变,虽曰烘动之鞭策于外,其进无由。天下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我辈积数千年之恶因,以受恶果于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责后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8〕(专集4,P60)。陈独秀揭橥文化批判之旗,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其对变革民族病因即传统深层文化的首要革命选择及对近世以来人们由末及本认识过程的推究,其取向与思路与梁启超极为相似,所受影响应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对象理解上,二人表现有明显的差异。梁启超对历史“恶因”的理解,指的是一种上下结合、长期积累的结果,梁启超并不批孔,因为“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盛于彼时者也”。也就是说,当时的孔教是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且与其他学说并立而长,应该是被肯定的。问题出在“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谋,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沈极矣”〔8〕(专集4,P59)。在这点上,陈独秀则不同,他及他的同道,首选的批判对象则为文化源头上的经典学说及其偶像。鲁迅虽也着力批孔,但他也更看重孔学流播变异的过程,在这方面又与梁氏有更多接近之处。此其一。其二,梁启超更为看重“恶因”生成的民间性、风俗性即社会生成的普遍性。他十分痛心于“国民之腐败”,曾说:“今之论国事者,每一启齿,未有不太息痛恨、唾骂官吏之无状矣。夫吾与官吏,则岂有恕辞焉!……虽然,吾以为官吏之可责者固甚深,而我国民之可责者亦复不浅。何也?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而非别一种族,与我国民渺不相属者也。故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8〕(文集5,P18)当然,梁启超虽作如是观,但并未将形成这种状况的基本责任归之于民。他认为,作为社会之理想的传统观念,及其长期的专制政体,均为其基本原因。只不过长期以来因果互生,造成今日革新之更大难题而已。在此问题上虽然陈独秀等并未作如此侧重的强调,但由其对国民伦理觉悟的重视,可见也并无实质性分歧。另外,梁启超对言文长期分离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即“言文分而人智局也”的指陈,并不乏洞见,实际上也启迪了“五四”时期对言文问题的思考。而对传统文化中家族制与专制,梁启超同样予以针砭:“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8 〕(文集5,P9)“五四”时期对家族制与专制的批判亦源乎此。梁启超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已作了根本性调整,而且已基本形成了向西方文化倾斜的价值认知模式,他明确声称:“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8〕(文集4,P61)而且多次强调,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向西方学习,自觉引进西方文明。应该说,“五四”时期的价值认知模式,正是在此时开辟成其基本架构的。
第三,对“国民性”的关注与批判,是20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中心话题,而这一话题,却是始自梁启超时期。梁启超深感国民素质之低劣,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有朝廷而无国家,“有部民而无国民”,他们常常视野窄狭,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8〕(专集4,P6)。 梁启超将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奴性”。他说:“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既言之矣。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8〕(文集5,P18、19)第二是“愚昧”。第三是“为我”。即所谓“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谚有之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国民人人脑中,皆横亘此二语,奉为名论,视为秘传,于是四万万人遂成为四万万国焉”〔8〕(文集5,P22,23)。 第四是“好伪”。第五是“怯懦”。第六是“无动”。梁启超谈到国民性时,常常用语峻急,意在借以棒喝麻木之人。他认为“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8 〕(文集5,P27)。不以棒喝,不足以促人醒悟。 梁启超对国民性问题的重视及对其病状的归纳,对后世颇有影响,尤其是对人人皆以奴隶自居又视他人为奴隶的独到发现与概括,以及对无血性之“旁观者”的指斥,都给鲁迅以深刻启发。在梁启超头脑中,抓到了内部的症结和找到了疗治的药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疗治积年痼疾,他对西方的“人权”、“民主”与“自由”极为崇尚,拼命加以鼓吹,这就必然同时鼓动起了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潮涌。他宣传天赋人权观念,有所谓“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力之能力”〔8〕(专集4,P58)之说;对于“自由”,更是鼓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自由视为“立国之本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8〕(专集4,P40),认为“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8〕(文集5,P46)他还特别强调人的自尊与独立,以为这是克服奴性的不二法门,甚至发出这样的慨叹:“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危哉微哉,独立之在我国乎!”〔8〕(文集5,P44)当然与“五四”时期相比, 梁启超的倡导远没有达到那种“个性”解放的高度,所言未免尚嫌空泛,而且同时强调了对它们的对立性规约。但事实上,“五四”时期尽管一时解构了对立范畴之间的约制,把一个方面推向极端,可是在其思想深处,对立一方的要求也并未消失。譬如鲁迅,一方面强调:“任个人而排众数”〔10〕(卷1,P46), 一方面却又说:“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10〕(卷8,P24 )这就又露出了梁启超影响的迹象。
第四,与“五四”时期相比,梁启超采取的也是激烈主义的历史态度。在梁氏的思想体系中,“破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接受日本影响的结果。他曾专门著文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插;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非经大刀阔斧,则输倕无所效其能;非经大黄芒硝,则参苓适足速其死。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11〕在他看来,这是一条历史的定律,也应该是采取历史行动者的必循的原则。因此在对待传统恶疾的问题上,他主张“苟欲救亡,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8〕(文集5,P17)。倡言“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8 〕(专集4,P60)“夫孰与忍片刻而保百年,苦一部而养全体也”〔8〕(专集4,P63)。
第五,与“五四”时期相同,其启蒙思潮必升浮起文学革命之舟。此项无须多言,因为这是最显见的事实。
以上诸项,论述的重点是两次启蒙思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施之于文学革命影响的一致性,但有此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学界将梁启超拒之于“现代转型”门外的另一理由,是他对文学的主张缺乏现代性内涵。笔者以为这也是为成见所囿,并不符合事实。因为至少有三点可以引以为据。第一,梁启超对“三界”革命的提倡,是在开放性的世界视野中提出的,而且主张从根本性上进行变革。无论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其触媒无一不是来自域外的启发。比如在谈到诗歌时,梁启超即明确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他所以认为黄公度等人“尚不具备诗家之资格”,原因就是他们“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8〕(专集22,P190,191 )。“文界革命”也是如此。 梁启超在为严复的《原富》所写的书评中说,“夫文艺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而为其所倡之“文界革命”,也同样强调了对“欧洲文思”的输入。“小说界革命”倡导的缘起,同样是受了西方的启示,即所谓“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8〕(文集3,P34)。正是西方小说在其社会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开启了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思路。
第二,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文论已明显不同,现代性已成为其基本属性。在诸种文体中,梁启超最为推重的是小说。可以他对小说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为例加以说明。梁氏的小说理论,包含着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内容,一个属于本体论,一个属于功能论。因为梁启超是由对文学独特功能的感受和认识而走近文学并对其作对象选择的,所以他有可能对文学作本体论方面的关注与思考。当时人们大多只是注意到了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因“凡人之性,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虽圣人无可如者也”〔8〕(文集3,P34)。梁启超在写《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时,即持这样的观点。但待到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其思考则有了明显的深化与发展。为什么小说会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成了他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还只是就小说对身边社会下层的人们的宣传作用,推重其作用;而到此时,却是着眼于“人类之普通性”,侧重于考察它的独特的审美艺术特征了。他认为,以“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来解释小说的魅力,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说到根本之处。第一,浅而易解的文字很多,人们何以偏偏以小说为阅读选择?更何况对那些饱学之士来说,对文字的渊古与浅易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第二,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但多不为世所重。最受欢迎的倒是那些读来令人心情沉痛的悲剧故事,人们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以自苦呢?因此上两种说法并未得其真谛。然后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着实精采得很。他说:“吾冥思之,穷鞫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愚之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至深,莫此为甚。此其二。”〔8〕(文集10,P6)读此空前之论,确有叹服之感。如此深刻而新警的剖析,岂可轻易将其完全排斥于现代心理学与美学之外!紧接着对小说所作的功能论方面的概括和分析,也是颇为独到而精采的。他把小说对人的支配作用,归结为“熏”、“浸”、“刺”、“提”四种力。看似很近乎古典的用词及命意,而实则是用现代的时空观、心理学及美学所作的辨析,深富智慧且颇有逻辑力量,自然也应归属于“现代”之列。还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对小说作本体性观照时,对小说之创作范型也进行了归纳。结合他对小说两种不同的本体性特征的阐释,提出“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8〕(文集10,P7)。此即为后世将小说分为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两类的开端。此外,梁启超对文学语言俗化的提倡,主张用口语甚至俚语,这也是其文学观念具有现代倾向的一个方面,与后世亦一脉相通。
第三,以小说为诸种文体中心的现代文体格局,是由梁启超的不无偏激的鼓吹密不可分的。就此而论,梁启超也是头功。
与上述评价的基本思路不同,如果我们逸出目前学界的“共识”性范围,作一些别样的甚至是逆向的思考,那么笔者认为,在研究和评估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系及作用时,有两个问题似乎不应被忽略:一个是所谓别样的思考,即,梁启超只是该时期的一个代表,而任何一时期的历史都是一种结构,决不会只有一种力量在,譬如在梁启超时期就还有个大名鼎鼎的王国维,那么,你承认不承认他也是那个阶段的一个代表?不承认没有理由,如果承认,那好,你承认不承认王国维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众所周知,恰恰是这个王国维,在那时已经做了大量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工作,而且进行了创辟性的研究与建构,他连现代主义的内涵都有了,你凭什么连同他一起把梁启超与之共享的时期排除在文学的现代转型之外?另一个是所谓逆向的思考,即我们应不应该换个角度想想,对被人们视为当时历史局限或者说负面存在的东西也给予重视,给予重新认识呢?比如,激烈主义的态度表现在对旧秩序的颠覆解构即历史价值范畴里无疑是应给以充分肯定,可是它在学理价值范畴中就未必是科学的了。再如,任何一种思想或事物,都一定会处在双重规约之中而与两端相系的,在某一历史关头会突出强调其某一方面,但对另一方面存在的冷静认识是否就永远不表现出价值呢?具体到梁启超,在对他进行评价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在当时,一方面以急激的态度对对立性观念范畴中的一极作极端强调,一方面又时常强调对另一极作相关思考的必要性。这固然表现了他的自缚手脚的局限性,但我们转回头去看这百年时,你又不能不承认他的不无道理的冷静。比方他对于借洋说以行恶的文化畸型物生成之可能的警示,证之于百年来的实际状况,竟被他不幸而言中矣。
最后要说明的问题是,既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梁启超时就已起始,那么为什么陈独秀等人在此后还要发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笔者以为这可从两方面得到解释:一为历史是一个过程,任何事物的生长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相对而言,梁启超虽拥有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创之功,但他的诸种主张毕竟远未达于成熟、圆满的状态。他本人对所处时代及所作努力的过渡性性质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船已离岸(故不能仍归之于此岸),但又未达于彼岸。二是历史又是回旋发展的。具体情况是,在梁启超鼓动启蒙、倡言文学“三界”革命不久,即被蓬勃而起的新的政治革命挤向了历史之河的边缘。新的政治革命以反清排满、保种保教为职志,在文化上势必就相应表现为向民族本位文化内收的趋势,构成了一次历史的回旋。正是在这种情势中,陈独秀等人凭借历史的蓄势,又掀动起了新一轮更为势大力猛的浪潮。如果据此判定某一历史行为的价值,那么仍然是由于历史回旋的原因,新时期的80年代又有新的浪涌,该又如何评价陈独秀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呢?同理,今天我们来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学转型中的作用,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尽量超越各种成见的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有了它,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和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为幸矣!
收稿日期:1999—10—15
标签:梁启超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