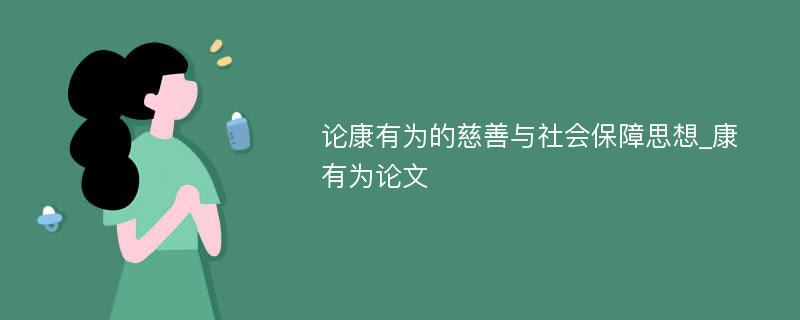
论康有为的慈善与社会保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障论文,慈善论文,康有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7)02-0062-02
康有为是晚清思想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提出的变法救亡理论和大同世界的设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些理论中,他还详尽阐释了其慈善和社会保障思想。在变法富强理论中,他提出“恤穷”,并将其同务农、劝工、惠商并列为养民富国的重要政策。他还主张扩展善堂的社会功能,认为善堂不仅要济贫,还应该宣传孔教和新学。在大同理论中,他抨击传统宗族保障制度的弊端,主张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社会保障制度。他的这些慈善和社会保障思想对近代中国慈善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康有为的慈善思想
康有为的慈善思想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主要体现在“恤贫”和对善堂社会功能的扩展上。前者是其变法富强理论的组成部分,后者是为宣传其主张、进行改革活动而提出的。
康有为将“恤穷”作为其变法图强的举措之一。他在《公车上书》中指出,若要自强,就必须变通旧法,而变法要以富国为先,除富国之法外,还要有养民之法,否则国无以富。养民有四法: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此前,多数慈善家和地方官员兴办善堂善会救助贫民,其目的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是为了实现其博施济众、兼善天下的理想,或者是积阴功以求善报。康有为将“恤穷”作为富国强民的要务,已经超越了其原本的施济功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赋予了它新的社会功能。具体如何“恤穷”,康有为主张应区分穷民的性质,给予不同的救助。对于游民无赖和有劳动能力的乞丐,他主张设立警惰院,教养他们。他指出:“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选善堂绅董司之。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绅董以其工业鬻给其食,十之取一,以充经费,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军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过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1](P129)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等贫民,康有为建议在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1](P130)。上述两种穷民,一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原因而产生的,另一种则是伦理或生理上有缺陷的穷民。后者是自周代文王以来,政府施政和慈善机构首要关注的对象;前者则是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末以降,善堂越来越关注的对象。晚清时,游民和乞丐的数量急剧膨胀,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公众的深切关注。《申报》等报纸曾多次刊登有识之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康有为亦认识到这一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和对国家富强的阻碍。他强调,无业流民因懒惰而陷于困苦的境地,在警惰院中就要从事具有惩罚性的劳动。警惰院的设想是对西方济贫机构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济贫观念也是西方传统的济贫观,它的管理方式则是沿袭中国传统的慈善机构。
康有为不仅将慈善事业与变法图强联系起来,而且他对善堂本身的社会功能的认知亦有扩展。他认为善堂不仅有施善与救济的功用,还可担负起宣传孔教与西学的使命。他在《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指出:“近善堂林立,广为施济,盖真行孔子之仁道者,惟未正定一尊,专崇孔子,又未专明孔子之学,遂若善堂仅为庶人工商而设,而深山愚氓,几徒知关帝文昌,而忘其有孔子,士大夫亦寡有过问者。……本堂创行善举,特奉孔子,如劝赈、赠医、施衣、施棺诸善事,开办有年,今欲推广专以发明圣道。”[2](P187)康有为没有将善堂看作单纯的施济机构,认为还可以利用它宣传孔教、推行自己的学说。他借助广仁善堂建立圣学会,设庚子拜经,广购中外图书和西方新器,并刊布报纸,以宣传孔教和西学。康有为认为善堂既可以从事慈善活动,也可以参与政治或文化活动。当然,善堂被赋予政治与文化功能,由来已久。例如,地方绅士借助善堂宣讲乡约,倡导惜字纸活动。清代在地方设置乡约教官,宣讲圣谕等内容。善堂常常参与宣讲乡约,显然是为了帮助政府教化民众以维护社会秩序。惜字纸则是儒生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以区别于其他阶层或职业的人而兴起的活动,并逐渐成为一种职业信仰。康有为对善堂社会功能的拓展不同于上述诸功用。他利用善堂宣传孔学与西学,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变法革新理论。可见,善堂在不同的时期都会被赋予一些特定的社会功能。晚清以降,中国饱受外来侵略之苦,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革新思潮的高涨,善堂除了施善与教化的功能外,也开始具有宣传维新和变革的功用。不仅康有为借助善堂,其他一些仁人志士也利用善堂参与某些政治、经济活动。如1906年,在收回粤汉铁路运动中,广东的九所善堂会同总商会和七十二行商联合创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参与反美爱国运动,力图收回铁路路权。
二、康有为的社会保障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游历欧美各国,在考察了各国的社会情况后,写就《大同书》,提出“大同世界”的构想。其中,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打破传统的宗族保障体系,确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理想社会保障制度。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生、老、病、死以及教育主要由家庭和宗族承担,之外的穷而无告者则由善堂、善会负责施济救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也主张穷民应该由善堂来救济。到20世纪初,他则改变了这一想法,主张建立由“公立政府”承担的保障体系。
康有为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宗族救助方式。他承认宗族相周恤,使得中国生齿日繁,成为世界人口之冠,但是宗族制的排他性使得中国人对本族之外的人鲜少救助。中国人捐献义田、义庄,救助贫民、兴办义学,仅限于其本族而他族难受其惠。这种宗族救助体系的自私性,使得中国人相互不能救助,从而导致中国的衰弱。他说:“中国人以族姓之团结,故同姓则亲之,异姓则疏之,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故自宗族以外,捐拾之举,为一县者寡矣,为一省者尤寡矣,至于捐巨金以为一国之学院、医院、贫病院、孤老院者无闻焉。……故四万万人不能相助,至以大地第一大国而至于寡弱,此即大地万国之所无,推其原因,亦由族姓土著积分之流弊也。”[4](P372)与中国人重宗族轻国家不同的是,欧美人重视国家而宗族观念淡薄。他说:“欧美人以所游为家,而中国人久游异国,莫不思归于其乡,诚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系人思者,不如各国人之所至无亲,故随地卜居,无合群之道,无相收之理也。”[4](P171-172)欧美人因宗族观念淡薄,才会捐献千百万金钱,创办学校、医院、恤贫院、养老院,救助整个国家的贫民。通过中西比较,康有为认为中国传统的救助体系只限于“自亲其亲”的范围,不如西方的广博,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说:“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4](P173)家制,在康有为看来,正如族制,行仁亦狭,不利于公养、公教、公恤民众。他指出:“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抽公费而办公益,以举行育婴、慈幼、养老、恤贫诸事。”[4](P190)
康有为提出建立一种政府完全承担的社会保障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宗族救助方式。他认为,应当去国界、种界、家界,一切财产归公,建立公政府,由政府承担公民的生育、教养、老病、死丧等事情。他描绘道:“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故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4](P283)在这一理想的“大同世界”中,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公政府承担,主要是“公养”、“公教”、“公恤”。其中,公养机构有人本院、育婴院和怀幼院。妇女怀孕后即入住人本院,当婴儿出生并断乳后,送入育婴院,婴儿三岁后则进怀幼院。公教机构有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儿童从六岁入小学院,十一岁进中学院,到二十岁出大学院,要接受十四年的义务教育。在此期间,每一位公民都会接受良好的人文和科学教育以及专门的技术训练。公恤机构包括养老院、恤贫院、养病院与化人院。人若有疾病可入养病院,而且盲、哑等残疾人也将在此得到妥善治疗和护理。失业无衣食者则入恤贫院,在院中,必须做具有惩罚性的苦工。凡满六十岁的公民即可进养老院,每位老人都将依照各人的功绩,享受相应的待遇。人死后则入化人院。
康有为不仅设想出如此完备和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就可能出现的弊端提出预防措施。他认为太平之世,人太逸乐,即使不工作,也有恤贫院收养。如果人人都怠于逸乐,就会使得大同之世复归于乱世。鉴于此,康有为构想出一套完备的惩罚措施。对惰工者,先是“计日罚锾”、既而削名誉,终则入恤贫院”[4](P284)。对有功绩者,也设置了一系列奖励机制。这说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并无平均主义色彩,而是在追求人人平等、人人幸福快乐的同时,也考虑到人与人的差别,设置了公平合理的奖惩机制。
在如何解决贫民和人生诸苦的问题上,康有为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建议举办慈善事业到主张确立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民间慈善组织只能承担穷而无告者的基本生活;而中国传统的宗族保障体系同近代的社会形态已经不相适应,且它对人的基本生活的保障十分有限。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设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收稿日期:2006-09-03
标签:康有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