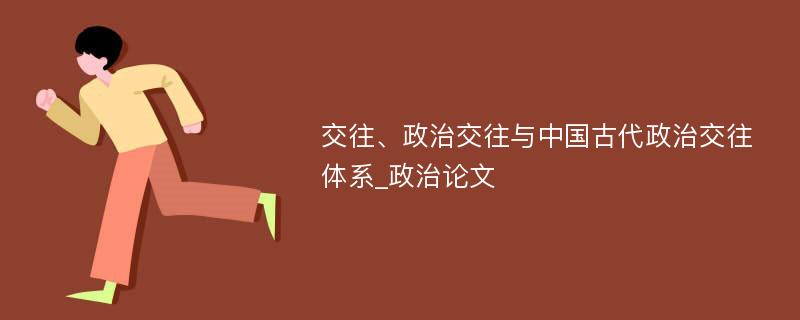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体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学界普遍认为,传播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人类须臾不可没有传播。而政治活动亦是如此,有学者指出:“自从有了政治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治传播”[1]。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自战国以来,官僚政治逐渐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逐步建立,制度之内的传播问题日显重要。阎步克先生在分析先秦官制中“史”官的发展分化时指出:“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正是在严格依照成文法典和充分运用文书档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而“乐师”的变迁对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也有重大影响[3]。从传播学意义上说,职掌文书法典的“史”官和职掌礼乐教化的“乐师”,其与传播相关的职能因政治环境复杂化而不断分化,并在官僚政治运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者总的分化趋向是:“史”官分化为行政、监察系统的官僚;乐师分化为礼仪、教化系统的官僚。前者涉及决策、行政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后者涉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息的存续与维护。阎步克先生认为:“这两个不同文化子系统的两立并存,以及这一格局对后世文化的重大影响,可以构成重要的研究课题,甚至是理解传统政治文化的钥匙之一。”[4]这一观点给从传播视角研究政治制度以重要启发,同样,它也可以作为把握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发展演变的线索。
本文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试对建构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框架作一简要论述。
(一)传播学中的“传播”释义及我国传播研究的旨趣。一般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港台地区引入中国大陆的。引入后被译为“传播学(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hramm)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本书主要是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决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5]从中可以看出,施氏所说的“传播”泛指人类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关于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施拉姆也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6]其他西方传播研究者对“communication”的定义有诸多不同,但总的来说,“communication”的涵义比较广泛,几乎可以囊括人类各种有意无意、单向双向的信息传递活动。鉴于此,我国传播学者张国良先生给“传播”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即“人类(自身及相互之间)传授(传送和接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7]。
《现代汉语词典》对“传播”的解释是“广泛散布”。而“传布”一词又被解释为“传播”。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察,也可以得到大体一致的结果。如《北史·突厥传》最早出现“传播”:“宜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又如,《宋史·贺铸传》云:“所谓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此外,《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中有几处在记载朝廷除授、政令等信息被人泄露的情况时使用了“传播”一词。如“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撰造无根之言”;“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中外”;“机密谋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等。这些古代文献中出现的“传播”就是“传布”,可解释为“广泛散布”,这与英文的“communication”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communication”还含有运输、通信、沟通及信息双向交流之意,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传播”基本没有这些意义。可以说,“沟通”、“交流”、“交往”等信息交互传递行为也应是“communication”的应有之义。可见,传播学之“传播”与中文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在内涵上是有差别的。关于这个问题,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文版的译者也意识到了,他们解释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学”的理由是:“传播学是在近四十年来报刊、广播、电视等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的问题,是信息的点到面的传播中的问题,故译为传播、传播学。用于个人间或两方面交换意见时,则译为交流。”[8]可见,如果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大众媒介,那么译为传播学尚可。但如果研究的是人类一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译为传播学就有些牵强,而且极易使人据中文的理解习惯而“望文生义”。这样容易导致对传播学之“传播”认识的褊狭,进而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问题界定狭窄。目前“传播学”已约定俗成,不便辄改,即便改为诸如“交流学”等也未必合适,因为这样命名同样缺乏概括性,只能根据情境或行文说话方便、准确而选用“交流”、“沟通”、“传递”、“传布”、“扩散”等。因而,不妨将信息的“广泛散布”称为狭义“传播”,而将所有涉及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内涵称为广义“传播”。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如信息决策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教育教化制度、图书文献整理保存制度等都涉及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保存等)时,使用的是广义“传播”。而这正是笔者试图建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
目前,我国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新闻传播或大众传播。而新闻传播或大众传播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媒体信息的广泛散布,“传播”的这一涵义与中文习惯上的理解基本一致。我国传播研究成果也多属于这一方面,恕不列举。此外,文化传播研究也大多是在“广泛散布”(也包括“传承”)意义上认识“传播”的。以上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适应了实际需要,是合理的。但总体上看,对传播学之“传播”如果仅作狭义理解,容易导致视野的狭窄,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与创新。
既然“传播”所指如此广泛,那么,人类的传播现象与行为无处不在。人类传播的特性被学者概括为形态多样性、时空遍布性、行为伴随性及极端重要性等几个方面[9]。这些特性表明,传播贯穿于人类的一切行为。笔者认为,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可以化约为传播活动,或者可以说,“政治就是传播”。
(二)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近20年来也在开拓传播研究的新领域,致力于使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并出版、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论著。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在视野上有所拓展,政治传播及制度问题也有所涉及,如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就设“政治领域的传播”一章,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辟有“政治传播”一章,但总体上不够系统全面,政治传播制度更不是专门论题,因而也没有明确的研究框架。
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与传播有关的问题已被学者涉及,如白纲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导论中,作者写道:“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机构(国家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形式);二是政策法令;三是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同时,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作出十个方面的界定[10],其中“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行政管理制度”、“监察制度”等几方面明显关涉或主要就是信息传播及反馈问题,而且书中的某些部分运用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的概念进行分析[11]。但由于学术旨趣与视野的不同,这些问题虽偶尔也从信息传播角度有所论述,但终究属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并非传播视角的自觉观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及研究框架就有了一定根据。然而,其基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1983年,台湾学者祝基滢先生的著作《政治传播学》出版,考察了政治传播的研究范围,但并未给“什么是政治传播”作出明确回答,而是说“政治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它的研究范围固广,但其理论尚未定型”[12]。而大陆传播学者邵培仁在1991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给“政治传播”下了初步定义,即“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3]。
笔者认为,政治传播应该是政治体系内的活动。关于政治活动,艾森斯塔得将其分为“立法性决策”或“最高统治”活动、行政活动、“党派政治”活动及司法活动几方面[14]。而政治传播活动就是贯穿于诸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很难精准区分,但可以感受到政治传播活动的存在。对于统治者来说,政治体系内的政治传播活动,是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因此,笔者更愿意借鉴戴逸区(K.W.Deutsch)的思路,强调在政治体系中,“建立控制传播的方法”[15],来定义及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因而,笔者暂且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内,统治者作为信息的中枢,利用信息输出、传递、扩散、存储及输入、反馈等方式,完成社会控制、监督、整合及存续,以保持政治稳定、延续的手段与活动。
而政治传播制度与政治制度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政治传播制度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关于“政治制度”,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16]。这个定义是对“政治制度”本质的说明,重点并不在于解释何谓“制度”。美国政治学家里普森(Leslie Lipson)认为:“所谓制度,就是在群体满足公共需要的重复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程式化的行为模式的产物。”[17]借鉴里氏对“制度”的解释,笔者对“政治传播制度”作如下定义: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三)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艾森斯塔得指出,在中央集权的历史帝国中,统治者政治目标的发展,总是为政治体系的衍生提供原动力。他们总是积极“创置或扶植用以动员资源和贯彻政策的各种机构”[18],统治者将创置的各种机构作为执行决策、政策、法令的必要手段,而这些机构就是政治传播的重要通道,“对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19]。笔者认为,机构、职掌、程序化活动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而以程序化活动为重点,政治传播制度就包含于其中。从信息传播角度观察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的体系大致包括如下五种制度:(1)信息中枢的政治决策制度;(2)政治信息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3)政治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4)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5)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五个方面相互关联,但又具有各自的功能,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1.信息中枢的决策制度。从现代政治学的认识来看,政治除了行使暴力镇压职能外,行政管理也是重要的职能。而无论是暴力镇压还是行政管理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传播活动,其都是决策活动。在古代王朝官僚政治活动中,决策活动受到高度重视。可以说,决策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首要问题。白纲等指出,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居于统帅地位,是‘纲’,或者叫作‘轴心’”。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决策权力是最为重要的传播权力,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白纲等认为,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主要研究皇帝制度、朝廷决策机构的构成形式及其机制运行。……朝廷决策系统及其机制运行则包括:决策机构的构成形式(御前会议、宰辅会议、百官会议、内侍参与)、决策的依据与信息传递渠道、决策的程序和方式(诏、制、敕、令的格式、颁布程序、各级官府执行程序)、运行机制(内廷与外朝、朝议与廷争、封驳制度、皇帝最终裁夺权)等”[20]。笔者所规划出的“信息中枢决策制度”与之大体相当。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笔者更重视决策的信息传播层面,如决策权或传播权终端的变化及信息流程环节,决策中信息的公开程度、传播圈层及参与度等。
2.政治信息的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政治信息传递的畅通,是以制度化的传递程序、渠道及媒介为保障的。在这方面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如汉代对公文文书传递的规定就极为详密,且公文文书种类繁多,以确保政令畅通。历代普遍设置了传递公文奏报的机构,如唐代的知匦使、进奏院,宋代的通进银台司、登闻鼓院、检院,明代的通政司等,是负责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的信息枢纽。它们不但传递正式公文,而且还编发公文信息的抄件,形成如唐进奏院状报、明清的塘报、京报等政治信息传播媒介,具有一定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宣传意义。此外,历代王朝的邮传设施及制度也是政治传播制度的重要方面。它是传递政治信息、控制幅员广大的帝国的一条重要的信息渠道。因而,历代王朝大都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法规对它的畅通、迅捷予以保障。
3.政治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据文献记载,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决策信息的收集。如《尚书·尧典》说:帝舜“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等。以后,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大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耳闻目睹,因此,亲自巡视各地成为统治习惯。虽然巡视的目的不仅是收集信息,而且还包括其他目的如宣示权威、震慑地方等,但不可否认它的信息收集作用。但毕竟君主的精力有限,巡视制度收集信息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而,历代还建立了其他收集政治信息的制度。据载,上古“尧有衢室之问”,“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遒人以木铎徇于路”,“采诗观风”等收集民情、治情信息的活动。以后这类活动被制度化并不断完善。此外,古代很早就实行上计制度,将各地的财政、民政等信息层层上报,利于统治者掌握施政情况;古代很早就建立了官吏政绩的考绩述职制度,通过它掌握吏治情况,作为奖惩依据;而且君主还定期或不定期下诏征求民间的对策,尽可能发挥民间士人的才智,增强统治的基础,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此种种,都属政治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
4.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依靠官僚制度的层层设置、环环相扣而运行的。各级官吏在执行信息中枢的指令时,君主的威慑力和对政治文化传统的信仰,基本可以保证各级官吏依法行政、按章办事。但自古君主大都深谙臣下、群吏并非仅仅依靠信仰来从政,往往会有“私利”,他们对君命是遵是违,是忠是奸,是廉是贪,还需要一定的信息反馈活动来行使监督控制的职能。于是,“乃设纠督之任以专察举之事”,设立专司监督臣下、整肃风纪、了解民情的信息监督职掌,作为皇帝的“耳目”与威慑力量。同时,社会风教、世态民情对王朝的政权稳固关系重大,因而,窥伺民间、体察民情的措施也必不可少。这就是所谓的监察制度。在极端专制的非常时期,君主甚至设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曹魏时期的“校事”、朱明时期的“厂卫”比较典型,发挥着一明一暗两条信息监控渠道的作用。这些都属于自上而下的信息监控,是君主的“耳目”。同时,古代王朝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也充分认识到君主不可能没有过失,君主的行为难免不合为君之道,甚至腐败荒淫。所以,历代君臣或是自觉或是遵循成规,普遍主张设置自下而上的信息监督、调节机制,意在对君主的政治决策、生活行为有所制约。这种制度化的活动和职官设置就是政治权力调节制度——谏议制度。应该说,谏议制度在政治调节、制约君主权力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谏议制度比较健全的时期,君主的绝对权力、决策失误及个人的无道行为会受到一些制约,政治往往较为清明。但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中,谏议制度免不了处于从属陪衬地位。虽然规谏君主的职责并不限于谏官,但它仅是制度之内对君主权力的有限调节,广大民众一般无权对君主施政及个人行为进行规谏,更何况历代王朝都制定了相关对言论限制的法规,而且谏议传播大都只在朝堂范围内进行,并不是公开的大众传播活动。它的意义固大,但评价也不宜过高。
“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权力调节制度”大致相当于中国史学界所研究的古代监察制度(含谏议或谏官制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制度与前述“政治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在运行上虽有重合,但所承担之政治功能并不相同,故应单列为一制度。
5.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艾森斯塔得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指出,中华帝国的政治目标属于文化传统取向型[21],帝国的政治得以维护的重要因素是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时,这种取向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视教育教化对于统治合法性的维护。历代王朝大都重视文化传统,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十分重视据实记录历史,并将其引申为后代的治国经验。普遍建立修史机构,设置修史人员。这反映出政治制度的一些特性,即通过官方修史延续政治统绪,表明合法性,建立一种政统接续的自我认定系统。其传播方向主要是以时间的延续为经,即类似于传播学家英尼斯(Harold Innis)所说的传播的“时间偏向”。除了修史外,还重视图书文档的校勘、编目、收藏。其传播学意义主要在于延续文化,自我确认为文化传承的担当者。其次,积极进行图书编辑出版活动,并通过它实现对社会舆论、知识、信仰的控制。尤其是从印刷技术成熟的宋代开始,王朝便开始逐渐加强对出版事业的管制,将其纳入王朝的政治轨道,形成大量官办的出版事业并制定出版法规。清代大规模编修图书既可以被认为是实现理想“王政”目标的途径,也可以被认为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再次,教育教化制度的建立也是王朝实施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包括:(1)王朝中央的官学教育制度,如太学制度、国子监制度等;(2)地方的府州县学及书院制度;(3)察举、征辟及科举取士制度;(4)皇帝皇子的教育与教化制度,如保傅制度、经筵制度、东宫教育制度等。教化传播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它是维系政治统治、传承政治文化、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因而,将教育教化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之一是非常重要的认识、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粗略概括,并非包举无遗,定有缺漏。它亦可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框架。应该说明,其研究重点不在于各制度的细枝末节(因为关于各制度的具体问题,史学界多有研究),而在于从总体上把握政治传播制度的状况或基本模式及不同制度间的关联,从而形成与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别的新的研究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