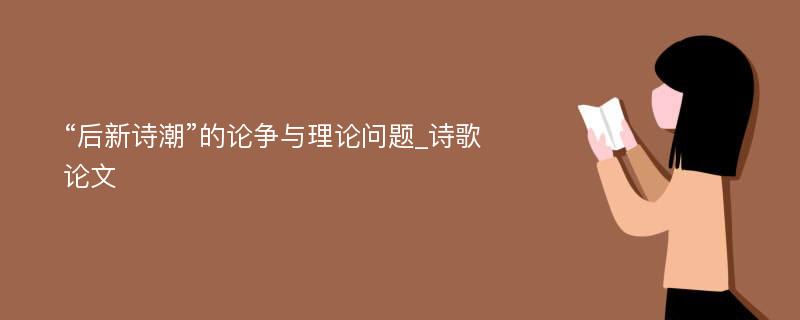
“后新诗潮”的论争及其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1997年7月,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检讨现代汉诗一百年来的历史与经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60人。在最后半天的自由发言中,学者们就现今诗坛上的问题、成绩与出路各抒己见。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诗刊》97年第1 期选载了谢冕先生的《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由于谢冕的文章很久以来不在《诗刊》上出现,这次选载说明了什么问题?紧接着福建社科院的刘登翰先生发表评论。他说,当年(1980年)在南宁诗会上,谢冕和孙绍振为别人“看不懂”的“朦胧诗”摇旗呐喊。历史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朦胧诗”不因某些人的“看不懂”而失去价值。而今,谢冕和孙绍振对现在的新诗表示“看不懂”,是否也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接着,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应该冷静地思考对待,不能急于下结论。因为这里可能暗含着审美趣味的变化等原因。
刘登翰和孙玉石的观点引起了一阵波动,显然,由于“朦胧诗”论战的情景宛在眼前,当年那些论战的人们如今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关于“崛起”的主张被证明是有理论的魄力与远见的。
而今,它让这些旗手们反回来对现今的诗歌创作表示“看不懂”,说这些人是“艺术的败家子”〔1〕与“沉溺于自恋的人们”,〔2〕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在回应着当年反对“朦胧诗”的主张。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检讨“崛起”理论的演变轨迹,更要检讨长期以来关于诗歌的基本观念与立场。
但谢冕先生对于他们上述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之所以写《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现在的诗歌创作存在着“浅薄和贫乏”的缺陷,而这种“浅薄和贫乏”是以“深奥”的外表为掩饰。因此,在如今创作多元、各种姿态均可亮相的“丰富”年代,创作成就却存在着“贫乏”特点。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他还谈到,在前几年的贵州诗会上,有些年轻的诗人们就认为谢冕代表的诗歌观念及批评应该“下课”了。其实,他无心上课,只是摆出一种事实,有许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都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我们写的,为什么现在有的诗要拒人于门外呢?同样,孙绍振先生也在会上谈到,当前诗歌的最大弊病在于“虚假”,不但在于虚假,而且也容易走向放浪,从人格的放浪到艺术形式的放浪。后来,他的这次讲话变成文字:《后新潮诗的反思》。大体说来,这两人对当今诗歌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他们据以立论的诗歌美学观点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诗歌当作是和人们生活相关的严肃艺术。因此,在批评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背景,都认为诗人应当担负起社会或艺术的职责。显然,他们认为,现在诗歌创作存在着对社会或艺术乃至个人不负责的现象。所以应该批评,乃至警告。
这次讨论是热烈的,且又在学术的规范内运作,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意气之争,有的只是把自己心中蕴积许久的观点陈述出来。会议的组织者王光明教授后来收到海外与会学者的赞扬信。尽管这次讨论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毕竟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当今诗歌的发展未来。有了这样的基础,有关后新潮诗的讨论才会更深入下去,才有可能对创作和理论产生久远的影响。
从理论的层面上说,他们的分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谢冕在《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中所说的:“对当前的诗感到失望的不仅有曾经反对过新诗潮,而且现在还在死守固有观念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主张对新诗宽容和变革、并且坚定地为新诗的现代化呼吁的更多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问,为什么原来对新诗宽容和变革的人现在回过头来反对当前的诗歌?是新诗发展过程出现波折,还是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坐标发生倾斜?在我看来,如果一直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当年《诗刊》批判孙绍振文章所具备的意识形态意味在这次选载中可能要淡薄得多。或许,它的确代表了许多对诗歌抱真诚态度的人们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又不能和诗歌创作保持一致。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了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给我们怎样的理论启示呢?
历史的回顾
如果我们检讨谢冕和孙绍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理论主张,可能会对我们理解他们现在的批评意见有所帮助。关于“朦胧诗”的论战及其“崛起”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解他们诗歌理论的最好材料。王光明先生《艰难的指向》在谈到谢冕的批评理论时说:
谢冕关于“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思考,在诗歌和理论界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回响……谢冕关于中国新诗的思考,他的对于历史道路的检讨和反思,以及他的批评新风格,除了其学术价值外,还昭示我们在民族生活经历了重大历史挫折后,他与同代思考者从盲目走向自觉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觉醒。
这段话实际上已经点出谢冕诗歌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谢冕那一代的批评家来说,关于诗歌的主张从来没有到要脱离人民和社会的地步。他们在诗歌批评中表达自己的“进取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觉醒”,甚至表达在经历了重大历史挫折后民族生活的新概念、新思想。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说到:“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即是把诗和社会生活联在一起。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并不矛盾,而最后发展到对“三个崛起”的批判,一方面既说明当时的理论界并未真正肃清“文革”以来文学观念的僵化模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意识形态急需建设的局面。1981年《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前加了编者按:
……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
《诗刊》的倾向性很明显,即把孙的文章列入到反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立场上。其实,孙文说:“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正是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但这对于刚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文化界、诗歌界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不是去探讨理论的来龙去脉,而是在字里行间寻找与意识形态相关或相反的字眼。探讨学术问题不是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因此,“朦胧诗”的论争最后竟发展到依靠组织和权力来解决。这真有点像古代的“上亲称制临决”了。
十几年前,谢冕和孙绍振所提倡的诗学主张至今还在他们的理论中听到回响。对于“朦胧诗”,除了强调要采取一种容忍和宽宏的态度外,还正面提出了诗的“美学原则”,即允许诗人表现自我的心灵,而不是一味纠缠于外部世界的歌颂上。孙绍振认为“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3 〕这些观点对于八十年代之前文学创作中强调政治性的“自我”而否定个体的“自我”无疑是尖锐的批评,但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并没有否定诗歌要和人民、时代保持一致的意味,并没有发展到诗歌应表现纯粹个体自我的理论追求。一方面,他们认为诗歌要以个体内心的体验为基础去反对那些标语式、口号式的空洞诗歌。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诗歌还是必须和人民、时代结合起来。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提到“传统”。谢冕说:“传统不是散发霉气的古董,传统在活泼泼地发展着。”〔4 〕孙绍振说:“目前年轻的革新者自然面临着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但是如果他们漠视了传统的习惯和积极因素,他们有一天会受到辩证法的惩罚。”〔5 〕他们所说的“传统”至少包含了诗歌和时代相结合这方面的含义。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谢冕据以反对当前诗歌弊病的一个例证就是举出许多伟大诗人的例子来说明“代言”的作用。但这点在八十年代的论争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今,面对当前诗歌创作的另一种现象,他们理论的这一面开始发挥作用了。
在武夷山诗会上,谢冕作了《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地梳理了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在最近读到一篇关于文化和诗的激情的宣言中,证明那些星星点点的理想的火光并未在世俗和物欲交织的风中熄灭。在那里,回应着上个世纪拯救国运的呼声,为振兴中国文化的激情充溢着那些不免宽泛和夸张的言辞之间。这至少给人以新的气息,即中国的知识者和诗人并没有沉溺,反省和批判的精神在一些人那里正在默默地生长。
有关诗歌和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段充溢激情的评论中表露无遗。诗人应当担负起神圣的任务。谢冕说:“这些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诗,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但又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得到传达。它们并不因理念而轻忽情感,也没有因思想而牺牲审美。也就是说,这些承载了社会历史内容的诗,并不因为‘代言’而失去诗的品质。诗不仅没有在完成它的使命中成为‘非诗’,相反,受众却因诗对社会历史的关切不由自主地亲近了诗。诗人因成为时代的‘代言者’而获得信赖。”他还说:“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对‘代言’带来了消极的后果。”〔6〕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 关于诗歌特征的思考让位于对诗歌价值问题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诗歌成为“代言”的角色反而有助于诗歌特征的价值完成。同样,孙绍振也说:“我们希望一切诗人都能把对于诗的使命感,对于个性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使命感统一起来,首先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才谈得上把自己的生命升华为诗。”〔7〕这些评论很明显摆出一种姿态, 即对于八十年代后期诗歌创作中自我与时代相脱节的倾向提出批评,要他们多关注诗歌与社会间更富有价值内涵的本质联系。
从“朦胧诗”到现在大致可以看出谢冕和孙绍振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在理论和情感,思想和审美,个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他们对后新诗潮提出批评正是担心中国新诗的发展会走进一条与“朦胧诗”之前本质相反的另一歧途。这是他们一贯的诗学理论主张导致的结果。
其实,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本世纪上半期的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就有类似的主张。 艾略特有感于维多利亚后期浪漫主义诗歌造成自我情感泛滥的弊端,强调逃避自我,提倡“玄学派”诗人、提倡“客观对应物”,对于诗的特征给予高度重视。他说:“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8〕但是, 艾略特又对诗的价值判断情有独钟。他说:“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决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9〕这个标准即是诗人作家“对人类所作的思考、 体验以及观察的总和。”〔10〕即他们说的“智慧”。这貌似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一方面既要反对诗歌的“非诗”性,另一方面又要对诗特别是诗人给予适当的限制。对于谢冕和孙绍振这一代的理论家而言,有谁至今公开宣称,他们反对艺术与时代相互促进的主张?有谁公开声明,诗歌应当深入内心生命而不顾及其余?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艺术主张。
就他们二人而言,由于受过北京大学的严格训练,在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就聆听过当时著名学者的教导,他们的艺术见解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艺术的审美物性给予充分重视,如何其芳、吴组缃、林庚诸先生的影响。这点后来用以攻击“朦胧诗”的反对者。其次,他们从不对艺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点后来用以批判后新诗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艺术见解有坚强的文学史基础,这是他们对自己理论深信不疑的原因。谢冕在武夷山诗会中以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李白等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持。他认为,这些大师从没有和时代脱节过,从没有沉浸在自我的圈子里。言外之意,后新诗潮的许多做法并不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因此,结论自然是,要想产生伟大的诗歌是困难的。这个问题直接摆在当今诗人的面前。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至今的确还没有产生伟大的诗歌作品,而且,我们还存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一直走下去,我们是否会产生出伟大的诗人呢?如果不能,后新诗潮的许多理论主张就有反省的必要。按照谢冕和孙绍振的看法,要想产生最伟大的诗篇,对诗不能抱最纯粹的观念。对于这个悖论,后新诗潮的作者们该如何解答呢?
语言及其他
无论如何,后新诗潮是以对“朦胧诗”的反动为其开始的,他们反对“朦胧诗”,宣称舒婷等人pass,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强调个人写作,这些都与“朦胧诗”相去甚远。
现在一般认为,“朦胧诗”代表着“一代人的呼声”,即把49年后出生的经过“文革”磨炼的知青一代的痛苦表达出来,从而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那个非常岁月里的心声。从诗歌理论上讲,由于他们的创作总是牵挂着要为人民、国家谋求“希望”、“明天”,实质上是把诗当作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性正是“朦胧诗”的共同写作策略。
所以,要反对这种工具性及其衍生的诗学理论。诗歌不是一种工具,无论用这个工具去完成怎样性质的任务。诗应是自足存在的,应当在有限的文本范围内完成诗歌本身的特性。 因此, 当他们宣布舒婷等人pass时,诗和自我语言等相关的理论也就纷纷出台,原先诗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淡忘了。
诗的工具性也好,诗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也好,实质上是诗和意识形态之间某种作用力的反映。“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们之所以要采取反抗的姿态,可能已经觉察到诗歌和意识形态之间亲近或对抗关系都将损毁诗歌的表现力,在更大程度上是摧毁了诗人寄托在诗歌中的各种写作自由及语言的魅力。至少,在“朦胧诗”那里,关于诗歌语言的运用远未达到充分发挥其表现力的境界,由于要代替抒情自我进行一种主张式的宣称,诗歌语言失却多方位的张力,从而也使得语言自身在文本内整合再生意义的创造能力下降。这点,对于诗来讲,是致命的。
所以,无论“朦胧诗”之后的诗人在写作策略上多么不同,在强调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以及充分使用语言带给写作的自由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天地。对于语言的实验,对于诗歌题材的挖掘,对于自我、生命的沉思,无疑大大激活了“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坛的创造力。他们把个人化语言、日常语言整合成一种有个性的诗歌写作来体现一种语言的魅力,从而把诗歌的表现力不断扩大,这是他们的成就。如朱文《中午的实验》:“早餐有煎鸡蛋,午餐有西红柿,晚餐有红肠/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我牢记所有成员的嗜好和进食时间。”
这类被谢冕称之为“个人化倾向”的诗歌,其特点是“增强了诗歌抒写个人情志的分量”,“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以往缺少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姿态。”〔11〕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谢冕认为“其重大意义不容怀疑。”〔12〕
但这里存在着深刻的理论悖谬,强调诗歌语言固然对表现诗歌本身的“诗性”有巨大帮助,对于诗歌写作沉溺于“非诗”状态尤具打击力,但诗歌的价值却又不是单纯地依据“语言”来衡量。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如但丁、歌德)对于诗歌语言的关注远不及他们对其他问题(包括诗与非诗的因素)的关注,这可能关乎艾略特所说的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本身。所以,当“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们在语言的运用中表现出一种狂欢的语词快感时,一种新的弊病也就可能随之产生。具体地说,由于对语言表现力的过度嗜好,语词与指称的物的距离就被无限拉大,不仅词和物的距离被拉大,词和词、句和句之间的缝隙也在不断拉大,这就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意象变得无足轻重,从而导致文本自足系统的破坏,文本变成单纯的语言舞蹈。也就是谢冕所说的:“我们无法进入诗人的世界,那里的形象与意象拒人于门外。”〔13〕
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同意臧棣的看法:“把写作的可能性简单地等同于写作的自足性,把写作的实验性直接地等同于写作的本文性,把写作的策略性错误地等同于写作的真理性。这样,写作在整体上必然蜕变为一种与主体的审美洞察无关的、即兴的制作。”〔14〕臧棣把这点归结为写作的有限性或写作的限度问题。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作为写作的有限性与限度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终又要指向诗歌的价值判断问题。“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们对诗歌语言的狂欢与嗜好似乎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主义观念,即他们能够借助语言来恢复过去被摧毁的诗歌神话。或者,他们对“朦胧诗”工具性的反动向人们展示诗歌宗教主义的观念,即他们可借助诗歌来达到超越语言、道德、文化逻辑,达到个体自由与远见卓识的纯粹状态。这些,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义极端膨胀的标志,它使得诗歌语言处于过度消耗的状态,并且还隐藏着这样的认识动因:诗人可以通过自己对诗歌语言或其他方面的纯粹专注状态而达到完全把握诗歌的“诗性”。但问题是,这里存在着个人有限性的事实。由于个体智能上的有限性使得任何一种行为(包括诗歌活动)要想达到对真理(包括诗歌的“诗性”)的把握是不可能的,因而,相反的例子是,那些伟大的诗人正是在承认个人有限性的前提下进行写作。关于这点,孙绍振就批评后新诗潮的偏颇:
(单纯)审美经验的积累要达到饱和,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心灵的纵深层次的探索和社会生活的探索结合起来呢?孤立地探索心灵固然是对过去孤立地强调外部社会环境的惩罚,但是孤立强调内心深层的探索难道就不会引起另一种惩罚吗?”〔15〕
这段话是在十年前说的,中国诗歌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已经成为个人化的写作,许多诗人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自己开始全面地反思。作为后新诗潮的重要人物之一,肖开愚在自己的“诗论”中就有令人深思的主张:“1.必须有所创新,在技巧、价值观和感觉等所有方面。2.降低语言敏感度,使语言摆脱神经质的困扰,不至于巧言令色。3.写作范围坚定地局限在现实生活或历史领域,在这个范围内使用个人经验和想像力。”〔16〕无论肖开愚的诗歌实践是否做到了以上三点,但至少说明,他对于自“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创作深有体会并具有深刻的反思精神。特别是第三点,即明确点出后新诗潮写作中个体的有限性问题。同样,后新诗潮的代表人物翟永明似乎在回应着“朦胧诗”的工具性:“诗就是我对外部世界交流的声音,在这个越来越使人陌生的时代,唯有诗歌能越过我内心的障碍与人们接触,它把个人的梦想建筑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地方,并使现实有了特殊的意义。”〔17〕我觉得,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渐渐显露出一种心智的成熟,像肖开愚明确主张把写作范围定在现实生活或历史领域,可能也是对个体内心孤立探索的一个反拨。有了这样的基础,当代的诗歌创作才有可能走向成熟。
总之,后新诗潮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些诗人而言,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他们都是一批可贵的实践者,中国当代诗歌必须依靠他们才能向某种目标靠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谢冕和孙绍振的批评当作是一种期待和呼唤,期待和呼唤新一代的伟大诗人。毕竟,对于后新诗潮的诗人而言,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误区。如何从他们的理论批评中警省思虑,如何从历史与传统的因素中汲取营养,如何摆脱纯粹个体的状态,都是现在诗人应该考虑的。海子说过:“但丁将中世纪经院体系和民间信仰,传统和文献,祖国与个人的忧患以及新时代的曙光——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歌德将个人自传类型上升到一种文明类型与神话宏观背景的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诗歌行为。”〔18〕这也是从历史和传统来立论的。因此,如果要问武夷山诗会以及谢冕和孙绍振的批评有何理论意义?那就是,把单纯的后新诗潮的讨论扩展到如何树立典范以及如何为中国当代诗歌寻求出路的问题。正如我们现在的学术需要巨人一样,我们的诗歌也需要巨人。
注释:
〔1〕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 见《厦门文学》1997年第10期。
〔2〕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
〔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见《诗刊》1981年第3期。
〔4〕见《在新的崛起面前》。
〔5〕见《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6〕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
〔7〕见《后新潮诗的反思》。
〔8〕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9〕艾略特:《宗教与文学》,见《艾略特诗学文集》。
〔10〕艾略特:《什么是基督教社会》,见《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12〕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
〔13〕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
〔14〕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见《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5〕孙绍振:《关于诗歌流派嬗变过速问题》,见《诗歌报》,1987年10月6日。
〔16〕肖开愚:《动物园·诗论》,见《厦门文学》1997年第10期。
〔17〕翟永明:《称之为一切·诗论》,见《厦门文学》1997年第10期。
〔18〕《诗学:一份提纲》,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
标签:诗歌论文; 孙绍振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谢冕论文; 朦胧诗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