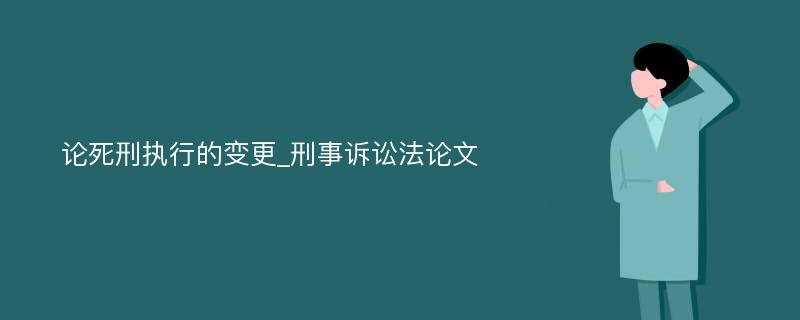
论死刑执行之变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5.04.004 刑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了死刑制度,同时分则中又有较多罪名的法定刑包含死刑,而我国的死刑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的思想,因此死刑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更,更应受到重视,以期更为严格地控制死刑。本文对此略加研究,以便对死刑执行中的刑罚变更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 一、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变更问题 (一)孕妇死刑禁止适用条款的保护对象 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各国对于妇女的死刑适用有着不同的规定,尽管没有国际规则禁止对妇女判处和执行死刑,但俄罗斯刑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对所有妇女均不适用死刑,白俄罗斯、蒙古、阿尔巴尼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也同样如此。不过对于孕妇,更多保留死刑的国家则规定不适用死刑,或者有的国家例如科威特法律规定:只要是刚刚生育的妇女,其判决就会自动被减为终身监禁。也有很多国家,则仅仅规定对孕妇暂缓执行死刑,有的国家没有规定妇女生育后至可被执行死刑的最短期限(例如巴巴多斯、喀麦隆、日本、黎巴嫩、尼日尔、卢旺达、韩国、泰国、多哥、土耳其及阿联酋),有的则规定了具体暂缓的期限,例如在印尼该期限是40天,在埃及和利比亚是2个月,在约旦是3个月,在菲律宾是1年,在也门是2年。[1]229但在美国,有10个州允许对孕妇执行死刑,虽然大多数州规定要到怀孕终止时才可以执行死刑。[2]262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对于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其保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即怀孕妇女本身还是同时包括胎儿?这直接涉及孕妇分娩后是否执行死刑的问题。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79条规定:受死刑宣告的妇女怀孕时根据法务大臣的命令停止死刑执行,但可在分娩之日起6个月内再发布执行死刑的命令。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了类似制度,其《刑事诉讼法》第465条第2项、第3项规定:受死刑谕知之妇女怀胎者,于其生产前,由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停止执行。于其生产后,非由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不得执行。在日本,一般认为胎儿没有责任[3]214,所以妇女正在怀孕时不能执行死刑,但分娩之后,这一障碍消失,自然可以对曾经怀孕的妇女执行死刑。显然,这样的规定本身并不是要保护怀孕妇女,而仍然仅仅关注于胎儿。因此,上述做法实际上也仅仅是死刑的暂停执行和恢复执行,而非死刑的变更。 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5项也规定,对于孕妇不得执行死刑。因而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彻底的,意味着在孕妇分娩以后仍然可以执行死刑。[4]82确实,对于这一条款所指的死刑禁止是永久的,还是一旦妊娠结束禁止也随之终止,始终存有疑问。对于丁斯坦而言,一旦孩子出世或者其他原因妊娠终止,该妇女即可以被执行死刑。在起草该规定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都讨论了关于禁止是否适用于孩子出生后,但是并未解决这一问题。[5]也有学者认为,按照公约文本,尤其第6条确定的废除主义的定位,特别是第2款第1句和第6款,一旦一个被指控犯有死罪或判处死刑的妇女怀孕,就永远不能执行该死刑判决。[6]143而《美洲人权公约》更进一步规定,对孕妇不得处以死刑,因而在形式上丝毫不存在对孕妇执行死刑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孕妇本身而非胎儿或者出生的婴儿,是这一规定的保护对象。不过,实践中更为精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如果孕妇在刑事诉讼进行期间已经分娩的,是否能够在量刑时适用死刑?甚至如果司法机关拖延量刑,在孕妇分娩前不决定其量刑,而恰恰在分娩后再决定适用死刑,这样的问题也仍然是棘手的,因为主要涉及孕妇认定的期间性问题。 (二)死刑执行变更中“正在怀孕的妇女”的理解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款第3项和第2款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怀孕事实不仅仅是死刑暂停事由,而是死刑变更的事由。这意味着,只要有怀孕事实的存在,无论其暂停执行后是否分娩或者流产(无论是自然或者强制流产),就足以使死刑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更。但是严格而言,上述规定仅局限地适用于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后所发生的特定情形,而且要求执行命令下达后该妇女正在怀孕。考虑到“正在”这一措辞的限时性,至少以下特定困难的情形不能适用该规范:其一,罪犯在死刑核准前,曾经存在过怀孕事实,核准时未发现因而其死刑被核准,但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后,被告人虽然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致使怀孕事实消失,但曾经怀孕的事实在此阶段被确认。其二,更为极端的情形是,例如罪犯在死刑核准后,才发生怀孕事实,但在死刑执行命令下达之前,该怀孕事实消失,因而不符合第251条所规定的在死刑执行命令下达后发现正在怀孕的事实,因而无法适用该规定。 上述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源于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该条同样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此后的司法解释也大体遵循了这一规定的限时性要件。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2条据此做了类似规定,其仍然使用了“罪犯正在怀孕的”这一措辞。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第6条亦作相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依法已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确认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依法改判。因此,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这一规定的“限时性”仍然得到遵循。 显然,针对前述两种特别困难的情形,不能援引“罪犯正在怀孕”这一规定。但是如何适用却存在悖论之处。对于第一种情形,理论上应当采取按照“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这一情形而处理,但无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第2款还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2款规定,前述停止执行的原因消失后,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执行。由于怀孕事实对于死刑判决具有永久性的停止意义而非暂停,这似乎意味着有关妇女怀孕的情形,根本不应该适用于“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这一程序,而应该比照“罪犯正在怀孕”的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而对于第二种情形,严格而言,与《刑事诉讼法》第251条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适用程序在性质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所发生的怀孕事实属于核准后新产生的事实,并不属于新发现的证据,属于死刑的执行变更,原判死刑的裁判包括核准裁决仍然具有其正确性;而后者则需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属于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原判死刑的裁判的正确性遭到否定,因而不属于死刑的执行变更,而是属于原裁判的纠正问题。 因此,前者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第5章所规定的针对错误裁判而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2款的表述为“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2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改判”,其措辞显然意味着该程序有别于审判监督程序,即“裁定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为死刑执行变更的特别程序。这一程序同《刑法》第79条所规定的针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减刑、假释程序一样,均属于刑罚执行变更的审判程序,而减刑、假释程序从来未被认为属于审判监督程序,也并未被认为属于一审或者上诉审程序,只能被认为属于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固然由于发生几率低,在实践中区分两者的意义并不明显,但至少在理论上应当厘清程序的相异性,将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变更程序作为一种独立的程序加以对待。 不过,司法解释的立场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变化。与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2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11条使用的“罪犯正在怀孕”这一表述不同的是,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51条所使用的同样是“罪犯正在怀孕”这一措辞,但是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18条第1款第5项的措辞却变成了“罪犯怀孕的”;第422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确认罪犯怀孕的,应当改判。“正在怀孕”这一措辞被婉转地转换成“怀孕”,从而为扩张《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款第3项的适用范围奠定了基础。 司法解释的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其根本原因应当是为了解决前述所举的困难情形的法条适用问题。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法》中限时性的“正在怀孕”演变为司法解释中的“怀孕”所蕴含的立场改变,以及如何扩张地理解“怀孕”这一死刑执行变更条件,对于死刑的变更范围尤其在程序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此,完全可以联系《刑法》第49条有关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范的立场予以解决。同最初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有必要厘清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变更这一规定的保护基点。应当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第1款第3项关于正在怀孕的妇女应当变更执行死刑的规定,并没有完全独立的保护基点,而依赖于《刑法》第49条的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但是后者的立场本身实际上也是极为暧昧的。上述两个规定显然并非单纯保护妇女的利益(否则应取消所有对妇女的死刑),也并非单纯地保护胎儿(否则怀孕状态消失后就不存在对胎儿的保护,即可恢复死刑执行)或者怀孕状态的妇女(否则在其分娩或者流产后就可恢复死刑执行),也并非保护新生婴儿的利益(否则应当如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关于保护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3条规定,将不得执行死刑的范围扩大到新生婴儿的母亲),甚至也不是保护曾经怀过孕的妇女(否则对所有而不论是否在审判时候怀孕的妇女都禁止适用死刑)。 正是因为规范保护基点的模糊,加上所谓“审判时”这一措辞的含混,导致实务上对此问题歧义颇多。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在1983年、1998年分别通过《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关于对怀孕的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指出:无论是在关押期间或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对怀孕的妇女都不应当为了要判处死刑而给进行人工流产,已经人工流产的仍应视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发现在羁押受审时已是孕妇的,也不适用死刑①;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②。上述解释虽然解决了羁押期间流产的问题,试图回避在非羁押状态下怀孕妇女的死刑问题,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时怀孕但在采取强制措施前自然分娩或自行流产的,或者在收容审查、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期间怀孕但在羁押前流产或分娩的,或者立案之后羁押之前分娩及在羁押过程中分娩的,或者立案之后羁押之前或羁押期间自然流产或分娩后因其他事实被起诉、审判的,是否能被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事实上,刑法上述规定的立场主要在于保护胎儿,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故意拖延程序等待妇女分娩后再启动诉讼程序或者采取强制流产或者分娩等行为③,在解释论上实际采取了极度扩张保护的立场,以便能够更为坚实地实现保护胎儿这一核心立场。因此在解释论上,我们认为对“审判时怀孕”应进行最广义的理解,只要在刑事诉讼的完整过程中,包括立案直至执行,曾经具有怀孕事实的,均阻碍死刑适用,而不论是否流产或分娩,不论流产或者分娩是否自愿,也不论是否属于羁押期间,更不论怀孕时的案由是否属于最终起诉、审判的案由。这样一种解释完全突破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背离”了条文的字面含义。 首先,立法上并未限定怀孕时必须处于羁押期间,虽然可能导致妇女在未剥夺自由之前尽速怀孕(这也是前述司法解释均强调妇女须在羁押期间怀孕的原因)④,但这属于强制措施的得当性或正确性问题,而不应在此加以特别限制;其次,立法仅强调怀孕事实,但并未限定怀孕之后的状态,更未强调最终处理的自愿性或自然性;再次,立法并未对怀孕时案由及最终案由是否同一做出限定,类似限定违背上述规定的保护基点。当然,怀孕事实必须发生在同一审判即同一刑事诉讼过程中,而不能将前一诉讼过程的怀孕事实转移至该诉讼过程法定停止后(例如撤案、已经做出不起诉决定或无罪释放)又重新开始的新的审判或诉讼过程。 基于上述立场,简而言之,对于正在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变更的基点的理解,也应当更多地从上述结论出发,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一样做目的性扩张解释,只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怀孕的事实,无论这一事实是否消失、何时消失以及为何消失,就应当停止死刑的执行而变更为其他刑罚。并且,考虑到一旦怀孕事实被证明,即使在前述第一种情形中,实际存在着原判决、裁定发生错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可能,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可以立即改判,因而没有必要发回,从而实质性地将《刑事诉讼法》第251条所规定的限时性的“正在怀孕”理解为非限时性的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怀孕事实。 由于此情形存在着绝对不适用死刑的限制,因此在依法改判时,当然不应宣判死刑,但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变更后的刑罚限制,这一点是极不妥当的。固然理论上可能一致地认为,在死刑停止执行后,应当变更为执行无期徒刑,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此并未完全地消除,从而使得依法改判可能存在不同的结论,因此应当明确规定变更执行为无期徒刑。尤其是考虑到刑法中存在着个别绝对死刑的规定,无期徒刑并非选择刑,如果不明确规定死刑变更为无期徒刑,在裁量时就可能出现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精神病人的死刑执行变更问题 被告人可能在死刑核准前为精神正常者,但是在执行之前突发精神疾病,或者间歇性精神病患在死刑执行之前也可能精神病发作,由于《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可能产生精神病人的死刑执行变更问题。 (一)精神病人的刑罚适应能力与死刑执行变更 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精神病人的死刑执行变更问题同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之间的关联。对于责任能力的意义,不同的学者存在着差异的见解。古典学派认为责任能力是作为对行为人进行道义谴责前提的自由意思决定的能力,行为人具有认识其行为价值的能力才能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而只有具有这种意思能力的人才能够实施犯罪,因此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而近代学派则认为责任能力是能够用刑罚手段达到社会防卫目的的能力,因此对于意志自由意义上的有能力者和无能力者,就其行为对于社会的责任而言并无不同。对于精神异常者,并非他们不应负责任,只是因为其无法适应刑罚从而不能通过刑罚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加以防卫,因此责任能力属于刑罚的适应能力。也有人主张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但是,结合《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表述,责任能力的核心是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应当认为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所谓犯罪能力事实上并非指精神病人造成法益侵害的客观效果的能力,而是是非辨别和行为控制能力,因而能够根据规范要求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即责任应答的能力。[7] 因此,责任能力应当局限于行为当时的能力,但所谓刑罚适应能力却主要指刑罚执行期间的能力⑤,否则就失去了其独立判定的意义,虽然两者在判定的内容上可能相同,但是判定的时点完全不同。同时,刑罚的适应能力更应该作为诉讼法的规定事项由刑事诉讼法加以规范,而不应由刑法加以调整。如果认为责任能力应当包括刑罚适应能力,则意味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在犯罪后患有精神病的,就变成了无责任能力人,而这样的答案显然同1983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中的规定相矛盾。[7]该解释指出,犯罪的时候精神正常,犯罪后患精神疾病的人,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法律规定判刑,罪该处死的,可以判处死刑。《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也意味着判定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时点为犯罪的时候是否精神正常。 显然,在具备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行为后欠缺刑罚适应能力的人,仍然应当认定构成犯罪且可以判处死刑。另外,即便认为责任能力中的刑罚能力不同于刑罚执行能力,所谓刑罚能力只是意味着适合科处刑罚这种对社会一般人的制裁而非保安处分的能力。[8]230但是在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时,并不需要进一步地证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对刑罚具有感受能力或者承受能力,犯罪能力的具备就意味着他当然具有答责能力,具备了科处刑罚的前提。固然责任能力中包含着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从而使其承担刑罚的含义,但并不存在独立判定刑罚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责任能力并不包含刑罚执行的适应能力,在死刑裁量过程中,并不需要判定刑罚执行的适应能力。 (二)刑罚适应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离 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仍然承认刑罚适应能力并认可其与责任能力和诉讼能力的区分。例如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21条规定,被鉴定人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力;第22条规定,被鉴定人在服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对于自由刑而言,按照《监狱法》第17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对其中暂予监外执行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收监;所列暂不收监的情形消失后,原判刑期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由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收监。 上述《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22条所规定的无服刑或者无受处罚能力,意味着虽然在刑罚裁量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刑罚的适应能力,但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仍然需要考察罪犯的刑罚适应性。上述规定虽然针对自由刑而言,而死刑执行不存在服刑问题,但是这一原则应当适用于死刑执行的变更。如果被认定没有受处罚能力,就意味着其对刑罚没有感知能力,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就无从实现。对于一个没有感知能力的罪犯执行刑罚,尤其是包括死刑在内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刑罚内容,无疑仅仅将其作为了一般预防的工具而非特殊预防的目的,从而丧失了刑罚的正义性。对于缺乏刑罚适应能力的犯罪人执行死刑,使得行刑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报复,成为一种消灭反社会者的手段而丧失了刑罚的本质。以美国为例,1985年针对36个授权适用死刑的州的调查表明,每个州或于成文法中、或于判例中、或于行政法规中规定了恩减条款,以保证具有精神缺陷者不被执行死刑。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福特诉威尼怀特案中依据宪法裁定,各州不得对无能力者执行死刑,且必须通过司法程序来对这一问题作出裁断。1999年,德克萨斯州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免除了无能力者的死刑,后来马里兰州、蒙大拿州决定,如果证实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精神疾病发作,就即时且永久地将其死刑判决减为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1]238-240类似例证在我国台湾地区,在死刑执行前,若发现犯罪人患有精神疾病,就意味着犯罪人没有死刑执行的适应能力,即应当暂停死刑执行。其《刑事诉讼法》第465条第1项、第3项规定,受死刑之谕知者,如在心神丧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停止执行,于其痊愈后,非有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命令,不得执行。这一规定同日本的规定相类似。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暂停死刑执行的情形中,并不包含死刑执行前突发精神疾病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但是考虑到在此种情形下,罪犯的精神正常状态对于死刑的正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针对此类情形,应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死刑犯患有精神疾病而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应当报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暂缓死刑执行,待其康复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下达死刑执行令。这一程序仍然属于刑罚执行的变更程序而区别于一般的审判程序。 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变更问题 《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即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以下简称“死缓”)。死缓制度构成我国死刑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对死刑的负面作用进行适当修正的主要措施。作为死刑暂缓执行的方式,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是否以及如何变更的问题。根据《刑法》第50条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人,其死刑执行的变更有3种处理结果:第一,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第二,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不过,该规定仍然存在着大量分歧: (一)故意犯罪的范围问题 一般认为,此处的“故意犯罪”性质如何,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故意犯罪是否完成均在所不问[9]83,只要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的,就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另外的观点则主张应当对此处的“故意犯罪”作限制解释,应当是指表明犯罪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10]417。在立法上,1979年《刑法》第46条规定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前提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但由于该条件在实践中较为含混,一些违反监管的行为也被认为符合这一条件而不恰当地变更死刑立即执行,导致死缓制度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死刑执行的变更存在着任意性和差异性。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分子在缓期执行期间,只要有不认罪服法、妨害其他罪犯改造、故意浪费原料,或故意损坏生产工具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公开拒绝劳动、屡犯监规、经教育不改的行为,或有现行犯罪活动,或隐瞒了重大罪行等,都应当认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而应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11]240-241因而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将这一条件改为现行的“故意犯罪”这一更为明确的要件,更加凸显了限制死刑的蕴意。不过,尽管理论上后者的解释更加符合死缓制度的设立用意,也更符合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但就立法措辞而言,完全没有限缩解释的余地,而且衡量故意的轻重也仍然存在着任意性的问题,可能导致在死刑执行上的巨大落差而产生不公正。因此,仍然应当统一地、不加区分地认定故意犯罪的范围。 但是,仍然存在着限缩解释“故意犯罪”的可能性,将其限制为必须经过公诉机关指控而为法院审判定罪确认的罪行,从而尽可能地将一些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不合理情形排除出去的可能。例如,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虽犯有故意犯罪,但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而被害人又未提起自诉的,可以认为罪犯并未构成审判确定意义上的犯罪,因而不应变更。又例如,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一旦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而未交付法院审判确定的,也应当排除出去,因为排除了审判机关的定罪确认,对于罪犯而言,如果其刑罚内容将直接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显得过于粗率。也正是如此,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中包含着对故意犯罪的独立认定程序。同前述刑罚的变更程序不同的是,这一程序可能经过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变更执行的裁判才能最终生效。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只要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就必须核准死刑,所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不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在是否核准问题上具有自由裁量权,因而认为除犯新罪应当判处死刑必须立即执行的以外,不能绝对地一律核准执行死刑的观点[12],同上述区分故意轻重而决定是否核准死刑的观点,存在着本质上的类似,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不核准死刑,在数罪并罚后,死缓必然吸收了新罪所判的刑罚,因而导致死缓犯实施即使较为严重但并不需要判处死刑的故意犯罪,其刑罚也不会加重,死缓制度的“死刑性”本质就形存实亡了。⑥ (二)死缓考验期内犯过失犯罪后的考验期限延长问题 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实施了过失犯罪的,应当如何处理?采上述限制解释说的学者的见解认为,在此场合,按照《刑法》第51条前段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因此应当对死缓犯在死缓期间的过失犯罪与原先判处的死缓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新的死缓而自然延长死缓考验期。[10]418这也是通常的观念,但这一观点完全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刑法》第50条规定,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这一措辞同“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规定相呼应,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故意犯罪对死缓的执行变更的决定性意义。没有故意犯罪即变更为无期徒刑,意味着即使有严重的违法行为甚至过失犯罪,也应该在二年期满后毫无保留地予以变更,否则这一规定就没有任何意义。 关键的问题在于:此处二年期满的起算应当从原死缓判决确定之日起还是数罪并罚后决定继续执行死缓之日起计算?同前述第51条前段的规定以及《刑法》第71条有关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相比,应当认为第50条的规定更具有特别性因而具有优先性。因此,在此类死缓的执行变更裁判中,固然需要对过失犯罪定罪量刑,但是应当援引的是《刑法》第50条而非第71条。实际上,即使采取第71条的数罪并罚方式,对新犯的过失犯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虽然再度决定执行死缓,但是这一死缓的确定时间不应该认为是在新的执行刑确定之日,而是在原死缓判决确定之日。更何况,原死缓判决的剩余考验刑期就应当被认为属于“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因此,死缓的考验期仍然应当是原死缓判决的剩余考验期,而不应重新起始计算。前述通说的结果在于: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但在死缓期间犯有过失犯罪的,由于必然存在着考验期限的重新起算,两年期满之后,也无法减为有期徒刑。因此,《刑法》第50条的规定就被变相地解释成为:只有没有任何犯罪,两年期满以后,才可减为无期徒刑。 诚然,后一理解容易给人造成在死缓期间只要没有故意犯罪,即使有过失犯罪,也必须变更刑罚为无期徒刑,因此可能对死缓犯的改造不利。而数罪并罚后延长死缓的实际考验期限不失为对死缓犯一种严肃的警告,因而其结论更具合理性,但这一解释显然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逻辑在应然意义上的正当性。 确实,从逻辑上讲,现行刑法对于死缓执行的变更忽略了过失犯罪的存在问题,因而建议在死缓的变更问题上规定: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但有过失犯罪的,应当对死缓犯在死缓期间的过失犯罪与原先判处的死缓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死缓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后一裁判确定之日起计算。如此一来,在死缓期间犯过失犯罪越晚,死缓执行的实际考验期就越长,对死缓期间犯过失犯罪的虽然不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仍然需要重新进行考验,以体现死缓的严肃性。 (三)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的期限问题 死缓变更执行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均需要在二年期满之后,但是通常认为如果故意犯罪的,变更立即执行死刑则不需要二年期满,在其故意犯罪后即可执行死刑。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死缓变更执行的标准单纯化为是否故意犯罪,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极为简单:在解释论上,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只要故意犯罪就变更立即执行死刑,是否完全用尽考验期对于变更执行的结果就毫无影响,此时时间的延长与其说是为了死缓犯的改善,不如说延长了死缓犯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前述变更执行的标准并非唯一。刑法规定,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产生了在考验期内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时,应当如何处理或者说何者优先的问题。如果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可以无需等到二年期满之后,就意味着死缓犯变更执行有期徒刑的机会大为减少,因而背离了设立死缓制度的根本目的即减少死刑的执行。因此综合考察,死缓考验期间故意犯罪的,也应当在二年期满后才能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这样就为死缓犯在剩余期间内的重大立功创造了前提。 但是笔者仍然需要解决究竟是哪种变更更为优先的问题。死缓犯可能先故意犯罪,后有重大立功;或者先有重大立功,后又故意犯罪,由于刑法规定忽略了两种情形可能并存的情形,因而没有规定何种规则优先。通常主张故意犯罪可以二年未满即可立即执行死刑,因而武断地掩盖了这一矛盾:只要可以随时立即执行,因重大立功而二年期满后可能的变更,也就毫无意义。这样一种观点实际是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方式更为优先,但是考虑到死缓制度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死刑的执行,因而允许又犯故意犯罪的死缓犯,继续考察,看其在剩余考验期内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不予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这样死缓制度的机能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转化成为重大立功变更为有期徒刑方式更为优先。不过,这一做法在立法上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于刑法未曾考虑到上述情形,因此二年期满后,既不执行死刑,也就必须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死缓期间仍然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显然较大,同其他只有重大立功情节而未故意犯罪因而减为有期徒刑的必然存在差异,两者的差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只能在15-20年的期限中加以体现,显然并不明显而不足以反映两者的区别。因此需要立法规定,在死缓期间,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的,无论先后,均变更执行为无期徒刑,这同单纯地具有重大立功而变更执行形成差别,以便既维持死缓的严厉性,又能够平衡地发挥其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 注释: ①虽然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理解“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的电话答复》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仍然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中,正好审判时妇女已经分娩,对其适用死刑并不违背刑法规定,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②对于上述文件对“审判时”这一措辞的扩张解释,亦有学者认为有违立法规定,应当使用立法修改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扩张解释的方法弥补立法的不合理,参见孟庆华:《刑罚适用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③虽然极为罕见或为孤例,但确实发生过侦查机关故意等待嫌疑人流产后的第二天予以立案的事例。 ④但是也有学者忽略了羁押这一要件,认为即使在取保候审期间怀孕但在羁押或者审判阶段并非怀孕妇女的,仍不应适用死刑,参见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⑤例如有的学者即认为服刑能力就是指刑罚适应能力,参见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24页。 ⑥死缓的死刑性意味着死缓正是因为同死刑立即执行紧密相连才具有威慑力,脱离执行的死刑不具备死刑本身的威慑力,参见林维:《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异化》,《河北法学》,2005年7期。标签:刑事诉讼法论文; 刑法论文; 故意犯罪论文; 法律论文; 羁押期限论文; 法制论文; 死缓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