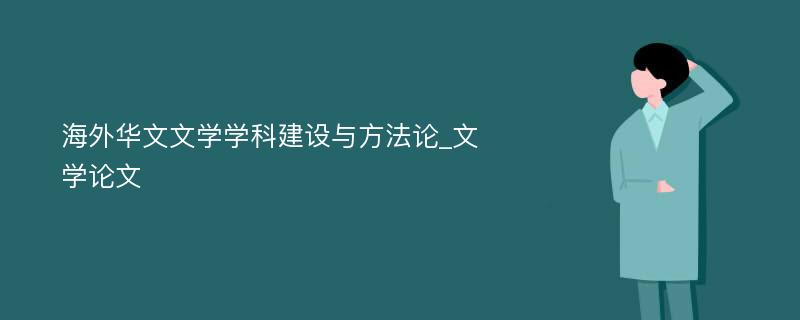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华文论文,学科建设论文,海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本世纪的80年代,如果从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台港文学研讨会”算起,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15年来,我们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对海外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以及如何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等重要问题的研讨,进而转入到学科本身发展中各种理论问题的追问,已经有了许多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海外华文文学这个领域已经无人不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但相对来说,如何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上做出更多的成绩,使其在学科建设上有更大的发展,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在这世纪之交,当人们纷纷在本学科领域作回顾与展望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联合世界范围的华文文学研究力量,彼此协调合作,在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
当80年代初广东、福建两省学者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内地倡导此项研究时,“不少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1〕由于开始时资料缺乏, 早期的开拓者都是从最原始的基本资料积累做起,而响应者则基本上是手头有什么资料就写什么,难免存在一些人所说的“瞎子摸象”、“失衡”、“误读”等现象。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多了,兼之两岸直接交往的逐步实现和最初这批学者奠基性工作的扩展,研究者拥有较多的资料,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热潮迅速展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继1982年、1984年在广东、福建召开的两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之后,1986年第三届会议在深圳大学举行就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这一更名说明,大家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第五届会议,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至此,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进入了研究的操作层面,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在这之后召开的第六、七、八届研讨会,与会学者很多,每一届的研讨会都有新的学术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92年在江西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活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形成一个体系,正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化人的注意和重视,经过充分酝酿,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的出现,即: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无论是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因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的内部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推动”。〔2〕只有这样,才能联合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进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和分析研究,更好地“发扬东方群体主义的宝贵内核”,重建新时代的华文文学。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论文和专著上。但是比之一些历史较久的传统学科,这一领域还很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还有若干局限,在研究上要踏上新一级台阶,困难仍然不少,必须在多方面努力,当中最重要的是应拓展和深化学科内部的理论研究,还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重视方法论的改革和更新。
记得1993年6 月暨南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在广州主办“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时,就有学者提出“建立学科观念问题”,并且认为“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是研究者的一种自觉”。与此同时,也认为“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却还存在许多盲点。”〔3〕事实上“盲点”确实存在,如把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混同一起”是否科学?又如这一领域作家流动性大,在研究中如何避免对他们“文学人生”的“肢解”?……此类问题,既涉及到“学科”内涵的界定,也关系到文学史的撰写,同这些问题相联系,还有如何确定作家“文化身份”等理论问题。当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华文文学整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基点是这个领域的文学在当代的发展。由于不同的人文生成环境,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与大陆本土华文文学不同的模式和轨迹,具有自己独特的进程和形态,因此,加强对其独特性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从我们现在发表和出版的许多论文和著作看,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一是作家论、作品论、作家传略、作家评传;二是“概论”、“导论”、“现状”、“概观”、“初探”;三是国别文论、文体论;四是论文集、辞书;五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早期的成果多是对某一作家的“个例”研究,“个例”研究可以是我们考察问题的基础和起点,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必然要进入整合性的研究、规律性的研究。学术史上许多事实说明,没有终极的研究目标,很难显示出真正的意义,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新起的领域,但它的发展同样要受到学科发展规律的制约。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研究的目,是要在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照下,把握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殊领域的文学特性。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成果中已有过各种各样的回答,有概念判断式的,也有现象描述式的,前者是回答“它是什么?”后者是回答“它是怎样的?”但要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学科,还必须做好学科“底部”的理论奠基工作,那就是对它作进一步的学理式探究,要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何以能成为一个学科?”而这就离不开研究者的学科自觉性和整合性的研究。
我曾在拙作《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题意义》中提出:“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其某类特殊的现象和空间,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4〕我们认为, 新的“命名”很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引起对某一问题的注意,从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和思路。所以在文中作以下追问:1.“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会引起何种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和思路?2.“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以后对原有的其他学科(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等)会造成怎样的学术冲击?3.“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已作为一门新学科存在?还是只作为一种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命名游走在其他学科之间?这些观点的提出,可以视作我们对学科建设问题的积极回应。旨在说明,在“海外华文文学”“命名”之后,要把它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建设,我们还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作更多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
华文文学的“根”是中华文化。但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中写作,在他们的背后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种种纠葛,他们的作品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对故土的回忆。他们在异域他乡坚持用华文写作,“这是一种‘灵魂’的活动”,〔5〕是意味着自己的灵魂已回到了故乡,也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寻找。他们自感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当今生存的地方,但他们也已不是故乡的人。这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精神活动!为了深入探讨他们的精神产品的特殊形态及其复杂性,就必须具有文化学的视野和跨文化的方法。海外华文作家在居住国生活,必然会受到居住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会把华族文化传播到居住国,无论是哪一方,接受的过程必然有所选择,也必然有基于不同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社会心态等等所作的解释和误解。华族文化传播到另一国时,会遇到异质文化,有一个播迁、冲突、认同、溶摄、变化的过程,从而以多少改变的形态出现,并且浸透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艺术形式之中,我们应在文学作品中研究这种文化“变异”的现象,研究这种传播与接受的发生过程,如这一传播与接受是从何时开始的?发生在什么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怎样的“变异”?同本土的华文文学作品比较二者的反差有多大?这种研究将大大丰富了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华文文学,也是对海外华文文学特殊性认识深入的一个方面。
“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或观念的观念。……好的方法在于提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6 〕比较方法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提出和运用,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从整体看,华文文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既要求“同”,也要明“异”,求“同”是有助于规律性问题的探索,明“异”是为了出新的。因为“异”有助于丰富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形象,因此更具有真正的意义。求“同”和明“异”都必须借助比较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在华文文学整体观照下,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相比较,在比较中探索其发展的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碰撞和认同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可以将本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特殊存在方式、美学模式、文学风格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衍变史;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群体的华文文学作比较,探讨它们在同居住国主流文化碰撞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反应与选择。这样做不只是求“同”和明“异”,而是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存在的方式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
将海外华文文学放入文化和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中去研究考察,用比较的方法,围绕某一问题或某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开放性和丰富性。此外,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文坛上女作家很多,而且不乏著名的女作家,在研究不同的作家群体的时候,如能注意到性别与文化的结合,以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这一领域的女作家及其文本,探索其“身份”的共同性、差异性、边缘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通往这个领域深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指出,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是多元的概念,不是一种确定的话语体制和方法,都面临着为自己定义的问题,有如一幅尚未完成的“自画像”。从广义上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身份”批评,它以性别和社会性别身份为出发点,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经历,被忽略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推向“中心”位置,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言说,侧重于对女作家独特的文化经历和身份的研究。因为海外华文女作家是在一个全球性多元化大背景下通过文学创作,来对“性别”、“民族”、“国家”等等问题进行思考与追问,基于她们多重的文化身份及处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混杂性”等特点,我们从研究对象出发,要找到关于它们及其创作的研究理论基点,也可以尝试运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是总体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同样包涵有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复杂性,具体到文学主题上,羁旅主题、乡恋主题等海外华文文学常见的主题,在女作家笔下也时常出现,但在表现和艺术地处理这些主题时,她们往往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从女性的视角切入,以女性的观点表现女性的感受,具有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独特的意识。例如她们会更为关注在文化碰撞冲突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将羁旅、放逐、怀乡等海外华人共同的处境及感受以女性的体验加以表述,而海外女性的双重边缘性处境及在婚恋中困惑的自省,实际上也反映了海外华人生活的特殊处境和情感生活;男与女、本族与异族、祖居国与居住国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透视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理论研究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当今世界上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特点。法国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形象学,主要就是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形象。在一般情况下,作家都是从自己民族文化出发,对异族文化的“他者”进行思考和解释,创造出他(她)所理解的形象。这是两种文化在文学上“对话”的结果,也是一种文学传统、观念对另一种文学传统、观念的过滤和选择,当中不无“误解”,但可以作为一种“镜象”,是异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中的折射。我在拙作《“女儿国”里的人文精神》中,〔7 〕曾经提出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问题,因为在不少海外华文作品里,特别是那些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主题的小说中,这种“他者”形象就更为常见。“他者”即“异”、“异己”,但华文作品中的这些“他者”,并非是现实中真正的“异”和“异己”,是经过华文作家的文化眼光、文化心理过滤过的,是作者按照符合本民族文化要求的道德标准、审美标准评判过的,是异族在华族文化中的“镜象”和折射,他们虽是我们眼中的“他者”,是华文作家笔下的异族人,但已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自己的“变异”。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他者”形象的考察、分析,一是可以反观自己的文化,把握两种文化在文学相遇的反差;二是通过不同文化在人物形象中的结合和“变异”,给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是其作者人生经验和艺术思想的体现。生活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华文作家,各有他们创作的出发点和艺术切入点。研究者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有的努力从总体去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有的则只从一个方面以本文、结构、符号、叙述等,来阐明这种文学现象中的某些问题,故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也会出现理论见解上的差异,在研讨中,我们应把不同的理论形态、见解,看作是激活自己思维的积极因素,拓展学术视野和理论构架,互识互补,共同把学科的理论建设推向前进。
注释:
〔1〕刘登翰:《在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见《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论文集》,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编。
〔2〕刘以鬯:1991年在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3〕同〔1〕。
〔4〕饶芃子、 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5〕叶君健:《我的外语生涯》,见《光明日报》1997年4月23日。
〔6〕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第31页,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饶芃子:《“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 见《香港文学》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