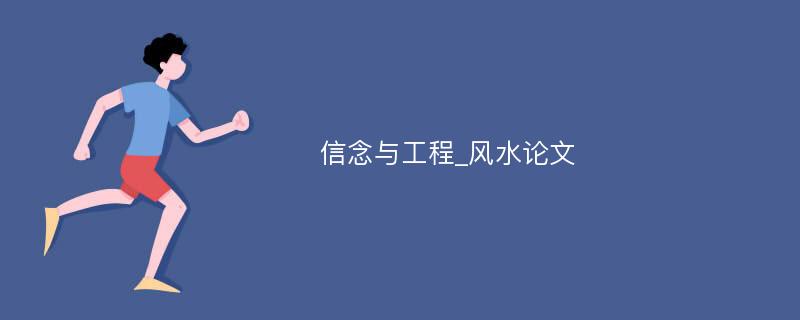
信仰与工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仰与工程”这一标题,就意味着论及二者的关系,要么是信仰中的工程问题,要么是工程中的信仰问题。前者主要体现为“精神创造的工程”行动对某种信仰体系的自我建构与生成,这里主要考察后者。
那么,什么是信仰?从不同的视角可以给出不同的回答,如从心理角度看,信仰是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参见《大英百科全书》)。从行为的角度看,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参见《辞海》)。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信仰是作为知识和实践行为之间一定的中间环节出现的,它不仅是,也不单纯是知识,而是充满人的意志、感情和愿望的,转变为信心的知识。”① 而从功能的角度,信仰则是“人类在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建构的‘宇宙图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社会模式’和价值尺度;在盲目的人生旅途上认定的目的和归宿”②。我本人更倾向从这种功能论、意义论乃至生存论的视野来界定信仰。因此,信仰不仅是“宇宙图示”、“社会模式”、“价值尺度”,而且是人类自我超越和意义寻求的生存方式。根据已故的高清海教授的观点,人与动物不同,具有“两重生命”——自在的肉体生命或种生命、自为生命或类生命。③ 就是说人的生命结构包含肉体的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文化的生命,那么,信仰则是人的精神生命与社会文化生命——“超生命的生命”或“主宰生命的生命”所决定的人的生存特性,即信仰理性与认知理性、伦理理性和美学理性构成人性的主要内容,规定着人生存的三种形态——“唯美形态”、“伦理形态”和“宗教形态”。④ 它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活动提供精神支撑和前验性的知识或意识,是人观念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表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度。就是说,人不能没有信仰,无论你是谁,你总要信些什么。弗罗姆在《生存还是占有》一书中说得更为确定,“没有信仰,人能够生活吗?婴儿难道不相信母亲的乳房吗?我们所有的人不是都相信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和我们自己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一事无成,就会变得绝望和内心深处充满恐惧。”⑤ 因为,“对自己、他人和整个人类以及人使自己真正成为人的能力的信念都含有一种可靠感,但是这种可靠感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以对规定我应该相信什么的那个权威的屈服为基础。这便是一种真理的可靠性,虽然我不能提出不容怀疑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是却能以我主观的经验为根据而相信它。(希伯来语中的信仰叫emuna,意思就是‘可靠性’、‘肯定性’;‘阿门’就是‘肯定的’、‘可靠的’、‘确实的’意思。)”⑥ 在他看来,“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只是对一些没有合理证明的答案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财产是由别人发明的一些说法、表述构成的,这些说法和表述之所以为人所接受,因为人们屈从于这些别人——往往是某种官僚机构。由于官僚机构实际上(或想像中)所拥有的权力,信仰会给人一种可靠感。信仰是一张入场券,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某一大的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摆脱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地思考和做出决定。”其实,“上帝本来是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象征,然而,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却成了一尊偶像。按照先知的说法,偶像不过是人的创造物,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偶像的身上从而削弱了自己”;而“在重生存的方式中,信仰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⑦ 可以说,信仰表达着个体或各种形式共同体(包括宗教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生活基调与生存样态。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把人的生存分为从低到高的三种形态——唯美生存、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那么,它们分别是建立在对重感性的享乐主义、道德观和神的信仰之上的生存选择。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将最终走向人的“自由个性”联合体形态。⑧ 与之相对应,高清海教授将其理解为:群体本位的“神化人”、个体本位的“物化人”,再到类本位的“人化人”。⑨ 我们则可以说,人类走过了信仰群体本位的“神化人”、信仰个体本位的“物化人”,再到信仰类本位的“人化人”。
我们还必须明确什么是工程?严格说来当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工程概念,有的把工程定义为,工程就是按照人类的目的而使自然人工化的过程,是“组织设计和建造人工物以满足某种明确需要的实践活动”⑩。有的认为,工程是人们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手段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以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11) 有的认为“凡是自觉依循虚体完形、通过利用现成实体完形以创造新的实体完形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及其成果,就是工程”(12)。有的认为,“工程是实际地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即“造物”。(13) 有的认为,工程是技术的系统,技术是工程的要素,一种技术的研究与实现过程就构成了工程。(14) 还有的认为,“工程就是人的物化,就是人的社会建构,工程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实现”(15)。可以看出,以上定义的着眼点是不同的,或从“自然”,或从“实践”(或从“造物”),或从“实体”,或从“技术”,或从“人的本质”等视角来界定工程。本人则主张把对工程的认识论理解放置在生存论的基地之上,不仅在空间的坐标下界定工程,而且在时间的视野中诠释工程,凸现工程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历史生成性。狭义地说(实证地看),工程是作为有价值取向的主体(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为了满足其特定需要,以一定经验知识或科学理论为基础,以一定技艺或技术为手段,以一定程序或规则为运作机制的变革现实的建构性的对象化活动及其成果。广义地说(在生存论视域下),工程不只是主体的建构、造物活动与活动成果,而且是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包含建构和培育)(16),是生存主体筹划着去存在的能在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工程作为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特定实践和建构方式,是人的“自为本性”、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特质所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类存在,是工程主体自为的存在,即通过“知道的做”或行动,将意识中的理想、目标等形而上的东西,对象化为持存的存在——实体,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同时通过非对象化活动丰富、提升人的类本性。如此,在空间的坐标下——共时地看,工程在结构上,可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即以工程意识为先导的工程行动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在工程的现实运行中,三者之间是双向互动、互为支撑的,共同组建工程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地说,生存主体以前验的工程文化为根基,以工程意识为先导,以工程方式去存在,进而通过工程行动,组建人工世界,创造各类实存工程。在时间的视野中——历时地看,工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即与人的历史性生存相关联的历史的生成与展开,其纵向结构可分为自在的工程(古代工程或以农业为主导的工程)、自为的工程(近现代工程或以工业为主导的工程)、自在自为的工程(后现代工程或以信息业为主导的工程),分别标志着顺从自然的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工业文明和寻求与自然和解的后工业文明。
在生存论视域下,科学、技术、工程等均构成人的存在样式或样态,但由于工程作为意识外化过程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具体结构和“骨骼”,就决定了工程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体现着人的“自为本性”和类本性。当人类从洪荒走出,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就开始了工程化生存,工程的存在样式是在先的,是比科学和技术更切近的人的存在方式。因为,无论从事任何活动,总是从一定目的出发,工程意识是先在的,作为行动的工程化实践活动是受先在的工程意识所支配的,而作为实存的工程以及人工世界则是工程意识的外化或客观化。同时,工程质量与水平往往受制于科学、技术及制度等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工程的主要矛盾是实然判断与应然判断的对立统一,实然对应物性——客观可测性,回答能做不能做问题,是工程活动的基础,体现合规律性、真理性;应然对应人性——主观目的性,回答该不该做的问题,是工程活动的主导,体现合目的性、价值性,反映人的生存要求、目标和理想。这就决定了工程不仅符合技术理性、遵循真理尺度,而且满足交往理性、依据价值尺度,更多地体现出工程的属人性和生存的维度。所以,必须看到,工程不只是“造物”的手段、工具,也不仅限于具有“造物”的功能,其根本则在于它是人的存在方式,内含于人的生存活动和行为中的东西,因此生存是工程的根本维度。工程的属人性同时也表明,人是工程的存在物,或者说工程是人之为人的属性,离开了工程,人将非人化,成为本能的、仅靠肉体需要支配的、沉没于自然之中的存在物——动物。
从“信仰”与“工程”的界定可以看出,信仰与工程就像哲学、科学、艺术等一样共同构成人类的多层面的生存样式,前者是人观念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表现为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度;后者则是人实证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地表达着人的认知理性、实践能力、生存需要、审美情趣等人文精神。其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早就指出,我们是用多种方式——思维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的和精神的方式等来掌握世界的。(17) 由于工程实践包含了科学、技术、制度、人文等多个维度,是科技理性与交往理性的统一,因而是在更高的层面综合地解读、掌握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因而必然内含着工程主体的信仰因素。或者说,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维度直接构成工程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关涉现实的工程运行,从具体的工程目的到方案设计,从功能到审美,从内容到形式,工程的实现总是或多或少地表达着人们的信仰成分。实际上,没有人类对改变自在自然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属人自然之能力的信仰所形成的工程意志,也就没有表达、确证和提升着人的类本性的工程,甚至可以说,工程是表达着信仰的工程,信仰更多地是对人的自为本性——类本性所决定的工程能力与价值取向的信仰。就二者的关系,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读和阐释。
1.作为满足信仰的工程
工程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不仅是人的类存在方式,而且反映、提升着人的类本性。当人类从洪荒走出时就开始自发的工程存在了,古人不仅知道按照自然的尺度而且懂得按人的尺度从事工程活动,尽管还停留在自在的工程阶段。而人的尺度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信仰。正是由于信仰万物有灵,先民的工程活动总是表现为顺应自然的以培育和养殖为主的农业工程,而且使这种工程活动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人们祈祷上天保佑风调雨顺,丰收后的祭天法祖以及各种与农耕有关的节日、民俗等,以至于形成了正如人们所说的小麦文明的欧洲文明,稻米文明的亚洲文明,玉米文明的拉丁美洲文明。据报道,玉米崇拜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墨西哥人来说,玉米绝不仅仅是食物,而是神物,是千百年历史中印第安人宗教崇拜的对象。”(18) 可见,即使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的工程也表达着人们的信仰。而有些工程几乎纯粹是出于满足信仰的目的,才被建造的,如埃及的金字塔,典雅静穆的希腊“帕提侬”神庙,中国的各类神殿,以及西方众多气势恢弘的教堂建筑等。从信仰的角度看工程,工程是信仰的表征,正如王振复所说,“与宣扬神性之崇高、静穆的古希腊神话、悲剧、荷马史诗相一致,古希腊的神庙建筑曾经在技术与工艺上,达到过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可谓鬼斧神工、似乎非人力所能为的建筑奇迹,体现了上帝与人的‘和解’。”(19) 如果说,“罗马式教堂的建筑构件以圆拱为主,整个建筑结构坚固厚实、四平八稳,强调整齐壮观和粗犷有力,于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中蕴涵着庄重肃穆的神圣感,显示出一种凝重威严的精神气质,表达着早期基督信仰的庄严性”,那么,被誉为中世纪基督教的最杰出的文化成就的哥特式建筑,尤其是它的天主教堂的建筑以艺术的形式,“不仅是那高耸入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镂的局部都在宣扬着基督宗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20) 可以说,西方的工程发展史,经历了古代自在的工程、近现代自为的工程、后现代自在自为的工程,分别标志着浓于超验信仰的顺从自然的农业文明、背离神的超验信仰(使自然祛魅)而崇尚理性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业文明和回归信仰的寻求人与自然和解的天人合一的后工业文明。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的“筑居”必须以“栖居”为指归,“筑居建造了为四重整体提供空间与位置的场所,筑居从天地人神凝聚成的元一那里接过来指令并在此指令下建造诸场所。筑居又从四重整体那里接过来所有用以监测与度量在各自情况下由已建成之场所所提供的诸空间的标准。建筑物保护四重整体,它们是以各自的方式来保护四重整体的物。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悦纳苍天,期待诸神,引导众生——这四重保护是栖居的原始的本质,是栖居存在、在场的方式”,而“筑居的本质是给定栖居……只有去栖居,我们才有所建造……无论如何,栖居是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众生正是依赖这一特征而存在”。(21) 实际上,据张法教授介绍,中国远古建筑的三种类型:(1)空地(仰韶文化姜寨);(2)坛台(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3)大屋子(仰韶文化大地湾),从空地立有象征天人沟通的中杆,坛台的“登之乃神,登之乃灵,登之为帝”,到把中杆放到大屋子之顶的寓意,无不传达着人们对“直接面对天的基本原则”的信仰,以及与自然沟通的愿望,反映着那种追求天地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与阴阳变易、有无相生和实虚共在的道的形上境界。
2.中国建筑工程中的风水观
中国的建筑工程是讲究风水的,从空地中心到坛台中心,再到屋宇(包括宗庙中心和宫殿中心)的建筑逻辑,都凝结着不同时期人们的风水观。过去有传统上备受尊重、视为智者的风水师,以及各种各样的风水理想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如以《葬书》为标志的风水理论形成阶段,到魏晋时的风水理想模型、宋代和明清间的风水理想模型,再到明清帝陵的风水模型);现在有热衷于研究风水文化的中外学者,以至于有人主张建立中国的风水学以及现代科学的风水学,由此可见风水对于中国建筑的重要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小到村落、民房建设,大到城镇、市政尤其是各类宫殿、楼台、庙宇的建设,大都离不开事先的风水观测。正如亢亮等所说,“中国的风水学在我国建筑、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这在我国大量的现存古城镇、古建筑、园林、民居及陵墓中得到印证。”(22) 据研究,无论是被作为多朝都城的北京,还是紫禁城的建筑,无不包含了严格的风水观测、考证和营造,尤其是紫禁城背靠景山面临金水典型地表达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水观——背山临水,实际上,为了符合这样一种风水观,景山和金水都是人工所为,这就更是说明了人们对好风水的看重与信仰。那么,何谓风水?根据《风水辩》的解释,“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又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23) 风水,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自然知识、人生哲理以及传统的美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实际上,风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圣的环境理论和方位理论。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人工自然环境与天然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其宗旨是勘查自然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选择和创造出适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使之达到阴阳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24) 应该说风水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地道的技术,它只能是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相适应的一种素朴的理论和信仰,追求天地人合一。只是这种信仰中包含了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一定经验积累的科学成分、一定的技艺方法,当然也包含一定所谓的迷信因素。然而这种对风水的信仰,即好的风水能够带来吉祥,能够建造好的建筑工程的观念,造就了中华大地独有的建筑文化风格:(1)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2)淡于宗教浓于伦理;(3)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4)达理而通情的技艺之美。(25) 当然这些不能仅仅归功于风水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对风水的好坏、善恶的信仰直接影响到古代中国建筑工程的布局和建设。崔世昌先生在《现代建筑与民族文化》一书中,不仅把“重山林风水”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之一,认为历代的职业风水先生,去除迷信成分,可称得上选址专家,他们相信:有山,易取其势,视野开阔,排水顺畅;有林,易取其物,仓柴丰盛,鸟鸣果香;有风,易得其动,空气清新,消暑灭病;有水,易得其利,鱼虾戏跃,鹅鸭成群。故此,若靠山面水,侧有良田沃土,阳光充沛,兼有舟楫之便,当然是公认的宜于人类生存的最佳选址。而且,崔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不仅重自然的山林风水,也重人工的山林风水,让人工的与自然的协调,院内的与院外的衔接,造成“天上人间”之境,使人产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心旷神怡之感。进而,他预言:“重山林风水的传统思想必将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得以发扬、发展,以创造优美的建筑环境,实现大自然的回归。”(26) 在我看来,这也是在现代工程中对融入作为技术的传统风水观的呼吁与价值判断——使工程亲近自然,寻求“无为”之“善为”的工程。其实,与中国有着同一种文化根源的日本,也是非常讲究建筑风水的。在盐野米松先生对传统手艺人的访谈中,一位宫殿木匠的口传秘诀之一是,“选四神相应的宝地”,就是东边要有清流,南边地势要低,比如有沼泽地或者浅谷最好。西边要是大道,北边要背着山才好。(27)
3.西方的上帝创世与工程
根据圣经,上帝凭借其智慧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本身。这样一个充满意义的活动按照先后时间顺序在六天内完成,可谓是宏大的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是宇宙最智慧的、第一个工程师。可是,上帝创世说又来自人的创造,这就预设了创造是人的本性,人是富有“自为本性”的存在,工程活动是人的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生存方式。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万象,那么,人类正在执行着上帝的指令——管理好自然及万物。因为人作为最高级的生物,被上帝赋予“管辖权”、“位高任重”(舒马赫语)。这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活动的“天命”:实施管理的职能。这里的管理就是一项工程活动,意味着不仅要认识自然,而且要倾听自然,照看、呵护自然,合理地开发、适度地利用自然,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拷问、剥夺、征服自然。如此说来,上帝创世的信仰不仅预设了人类的工程活动,而且暗示了人应该如何去从事工程活动。根据《创世纪》第11章,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们在往东迁移的时代,“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段故事告诉人们,我们人类的工程是有限的,不可以像上帝那样,说什么就可以建造什么,人尽管有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界限的,能做的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上帝永远是人的规约,预示出价值和意义构成人行动——工程活动等行为原则的先在性。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大规模工程活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人类忘却了自己的“天命”,狂妄自大,物欲横流,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无节制地奴役、宰制自然。用弗罗姆的话说:“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几代人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石之上。他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征服自然界、让物质财富涌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和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人通过自身的积极活动来统治自然界从而也开始了人类文明。但是,在工业时代到来以前,这种统治一直是有限的。人用机械能和核能取代了人力和兽力,又用计算机代替了人脑,工业上的进步使我们更为坚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成为能够创造第二个世界的人。为了新的创造,我们只需把自然界当作建筑材料的来源。”“但是,实际上,工业社会从未能兑现它的伟大允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无限制地去满足所有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乐,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幸福(Well-being);
——想独立地主宰我们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们认识到,大家都变成了官僚机器的齿轮;
——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业—国家机器操纵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不断发展的经济进步仅局限于一些富有的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28)
与此同时,人的精神世界遭到了空前的忽视,因而也使人自身越来越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人类沉沦了,坠入黑暗的深渊,苦痛、无名的悲哀、焦灼与不安向人不断袭来。(29) 作为人类良知的思想家们和有识之士,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的工程实践发出警报、拉响警笛。人们共同寻求走出困境、摆脱人类生存危机的方式和道路。海德格尔指出,要想拯救自身,现代人必须面对栖居的困境,躬身自省,迷途知返,重返本真,并身体力行。要努力克服情感匮乏,关怀生命的终极价值,重视人类的内在性,“超越那种垂涎于物的贪婪目光而进行的言语活动,超越欲光闪闪的眼睛活动而转向内心活动”,以期达到真正的生存境界。与万物同住同栖,与大自然亲密相处,成为本真的人,生活在大地之上,苍穹之下,从事隶属于栖居的筑居,建造需要建造的一切,养育生长着的万物使之枝叶繁茂,春华秋实。拯救大地,不再征服它,役使它,而是使它获得自由,使它进入自身的存在之中,让大地成为大地,从而达到诗意地栖居。(30)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所带来的人类工程实践的异化,并探索寻求消除异化、解放人类自身的新的社会工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我们可以说人类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三自”逻辑,即(1)“自然的逻辑”可称为“暴力的逻辑”;(2)“自私的逻辑”也是“资本的逻辑”;(3)“自立的逻辑”或“自由的逻辑”,人类从“自然的逻辑”到“自私的逻辑”再到“自由的逻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或规律。(31)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的逻辑”以及“自私的逻辑”或“资本的逻辑”是工程异化(原本属于人,为了人的工程,却反而奴役人、控制人,吞噬甚至危及人的可持续生存)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种族歧视、国家冲突、利益争夺、热战冷战,属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精神萎缩、信仰危机、道德沦落,属于人与自身本质的关系问题。这几方面的问题,几乎覆盖了人性的整个内容,它表明‘人’的观念问题再次凸现出来,而且是以从来没有过的尖锐形式和严重性质摆在人们面前。”(32) 而所有这一切都建基在人的工程实践基础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反思与人性相关的工程活动,而只有把对工程的认识论研究放置在生存论的基地之上,全面解读工程的丰富内涵与特质,正视人·工程·生存的互蕴共容性,才能将人类的工程活动置于形而上的观照、审视和批判之下,摆脱对工程福祉的盲目信仰,正视工程的“两重性”,树立“有限工程”意识与和谐发展的工程观,进而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使其真正成为属人和为着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不断完善类本性的工程。
注释:
①柯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271页。
②冯天策:《信仰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③⑨(31)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73~74、15页。
④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上),阎嘉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⑤⑥⑦(28)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8、49、47~48、3~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⑩王沛民等:《工程教育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11)朱高峰:《工程与工程师》,《学术报告厅——科学之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2)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3)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4)王洪波:《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简论》,《首次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会议论文》,2001年。
(15)安维复:《我建构故我在》,《工程研究》(第1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6)(21)(29)海德格尔:《诗·语言·思》,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65、162~164、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18)孙扶民:《没有玉米,就没有墨西哥》,《环球时报》2003年7月18日。
(19)(25)王振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0页。
(20)赵林:《基督宗教信仰与哥特式建筑》,《中国宗教》2004年第10期。
(22)(23)(24)亢亮等:《风水与建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26)崔世昌:《现代建筑与民族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27)盐野米松:《留住手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0)刘孝廷:《社会发展理论》(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