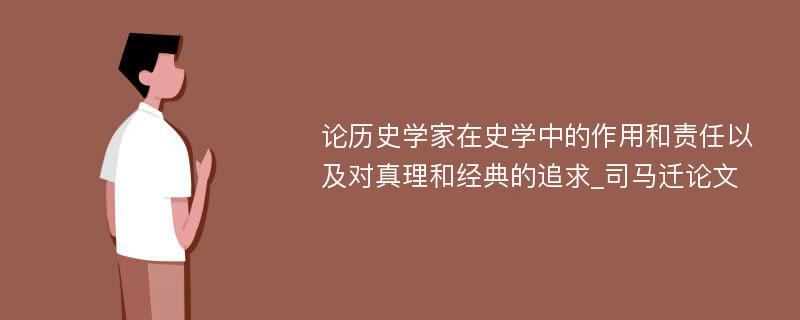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角色论文,责任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而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而与客观历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丰富宝藏的钥匙。
本文将按照这样的思考程序来阐述对于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这就是: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它们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一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及史家的社会责任
中国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产生有古老的渊源和长期发展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史家是史官。至晚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476年),中国古代史官的角色意识已经突出地显露出来。 有两个人们所熟知的事例可作为明证。第一个事例发生在公元前607 年:晋国史官董狐因为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一事而同执政大夫赵盾发生争论,并在争论中占了上风。〔1〕另一个事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齐国太史因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一事而被手握大权的大夫崔杼所杀,太史之弟因照样记载又被崔杼先后杀死二人,直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才照样记载了这件事。这时,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便执简以往,欲为书之,中途听说已经记载下来,便返回去了。〔2〕这里,董狐、 齐太史兄弟数人、南史氏等,都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这一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因此,他们不畏权势,即使献出生命以殉其职也在所不惜。这是当时史家之角色意识的极崇高的表现。当然,在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从史家个人的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明全部问题;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史家的这种角色意识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遵循的“礼”的要求。西周以来,天子于礼有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3〕此即“君举必书”之礼。〔4〕在王权不断衰微,诸侯、大夫势力相继崛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也在诸侯、大夫中间推行起来。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都是诸侯国的史官;国君被杀,按“礼”的要求是必须记载下来的。不仅如此,就是作为大夫的赵盾,也有自己的史臣。史载,周舍对赵盾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5〕所谓“谔谔之臣”,是同“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直接联系的。由此可见,“君举必书”之礼,一方面反映了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及时记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对各级贵族的约束。是否可以认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地表现了史家的角色意识。春秋末年,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因为他“书法不隐”;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因为他“为法受恶”。〔6〕此处所谓“法”, 是指法度,即当时“礼”制的规范。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从史家的主体方面和史家所处的环境方面,说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史家的角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增强,而升华。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原有的角色意识突破君臣的、伦理的藩篱而面向社会。这一变化的滥觞,当始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论孔子作《春秋》一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尽管《春秋》还是尊周礼,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评论历史的做法,已突破了过去史官们才具有的那种职守的规范;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识已不同于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们的角色意识了。
然而,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的主要标志的真正体现者,还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司马迁很尊崇孔子、推重《春秋》,然而他著《史记》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了。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是“述往事,思来者”。〔8〕由此可以看出, 司马迁的博大胸怀是要拥抱以往的全部历史,探讨古往今来的成败兴坏之理,使后人有所思考和启迪。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肠一日而几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面向社会到在一定意义上的面向民众。其实,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中,史家或多或少都会认识到民众的存在及其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司马光是极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9〕他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知识的抉择,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同“国家盛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不分可割开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家能够这样来看待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总是同史家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着。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的勇气,一个重要的趋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关系中,至少在形式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惜以死殉职,正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如上所述,孔子修《春秋》,也是受到社会的趋动而为。至于司马迁父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本人都有极明白的阐述。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极其深刻地表明了他们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密切联系,表明了他们对于被“天下称诵”的周公和“学者至今则之”的孔子,是何等心向往之。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思来者”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了他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感。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与统一:他希望《资治通鉴》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倘果真如此,他自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10〕这就是说,史家的目的,是希望统治集团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政治统治以达到“盛德”和“至治”的地步,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正是为着这个目的,他认为他的精力“尽于此书”是值得的。
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绝大多数史家从不把史职仅仅视为个人的功名和权力,而是把这一职守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个别的例外乃至于少数的异常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反映中国史学的主流。
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要影响着、铸造着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发展趋向。
二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上文所论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这就是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与经世目的及其相互间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具体说来,史家的角色意识同史学的求真要求相关联,史家的社会责任同史学的经世目的相贯通。其间固有种种深层的联系,本文将在下一个问题中阐述。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中国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享有盛誉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公元661年—721年)认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1〕刘知几把史学工作大致上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书事记言”,后一个阶段是“勒成删定”,前后“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前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闻实录”,一要“博”,二要“实”;后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识通才”,一是“识”,二是“才”。按照刘知几的思想体系,结合他关于才、学、识的理论来看,“博闻实录”可以看作是“史学”,“俊识通才”包含了“史识”和“史才”。那末,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础呢?答曰:“博闻实录”是基础。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自无从“勒成删定”,而“俊识通才”也就成了空话。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没有“俊识通才”去“勒成删定”,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刘知几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细心的研究者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篇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饮誉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或“叙述当时”,“务在审实”等等,都需要“仗气”与“犯讳”,显示了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刘知几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几、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实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实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年—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人的劝说之下, 翻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公元670—749年)与刘知几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几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12〕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的然而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这如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这种董孤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应当指出,刘知几说的“俊识通才”,一方面当以“博闻实录”的“当时之简”为基础,一方面在“勒成删定”中同样要求贯穿求真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识”与“才”。如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司马迁《史记》所记商代以下的历史是可靠的,这一事实使中外学人皆为之惊叹不已。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又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勒成删定”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对于史家的求真精神实是严峻的考验。为使今人信服、后人不疑,司马光“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14〕使之成为阅读《资治通鉴》的必备参考书。由《资治通鉴》而派生出来《资治通鉴考异》,这是极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此外,从魏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史注的繁荣,直到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兴盛,也都闪烁着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之光。
当然,中国史学上也的确存在不少曲笔。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是关于曲笔现象的很有分量的专文。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唐代诸帝实录,其中就出现过几次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15〕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以后的史学中,也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毕竟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话的意思是: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象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从“书法不隐”,到史学家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证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这样的准则和传统,求实精神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的位置。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将发展为史学的经世思想。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史学思想也是如此。从具体的原因来看,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识所趋动,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了尽其所学为社会所用的史学经世思想。这在许多史家身上都有突出的反映,以至于使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问题在于,史学家们采取何种方法以史学经世呢?
——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6〕当属于这种方式。后来,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7〕刘知几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18〕也是这个意思。
——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春秋》之后,《左传》、《国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记载,诸子论史也多以此为宗旨。在陆贾的说服之下,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9〕这是历史上政论家、史论家和政治家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历代正史、《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各种体例的史书,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
——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这种方式, 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 唐代大史学家杜佑(公元735 —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 徵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同时代的人评价《通典》的旨趣和价值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20〕“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21〕清乾隆帝评论《通典》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22〕本文一再列举人们对《通典》的评论,意在藉此说明中国典制体史书在史学之经世目的方面的作用。《通典》,不过是它们当中的杰作和代表罢了。
——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23〕使史学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史学经世的方式和途径,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不一一列举。而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是作了回答的。《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说:“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此篇广列事实,证明一些史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的经世的基础。换言之,如无史学的求真,便无以谈论史学的经世;求真与经世是密切联系的,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许多地方都是在阐述这个道理。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史书,应当做到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应当统一起来、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24〕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这就是说,史学的经世与史学的求真不是抵触的而是协调的、一致的。在中国史学上,也确有为着“经世”的目的(这常常表现为以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为目的),而不顾及到甚至有意或无意损害了史学的求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它有悖于本来意义上的史学经世思想。
在讨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史家还有一点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即史学的经世固然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但史学的经世并不等于照搬历史或简单地模仿历史。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记,岂可绲乎?”〔25〕这是中国史家较早地然而却是明确地指出了以历史为借鉴和混同古今的区别。可见,中国史学的经世主张,并不象常被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告诫人们去搬用历史、模仿前人而已。关于这一点,清人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型、而终古不易也哉!”〔26〕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不穷”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
三 角色与责任和求真与经世的关系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那末,当我们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关于信史原则。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27〕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作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28〕这都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的态度。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9〕这个认识不必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0〕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则传疑,盖则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的“爱奇”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的简要论说。对“信史”作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月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31〕吴缜说的“信史”,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无疑”、“莫敢轻议”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
应当指出,这种信史原则的萌生、形成和确认,同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史学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联系:它是角色意识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求真精神反映出来。换言之,没有史家的角色意识,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对于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史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信史原则必将成为空话。可以认为,从“书法不隐”到“实事求是”,贯穿其间的便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信史原则和对于信史的不断追求。
关于功能信念。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有一贯穿其间的共同认识,即确信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国语·楚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庄王请教大夫申叔时,应当对太子进行怎样的教育,申叔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32〕据三国时人韦昭注: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是“五帝之书”。可见,这些书大多是历史记载或关于历史方面的内容。从申叔时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唐代的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关于史学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唐太宗在讲到史学的功用时,极为感概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33〕史家刘知几分析了竹帛与史官的作用后总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34〕清人浦起龙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反复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总括其功用”。可见,他是深得刘知几论史的要旨。
唐代以下,论史学功能的学人更多了,其中如胡三省论史之载道,王夫之论史学的治身、治世,顾炎武论史学与培育人才,龚自珍论史家的“善入”、“善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并倡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等。其间,都贯穿着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确认和信念。
准此,则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
注释:
〔1〕 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2〕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 《礼记·玉藻》。
〔4〕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5〕 《韩诗外传》卷7。
〔6〕 《左传》宣公二年。
〔7〕〔16〕《孟子·滕文公下》。
〔8〕 《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9〕〔10〕〔14〕 《进〈资治通鉴〉表》。
〔11〕〔23〕〔34〕 《史通·史官建置》。
〔12〕 见《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
〔13〕 《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15〕 参见笔者所撰《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韩愈与〈顺宗实录〉》等文,均收在《唐代史学论稿》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 《史记·太史公自序》。
〔18〕 《史通·直笔》。
〔19〕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 李翰《通典》序。
〔21〕 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见《唐文粹》卷68。
〔22〕 乾隆丁卯《重刻〈通典〉序》。
〔24〕〔31〕参见《新唐书纠谬序》。
〔25〕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6〕 《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
〔27〕 《论语·卫灵公》。
〔28〕 参见《论语·八佾》。
〔29〕 《谷梁传》桓公五年。
〔30〕 《史记·三代世表》序。
〔32〕 《国语·楚语上》。
〔33〕 《修晋书诏》,见《唐大诏令集》卷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