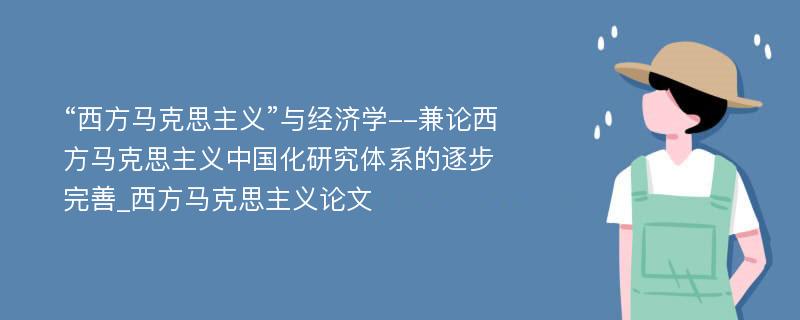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体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6;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5-0067-07
西方学者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对其研究范围和理论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2005年,我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升为二级学科①,开始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课程。现实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需要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新的思索。
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长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脱离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哲学思潮”(“哲学说”),后来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经济学(“转向说”)。本文第一、二部分分别概述人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之间关系上的“哲学说”和“转向说”。本文第三部分则结合我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谈一谈我们自己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并使用。在20世纪30年代,柯尔施(Karl Korsch)在其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就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分析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为例表明综合主客体的可能性,突出了卢卡奇对早期马克思的回归。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1976年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安德森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并列出一个简表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杰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菲弗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哲学、文化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放弃对经济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有创见地论述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方面、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柯尔施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转移到大学这个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相关的学者“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1](P62、66)
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说:“佩里·安德森是他那代人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2](Pix)因此,安德森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学者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源自于中欧和西欧的一种哲学的和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转向文化、哲学和艺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思想,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较多地注意分析‘主观的’结构——商品拜物教、异化或意识形态,而比较少地分析那些‘客观的’结构——帝国主义或积累。”[3](P581、581-582)美国学者罗伯特·A·戈尔曼(Robert A.Gorman)在《新马克思主义》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在重要理论问题上模糊不清,具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了新马克思主义”。该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所有图景,考察了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的著作的理论联系。但是,“排除了大批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4](Pix、x)后来,他在《新马克思主义人物传记辞典》中将新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非正统的”、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都采用一种哲学,同时,“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成分复杂的运动,它的不同成分之间的裂缝也像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不同学派之间的裂缝一样宽”。[5](Pviii)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但是,他们在其政治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缺陷就在于脱离经济学,忽视工人阶级的实践。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而这一“哲学转折”使这些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结果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1](P41、45、59、65)因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观点”。[6](P23)而雅各比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退缩,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的前进。在这一点上,我与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观点不同”。“我并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倒退的不幸的弯路”。[7](P6)后来,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种哲学形式,但这种哲学化衬托出政治含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往往打上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后果所带来的烙印,这指的是20世纪西欧革命的毫无例外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这些失败所作的哲学思考”。[3](P581)
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安德森的看法②。我国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一种哲学思潮。有的学者认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渊源,有政治和哲学两个方面”。[8](P6)“从研究领域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注意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了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9](P92)还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其次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不太涉足经济学领域”。[10](P253)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正如菲利浦·安东尼·奥哈拉(Phillip Anthony O'Hara)所说:“到60年代,美国的变革力量特别强大,特别关于战后繁荣、越战、公民权利运动、学生反抗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运动,为致力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织的出现提供强大的支撑。”[11]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转向经济学。
1983年,安德森出版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探讨过去几年历史唯物主义的运动”,并“检讨一下我早先的那些推测是否有应验”。他说:“实际结果并非完全吻合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结论。”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的下限大体上可以划到70年代中期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逃避现实的传统,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社会问题,“这个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连同其认识论方面或美学方面之阴沉的或奥秘的色彩——实际上已近终结;取而代之,另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出现,以其神奇的速度和充分的自信心,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那些它的前辈所忽视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制度问题”。[12](P3、1、19、18)
安德森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的重心是德语和拉丁语民族的欧洲,现在转变为英语地区。与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向经济学、社会学等转变。“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博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同时,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力量向经济学、社会学等转移,并不意味着哲学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之如此扩展,并未引起哲学或文化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硕果累累的独特园地——之相应的收缩”。到了7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问题研究,转向经济学,安德森将其看作是“7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复兴”,“历史唯物主义就广泛渗透到美国校园”。[12](P24、22、30、28)
1979年,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在该书的第五篇“欧洲和美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学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和主要思想。他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到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了经济学,“这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由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问题和发展问题的严重关切”。[13](P355)
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哲学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转变。早在1995年,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超越国内与国外的对立,超越哲学与经济学的对立。[14]有的学者根据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区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主题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且在研究领域上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前者主要限于哲学领域,后者则突破了哲学的局限,扩展到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哲学,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15]
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说”肯定了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转向说”没有充分肯定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历史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潜流已经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它的起落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与劳动和其他民众的斗争相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时期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强调社会斗争成为社会变化的源泉的经济来说根本不是有利的环境。马克思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重新出现和后来发展是直接回应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一’的公民权利、反战和女性劳动。随着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劳动—资本关系的破裂,它发展的步伐已经加快”。[16](P53)熊彼特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并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状况。他说:“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或多或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发掘出一些新东西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熊彼特看来,到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鲍尔、库诺、格罗斯曼、希法亭、卢森堡和施特尔伯格。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劳动价值论以及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变的所谓“转型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崩溃问题,从而是积累理论、危机理论以及日益贫困化理论。”[17](P197、199)奥哈拉也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以及60年代,斯威齐(以及后来的巴兰)以及其他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出版《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也起作用),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做了大量工作”。[11]
我国学术界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学术界缺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始资料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行得比较“艰难”③。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概括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阶段,分析了我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阐述了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点④。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或者说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缺憾。
随着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二级学科,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涵盖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就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方面完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需要做到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反思;二是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反思西方学者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和意识形态偏见。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甚至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西欧的共产党已经斯大林化,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政策,“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打上了与众不同的烙印”。[1](P59)戈尔曼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更接近于传统的西方价值观念,而不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5](Pviii)安德鲁·莱文认为,“从政治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同正统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共产党相对抗的,尽管在很多时候这种对抗不是公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参照物或对立面,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也明显走向终结”。[18](P45)
但是,由于苏联在20世纪上半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对苏联经济建设持肯定的态度,许多人也因此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被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我们从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英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布劳格认为,多布是一位在美国一流大学“拥有教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其整个成熟时期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理论问题上是坚持莫斯科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19](P68)霍华德和金在《保罗·斯威齐的经济学贡献》一文中说:“到1960年,斯威齐可能最好被描述为独立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不仅多布和斯威齐的思想长期没有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甚至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重要经济学家格罗斯曼由于晚年回到社会主义国家波兰而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不为人所认识”。[20]其实,有的西方学者也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J.G.默奎尔(J.G.Merquior)认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非苏联的、非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革命理论家里吉斯·德勃内(Regis Debray)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做出重大贡献,“但是,没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到他们头上”。“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个标签是用词不当的”。[21](P2)显然,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必须抛弃西方学者的这种意识形态偏见。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最初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欧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并没有全面反映美国等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前言”中清楚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打算将这本小册子“写成介绍一些作家评论最近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本论文集”,并且认为英国文化明显缺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传统,“因此,本书中论述欧洲‘大陆’传统的内容,部分地是以前对英国‘岛国’类型所作评述的继续”。[1](P3、4)雅各比更为明确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交换使用”。[7](P8)所以,默奎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地理上的含义就具有误导性了”。[21](P1)
美国等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明显与欧洲不同,正如赫伯特·金蒂斯所说:“我们注意到欧洲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许多观念仅仅是与其更早时代相联系的占支配地位的苏联式理解的结果,并不必然适用于一般的发达资本主义,更不适用于美国”。[16](P55)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英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学。英国虽然尚无广泛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已有了重要的贡献。他说:“在英国,知识分子作出最大努力的方面也许在经济学”。“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独创性的贡献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13](P345、342)我们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不能仅仅包括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括美国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
我们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首先要认识到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趋势。从现实来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在不断累积,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从方法论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能够与工人阶级运动有效结合起来,必然越来越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说:“如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还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一般可能会回到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去,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是它对主流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不充分假定的批判的基础”。[22](P6)
其次,我们要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成立较晚,人们常常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巴兰最早提出的“经济剩余”是美国20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人们在很长时间里仅仅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其进行研究和评析,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拉塞尔·雅各比认为,“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具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印记”。巴兰和斯威齐的“经济剩余”概念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一个小的修正。它对这个经济概念增加了批判的、道德的层面;它使他们讨论日常生活中的特征——性别、消费方式等——规避了平淡的经济方法”。“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本身来源于巴兰早期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857),而它又源于海克默尔的‘客观理性’。”[7](P109、110)霍华德和金在《保罗·斯威齐的经济学贡献》一文中也认为,“巴兰的经济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他那个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也促使他比斯威齐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我们理解巴兰提出“经济剩余”概念和“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必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联系起来。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2005年12月发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提出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科学的通知》,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增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②我国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参见陈学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载《教学与研究》,2008,(9)。
③李惠斌在回顾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这样说:“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艰难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我使用‘艰难’这个词,是因为这些西方马克思理论一开始就被一些学者界定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当做‘自由化思潮’或异端邪说加以批判”。参见李惠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年刊),2004。
④关于一些学者对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的思考,参见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十年——兼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路的现代转换》,载《理论月刊》,2002,(3);陈学明:《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求是学刊》,2001,(4)。
标签: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安德森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