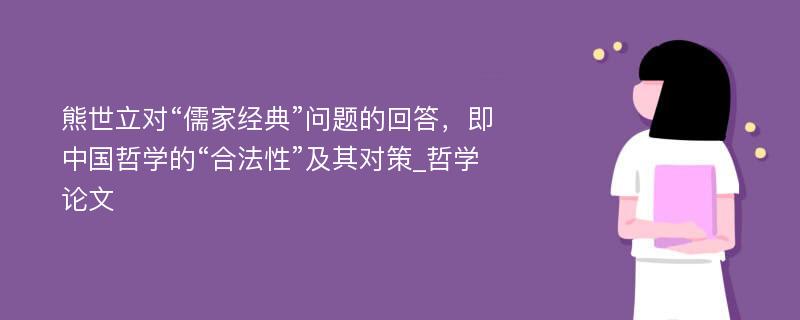
熊十力答“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质疑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合法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6-0034-05
关于对“六经”的最早论述,可以追溯到《庄子·天下篇》,后人多沿用于此。在《庄子·天下篇》中对“六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叙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489《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传统说的“六经”。在这里,“六经”开始成为研究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到南宋时,形成了儒家十三部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历代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统称为经学。
所谓“经学”,就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儒家经典之学。在两汉时期,就有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所谓今文经学是指汉代学者根据以当时通用的文字即隶书记录下来的儒学经典而阐发的学问,在西汉时期广为流行;而古文经学是指汉代学者根据从民间或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儒学经典而产生的学问,它盛行于东汉时期。其实,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今文经学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来注经,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是“义理之学”,强调“经世致用”。而古文经学则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近于史学,侧重于“考据之学”,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接受,这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完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第一次转向,即“经学的政治化”。
宋明理学和“乾嘉学派”,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窠臼,只是释经的理路不同。宋明理学着重从理气心性等方面解经,也就是说从“义理”方面解经,也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而“乾嘉学派”与宋明理学是两种不同的治经方式。“乾嘉学派”重罗列证据而少理论发挥,文风朴实简洁,所以有“考据学”、“朴学”之称,也有“汉学”之称,也就是所谓的“我注六经”派。
在历史上看,自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以后,对“六经”的认识走向片面。我们知道,“六经皆史”的思想可以上溯于王阳明,不过王阳明对“经”“史”进行了正确地解读,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2]28-29。到了章学诚,他把“道”、“事”、“经”、“史”割裂开来,得出了“六经皆史”[3]5的论断,把“经”“道”这一面完全抛弃,采取极端主义的立场。从现在来看,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对待“六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经史结合”即史论结合,史就是历史的方法,“论”就是哲学的方法。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采用“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结合的方法。“阐旧邦以辅新命”,“旧邦”、“新命”之语,出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阐旧邦”就得“照着讲”,注重原始文本的原义,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接着讲”就是辅“新命”,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学史必须“照着讲”,而经学必须“接着讲”,经学与经学史要结合,史和论要结合,坚持“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说,“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结合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释经之方法。
熊先生对“六经”的态度,就是采取“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也就是在“照着讲”“六经”的基础上,继续采取“接着讲”“六经”的方法,即采取“经学泛哲学化”的理路。
关于“经学”是不是哲学,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界长期以来争讼不休的问题之一。
熊先生给经学的定位是:“是学术,不可说为宗教;是哲学,而迥超西学(西洋哲学);非宗教,而可代替宗教。”[4]731在这里,熊十力不但直接地把经学和哲学画上了等号,而且还认为中国哲学迥超西学即西洋哲学。将经学等同于哲学,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困难,而熊先生还认为中国哲学优胜于西方哲学,这就更增加了困难的难度。因此,熊十力先生为了消弭其中的紧张,就必须对哲学的内涵加以重新界定。他说:“有谓经学非宗教,亦非哲学者,此大谬。经学是德慧的学问,何谓非哲学乎?须知,哲学固不以理智或知识为止境,必至德慧具足,而后为哲学极诣耳。”[4]733熊先生认为“经学是德慧的学问”,不是把“理智或知识”当作哲学所追求的止境的学问。西方哲学在“理智或知识”方面见长,是“爱智慧”的学问。熊十力对哲学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必至德慧具足”。从此定义出发,熊先生经过自己转换概念,不但心安理得地肯定了经学就是哲学,而且还认为经学为“哲学之极诣”。现在看来,把哲学看作是关注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意义,从而提升个体的生存境界和精神境界以及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德慧之学,让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由此看来,熊先生的这一转换,使哲学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熊十力不但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而且还进一步指出经学与一般哲学的区别。他说:“圣学归本尽性至命,此是圣学与世间哲学根本区别处。”[5]345这样,熊十力给经学的界定是,经学在本质上是性理之学、性命之学、德慧之学,西方哲学则是“爱智”之学,而佛学则是宗教之学。这样,熊十力所“圈定”的经学,在传统上是比较接近于宋学的主流即“义理之学”的。因此,熊先生所理解的“哲学”,并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熊十力还指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成功之处,他说:“中国人在哲学上是真能证见实相。所以,他总在人伦日用间致力,即由实践以得到真理的实现。如此,则理性,知能,真理,实相,生命,直是同一事物而异其名。中人在这方面有特别成功。”[6]308-309熊十力认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还优于西洋哲学,其优越处是通过道德践履,在人伦日用间致力,“真能证见实相”即真能见“体”,而西洋哲学却不能证见“实相”即“体”,只在“用”的范围内兜圈子。可以说,熊十力经过如此这般奇妙的“合拢”之后,经学便同哲学走到了一起,经学也就变成了哲学,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被熊十力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关于熊十力先生提出的“经学就是哲学”的论断,在当时就遭到同时代的梁漱溟先生和马一浮先生的反对。梁漱溟先生不赞同把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等同于今人所谓的“哲学”,认为这样便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儒学的特征,没有指出东方古人之学在学术上应有的位置,也没有指出近代以来西洋学术风气之浅隘阙失。梁漱溟说:
至如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可等同于今人之所谓“哲学”,在熊先生何尝不晓得,却竟随俗漫然亦以哲学称之。这便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儒家特征,没有尽到原儒的任务。他不从根本上把学术内涵分类清理一番,彻底纠正近代以来西洋学术风气之浅隘阙失,确当地指出东方古人之学在学术上应有的位置,而只不过有时强调说“哲学应该如何如何”。[7]141
马一浮先生也不赞同熊先生把经学当作哲学的观点。马一浮在看了熊十力的《十力语要》之后,肯定熊先生的观点“大体甚好”,认为熊十力以孟子的“形色即天性”为旨归,实乃能见其大。而对其“多用时人术语”则不认同。马一浮先生不赞成熊十力借用西洋的本体论、宇宙论等名词概念,来表达东方人特有的思想,这不但把经学哲学化了,而且还用哲学的眼光来打量东方古学,这对马一浮来说,是绝对不赞成的。经学有经学的范畴,西学有西学的概念,如果用经学的范畴来“格义”西方哲学的范畴,或者用西洋哲学的范畴来论述中国传统经学的范畴,恐怕有意义“错位”不搭界的嫌疑,也有“驴唇不对马嘴”的诟病,难免择焉未精。他说:
熊先生新出《语要》,大体甚好。其非释氏之趣寂,而以孟子形色天性为归,实为能见其大。其判哲学家领域当以本体论为主,亦可为近时言哲学者针剳一上。但以方便施设,故多用时人术语,不免择焉未精。自余立言稍易处固有之,然大旨要人向内体究,意余于言。[8]819-820
可见,熊十力把经学当做哲学,在当时就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在现在也有许多人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到底经学是不是哲学。这就难怪熊先生在当时就曾经非常无奈地对梁漱溟说过:“我喜用西洋旧学宇宙论、本体论等论调,来谈东方古人身心性命切实受用之学,你自声明不赞成。这不止你不赞成,欧阳师、一浮向来也不赞成。我所以独喜用者,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深心。……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功夫。”[9]758-759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熊先生内心的孤独、无奈和寂寞,难以寻觅到真正的“知音”,看来真是如他所说的“举头望天外,无我这般人”[10]267。
熊十力先生在这里已经敏感地牵涉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即“经学到底是不是哲学”的问题。谈到这里,人们难免就会想起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句刺痛中国人神经的话,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可以说这一句话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感情,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天朝大国”竟然没有哲学!黑格尔曾鄙薄《论语》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易经》“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11]178。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12]178。笔者认为,这些论断都是西方人所抱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偏见或对“本位文化”优越的傲慢,可以说是站在西方本位文化立场上的一孔之见,是不可取的。但虽不可取,它却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我们对“什么是哲学”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
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化观上,提出了“别共殊”的文化观形上学内核思想。他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其“共相”和“殊相”两方面,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即“殊相”的一面,但也有其“共相”的一面。在这里,冯先生用“别共殊”来给中国哲学留地盘。牟宗三先生遵循着冯友兰先生的逻辑理路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讲的比较到位。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当然哲学也不例外,他首次讲到了“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所蕴含的理论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他说哲学“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13]2-3。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给“中国哲学”以地位和地盘,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的角度上讲它仍可以称为“哲学”,因为哲学不止一种。在这里,不论冯友兰先生还是牟宗三先生都毫无疑问地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冯友兰先生还把自己的书叫作《中国哲学简史》,这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关于哲学形态多种多样,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这一切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在对科学的分类中看出,他把科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的“纯粹哲学”和“科学”之外,还有一种“一切科学和技术都以善为目的”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些属于“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的“实践智慧”[14]2-4。从这种分类来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颇与“中国哲学”相近。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也曾说过,哲学乃“求达至善之术”,人类理性分为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其实理性只有一个,就知识论领域来看,是思辨理性,而就人生领域来讲,是实践理性,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比思辨理性更占有“优先地位”[15]102-115。这种“实践智慧”后来也受到现代西方诠释学家伽达默尔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种思想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相一致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哲学的伦理学的特质。循此思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E.莱维纳斯打破了西方哲学“存在论—知识论”传统窠臼,提出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断[16]92,可谓石破天惊,一语中的,打消了中国经学是不是哲学的疑问。瑞士学者皮亚杰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中指出,哲学学科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但是,“唯一肯定的命题……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17]8。从这些思想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哲学在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中,虽然还处于劣势,其优势也渐渐地朗显出来。
熊先生以“经学就是哲学”的论断,回答了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质疑。其实,熊先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是将“经学”泛哲学化。当然走“经学泛哲学化”的理路,并不是熊先生的首创,其实早在孔子删订“六经”时,就已经开始了“经学泛哲学化”的历程。孔子是以塑造人的道德品质为主线,开始建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孔子认为,《诗经》具有非常强的性情陶冶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8]185孔子也非常重视《尚书》。有人问他:“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8]20-21把孝悌的道理施于政事,在孔子言里,这就是从政了。“礼”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因此孔子常讲:“不学礼,无以立。”[18]178《乐》指《乐经》,具有“导和”即性情教育功能。关于《易经》,更是孔子晚年所喜爱者,曾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19]1424之说。孔子常通过阐述《易》来进行道德教化:“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18]141言外之意,对于没有恒心的人来说,不用占卜就可知他们必遭羞辱的结果。孔子在编写《春秋》的过程中,寓自己之理想于褒贬之中,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0]155。可见,孔子在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高级“六艺”时,所强调和凸显者乃道德伦理。也就是说,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其核心。
熊先生也继承了孔子这一思路,开始了“经学泛哲学化”的过程。关于熊先生“经学就是哲学”的命题,如果从存在层面上来看,“经学是哲学”是错的。不管怎么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21]5,其实是在描写男女之间的恋情的,给以冠上“一言以蔽之,思无邪”[18]11的帽子,总觉得底气不足。《论语》还记载孔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谓《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18]185直到今天,关于“人而不谓《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之义,也颇难理解。我们必须清楚,《诗经》就是文学,《春秋》就是历史,《乐经》就是音乐,《尚书》就是政治。熊先生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以“义理之科”为主脑,以六经为旨归,开始了将“经学泛哲学化”的历程。他说:
是故言中学,则四科摄尽(按:四科即义理之科、经济之科、考据之科和文学之科)。南皮所云中学,若据宗本以言,即经学耳。对西学言,则泛称中学,亦无不宜。中学在昔,虽不妨析以四科,然义理之科,特为主脑。义理一科,虽亦含摄诸子余家,要以六经为归。天人之蕴,神化之妙。与夫人生日用之当然,六经之所发明,寓极玄于极近,穷幽微于甚显,体至精于至粗,融形上形下而一贯,至矣尽矣,高矣,美矣,无得而称矣。”[4]561-562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熊先生是深思熟虑地把经学肢解化,从衍生的角度,从自己的存在感受出发,以己解经,发掘“六经”中的“微言大义”,走的是一条将经学泛哲学化、泛道德化或者说泛政治化的理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学即哲学”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不必给以过多的苛求。
熊先生在《读经示要》中,总结了“六经”的哲学主旨即“内圣外王”之道。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从九个方面总结了儒家“六经”的“内圣外王”之旨:(一)“仁以为体”;(二)“格物为用”;(三)“成恕均平为经”;(四)“随时更化为权”;(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齐刑,归于礼让”;(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极于万物各得其所”;(九)“终乎以群龙无首”[4]581-618。“以仁为体”即“内圣”,以“格物致知”为大本之用。也就是说以“内圣”为体,以“外王”为用,或者说以“外王”为体,以“内圣”为用,即“内圣”即“外王”。一句话,“体用不二”。“内圣学”即“体”就是人生哲学,“外王学”即“用”就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科技哲学。熊十力希望人们要精心培育、呵护这一“以仁为体”的胚胎,使它生机勃发,吐芽抽枝,由此,社会才会找到其枝条繁茂的生长点,可以成就天下之大治。这样,治理国家的途径归根结底便靠君子的道德修养了,通过“道德”的启示化民成俗,通过“道德”的践履平定天下。质言之,君子的道德修养不仅是治国的“南面之术”,而且亦是良好社会秩序的生发处。可见,通过熊先生对“六经”主旨的阐释,可以看出,他把“六经泛哲学化”了,更多的是把经学当作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
不管怎样,熊先生提出的“经学就是哲学”的论断,解决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既解答了人们对中国经学的疑问,又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即走“经学泛哲学化”的道路。此论断和对策颇有见地,这是熊先生超迈于同时代的人如梁漱溟、马一浮等大师的过人之处,值得充分肯定。从这个角度,说明熊十力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有先见之明。一方面,奠定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地位,或中国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显示了熊先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笔者也赞同熊先生的“经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虽然有把“经学”泛哲学化的嫌疑,但我们断不可否认“六经”,尤其是《大易》中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