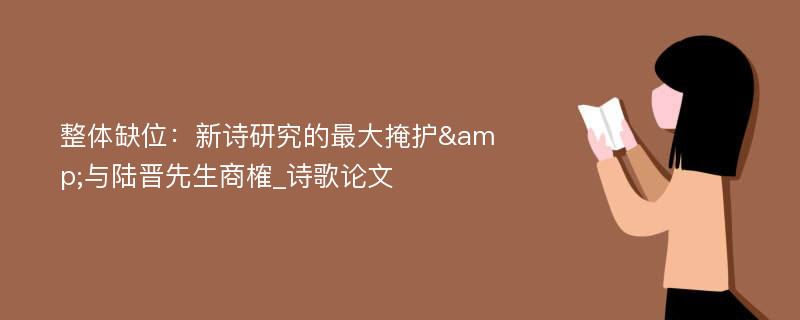
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与吕进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缺失论文,吕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50年报告“清单”代表什么
吕进先生在《文学评论》2002年5期发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对50年新诗研究做了一次看似详备的“总结”。他把半个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政治论时期、观念更新时期和文体建设时期,以及两个成果相对丰硕的领域:诗人个案研究和新诗文体研究。
时段划分和成果推举及其命名,有其个人依据和充分的个人自由度,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五部分陈述中,吕先生恰恰缺失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对20世纪后20年——新诗研究中最活跃部分的整体遗失。
第一时段政治论时期,只用了800来字,可见吕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前28年:成果寥寥,没什么谈头;新诗研究最重要的景观与成果,自然在后20年了。吕先生介绍了传统派、崛起派、上园派三个批评群落,提供30多人名单,以及个案研究13部论著、文体研究12部论著。在这皇皇“名单”里,哪怕粗心的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个案研究专著之内容范围,90%以上便在1949年划上句号,而文体研究论著,几乎也不涉及20世纪最后20年。这样倾斜的清单,是否真实代表50年来新诗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实在令人生疑。况且这份报告,早先作为“韩国汉城中文中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在开幕式上隆重推出。一大群汉学家们以此为蓝本,深信不疑,殊不知,它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误读了中国的新诗研究。
50年新诗研究:对另一支队伍的“冻结”
吕先生的确用心良苦,精心做了准备,但只要是业内人士,不难发现,这份“年终”报告的最大“特色”,是省却了新诗研究中的另外一大部分人,我主要指的是——另一支从事后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中青年队伍。
这批人年龄在40到55岁之间,早在80年代初,就活跃在新诗—现代诗研究前沿,且一直往纵深处挺进。20年来,他们总共发表几百篇论文,出版几十部论著,在众多盲区、险区做着艰难的勘测作业,为后来所谓的新诗史、当代史、先锋史、流变史做了大量前期的“清扫梳理”工作。
尽管他们难免表现出某些激进、偏颇、片面,但与先锋小说研究者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一翼。奇怪的是,先锋小说的研究者(全国百把人吧)从北京中心的陈晓明们到边缘的谢有顺们,都得到认可。惟独难度并不低于先锋小说和其他文类研究的先锋诗研究者,在这份“权威”报告中,出现了“整体缺席”?!
打个比方,如果说,对新诗的研究(或曰百年汉诗研究),犹如对一个人生长过程的研究,现在的情况是,在“他”的哺乳期、婴儿期,集结的力量有些过剩(有关郭沫若的论文有几千了)。研究视角完全可以细致到诸如婴儿期吃的是雀巢奶粉,还是克宁奶粉,维生素A用多了,还是胡萝卜素少了。在“他”的童年期,也完全可以细致到:穿布鞋上学是出于什么心理,嗜爱的辣椒对嗓子有什么影响(有关闻一多的专著有几十部了)。这就是说,在“他”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早已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一部部重复多于拓展的幼儿史、童年史、少年史(各种各样的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论述又有多少部了),可是“他”的青年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进行时段”,大量先锋形态、针对性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正视。应该知道,研究“他”早期的奶粉、维生素、肌肉骨骼、体重身高、营养配方,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为“他”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提供有效参照,促成一个人的成型。拒斥现在进行时段研究,无力与现在进行时段对话,哪怕再“正确”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而真正困扰我们且又十分重要的,正是当下这种生成性研究,它涉及比幼儿期来得多的纠缠与迷乱,比如“他”的初恋,“他”的自我,“他”的开放性气质,“他”的青春期躁动,“他”的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直呈现谜样的难辨。20年来,此类难度不小的“辨析”工作,一直由这一支生力军进行着。
笔者偏居东南一隅,平时孤陋寡闻,仅就手头阅读到的这批人的部分论著,不假思索便可开列出与吕进先生完全不同的清单。
唐晓渡:《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40万字,集作者20年诗论精粹,侧重诗学精神思想的深度挖掘)。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90万字,大陆最早的细读式文本批评);《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致力于生命与语言的互动探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国内最早的语义学批评之一);《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对90年代诗歌现场发言)。沈奇:《拒绝与再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进行时体验与当下文化结合,有独特切入点);《台湾诗人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引入两岸比较与整合理念的新一轮台湾诗研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0年代10年论集,新诗潮最前卫的理论代言)。周伦佑:《反价值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年文论,第三代最重要的解构理论)。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大陆现代诗进程的宏观描述,侧重百年汉诗研究)。章亚昕:《生命的陀螺》,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一部被忽略,却尝试古诗论与现代融合的感悟式“诗思维”);《现代诗美流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入,是所有关于诗隐喻阐述中最为深刻的)。吴晓:《诗美与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较早的意象思维研究)。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第二部西部诗论);《母语诗学纲要》,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诗学建构,一个有活力的开端)。燎原:《西部大荒中的庆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内第一部西部诗论);《扑向太阳的豹子——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子专著)。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文论的吸收与当下诗界焦点的回应);《中西诗学的汇通——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第一部研究第三代诗专著);《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大陆最先研究朦胧诗专著);《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60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多次被援引的《季节轮换——新生代诗潮》(李振声,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新诗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吸收》(金丝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刘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兆平的《诗美的解悟》;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以及活跃于“双栖”战线的张清华;仿效《流放者归来》的三卷本《旁观者》作者钟鸣;在线的张闳、张柠、刘翔(杭州)、孙基林、毕光明和专做新诗版本学、新诗“年表”被称为中国新诗“司库”的刘福春,等等(注:借此机会,我还要说,新诗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诗人的直接参与,这是其他文类研究少有的。同以往一样,新诗的理论建设,许多命题、方法、设想、建构,一开始就是由诗人直接提出来的。诗人的许多诗论、随笔、经验,有时看似缺乏系统却异常尖新深刻,它们往往成为诗学某一命题、术语、范畴的先导。比如诗人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汉语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独到见解,诗人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诗本体的深入,诗人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的某些穿越,诗人成明进的《感性诗学》(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对“意味诗”的全面掘进,以及诗人藏棣、西川、王家新、黄灿然、杨小滨、西渡等的文论都很有见地。诗学建设,诗人言说是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忽略这一行当的规律特点,是重大失策。)。
而吕先生的“总结”对上述这些人——本质上是新诗潮理论的后继者——的成果根本视而不见,只是在正文,提及论文一篇,偏废如此之大,实在叫人吃惊!不得已,笔者只好站出来为这支队伍“小结”,笔者的意思并非为谁争上“大名单”,也不是多少人上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先锋诗歌研究,事关整个新诗研究的问题。
对于新诗潮理论的前辈们,“总结”报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吕先生这次肯定谢冕先生,还“小心”地点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然而众所周知,谢冕的十余部著述,从对朦胧诗率先推举《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国新诗潮论》到《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对整个新诗潮的推动和百年新诗研究,所发挥的旗帜性作用,再怎样评价也都是不为过的。同辈的孙绍振,对个体主体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学的高扬,晚近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警戒,一直保有理论家的睿智与敏锐。郑敏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连同她持续发表的一系列回归古典的文论,显示了诗家对诗质的深刻洞察。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缪斯的空间》在诗美芳草地上操持,屡有建树。吴思敬的《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创作主体内部,做出方法论上的有益尝试,大大超越被吕文点中的1987年版的《诗歌鉴赏心理》。还有洪子诚、刘登翰的《新诗史》、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或史或论,同样成果卓著。
由上面简要清理,可见出一条线索,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续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坚。20年来,两支在倾向上承传的队伍,业已形成自己较浓郁的特色:较开放的前卫诗学理论,较丰富的理论想像力和批评锐气,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构想、假说,以及建设性思辨;艺术直觉、艺术敏感较强,在感性批评中努力发散理性活力,在话语转型中寻觅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吕先生严重的排它性,最终导致两份完全不同结果的“清单”。此番的“盲视”及“障眼法”,在小说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无法被接受的。
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说穿了,这是20年来新诗研究在立场、观念(包括方法论)上分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我们与吕先生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新诗研究的前沿应该定在哪里?
吕先生认为新诗研究的前沿是文体理论。他说,“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致力解决诗与散文的关系”;“中国新诗文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其次是轨迹学”(注:吕进:《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先看看吕先生前沿学科的研究大著《中国现代诗学》,在自撰导言中称该书为“诗学新思维”,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做出“6个重要突破”(注:吕进:《中国现代诗学》,2页,重庆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当年十分兴奋,真想为同道的成果祝贺,然翻阅之后,未免疑窦多多。该书当然是一部分类学著作,主要围绕着抒情诗(或诗的情感性)做一些论述。按照吕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标准看,计有抒情诗特征属性2章,语言4章,生成3章,诗人修养1章,诗的风格2章,分类3章,轨迹动向2章,自是十分辉煌了,姑且就把它视为一部具备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当时很粗浅的我看出“破绽”: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诗歌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变异;看到情感图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却没有看到抒情的弱化、细化与转化趋势(早在1987年孙绍振就对情感的“极化”“细化”“弱化”做过深刻表述(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7章《诗歌的审美规范》,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他看到理智在情感中的不小作用,却没有看到“情绪”中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早在1987年的周伦佑就有大量“非情态”写作论述(注:周伦佑:《反表现——超情态》,见民刊《非非》,总2期,1988。));他看到抒情诗的外在音乐性,却对抒情诗的内在音乐性——内在节奏点到为止(早在1985年陈仲义已有专门论述内在节奏的章节(注:见《论诗的音乐性》下篇《内在旋律》,《艺谭》,1985年3期。));他看到抒情诗线性的“灵感—寻思—寻言”三阶段,却少掉了更具互动空间的“意象思维”和“非意象思维”(同期的吴晓早已发表了许多关于意象思维文章(注: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看到抒情诗媒介的特征,却未能触及语言的陌生化张力(早在1979年台湾李英豪就有这方面的出色论文(注:李英豪:《论现代诗的张力》,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卷,台湾故乡出版社,1979。))。
比照同期的同类项研究,可见该书并非取得6大突破进展,阐述的还多是现实的与浪漫的诗歌普泛的品质,“漏掉”了其他更多特殊、独到、隐秘、幽微的东西。而这些被“漏掉”的,才是诗歌的真正奥秘。在我看来,该书不少提法,其实都是抒情诗的基本“常识”,基本常识被拔高为前沿的突破性成果,实在难以理解(注:难以理解的还有一点,在《中国现代诗学》这么一个庞大严谨的框架下,吕先生把自己与他人的文章共16篇,作为附录放进各个章节,似乎是为求取多样化效果。计有与他人通信10篇(别人就占了5篇)、评论2篇、短文1篇、开幕词1篇、闭幕词1篇、为人作序1篇。不知道那么多通信、短文,在《中国现代诗学》这样重的磅秤下,能称出多少“例证”重量?反倒给人水分的感觉,至少在体例安排上是不妥的。)。
如果说,新诗研究主要涵盖三大层面:诗学理论(如范畴概念的基础建设、诗歌形态所体现的属性特征等),诗歌批评(如诗人文本解读、诗人个案研究等),诗歌史(如社团、思潮、运动、诗风,以诗歌现象为线索),那么,新诗研究的前沿视野,自然聚集于诗学理论、诗歌批评、诗歌史的“问题意识”上了。问题意识就是善于清除伪命题、假命题,善于提出真问题,善于拽住这三大层面的核心要害。
新诗研究的前沿与其他文类不大相同的地方有:1.它是感悟性及灵性特强的研究;2.研究对象的各种本体元素特别活跃;3.无论蜕变或转化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快。这就需要研究者有很好的“跟踪”嗅觉意识,有直接面对诗歌实践的应对能力,否则容易落入“隔”的窘地。那种对当下写作实践隔岸观火、凭观念开中药铺、满足“二手”、进行平庸理论套用的做法,是难于抵达诗的真谛和诗研究高地的。
据此“问题意识”,笔者想尖锐指出,新诗研究的前沿:在于新诗的现代转型,而不是在分类学——什么抒情诗叙事诗寓言诗儿童诗之类的分类研究,甚至可以说,新诗的转型,才是新诗研究——前沿中的前沿,难点中的难点。
前沿就是前列、前端、前矛、突前的意思,它往往是矛盾与动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转型则是新与旧价值的“交接”,是旧的扬弃、新的寻求过程。新诗的转型,是一次历史文化机遇。白话诗——新诗的基础,向广义现代诗——过渡形态和现代诗——突前部位的转型,不是新诗一种类型和风格的简单演变,而是充满新质的、新型的“摆渡”。转型中的突前部位——现代诗形态,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先锋色彩体现于——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的针尖般洞穿。
新诗的转型,聚焦于现代性上。新诗的现代性,是新诗自身不断裂变与重组过程的行进状态。它的真精神,不是依赖“他者”影响,或绝对继承关系,而主要靠自身充满生机的实践和自身内在发展逻辑。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它与过去的断裂(或曰对过去的重新发现),重视溶入当前,面向未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诗何以比其他文类拥有更多“火气”,勇于对传统老化固化作出摒弃,勇于对新质元素孜孜追取,勇于深入自身“诗意与诗艺的双重蜕变”,不仅从“他场”上,回到“诗的自觉”,更在“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再接受”中,走向全面开放。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创造性转换、生存与言说同构、生命与语言互动,诸如此类,都直指白话诗在现代语境中,螺旋式迁演到现代汉诗轨道。
具体说开去,就诗学理论层面,这批人抓住存在/生命/语言“本位”,涉及诸多转型期诗学形态:计有象征诗学、意象诗学、超现实诗学、生命诗学、语言诗学、新古典诗学、文化诗学、日常诗学、叙事诗学、解构诗学……并且对“下一级”诗歌术语、命名,也有各种新的发掘,比如:语感、智性、诗想、冷抒情、句意象、情绪流、宣叙调、及物、张力、叙事、反讽、戏剧性……不敢说刷新许多命题,却在很大范围内有所拓展。
在诗歌批评层面,从文本个案来看,20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是敏锐地推出了一批诗人,这些诗人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有目共睹。从北岛到西川、藏棣,从韩东、于坚到伊沙,不下30人。不仅大大凸现了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昌耀,还挖掘了被埋没的灰娃、胡宽;不懈地使潜在写作的食指、芒克、黄翔重见天日,更让海子的神性写作升温(单是海子的研究集就出了5部,一点也不比穆旦研究少)。8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诗歌史的诗人,哪一位与这批人的系列诗人论没有关系?
就诗歌史看,这批人对各个社团运动流派现象更是“一网打尽”,自“文革”地下的“白洋淀”、“前朦胧”、“归来派”、“西部潮”到“非非”、“他们”、“倾向”,从“民间”、“知识分子”到“中间代”、“70后”,从“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到最新诗网络……形形色色诗歌在场追踪分析,不乏急切冲动,却为新诗后20年版图提供第一遍厚厚的草稿。
这些研究,同时贯穿在20年来许多新诗的关键词,反复阐述、深入打开:如异化、人本、蜕变、嬗递、多元、相对、生命体验、语言意识、诗本体、介入、中国场、本土经验、母语、现代性、互文、综合等等。以个体的主体性和诗本体为例:从最早的“大我”、“小我”之争,“传声筒”与“心灵秘密”的分歧到“个人化书写”再到“私密性”探讨,从现实的“反映”到心灵化“反应”,再到“生命语言本体化”……以及诗的神性、俗化、神秘、纯粹等各种品质的充分体认,都标示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钻头,一直面向最坚硬的岩层旋进。
与此同时,大量针对性到位的论文,在诗界受到广泛关注,单举90年代宏观论述的,信手拈来就有:《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徐敬亚)、《’89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欧阳江河)、《第三代诗论》与《红色写作》(周伦佑)、《后朦胧诗:作为写作的一种诗歌》与《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臧棣)、《时间神话的终结》与《新诗现代性的重建》(唐晓渡)、《在历史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诗歌》(刘翔)、《中国当代诗潮的流变》(燎原)、《论朦胧诗》(席云舒)、《新诗潮新论》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王光明)、《90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梦亦非)、《后朦胧诗系列论》(陈旭光)、《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0)四种主要写作向度》(陈仲义),等等(注:这方面的论文,还可参阅吴思敬主编:《磁场与魔方——新诗潮诗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社,1989)、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少儿出版社,1999,以及对80年代诗学理论研究的研究文章《在历史转换中生成着‘诗本体’》,见《文学评论》,1994年1期。)。
正是上述这批人,集中围绕新诗转型的前沿课题,在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的互否与重塑、蜕变与顺应中,进行大量建设性探讨。主体性和本体性是他们的主要突破口,有关现代诗、先锋诗的精神、语言、美学、结构与解构诸多难题,都给予足够回应,并且维持在一种历史与当下的互文动态语境中。
谢冕,一直以来从文化社会现实层面,发掘新诗嬗递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出高屋建瓴的视野;郑敏对新诗语言与形式的关注上升至文化视角的反思,获得诗界热烈反响;唐晓渡深入个人主体性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展示以发现问题见长的思想色彩;周伦佑从本土出发的“变构”理论,在消解中促成诗歌可能性空间寻找,形成一时风气;耿占春有关诗歌基本图式与言说的本体论铺开,有较强的理论前导;程光炜关于“重读”文本的诗歌史写作,取得较大进展;其他诸如王光明一直持续百年汉诗理论整合研究,李震集中瞄准汉语诗学建构,陈旭光对现代主义路向的有效梳理,杨远宏关于重建诗歌精神系列论文,陈超对各种“艰涩”文本精到阐释,沈奇的当下捕捉和现场追索,陈仲义对转型期现代诗16种形态的挖掘等等,都标示着前沿研究可能抵达的幅度和深度。
浏览上述几十部著述和检视几百篇论文(注:还需要指出,作为中国惟一公开出版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20年来,先后出版近50辑,为艰难的先锋诗歌研究提供阵地。),可知这支队伍,一直活跃于新诗的前沿研究课题——新诗的现代转型。以“新诗的问题意识”和现代性作为楔子,尤其在新诗本体性、主体性两大维度上取得长足进展。这些研究总体成效可归纳为下面五点:
1.考察与确证新诗,自白话诗到广义现代诗到现代诗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某些超越性,在理论上充分打开多元与相对空间,加快其嬗递与转型的时间速度。
2.密切联系实际,从大量第一手感性资料进入诗歌内部,在诗歌诸多图式、模态、元素、因子中挖掘生长性,推动新诗转型过程中的自我增殖及其自洽性。
3.侧重外来思潮吸纳,在全球化的边缘化叉口,对诗学理念、观念做出重大调整,由此与传统诗学展开碰撞,特别注重对写作实践的经验提升,努力使之转化为诗学构成,为新诗的现代性理论话语做出开头。
4.注重方法论引入,尤其是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语言分析哲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从以前较宏大的泛读进入到细读式文本批评研究,对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做出一次强有力的填补。
5.在广泛的诗潮、流派、现象研究基础上,发现与推举一批代表大陆诗歌成就的诗人、文本,为20世纪新诗史最后20年提供人物“亮点”和诗写范式。
笔者敢于做出如上断言,是基于20年大量前沿研究依据。新诗的转型,不少地方是得借助上述犀利的理论批评犁铧的,或前引、或后推,与时俱进,不断历险。这与那些跟在后面,求稳求妥地干些拣拾麦穗的活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反省:先锋诗歌研究的评价
今天,面对新诗潮理论强大的后继者们,客观地说,吕先生碰上棘手难题,要么像从前那样顺机批判一番(如重庆诗会),要么闭眼“绕道走”,权衡之下,最后来个“冷冻”处理。
这一“整体冻结”,没想到,恰恰屏蔽了新诗研究中最具生气的那一部分。说穿了,也是对整个先锋诗歌写作实践的屏蔽。它使我想起早先古远清先生发表在《诗刊》上一篇总结新时期诗歌的论文,也是只字不提朦胧诗(或许被删节了?不得而知)。而大家知道,朦胧诗潮在当时公众眼里已是新时期重大的诗歌景观。设想一下,20世纪中国小说史,删除马原以后的20年,会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史?现在,抹掉先锋诗20年的重要实践,20世纪的新诗史及新诗研究如何面对真实与后来者呢?
有人估测,新诗潮发端以来,以高潮期民间诗歌社团2000家、低潮期200家平均值计算,大陆民间诗歌社团维持量将不少于500家(单诗歌网站就有200余家,个人诗网页不计)。加上每年先锋诗集出版量逾百部,诗作发表量逾万,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先锋诗歌写作,即使其负面屡遭指责,但其整体生命力却不见衰竭。一波又一波的生命涌动体现着它的价值。
这里,涉及对先锋诗歌的评价问题。20年的先锋诗歌写作实践,一般公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6)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第二阶段(1986—2000)以第三代为主的后新诗潮。有趣的是,先前不大接受第一阶段新诗潮的人,现在基本接受了,对第二阶段,研究者中多数前辈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在我看来,第二阶段主导倾向是对第一阶段的消解,不管消解中的建构,或解构中的建设如何,它们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着眼于生存/形式(言说)最大限度的敞开。后新诗潮企图在文化上对传统诗教、诗美、诗法、诗语进行全面突围。一方面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是最大程度打开诗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打开途径中,不乏冲动的极端和失度实验,导致了非诗倾向和不少艺术内伤。简而言之,大体肯定的第一阶段和泥沙俱下沉淀之后得失、功过兼杂的第二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基本状况。应该说,20世纪最后20年,是百年新诗写作和研究最畅达、最放开的20年,它告别意识形态钳制,筑就多元与相对的诗写格局,在全球一体化国际接轨中,初步打造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型。新诗前沿研究的视域和真功夫,就是从众说纷纭、万分复杂的现象中,祛除实践探索失误,大力发掘萌芽状的生成性,并把这一生成贯穿在整个转型期。
一些人否定第二阶段——后新诗潮诗歌现象,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既然后新诗潮不是原来诗歌规范意义上的诗,就可以不必把它当做诗进行学术确认”,“即便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未必是合理的存在”(注:见《思想的交锋课题的深入》,见《文学评论》,2002年1期。)。这种说法是在先入为主的一棍子否决前提下,才显出道理(深究其里,也缺乏辨证)。不过,学术的穿透力恰好就体现在这里。新学人李震正是通过当下活生生的诗歌现象,从严力、王小妮、于坚等个案经验生成中,用20万字“母语”,激发出“回归本土文化语境,建构汉语诗歌生态学;返回母语,建构汉语诗歌批评话语;返回文本,走向深度综合”的构想。这种立足当下鲜活实践、从而筛滤提升诗学的构想,正显示先锋研究的活力。这里,有必要再严肃廓清一下:所谓先锋诗歌,无疑是代表了独立、个人性、探索和创造意识。先锋诗歌实践,永远是自由心灵的无限寻找,固然其大部分可能最终不能转化为经典,然而对先锋诗歌现象的各种研究,是完全可以从中得出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东西。李震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吕进先生不承认观念偏守和对情况“失察”,坚持认为这批人的前沿研究因太切近对象,无法进入成果评价,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与心态十足代表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偏见与曲解。
众所周知,诗歌由于形式简括,各种本体元素十分活跃,故诗歌变革变幻常常成为其他文类变化的先声(如朦胧诗的“对抗”“介入”写作之于“伤痕”、第三代的“整体主义”之于“寻根”、“黑夜意识”之于女性写作)。正是这批人大量前沿性钻探,才提供了较清晰的新诗前沿地质纹理,甚而触引出部分“原油”,为后来的诗歌流派史、流变史、文体史,打下雄厚铺垫。倘若把这些颇具艰苦冒险的作业视为“非学术”、“靠不住”,不能纳入成果与学科范围,岂不再次暴露学界裹足不前、欠缺进取胆气?倘若学界坚持而不反省自己的评价机制,肯定会再次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尤其是先锋诗歌研究的人为障碍。只有现象复述而不见研究者灼见,只有史料编写而缺少自出机杼的解读诠释,多年惯性养成的“温吞水”学风,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研究状态。没有太多创意的“成果”,即使再堆积如山,最多也只能唬唬圈外人。
这里,再次涉及前沿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前沿研究有许多命题涉及当代性、当下性,它确实与学术研究构成一对矛盾。一些人坚持认为:坚持当代性肯定会背离学术本位,因此为维护学术规范的全面稳妥而坚决放逐当代性、当下性,长期来,学术本位瘟疫般防备“轻佻”的当代性当下性,以为掺多了,学术就不纯不正。殊不知,任何学术本位只要存在于“今天”,都无法逃避其当代性、当下性,一旦脱离它,其隐含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敏锐肯定会遭到损害,因为任何当代性都关联着连续的历史,任何当下性都回应着动态的历史。它们之间的“互文”,恰恰蕴藏着无限契机。
许多研究者对当下现象不屑一顾,其实现象具有无限丰富性。排除现象的丰富,实则是自我削弱研究前沿的地基。杨义看得比一般人清楚,“现象总是远远大于理论,这就给理论创新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注:杨义:《文学研究走向21世纪》,见《文学评论》,2000年1期。)。王晓明也说:“研究者对当代生活深切的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术活力的来源。”(注:见《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文学评论》,2002年2期。)他们都指出当代生活和当下现象对前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的,有了当下的参与,才有前沿研究的刺激(包括激情、思想、领悟),有了突显的前沿研究,才会更多激活后续研究(注:在先锋诗歌研究受到怀疑时,尚有新鲜血液加入:敬文东的《指引和注视》、谭五昌:《秩序的生长——后朦胧文化诗学研究》(合作),姜涛(90年代叙事),周瓒(女性诗歌),李润霞(“文革”诗歌),汪剑钊、张桃洲(以上都是博士)等,有力地延续这一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像今天这样整体缺省、整体被遮蔽的“事件”,是极为罕见的。它是诗歌界重大矛盾分歧在新形势下的大暴露,有必要引起争鸣,通过争论争鸣,推动新诗研究走上广阔而不是偏狭的道路。
最后,我们愿意再次触及新诗研究几个“老大难”问题,提出来供同道们教正:
一、作为前沿性的先锋诗歌研究,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大力支持与认可。固然它的某些超前话语、方法论,与公众知解力、审美习性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全局性主流语境的结果,但也表明学界内部、学术视阈的偏守(说严重一点,还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以及由此带来的滞后的评价标准。反省滞后的评价标准,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可否认,诗学立场、观念,冲突、分歧是正常的,它带来的排它性,反倒有助于学术竞争繁荣,但是排它性必须维持在起码的底线。不应该在貌似公允客观的话语权力下,公然抹掉另一方有影响的存在。如若学界继续助长和维持这种局面,谈何学术公德、公平?谈何建立科学、良性的发展机制?
二、诗歌领域无论是实践或理论研究,最具变革因素与生机力量都在其前沿地段。新诗的现代转型,是新诗最困难的前沿课题。先锋诗歌研究处于新诗研究的前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被垢病的不断“追新”“求新”,刺激了整个新诗研究。淡化或压制其存在,甚至视为“非学术”“非学理”,是十分可笑的。正因为它是一种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诗歌本身创作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故新诗研究决不可与当下、现场“脱节”。新诗传统,很大一部分来自新诗自身的生长;新诗的当下现象,往往孕育着新诗建构最优秀的胚芽。放弃它,实则是放弃最好的诗学资源。聪明的办法是在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中找到平衡点。从活生生的正反实践中,加大力度,促成鲜活的生成诗学。
三、前沿地带的“工兵”作业,最需要敏捷的穿透力。其难度绝不亚于甚至超过后续工作。无论对哪种研究类型(长线或短线)的研究者来说,观念视野、方法思维、知识更新,都提出更高要求。就新诗研究的特殊性讲,它还断断少不了研究者,面对第一手感性对象,弥足珍贵的生命灵悟。这种生命灵悟,强烈感应着诗歌本体的生命化,达成活络的对流,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研究生动光彩起来,它大大高于经院思辨。那种靠吃“本本”、理念先行的“演绎”是走不远的,它太欠缺生命活体的热气。而无论是侧重本土的灵性思维或外来分析思路,关键是充满个性化的求索、开拓、原创(或曰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应该永远摆在新诗研究意识的首位。
责任编辑注:吕进先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本刊未转载,读者如需要,请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