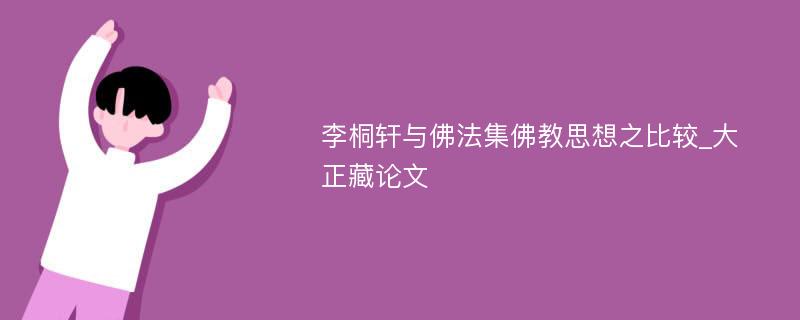
李通玄与法藏的佛学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学论文,思想论文,李通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通玄(635—730)和法藏(643—712)处于同一时代,都值唐朝盛世。法藏为出家的僧人,居于唐朝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李通玄是佛教的信仰者,独自生活在佛教盛行之五台山地区。法藏略晚于李通玄出生,但盛名在先;李通玄寿龄高长,晚于法藏而卒,而影响在后。他们两人一是华严宗的实际创造者,一是隐居荒野、深入民众的华严学修行者。一是华严宗的正宗,一是华严宗思想的异端。对这两位处于同时代,却有着不同华严思想倾向的人物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先简要论述客观背景的不同,然后就判教、佛性思想、修持实践三方面,对这两位华严巨人的佛学思想进行比较。
一、客观背景的差别
李通玄和法藏所处的地理与政治的环境,以及身世、素养、身份、地位都是不同的,法藏生活于唐都长安,且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则天为母亲荣国夫人舍宅为太原寺, 法藏也由此机缘得以正式剃度,并主持武则天的家庙。法藏出家不久,尚未受戒,就承旨在寺内讲《华严经》,时值端午节,武则天特意写信并派人送去衣裳等,信中说:“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事数。愿师承兹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龄,永耀传灯,常为导首。”〔1 〕对法藏大加称赞。武则天正式登基后,出于政治需要,对佛教更加重视,亲自为新译《华严经》制序,并召法藏于洛阳授记寺开讲此经。继武则天即位的唐中宗,对法藏也很重视,赐法藏“鸿胪卿”之号,称赞法藏“阐扬释教,拯济迷津”。其后睿宗也请法藏为他授菩萨戒。从上面一系列活动看,法藏的出家、修道、讲经都是与武则天及唐中宗、唐睿宗的支持分不开的。他交往于上层社会,讲经布道的对象有很大一部分是达官贵人,这部分听众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针对这些人宣传佛教,就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这就形成了法藏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理论重于实践。而李通玄则完全处于政治漩涡之外,他所处的是荒漠的山野,广阔的五台山地区,他所面对的是朴实的农夫。他的生活大部分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从沧州游学至五台山,并在此接触佛教。有关他的历史记载中没有提到他和政治有什么瓜葛,倒是有不少和普通村民交往,受村民尊敬的事例。李通玄是一个隐居独修者。他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带有禅僧的风格。自然,在他的著作中,重视修持实践的成份也就多一些。
法藏的祖先为西域康居人,他本人出生于佛教信徒的家庭,精通梵汉语言,曾参与《华严经》的翻译。这种种族的特点与语言的能力使法藏理解同样传自于西域一带的《华严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李通玄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他所处的环境与接触佛教时的年龄来看,他对梵语及西域的语言恐怕是不会精通的,但他却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尤其是有多年的学《易》心得体会。由于这种背景,他所理解的《华严经》与法藏的理解相比较,自然又有另一种气象。
再则,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造者,一宗的宗主,曾在长安、洛阳两地主持多个寺庙。其弟子也很多,成名的如上首弟子慧苑,在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法藏逝世时也引起了朝野的巨大震动,因他是侨民,葬礼费用由官方供给,并以外宾司礼仪隆重对待。法藏的一生可谓是“其生也荣,其死也哀。”〔2〕相对说来, 李通玄则生活在安静恬淡的环境中。他既没有出家,也没有主持过寺庙。历史记载中,和他打交道的除了朴实的山民外,多是一些不可信的仙女和神异动物,如虎为李通玄驮经,仙女供给李通玄茶饭等。李通玄也仅有一个不出名的弟子照明。他去世的时候,当然没有隆重的葬礼,只是有“二白鹤哀唳当空,二鹿相叫连夕”〔3〕的神异记载。安葬时,“择地于大山之阴, 累石为坟。”〔4〕与法藏隆重的葬礼相比,反差是很大的。
由于李通玄和法藏种种客观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佛教思想的不同。
二、判教的异同
法藏的判教学说是“五教十宗”,李通玄的判教是“十教十宗”,二者的判教学说,从形式到具体内容既有相同之点,也有区别之处。首先,我们来分析“五教”与“十教”的区别。李通玄在《新华严经论》卷第三中立“第二依宗教别”时说:
“如来设教亦复如是,称自根缘,得自心之法,随增广而成熟之,亦无常宗而成立教,对病施药,病痊药除……法既无穷,宗教无尽,无前后际,普备诸根,但为众生自分前后,且如毗卢遮那之教,无始无终,称性无方,无断无绝,随其根类自见入胎出家,说始终教行,入寂涅槃。”
这就是说,所谓教法是佛针对众生根机的不同,随机所设,如同针对不同的病而施用不同的药一样。李通玄认为判教分前后差别,是就众生说的,从佛的根本意旨看,其义理没有差别。判教前后高低不同只是权宜教化的手段。这是李通玄判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法藏判教则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一是按佛教法的深浅次第加以安排,成立五教十宗说。二是从一乘的角度,把佛所说的法都包含于《华严经》中,《华严经》是“别教一乘”,而《法华经》代表“会三归一”之一乘,同于三乘所说,故称“同教一乘”。三是依根本佛说与佛教化所说,立“本末”二教之分别。根本佛说,是佛阐述自证之境界的说法,它是直显之法门,为其它法门的根据,是“本”;佛教化所说是根据三乘需要而说,是从“本”教产生出来的“逐机末教”,因而是“末”。
在法藏和李通玄判教之前,已存在有多家判教学说。法藏立十家以为借鉴,李通玄除法藏提到的十家判教外,又列举了法藏的五教及另外两家的三种判教,这样李通玄就有十三家判教作为参考。由此看来,李通玄判教是建立在比法藏更广阔的视野上。
李通玄的十教与法藏的五教分别是:
李通玄的十教法藏的五教
1.小乘纯有教1.小乘教
2.说《般若》破有明空教 2.大乘始教
3.说《解深密经》和会空有教 3.大乘终教
4.说《楞伽经》说假即真教4.顿教
5.说《维摩经》即俗恒真教5.圆教
6.说《法华经》引权归实教
7.说《涅槃经》令诸三乘舍权归实教
8.说《华严经》于刹那际,通摄三世及十世同圆融教
9.共不共教
10.不共共教
从上可以看出,李通玄判教中的前五种与法藏判教的前四种在内容上是大体一致的,这表明李通玄基本上认同了法藏关于小乘、《般若》类经典与《解深密经》(大乘始教)、《楞伽经》(大乘终教)、《维摩经》(顿教)这样一种佛教理论发展次序的安排。但在后面部分就有了不同,《法华》、《涅槃》作为大乘经典,其理论超出了以前的种种经典。从这类经典出现的时间看,也大致在一个时期。就理论而言,《法华》、《涅槃》、《华严》都属于大乘有宗部经典,都倡导众生有佛性这个基本观点,因此如何安排这三种经典,特别是《法华经》,就有了差别。《法华经》是天台宗的宗经,法藏也推重《法华经》,但他更重视《华严经》,为了协调《华严经》与《法华经》,单立五教之说就显得有些单薄,因此法藏就用“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的说法。这样就有两种一乘,虽然法藏认为《华严经》是不同于它教的一乘,《法华经》是同于它教的一乘,但仍然存在着哪个是究竟一乘,哪个更圆融的问题。李通玄明确地把《法华》、《涅槃》列入十教之中,就避免了法藏在安排此类经典时出现的矛盾。
法藏判教中也吸收了天台宗判教的内容,他把天台判教中“化法”(内容)与“化仪”(形式)揉和在一起,形成了五教说,这就使其判教标准不一致,也引起了后来佛教学者的批评。在李通玄的判教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他的判教所依的标准也是不统一的。从李通玄十教中前八种看,是以经典所代表思想为次序进行教判,而第九、第十中的判教又提出了共与不共的问题。共不共指众生共有佛性,然见佛不共;不共共是讲众生根机虽各有不同,但其闻法同,只是得益又有所不同。共与不共不再是依据经典的判别,而是对众生根机与闻法的关系的分析,这样,在李通玄的判教中,也存在有两种判教标准,也就是说法藏和李通玄的判教标准都存在类似的缺陷。
此外,李通玄和法藏对《华严经》的地位判定虽有一致性,都把它视为圆教,但由于李通玄和法藏判教目的不同,对《华严经》的评判态度也产生了差别。法藏处于诸宗竟立的长安,当时天台、唯识等宗派也有很强的势力,特别是唯识在当时的长安吸引了很多的信众,因此法藏在判教上就有很强烈的抬高本宗,而贬斥别宗经典的倾向。他一再强调《华严经》是一乘圆教,是别教一乘而不与别的教法共,即使他也认为《法华》很重要,但仍然把它作为同教,认为它与三乘之教是共与同的。他还认为别教一乘是本,其余三乘是末。〔5 〕李通玄既没有创宗的条件,也没有创宗的欲望,处于恬静的山野之间,没有法藏那种强烈的竞争要求,因此他在判教时用语也就缓和得多。谈及《华严经》的地位也只是说:“一切权教法门,总在其中。”〔6 〕对于自己所立的十教教判,又屡次强调:“如是十教,总是如来于本法界一刹那际一时一声,顿印如响,随诸众生自分根为渐顿不同。”〔7〕十教之说都是佛说, 只是基于不同根机之人,才说有十种教之分。
就判教的宗而言,李通玄与法藏都立十宗,但是宗之所依又有所不同,李通玄是“依教分宗”,法藏是“依理分宗”。李通玄所立十宗因是依教而立,所以就与十教基本对应,法藏依理分宗,十宗内容与五教虽是大同但有少异。法藏的十宗说是五教的具体说明与补充,而李
通玄的十宗与十教,则是从不同角度阐明的同一个问题。李通玄与法藏十宗的具体内容如下:
李通玄的十宗 法藏的十宗
1.小乘戒经为情有宗1.我法俱有宗
2.菩萨戒为情有及真俱示为宗2.法有我无宗
3.般若教为说空彰实为宗3.法无去来宗
4.《解深密经》为不空不有为宗 4.现通假实宗
5.《楞伽经》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宗5.俗妄真实宗
6.《维摩经》以会融染净二见现不思议为宗6.诸法但名宗
7.《法华经》会权就实为宗 7.一切皆空宗
8.《大集经》以守护正法为宗8.真德不空宗
9.《涅槃经》明佛性为宗9.相想俱绝宗
10.《华严经》即以此经名一切诸佛根本智慧, 10.圆明俱德宗
因果圆满,一多相彻,法界理事自在缘起
无碍佛乘为宗。
上面两种十宗中,法藏的十宗对小乘作了具体的分类,而李通玄的十宗则对大乘的阐述较为详细,基本上涵盖了大乘几部主要经典的基本思想。
总起来看,李通玄和法藏判教学说的区别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内容上,即一家立五教十宗,一家立十教十宗,这表明二人对于佛教经典及其发展的看法是有一定区别的。二是在判教态度上,李通玄和法藏都以《华严经》为最高的经典,李通玄并不贬斥其它经典,而法藏贬斥其他经典,并藉以确立华严宗的地位。
三、佛性思想的区别
佛性论在大乘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关系众生本性以及是否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问题,是大乘诸宗派都要涉及的领域。李通玄和法藏的佛性思想的差别主要集中于佛性概念的外延上,即李通玄是在法性与人性共通的基础上论佛性,法藏则是基于人性论佛性。
法藏认为,有情众生具有成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佛性,无情之物具有的真如理体称为法性,成佛只限于有情。李通玄针对这类观点明确地指出:“如化佛权教中说有情有佛性,无情无佛性,一切草木不能成道转法轮。”〔8〕有情有佛性,无情无佛性是权说, 是化佛所说,不是如来设教的本意。在李通玄看来,无情、有情都能成佛,因为:
第一,李通玄认为《华严经》是“越情实教”,他说:“如《华严经》,即是越情实教。”〔9〕也就是说,《华严经》对有情、 无情的成佛问题是不加区分的。李通玄举例说,《华严经》中说功德林菩萨等从所来的国家时,把它们的国家叫“慧”,而一切境界又都是“慧林”〔10〕。这就是把菩萨、众生与诸国土境界都看成是一体的。他认为:
“无有情无情故,所以然者,无二见故,为一真智境界,无成佛者,无不成者故。”〔11〕
“二见”,指有、无二种偏见。执有是“有见”,执空是“空见”。佛教认为前者有增益之过,后者有损减之错,都不合于中道的原则,是错误的见解。这里,“二见”指把整个世间分成有情与无情的二种观点,李通玄认为有情众生与无情之物都是由“真智慧”境界所变现,二者是相通和圆融的,因此就不存在有情成佛而无情不成佛的分别。
第二,李通玄认为,有情无情与成佛不成佛这两对用语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因为有情无情是“依业说”,成佛不成佛“非属业”。所谓“业”是造作的意思,具体指内心的活动和由内心所发动的言语和行为,以及这些活动所引起的力用。李通玄认为,
“夫有情无情者,此是依业说,夫论成佛者,非属业故,若非属业者,即非有情非无情故,何得出情法上计言有成佛不成佛耶?”〔12〕
也就是说,有情、无情是就“业”说的,而成佛不成佛不是就“业”说的。在李通玄看来,有情、无情与“业”相关,是有分别之见,而佛则是“觉悟”、“得度”、“解脱”,是真智慧的体现,是超越情知之见,没有有情无情之分,也没有成佛不成佛之别的超越境界。李通玄认为,只见有情成佛,不见无情成佛是一种偏颇、错误的见解。
第三,针对强调佛性与法性不同的观点。李通玄说:
“夫言理性遍非情而不同有情成佛者,此由未见法空,不依实慧,未了得世间诸相本来常住,但见随情识变生灭之相而妄斟酌。言非情但有其理遍故,只如成佛,岂可理外别有佛耶?若理即是佛者,于此理中,情与非情本无异相,岂从妄见立情非情耶?”〔13〕
这段话中包含了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李通玄认为把法性、理性定位于非情,把佛性定位于有情,这是只见现象而不见本质,只见“随缘”,不见“不变”。也就是说持无情无佛性者,只看到世间有情、无情的生灭表相的不同,看不到它们都具有“本来常住”的本性,因此而妄加分别。其二,李通玄认为将理与佛隔离在不同的对象上,就会导出“理外别有佛”的看法,若以理即是佛,那么在此同一理中,就不会有有情无情与成佛不成佛的分别。
李通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比较早提出“无情有性”说的佛教学者。他的这种观点同天台宗湛然(711—782年)的“无情有性”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湛然之说影响颇大,而使后人以为此说乃湛然首创,实际上李通玄的说法略早于或至少是同时于湛然的。
李通玄的“无情有性”说,一方面是对法藏“无情无性”说的否定,一方面又与法藏的“无情无佛性而为法性”相通。李通玄和法藏的“佛性”、“法性”同指宇宙和人生的本性、本体。法藏还称之为“真知”、“一心法界”,李通玄则又称为“真智慧”、“一真智境”。李通玄所谓“佛性”是指“真智慧”本体在有情、无情上的统一化体现,法藏则认为“本性”在有情、无情上的表现是分离的:有情有佛性,无情为法性。他们两人同视佛性、法性为本体,这是相同的。
李通玄将佛性扩展到无情之物,这同《华严经》的法身人格化倾向是一致的。《华严经》以毗卢遮那为教主,毗卢遮那佛在《华严经》中不单是美好理想的体现,也是法身智慧的人格化、法性本体的实体化。李通玄说:
“毗卢遮那者,名种种光明遍照也。以法身悲智,示相教光,用对诸根,随情现色。为情乘相别,见异佛殊,以体用混收,本是毗卢遮那一智身也。”〔14〕
这样,毗卢遮那佛作为法身、智身遍化于一切事物中,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切事物都含有佛性。李通玄正以此为据,认为“无情有性”。
此外,李通玄身处山林之间,与草木山水等无情之物为邻,游学参化,独自体悟,冥想之中,当有可能得到某种虚幻体验,从而体认无情也有性的观念。
四、观法实践的区别
法藏的著作中,讲观法的很多,主要集中在《华严发菩提心章》、《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及《华严经探玄记》中。他的主要观法有法界观、十重唯识观和妄尽还源观。在他的法界缘起理论中,作为核心内容的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也是属于观法的。所谓观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是在宗教修持中树立一种形象,这种对象可以是一种特定对象,也可以是一种理论,通过运用直观智慧,专心观想,并企求以此获得解脱。观法也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的。
法藏认为:“据门陈教,教即门而不殊。”〔15〕所谓“门”即指“观门”,教观相即是法藏观法的新特色,这在法藏的几种主要的观法中都体现出来了,法藏在《华严游心法界记》中立五门观法:法是我非门,缘生无性门,事理混融门,言尽理显门和法界无碍门,并且将此五门分别配于小乘教、大乘始教、终教、顿教、圆教五教。法藏的十重唯识观也和五教联系在一起。小乘教不讲唯识,不在其中。其余的相见俱存唯识观、摄相归见唯识观、摄数归五唯识观等三门观法属大乘始教,以末归本唯识观、摄相归性唯识观、转真成事唯识观、理事俱融唯识观等四门观法属大乘终教与顿教,融事相入唯识观、全事相即唯识观、帝网无碍唯识观为圆教中之别教一乘,而总括以上十门观法则是同教。法藏上述的观门都配于教法,二者相即一致,法藏重视教观一致、一体,有以教(理论)代观(实践)的倾向。
法藏在《妄尽还源观》中提出了“海印三昧”与“华严三昧”的说法。所谓“海印三昧”,即是,
“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言尽心澄,万象齐现,犹如大海,因风起浪,若风止息,海水澄清,无象无现。”〔16〕
所谓的华严三昧,是,
“法界圆明自在用,是华严三昧。谓广修万行,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证菩提。”〔17〕
海印三昧是不可说的世界,只能证果才能体验,它是绝言语、绝思虑的一种直觉世界。法藏通过两个方面来对海印三昧境界进行说明。《五教章》开首就说:“今将开释如来海印三昧一乘教义,略作十门。”〔18〕这十门中主要就包括因与果。华严三昧就是从因的角度对海印三昧的说明,也是试图通过解行而达到证果。《华严经》强调果分不可说,因分可说,强调入于法界之中的具体的参学,但是这一点在法藏的学说中没有受到重视,而湮没在法界缘起理论即十玄缘起中。十玄缘起是从果的角度对海印三昧的说明,十玄无碍的理论依据的是“性起”的思想,它强调事事无碍的圆融,事事无碍是所证之果,从所证之果再到解行,这是法藏独特的作风,与一般修行实践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所不同。十玄缘起既是一种理论,是对海印三昧境界的说明,同时,它又是一种实践,即它既是观,又是教。教与观相即,观法也即教理,这表明法藏把观法消解于教理之中,从教法、理论来理解观法,这样观就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观法,而成为了一种理论,观法的浓厚实践特点消失了,最终的结果是淡化实践,突出理论。
在李通玄的观法中,出现了不同的倾向。他反于法藏高谈理论的作风,独创了以实践为主的华严学风。对于六相圆融,不象法藏那样把它理解为对华严境界的描述,而是恢复《华严经》中从十地修行的角度来理解,使六相圆融说不脱离于实践。对于十玄缘起说法也是如此,李通玄在十玄中增加了“智”的概念,强调“理事圆融”,重新开辟了从浅至深的实践途径。
此外,李通玄比较重视的佛光观与三圣圆融观,这都是通过对具体形象的直观来进行修持的,佛光观是对光明的观照,三圣圆融观是对佛、菩萨形象的观想。这些观照、观想,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而在法藏的观法中,包括十玄六相观、十重唯识观在内的种种观法,都是一种理论的观照。
总之,李通玄和法藏的观法实践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即一个是重实践的观法,一个是重理论的观法。李通玄强调止为观之先,法藏则以观代止;李通玄主张教观相分,法藏则以教代观。
注释:
〔1〕《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第175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2〕《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第187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3〕《长者事迹》,《续藏经》第一辑,第五套,第四册, 第328页。
〔4〕《长者事迹》,《续藏经》第一辑,第五套,第四册, 第328页。
〔5〕参见《华严—乘教义分齐章》卷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集》第二卷,第二册,第131页。
〔6〕《新华严经论》卷3,《大正藏》卷36,第737页上。
〔7〕《新华严经论》卷3,《大正藏》卷36,第737页下。
〔8〕《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4页下。
〔9〕《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4页下。
〔10〕《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4页下。
〔11〕《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4页下。
〔12〕《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5页上。
〔13〕《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5页上。
〔14〕《新华严经论》卷6,《大正藏》卷36,第758页中一下。
〔15〕《华严游心法界记》,《大正藏》卷45,第642页下。
〔16〕《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第99页。
〔17〕《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第99页。
〔18〕《华严—乘教义分齐章》,《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