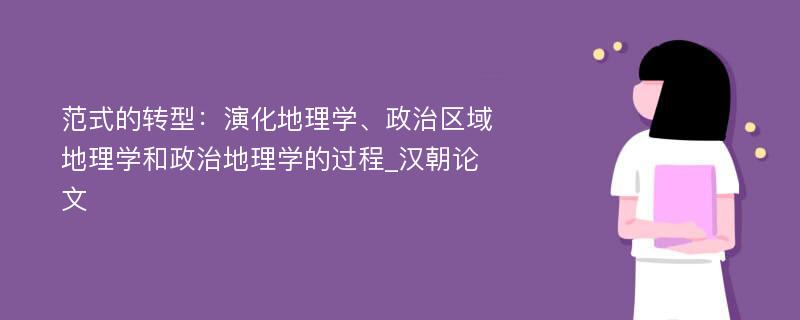
范式的转换——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论文,范式论文,政区论文,沿革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现代学科的形成而言,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甚至是至今还没有完全定性的学科。在中国最先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是上一世纪30年代创办的《禹贡》杂志,但却是以《禹贡》的英文名称Historical Geography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见其时的《禹贡》主要还是研究传统的中国沿革地理的学术刊物。所谓沿革地理,主要的研究一是疆域政区的沿革,一是河流水体的变迁,实际上还带有很浓厚的历史学的分支性质,前者与疆域政区沿革史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国外,历史地理也出现得很晚,而且学科性质也存在游移现象,有的认为历史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有的则认为它是历史与地理的接合部。
虽然《禹贡》杂志基本上还是沿草地理的研究模式,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地理学的雏形开始出现。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80年代的时候,历史地理的学科性质基本上已经定谳,那就是将其定义为是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认为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以区别于人类出现以前的古地理以及当代的地理。因此地理学科所有的分支在历史地理学中也都应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学中也应该有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两大分支。而在历史人文地理中又应该有次一级的分支,即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之分。而在历史政治地理中又可以更加细分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疆域地理等等。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历史方法,因此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及地理学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表面上的学科性质有点近似于历史学的分支,研究者如果没有历史学素养,就很难在这一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所以今天教育部将历史地理当成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来对待,也有其一定原因,虽然从根本上讲并不合理。
在中国,由于历史学的发达,对于史学的各个侧面与分支都有长远的研究史,其中对政治史的研究尤被重视。行政区划变迁的内容与政治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对行政区划变迁史的研究也历来受到注意。因而历史政治地理的前身不但是沿革地理,而且实际上还是沿革史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如果要研究政治地理的发展过程,必须从行政区划沿革史说起。
一、行政区划沿革史的研究
如果我们对这一研究过程加以回顾,大致可以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史料编纂阶段。
可以说,自从行政区划出现以后,有关其变迁情况,诸如置废分合等记载就成为史书的内容之一,在《左传》、《史记》等重要史籍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古代史籍之所以重视政区的记载是因为政区实际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职官的任命是以行政区划的存在为前提的(也有个别的例外),这就是《周礼·职方》所说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顺序。但起初有关政区的记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还算不上是一种研究。《史记》虽有八书之作,但其中有天官而无地理,甚至连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这样的大事,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不罗列三十六郡之名目,致使后人至今聚讼纷纭。到了班固修《汉书》的时候,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班固把西汉末年的政区面貌,以《地理志》的形式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对该时期的政区地理格局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历史编纂家的这个创造,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但其时能够意识到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框架,容纳西汉时期其他地理内容(例如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在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方面已是一个质的飞跃。更何况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经用简单的语句来叙述郡级政区的沿革以及部分县级政区的由来,这已经可以算是一种研究了。班固《地理志》的编纂显然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楷模,因此在《汉书》之后,相继有十五部正史模仿其体例,也写出了自己的《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职方考》)专篇。
随着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家对政区变迁越来越重视。隋唐以后,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比正史地理志内容更加丰富,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元丰九域志》以下,直至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都属于这一类地理总志的范畴。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某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如果以民国时期为断限,这样的地方志至今大约还留下有万种以上。地理总志与部分地方志和正史地理志一样,也是研究政区变迁的另一类资源。此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行政区划的专篇,如《通典·州郡典》、《通志·舆地略》与《文献通考·方舆考》,其中《州郡典》与《方舆考》的作用有似正史地理志。由于行政区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几乎是无时不变,因此在上述地理文献中,不仅记载当代的地理面貌,对前代的地理情况也有所叙述。所以就一般的意义说来,这些地理文献事实上也是历史地理文献。但从根本上说来,所有这些记述,多是某一代(有时只是一代中的某一时间断限)政区的罗列或某一政区在历代置废变化的记述,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
除了文字叙述以外,前代学者根据有关文献,曾编绘一些历史地图集,如晋代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以反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
第二阶段是个别的考证订讹。
虽然历史文献有着历代政区的记载,但如果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对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隆嘉庆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清代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门学问,对正史地理志与全国地理总志以及有关政区的历史记载进行全面深入的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述文献在文字方面的校勘订讹,解释文献记载中相互矛盾现象,恢复史籍的本来面貌。这些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其中最出色的学者是钱大昕,在他所著的《廿二史考异》中,对各正史有关政区变迁记载的匡正,大都是独具慧眼发千古之覆的重要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虽然大都是个案式的,但却为整体的政区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类似钱氏成就的学者虽然凤毛麟角,但都或多或少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当然清代也有些学者虽然有名气,但在沿革地理考证方面其实成就不大,有些研究甚至是错误的(譬如王鸣盛),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第三阶段是整体复原研究。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即:
1.历代大势的研究阶段
差不多在考证订讹的同时,就有学者开始从事综合研究,即以已有的史料为根据复原史籍上未曾记载的政区面貌。例如,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研究就引起一股热潮,清代不少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这是综合研究的典型尝试。与此同时,还有些学者从事补写某些朝代或历史时期的地理志的工作,如补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补志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当代还有人从事(最近一部是《北齐书地理志》),另外还有人进一步对这些补志的不足之处再作订补,这一工作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有人将眼光从个别朝代转移到整个历史时期,将历代地理志所反映的政区面貌连缀起来,编成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舆地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与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但无论是复原秦始皇三十六郡,还是做补志,还是编辑历代沿革表与舆地图,所有这些研究者,都还是将地理志认作某一朝代的经制,以之为指导研究的基本思路。换句话说,一般的研究者大都以为秦一代的政区就是三十六郡,而西汉一代的政区就是《汉书·地理志》里所载的一百零三个郡国,还没有更深入地想到秦一代十来年,三十六郡未必一成不变。西汉一代二百年,其郡国变迁更是繁复。这种以为一个朝代只有一副政区面貌的认识与研究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通代的研究。这种认识一直到上一世纪70年代还存在,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极为珍贵的古地图,墓主的下葬年代在汉文帝时,其时的长沙国疆域,比《汉书·地理志》所载范围大得多,但受到研究时认识水平的限制,有些历史地理学者,仍只能以《地理志》所载的长沙国为说。其实在这一阶段中,未必没有人认识到在一个朝代之中,政区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复原一个朝代的代表性政区,有各正史的地理志作基本依据,相对而言,难度较小(虽然也很难),研究一个朝代之中的政区变化过程,只有不成系统的零星的记载可参考,难度很大。所以直到上一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问世时,政区变迁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历代大势的水平。
历代大势研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汉书·地理志》所列百三郡国,只是西汉一代政区经过繁复变化尘埃落定以后的结果,光从百三郡国分布图上看不出政治过程对西汉政区的影响,也看不出政区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过程。我们看不出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叛乱之前的诸侯王国的实力,不能直观地理解汉文帝时贾谊所提的治安策在当时已经发生作用,因为经过“分封诸侯少其力”以后,叛乱七国已经小而无能为了。《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极力想复原汉初与西汉中期的政治地理形势,在该书中画了好几张地图,但由于政区变迁的研究十分专门,这些地图除西汉末年百三郡国一幅外,没有一幅是正确的。
2.断代研究阶段
所谓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是指复原一个朝代之中的政区变化全过程,这也是姑且用之的提法,因为这样的研究至今充其量不过二十来年,尚未蔚为大观。但就在清代乾嘉时期,已经开始有人意识到,地理志并不能代表一个朝代的政区面貌,因为政区的变化几乎是无时不在发生,要全面反映这一变化过程,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由徐文笵所著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定稿于嘉庆八年,1803年,但属稿很早,初稿至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即已完成,因钱大昕于此年已为之作序),就想要理清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的政区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是分裂时期,有的国家与有的朝代历时很短,如果全部弄清,则近乎是断代研究了,当然实际上还不完全是。要认识到行政区划是无时不变,而不是在一个时代里一成不变,也并不容易。清代虽然有聪明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情形,但还有许多人没有悟到这一点,如王鸣盛就不明白此理,将《汉书·地理志》表现的西汉末年现象拿来批评《汉书》纪传记载的不实。
清末,这种想要透视断代政区面貌的要求更显迫切,吴增仅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由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可以说是一种断代研究开端的标志。该表虽未能详及逐年的变化,但在经过考证后,能列出魏、蜀、吴三国每一代君主在位时的所有州郡县名目,以反映三国时期的政区变化情况,已属难能可贵,因为详细到这样小的时间段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均为前人所未见。与此著性质相类似的是王国维的《秦郡考》与《汉郡考》。前者不但想确定秦始皇三十六郡是哪一些,而且试图研究秦一代的郡目。也就是说,想研究秦一代郡的数目与名目的变化,其结论是秦一代有四十八郡,并考证出这四十八郡的名称。这里所谓的“秦一代”,已暗含断代研究的意味。当然受到史料的限制,王氏未能逐年列出这些变化(当然有些变化受到史料的限制,是永远无法达到以逐年为尺度的)。《汉郡考》虽不是研究西汉一代的政区变化,但已接触到关键的问题,说明从汉高祖到文、景、武帝,汉郡数目也是变化的,而《汉书·地理志》在对各代皇帝创建的郡数记载是错误的。这不但是修订史籍错误之作,还是朝代内部变迁的研究。当然王氏的研究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参谭其骧《秦郡新考》与周振鹤《汉郡再考》),但这两篇文章却是振聋发聩之作,代表一种新的断代政区变迁研究的思路。
到上一世纪30年代,以《禹贡》杂志编辑者与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地理学者,也把眼光投向更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但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际。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注意到两个方面的事,一是年代断限,二是增加总图。所谓年代断限就是在《图集》里大部分朝代的地图上都标明具体年代,如唐代是开元二十九年,明代是万历十年,以表明这幅地图上的地理现象(包括疆域政区与自然现象),并非一个朝代的不变的面貌,而只是那一年的实况而已。这一做法从未有过,说明对一个朝代的政区变化已开始受到注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来不及进行所有朝代的政区变迁全过程的研究,所以又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做法,就是在一些疆域政区变化较大的朝代里增加总图,这些总图表现一些关键年代的疆域与政区的大概,虽然比分幅图简略,但大致已能使读者明白该朝代在不同时期疆域政区的大致变迁。这些做法表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已远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深入,研究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但是增加总图毕竟只在关键年代,也是在历史资料比较丰富的年代,至于复原一个朝代内部政区变迁全过程,亦即以年度为标尺复原每一年的政区面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当时还是没有把握的。上一世纪70年代末,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再度受到重视,使研究表面上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纯学术课题得到施展的机会。在这种学术环境下,研究者经过逐步的探索,发现复原西汉一代郡级政区逐年的变化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发现是将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的结果,起初的研究只是一个王子侯国,随后及于一个诸侯王国,接着是所有诸侯王国,而后才及于整个西汉的所有政区。这种探索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原始史料的不足,如《汉书》中简单的一句“削两县”的记载,使人无法知道所削究竟是哪两县,又位于何处,于是也就无法复原削县前的王国封域,这样一来,就谈不上复原政区变迁的全过程了。所以在起初,研究者根本没有把复原西汉一代政区变迁全过程悬为鹄的,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才发现如果方法运用得当,是可以将上述“削两县”一类的谜破解出来的,所以如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在这里是用不上的。这种逐步研究的成果体现为《西汉政区地理》一书,这实际上是有同一思路的导师与研究生两代人的共同创造(参见《西汉政区地理》序)。
这样的研究因为与过去的通代的研究在深度方面有所不同,所以称之为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就如同于历史学中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一样。当然西汉政区地理研究的完成,并不表明任何朝代都有可能取得同等的研究成果,例如北朝时期的政区变迁过程也是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有关资料比西汉一代更为缺乏。而且就西汉而言,所解决的主要是郡级政区问题,县级政区的变迁限于传世史料的不足,不能复原其全貌,只能有赖今后考古发现的补充,局部地予以复原(如相当数量封泥的发现与张家山汉简等简牍的出土使秦县与汉初属县大体可以弄清)。而唐代以后,由于政区变迁资料的相对丰富,又使得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有可能取得比西汉更详尽的成果。要之,我们大体可以说,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的阶段已经开始,除《西汉政区地理》以外,《明代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东汉政区地理》也都是同类的成果。而从2008年开始分卷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则是企图将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扩展到所有的朝代。
以上三个阶段的分析是从历时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说明人们的认识已从有关政区史料的正误,到个别的政区变迁,从历代的变迁大势,到所有朝代的变迁全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将取代前一阶段的工作,因为第一二阶段的工作是永远需要的。例如每年由民政部编纂的《行政区划简册》就是第一阶段的工作,为今后的研究积累了可靠的原始资料。历史地理学界经常进行的,其他个案式的政区变迁的考证则是第二阶段的工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则第三阶段就无法进行。
但研究这些变迁,除历代舆地图外,都还只是政区名目的变迁(也就是说只讨论政区数量与名称的变化),还未牵涉到政区所有要素的变迁。地理学的成果一般都需要表现在地图之上,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也不例外,其最终成果应该表现在文字的叙述与图表的编撰并存才算完备。事实上在清代中期沿革地理研究中,有许多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这些研究者中,有的只是进行纯粹的文献考证,并不顾及考证结果是否符合地理要素。结果在考证过程看来似乎无误的情况下,却解决不了地理上的变迁问题,清代刘文淇的《楚汉诸侯疆域志》就是如此。所以除了政区名目的考证之外,还必须有界址问题(包括边界与幅员)才算政区地理研究的完成。
二、政区变迁史的研究
整体性的政区变迁过程的研究成果有图、表、志、史等形式。图指历史地图,表指沿革表,志指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史是指以文字叙述为主的专门史。事实上,完整的政区变迁史应由文字的叙述论证与沿革表和历史地图组成。
中国历来重视历史地图的编纂,左图右史是典型的中国史籍模式。还在晋代就有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表现传说中夏代的地理面貌,而中国现存最早表现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大势的历史地图集是南宋刊行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此后,一直到晚清,类似的历史地图集代有所出,直到清末,杨守敬集大成的《历代舆地图》问世,代表着传统历史地图集的终结(与此相应,在东瀛日本也一直有这类地图集行世,如长久保赤水的《唐土州郡沿革图》与重野安绎等的《支那疆域沿革图》)。清末民初,新式的历史地理图集也开始出现,到上一世纪8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行世,则是以现代地理科学思想为指导的,反映历代疆域政区与河流水体变迁过程的最杰出成果。
沿革表的编制最具中国特色,如果中国不是使用方块汉字,而是使用西方的拼音文字,大约也不可能有沿革表的产生。方块汉字最集约地容纳了尽可能多的信息量,使沿革表的编制成为可能。沿革表的编制方式是以政区为经,以时代为纬。这样从纵向可以看出此政区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从横向看则表明某一朝代存在哪些政区。早期沿革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芳绩撰于康熙六年(1667)的《历代地理沿革表》(但实际刊行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或稍后),该表分三大部分,分别表示部(即高层政区)、郡、县三级政区在历史时期的沿革过程(县级政区是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十一时期,统县政区在其前加上秦,高层政区在其前加上虞)。除了这种分层级的、全国范围的沿革表外,在某些地理总志中,也有分地区编撰的沿革表。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全国为二十一个统部,在每个统部前都列有该统部范围内府级政区从秦到明共十一个历史时期的沿革(加上当代即清代则为十二时期),同时在各府级政区内又另列表反映该府所属各县的沿革。沿革表的优点是简捷明了,但缺点是必须分而治之,如果想在一个表内反映全国范围各层级政区的逐年变化,则在技术上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在阅读上也有很大的困难。沿革表至今还在使用,而且随着个案研究的深入,地区性的沿革表的年代变化可以越做越详细,但由于整体研究的不足,不同地区的变迁并不一定在同时发生,就使得这些表格在时间上无法拼接,因而看不出同一年代的全国甚至较大范围内的政区面貌。
地理志与地理总志本来是以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期的政区作为基本框架的地理著作,不是表现历代政区变化的专门史,但由于志书一般都有专门部分以追述历代政区的建置沿革,这部分内容的组合其实就是简略的前代政区变化大势。这一点在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表现最为清楚,在每个统部、每个府与每个县都要述其历代沿革(统部与府从《禹贡》起,县从秦汉起),当然都只能以朝代为尺度,而不可能更精细。正史地理志一般比较单一,既不附表,也不附图。而地理总志却往往附图,有时志文反倒成为图的附说。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以图为主,以志为副的。只是流传过程中,图已亡佚,只有志文留了下来。当然其中的图也是当代地图,而不是历史地图。《大清一统志》是传统地理总志的最后一部,卷帙最繁,内容最丰富,除了大量的,以文字叙述的当代(即清代)的地理内容外,还附有详细至统县级政区的地图以及沿革表,是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志书。
尽管以图、表、志形式出现的政区变迁过程的研究成果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但是用现代方式撰写的,以行政区划为对象的专门史却迟迟未曾露面。图、表、志的形式各有其特点,但毕竟都有所侧重,缺乏综合性,读者无法从中看出动态的政区变化过程。尤其是志书,其重点是表现当代地理,沿革部分被割裂在各个政区当中,失去整体性的面貌。理想的行政区划史应该是包含文字叙述,并且附以图表的综合性著作。但这必须是在专门史成为一种新型的历史编纂对象以后,才有可能产生。在中国,直到上一世纪末,在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之后,才有专门史出现。但这些专门史起初还只是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后来则有军事史、文化史等,至于政区史这样的更加专门的分支,要到30年代才出现苗头。当然追溯源头可以从沿革图说这种形式说起,以下我们就来回顾百年来叙述政区变迁大势的专门著作。
1.以疆域沿革史形式出现
《支那疆域沿革略说》。重野安绎与河田罴两人合著,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七月初版,东京富山房发行。是书实际上是两氏所著《支那疆域沿革图》的图说,但可看成是近代关于中国疆域与政区变迁的第一部简史。该书四万余字,其凡例说明了此书写作的旨趣:“支那疆域沿革图成,历代版图广狭则就图知之。至其盛衰变迁攻守胜败等,非图上所能载,因作此编以附之。”此书是为简要说明中国疆域变迁而作,非政区变迁之专史。但疆域之广狭盈缩,需以其所包含之政区来表示,所以在间接上就等于叙述了历代政区的变迁。因为是图说,所以该书不以章节名,而以图为名,共分十六节图说。第一图夏代疆域沿革(商包括在其中),以下依次为周代、周末七国、秦代、两汉、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宋辽、南宋金、元代、明代、清代。夏代沿袭旧说,以《禹贡》九州为夏代政区的真实面貌,这是中国人之传统看法,非两氏之误。在当时分此十六图已见卓识,秦隋两代虽短,但于疆域政区变迁关系甚钜,所以各列为一图,而且详其变迁,于秦代尤甚,详辨始皇帝统一天下时,分为三十六郡的几种说法。此《略说》据我所见至少出了十版,可见其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中国舆地学会曾将此书翻印,以线装书的形式行世,但未标示刊行年月。最近则又发现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于1902年的《中国历代疆域沿革考》亦是《略说》的翻版。
国人所写政区史一类著作似始于《中国地理沿革史》,乃中国地理学界耆宿张相文于民国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所编讲义。原讲义未见,至1936年张相文之子张星烺将其父著作汇为《南园丛稿》时,收入此《沿革史》,始正式行世。全史约十万字,共三十二章,叙述从禹贡九州直到民国时期的疆域变迁大势及政区分划概况。绪言极短,略云:“……顾于历史中印证地理,其山川形势,既随世运而变迁,疆宇分合,常因政治而转移,繁变纷纭,已觉不可胜纪,又或州郡侨置,地异而名同,陵谷迁移,名同而地异。今试由民国而上溯明清,地名改易,殆已十之二三。更由明清而上溯唐宋,远及秦汉,其同者不及十之一二,而异者乃至十之八九。因是考证沿革,乃占史类之重要部分,自《尔雅》、《职方》以及历代地志,皆各有专书论之,然篇帙浩繁,无暇备述,兹特举其大体,为治史者开其端绪焉。”
正文部分虽然分章,但实际上与现在学术著作的章节不同,不成体系,只不过是简单的分段而已。各章有两类内容,一类以“秦之疆域”、“汉代疆域”为名,依正史地理志列出每个朝代的郡国州县名称,亦即借郡国州县的分布来说明疆域的伸缩,并在每郡下注明此郡于前代为何郡,及相当于今为何地。另一类以叙事的方式来说明疆域的动态变化,如“汉之外竞”,“晋之统一”等。除了简单罗列事实以外,在行文中也偶尔涉及政区设置缘由,如论秦代政区时说,秦境北部因“匈奴未灭,边防极重,故置郡愈多”,而长江流域因“南方水乡,且无外患,故置郡愈少也。”但全书重在说明疆域变迁,而且主要是从地名的更易来说明这一变迁过程,还不是专门的政区史。此外,该沿革史因为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仍然延续以《禹贡》九州为夏代的疆域区划等传统观念,故未能行之久远。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顾颉刚、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全书有十五万多字。与前者传统的线装书形式不同,这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推出的精装道林纸本,外观上已具新气息。内容则是此前沿草地理学的革命性的发展与总结。该书虽然也是从传说时代起,历数各个历史时期疆域变迁之大略和行政区划的变迁大概,但却不仅仅是一些地名的罗列,还比较系统科学地阐述疆域变迁的原因,政区变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论述了与疆域伸缩同时的民族变迁以及与郡县设置有关的人口迁徙等现象,是一部内容远较前此同类著作详瞻全面的沿革地理著作。或者也可以说是研究政区变迁的第二阶段的代表性著作,也是解放以前最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
在本书以前的同类著作都以疆域变迁为重点,此书则疆域伸缩与区划并重,只是当时尚未明确其为行政区划,而称为疆域区划。所以实质上这是一部疆域政区沿革史。在绪论中亦说出了这个思想:“其地方制度州郡区划与夫人户之迁移,亦疆域史之所不可少者,因并论及,著之于编。”不过这里又把疆域史的范围不适当地放大了。其实人口迁移可以另有专史解决之,甚至疆域史与政区史也可以分别治之。但其时专门史的发展不过数十年,自然不能多所苛求。该书写法也相当规范,除绪论外,还专辟一章叙述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之成绩。观点则是全新的,因为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主帅,已经考证出《尚书·禹贡》为战国时人所作,不是传说中夏代疆域区划的真实记录。所以该书第三章的标题是“夏民族之历史传说及其活动范围”,远比过去惯用的《夏代疆域》要准确科学得多。该书之出,不但是学术上的发展,也有时势上的需要,写作此书时,正当抗战开始,所以在绪论中,作者说:“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付敌人,爰有是书之作。”
在形式上,本书也显出新型的学术著作的气息,章节体系完善,章目基本上以历代疆域概述为名,每个朝代一章。节目则以疆域范围及疆域区划为主,兼及地方制度。而且每一朝代附有一幅疆域图,将疆域政区变化落实到地理方面,以与文字相互映照。
在《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前后还出现两种值得一提的同一类型,但篇幅小得多的著作,一是1931年刘麟生所编《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只有六万字;二是童书业所著《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约七万字。这两本书虽然篇幅都很小,但在学术概念方面却有比《中国疆域沿革史》优胜之处。刘著的第四章为“历代政治区划”(其他各章为:一、沿革地理的意义及其应用,二、中国沿革地理中的重要著作,三、历代建都考,五、封建与割据,六、水道变迁大势,七、历史上的形胜之地,八、邻国与藩邦),“政治区划”一语显然比顾著的“疆域区划”清晰。童著则更进一步,将其《沿革略》分成三篇,第一篇是历代疆域范围,第二篇是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不但明确将疆域伸缩与政区变迁分开论述,而且正式提出“行政区划”概念。不过第二篇主要是讲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即从郡县制到州制到道府制、省制的变化,而不是行政区划要素(层级、幅员、边界等)变迁情况的实录。该书第三篇“四裔民族”,应该属民族史或民族地理范围,不合阑入此书。但这是时人的观点,非关童书业一人之事。
2.与地方行政制度相结合的形式
如果说上一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政区变迁的著作是以疆域沿革史的面貌出现的话,50年代以后则是以地方行政制度的形式出现。因为研究者多瞩目于中央制度,所以地方行政制度历来为制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随着专门史分支学科的日益受到重视,地方制度研究专著才逐渐问世。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本书以相当详尽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历述行政区划制度与地方官制的变迁。其中有些观点十分精辟,如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督区看成行政区划的一种,尤为作者的卓识。不过此书只写到南北朝为止,隋以后付之阙如,未免可惜,但以一人之力成此大作,实属不易。80年代,又有程幸超之《中国地方政府》行世,其中也讲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除以上两种类型的著作以外,也有《中国历代行政区划》这样的专门论著出现,但多是罗列一个朝代的政区名称而已。80年代以后,虽有两三种政区沿革史面世,但不仅内容单薄,且著者并非素来从事政区史研究,而是缀合一般资料而成,深度明显不够。
由于已出版的与政区变迁有关的著作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谭其骧先生久有将自己以及前人对政区变迁研究的成果,撰写成书的打算,但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但尽管如此,他仍然留下了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即《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图说。在谭先生本人而言,他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每幅总图撰写图说,而不是撰写一部政区史的著作,但在实际上,这些图说的组合,却是一部极简明的中国历代政区变迁史,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变迁大势最精辟的总结。
除此之外,至今一直没有专门的行政区划史。这种区划史应该表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制度方面入手,论述政区制度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是以严谨的考证为基础,复原政区变迁的全过程。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以多人合作的形式撰写这样一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不但将历代的行政区划变迁考证叙述出来,而且还要将每一朝代内部的具体变迁情况复原清楚。这部行政区划通史实际上是各个朝代横切面的政区地理的纵向的连续画面。如果我们将沿革史看成是劈柴的工作,我们从柴薪的纵断面里可以看见木材的纵向纹理,也就是看到全国范围内,或一个地区范围内随着时间前进的政区建置变迁。而政区地理则是横向锯木,看到是木材的断面情况,也就是某一时段的全国或某一地域的政区面貌。与此同时,由于政区地理研究的深入,也就为历代疆域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因此在每个断代分卷的前头都首先是该朝代的疆域概述。实际上将疆域与政区变迁史合而为一。
三、从历史政区地理到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
历史政区地理是80年代以后提出的新概念,这个概念与政区沿革史的差别正如上面所述。也就是说历史政区地理强调共时的政区结构,而政区沿革着重于政区的历时变化。连续性的共时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自然比过去以一个朝代为尺度的政区沿革史研究更加细密。但很显然,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复原政区的历史原貌方面,而应该进一步作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规律性的探索与理论性的提高,因此从历史政区地理提升到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在90年代以后也逐渐出现。
政治地理学在西方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时间不过百来年。溯源追本,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早就被注意到了的。早在公元前后,欧洲的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都将政治观察引入他们的地理著作中去。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地理学家们也没有忽略对政治形势的注意。17和18世纪时欧洲学者也将“统计学”和地理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所谓统计学当时意味着与国家有关的资料,诸如区域、边界、人口、进出口的产品和物品等等。虽然这些都还算不上是政治地理学的范畴,但是政治学和地理学能够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时髦学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世纪晚期兴起的“纯地理”学派也企图将政治框架的地理资料附丽于自然的地理框架上。虽然政治学与地理学在时间与空间上一直互相交叉,但是直到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才在1897年正式提出“政治地理学”这一明确的学科名称,他的名言:“每一个国家都是部分人性(humanity)与部分地域(earth)用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对西方的许多地理学家发生深刻的影响。当然,“政治地理”概念的提出则要早到康德或更早,这里暂不去说它。
此后一百年间,政治地理学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学科框架,而且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新理论新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首先只注重在全球的尺度方面。于是先有海权论,再有陆权论,而后还出现过地缘政治学的这样的恶性肿瘤。看得出来,政治地理学直到二次大战前还没有成为一门稳定的学科分支,也还难以用一个惟一的概念来定义它。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地理学和政治学学者都进入了该领域,而且各有其创见。二是地理学本身的宽泛性,使得其分支学科易于产生变形(地缘政治学的产生恐怕与这两个原因不无关系)。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歇,政治地理学重新被提起。虽然仍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6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即政治地理最关心的是地理区域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可将此观点视作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方向。至于地缘政治学在世纪之交又重新出现,但是与二战前的面貌已经有本质上的大同。
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地理学基本上有三种尺度,一是国际或者说是全球的尺度,讨论的主要是全球的政治格局、世界秩序。在数十年前,政治地理学主要关注的是全球问题,因为对于观察政治与经济安全问题而言,一个民族国家显然是太简单规模太小的框架。全球性的观点与地缘战略认识始终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直到近三四十年,对于全球的政治关系依然是政治地理学家关心所在。例如西方政治地理学家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外围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对两极世界,多元世界的提法都是大尺度的范围。甚至政治家们在二战以后提出的两大阵营,二十多年前中国提出的三个世界(与上述三个世界不同)概念,其实也是政治地理思想的一种表述。第二种尺度是国家尺度,研究国家的疆域,边疆区,国家之间的边界,首都的设置,国家的地理位置、形状等等;第三种尺度是地方尺度,研究国家的政区结构(层级与管理幅度),选举区地理,地方与中央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等等。后两种尺度在近几十年中有比较快的发展,这与二战以后,局部的战争仍然不时发生,而全球性与大区域范围内的战争未再出现的形势不无关系。
政治地理学在西方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但至今不能说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将其比喻为一个容易从科学规范中走失的儿童。尤其在第三种尺度即地方尺度的研究方面,就像科克本(Cockburn)所说,西方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
对于西方的政治地理学理论,中国的学者很早就引起注意,20世纪初已有留日学生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而了解了西方的政治地理,随后也有一些学者直接由西文翻译的政治地理著作。甚至早在1902年湖北的乡试中,第一场的中国史事论考题里,就有一题是直接问到政治地理学的。但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地理学始终没有得到自身的充分的发展,并未产生自己的政治地理学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没有必要详加分析。但是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处于长期受辱的地位,无论政治学家或政治地理学家的产生都没有必需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政治地理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如何从地理角度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在分裂时期如何运用政治地理原则与对峙政权相处,都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在行政区域的分划方面,历代中央政府都花了很大力气进行实践,每一代都对前一代的做法有沿有革,积累了大量的政区变迁与政治过程之间关系的资料,这事实上就是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的实证基础。
按理说,历史政治地理应该在政治地理理论充分发展以后,才进一步延伸的研究工作,但实际上理论的建立有赖于实证研究的充实,如上所述,在地方尺度方面,西方就没有现成的政治地理理论可用,而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倒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如何从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家或政治学家(如果用现在的概念去委曲古人的话),以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潜在的政治地理思维,并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比较,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这一方面似乎还未曾作过认真的探讨。当前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多半是从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着眼。而政治思想从来不包括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制度则常常忽视地方制度。要而言之,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在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分别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关系的密切。
1.《禹贡》所表达的理想政治地理区划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伪托为夏朝大禹所著,被收入五经之一的《尚书》之中。由于《尚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所以《禹贡》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存在过的地理现象。但20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证明《禹贡》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作品,是当时人统一意识和地理知识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当时一些思想家的理想构思。如果从政治地理视角看来,在《禹贡》之中存在着不同的两种地理区划:上半篇的九州制是一种分块式的政治地理区划,下半篇的五服制则是圈层型政治地理区划。这两种区划理念,在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中,都有其实践例证,我已另文予以论述,此处不赘。
2.地理志的编纂反映历史学家的政治地理观点
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大都有地理志的专篇。从唐代以后,又开始有全国地理总志单独成书,内容比地理志有所加详。宋代以后,地方志编纂已经制度化,也从区域的角度反映行政区划的形势。此外,在许多政书中也列有行政区划内容。这些专篇与专著是历史学家将地理现象视作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各种地理志毫无例外都以疆域政区作为框架,而把其他地理现象,如自然环境(以水道分布为主)、经济、文化等内容,纳入这个框架之中。行政区划是中央政府为行政管理方便而人为分划的区域,历史学家们将各种地理现象都系于相关的行政区划之下,而不是单独作为个别或分类的地理现象(例如作为水文地理名著的《水经注》是以水道为经,而将其他人文地理现象系于相关的水道河流之下)予以描述,说明他们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而是与政治有关的体制问题。
3.政治家的政治地理实践
这里政治学家的意义比较宽泛,包括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与制定政策的官员。在这方面有极为丰富而且形形色色的实例。
缓衡地带的设立。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隙地的保留是为了保持政治势力的平衡,所以宋、郑两国对于隙地中的六个城邑相约不去占领。后来秦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瓯脱地带,唐帝国与吐蕃之间的闲田都有类似的作用。
边疆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管理方法。如秦代的道、汉代的初郡、唐代的羁縻府州、元代的宣政院辖地、明代的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等,其行政制度都与正式郡县有所差异。
以改变政治地理格局作为政治手段。汉初皇帝专制威权未立,只能以一定的地域分封诸侯王国,容许他们处于半独立状态,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与此同时,又逐步设置同姓诸侯王国来抗衡异姓诸侯。为了这个目的,同姓诸侯王国的封域都较大,以便有足够的拱卫中央政权的政治力量。在异姓诸侯被清除以后,同姓王国又成了不利于中央集权的障碍,于是贾谊、晁错与主父偃又先后以众建诸侯、削藩与推恩等措施,用分裂王国封域、削夺王国支郡与蚕食王国本郡的手段,将同姓王国的领域几近削夺殆尽,这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以地理方式来处理政治难题的实例,或许可称之为政治地理手段。
政治区域与自然地理环境的背离。政治与行政并非永远一致,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抛弃行政管理的方便。行政区划的变迁有时并不是行政管理的需要引起,而是服从某种政治目的。如秦代的郡与山川形势符合,而西汉时期却相背离。这种背离完全出于政治的需要。
行政区划诸要素的变迁。这些要素主要有结构(层级与管理幅度)、幅员与边界,其中层级的反复变化,例如从二级制到三级制变化的两个循环,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互为消长的过程。划定犬牙交错的边界则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如秦朝在划定岭南三郡与内地诸郡界线时,就有意不使其与南岭山脉重合,以有效地控制岭南地区。汉代诸侯王国之间的边界分划,也故意使其犬牙相入,以便于遏止可能发生的叛乱。而统县政区的幅员从秦代以来逐步缩小,也隐含着缩小地方官权力的企图,与政治目的息息相关。
至于首都的定位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似乎存在着两大基本原则:一是离强敌不远而又有险可守;二是能号令全国而无匮乏之虞。统一王朝中最重要的两个首都长安与北京就是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建立的。
但无论是思想家们体现在地理方面的理想政治制度,还是历史学家们对疆域政区作为政治体制一部分的观点,抑或是政治家们的政治地理实践,在我国都还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研究,从未有人从这三个角度来探索中国固有的政治地理思想,并进一步用政治地理理论来进行审视与分析。由于缺乏系统与理论性的研究也使得我们从未制定明确的科学性的术语来表达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一些对象。如对于行政区划层级的称呼,就很含糊,缺乏规范。甚至对于疆域政区的研究过去也只归于沿革地理,或后来的历史地理范畴,在80年代以前甚至从未提出诸如政区地理或疆域政区地理这样的名称。虽然这两个术语是否可行还应经过厘定,但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讨论或评论,却从侧面说明政治地理在我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对于疆域政区的研究之所以有着深远的传统,如上所述,是因为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在中国逐渐形成。因此对于地域上如何治理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着朝野的重视,也因此在浩瀚的典籍中保留着公私两方面的丰富的政治地理资料,所有这些文献资料都不同程度表明国家政治体制与地理现象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传世或出土文献)这一丰富资源来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框架是一个应该引起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重视的问题。
那么,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政治地理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来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
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必须将国家的疆域与行政区划变迁记录下来,以作为一种与人物、事件同等重要的历史记载。但是对于影响疆域政区变迁的原因或者规律却未有系统的记录与分析,因此从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就都集中在复原历代疆域政区面貌方面,而不及于为什么历代的面貌有所差异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将前一方面研究称为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话,那么包括前后两方面内容的研究或许就与政治地理学的概念相一致了。
政治地理的研究范围很广,在此我们先集中于以疆域政区,尤其是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研究对象作一阐述。那么,在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想应该至少有以下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步骤的内容:
第一部分,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这是理解与阐释变迁原因以及探索与总结变迁规律,并进而提出解决当前或今后有关国家疆界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策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疆域政区变迁极其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一研究工作完成,也不能因为这一工作未曾完成就不进行关于变迁原因一类的研究。
已经完成的历代研究最主要的,也是最系统的成果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他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编》中所写的图说。今后的任务是完成各个朝代的断代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组成一个历代疆域政区地理系列,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与《中国疆域变迁通史》,复原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变迁的全过程,基本上完成中国政治地理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部分工作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历来对疆域政区的研究大体上是整体式的,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例如说,对于疆域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讨版图的伸缩、领土的归属以及国界的划定。但未将历史上的王朝版图分成边疆区、核心区、缓冲区或其他有关的概念,去进行研究与分析。对于具体的边疆地理当然也有研究,但多半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其与整个国家疆域变迁的关系,而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的地理考证。例如对唐代羁縻府州,对明代羁縻都卫的具体地理位置大都能够确定,但对其在政治地理方面所起的作用则还不够,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也是如此。历来只注意复原政区的整体面貌,从政区名目的变化,到政区的置废分合,以及政区界址的确定等等。这对于政区地理研究来说就已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对于政治地理而言就远远不够。政治地理研究还应该在行政区划变迁的整体面貌已经清楚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将政区分解成结构、边界、幅员等因素,分别研究这些因素的变迁过程,以便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第三部分工作做准备。同时还要建立与界定一整套政治地理术语,这一工作过去也未曾有人做过。1990年,我写了一部《体国经野之道》,提出了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的概念,地域型政区与城市型政区的概念,这些术语是否得当,还需讨论。该书将政区分解为结构、边界、幅员等因素进行历史时期变迁的研究,是参照了中国历史地理传统的研究对象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某些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是否符合我国国情,也还需要推敲。
在政区结构、幅员、边界之外,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还应该研究以下这些与政区有关的问题:政区与地方行政组织等级的关系,政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政区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政区的形态(单式与复式),特殊的政区样式(如军事型政区、财务督理型政区、虚幻型政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区形式,都必须分门别类进行充分研究。第二部分工作主要仍然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是历史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但更集中的是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
第三部分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何有如此繁复的变迁过程。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权力在绝对意义上的稳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稳定与均衡始终是相对的,经常存在着要打破稳定与均衡的动力的变革因素。当这些因素在政治过程的均衡条件变得不能控制时,就会发生政治权力的变革。就特殊意义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以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如何有效进行行政管理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以及民生的需要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代政治家都殚精竭虑,力图寻求最合适的途径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为了维持政治权力的稳定,为了处理上述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两大问题,政治地理手段的运用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但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或者说,历史学家未能从政治地理角度来分析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原因,一直只停留在简单的“进步”或“倒退”的思维之中,使得事件的诠释始终不得要领。
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中,政治地理是前景广阔的分支,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面对极其丰富的文献遗存,使得政治地理的研究有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有利的研究空间,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地理研究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