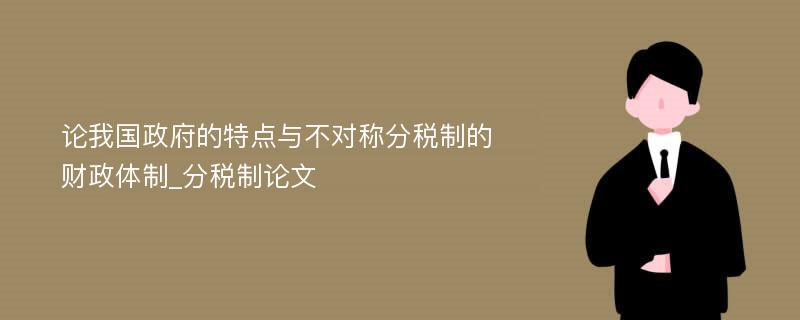
论中国政府特性和非对称型分税制加分益制财政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税制论文,中国政府论文,加分论文,体制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期学术界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研究综述
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实行20年,学术界评价不一。第一类是正面观点,认为财政分权和分税制财政体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积极性,是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钱颖一等(1996、1997、1998、1999)、邹恒甫等(1998、2005)、张晏与龚六堂(2005)。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分税制总体框架合适,如刘玲玲等(2008)。①最近有的学者如孙秀林和周飞舟(2013)指出分税制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②
第二类是持比较否定的观点,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分析分税制存在的严重缺陷,主张要对分税制作系统全面改革。如王振宇(2006)、陈宪等(2008)、张文春等(2008)、陶勇(2008)、匡小平等(2010)、浙江省财政厅课题组(2013)。③他们中间,有的认为分税制属于集权,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影响了地方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特别是对发达地区负面影响更大。有的则认为分税制导致区域间财力的差异使公共服务区域差异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将危及社会公平与稳定。还有一些学者基于这样的逻辑即分税制导致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导致房价上涨出现泡沫,如果泡沫破裂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所以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持比较否定的态度,如张双长等(2010)、周彬等(2010)、吕炜(2012)、宫汝凯(2012)、黄国龙等(2013)。④
第三类观点认为总体框架问题不大,但作为分税制核心内容之一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转移支付没有起到纠正地区差异的作用,如尹恒等(2007)、张恒龙等(2007)、江新昶(2007)、伏润民等(2008)、郭庆旺等(2008)、范子英等(2010)、贾晓俊等(2012)、褚敏等(2013)、涂立桥(2013)。⑤
各路专家学者之所以对分税制有如此不同的意见,是因为评价标准不一以及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政府特性不够了解。本文重点探索中国政府特性,揭示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性质以及对经济发展状态截然不同的影响,接着提出评价分税制的系列标准,在对分税制进行理性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看法。
二、中西差异和中国政府特性
一国的财政体制是一国的发展阶段、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综合作用的产物。要正确评价财政体制,只能从具体的国情出发,综合地全面地加以考察。学者们对包括财政体制在内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偏颇,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策结论大多源自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以英美发展阶段、文化和体制为假定前提,其思维方式是英美化的,不能直接适用于对中国的分析。了解中西差异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构建适合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新范式。
(一)中西时间、文化、治理模式和经济制度的差异
1.时间差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18世纪就指出时间具有两重性,可分为编年史的时间和概念中时间(或逻辑学的时间)。⑥年历和钟表刻度所计量的时间属于编年史时间,是以公历纪年为代表的时间符号,描绘均匀流逝的经验事实的序列,具有绝对的数量性、平面性和等质性。逻辑学的时间或概念中的时间,存在于认识活动之中,刻画事物发展程度和性质差异,具有相对的质量性、立体性和异质性。从经济角度,后者也就是经济发展史意义上的时间划分,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体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编年史时间中,存在许多逻辑学时间。编年史时间和逻辑学时间差异,类似于人的生物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异。例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美国大家都处于2013年(即编年史时间),但美国等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阶段,而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时间阶段,这是中西时间差异的客观体现。我们评价、分析和谋划财政体制变革不能忽视这些差异。
2.文化差异。文化在字典上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而人和动物的差别就是人结成社会,社会中存在各种人与人的关系,故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模式”。在这一方面,中西存在明显的差异。西方人讲究对价和契约,易于形成直接的社会交换关系,中国人讲究面子、人情和关系,易于形成间接的社会交换关系。文化对财税制度的选择及其运行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作者曾经做过系统阐述,⑦此处不赘述。
3.社会治理差异。在不同的文化影响下,西方倾向于自治,靠自己、靠自愿合作。而中国倾向于他治,人民更希望明君圣主、贤吏好官来为民做主。这是导致中国政府职能范围比较大的重要原因。
4.经济差异。主要表现在所有制上,西方主要是资产私有制,而中国主要是资产公有制,表现为国有制或政府所有制。如果仅仅以私有制为主经济社会的理论概念来观察分析以公有制为主经济社会的事实,不可避免会出现偏颇。
(二)中国政府的特性
以上四个方面的差异,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对于政府差异,则少有人涉及。中西对社会管理中心都给予“政府(Government)”的名称,甚至官员名称及其层级也可互译,但其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被忽视了的政府差异是当代中西差异的核心部分,下面从中国和美国比较的角度阐述中国政府的特性。
1.“物业公司”与“资产公司”的差异。如果将政府比作公司的话,美国的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是“物业公司”,而中国政府是“资产公司”。美国的各级政府几乎不拥有可变现的大额资产,它们不拥有大量的土地、金融资本、企业资本,仅仅拥有办公楼、国家公园、博物馆等少量资产。中国政府则是一个特大型的资产公司,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即国有,实际上为政府所有,故政府是最大的业主,拥有最多的资产。以土地和金融资产为例,中国的城镇实行土地产权国有,农村土地产权集体所有,但国家在需要时可以征用,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央汇金公司公布的信息,当前国有金融资本大约为4万亿~5万亿元,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占全部金融资本的比重为60%~70%,如果包括非金融国有企业入股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股本,金融行业国有资本占比则在80%左右。⑧拥有这样庞大的资产体量在世界各国政府中首屈一指。
2.众多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单一无限责任公司的差异。美国各级政府是相互独立的物业公司,而中国的政府资产公司是无限责任公司,且仅此一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截至2012年美国共有89 004个地方政府,包括19 522个自治市、3031个县、16 364个镇、50 087个特别区,加上1个联邦政府、50个州政府,共有89055个政府。⑨尽管存在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或补助,但它们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如果需要合作就通过订立契约进行;如果产生纠纷就通过法院来解决,不存在上级政府指挥、协调、命令下级政府的情况(实际上不存在“上级”、“下级”概念和事实),因此它们应该算是89 055个独立的物业公司,这些公司从法律上讲如果出现资不抵债就会破产,实践中也经常发生一些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因此每年政府数均有增减。中国的情况则不相同,中国政府公司其实只有一家,但拥有很多分公司。一类分公司名称叫“政府”的体系,即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属还有地市、县、乡镇政府等分分公司,它们之间是层层的隶属关系,下级政府的官员实际上由上级任命,下级要按上级的统一指令行事。另一类分公司属于国有资产体系,包括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公办大学等,它们实质上是资产公司的专业部门,统一按上级指令最终是按中央指令行动。虽然看上去(并且法律上)这些分公司、分分公司都是独立法人,但实际上责任是连带的,下级公司若出现资不抵债即由它们依附的上级政府或部门解决,或者由上级单位动员兄弟地区或部门援助解决,或最终由中央政府买单。因此,这样庞大的一家公司实质上是无限责任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还有一处模糊地带,就是农村。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政府可征用,因此最基层的村委会并不是独立的公司,而是依附了这个特大型资产公司,其发展状态如何取决于其从这个特大型资产公司获得资源的多寡。是把农村村委会当作各个独立“公司”看待,还是一视同仁地将其看作整个资产公司下的一个个分分公司,将会主导我们将来农村改革的思路。本文暂把农村称为半分公司。于是,一个特大型的拥有许多分公司、分分公司的无限责任资产公司、许许多多半分公司,加上许多大小不等独立法人(主要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构成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3.人民与“公司”关系的“外部性”和“内部性”差异。美国各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众多独立“物业公司”和辖区业主或服务对象的关系,属于你我有别的外部关系;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关系,是一个特大型资产公司内部“经理人”和全体股东的关系,也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属于利益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在美国体系下,业主对物业公司的谈判势力较强,美国各级的议会可以看做是业主委员会,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预算收支问题,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决定税收规模和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成员均通过党派竞争推举候选人、经业主选举产生。物业公司的职责仅是确保公共产品的提供,让社会机制能够正常运转,不干预业主内部事务。当业主对物业公司不满时,可“用手投票”更换政府领导人,也可“用脚投票”迁移去其他地区,让辖区内的政府破产,理论上联邦政府也可因资不抵债而破产,个别政府破产不影响其他政府的存在。在中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大公司内部“雇员”与“雇主”的关系。“雇主”是集体,其成员选择采用老雇主选新雇主、上级雇主选下级雇主、雇员参与并认可等选能任贤的办法。雇主集体成员需要自省自律,树立对股东负责的信念,以雇员(也是股东)整体利益为导向,实现把资产公司蛋糕做大并尽量公平地分配蛋糕的共同愿望。政府对全体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只有当多数人民难以认同这个政府时,政府才会整体瓦解。一旦政府瓦解,就意味着人民共同所有的特大型资产公司破产,人民作为股东和雇员将承受多元损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般情况下,人民也不会让与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这家特大型资产公司破产。由于资产公司内部存在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不存在个别政府破产问题。中国政府的权责以及生命力远大于美国联邦、州和众多地方政府。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是一个中国全体人民共有的特大型无限责任资产公司,也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物业公司职责。
(三)中国政府特性和重大经济事件的不同后果
正是因为许多专家学者忽视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特性,简单地采用西方固有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中国、预测中国,结果往往与事实大相径庭。相反,只要充分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种种特性,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许许多多重大经济事件的后果为什么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例如政府债务、房价高涨、土地财政。
学术界多数学者基于一般经济学分析思维和出于对西欧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出现联邦政府停摆危机的关注和担忧,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弄不好也将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笔者当然不认为地方政府可以无限借债,但学术界多数人的观点也不无偏颇。其偏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的特性。在西方体制下,政府借债只能是公债,公债靠税收归还,一旦人民即业主不同意增税,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解决政府开支不足问题,这个办法遇到债务上限就不可持续,主权债务危机就会爆发。在中国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是特大型资产公司的分公司,拥有土地等巨额资产。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务是以资产为依据的,不是公债。按照会计学常识,只要发行或欠下的债务没有超过其拥有的资产数额,就不存在资不抵债的债务风险,更谈不上债务危机。更何况中国和西方国家借债的用途不同,西方国家借债用于公共产品提供,用于公共消费。中国地方政府借债主要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创造了新资产的同时还实现了其他资产的保值增值。此外,在中国由于预算编制和执行往往留有余地,加上时间差,各级政府和单位存有大额沉淀资金,按照经验数据,较发达地区和资金量大的部门其沉淀下来的资金相当于一年的预算收入。这些资金可以被看成是“隐性资产”,是部门或地方政府承担“隐性债务”的依托。学术界在计算地方政府或部门隐性债务时,忽视了隐性资产的存在,扩大了净债务数额。
对高房价及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存在同样的情况。多数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和西方国家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就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的逻辑,也认定中国房价高涨必然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笔者不认为房价越高越好,主张房价要平稳,但也不敢苟同多数学者的上述逻辑。上述逻辑同样忽视了中国政府的特性。在西方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一般私有,政府不拥有大量资产。公民购房时大量依赖银行贷款,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时,购房者还不起债,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引发连锁反应,达到一定规模就爆发金融危机。出现危机时,政府只能通过借债增加财政赤字的办法救助,这个力度是非常有限的,且后续负面影响很大。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主要金融体系为国有,实际上是政府组成部分,国有银行一旦出现呆坏账,政府可统筹兼顾,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待经济复苏,资产升值,又会实现经济平衡和增长。中国的国有银行基于政府信用,实质只是这个特大型资产公司的专业部门,以全民为后盾,故而出现类似于次贷危机情况的概率是很小的。如果利用好这一优势,中国完全可以拥有相较西方国家更长的经济繁荣周期。基于上述讨论,中国不用担心房价过高后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金融危机,也不需要简单地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办法实行房地产市场调控,而是可以更自主地让市场对房地产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职责是建立让房价平稳的机制(如破除土地供应垄断和房屋开发垄断、禁止销售毛坯房让房屋不仅是投资品等),而不是直接去控制房价。
学术界对土地财政一片骂声,认为土地财政是不合理的、是分税制下的无奈之举,不是一种正常的可持续的经济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手,已成为当前中国房地产投机泡沫积累起来的重要原因。⑩土地财政中隐含了寻租、土地资源利用代际不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财政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11)土地财政扭曲了政府职能,削弱了宏观调控,加大了金融风险,加剧了社会不稳定隐患。(12)
土地财政正面的实际经济后果与完全负面的理论评价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学术界对土地财政做出几乎一致的完全否定的看法,是因为学者们被政府只能是“物业公司”并且只能提供公共产品的思维定势固化了,对政府从事经济活动,甚至“卖地”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哪有政府卖地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中国政府的特性,只看到政府这个名称,没有见到政府的实质。根据前面分析,既然中国各级政府是资产公司,那么土地作为政府资产公司重要的资产,政府作为“地主”适时运用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和天赋资源,拨动其他资源,发展经济,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美国的土地是私有的,在国家发展历程中自然由私人开发,而中国的土地为政府所有,当然应该由政府这个资产公司主导开发。土地财政实际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土地滚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推动城镇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机制;2.通过土地资产变现,增大市县财力,加速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城乡差异,改善民生;3.通过土地开发经营过程,提升土地价值,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中国政府这一特大型资产公司的资产总量。土地财政也是可持续的。中国幅员辽阔,户籍角度的城镇化进程刚刚过半,地理角度的城镇化还只是点的进行未实现面的展开,未开发的土地还有很多。且中国的建筑寿命普遍较短,即使地理角度的城镇化完成,还将面临旧城改造。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是还有房地产市场而且某些时候还很红火吗?因此,关于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可否认,当前土地财政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土地供应垄断是导致房价只升不降的原因,但这是垄断问题,而不是土地财政本身的问题;全民土地,但市县受益,某些财力雄厚的地区因此而过度提供公共产品,土地收益在这个特大型资产公司内部的分配不合理,一定程度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低价征用、高价出售使农村集体土地收益被严重剥夺,需要通过土地市场城乡一体化来解决。这些都属于运作体制、分配体制、管理体制的问题,不能以此否定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些问题通过完善分税制也可以化解。
三、理性并全面地分析评价分税制
对中西差异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政府特性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使我们看到在判断财政体制是否合意时,除了要根据经济学一般标准还要根据基于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背景的评价标准,从而才能客观全面把握现行分税制的情况及其发展方向。
(一)分析评价分税制的标准
经济学关于财政体制是否合意有三项一般标准,即效率、公平和确定。
效率标准,指边际税收等于公共产品边际成本,满足纳税人偏好,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讲规模经济,防止被迫性区际移民等,通俗地讲就是要恰到好处、没有扭曲。
公平标准,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避免区域差异扩大等,通俗地讲就是在分配财政利益时能够使老百姓权利共享、受益均等。
确定标准,强调规定明确、政策透明,相对稳定,可预期,以减少行政成本、防止腐败。
在政府仅仅是“物业公司”的社会中,这些标准就足够了。但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政府性质的差异,这些标准就不够充分了。在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着眼点不是独立“物业公司”之间的你我关系,而是特大型资产公司内部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除上述三项标准外还要加上五项标准,包括:
第一,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政府是资产、资本的最大所有者和经营者,经济发展由政府主导,财政体制是否合意要看是否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使蛋糕做大,公司内部所有成员利益增加,这是判断财政体制好坏的第一标准。
第二,是否有利于政治稳定。就是能否避免长期以来重复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散就乱的局面,避免过分集中也避免诸侯割据。特别要避免各级分公司都成为独立公司,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一特大型资产公司很容易陷于瓦解。
第三,是否有利于达到区域均衡。在中国,因为自然禀赋等原因,区域差异比较大,财政体制必须致力于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如果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这些差距,就违反了公司内部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会降低公司成员对公司的认同感,严重时会导致公司离散。
第四,是否改善了民生。即是否使教育、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居住条件等得到不断改善。公司的利益增加应当让全体公司成员共享,通过民生改善,让公司成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司的存在和发展才有意义。
第五,是否节约了财政成本。财政收支决策、运行,财力在各个分公司、分分公司的分配,需要付出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些成本是对资源的虚耗,要厉行节约。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是非对称型财政体制
笔者曾经提出并系统论证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是“非对称型分税制”。(13)其目标是正确处理中国政府这一特大型资产公司内部不同层级分公司的利益关系,既保证资产公司整体稳定,又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其基本特征是中央税占全部税收总额的大部分、地方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大多数。1.以中央税为主体的税种划分。特别是流转税,税负可转嫁,不宜做地方税,而要适当地先集中后分配。不一定建立地方税体系,即使要建,地方税体系也不必全国“一刀切”,而要依照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分别制定。2.税收管理权以中央为主。3.税款的使用以地方为主。
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要建立“对称型分税制”的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观点认为,既然从政治体制上实行分级管理,财政也应当实行分级管理,每一级政府均有其独立的财政,相应地要建立地方税收体系,获得能满足其财政支出需要的税收。这是许多人认同的观点,已成为处理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的重要理论原则。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提出“七个一级”即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习惯思维,即收支对称、分级包干。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一种办法(总额分成、定额或比例上解、定额补助或分税)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后各管各的,包干到底、自求平衡、分灶吃饭。
首先,上述观点存在认识误区。这是一种对美国体制做了简单化、表面化观察而得来的认识。在美国,各层次政府为独立的物业公司,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可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由中央获得大部分收入,然后通过一定方式在各层级政府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在美国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税系,联邦以所得税为主、州以销售税和附征的所得税为主,而地方政府形成了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系。确实形成了“七个一级”。这是美国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制度形成基于美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即便如此,美国的分税制也不是完全对称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其本级税收收入只占其预算开支的一部分,联邦和州的转移支付是它们的重要收入来源,据统计,2011年美国州和地方财政总收入中来自联邦转移支付的部分达24.7%,通过州和地方税系收取的税收只占51.2%,其余为规费收入;地方政府层面,来自联邦和州的转移支付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为33.19%,来源本级政府税收收入占34.63%,其中房地产税占25.7%。(14)在中国,由于政府是一个特大型的资产公司,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无限连带责任关系,不可能通过“七个一级”实现真正的分灶吃饭。即使刻意去做了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也是名不副实。
其次,不符合效率原则。即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存在,相当多的地方通过地方税体系获得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其财政需要。更何况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让各地财力自求平衡,会使区域差距恶化,轻则造成市场分割,重则导致地区割据,还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地方为了自求财政平衡,必然热衷于举办一些短期内见效、收入大的项目,使某些从全国看来要限制发展的落后企业、落后产品,在地方成为保护扶植对象,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情况难以有效制止,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对地方政府实行对称型分税制财政体制会产生很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
再次,不具备实行的税制条件。建立对称型分税制财政体制,还存在税制结构上的障碍。要让一级政权均有独立的地方税体系,且能够做到收支自求平衡,前提是通过地方税体系获得的收入能够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而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主要税源(如所得税、增值税等)分布存在层次均衡性,次主要税源(如财产税、单环节流转税)分布存在区域均衡性。所得税比较符合层次均衡性的要求,即每一级政府均可同源征收,但中国目前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最大宗的税源采取流转税征收的方式,流转税具有可转嫁性,负税人与纳税人往往不一致,纳税地与负税地也往往不一致,各级政府对同一税源多级征税会产生很大扭曲,故对流转税只能采取一级政府征收的办法,道道课征的流转税(增值税、传统全值流转税)最好由中央政府课征,然后采取纵向分配的办法。
次主要税源是否存在区域分布均衡性是地方政府能否形成主体税种的关键。只有区域经济平衡,单环节的流转税(如零售税)、财产税的税源分布才能处于均衡状态,一方面才能做到负税人居住地课税,从而建立纳税与用税(提供公共产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财政公平;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不同区域的政府能通过地方税获得基本收入。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次主要税源的分布很不均衡,发达地区税源很大,而相对落后地区税源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一级政权通过一级地方税体系,不可能实现基本财政收支的平衡。总会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需要上级的支持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三)对现行分税制的总体评价和分税制加分益制的设想
目前中国财政体制属于不完全的非对称型分税制。从一般预算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各居其半,但中央财政收入很大部分通过转移支付成为地方收入重要来源,最终财政支出是地方占大部分(约85%)、中央占小部分(约15%)。
根据前述评价标准,仅从一般预算角度,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其大架构、大格局合适。根据实证研究成果,分税制与高速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满足第一项标准即经济发展。近20年中国政局稳定,中央地方关系整体协调,符合政治稳定的标准。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硬件设施、教育硬件设施、城市其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符合民生改善的标准。
但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般预算领域的问题。表现为不能有力地促进区域均衡,转移支付没有起到纠正地区差异的作用;由于实行两套税务系统、转移支付制度不够透明规范导致“跑部进京”现象严重,财政成本增加。二是不完全带来的不公平问题。目前的财政体制只是一般预算的财政体制,还没有综合考虑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基金预算及国有资本预算、社会保险预算。目前的分税制仅把一般预算的收支加以安排,而不包括土地财政收益、其他国有资产收益。特大型资产公司的资产人民共有、风险共当,但收益却是部分人群独享,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例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土地财政收入仅归拥有卖地权的城市政府和县级政府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全民投入、全民担当风险,企业经营不善造成损失甚至破产皆由这个特大型资产公司负连带责任,实际上是由全民买单,但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的高管独享。
进一步完善的目标是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完全的非对称型分税制加分益制的财政体制。
首先,管理具有现代性。从制度、管理和程序方面,完善一般预算领域的分税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税收分享、转移支付等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防止腐败、降低运行成本。但任何改革都要谨慎,谋定而后动,防止朝令夕改,保持制度的长期稳定和可预期,更能减少民众福利损失。
其次,资产增益全民共享。未来的财政改革,不仅要实现一般预算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要实现全民资产增益人人共享。既然中国政府是一个特大型资产公司,全体人民都是公司的股东也是雇员,作为雇员应当获得由市场决定的工资,作为股东应当获得资产收益,因此“公司”获得的资产增益和其他收益应当人人共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税收以外的资产收益特别是土地财政净收益、国有资产净收益,也应当按照中央得收入大头、支出大部分划拨地方的非对称原则安排。资产收益的大部分进入中央户头,可设统一的资产预算,也可保留目前的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分别核算;中央确定其使用方面和政策,原则上以增加社会保险金、建立中国公民国有资产收益账户等直接间接方式让中国人民共享,让人民通过切身的增益享有,体现对全民资产的所有,直接分享国家发展的利益,增加对政府即人民自己的特大型资产公司的认同和责任。款项通过中央下拨方式交给地方各级政府或部门进行具体分配。政府同时鼓励富裕家庭把他们分到的国有资产收益捐赠给较为贫困的家庭。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完全的非对称型分税制加分益制的财政体制,达到特大型资产公司内部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全体人民参与建设也参与发展利益共享,整个社会实现和谐的理想境界,让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建立在坚实的财政体制上。
①QIAN,Y.Y.& WEINGAST,B.R.,1996,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olicy Reform,1(2); QIAN,Y.Y.& WEINGAST,B.R.,1997,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1(4); QIAN,Y.Y.& GERARD,R.,1998,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5); JIN,H.H.,etc.,1999,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Working Papers 99013,Stanford University; ZHANG,T.& ZOU,H.F.,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7(2); JIN,J.& ZOU,H.F.,2005,Fiscal Decentralization,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signments,and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6(6);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5卷第1期;刘玲玲、冯懿男《分税制下的财政体制改革与地方财力变化》,《税务研究》2010年第4期。
②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③王振宇《分税制财政体制“缺陷性”研究》,《财政研究》2006年第8期。陶勇《分税制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税务研究》2008年第4期。陈宪、张恒龙《分税制改革、财政均等化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张文春、王薇、李洋《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10期。匡小平、肖建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财政体制原因分析》,《财政研究》2010年第12期。浙江省财政厅课题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发达地区财政影响分析——基于江浙沪数据》,《财政研究》2013年第2期。
④周彬、杜两省《“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上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8期。张双长、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基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视角》,《财政研究》2010年第7期。宫汝凯《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城镇房价水平——基于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2年第8期。吕炜、刘晨晖《财政支出、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投机泡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财贸经济》2012年第2期。黄国龙、蔡佳红《“土地财政”的分税制根源及其对策》,《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⑤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张恒龙、陈宪《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经济科学》2007年第1期。江新昶《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财贸经济》2007年第6期。伏润民、常斌、缪小林《我国省对县(市)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基于DE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贾晓俊、岳希明《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褚敏、靳涛《分税制后的中央转移支付有效率吗?—基于中央转移支付对地区间增长公平与效率的检验》,《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涂立桥《中央转移支付的财力均衡效应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3年第5期。
⑥余治平《红色学者:思想与人生的传奇之旅——梁志学教授访谈录》,《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
⑦杨斌《中西文化差异与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3年第5期。
⑧周星旺《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面临结构调整》,《中国金融》2013年第14期。
⑨http://www2.census.gov/govs/cog/g12_org.pdf.
⑩宫汝凯《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城镇房价水平——基于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2年第8期。吕炜、刘晨晖《财政支出、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投机泡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财贸经济》2012年第12期。
(11)程瑶《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土地财政》,《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1期。
(12)侯作前、刘明明《从“土地财政”着我国地方财税制度的问题与完善》,《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3)杨斌《西方国家分税制的比较》,《涉外税务》1993年第4期。杨斌《非对称型分税制:我国分税制的改革方向》,《中国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杨斌《关于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依据的论辩》,《税务研究》2006年第5期。
(14)http://www2.census.gov/govs/local/summary_report.pdf.
标签:分税制论文; 土地财政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中央财政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地方税论文; 财政学论文; 地方财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