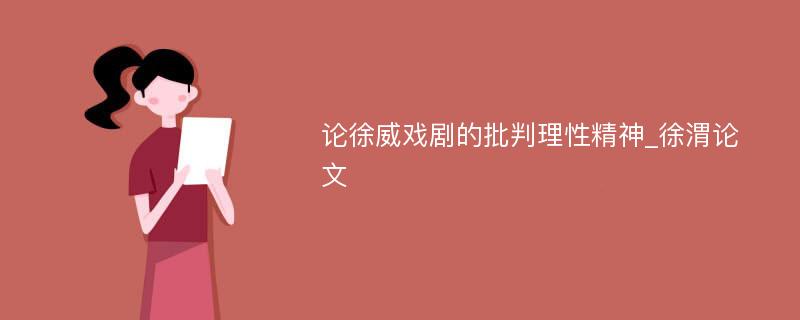
试论徐渭戏剧的批判理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戏剧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四声猿》为代表的徐渭戏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而且独特的地位。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启蒙家,徐渭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理论上都为中国戏曲投射出一道亮丽的光彩。道人在《四声猿原跋》中说:“不特宜玩其词,更应辨其声”,本文正试图通过蕴藉在徐渭戏剧创作及理论中的批判理性精神来打开一扇研究徐渭的窗口,以《四声猿》为中心(因《歌代啸》作者尚有争议,故不作本文论述重点。但笔者个人倾向于该剧为徐渭所作),兼及其他,作散射状论述,共同完成对徐渭作品中批判理性精神的理论建构。
一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潮的形成无不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哲学背景;另一方面,这种文艺思潮一经形成,又会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产生巨大反作用力,推动(或滞缓)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赵景深先生指出:“徐渭的剧作代表了明代杂剧的转变”这不仅因为徐渭戏剧曾使明万历以降渐呈衰势的北杂剧重现生机,更是由于徐渭戏剧中所洋溢的批判理性精神恰恰契合并投射了当时进步社会思潮的初端。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兴起,中国资本主义在明中叶开始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李贽为代表的浪漫思潮以风起云涌之势由哲学向文学艺术领域迅速蔓延。李贽“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他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倡异端,揭发道学”在这种哲学空气的涵养下,涌现了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文学艺术家,“这些人物之间,互相倾倒,赞赏,推引,交往,如袁中郎之于徐渭,汤显祖之于三袁,徐渭之于汤显祖……都有意地推动了这股浪漫思潮”。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热情赞赏了徐渭的人格和艺术,汤显祖则面对徐渭戏剧发生“安得生致文长,自技其舌”的沉重叹息……我们反观徐渭戏剧,便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启蒙思潮的浸透与影响,才奠定了徐渭戏剧中批判理性精神的主色调。
徐渭把“贱相色,重本色”视为艺术的核心,并使之成为自己戏剧创作的贯串与主导——这与李贽所极力倡导的“童心说”如出一辙:“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徐渭注重唯真是求的“本色”,李贽呼唤“绝假纯真”的“童心”,由此可见徐渭戏剧中所蕴藉的批判理性精神与当时整个社会启蒙思潮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正是源于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涵养,才为徐渭戏剧批判理性精神的存在找到了适合的土壤。
我们在分析社会哲学空气对徐渭艺术风格之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同样不应忽视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建构的内动力——这就是徐渭坎坷奇异的生命历程和怪诞疏狂的个性特征——这几乎是每一个研究徐渭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少有才名,后虽屡应乡试而不第,空怀经世之志,书剑飘零而终。“不为儒缚”的思想性格改变了他的仕途命运,而这种悲惨的人生境遇又为其艺术创作深深地埋下了批判理性的种子。徐渭对于陈腐的封建观念和权贵们的鲜廉寡耻深恶痛绝,恨之入骨。37岁时,徐渭应邀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作书记,“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显示了他出众的才华。后因胡获罪下狱,徐渭清名受污,一度发狂。45岁时他写下了《自为墓志铭》,曾“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锥碎肾囊,皆不死”,后因疑杀继室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经“张阳和力解,乃得出”,晚年变卖书画谋生,终年72岁……
一个自由的灵魂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与戕害下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人格得不到伸张,个性得不到解放,徐渭“不为儒缚”的民主理想被严酷的封建现实击得粉碎——批判理性精神也正由此而诞生。我以为,心理承受力的崩溃以致病态发狂只是徐渭难于偕俗的强烈个性的畸型反映,这并不就意味着由此便消除了其作品的理性精神。恰恰相反,徐渭在戏剧创作中“捏奇趣以吐块垒,衍旧闻而判时事”,将人生的悲惨与不幸凝成一部“意气豪达”的“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以理性的思辨与觉悟暴露社会时弊,张扬人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使徐渭戏剧富有深刻的启蒙意义和博大的思想内涵。
二
徐渭自己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在这里,他虽没有提及他的戏曲创作,但一部《四声猿》所带给当时及后世的深刻影响,足以使徐渭名噪古代剧坛,
“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四声耶?”徐渭将自己四个独立的戏曲剧本合集名为《四声猿》,其对现实的批判讽喻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四声猿》中每一部戏都立足当世,直面现实,深刻地揭露并批判社会形态及观念上的种种痼疾,大胆运用变形、夸张、离奇、象征等艺术手法,使批判理性精神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和抒展,正所谓“借彼异迹,吐我奇气”。如果容许我们用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概念来比较中国戏剧,那么在中国,相似特征的戏剧思潮至少被生活在十六世纪的徐渭提前了二百多年!(当然,在欧洲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先声的还有十八世纪兴起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潮)所不同的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对社会的推动力更大,而中国的启蒙戏剧思潮不过是黑夜中一闪即逝的一束光点,旋即就被更黑暗的政治现实给吞噬了。
《四声猿》凝聚了徐渭对现实社会热切的关注和冷峻的思考。他试图将现实社会对他的束缚、压迫乃至异化过程全部投注到他的戏剧创作中。现实中的徐渭“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荡似玩,人多病之”诸如此类不偕世俗的强烈个性使他无法超脱现实,而现实的厄运又在一次次荡涤他自由的心灵,使他更清醒、更理性地认识世界,让他能在戏剧中听听自己灵魂真实的控诉。
徐渭全部戏剧无不显示着批判理性的光芒。
在《四声猿》中,《狂鼓史》之于封建反动统治者“指驴为马”的痛骂,其意在于“借正平身后一骂,以发挥其抑郁不平之气”;《玉禅师》则向后人昭示了封建宗教的伪善面目,并由此引申出对“官法”与“佛法”的现实社会矛盾斗争的独特思考;在《雌木兰》和《女状元》中,徐渭塑造了一文一武两个光彩照人的巾帼形象,向“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社会现实和传统观念发出猛烈的挑战。他提出的“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儿”,正是这种创作题旨的直接体现。
不仅如此,徐渭还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审视和评价,投射在剧本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情节结构中,共同构筑完成多层的复杂戏剧主题。
在《狂鼓史》中,徐渭曲折地表达了悼沈炼、抵严嵩的思想倾向。沈炼作为徐渭的同乡和姊丈,又被徐渭引为知己,他因上疏参劾严嵩十大罪状而被严氏集团所斩杀。沈炼的死对徐渭触动极大,徐渭事后曾在许多诗文中以祢衡喻沈炼,表达了对严氏反动统治集团的义愤和仇视。更可贵的是,徐渭不仅仅囿于通过剧作宣泄个人情绪,而是用理性的精神将个人悲愤之情融为一个时代的呼声,上升为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创作主题。
“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
“害贤良呵,有百万来还添上七八,杀公卿呵,那里查”
在这里,严氏集团屠戮无辜、迫害忠良的反动面目被揭露得微毫毕现,入木三分。徐复祚称该剧是:“有为之作也,意气豪侠,如其为人”诚信斯言。
《玉禅师》是徐渭“早年之笔”尽管孟称舜称此剧在技巧上还“微有嫩处”,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徐渭鲜明的个人思想倾向。徐渭早年曾慕过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叩于禅……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这些经历不能不对徐渭的宗教思想产生作用。尤其是他曾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寓居玛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读所,伴其读”,时年徐渭31岁,这些经历使其对佛教生活由间接的“耳闻”转入直接的“目睹”和“身历”,想来一定会对徐渭创作《玉禅师》提供丰富而真实的素材。徐渭的《玉禅师》摆脱了一般“神仙道化”戏的窠臼,独辟蹊径,在剧中引入了对宗教本质的理性思考。在明统治者“崇道抑佛”的政策冲击下,佛教自身欺世虚伪的特点也日益暴露出来,逐渐滑入堕落的泥潭。在剧中,修行十年的玉通和尚只因未去庭参新任府尹柳宣教而被柳设计犯色破戒——戏一开始,就提示了“官法”的霸道与“佛法”的虚弱这一尖锐的社会矛盾,而玉通在妓女红莲的引诱下自甘堕落的心理行为,一方面将人性的真实呈现出来,使“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又深刻讽喻了佛教的伪善本质和僧侣的假道学面貌。红莲深夜叩门投宿,玉通即问懒道人“那妇人老也小?”当得知“止不过十七八岁”且“生得绝样时”时,玉通就已动心,偏又卖乖地说“叫她去,可又没有处,也罢……”于是放她入寺。夜半,红莲百般引诱欲使玉通破戒成奸,玉通先是慌忙阻止“快不要,快不要,快到窗儿外去”,但此时,我们分明可以听到一个长期不近女色的和尚在欲望和理智的两难决择时发出的“咚咚”的心跳声。终于,情欲战胜了理智,虚伪的宗教防线一击即溃。
“当时西天那摩登迦女,是有个神通的娼妇,用一个淫咒把阿难菩萨霎时间摄去……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
玉通轻易地原谅了自己的荒唐。从这段自嘲中,僧侣的假道学面目毕现无遗。
《玉禅师》第二出写了玉通抱怨投胎为柳宣教之女柳翠,作了妓女,后经月明和尚点拨自悟,终成正果。在这里,徐渭以点睛之笔对宗教本质作出了理性的归结——破除了宗教的神秘色彩,通过对佛界与尘俗的转化过程的描写,还佛文以“一丝我相”的真实面目。恰如月明和尚叙说的“法门大意”。
“俺法门象什么?象荷叶上的露水珠,又要沾着,又要沾不着;又象荷叶于淤泥藕节,又不要龌龊,又要些龌龊……”
从而揭示出“佛菩萨尚且要投胎报怨,世间人怎免得欠债还钱”的思想主题。看来,徐渭写佛界,其根本目的还在于观照社会现实。
钟人杰在《四声猿》引中说徐渭戏剧“皆人生至奇至怪之事,使世界骇咤震动者也”。的确,徐渭善于捕捉“至奇至怪之事”敷衍成戏。如果说《玉禅师》和《狂鼓史》描写了飘渺虚幻的佛界与阴间,那么徐渭在《雌木兰》和《女状元》中,则将笔触投向人间现实,并且直指封建社会中具有启蒙意义的妇女问题。
徐渭是一个“以旧事衍新篇”的能手。从这种对戏剧本事的开掘、加工与演绎过程中,徐渭自觉地将个人的经历、志趣融入其中,从而也就使徐渭戏剧呈现出深层意义上的多主题。
徐渭亲历过明代抗倭斗争,并对北方抵抗鞑靼入侵的战争十分关注,表现出炽烈的爱国热情——这些生活对他创作《雌木兰》不无影响。《雌木兰》取材于汉乐府诗《木兰辞》,但在徐渭剧作中增加了出场人物,延展了故事情节,并深化和升华了原叙事诗的主题思想,用理性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封建观念,发出了“裙衩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的社会呼声。
另据载,在徐渭生活的时代,确也出过象木兰一样的巾帼抗倭英雄,如广西少数民族军队里就出过一个田州瓦氏,作战颇称英勇……等等。可见,这些现实生活中“至奇至怪之事”带给徐渭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灵感,更提供了一条理性思辨的藤蔓。在《雌木兰》中,徐渭针对时弊提出许多解放妇女禁锢的先进思想,例如在第一出中:
“生脱下凌波袜一弯,好些难,几年价收拾得凤头尖,急忙的玫抹做航儿泛,怎生就凑得满帮儿楦。”
类似这种主张“放脚”的启蒙思想,能由生活在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徐渭揭示出来,尤为难得。
《女状元》较之《雌木兰》在情节结构上更加复杂离奇,妙趣横生,表现视角更为独特,批判指向更为犀利大胆。徐渭在剧中塑造了一个集才子、佳人于一身,“论才学,好攀龙”“既工书画琴棋,兼治描鸾绣凤”的全才女子黄崇嘏的形象。黄因家道中落,穷居一寓,自信“若肯改装一战,管倩取唾手魁名”,遂应举而中状元。他不仅文艺出众,而且“吏事精敏”,颇得周丞相赏识,欲将女儿许配给“他”。后被识破女身,与丞相之子成亲。
黄崇嘏的形象是徐渭审美理想的体现者。“才子佳人信有之,一身兼得古来谁?”——这是徐渭对妇女人格精神的张扬和呐喊。值得一提的是,徐渭还结合自己“举于乡者人而不一售”的坎坷经历,将笔锋刺向封建科举制度的流弊。他认为腐败的科举制度是导致吏治腐败的根源,对此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喻,并对合理的科举制度提出了大胆的构想:
(生)诸生,上年这场屋中主司命题,大约遵奉前规。你每诸生对时,可也多循旧套。况本朝向来以词赋取士,近日乐府就是词赋之流。我如今要洗一洗这头巾的气习,只摘蜀中美谈雅事为题,令诸生各赋一乐府,就当面吟咏,这也当面品评。
——《女状元》第二出
在同一出中,徐渭又借试官周庠与考生胡彦的一段对白,对这种科场陋习尽情奚落:
(外)“得”字不押韵了。(丑)韵有什么正经,诗韵就是命运一般。宗师说他韵好,这韵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师说他韵不好,这韵叶的也是不好的。运在宗师,不在胡彦。所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外)也要合天下的公论。(丑)咳!宗师差了。若重在公论,又不消说“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了。
笔者在此不惜大段引过原文,是缘于笔者认为这不仅代表了徐渭对新的科举制度的强烈呼声,更切合了当时进步社会思潮的脉搏,成为当时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徐渭批判理性精神的写照。徐渭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一跃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其剧作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自然也会因此而延展和深入。
三
“艺术家的独创性不仅见于他服从风格的规律,而且还要见于他主体方面得到了灵感,因而不只是听命于个人的特殊的作风,而是能掌握住一种本身有理性的题材,受艺术家主体性的指导,把这题材表现出来,既符合所选艺术种类的本质和概念,又符合理性的普遍概念”。
黑格尔在论述艺术家的独创性时作了如上阐释。我们结合徐渭戏剧便不难发现,徐渭在戏剧形式上所作的诸种尝试和革新,其实正体现了由内容的“至奇至怪”而带来的在形式上的“不执于法,亦不局于法”,渗透着徐渭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扬弃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在这里,徐渭将破格以求的艺术形式纳入批判理性的整体戏剧精神框架中,使形式成为内容的有机部分,而不再是简单的附属关系或决定关系。
我们知道,北曲杂剧在明中叶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尽管时人不乏杂剧创作,但由于舞台演出实践的减少,使北杂剧更多地沦为案头之作,终难挽回曲高和寡、名存实亡的现实结局。徐渭大胆提出“本色”的戏剧观,重新重视戏曲的舞台特征和市民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杂剧的衰颓局势。
徐渭认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者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这种观点既是对“今人时文气”的理性批判,又为戏曲重新接近市民观众铺展了一条明路。徐渭认识到戏剧只有经过观演过程的推动,才可能作用于普通市民观众的思想情感,从而实现戏剧的社会存在价值,正所谓“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体现在创作中,徐渭这种对戏剧形式的审美追求是一始贯终的。
从对戏剧本事的选择与改造上看,徐渭“至奇至怪之事”的选题原则便体现了市民审美的求俗特征。市民文化给了徐渭丰厚的创作营养,徐渭又将其艺术地反馈给了观众,从而缩短了戏剧的审美距离。在徐渭戏剧中“俄而判鬼,俄而僧伎,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可谓无奇不有,这些题材又多取自民间,或演义故事(如《狂鼓史》)或西湖传说(如《玉禅师》)或乐府诗词(如《雌木兰》)或民间传奇(如《女状元》),既满足了市民观众的普遍审美要求,同时也使戏剧中的批判理性精神得以播扬和影响。尽管徐渭自己对其手段“不甚爱惜,才脱稿辄弃去”,但他毕竟还是肯定创作的社会价值的。
在《四声猿》中,徐渭大量运用民间俚语,务使“奴童、妇女皆喻”,甚至开创性地将《鹧鸪》等民间小调引入剧作。在结构体例上不拘一格,突破传统,少则一折,多则五出,使形式尽可能地适应内容的要求。诚如周贻白先生所言:“若绳之以元剧规律,皆为创例。”
徐渭还非常注重剧作的舞台动作性,深谙舞蹈动作在表演中揭示人物的独特功能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的剧场效果。在《玉禅师》中,出现了“打杭州话”的生活细节描写,并把根据民间上元节演出的“耍和尚”的舞蹈技艺表演融在剧本中。在《雌木兰》中,木兰出征前的演习枪棒武艺的动作提示……这些无疑丰富了剧作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同时观照了戏剧演出的舞台性。
王骥德在《曲律》中称徐渭戏剧“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又说他“好谈词曲,每右本色”。在这里,“奇绝”与“本色”看似一种对立关系,碍于我们认识徐渭戏剧的本质特征。然而我以为,“奇绝”与“本色”乃是统一于徐渭批判理性精神建构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二者是方法与目的的有机关联——正是徐渭对“本色”的艺术追求,才促使他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现实更本质的真实,也才使徐渭戏剧呈现出“奇绝”的艺术风貌。
当代作家史铁生说:“一切形式都是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方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对于徐渭也不例外。徐渭在戏剧形式上破格以求,“不执于法”,在本质上恰恰折射了他与“外部世界相处的方式”,同时也是蕴藉着批判理性精神的戏剧内容对形式的客观要求和反映。
四
纵观中国戏曲史,身兼剧作家与理论家的人并不多见,徐渭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徐渭戏剧整体的一部分,他的戏剧理论也直接受到明启蒙主义文艺思潮的浸染,呈现出批判理性的精神特征。在戏剧观念上,他主张“感发人心,歌者使奴童、妇女皆喻”的求俗性;并力求使戏剧实现象诗歌一样的“兴观群怨”的艺术审美功能和社会接受价值。徐渭的理论贯彻在他的剧作实践中,便形成了一种理论与创作相互观照的有机整体。可以说,徐渭的戏剧理论是徐渭戏剧中批判理性精神的外拓与发展。
徐渭针对晚期文艺创作中咬文嚼字、无病呻吟,就范于八股,受制于律条的恶劣风气作了理性的批判,提出“贵本色”、尚“真情”的理论呼声。“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己。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喻,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皆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入即席挥尘,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情弥易,传入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徐渭如此推崇真情,认为唯“真情”是达到“动人”的必然途径,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戏剧审美接受的根源。徐渭的戏剧创作也正是循着这条规律,有感而作,去矫饰,显真情,“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使创作主体完全融入客观形象之中。在此,我们不妨以李贽的创作理论来观照徐渭的创作道路,就会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之也。其胸中有如许无可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之所以赘述李贽的理论,是我以为,徐渭生活时代所掀起的文艺思潮,既使徐渭成为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这些人之间又是在互相启发、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凝成一种哲学文化空气。我们研究徐渭的戏剧理论也同样不应孤立地对待。笔者试图通过横向比较,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徐渭戏剧观的形成背景。
徐渭十分注重戏曲审美的市民文化属性。他始终把“求俗”作为其戏剧创作的追求目标。在对南北曲特点的比较中,徐渭曾多次阐释了戏曲创作应符合市民普遍审美心理的鲜明观点。“‘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守而不自觉……夫二音鄙俚之极,尚足感人于此,不知正音之感何足也?”在批判《香囊记》时,徐渭说:“与其之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主张“越俗越家常”“尤宜俗宜真”。在《四声猿》中,徐渭以这种“俗而鄙”的创作精神主导全剧——这也正是徐渭戏剧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徐渭的戏剧不仅囿于个人真情的抒发与表达,或沉溺于消极的人生宣泄之中,而“以一种较强的主体能动意识对自己所触及、所表达的内容,所展示的生活进行冷静的审视;以完善的自我,开拓作品的独特内涵;以挺立的人格向社会、向生活发言”。徐渭非常强调戏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在《答许口北》一文中谈到艺术的社会功用时说:“此事并无他端……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一诀尽之矣”,虽不是针对戏剧而论,但反映在徐渭戏剧中,这种对儒学“兴、观、群、怨”的文艺价值观的继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使徐渭戏剧在社会功用上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契合时代的主流,折射现实的思考,如他自己所说的“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
当然,徐渭在戏剧理论上的贡献远不止于上述几点,笔者仅把批判理性精神在徐渭戏剧理论中的侧重体现作为论述重点,对其理论作一提纲挈领式的简要归结,所以对诸如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内容均较少涉及。
结束语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不免可以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戏剧。
徐渭作为中国十六世纪伟大的戏剧家,他在戏剧中所体现的批判理性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浓缩,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本文试从徐渭戏剧中批判理性精神的形成背景;批判理性精神在戏剧内容中的体现;由批判理性精神作引导的对戏剧形式的改造与革新;理论与创作相互观照所体现出的批判理性精神……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勾划大概,探讨徐渭戏剧的批判理性实质。
诚然,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戏剧家,谁又能说:“我们已经把徐渭说尽了”呢?
编者按:本文中的引文出处,由于版面所限,不一一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