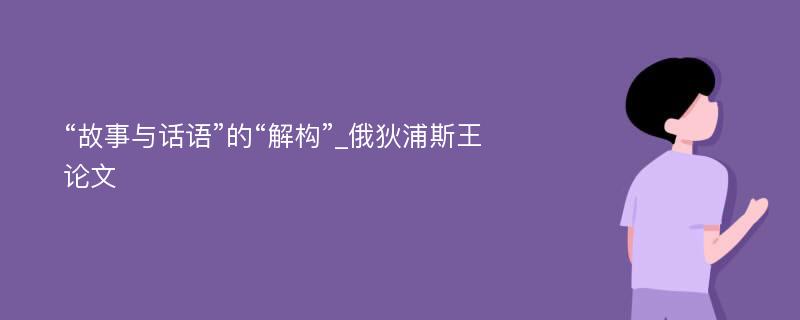
“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是著名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于1966年率先提出的。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叙事学界普遍采纳了这一区分,使之成为叙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171.)。30多年来,叙事学家们对这一前提广为运用、阐发和修正,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解构思潮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出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解构这一区分的努力。本文将剖析四位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分的解构,旨在清理有关混乱,揭示叙事作品的一些本质性特征,更好地把握作者、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乔纳森·卡勒的解构之“解构”
乔纳森·卡勒在1981年出版的《符号的追寻》一书中,以“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为题,辟专章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进行了解构。卡勒不是通过抽象论证而是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叙事学假定事件先于报道或表达它们的话语而存在,由此建立起一种等级体系,但叙事作品在运作时经常颠覆这一体系。这些作品不是将事件表达为已知的事实,而是表达为话语力量或要求的产物。”(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172.)卡勒举的第一个实例是《俄狄浦斯王》。通常认为这一古希腊悲剧叙述了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但卡勒提出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该剧,即并不存在俄狄浦斯弑父的事实,而是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使我们假定俄狄浦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卡勒提出的论据是:俄狄浦斯独自杀害了一位老人,位拉伊俄斯一位幸存的随从却说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当俄狄浦斯见到这惟一的证人时,并没有追问凶手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只是盘问有关自己和拉伊俄斯父子关系的事情。卡勒由此得出结论说:俄狄浦斯自己和所有读者都确信俄氏是凶手,但这种确信却并非来自对事实的揭示,而是由于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让人做出了一种凭空武断的推导。有趣的是,卡勒自己声明:“当然,我并不是说俄狄浦斯真的是无辜的,真的是受了2,400年的冤枉。”(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174.)从“当然”、“真的”等词语可以看出,在卡勒心目中,那位证人说凶手究竟是“一伙人”还是“一个人”对事实并非真的有影响。卡勒这么写道:
有神喻说拉伊俄斯会被儿子杀害;俄狄浦斯承认在一个可能相关的时间和地点杀害了一位老人;因此当牧羊人揭示出俄狄浦斯实际上是拉伊俄斯之子时,俄狄浦斯就武断地下了一个结论(读者也全跟着他的思路走),即自己就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他的结论并非来自涉及以往行为的新的证据,而是来自意义的力量,来自神喻与叙事连贯性要求的交互作用。话语力量的交汇要求他必须成为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他也就服从了这种意义的力量。……假如俄狄浦斯抗拒意义的逻辑,争辩说“尽管他是我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杀了他”,要求得到有关那一事件的更多的证据,那么俄狄浦斯就不会获得那必不可少的悲剧身份。(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p.174-175.)
在进行这番论述时,卡勒似乎忘却了这一悲剧是索福科勒斯的创作物。的确,索福科勒斯没有让证人说明杀死拉伊俄斯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但这只是因为在古希腊的那一语境中,神喻和其他证据已足以说明俄狄浦斯就是凶手。假若俄狄浦斯“要求得到有关那一事件的更多的证据”,索福科勒斯完全可以、也无疑会让证人更正自己的言词,说明凶手实际上为一人——如果他意在创作一部悲剧。这样,俄狄浦斯的悲剧身份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探讨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时,我们必须牢记作品中的故事并非真实事件,而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它同时具有人造性、摹仿性和主题性(详见下文)。作者在创作故事时,既可遵循叙事连贯性的要求,也完全可以为了某种目的而背离这种要求。话语只能表达作者创作的事件,而并不能自身产生事件。
西方批评家在反驳卡勒的观点时,倾向于从因果逻辑关系出发来考虑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很难切中要害。莫尼卡·弗吕德尼克在1996年出版的《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说:“俄狄浦斯一心追踪自己的往事,发现了一些巧合;但他所发现的东西一直存在于故事层次——如果他没有杀害拉伊俄斯,他就不会现在发现这一事件……”。(注:Monika Fludernik,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London:Routledge,1996,pp.320-321.)与此相类似,埃玛·卡法莱诺斯在1997年发表在《当代诗学》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暗指俄狄浦斯杀害了拉伊俄斯,但这种意义的交汇不能使这一行为发生,而只能使这一行为显得重要。一个效果并不能引起一个先前的事件。”(注:Emma Kafalenos,"Functions after Propp:Words to Talk aboutHow We Read Narrative,"Poetics Today 18 (1997),p.471.)两位学者都将俄狄浦斯弑父视为毋庸置疑的原因,抓住因果关系来看问题,但这样做并不能驳倒卡勒,因为卡勒认为俄狄浦斯不是发现了一个事实,而是在话语力量的作用下,凭空做出了一种推断。两位学者在反驳卡勒时,都绕开了这一关键问题,以确实发生了这一事件为前提来展开论证,可以说是跑了题。
卡勒给出的第二个实例是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狄隆达》。狄隆达是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的养子,很有天赋,性格敏感,但这位年轻人决定不了该从事什么职业。他碰巧救了一位企图自杀的穷苦的犹太姑娘,后来又跟这位犹太姑娘的哥哥学习希伯来语。他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上了那位犹太姑娘,也被犹太朋友视为知己。这时,他母亲向他揭示了他的身世: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小说强调这一往事的因果力量:狄隆达的性格以及与犹太文化的关联源于他的犹太血统。卡勒引用了辛西娅·蔡斯的下面这段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情节中的一系列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狄隆达被揭示出来的身世。对狄隆达的情况的叙述使读者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即故事的发展——明确要求揭示出他属于犹太血统。如果狄隆达的成长小说要继续向前发展,他的性格必须定型,而这必须通过他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来实现。据叙述者所述,在这以前,主要由于不了解自己的身世,狄隆达对自己的命运认识不清……(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p.176-177.)
与《俄狄浦斯王》那一实例不同,卡勒在此对狄隆达的犹太血统没有任何疑问。有趣的是,蔡斯的分析非但不能支撑,反而只会颠覆卡勒的观点。正如蔡斯所言,要求揭示狄隆达的犹太血统的是他的“命运的发展”、“故事的发展”,是“情节中的一系列事件”,而非卡勒所说的“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诚然,在话语层次上采用的延迟揭示这一身世的技巧产生了很强的戏剧性效果,但狄隆达的犹太血统跟“他目前的性格以及他目前与犹太种族的联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存在于故事之中。在此,我们不应忘记作者艾略特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创造者,她完全可以赋予狄隆达另外一个血统——一个非犹太血统。诚然,假若艾略特为了某种目的这么做了,那么当小说揭示出狄隆达属于非犹太血统时,读者一定会感到出乎意料,并不得不修正自己的阐释框架,也会尽力挖掘作者为何这么做的原因。但这只是故事的创作(和与之相应的阐释)这一层面上的问题,与话语层次无关。不难看出,卡勒所说的“叙事连贯性的要求”实际上属于故事而非话语这一层次。卡勒之所以误认为这是话语层次的问题,显然是因为他忽略了故事是作者的艺术创造物,是一个具有主题意义的结构,而非真实事件。我们应当认识到:小说家在创作故事事件本身时,就得考虑叙事连贯性的要求。他们一般都遵从这种要求,但也完全可以为了特定目的而背离这种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卡勒在解构性地颠覆故事与话语的所谓等级关系时,并不想摒弃结构主义的视角。他认为结构主义的视角(话语表达独立存在的事件)和他的解构主义视角(事件是话语力量的产物)均不可或缺,但又绝对不可调和。在卡勒看来,倘若我们仅仅采纳结构主义的视角,那么我们就无法揭示“话语决定故事所产生的效果”(如前所述,这实际上是故事层次上叙事连贯性的要求对故事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仅采用解构主义的视角,那么我们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叙事的力量:哪怕极度背离常规的小说,其效果也以一种假定为基础,即作品中令人困惑的一系列语句是对事件的表达(也许我们难以说出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这些先于话语或独立于话语而存在的事件,一般具有话语尚未报道出来的特征,也就是说,话语会对事件信息进行颇有意义的选择,甚至压制。若没有这种假定,作品就会失去其错综复杂、引人入胜的力量。卡勒认为这两种视角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而由于这种对立,也就不可能存在连贯一致、不自相矛盾的叙事科学。(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1,pp.186-187.)
然而,笔者认为,这两种叙事逻辑并非不可调和。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想借用詹姆斯·费伦在分析人物时采用的一个理论模式。费伦认为虚构人物由三种成分组成:1)人造性或虚构性成分;2)摹仿性成分;3)主题性成分。(注:James Phelan,"Narrative Discourse,Literary Character,and Ideology,"in Reading Narrative,edited by James Phelan,Columbus:Ohio State Univ.Press,1989,p.134.See also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Press,1996.)同样,故事事件也由这三种成分组成。首先,与真实事件不同,故事事件是由作者虚构出来的,因此具有“人造性”。与此同时,故事事件又以不同的方式具有摹仿性。正是由于故事的摹仿性,我们在阐释叙事作品时,总是以真实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时间进程为依据,来推导作品中故事事件本来的顺序和因果关系。此外,小说家创作故事的目的是表达特定主题。由于故事的主题性,倘若索福克勒斯意在创作一部悲剧,他就必定会将俄狄浦斯写成弑父的凶手——无论话语层次以何顺序或以何方式来展示这一事件。同样,由于故事的主题性,乔治·艾略特赋予了狄隆达犹太血统,从而使故事可以连贯地向前发展。也正是因为故事具有主题性,我们可以探讨作品中的故事事件是否恰当有效地表达了作品的宏旨。
有趣的是,在论证所谓“话语”的作用时,卡勒于不觉之中突出了故事的主题性。这是(经典)叙事学未予关注的一个范畴。当叙事学家探讨故事的结构时,一般仅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语法,忽略故事事件在具体语境中的主题功能,当叙事学家探讨话语这一层次时,则往往将故事事件视为既定存在,聚焦于表达故事事件的方式。叙事学家对故事主题性的忽略很可能是导致卡勒做出解构性努力的原因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卡勒虽然关注故事事件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但并末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作者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虚构事件本身的主题性,而是将之归结于话语层次的作用。不难看出,我们一旦意识到故事本身同时具有人造性、摹仿性和主题性,卡勒认为不可调和的两种视角马上就能达到和谐统一:由于故事具有摹仿性,我们将虚构的故事事件视为先于话语表达或独立于话语表达的存在。而由于故事的主题性,作者往往致力于创造一个能较好地表达特定意义的故事,因此故事事件看上去是为特定主题目的服务的。毋庸置疑,有了这种和谐统一,卡勒的解构也就显得多余了。
帕特里克·奥尼尔的解构之“解构”
在1994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话语的虚构》一书中,帕特里克·奥尼尔也辟专章对故事与话语之分进行了解构。奥尼尔开篇即断言:“叙事话语一个最为明显的任务就是对要讲述的故事中的各种事件和参与者进行选择和安排……这种对叙事的切合实际的看法似乎毫无疑问,但倘若用文学理论来仔细考察,它就会出乎意料地迅速解构,这种解构会给人带来某种不安。”就故事而言,奥尼尔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外在的观察者(譬如读者)来说,故事世界不仅不可触及,而且总是具有潜在的荒诞性,最终也是难以描述的。而对于(内部的)行动者或参与者来说,故事世界是完全临时性的,根本不稳定的,也是完全无法逃离的。”(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34.)让我们首先聚焦于故事与外在观察者的关系,逐个考察一下奥尼尔提出的三个特征。奥尼尔之所以认为读者无法接触故事是因为“只有通过产生故事的话语,我们才能接触到它”,因此故事根本不可能构成“首要层次”。的确,作为读者,我们只能从话语推导出故事,但如果我们从作者的创作或“真实的叙述过程”(注:参见Dan Shen,"Narrative,Reality,and Narrator as Construct,"Narrative 9 (2001),pp.124-126.)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故事独立于话语的存在。且以《俄狄浦斯王》为例,我们可以假定索福克勒斯在写作之前就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构思了故事的基本事件——襁褓中的俄狄浦斯被扔进喀泰戎山——被牧羊人所救——在三岔路口杀害了父亲拉伊俄斯——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与拉伊俄斯的遗孀(自己的母亲)成婚,如此等等。然后在写作过程中,再对这些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包括采用倒叙和延迟揭示的手法来加强悲剧效果。诚然,在写作时,作者往往会对先前的构思进行增删和改动,但无论是构思于写作之前还是写作之中,他的写作总是在表达脑海中构思出来的故事事实。也就是说,故事在作者的想象世界里,有其先前(或许是十分短暂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奥尼尔或许不会认同,但他却于无意之中承认了故事以摹仿性为基础的先前存在和首要地位:“一个叙事不仅产生一个严格限定的故事,同时也产生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限定的故事世界。这个世界从原则上说是无限的,包含不可穷尽的虚拟事件和存在体[即人物和背景]。叙事仅仅实现了讲述出来的故事本身所包含的事件和存在体。”(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40.)既然说讲述出来的故事仅仅“实现了”故事世界中的一部分事件和存在体,也就承认了故事世界的先前存在和首要存在,这种存在的根基就是故事的摹仿性。奥尼尔甚至赞同有的传统批评家对故事挖根究底的做法,譬如推导哈姆雷特的父亲对他有何影响,麦克白夫人有几个孩子等等。的确,由于故事具有摹仿性,我们可以推导话语尚未表达的一些故事特征,但这样的推导必须以文本线索为基础,否则就是取代作者来创造故事事件。
至于故事具有荒诞性这一点,奥尼尔作了这么一番解释:“由于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才能接触到故事事件,因此故事世界总是潜在地超越现实主义的范畴,总是潜在地走向非现实,走向荒诞,让人完全出乎意料。”(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37.)然而,正如奥尼尔所言,我们也同样“只能通过话语才能按触到历史事实”,(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p.35-36.)可是历史中的事件却不能过于“超越现实主义的范畴”。毋庸置疑,我们不应把一些小说中包含的离奇事件(譬如人变甲虫、兔子说话等等)归结于读者只能通过话语来接触事件,而应将之归结于小说的虚构性或人造性。由于故事是虚构的,因此可以包含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些虚构成分并不影响(虚构)故事与话语的区分。
至于说故事“难以描述”这一点,奥尼尔举出了两个实例,旨在说明故事世界“逃避和超越描述”。第一个实例为概述。在读到“王子杀死了龙,救出了公主”这一概述时,我们不清楚具体细节。“王子是小心翼翼地从后面爬到了龙的身上,用一把可靠的利剑一下就把它消灭了吗?或者说,他是勇敢地冲了上去,用一把匕首好几下才把它刺死呢?这场战斗是持续了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天,那位精疲力竭的王子才想方设法最终战胜了那个怪物吗?如此等等。”(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p.38-39.)我们知道,概述是作者有意采用的一种叙述手法。作者采用这一手法并非因为无法做出更为具体的描述,而是因为没有必要给出更多的细节。有趣的是,奥尼尔在分析中明确区分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故事的摹仿性为基础)和话语层次上的概略表达,这无疑有利于证实而非颠覆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另一个实例涉及对一个行为的具体描述:“吉姆向门口走去。”奥尼尔说这句话“包含‘吉姆决定朝门口走’,‘吉姆将身子的重心移至左脚’,‘吉姆将右脚向前迈’,‘吉姆将右脚放到了地上’,‘吉姆将重心移至右脚’,如此等等,更不用说那无数更为细小的动作了。”(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39.)在此,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作者在写作时通常遵循创作规约。“吉姆向门口走去”是一种规约性表达,而奥尼尔进行的细节描述则很像电影中的慢镜头,有违常规表达法。实际上,奥尼尔所描述的细节“‘吉姆决定朝门口走’,‘吉姆将身子的重心移至左脚’,‘吉姆将右脚向前迈’,‘吉姆将右脚放到了地上’”等等,完全可以从“吉姆向门口走去”这句话推导出来。作者若没有给出这些细节,并不是因为无法进行这样的描述,而只是因为没有必要,或不愿违背规约表达法。不难看出,奥尼尔的论证不仅没有说明故事世界“难以描述”,反而证实了作者在描写上的主动权和选择权——故事世界是可以由作者任意描述的。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故事内部的行动者与故事世界的关系。奥尼尔说:
故事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正如米克·巴尔所指出的(1985:149),故事的叙述者只需用一个词语就可改变整个故事的构成:“约翰终于逃出了那头发怒的熊的掌心”和“约翰最终未能逃出那头发怒的熊的掌心”,这(至少对于一个人物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差别。最后一点,故事中的行动者从理论上说无法逃出他们居住的世界,像《李尔王》中苍蝇与顽童的关系一样,他们绝对无法反抗话语做出的武断的叙事决定——那些居住在话语中的叙述之神为了开心而将他们弄死。(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41.)
这段文字突出体现了虚构故事的人造性。但我们不应忘记,小说家虽然能以任何方式来创作故事,但通常会考虑叙事规约和作品的宏旨。重要的是,一部小说一经发表,作者就无法改变那一文本中的故事。在探讨故事与话语之分时,涉及的肯定是业已发表的作品,而非创作过程中的草稿。从这一角度看,故事绝不是“临时性的”和“不稳定的”。此外,我们还应牢记虚构的叙述者本身也是小说家的创造物,只能按小说家的意愿行事。至于奥尼尔所说的人物无法逃离故事世界这一点,他似乎忘却了人物并非真人,而是作者的创造物。在此,奥尼尔显然混淆了虚构故事的摹仿性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之间的界限。
在对故事与话语的关系进行了上面这番总论之后,奥尼尔接下去具体探讨了叙事作品中的时间、空间、人物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奥尼尔的探讨与热奈特(1980)、里蒙-凯南(1983)、巴尔(1985)和查特曼(1978)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论述大同小异。(注:G.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trans.J.E.Lewin,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0;S.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London:Methuen,1983;M.Bal,Narratology,trans.C.Van Boheemen,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85;S.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78.)可以说,他只是举出了一些实例来阐发这些(赞成故事与话语之分的)叙事学家的观点。但在论及人物时,他在借用里蒙-凯南的模式的基础上,还在两个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探讨了读者对人物的重新建构过程,强调了语境和阐释框架的作用,但并未对故事与话语之分进行解构。另一方面,在探讨直接表明人物的性质或角色的“说明性的名字”(譬如“道德先生”)时,他评论道:“这突出表明话语优先于故事:最重要的是想表达的叙事要旨,而不是塑造人物的过程。”(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52.)笔者认为,奥尼尔的评论混淆了故事与话语的界限。其实,“说明性的名字”只是与故事本身的主题性相关。作者给人物安上这么一个名字,目的在于让人物更好地在故事的主题结构中起作用。应该说,“说明性的名字”显示的是故事本身的主题性优先于其本身的摹仿性,而非“话语优先于故事”。
最后,奥尼尔给出了一个实例作为总结,这是1947年出版的《文体练习》一书对文体的一种演示,即用99种不同风格来讲述同一个故事,从而出现了99个不同版本。奥尼尔作了这么一番评论:
每一个微观话语(即每一个版本)讲述的故事都是恒定不变的,这是关于一位性情暴躁、注重时髦、每天赶车上班的年轻人的故事。但整个大文本[即99个版本作为一个整体]中的故事,则是有关叙述者的精彩表现的故事。换句话说,话语就是故事。虽然表面上看是对故事进行了至少99次表达——谁又能要求更多次数呢?——实际上话语(芝诺(注:芝诺是古希腊哲学家,以提出一系列悖论而闻名。奥尼尔认为芝诺是“世界上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第一解构主义者”)的影子)已设法将故事完全排除在外,话语在读者的注意力中成功地完全篡夺了故事的位置。(注:Patrick O'Neill,Fictions of Discourse:Reading Narrative Theory,Toronto:Univ.of Toronto Press,1994,pp.56-57.)
从表面上看,这番话解构性非常强,直接声称话语“就是故事”。但实际上,这番话具有结构主义的实质,因为奥尼尔承认在99个版本中,故事恒定不变(unchanging),只是读者在面对这99个版本时,可能会将注意力放在它们的不同叙述风格上。但这并不影响对(那个恒定不变的)故事和(99个不同)话语的区分。
哈里·肖的解构之“解构”
上面两位学者对故事与话语之分的解构均紧紧扣住作品自身展开,哈里·肖在美国《叙事》期刊1995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则着眼于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肖的挑战是对查特曼捍卫这一区分的努力的直接回应。在1990年出版的《叙事术语评论》一书中,查特曼明确提出:“若要保持故事与话语这一不可或缺的区分,就不能用一个术语——无论是‘视点’还是‘视角’,或是任何其他词语——来统一描述叙述者与人物互为分离的行为……只有人物居住在虚构的故事世界里,因此只有人物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只有人物具有故事里的意识,可以从故事里的位置来观察和思考事物。”(注: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90.)故事外的叙述者处于话语空间之中,只能讲述人物的所见所闻。正如肖所指出的,查特曼在论述中有意无意地将叙述者非人化。“假如叙述者不是一个人,也不像是一个人,那就更容易将叙事功能严格地与人物功能区分开来……反之,若将叙述者人格化(或换个角度说,拒绝将叙述者非人化)……那么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界限就很可能会消失”。(注:Harry E.Shaw,"Loose Narrators:Display,Engagement,and the Search for a Place in History in Realist Fiction,"Narrative 3 (1995),p.97.)肖举了大量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实例,说明故事外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十分人格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发表议论时感情充沛。这些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还不时地直接向读者发话,力求感染读者。仅举一例:
母亲,假如您的哈里或者您的威利明天一早就会被一个残忍的奴隶贩子从您怀里夺走——假如您见到了这个奴隶贩子,还听说卖身契已经签署和交付,您只剩下从夜里12点到早晨这么一点点时间来逃跑——那么您又会走得多快呢?
这是引自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段。在肖看来,这样直接向读者发话不仅打破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界限,而且也打破了读者的现实世界与小说的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以及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界限,以及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界限。
肖特别强调在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不少进入了故事空间的叙述者是历史化的叙述者,与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连,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眼光和世界观。他们揭示出历史在小说中的位置和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并迫使读者关注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肖评论道:
若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性来自于对社会进行历史性的描述,那么它就应该把所有主观意识(包括叙述的意识)全都展示为像所描述的人物一样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因此,查特曼所坚持的对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绝对区分,就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和界定上的问题,而且也是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提出的问题。假如对这两个空间的绝对区分可以站住脚,假如这一区分使叙述者得以摆脱故事空间的历史限制,那么仍然可以创作出艺术性的消遣作品。但以其有限的叙述可能性,则难以创作出历史主义所说的那种反映时代情形的作品。这样看来,现实主义的小说要求有一个历史化的叙述者。(注:Harry E.Shaw,"Loose Narrators:Display,Engagement,and the Search for a Place in History in Realist Fiction,"Narrative 3 (1995),p.104.)
肖区分了两种历史化的叙述者。一种是声音和心灵都具有历史意识,但只在话语空间运作,不影响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发现这样做还不够,还需要利用故事空间的感染力来戏剧性地表达叙述者的历史本质。既然现实主义小说描写历史中的人物,那么“如果能使叙述者的空间看上去与人物的空间合为一体(can be made to seem tomerge),叙述者看上去也就像是在历史中活动了。”(注:Harry E.Shaw,"Loose Narrators:Display,Engagement,and the Search fora Place in History in Realist Fiction,"Narrative 3 (1995),p.104.)一方面,肖断言这种历史化的叙述者消除了故事与话语之分,但另一方面,他又于不觉之中承认了这一区分依然存在:叙述者的空间只是“看上去”(而非真正的)与人物的空间合为一体。实际上,肖在论述中反复提到这些叙述者只是作为一个“名义人物”或“隐身人物”而“比喻性地”进入故事空间。肖还说最好将这样的叙述者描述为“摹仿一个碰巧在场的人的角色”。(注:Harry E.Shaw,"Loose Narrators:Display,Engagement,and the Search for a Place in History in Realist Fiction,"Narrative 3 (1995),p.99.)在笔者看来,这根本不影响故事与话语的区分。第三人称叙述者无论多么全知全能,无论多么感情充沛,无论多么富有历史色彩,都只能讲述故事、发表议论,而不能真正参与故事事件(除非变成人物或第一人称叙述者)。同样,他们只能对故事外的读者发话,而无法与故事内的人物直接交流。也就是说,这些人格化、历史化的叙述者仍然处于话语空间中,并没有真正进入故事空间。
前文提到,肖的这篇文章是对查特曼的观点的一种反应,笔者认为,尽管查特曼的本意是捍卫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但他在把视角或视点囿于故事空间的人物时,却无意之中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查特曼自己将“话语”界定为“表达内容的方式”。(注: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78,p.19.)叙事视角为表达故事的方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话语范畴,而不是故事范畴。诚然,叙述者常常借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件。可以说充当叙事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具有双重性质:作为故事内人物的感知,它属于故事层次;而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它又属于话语这一层次。这导致了故事与话语在这一局部难以区分,但并不影响总体区分。至于故事外的全知叙述者为何能观察到故事内的情况,这无疑是叙事规约在起作用。由于有关虚构惯例的存在,处于另一时空中的全知叙述者不仅能“目睹”故事中人物的言行,而且能透视人物的内心。至于海明威的《杀手》这种叙述者仅仅外在观察人物的作品,叙事规约则使叙述者起到一部摄像机的作用,“身临其境”地记录人物的言行。毋庸置疑,无论是上帝般的全知观察还是摄像般的外在观察,第三人称叙述者只能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比喻性地进入故事空间,这并不会真正影响故事与话语的区分。
布赖恩·理查森的解构之“解构”
在2001年美国《叙事》期刊第2期上,布赖恩·理查森发表了一篇论文,集中探讨“消解叙述”(denarration)。所谓“消解叙述”就是先报道一些信息,然后又对之进行否定。这种现象在晚期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中较为常见。理查森认为消解叙述在有的作品中颠覆了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塞缪尔·贝克特的《莫洛伊》就是如此。在这一作品中,叙述者先是说自己坐在岩石上,看到人物甲和人物丙慢慢朝对方走去。他很肯定这发生在农村,那条路旁边“没有围篱和沟渠”,“母牛在广阔的田野里吃草”。但后来他却说:“或许我将不同的场合混到一起了,还有不同的时间……或许人物甲是某一天在某一个地方,而人物丙是在另一个场合,那块岩石和我本人则是在又一个场合。至于母牛、天空、海洋、山脉等其他因素,也是如此。”理查森对此评论道:
因果和时间关系变得含糊不清;只剩下那些因素自身。它们相互之间缺乏关联,看上去,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成别的组合。当然,当因果和时间关系这么轻而易举地否定之后,那些因素本身的事实性也就大受影响。可以肯定那确实是一头母牛,而不是一只羊,一只鸟,或是一个男孩吗?……(注:Brian Richardson,"Denarration in Fiction: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Narrative 9 (2001),pp.168-169.)
笔者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己难以区分叙述话语与故事事实,但实际上这一区分依然在发挥关键性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区分,理查森才会发问:“可以肯定那确实是一头母牛,而不是一只羊,一只鸟,或是一个男孩吗?”也就是说,读者相信在极不稳定的叙述后面,依然存在稳定的故事事实。如果说这里的“消解叙述”仅囿于局部的话,有的地方的消解叙述涉及的范围则更广,譬如,叙述者说:“当我说‘我曾说’等等时,我的意思是我稀里糊涂地知道事情是这样,但并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理查森断言,这样的消解叙述在整部作品中颠覆了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因为到头来,我们只能肯定叙述者告诉我们的与‘真正发生了的事相去甚远’”。(注:Brian Richardson,"Denarration in Fiction: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Narrative 9 (2001),p.170.)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宏观消解叙述依然没有颠覆故事与话语之分。正是由于这一区分,我们才会区别“真正发生了的事”(故事)与“叙述者告诉我们的”(话语),理查森这里的偏误源于叙事学界对故事的片面定义。理查森这样写道:
被消解了的事件向叙事理论提出了另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莫洛伊》这样的文本中,如何将故事与话语区分开来?若如里蒙-凯南所言:“‘故事’指的是从文本中推导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建构的所述事件”的话,那么当话语在进程中否认、否定和抹去先前叙述的事件时,我们又怎么能重新建构故事呢?……通常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在这里崩溃了,我们面对的只是话语,而没有一个可推导出来的故事。作品的话语是确定的,但其故事却根本无法确定。(注:Brian Richardson,"Denarration in Fiction: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Narrative 9 (2001),p.173.)
叙事学界对故事的看法一般与里蒙-凯南相同,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相当片面,因为它仅考虑了叙事交流的接收者(读者),而忽略了叙事交流的信息发送者(作者)。同时,这一看法聚焦于故事的人造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故事的摹仿性。作为故事创造者的作者无疑知道“真正发生了的事”。此外,如前所述,由于故事具有摹仿性,因此存在独立于文本的故事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事实可以被话语在不同程度上扭曲或者遮蔽,但读者在阅读时会尽力透过扭曲性或遮蔽性的话语,来推导建构较为合情合理的故事。无论这一过程多么困难,只要故事仍有一定的摹仿性,读者就不会放弃这种努力。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话语与故事之分”是否仍在起作用,即阅读时是否仍在推导“真正发生了的事”,是否仍在思考“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扭曲了故事”。只要不停止这样的追问,话语与故事之分就依然存在。
在晚期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中,尤其是第一人称叙述中,消解叙述屡见不鲜,同时还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可靠叙述”。作者之所以让这些叙述者进行或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或片面错误的描述,往往是为了塑造叙述者的主观意识,展示其独特的叙述方法,或显示语言在话语层次上的破坏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消解叙述与通常所说的不可靠叙述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后者往往是叙述者无意之中造成的,其原因往往在于叙述者记性不好、智力低下、精神错乱、看问题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信息渠道狭窄或信息本身有误,如此等等。这样的不可靠叙述一般不会影响故事与话语之分。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叙述者“不可靠”,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叙述与我们推导出来的故事事实不符——这是本来可以被可靠的叙述者表达的故事事实。
与此相对照,消解叙述往往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有意在玩一种叙述游戏。笔者认为,消解叙述究竟是否影响故事与话语之分取决于这一游戏究竟是作者让叙述者自己玩的,还是作者和叙述者共同玩的;这一判断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摹仿性。倘若属于前一种情况,在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就会有距离,读者就会相信存在为作者所知的稳定的故事事实,只是因为叙述者自己撒谎,前后矛盾,才给建构事实带来了困难。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影响读者对“真正发生了什么”的追问,无论答案多么难以找寻。但倘若作者创造作品(或作品的某些部分)只是为了玩一种由消解叙述构成的叙述游戏,那么在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就不会有距离。而既然作者旨在玩叙述游戏,作品(或作品的那些部分)就根本无故事可言。笔者认为,故事与话语之分以作品的摹仿性为根基。在虚构故事中,故事事件有时荒诞离奇,但我们依然可以区分谎诞的故事和叙述它的话语。也就是说,事件本身的谎诞性并不影响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因为虚构叙事的规约允许这种摹仿的存在。但当作品仅仅构成作者的叙述游戏或者文字游戏时,摹仿性就不复存在,读者不会再追问“真正发生了什么”,故事与话语之分自然也就不再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有的后现代小说以其纯粹的叙述游戏而消解了故事与话语之分,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故事与话语也并非总是可以区分。在这一文类中,也存在故事与话语的各种局部重合,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在此不赘。(注:Dan Shen,"Defence and Challenge: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tory and Discourse,"forthcoming in Narrative.)
通观30年来西方批评理论界对故事与话语之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种为绝对捍卫,另一种为各种形式的颠覆。但无论是属于哪种倾向,这些讨论一般都出现了偏误,偏误之源就在于没有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虚构故事本身同时具有人造性、摹仿性和主题性,认识到故事世界与话语世界之间的本质界限,认识到故事与话语之分以摹仿性为根基,同时认识到在具有摹仿性的作品中,故事与话语之间仍可存在各种形式的局部重合。本文选取了四种颇有影响的解构性观点进行了剖析,希望这有利于揭示叙事作品的一些基本特征,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作者、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把握虚构叙事的实质性内涵。
标签:俄狄浦斯王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叙事学论文; DISCOURSE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