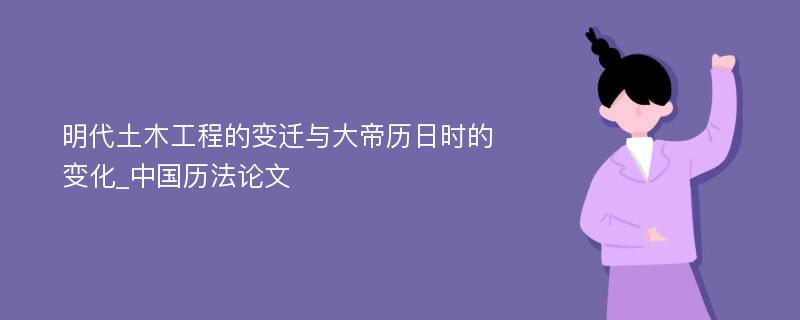
土木之变与明代《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变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土木论文,昼夜论文,之变论文,时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2)02-0139-05
有明一代,官方在行用《大统历》的同时并未放弃改革。学界对此虽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对发生在正统末至景泰初的历法变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明代《大统历》系统中最初行用的昼夜时刻是南京数值,英宗将其改为北京相应时刻,景帝登基后又改回南京时刻。前人论述此事,常以景帝时复旧为历史倒退立论。如周绍良先生评论说:“彭德清所上言是科学的,是按北极地理求得的,但被一些保守腐儒所否决”,①语焉未详。陈美东先生观点与周氏相类,对整个事件过程未进行更多探讨。②景帝复旧之缘由,迄今未见合理解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及相关背景进行初步考察。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英宗朝修改《大统历》昼夜时刻
历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活动中具有特殊意义。任何政权建立之后都要颁历天下,以示其为“正朔”之所在。吴元年(1367)冬至日,太史院使刘基进献《戊申岁大统历》,明太祖朱元璋将其颁行天下,自此通行《大统历》成为一代定制。明初的《大统历》主要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略加改编而成,其中一项重要的变动就是将《授时历》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昼夜时刻数值改为京师南京的相应时刻。这是因为帝王肩负着“敬授民时”的职责,而自金元以降,官方又以都城所在地的昼夜时刻作为其时刻制度之标准。金代《重修大明历》昼夜时刻尚沿用宋制,以开封北极出地计算而来;而元朝建都北京后,其《授时历》改为北京数值。这种出于政治考虑的数值选取就此成为历法技术规范的一部分。
成祖通过“靖难”夺得帝位后,开始营建并迁都北京,但中经洪熙、宣德两朝反复,直到正统六年(1441),才最终确定。③在此过程中,明廷于正统二年(1437)开始将南京观星台的各种天文仪器复制运到北京进行铸造安装。④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向皇帝上书汇报了使用新铸仪器的测验结果:
钦蒙造铸铜仪,委夏官正刘信考较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⑤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北京的地理纬度高于南京,故北京的昼夜时间与南京不同;就北京的冬至日夜晚和夏至日白天时间而言,其各比南京长达三刻,这些差异在时间计量上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永乐以来,朝廷行用的漏刻制度仍为南京系统,如此报时会与北京实际明显不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彭德清建议“今宫禁与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⑥。英宗采纳其建议,命内官监根据实测的北京昼夜时间改造漏刻制度,准许彭德清将《大统历》系统中所使用的南京昼夜时刻改为北京相应时刻。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钦天监编造十四年(1449)历日(历书俗称历日)时,其昼夜时刻数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推算。这与明初《大统历》对《授时历》昼夜时刻改动的思路同符合契,与当时历法技术规范的要求一致,是合理可行的。
由于《大统历》的修改是历法的技术层面问题,天文历法之学又为官方所垄断,故虽有变更昼夜时刻之举,其起初仅关乎天文官员,并未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另一方面,历法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统一编造并颁行历日来体现。历日是古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其每日下各有历注。有了历注的引导,人们才能根据吉凶宜忌安排行事。为了体现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历注中还附有昼夜时刻制度标准,对不同日期的昼夜时刻作出规定,指导着普天之下的漏刻改箭,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社会直接影响从上到下的日常起居。
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出版,所收录的明代大统历日中,恰有这次改制前后所编的正统十三年和十四年本,对比相应日期的历注,就会发现昼夜时刻明显不同。⑦无疑,前者采用的是南京昼夜时刻,后者为北京昼夜时刻。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亲临奉天殿,将正统十四年历日颁赐文武群臣,随之流布民间。当朝廷上下、闾巷小民接到政府新颁的历日,发现历注中的时刻制度与往年不同,会做何反应呢?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时的文献记载,仅在后世的追述中发现一些线索。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正统戊辰,上从钦天监正彭德清之请,改加冬夏二至昼夜各五十一刻,颁次年历,时皆叹诧为异事。”⑧又称:“是冬所颁大统历日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⑨此外,邢云路追论其事,亦谓“人骇以为异”⑩。虽然他们记载具体数字有误,但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当时朝野对历日昼夜时刻变更一事不得其解。
二、岳正论己巳《大统历》
颁历之后,朝野虽对时刻制度颇存疑惑,却是一度集体噤声。据沈德符说:“仅见岳季方所纪,亦以为怪,然亦北狩以后,追述往事耳。”(11)岳季方即岳正,字季方,正统十三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天顺元年(1457)入阁。黄云眉先生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其考证《明史·历志》时曾点出:“按岳正有正统己巳历议一文,载文集,可参阅。”(12)
岳正文集《类博稿》收录《明故琴乐先生墓志铭》一文,其中回忆了他在颁历之后对《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一事的讨论,披露出一些细节:
予及第之明年,颁己巳之朔礼成而观其书,书二至之晷有昼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诸家历法,无有也。先生时为(钦天监)五官司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进士,因以所私问之。先生曰:“子以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会日,以日会天,天运常舒,日月常缩,历家以其舒者、缩者之中气置闰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积三岁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极,日行中道,冬至行极南,至牵牛得四十刻,为日短;夏至行极北,至东井得六十刻,为日长;春秋分则行南北中,东至角西至娄为昼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变。故古者以历名家者,必以其变者立差法以权衡之,则变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欤?”先生曰:“如子言诚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将居其职而不与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历者,圣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拨(揆)之,能无摇其支(本)乎?”予始悟当时用事者亦(方)赫赫,必以先生为忌。已而果有土墓之变,益以服先生之高识矣。(13)
琴乐先生名王义,曾在钦天监任职,《大明正统十四年岁次己巳大统历》后所附的制历官员名单中,就有“将仕郎五官司历王义”字样,(14)说明他确实参与了历日的编写工作。王义之子王琮,系岳正同科进士,一度官居户部主事。需要指出的是,岳正及第在正统十三年,而十四年历日实颁于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故此处“明年”有误。另外,该年历日二至晷刻之长当为六十二刻,而非六十一刻。(15)
确实,在明朝迁都的特定情况下,政府在修改历法时唯独变更昼夜时刻一项,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岳正感到无所适从,就基于自身的儒家知识结构背景出发进行判断。其论置闰,谓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唯此数值不见于天文历法典籍。试取传统阴阳合历19年7闰之法推算,19年×12=228月,置闰当添7月,为235月,即每年多出7/19月,积3年,则多出21/19月。取朔望月长度29.5日,则29.5×21/19=32.60日,每日百刻,就与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基本相合。故可推断岳正经过计算得出此数值,以示编排节气置闰月规律的灵活可变,即“活者”。其论昼夜时刻,谓冬至日短四十刻、夏至日长六十刻云云,此数值当沿袭汉儒马融注《尚书·尧典》。而《大统历》昼夜时刻原为冬至昼四十一刻,夏至昼五十九刻,变更后为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故句中数值应为泛指,其意为各节气与昼夜时刻长短之间的关系恒定不变,即“死者”。
通过对比正统十三年和十四年历日即可知,改用北京昼夜时刻数值后,各节气与昼夜时刻的编排确实出现了较大变动。岳正无法接受这种变化,他以为历家当注重编排节气与置闰,而不应变更时刻制度。实际上,由于对历法技术规范未得要领,岳正的质疑出现了偏差。
作为编历官员,王义看来也不同意变更昼夜时刻,语似旷达,却流露出不满和无奈。他进一步提出历法是“圣政”的根基,担心这次《大统历》的修改会动摇统治。王义闪烁其词的表现令岳正意识到来自“用事者”的巨大压力。
其后,正是在新历行用的当年即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明军死伤达数十万,英宗被俘,瓦剌兵临北京城下,一时人心惶惶,明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根据历法关系到王朝盛衰运数的传统观念,岳正遂将土木之变与《大统历》时刻制度的“不当”修改进行了关联附会。
三、《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的政治背景
《大统历》时刻制度的反复修改虽然前后仅两年,却为我们观察正统、景泰年间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提供了又一条线索。
正统中期以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擅权,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即为其党羽。据《明史》记载,彭氏“素为振腹心,凡天文有变皆匿不奏”(16)。在王振的支持下,他甚至变更了祖制。如成化年间,钦天监五官灵台郎刘伸上奏追溯:“自洪武以来,凡天象有变,本台官辄自具奏,不用本监印信,至正统间,监正彭得(德)清等始变旧制。”(17)王振通过彭德清垄断了天文事务,成为其弄权的重要手段。于是彭德清“倚振势为奸,公卿多趋谒”,以一介五品监正而猖獗一时,与其有隙者,即被寻机报复。翰林侍讲刘球为彭氏同乡,却“绝不与通,德清恨之。”正统八年(1443)五月,雷击奉天殿鸱吻,刘球应诏上书,彭氏“遂摘疏中揽权语,谓振曰:‘此指公耳。’”王振“固已衔之”,当即大怒,遂矫诏逮捕刘球下狱并杀害。(18)即此可以想见,正统末年彭德清倡言时刻制度改革,必以王振为后台,故“举朝无一语诘责”;岳正等人虽心怀困惑,“当其时亦未能昌言相驳也”(19)。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朝野一片沉寂。
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瓦剌,王振、彭德清等随行。八月十五日,明军兵溃土木堡,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彭德清侥幸逃归。经此事变,彭氏被控“不择善地驻劄”,顿成导致“逆虏犯跸,邀留乘舆,扈从官军,肝脑涂地”(20)之直接责任者。郕王朱祁钰即景帝掌权后,立即下令查处王振一党,籍没其家。十月中旬,彭德清瘐死狱中,为了平息民愤,景帝“命仍斩其首”,罪名是“党王振,匿天变不奏,及从征,不择利地驻师”(21),并将其全家发配辽东充军。
景帝安抚了北京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犯,并顺应形势将英宗朝弊政逐一革除。明廷反思祸始,一时言路大开,而王振及其党羽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迟至景泰二年(1451),仍有人因与彭德清相厚而被攻诘。(22)可以想见,“罪人”、“奸党”彭德清主持的《大统历》时刻制度变更,受其政治立场牵连,势必被视为乱政之举。于是大臣一改原先的缄默,“群然非之”(23)。
景帝即位的那年冬天,天文生马轼上书对改历一事提出异议,称“昼夜时刻不宜改”(24),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关于马轼的生平事迹,已有学者介绍过:马轼字敬瞻,除了精于占候之学外,以山水画闻名,更兼诗文之长,因此享誉京城,广结士人。(25)岳正系顺天府漷县人,身为会元、探花,也是当时造诣颇深的书画家,所画葡萄堪称一绝;他对天文历法兴趣浓厚,与钦天监五官司历王义“雅相知”。可见岳、马两人的交际圈有很大重合。迟至天顺初年,岳正居阁臣之位而遭贬谪,离京之日,只有时任漏刻博士的马轼前来饯别并作诗唱和。(26)如此深厚的情谊大抵需要长期交往积淀而成。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隐约感到马轼上书背后可能存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孙高亮在《于少保萃忠传》里假杨善之口评价景帝“聪明英武,纳谏如流,采听舆言,有若学士刘定之,给事郑林、王士俊,主事李贤,员外项忠,监生练纲,千户龚遂荣,天文生马轼,御医孙瑛,卫士曹习古等,各献奇策,俱皆升任。”(27)虽系小说家言,必有所本,可为马轼活跃于景泰朝添一佐证。
四、景泰朝更定《大统历》昼夜时刻
马轼上书后,因事关重大,景帝命礼部会官讨论。一些官员反对马轼之说,以新任钦天监监正许惇为代表,他道出此中原委:“正统间,监正彭德清于观象台测验,以北京较之南京,北极出地上三高度,南极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刻,奏准改入《大统历》(力),永为定式。”(28)根据前朝实测所得两京出地高度、昼夜长度等数据,许氏认为将昼夜时刻改为北京数值之举是合理的。有的学者认为许说“谬误”,(29)值得商榷。《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中收录有“正统十一年本历日”,所附的制历天文官员名单中有“承直郎中官正许惇”(30),意味着许惇在前一年即正统十年(1445)就已担任中官正职务了。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他由中官正升任监正,(31)是一位专业出身的天文官员,故其质疑马轼“起自军匠,不谙历数,妄以己意要改旧制,所言难允”(32),礼部尚书胡濙也对许惇表示支持,而后人沈德符却斥其为“附会执奏”(33)。
然而,景帝最终做出如下结论,肯定了马轼的建议:
历虽造于京都,而太阳出入度数则当以四方之中为准,则是以尧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测验于四方,以定四时之仲。今京师观象台在尧幽都之地,太阳出入度数其可以为准乎?今后造历,宜悉照洪武、永乐间旧式。(34)
景帝征引《尚书·尧典》,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地中概念。自汉朝起,浑天说在天文历法界长期流行,以大地为平面,其大小又是有限的,这样当然有一中心,由此产生地中概念。(35)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漏刻制度就应采用地中的昼夜时刻作为标准。古代中国人认为天下之中在河南某地,故以河南地中时刻为国家时刻制度之标准。元代定都北京后,从其统治中心出发对历法技术规范进行了调整,不再以河南地中而是以北京的昼夜时刻作为时刻制度标准,这样实际上背离了浑天说宇宙观。明初《大统历》继承了元代《授时历》的调整思路,因为元、明两朝的情况相同,都城均不在河南。现在景帝重拾浑天旧说,认为北京观象台位于“尧幽都之地”,其昼夜时刻不能作为时刻制度标准,借以否定英宗变更《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做法。不过,所谓恢复祖制,实际上就是采用原先的南京昼夜时刻。按景帝的逻辑,我们从地中说的角度进行思考,则南京也地处一隅,其昼夜时刻同样是不可用的。
在土木之变后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大统历》昼夜时刻复原是不可避免的。景帝看来无心纠缠,故另辟蹊径,引入传统的地中说,模糊问题焦点,而后偷换概念,以尊崇祖制告终。无论如何,就此平息了这场争论。至于后人沈德符称:“读帝此旨,评驳精确,顿令星官缄口”,“(尚书胡濙)以身主其事,不免护前,遂非,其如景帝圣明,不可面欺何?”(36)这种看法,却可能反映了一般士民的认识。
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诏,正式将《大统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中收有“景泰元年本历日”,其昼夜时刻仍为北京数值,而《汇编》还收录有景泰三年本,昼夜时刻已改回旧制。周绍良先生曾据此认为《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可能只实行二年或三年”(37)。景泰元年本之所以采用北京昼夜时刻,是因为该历早已造完,并于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颁布,所以不及更定。景泰二年本历日,目前还没有见到,疑其或已亡轶。由于景帝下诏改回旧制的时间为正统十四年十二月,而景泰二年本造于景泰元年(1450),应是改回旧制之后,故此历中昼夜时刻应已改回南京旧制。
自景泰二年(1451)始,《大统历》继续行用南京昼夜时刻。即便英宗复辟,也未改动。《汇编》所收录的最晚的明代历日为崇祯十四年本,其中昼夜时刻仍行用南京数值。由于明末改《大统历》为西法的计划最终未实行,所以南京昼夜时刻一直行用到明朝灭亡。故有明一代,仅正统十四年及景泰元年历日中行用了北京昼夜时刻。
五、结语
清人梅文鼎对景泰朝复旧之事评述说:“士大夫既未考诸《元史》,畴人子弟失其官守,又不能执历草以争,遂旋行而罢。”(38)梅氏将事件发展方向归咎于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缺陷以及技术官员未能尽职,其实忽视了政治背景:明英宗改制后不久,旋即爆发土木之变,其时政局剧转,群情激愤,景帝为稳定局面而大举否定前朝施政。本文所考察之《大统历》昼夜时刻改回科学层面上更不合理的旧制,正是此特定情势下的产物。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与皇权政治有着紧密关联。(39)帝王自称天子,受命于天,建立灵台,独占通天之特权。江晓原先生关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天文学”特征,为强调它与现代天文学的不同,而将前者称为“天学”(40)。
历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数理含量最高的精华部分,对其地位与性质的理解,需要基于国家政治的视野。《尚书·尧典》中,“观象授时”即是帝王施政之首务。长期以来,星历之习学,为官方垄断,历法之制定,为国家要政,历日之颁赐,为朝廷盛典。历法的变更,影响到王朝正朔,这是关系统治权威的大事,因此常常会引发争论。持异议的双方或多方,并非是简单地进步与落后,或真理与谬误之冲突。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政治与文化活动。(41)
[收稿日期]2011-12-09
注释:
①周绍良:《明〈大统历〉》,载《文博》1985年第6期。
②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第556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上册,第225-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明英宗实录》卷二“正统二年二月乙亥”条,第540-541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条,第3120-3121页。
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条,第3121页。
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又见周绍良:《明〈大统历〉》,载《文博》1985年第6期。
⑧(1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禨祥·土木之祸咎徵》,第73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厘正历法》,第527页。
⑩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六五《历议六·辨大统历之失》,第689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明史卷三十一(历志一)考证”,第29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岳正:《类博稿》卷十《明故琴乐先生墓志铭》,12a-14a,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八年刻本。“揆”、“本”、“方”三字据《明经世文编》改。另见陈子龙等编、岳正撰:《明经世文编》卷三二《正统己巳历议》,第22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第1册,第128页。
(15)检索古籍发现,后世多种历史文献记述这件事情,内容大体相同,但其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基本上都错误沿用了“昼夜六十一刻”数据,未加订正。究其史料源头,当为年代较早的《类博稿》。
(16)(18)《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第4406、440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成化十一年四月戊戌”条,第2616-2617页。
(1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禨祥·土木之祸咎徵》,第737页。
(20)《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条,第3521-3522页。
(2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己未”条,第3632页。
(22)《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六“景泰二年七月己亥”条,第4415页。
(23)《明史》卷三三《志第九·历三》,第621页。
(24)《明史》卷三一《志第七·历一》,第517-518页。
(25)(26)(29)马明达:《明马轼、马愈族属考》,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27)孙高亮:《于少保萃忠传》卷五,第三三回,第400页,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712页,“力”字系衍文。
(3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第1册,第32页。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辰”条,第3574页。
(3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712页。
(3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厘正历法》,第527页。
(3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712页。由于《英宗实录》修于成化朝,笔者不排除景帝之言被史臣删改过的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只能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分析。
(35)参见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厘正历法》,第527页。
(37)周绍良:《明〈大统历〉》,载《文博》1985年第6期。
(38)梅文鼎:《大统历志》卷三《黄道每度昼夜刻立成》,第85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孙小淳:《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
(40)江晓原:《天学真原》,第1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1)钮卫星:《汉唐之际历法改革中各作用因素之分析》,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