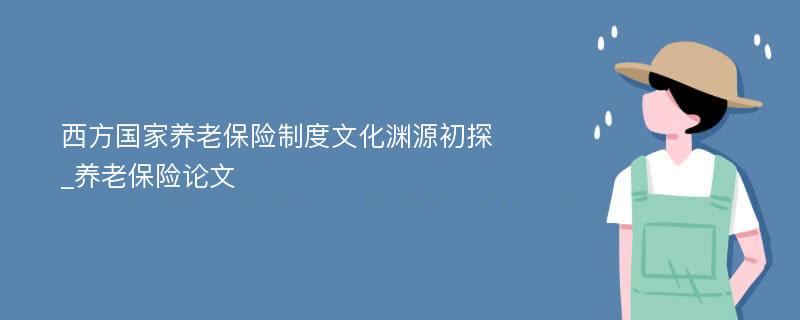
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西方国家论文,根源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4—0006—05
社会保险制度分析表明,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深深植根于特定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条件,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注:林义:《社会保险制度分析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显然,养老保险制度不应仅仅停留于对运行机制、技术设定的探讨,而应充分关注其制度与文化设定。在某种意义上,制度与文化根源的探讨,更有助于揭示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内在约束条件。
然而,迄今为止,国外对养老保险起源的大量研究,集中于养老保险产生的一般经济、政治条件的探讨,而忽略早期制度基础和制度形式的研究,不仅割裂了它与早期社会保护形式的内在关联,而且大多集中于欧美文化圈。虽有一些研究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养老保险发展,但往往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当我们对养老保险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制度文化层面,尤其是侧重从跨学科、跨文化的新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养老保险的制度与文化根源,而且有助于揭示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危机的根源和其内在的文化矛盾。
由于近代强有力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传统被挤压到狭小的空间。在重新反思工具理性局限的时代,应当呼唤人文传统的回归。近代文化史之父,德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赫尔德说过,“文化是人的血液”,“文化是人类的第二自然并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识”。(注: d 'Epimar: Individualism and Solidarity Today,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91,Vol,8,57,Mueller: Zu Herders Auffassung von Wess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Kulcur,in Ziegengeist,G ( Hrsg) :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978,p36.)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的骨髓,人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行为、观念传统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均深深地植根于早期文化设定和文明起源进程。即便对异常精巧和复杂技术外观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设定,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对抗既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设定。
一、老年经济保障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
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是近代西方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虽然直观地采取传统私人保险制度的一些外在形式,但它在深层次上受文化传统的制约。老年经济保障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不应将它同老年社会史与文化史割裂开来,亦不应忽略西方社会老年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 (注:Dea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9,p11.)在西方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老年问题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问题,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已存在了若干世纪”。“西方文明曾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龌龊的态度对待老年人”,老年人的“有关问题远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便普遍存在,它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注:Steatns: Old Age in European Society,Holmes and Meier,1976,p22—23.)相反,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中,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通常是通过家庭或扩展的家庭结构来实现。“尊老爱幼”是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并且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中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跨越。因而,养老保险问题,亦或老年经济保障方式不仅应纳入文化发展的框架,而且应当从跨文化的比较中,为进一步分析、反思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在西方社会的长期历史演化进程中,老年经济保障一般是通过家庭、教会、各类自愿互助组织、私人保险、政府救助以及发展到近代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险来实施的。这一发展路径,从根本上说,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个人主义乃西方文化的极为重要的内核,它已经影响西方社会两千多年并将继续下去。(注:d Epingy,1991,p57.)个人的自由、平等及私有产权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代际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每一代均强调自己的权利。(注:Cole:The Journey of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ging in Americ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1992,p56.)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影响到西方社会中老年人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
正如西方著名学者Beauvoir指出的那样:“人的老年及其地位的下降,总是出现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结构内部……它无疑与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征相关联”。(注:Deat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s, 1989,p15.)显然,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对于西方社会各类自愿互助组织的广泛存在,较强的团体内互助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基督教自助、互助的文化传统,也对各类自愿互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保险不过是在既有社会保护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基础之上,由现代国家强制推行和组织实施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至少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条件下原有社会保护形式的某种延伸,它既保留着西方传统社会保护的某些制度内核,而区别于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家庭保障形式;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干预介于其间,使养老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自愿互助制度。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来自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不应仅仅是指日益增大的老年人口赡养比例、难以支撑的养老保险费用的巨额支出,而且包括来自传统方面的严峻挑战。西方老年文化史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象征,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是以青少年为导向的文化。自中世纪以来,西方许多艺术家均采用共同的象征手法,赞美和颂扬青年的万象生机,诅咒象征枯枝、坟墓的老年萧条景象。(注:Cole:The Journey of Life,1992,p1—31.)社会福利政策长期以来侧重于强调儿童及青年福利,而大多数社会福利史、家庭史则完全集中于讨论青少年的福利发展,而忽略了老年人的福利问题。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老年问题仅仅是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并带来严重后果的背景下才引起普遍关注。现代西方文明,凭借现代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也最先形成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峻挑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工业社会创造了老年这一新的、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且文化要素无疑推进了这一增长进程”。(注:Clark and Anderson:Culture and Aging,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1967,p16.)一个明显的悖论在于,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首先产生于老年文化最薄弱链条下的西方社会。因而,人口老化对西方传统提出了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从根本上说,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危机并非是唯一的但确是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它在深层次上反映出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二、西方家庭结构与养老保险起源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表明,家庭无疑是为老年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保障的最重要、最安全的社会制度。即便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物质生存条件中,老年人的保障问题一般通过家庭或原始公社来解决。但长期以来,代际间松散的联系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西方老年史和家庭史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以前,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结构是核心家庭而不是扩展的家庭形式。(注:Hareven,T:Aging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 Over the Life Course. Walter de Gruyter,Berlin,New YOrk,1996,p1.)欧洲社会普遍存在老一代向青年一代转移财产或遗产的习俗。“自中世纪以来,农场主同其子女之间的遗产和退休合同表明,产权与所有权通常用于作为老年经济保障的交换条件”。(注:Quadagno,J.:Old Age in IndustrializingEngland,in:Hess,B(eds): Growing Old in American,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1985,p46.)老年人通过转移私有产权或遗产给子女,换取子女签署的退休合同和有限的退休保障。这类合同通常极为详尽,规定子女应提供的食物数量、其它物品及居住空间。由于西方社会老年人权力的逐渐减弱,尤其是伴随着私有产权和遗产的正式转移,使其对年轻人的控制力更是非常微弱,经常出现拒绝赡养老人的现象发生。由于退休合同所提供的老年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财产尤其是凭借牧场和羊毛为交换条件来维持而并非年轻一代应尽的社会责任。工业化进程无疑严重摧毁了退休合同这种脆弱家庭保障制度的基础。由于大量农民被剥夺了世代拥有的土地、农场和牧场,难以继续维持产权、遗产交换和退休合同。另一方面,年轻人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不再谋求遗产和等待签署退休合同等,均使脆弱的退休合同难以维持。相反,对于那些没有或仅有很少财产或遗产交换的老年人,则更难获得以私有产权交易为基础的退休合同及其有限的老年保障。因而,西方特定的家庭结构和退休合同的脆弱联系亦是教会救助及自愿互助机构普遍存在的重要社会基础。
不仅如此,这种松散的退休合同和代际间的联系,一方面为通过教会救助和自愿互助组织提供保障奠立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同时,为政府强制养老保险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而另一方面也使政府强制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某种隐含的不稳定要素。尤其是在以代际间收入再分配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能否组织好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是否存在不同代际劳动者普遍的社会认同,乃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极为重要的潜在文化条件。如果赡养老人尚未构成青年一代普遍认同的社会责任,而仅仅靠产权交易的对等性来维持,那么,政府组织的这类计划则会在特定背景下面临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代际接力(侧重于老一代对下一代的单向哺育责任)的模式,试图通过政府强制组织实施的养老保险计划而实现反馈模式(哺育与赡养的双向责任)的内在约束条件和要求,事实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亦是目前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危机背后的深层文化矛盾。
相反,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中,家庭一直是实现老年经济、精神保障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尊老爱幼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发展中凝聚的优良传统,亦是东西方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重大差异。经过几千年家庭文化的积淀,形成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文化特质。古往今来,家的观念与家庭成员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构成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导向文化观的一个根本之点。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扩大的家庭文化观对中国长期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惟有在跨文化的分析视野中,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潜在价值。中国家庭文化观的弘扬,其价值将远远超出单纯保存国粹的范围,而必将为世界更多的民族和国家所认识。
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许多非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保障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尊重老人、赡养老人依旧是许多非西方社会迄今依然遵循的传统。在一些亚洲国家,扩大的家庭模式、几代人共同居住的生活方式依旧非常普遍。尊老、养老仍是家庭成员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认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在东南亚地区至今仍不算十分发达,相反,家庭养老和传统社会救助却是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值得重视的制度文化特征。因而,养老方式及养老保险制度绝非是运行机制的简单移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与社会的文化认同,而后者在根本上最终影响和制约老年保障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如美国著名家庭史专家Hareven所言, “文化传统对选择代际扶持模式发挥着主导作用”。(注:Hareven,T.1996,p11.)
70年代有关福利国家发展的研究曾揭示,由国家干预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及私人福利机构受到毁坏的条件下,由社会福利机构取而代之而发挥某种暂时性的作用。(注:Titmuss, R: Essays on Social Ploicy.An Introduction.London1974,p30.)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的真正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懂得如何放弃它。当我们深入分析西方国家养老保险起源问题时,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安排中包含着某种内在的文化矛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衍生的由政府组织和强制实施的制度形式能否在不具备强有力家庭文化传统支持的条件下得以长久地运行,尤其在缺乏家庭结构内反馈型代际模式的文化认同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强制充当“家长”的角色以维持代际间转移的社会保险的运行,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风险。当我们留心到赫尔德和黑格尔对西方国家的起源的论述,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形成于家庭解体之后并与应付市民社会的挑战密切相关。(注:Adler:Herder und die deutsche Aufklaerung,1968,p222.Heising:Hegel's Idea of the State,1971,s119.)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在长期的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制度形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这预示,惟有在跨文化的分析视野中,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中隐含的固有文化矛盾,即在缺乏家庭文化基础的西方国家中,政府企图扮演“家长”角色,组织控制社会保险所必然面临的困境。这注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在制度安排中存在严重的文化缺陷和难以调和的内在文化矛盾。
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在其初创阶段,大都借鉴私人保险的基金制运行模式。有学者认为,由于战争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二战后均采取现收现付制。尽管这一转变的内在原因仍有待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向基金制和私有化路径发展的趋势,并非仅仅由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经济影响等显性因素而能够给予圆满解释。这一改革调整的背后,隐含着极其深刻的制度文化根源,对于由政府强制实施、强调劳动者代际间收入再分配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如果缺乏年轻一代对老一代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的、普遍的文化认同,缺乏以家庭文化为基础的强有力代际间文化联系,而仅仅凭借经济利益关系,现收现付模式或可视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暂时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最终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观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已严重威胁到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和文化根基。这一文化矛盾必将在深层次上制约和影响西方国家养老保险未来的改革发展走势。在此意义上,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私有化的改革发展走势,正是其为克服既有文化矛盾的必然反映。西方有识之士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成为21世纪西方的巨大社会演变,也将是西方历史上自工业化革命以来社会的重大转折点。(注:何农: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是福利还是负担?《光明日报》1999年4月9日。)当我们从制度分析的角度透视这一演化进程,应当承认这一推测的合理性。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养老保险是为解决工业化背景下家庭保障的瓦解而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悖论是,这种制度安排则进一步削弱了既定文化设定中家庭的作用。“家庭及经济制度受到政府养老保险计划的严重影响,而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是其最危险的后果之一”。(注:Lubove,R:The Sttruggle for Social Security 1900 — 193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06.)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批评福利国家时曾指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早期的(收入)转移有助于加强家庭联系,而强制性转移则削弱这种联系”。(注: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9、125页。)自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西方国家大多数青年人自孩提时代起便知道,赡养老人是国家社会保险的事情而非家庭成员的责任,对国家而言,随着社会进步,个人和家庭理应承担更多的养老保险责任。因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危机远远超越一般技术设定、经济和政治设定,而是植根于长期文化传承的内在轨迹,西方国家的养老保险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似乎处于“责任空谷”之中。
三、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与文化矛盾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养老保险起源发展的进程中,它不但直接植根于各类自愿互助制度尤其是传统私人保险制度,而且在国家干预之下,直接承袭其重要的制度内核。(注:林义著:《社会保险制度分析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尤为关注二者的关联及其对养老保险起源的重要影响,关注国家干预自愿互助制度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德国作为社会保险的发源地,关于德国社会保险起源成为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颇受重视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德国最初社会保险立法进程中,德国首相俾斯麦与其对手德国工商部长洛曼(Lohmann )之间展开的激烈辩论令人深思。对于德国首相俾斯麦及其追随者而言,强调通过国家对自愿互助机构和私人保险制度的干预,“国家必须控制和接管所有人寿保险、 工伤和医疗保险计划”。 (注:Karrengerg,F: Geschichte der sozialer Ideen im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1969,s598。)现代国家干预理论和福利国家的重要奠基者阿道夫·瓦格纳,不仅非常强调国家对社会政策的干预,并主张对交通、银行和保险业实行国有化管理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强调建立国家强制保险计划并推行社会税计划。 (注:Wanger, A: Staat: in nation-alokonomischer Hinsicht,in Conrad,J (Hrsg):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Bd,8.1911.S738.)
与此相反,洛曼则强调发挥传统自愿互助组织的作用,强烈反对俾斯麦的强制社会保险计划。洛曼坚持认为,国家仅仅应当加强对自愿互助组织提供资助,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强烈批评国家强制保险计划和反对在最初的工伤保险立法中采用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显然,现行纳费这一代劳动者的未决责任取决于未来不确定的团体成员,完全改变了自愿互助组织长期遵循的共同原则”。
(注:Tennstedt and Winter:Jeder Tag hat seine eigenen Sorgen…,Die Anfang des Sozialstaats im Deutschen Reich von 1871.Zeitschaft fur Sozialreform,1995,Vol.41,s682.)值得重视的是,洛曼在1874—1876年曾详尽地研究了英国“友爱社”及其经验教训,他强调应保证自愿互助组织财务的自主性和财务稳定,国家在必要时应为其提供帮助。但国家强制保险计划在未来的发展中必然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注:Zitt,R.:Zwischen Innerer
Mission
und
Staatlicher Sozialpolitik,Universitatsverlag,1997,s171.)
令人深思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德国最早养老保险立法进程的历史文献至今尚未公诸于众,我们无法了解在世界上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起源问题上俾斯麦和洛曼之间激烈辩论的真相。然而,从双方的基本分歧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国家是否能够通过强制社会保险的方式取代和控制欧美社会经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自愿互助和私人保险制度。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再一次超越于一般技术、运行机制的设定乃至一般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解释,而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制度设定。
关于养老保险乃至福利国家起源的大量研究,集中于欧美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方面,而观念文化方面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略。(注: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States, Social Knowledge,and Modern Social Poli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3.)事实上,洛曼坚决反对国家强制保险计划的政策主张,植根于他对社会史尤其是宗教文化问题的长期关注。洛曼曾强调,“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忽略对教会史的分析,将发现我们文化发展的全面危机”;“我们的家庭制度发展止于子女达到成年阶段”。(注:Machtan,L (Hrsg):Mut zur Moral. Aus der privaten Korrespondenz des, Gesellschaft- sreformers Theodor Lohmann,Bd.1 (1850—1853).Bremen.1995,s324—325.)因而,洛曼反对国家强制社会保险计划的主张,反映出他对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切关注。
在养老保险起源问题上,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克服商业保险市场上因逆选择、道德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所作出的一种制度选择,需要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实现“家长式”的关怀,进而取代或部分取代传统自愿互助和私人保险制度的职能。(注:Diamond, P: A Framework for Social Security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5,Vol.8,p57—74.)在近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险起源发展的进程中,几乎都存在自愿互助组织和私人保险机构的顽强抵制。(注:Gilbert,B: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Michael Joseph,1966.Quadagno,J: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ge Secur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Lubove: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Security,1968.)这种抵制固然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 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则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因素。70年代,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坚持,无论从观念文化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政府干预远远超过了它自身的职责和能力界限。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所隐含的文化矛盾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变得不可调和。各类自愿互助组织和私人保险制度,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自助互助的内在精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化成较为成熟的制度形式,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所强调的自助与团体内人人平等的互助,亦是西方文化长期演化的自然历史结果。近代国家机器的膨胀及其对各类自愿互助制度的过度干预,会严重摧毁和影响这类制度,并带来灾害性的后果。(注:Loan, A: Institutional Base of the Spontaneous Order:Surety ans Assurance, Humane Studies Review,1991,Vol.7,No,1.)
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运行机制层面的分析,私人保险和社会保险均遵循一些保险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团体内在的平等互助和精算平衡原则等,然而在文化和制度设定中二者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遵循西方社会长期演化中形成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和团体内的平等互助精神,而后者似乎更强调近代理性原则和国家干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长期发展的西方文化传统。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迅猛发展,使其经济、政治、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与私人保险制度在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差异。事实上,以国家干预其间的养老保险制度所遵循的团体内互助原则,也难超越由长期历史文化传承及社会结构决定的自助和互助的内在文化基础。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异常复杂的财务机制,无论是现收现付还是基金制,二者的差异并非单纯的技术设定和经济内涵能够解释,它必然受深层的文化因素制约。早期私人保险制度采取基金制机制,乃是团体内个人自助与互助原则内在精神的体现。但对国家干预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不论采取何种财务机制,它已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背离了长期形成的自愿与互助的隐性文化传统。即使对最早产生的德国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尽管在形式上仍与私人保险的财务机制保持某种一致,由于国家的直接控制而非间接资助,已内在地有别于私人保险制度所依以建立的制度文化基础,但它毕竟还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即强调个人责任的一面。而二战以后,欧美国家普遍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机制,则完全演变为由国家直接组织和控制的、以代际间隐性交换合同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几乎割裂了它同自愿互助原则的内在联系。这一转化必然在人口老龄化前景下演化为代际之间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养老保险制度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激烈冲突。显然,养老保险内在的文化设定不能、也不可能长期背离自愿互助和私人保险制度依以形成、发展的文化基础。近代养老保险曾经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克服自愿互助机构缺陷而登台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它目前已陷入远较传统自愿互助机构更为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
因而,西方国家社会保险私有化的发展趋势,正是为了克服其内在的文化矛盾而面临的必然选择。这是我们研究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西方国家养老保险面临的危机并非财务机制的危机,也非政治选择方面的问题,而是制度安排中的深层次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家庭结构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惟有从养老保险制度与文化的内在根源的分析中,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国家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的未来走势,并为重新审视众多非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和社会政策的自身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思路和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标签:养老保险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养老保险体系论文; 互助保险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家庭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