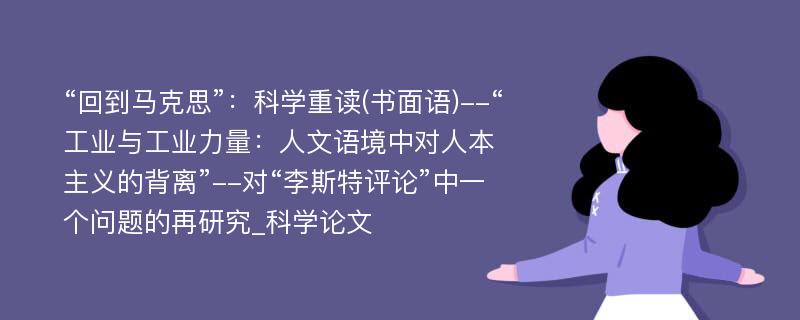
《回到马克思》:一种科学的再阅读(笔谈)——工业与工业力:在人本学语境中对人本主义的背离——对《评李斯特》中一个问题的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马克思论文,工业论文,人本主义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5)02-0001-16
张一兵教授在他的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指出,马克思 在《评李斯特》中已经开始了“从人学主体辩证法向客观的历史辩证法的无意识的过渡 ”。张教授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从马克思在该文本中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关节 点——工业与工业力的区分——出发对此进行分析,而只是从整体上指认了这一转变。 也就是说,张教授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他区分了工业与工业制度、 工业与工业力,从而开始了对人本主义逻辑的无意识的但有决定性的解构。
首先,马克思把工业理解为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对自然力的占有,由此对工业与工业 制度、工业与工业力进行了区分。“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 自己的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 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 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 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 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 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 民出版社,1979版,第257页、第258-259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页。)这段话实 际上包含了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马克思在这里把工业看成是人类的主体性得到 充分展现的活动,即人类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生活条件的活动。第二,这里的工 业已经不是原来笼统的工业了,而是“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 的环境”的生产活动。工业与其从事活动的工业制度或资产阶级社会不是一回事。可以 说,马克思此时已经无意识地将工业与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了。张教授所说的“ 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没有将工业与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区别开来”是不够准确的。因此,第 三,这样理解的工业实际上也就是存在于工业活动中的人的主体性力量,即工业力,正 是这种力量成为最终消灭作为制度而存在的“工业”本身。虽然马克思此时的认识还没 有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水平,也把现实的“工业”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 代名词,即“工业 = 资产阶级社会”,但这种对工业理解视角的转换则表明了马克思 理论思路的重大转换,“他已经在让一种新的从现实工业出发的理论思路占了自己理论 运演的上风”。(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 民出版社,1999版,第337页、第338页、第338页、第339页。)当马克思把工业与工业 制度(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区分,并从中拉出一条工业力的线索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无意 识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人本主义逻辑的崭新逻辑。张教授的指认是正确的,但不够细致 ,在细节上也有偏差。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工业中存在的工业力对工业本身的颠覆是废除工业 的基础和内在力量。第一,马克思指出,“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 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 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 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 西提供与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第258页、第259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 发展的东西”就是上面所说的工业力,而废除当前的工业也就是消除资产阶级制度而为 工业力的发展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基础。换言之,“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 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 渡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8页、第 259页。)马克思已经非常准确地把废除工业的基础奠定在工业力的基础之上了,即摆脱 工业对工业力的羁绊就要“考察这种力量本身”。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提出要“把目前 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马克思此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要消除的并不是工 业(客观必然性的‘是’),而是工业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而工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本身就是走向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37页、第338页、第33 8页、第339页。)张教授的这一指认无疑是深刻的,但他没有明确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认 识的获得恰恰是建立在对工业与工业力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的。很明显,马克思此时的 论述不再是以劳动异化理论为出发点的思辨推理(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而是从现实的 工业及其发展矛盾出发进行的论证。马克思用人本主义的话语说出了与之完全异质的东 西。
第二,工业力对工业的颠覆是通过无产阶级实现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 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同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 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率的工 具(承担者);它们将砸碎自己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 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 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 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 会桎梏的那种锁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 57页、第258-259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页。)与以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不 同,马克思此时不再从人的本质异化和对这个异化的扬弃来进行论证,而是直接从工业 本身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指出工业本身存在着两种砸碎工业外 壳(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一个是工业本身具有的力量——工业力,另一个是社会力量 ——无产阶级。这两种力量虽然目前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是资产者实现自己的利润率 的工具或承担者,但同时又是“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 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工业(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已经生 长出了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力量,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超越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再是 对某种理想状态的复归,而是现实历史的必然趋势。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 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 现代工人——无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8年版,第14页。)在这里,虽然还带有人本主义的气息,但已经没有了异化史 观的论证方式。“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不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要求,而是现实历史 的必然趋势了”。(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 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37页、第338页、第338页、第339页。)马克思将工业力与无 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无疑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发展。张教授似乎没有明确指认二者之间 的联系。
最后,由于马克思初步区分了工业与工业力,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区别对待工业与工业 力,批判工业而不是批判工业力,肯定工业力而不是肯定工业。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 思批评了圣西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如果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 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的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 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57页、第258-259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 页。)就会造成将工业和工厂制度神圣化,就会找不到真正克服和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 现实力量。马克思认为圣西门学派的错误就在于这种混淆,他指出,“圣西门学派狂热 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 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 第257页、第258-259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页。)因此,虽然圣西门学派也向交 换价值、当前的社会制度、私有制进攻,但由于这一混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变 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这样,圣西门学派在不自觉中跌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 ,因为“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 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 民出版社,1979版,第257页、第258-259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页。)因此,要 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就必须将工业与工业力区分开来,认识到工业力以及使用这一力量 的无产者是真正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打破工业对人的统治的现实力量。张教授没有从马 克思区分工业力与工业的角度对此展开论述,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小疏忽。
由于区分了工业与工业力,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和对无产 阶级革命的论证,虽然还是在人本主义的总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的,还存在着对人性的呼 唤,但其批判和论证的起点和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他不再从理想的劳动出发认为 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劳动被异化了的社会,进而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超越和克服是对 劳动和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是从工业本身出发,从分析工业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揭示 资产阶级社会灭亡的内在力量和现实条件。正是这一理论张力使马克思在人本学的语境 中开始了对人本主义的背离。由于这一区分,“‘工业’的现实历史发展已经开始成为 马克思理论逻辑中主要的运演过程,而人和人的本质的异化逻辑只剩下一个没有血肉的 空骨架。一旦这个逻辑构架被自觉打碎,无意识的破坏变成有意图的颠覆,一个新的思 想境界就会诞生。”(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 苏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337页、第338页、第338页、第339页。)无疑,张教授在《 回到马克思》中对此的论断总体上是正确和深刻的,但还有待深化和具体化。这也是本 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