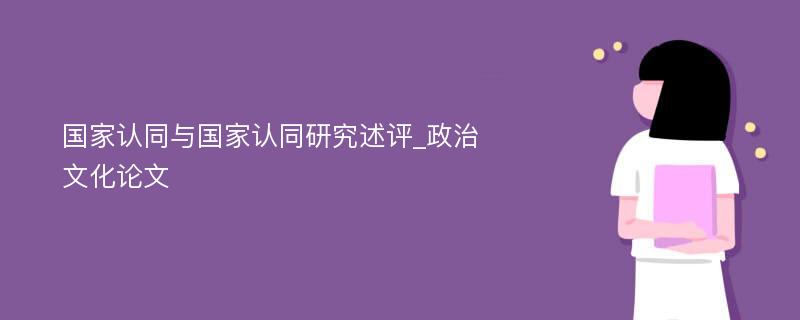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中的人参与了不同群体形式的建构,扮演着多个角色,由此形成了一个个角色集。社会成员因隶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传统国家中,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而民族-国家时代,“其内部的行政调节仰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特性的条件”,① 民族国家建构后的社会成员所担任的角色集较之传统社会亦发生着变化。作为某个民族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群体里担任的角色集中较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② 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③
一、采借初探:多维视野下对民族认同研究的聚焦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把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④“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⑤ 后来,埃里克森(E.H.Erikson)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因此把“认同”放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指出“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就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⑥ 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到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汇,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民族认同的概念开始,学界就展开了丰富的讨论,由此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要素、对文化适应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等问题的系统研究。
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族群与族群认同的研究论文很多。国内学者在借用“族群”概念的同时,也试图对其重新定义和解释,以适应中国的国情。王希恩把民族认同界定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⑧ 庄锡昌进一步划分了民族认同的类型,认为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⑨ 郑晓云认为,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意识,即对“我”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的看法。⑩ 王亚鹏在卡拉所提民族认同定义和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态度是民族认同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而群体认同的态度表现在民族认同上有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之分。前者是指成员以身为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满了优越感,行为上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积极的民族认同不仅使民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同时也会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认同模式在强势民族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成员以一种悲观甚至是自卑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以自己隶属本民族的一员感到耻辱,因而产生了一种认同的污名感(stigma)。这种消极的民族认同运作的结果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部分民族成员不愿意暴露其民族身份。(11)
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学者们多把目光集中在认同模式的划分及族群关系上。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是针对美国有色人种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获得积极的民族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进行的。最初,研究者往往只对少数族群,且多以美国黑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移民、难民、留学生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认同研究情有独钟,其研究领域主要包含对少数民族族群的自我认同及跨文化族群认同研究。伴随着对弱势族群认同研究的热潮,西方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族群认同研究的模式来解释特定族群的认同发展状态。菲尼(J.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12) 70年代格罗斯(Feliks 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13) 这一模型勾画出了黑人青少年认同发展的方向——最初表现出对白人的过分认同,贬低自己的文化,而这种认同是极不健康的,直至发展到认同于自己的黑人群体,走向健康的认同。1996年赫尔姆斯(J.E.Helms)提出了白人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后,又于同年提出了更具有包容性的适合于所有有色人种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14) 这一认同发展模式的发展过程由以下发展的因素组成,分别是一致性(Conformity)、不协调(Dissonance)、浸入-浮现(Immersion-Emers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及整合意识(Integrative Awareness)。赫尔姆斯认为,认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认知、情感因素的图式,从图式可以测定出认同的不同维度和发展水平。
除了对认同模式的划分进行研究外,国外部分学者倾向于从族群边界及边界维持的角度来解释族群现象。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首次提出从族群结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他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族群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其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因素是其社会边界,而社会边界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15) 此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泰勒(Charles Taylor)、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人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并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身份日益模糊化。(16) 与此同时,国内关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相关专著。(17) 张剑峰指出,族群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即心理认同和文化实践认同决定的行为边界才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18) 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各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结构和认知结构。(19) 周大鸣对族群、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进行了系统描述,并指出“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些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20) 栗志刚则进一步强调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石。(21)
关于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研究者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但都认为青少年时期不仅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较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民族认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对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进行了探索性量化研究,如万明钢、张庆林等。(22) 一些学者通过对藏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汉族朋友的数量、父母民族身份、学习汉语的时间与其民族认同息息相关。不少研究者都认为民族认同对文化适应、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3) 高永久认为,积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往往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协调和有序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对本民族及祖国的强烈情感,二是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公正的强烈需求,三是对本民族自身利益的关切。(24)
关于民族认同,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原生论强调认同中那种相对稳定、依靠传承而延续的维持认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先赋、原生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个体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即族群文化儒化的结果。(25) 工具论则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在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指南针。事实上,认同意识的强弱,既源自原生性的因素,也受到现实条件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是原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的相互博弈。在不同时期,人们认同意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因此“原生论”和“工具论”的二元预设,使得任一理论都无力单独对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王明珂先生指出:“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需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26)
我国学者在对西方族群理论思考的同时,将族群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注重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族群理论的发展。祁进玉认为,王明珂在其研究中引进族群认同理论,分析特定情景中族群间的资源竞争与配置,“中心”和“边缘”的形成与变迁现象。(27) 另外,从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缘形成来解读“中国人”认同的本质,并且探讨了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28) 同时,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研究少数民族取向到同时注重对汉族的重新思考。黄淑娉重点探讨了汉族三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的文化特点,(29) 徐杰舜从历史人类学视角描述了华南族群汉民族的认同。(30)
长期以来,尽管前辈学者在民族认同研究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族群认同研究的面仍不够广,来自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还不够多,难以形成基于实证调查材料之上的理论体系。我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学界对民族认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所以族群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族群理论本土化有待加强。有关民族认同的界定存在两种指向,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近年来,国内学者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认同”研究冠以“族群认同”之名,欲与来自英语学界的概念“ethnic group”相对应,因此“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然而,当前不少学者在其研究中把许多社会群体都称之为“族群”,由此引发了族群主义的“认同喧嚣”。(31) 鉴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但在英文翻译中又较为慎重,某种程度上反映和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32)
二、哲思关怀: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
“国家认同”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33) 特别是随着苏联剧变、东欧解体,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连,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而公民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诚如高丙中指出:“个人、社会和国家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34)
长期以来,学者们致力于国家认同的思考,深表对社会稳定的关切之情。虽然西方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出发,并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国家认同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从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直至国家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皆有涉及,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35) 国家认同是公民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则担负着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使命。(36)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37)
尽管学者从不同的研究取向来界定国家认同概念,但只有少数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给予精确定义。佐斌总结了国外关于国家认同感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这些成分可以相对被区分为知识和观念亚系统、情感与评价亚系统。作为认知成分的前者包括了人们对自己国家和人群的知识和相关看法;后者作为情感成分,涉及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和人群的情感、情绪和评价等方面。(38) 此外,陈晶等对我国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证研究。(39)
随着族群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学术意义的族群研究与政治意义的国家认同的结合点,转而对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40) 近年来对新疆地区的研究亦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维吾尔族学生群体。(41) 何峰通过问卷调查,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分析,探索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丰富了国家认同研究的实证性。(42) 李崇林则从历史和现实原因入手,分析了在新疆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并为和谐新疆的构建献计献策。(4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引发了不少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对跨境(国/界)民族的关注。可以说,跨境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郝时远强调:“中国陆路边疆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跨国民族现象的现实,而当前打着‘同一民族’、‘同一宗教’旗号的‘三种势力’及其渗透性影响,在中国边疆地区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因此应加强跨界民族的研究。”(44)
马曼丽等人完成的《西北跨国民族丛书》展开了对西北跨国民族的系统研究,其中《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侧重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西北跨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跨国民族的交互影响、跨国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解读,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理论探索价值。(45) 周建新侧重研究多国别之间的跨国民族及其相关问题,讨论了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族群结构特点,强调国家关系对跨国民族关系的影响。(46) 另有学者从历史、文化信仰、心理素质和语言等各方面揭示跨国民族认同的依据。(47) 其中,石茂明以苗族的一支Hmong人为例,研究其跨国状况和跨国带来的相关问题,并开展了跨国Hmong人专题研究,对其族名变异与认同变迁进行了专门探讨。吴楚克指出,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
除了关注西北民族的研究外,学者们对西南边疆跨境(国/界)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尤其是何博的硕士论文《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云南大学2007年)和谷禾的博士论文《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研究——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探讨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外,龙耀等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西南跨国民族子女的国家认同现状;(48) 和跃宁以云南省德宏州中缅边境跨境民族为例,探讨了中缅边境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49) 丰富了跨境民族研究的实证材料。
综上,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国家认同的研究取得了进步,无论是从政治学视角、民族文化的视角,还是从心理层面对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都体现了学界对国家认同研究的多向思考;关于对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现及如何培育国家认同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国家认同研究的关怀。但后者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还显不足,特别是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
事实上,多民族国家除了把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政治共同体进行建构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一种能够包含国内所有族类共同体的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即国族。国族的发展过程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互动、涵化的过程。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中华民族陷入长久的分裂,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分裂、主张和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感情和传统,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根基之所在。在这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上,演化出多元的民族,而当汉族形成民族实体以后,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这一自在的国族实体,在近百年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国族实体。(50) 因此,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政体概念上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已经完成了民族融合过程的民族,但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是同一个观念,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实体。故国家认同包含了对中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两层含义。
在如何增强中国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问题上,马戎认为,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存在着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21世纪的中国不仅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民族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民族意识。(51)
为此,学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郝时远认为,民族(族群)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其表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难以对其做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认定,用“文化化”来形容美国的族群政策和评价其消融族群意识、民族主义的成功作用是片面和不准确的。(52) 王希恩在赞赏马戎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的同时,指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非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当前仍需坚持、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53) 陈建樾则驳斥了马戎以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取代民族身份上的多元一体,以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通过“文化化”来淡化民族问题的观点,强调一种包容多元、融会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他认为,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54) 李红杰也强调,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多民族国家必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多样性,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55) 朱伦虽然无意驳斥马戎的观点,却指出承认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必须包括自治权和共治权两个方面。他认为,民族自治具有固化民族界限、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而共治是对自治客观造成的民族界限的一种弥合,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强共同的国民意识,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56) 王建娥强调,不能因为当前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变迁而否定自治价值、取消自治制度,不能将“共治”价值绝对化、用共治取代自治,或用多元文化主义取代民族自治制度,更不能将民族关系“去政治化”。相反,多民族国家要设计出包容族裔文化多样性差异,协调其分歧的灵活机制,尊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保护多元社会民族和文化多样,不断发展和完善自治-共治机制,实现族际政治民主化,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从而巩固国家统一,创造社会的和谐。(57)
笔者认为,学术专家们在族际关系、民族问题的研究上积极辩争,其目的都是为强构国家认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体现了学术服务现实社会的应用特点。然而已有的成果尚有不足之处:多是从“应然”维度进行的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不足;理论层面阐释多,关注现实的实证性分析不够;泛论性阐释多,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较为缺乏。(58)
三、拓展争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学界在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进行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学者们首先对民族、国家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三种模式,即矛盾冲突关系、调适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民族”指一国内部处于次国家层次的各种具有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差异性的族类共同体;“国家”就是在一定地理边界内具有对外主权独立性和对内统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联结局限性基础之上,通过地域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联系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建构。(59) 钱雪梅也指出:“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有特定的疆域及主权,一般由两个以上的族群组成,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公共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60)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两者都是其成员对所属群体的认可,都能增强本群体凝聚力,而且都受情境影响。学界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两者进行辩争。郑晓云认为民族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种认同,使我们就能够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界限。从认同对象上看,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其所属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其认同必然是多元的,而国家认同的对象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政治共同体。(61) 就认同与个人行为规范的关系而言,国家的规则和惯例具有强制性,而族群习俗相对则宽松很多。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主权,族群则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的权威要求服从和秩序,这主要依靠以暴力机关为后盾的法律制度来确立和维护。(62) 从成长机制上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有很大差异。每一个人都出生、成长于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或族群之中,受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所谓的“民族”,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就具有先赋性特点。诚如王希恩所言:“民族认同是具有天然群聚性和类别感知能力的人类都能具有的社会认知,有很强的自发性。”(63)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意识的投射或转化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64) 倘若国家在与民族的互动中,某个民族感受到自身利益的被剥夺感,那么其民族意识就会增强,民族认同也会随之提高。与民族认同具有原生性因素驱动不同,国家认同是纯粹构建起来的概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传统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65) 正如波齐(G.Poggi)所考察的,国家的创建过程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统治者依靠其统治机构来扩展和保证他们的权力基础,并且提高他们自己在管理和动员社会资源时的有效性与影响力”。(66) 因此,任何国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动员来建构共同意义的过程。国家认同的建构性特点在陈志明的研究中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论证。他以马来西亚为例,分析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而成为不同的民族。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新加坡的华人今天都自视为不同的群体,其差异源于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参与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的形成。(67)
20世纪中期以来,在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进行区别的基础上,二者的关系备受学者关注。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68) 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前提。一方面,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国家是各个民族利益保障的共同政治屋顶,民族认同只有在国家的机体内才能得以形成和发展。为寻求现实的利益保障,民族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国家认同进行巩固。“国家认同为民族认同构建安全的地域和心理边界”。(69) 近现代国家建立之后,国家控制力的不断加强,使得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意识不断加强。在国家主义盛行的今天,爱国成为超越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界限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因此,明确而坚定的国家认同,是任何民族得以健康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总之,民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员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依赖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概不例外。(70) 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没有民族也无所谓国家。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以国家为存在形式。(71) 这里的民族当然是指国族,而中华民族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构成,所以中华民族就是56个民族融合而成的国族。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必须仰赖生活在国家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的支持。在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与“我群意识”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而且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巩固和不断强化的国家认同,会对民族认同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多样性的民族认同及其增强,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某种消解性的影响,导致对国家认同的侵蚀。因此,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72)
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上,许多学者聚焦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产生的矛盾和张力。20世纪经历了多次“民族主义”浪潮,特别是90年代苏联解体后引发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学者对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民族与国家认同(ethnic and state identity)给予了大量关注。相关研究显示,民族独立与国家整合相互交错,民族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而防止国土分裂则是国家整合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政府长期的重要任务。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国家整合努力的障碍,而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则会反过来激发族群的自我意识,可能导致民族独立运动兴起。(73) 国内学者也在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中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能产生的冲突问题。一方面,其全体成员因系同一民族而具有共同的民族观念和感情;另一方面,又因其成员分属不同国家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在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发生冲突时,跨境民族中有些人的民族观念往往超出国家观念。(74)
冲突论的视角在学者们探索边疆治理的研究方案中成为了一个焦点,认为要提升国家认同程度,国家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要求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倾斜。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少数民族就会产生被弃感或受歧视感,这种质疑在民族精英系统化地说教、导引下,往往会转变为对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和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其结果是强化民族认同,促进民族主义的产生,进而破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因此,周平提出要淡化族际界限,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方式促进族际政治整合,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75)
冲突论研究者大多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在搭建起宏观的解释框架时把复杂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简单地置于对立冲突的情况,忽略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和谐共生的面向。费孝通先生认为,尽管认同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但不同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与矛盾。“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76) 周建新总结了中越、中老、中缅边境跨国民族在认同与互动上表现出的层次性:首先,在最高层次上表现为国家的认同与互动,即政治文化民族的认同与互动,其互动通常表现为国家关系的互动;其次为跨国民族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与互动,即各国法定或社会公认民族彼此的区分与互动;再次为跨国民族内部的认同与互动,即跨国民族内部不同部分的认同与互动;最后为跨国民族内部亚族群的认同与互动。各层次的认同与互动均受到不同时空范围内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77) 陈心林考察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层次与变迁,提出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体现出高层次与低层次认同并存不悖、各自发展的特点,其变迁趋势是由血缘性、地缘性认同向国家认同的方向发展。(78) 此外,祁进玉对青海土族、(79) 王纪芒对朝鲜族、(80) 胡青对云南昭通回族(81) 的研究等也都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的事实。
在面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矛盾的事实情况下,学者们在其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颖而又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二者共存和统一的基础。如张海超、罗慧翾、张友国、贺金瑞、栗志刚等。(82) 张友国指出要达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键是要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的基础上,承认双重认同与文化多元,积极建构一元政治意识。贺金瑞在关注两者矛盾时,积极探索我国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方法,推动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栗志刚认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奠定了民族认同(这里即指广义的民族,即国族)的基础,是民族认同的外部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和内部依据,是民族认同之根。所以要加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才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根本。
学界在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给予或矛盾对抗、或调适共生的研究视角外,另有学者从权力关系的视角给予了认同研究新的解读。
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在对中国西南彝族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进行研究时,更为关注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民族政策不断塑造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并以此来强化国家认同,展示了其中权力关系的运用。(83) 而事实上,这种权力关系的运用不只于国家,族群也在积极利用它来促进自己的身份建构,达成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一些研究说明了少数民族的形成既有政府起到的界定作用,也是民众积极“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和少数民族政策来界定自己民族身份的结果。萧凤霞等认为,族群分类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上各种力量都会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府的符号象征,来宣示自己的权势和特性。(84) 高丙中通过研究指出,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85) 有学者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地展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吴羽、姚燕在研究中发现,贵州屯堡人的家谱编撰通过对屯堡族群与国家关系的选择性记忆,勾连了家庭、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动利用来自国家的权威力量,以促进屯堡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86) 王文光等指出,滇西北的“勒墨”支系部分群众表现出“我非白族”的认同观,而大理的部分白族则表现出“汉族祖源”的认同观,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把民族认同作为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工具。(87)
可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如果过于突出民族认同会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反之,如果忽视民族认同存在或压制民族认同也会引起民族不满,破坏民族团结,导致社会失序。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甚或决定国家的命运,或兴或衰,或合或分,至今很多国家仍然深陷其中,难以轻装前行。因此,如何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只能释放善意,与民族结伴同行。我们在无从改变二者并存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只能改变我们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接受民族的存在,并坦然接受她的善和不宜,并设法使其成为有宜者。(88)
总体上看来,学界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成就卓然。或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国家关系的角度进行宏观分析,或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进行个案研究,但还未能将宏观的结构分析与个体研究充分地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民族研究中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些不足。因此,引入身份认同理论,把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将是值得探索的一个研究空间。由此,努力总结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变迁的规律或机理,以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
注释: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② 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90页。
④ 参见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⑤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⑥ 参见贾志斌:《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⑦ 参见Carla J.,Reginald J.,“Racial Identity,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ling and Development,1998 Vol.26(No.1)。
⑧ 参见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⑨ 参见李忠、石文典:《当代民族认同研究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⑩ 参见郑晓云:《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强盛——兼论祖国统一》,《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 参见王亚鹏:《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心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1期。
(12) 参见J.Phinney,“Stage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1989,9(1~2)。
(13) 参见万明钢、王舟:《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14) 参见Helms,J.E.,“An Update of Helms's White and People of Color Racial Identity Models,” Ponterotto JG,Casas,J.M.,Suzuki LA,Alexander,C.M.eds.,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ling,Thousand oaks.CA:Sage,1996,pp.181-198。
(15) 参见[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6)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加]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7)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参见张剑峰:《族群认同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
(19) 参见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0) 周大鸣:《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1) 参见栗志刚:《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内涵》,《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22) 参见万明钢、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心理学报》2004年第1期;张庆林、史慧颖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内隐维度的调查》,《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3) 参见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史慧颖、张庆林、范丰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24) 参见高永久:《论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5) 参见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2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27) 参见祁进玉:《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兼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8)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29) 参见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0) 参见徐杰舜等:《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1) 参见Gunnar Haaland著、徐大慰译:《跨国人口流动与族群认同——以东南亚的尼泊尔移民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朱杰、卞文伯:《宽容同性恋族群的现实意义》,《中国性科学》2010年第9期。
(32) 郝时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 group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和《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两篇文章中指出,“族群”一词已成为了相当泛化的概念,对“ethnic group”这一术语的学科认识和学术理解不能简单地从某些定义出发而忽视其应用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具体指称对象,要科学地吸收与借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进步和中国学者认识的深化,学者们认为,汉语“民族”需要用不同的英译,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国情,比如,“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英文名称“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 of PRC”变更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PRC”、“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译名在2008年11月由“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33) 参见袁鹤龄:《国家认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国因素、中国因素与台湾的“国家认同”》,《台湾:理论与政策》2000年第2期。
(34)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5) 参见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6) 参见徐则平:《试论民族文化认同的“软实力”价值》,《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37) 参见贾志斌:《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8) 参见佐斌:《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年第2期。
(39) 参见陈晶、佐斌、周少慧:《5—16岁儿童对中国人形象的评价与喜好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4期。
(40) 参见陈志明著、罗左毅译:《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第6期;庞金友:《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
(41) 参见王嘉毅:《新疆南疆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42) 参见何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途径与方法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3) 参见李崇林:《挑战与应对:认同与和谐新疆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4) 郝时远:《加强跨国民族,研究促进边疆稳定发展》,《中国民族》2005年第1期。
(45) 参见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46) 参见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7) 参见张晓:《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和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杨文炯:《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吴楚克:《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
(48) 参见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49) 参见和跃宁:《浅谈德宏州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国家认同》,《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50)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2页。
(51) 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2) 参见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53) 参见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4) 参见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
(55) 参见李红杰:《论民族国家及其选择的多向性》,《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辩证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6) 参见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57) 参见王建娥:《族际政治视野中的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58) 参见李瑞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认同”研究概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59) 参见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60)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1) 参见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8页。
(62) 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3)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64)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65)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第4页。
(66) G.Poggi,The Stat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01.
(67) 参见陈志明著、罗左毅译:《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68) 参见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69) 徐黎丽:《论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70) 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征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71) 参见李崇林:《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探析》,《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72) 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73) 参见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74) 参见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75) 参见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76)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77) 参见周建新:《和平跨居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78) 参见陈心林:《认同的层次与变迁——潭溪土家族的个案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79) 参见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
(80) 参见王纪芒:《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4期。
(81) 参见胡青、马良灿:《回族家谱的三个维度:族源、族规与人伦》,《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
(82) 参见张海超:《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罗慧翾:《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理论视野》2009年第8期;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栗志刚:《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内涵》,《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83) 参见[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4) 参见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5) 参见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86) 参见吴羽、姚燕:《“国”与“家”的联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87) 参见王文光、张曙晖:《利益、权利与民族认同——对白族民族认同问题的民族学考察》,《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
(88) 参见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认同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