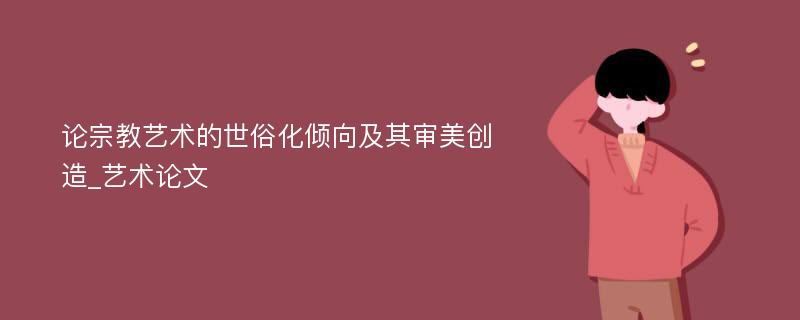
论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及其审美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俗论文,倾向论文,宗教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从宗教艺术发展史看,宗教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宗教艺术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常通过艺术的描写达到谐调一致。宗教艺术的世俗化体现了人类快乐的基本本能及其对欲望的追求;民间的世俗意识也深深影响到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如宗教艺术与民间节日、风俗的相结合,宗教故事在民间产生的变异等等,使宗教艺术得到“俗”的改造;宗教艺术的审美造造也仍然采用世俗的方式来进行,世俗化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宗教艺术美学效果与宗教效果的创造。
关键词 宗教艺术 世俗化 民间世俗意识 世俗化渗透 审美创造
从宗教的目的与要求看,宗教总是把天国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相对立的。宗教所孜孜追求的就是要灭绝世俗的享受,宣传的就是尘世的琐微与卑下,以衬托出天国的神圣与美好。但是,宗教在创建自己的教义体系和弘教时,却不可能与现实的世俗社会相脱离,而且宗教想象所创造的神圣形象与神圣境界也不可能毫无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相反,为了推销教义并使其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宗教还要有意识地与世俗社会相适应,并选择恰当的宣传方式。宗教艺术作为宣教辅教的一种方式,在世俗化一点上也就首当其冲,而且最为突出。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随着宗教艺术创造者身份与思想的越来越复杂,宗教艺术中的世俗化成分也就愈来愈多,愈来愈浓。从宗教与宗教艺术发展史看,事实证明,宗教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宗教要存在下去,就必然要与世俗社会相调适,而在这种调适过程中,宗教及其宗教艺术就要接纳世俗的内容,在有些时候甚至宗教与宗教艺术还对社会的世俗化起到某种推进作用。
一
不管怎么说,宗教艺术中始终表现出追求神圣与肯定世俗的矛盾。作为宗教理想,自然提倡人应该为天国服务,要抑止住人的一切本能欲望,包括人的快乐本能与享受本能。但是在具体的宗教训诫与艺述描术中,宗教又不得不承认了人的本能欲望是难以遏止的,比如《圣经》中的原罪故事,亚当、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味美可口的果子,这说明人所具有的感官欲望与美的愿望是天生的。《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在经过6天的创造工作以后,也要象人一样休息与享受一下,于是有了星期日,他同样不能免除人的享受本能的支配。伊甸园中,也到处充满可以满足人的感官欲望的树木花草与食物,“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①。《圣经》中的《雅歌》是一篇描写爱情的诗篇,其中的许多比喻采用的就是以色味诱人的果子来形容爱情充满心间时那种快乐感受的: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
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又如:
我妹子,我新妇,
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并风仙花与哪哒树,
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
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
北风啊,兴起!
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
吃他佳美的果子。
这最后一节诗内虽然隐含着性爱,但这种优雅的比喻却是以一种世俗享受出现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圣经》的神圣,另一方面也使世俗的爱情显得神圣化。因此《雅歌》中的爱情描写是一种宗教情调与世俗享受相混合的艺术描写。神圣与世俗的矛盾正是通过这种艺术描写谐调一致的。
宗教中的天堂与仙境,也并非是宗教所推崇的那种禁欲主义的超尘脱俗之地,相反,许多宗教中的天堂与仙境则是一个充分享福的处所。宗教对来世的允诺最主要的就是享福与快乐,而这些幸福与快乐又都是从人间搬去的。这也就是说人在世间所能与所愿望享受到的东西,在天堂与仙境中同样可以享受到,而且对它们的享受更加随心所欲。中国道教的仙境,在道教艺术的描写中往往是带上很浓的世俗色彩的。如《太平广记》卷七○引《北梦琐言》中写张建章海上遇仙女,受女仙招待,“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太平广记》卷四七写唐宪宗游海上仙山,饮龙膏之酒,“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等等,这些描写无不带有将仙境世俗化的倾向。这真是“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道教传说还说淮南王刘安升仙时竟能将家中的鸡犬也一同带到天上,使神仙生活还带上鸡鸣狗吠的田园村落色彩。魏晋神仙道教还创造了一种“地仙”的理想境界,成为“地仙”的人,既可在人间做官,享受人间幸福,又能在想做“天仙”时服下成为“地仙”时剩下的半剂金丹飞升上天。“地仙”生活正是世俗生活的补充与延长,也正是神仙们想充分享受世俗生活而又不碍其在天国永久享福的最现实的选择。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还表现在神与凡人的融合性上。道教认为人人皆可成仙,只要人遵守道教教规,服金丹,修长生术,就可进入神仙境界。在道教小说《列仙传》的仙人队伍中,有帝王,也有宫女、门卒甚至乞丐,有商人、医师,也有补鞋的、磨镜的。道教小说中流行最广的八仙传说,其人物均由凡人修炼而成,都经历过贪嗔痴爱的考验。神仙道化剧中的神仙形象几乎都是人神参半的混合体。佛教艺术中的大肚弥勒佛像,也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形象。他袒胸凸肚,裂嘴呵呵大笑,一副享尽人间幸福、化天下一切不快之事为快事的快活神情。还有济公,本俗人出家,但却嗜酒贪肉,出入妓家,疯疯颠颠,于颠狂之中又常济穷护教,不乏菩萨心肠,为众生排忧解难。这些神佛形象,无不充满世俗的生活情调,并流露出人生应有的享受欲望。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还体现在它对王权的依附上。两晋时期,佛教已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主动地与封建王权相调适。到南北朝与唐代,佛教更出现了国教化的迹象,开始带有一些官方的性质。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多少反映出僧侣已为官方所控制的趋势。僧侣也有意依附王朝,求得王朝的支持而加以发展。这种趋势反映到宗教艺术中来,就是佛教艺术对皇帝大臣的有意奉迎,以及官方意识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如北魏时斯沙门统昙曜负责开建云冈石窟,为了突出北魏皇帝的教主地位,就有意将几尊大佛按照北魏几位皇帝的相貌加以雕塑。敦煌变文中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在叙述讲经功德时,则明显表现出是对皇帝、朝廷卿相生活的祝愿:
伏愿我今圣皇帝,宝位常安万万年,
海晏河清乐泰平,四海八方长奉国。
六条宝阶尧风扇,舜日光辉照帝城。
东宫内苑彩嫔妃,太子诸王金叶茂,
公主永承天寿禄,郡主将为松比年。
朝廷卿相保忠贞,州县官僚顺家国。
普愿今朝闻妙法,永舍三涂六道身。
佛前坐持宝莲花,齐证如来无漏体。
有的讲经文还把皇帝比作佛,把王法比作佛法。在讲经文说完佛德以后,还要说一句“亦我皇帝云云”之类的捧场话。对王权依附所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能发展寺院的经济。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施舍以及支持,常使寺院拥有大量财物和土地。魏晋至唐,一些寺院僧人因为皇帝的宠爱,而过着豪华的享受生活,而一些寺院的建筑也辉煌无比,俨然一座人间乐园。难怪当时连许多皇宫中的公主、嫔妃也愿意在寺院中入尼修道。寺院做法事时还举行各种伎乐活动,《洛阳伽蓝记》载:“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②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伎乐歌舞状况。如第172窟南北壁上大型“净土变”画面中,就有佛说法时前台置伎乐歌舞的场面。实际上,佛与天部诸神也要享受伎乐,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伎乐”、“歌舞天人”,都是轮流为诸天作乐的,是供养佛的“伎人”。“飞天”形象的大量出现,也展示出人类快乐的基本本能及其对欲望的追求,实则也代表人间信众的快乐欲求。
二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还与民间世俗意识的影响与渗透是分不开的。
宗教艺术是为宗教的宣传服务的。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使宗教教义更能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宗教艺术首先采用世俗的方式进行宣传。在印度,佛教常常与戏剧携手,在戏剧中灌输与宣传佛教的教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采取了造像、转读与唱导等形式。佛教造像本来是为了僧徒观像坐禅开悟的,但为了吸引一般百姓,佛教的像教法则主张应该首先使百姓从感官上接受佛像,进而崇信佛祖,皈依三宝。慧远在《襄阳造丈六金像颂》中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从而使得“四辈悦情,道俗齐趣,迹响和应者如林”。慧远在庐山上首创唱导制度,也针对不同的对象而选择不同的方式,对君王贵族,就引经据典,语言上也华丽典雅;而对一般庶众,则用通俗的形象和具体的事例来宣唱;如果是“山民野处”,则又是“近局言辞,陈斥罪目”③,直接讲述他们的罪孽,劝说其信佛皈教。可以说,唱导早就露出了“适俗”的倾向。唐代的俗讲,为了适应听众的需要或吸引人布施,则干脆抛弃南北朝时期谈空说有、宣讲教义的形式,而是专门摄取佛经中的某些故事加以发挥,甚至还出现“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④,以至于朝廷也出面来干涉了。敦煌变文中,除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思想外,也夹杂着世俗的忠孝意识。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目连对母亲的孝就是宣传的重点。目连救母故事及其以后演变而成的多种目连戏,之所以受到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宣传孝的成分起了很大的作用。变文中除讲宗教故事外,还讲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也演唱民间传说故事,如《孟姜女变文》,还演唱当代的时事,如《张议潮变文》。这些非宗教故事的内容中既掺杂进一些宗教观念,但主要仍是世俗的忠孝报国、从一而终的伦理思想。另外,即使是在一些直接从佛经中改写过来的变文故事中,也同样渗透了民间的世俗意识。如《欢喜国王缘》是从《杂宝藏经》卷十《优陀羡王缘》改写的,经文中讲的是有相夫人出家,因功德升天;国王也让位于太子随之升天。而变文中,有相夫人持斋戒而升天,王也持八斋戒而升天,夫妻共住天上,享受净土园地之福。八斋戒则是戒律与人伦礼教的结合;夫妻共升天而永不离别,则把民间现世的夫妻爱情搬到了天上。还有《丑女因缘》,丑女因为深深忏悔前罪,为佛祖世尊亲自垂赐加被,忽然间就变成了容貌端庄、举世无双的美女,与驸马一起在人间过着幸福的生活。变文的重点也放在对现世幸福的向往上。
宗教艺术与民间的节日、风俗相结合的现象,也是民间世俗意识向宗教艺术渗透的重要途径。中国各地的节日必要迎神、游神,而佛教、道教的庙会又必然要演出宗教性戏剧,还有各种神诞节也要举行祭神歌舞活动。这些活动由于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往往演变成全民性的娱乐活动,也就是说,名为娱神,实为娱人。如每年夏历的7月15日,佛教要举行最隆重的“盂兰盆会”,而道教则把这一天定为“中元节”,热热闹闹地上演各种仙佛鬼神故事,盂兰盆节上演的《目连戏》,本是佛教用以宣传佛教因果报应与超度亡魂、地狱轮回思想的,是盂兰盆会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但经过长期的演变,后来它的娱神、驱鬼、祈福的宗教功能就不只局限于佛教了,在道教的打醮活动中也出现,民间的驱除疫疠、祓除不祥的驱鬼活动也用它。当演到招鬼魂与驱鬼魂时,百姓则齐声呐喊,鞭炮齐鸣,热闹非凡。这正是民间世俗的功利意识对宗教艺术的渗透。
民间宗教节日与祭祀活动中的宗教戏剧演出,为了迎合民众心理的需要,有时还插入俗戏,使俗戏与宗教戏混合为一,让宗教戏得以扩大延伸。不仅如此,一些与宗教禁欲主义大相悖逆的“淫戏”也时有出现,甚至使演出场地成为肆行谑笑、有伤“风化”的场所。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地方官就下令禁止在迎神赛会上演出“淫戏”。清代周际华在任地方官时就曾出令《禁夜戏淫词示》,其中说到:
民间演戏,所以事神,果其诚敬事修,以崇报赛,原不必过于禁止。
惟是瞧唱者多,则游手必众;聚赌者出,则祸事必生;且使青年妇女,涂
脂抹粉,结伴观场,竟置女红于不问,而少年轻薄子,从中混杂,送目传
眉,最足为诲淫之渐。更兼开场作剧,无非谑语狂言,或逞妖艳之情,或
传邪僻之态,说真道假,顿起私心,风俗之浇,皆因于此。⑤
民众的世俗意识也促使宗教艺术作出某种迎合与改变。而宗教艺术,也正是世俗的方式与意识,在寓教于乐之中向观众灌输宗教精神与宗教意识的。
一些宗教故事由于在民间流传,也受到民间世俗意识的影响,发生了变异,最后成为了世俗艺术。如白蛇的故事,本是一个民间宗教故事,说的是蛇妖经常出来害人,最后为道教真人或佛教法师降服。此故事在南宋时已在民间流传,最初白蛇是作为害人的妖出现的。明代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所选的《西湖三塔记》中,白蛇就纯粹是一个害人精。但经过民间说唱艺术的进一步演化,到了后来文人黄图珌写成的《雷峰塔》传奇里,白蛇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妇女形象,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所爱之人的关心爱护以及最后的被镇压都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主题也转化为谴责男子负心的世俗内容。虽然其中白蛇还是妖,但人情味却很浓,她并不害人,有着温柔体贴的性格,执著地追求人间的爱情。结尾“塔圆”当中虽然也宣传了佛教的色空思想与宿命论观点,但戏的前半部分则充满生活气息与世俗情调。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悲剧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爱情悲剧。因此,象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是在宗教的外衣下,潜藏着人间否定暴政、追求自由、渴望幸福的非宗教性的世俗艺术作品。
三
宗教艺术自然也包含着对美的追求,它也有它的美学理想与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宗教通过宗教艺术将其宗教理想美学化、艺术化,换句话说,宗教艺术起到了一个将宗教理想进行美学转换的作用。比如,道教的神仙境界、佛教的西方净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天堂理想,无不都是通过优美的艺术语言,将其美好的情景描绘出来的。但是,正如我们前文说到过的,宗教的天堂理想与神仙境界并非完全没有世俗世界的影子,宗教艺术的美学创造也仍然采用世俗的方式来吸引信徒,实际上是把人的世俗欲望加以升华与净化,然后再以超现实方式表现出来。神仙世界与天堂理想通过美学的创造因而更具有宗教效应。
因此,宗教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世俗化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其美学效果与宗教效果的创造。
宗教艺术在其美学创造中之所以会受到世俗意识的影响,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由于艺术创造本身的审美特性决定的。宗教艺术也是艺术。艺术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源自现实又反映现实,追求理想又创造理想。宗教艺术要面对世间,教育众生,同样不能脱离现实,而且还要从世间取材,将世俗生活宗教化、艺术化。象《圣经》中的《雅歌》,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的爱情诗歌,许多诗句颇有民歌风味,它通过男女恋人间的相互爱慕之情的倾诉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爱情生活的渴望。佛教中的许多寓言故事,也大多取自于民间,虽然其中也寄寓着宗教性的劝戒与警示,但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幽默、诙谐、机智与哲理又带有相当浓厚的民间色彩与世俗色彩。实际上,这是宗教将民间的故事窃为己有,虽然给它涂上一层宗教色彩,但其民间艺术的审美特性仍掩盖不住。另一种方式则是,宗教艺术在创造艺术形象时,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由于现实的力量,往往使得世间生活的气息盖过宗教的意味,美的力量突出,宗教意义退为其次。比如拉斐尔所创造的宗教艺术形象,就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他的《西斯廷圣母》图中,教皇西斯廷二世虽身披华丽的绣衣,但神情却显出一副忠厚长者的纯朴性格,他正做着恭迎与引路的姿态;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基督,从云中飘然降落。那健康而壮实的身材、简朴的衣装和赤裸着的双足,象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妇女,其温柔的大眼中含有一种哀伤悲悯的眼光,又象是一位人间的慈母。据说,圣母的形象是拉斐尔观察了许多美丽的妇女,然后选出最美的一个来做模特儿加以创造的。他还说过由于美的人太少,还不得不求助于头脑中的理想的美的形象。这种尊重自然与理想创造的结合,使这幅著名的宗教画远远超出了它的宗教意义,而成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的艺术典范。路加·特·来登的宗教画《玛兰特纳的舞蹈》,画面表现的是法兰德斯乡间节日的欢乐气氛,而圣经中的宗教人物却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委罗内塞喜欢用圣经中的故事来表现庞大的宴会场面,他的《西门家的宴会》,因为画进了太多的现实人物,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以致于他最后不得不把画改名为《利未家的宴会》。他的宴会画反映的主要是当时人们寻欢作乐的豪华生活,而画中的基督和圣徒们反而成了点缀。
其次,由于宗教艺术创造者思想、性格、美学情趣和生活背景与宗教的要求形成差距,他们在创造宗教艺术作品时并不一定完全以颂神与宣教为目的,而是融进了时代的精神、个人的情感与美学理想,甚至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制约了他的创作,这便使得他所创造的宗教艺术作品具有较浓的现实内容和世俗色彩。正是这种现实的内容与世俗的色彩,才使得宗教艺术作品超越宗教的内容,突破神性的束缚,而闪现出美的光辉。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由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和重视艺术传统的创作思想,他所创造的雕塑《哀悼基督》、《摩西》等,保持了相当强的民族与民间色彩,更突出了生活的真实感与性格的具体化。《哀悼基督》中的圣母一手枕着死去的基督,一手摊开,表现出一种无望的悲伤。那俯首沉思的神态流露出一个母亲的慈爱和忧思。这位怀抱着儿子尸体的母亲,令人想起了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母亲,她亦是作者祖国的象征。艺术家通过这一宗教题材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摩西》所表现的是摩西突闻事变时的一刹那间的神态,集中突出了他嫉恶如仇和大义凛然的内心力量。《摩西》的创作正值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勾结西班牙军队在普拉图附近大量屠杀佛罗伦萨人之后,当时艺术家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愤慨,一种对叛国者无比愤恨的感情就凝聚到了《摩西》的创作上。圣经中曾写到当摩西得知有人因恶人引诱而成了民族叛徒时,一怒之下摔碎了法版。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就表现摩西听说人叛变后的愤怒神情。艺术家正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于宗教题材的创作中,使其表现出现实感和人间的生气。米开朗琪罗曾经在保卫共和国的战争中与人民站在一起,反抗入侵的西班牙和教皇的军队,他自己还亲自担任过城防工事建筑的总领导。抵抗失败后。米开朗琪罗也成了俘虏,被教皇命令去完成美第奇家神庙的雕塑与壁画。这时的米开朗琪罗无比痛苦和悲愤。于是,在创作壁画《最后的审判》时,则通过描绘基督的审判倾注了艺术家惩恶扬善的良好愿望。在这幅宗教画中,一大群为信仰而殉难的圣徒,各自拿着受害时的刑具向基督诉说自己的冤屈;彼得捧着大钥匙,安德列带着十字架,而巴托罗米欧甚至提着他被迫害牺牲时剥下来的人皮。有的研究者指出,这张人皮画上的面孔就是米开朗琪罗自己。画面中间的基督在听说圣徒们的倾诉后,无比沉痛,他高举右手即将发生最后的判决。因此,画面的意义实际已超过宗教题材的善恶报应思想,而带有非常现实的反抗内容,这使此画的艺术魅力变得更为丰富而深刻。
再次,宗教艺术又是受社会的美学思潮、美学趣味影响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趋势,艺术总要表现时代精神与人民要求,艺术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宗教艺术的发展史表明,它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中,也必然表现出世俗的倾向。它的适俗和它与社会美思潮、美学趣味的融和,在意义上是相近相通的。这种“俗”不仅是宗教艺术反映的内容是现实的,而且在形式上也受时俗的影响,在美学趣味、美学崇尚上也是与世俗社会一致的。魏晋南北朝玄学追求简约,士大夫们追求清逸高超的脱俗人格,更讲究人的神明与内秀,社会上的审美趣味也走向重神、贵清、贵自然,这无论是在艺术创作上或是艺术品评、人格品评上都表现出来。这种时尚影响到当时的宗教雕塑与绘画之中,则有了那种秀骨清相的佛教人物,如顾恺之设计的维摩诘像,有“清赢”之容,为的是表现出人物高度的智慧与脱俗的风度。连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设计的道教人物张天师也是“形瘦而神气远”。北朝的菩萨亦与当时社会的动乱和苦难的悲剧气氛相适应,充满了忧患感、悲凉感。还有那些苦修像则更是一副苦楚相。如敦煌莫高窟第248窟(北魏时作)中心柱西向龛的苦修菩萨像,眼窝深陷,皮肉松驰,肋骨凸现,枯瘦衰老。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北魏时造)的迦叶像,虽然面部被盗,无法得知其表情,但他的身姿、动态以及前胸肋骨一条条显现, 厚重的袈裟和手中的锡杖,都表现出他是一位历经长途跋涉、经过艰辛磨难的苦行僧。而莫高窟北朝壁画里,绝大多数主题都表现宗教“忍辱牺牲”,大量画面刻划了人的生离死别,人被水淹、火烧、狼吃、虎啖以及被活埋、钉钉等悲惨场面。虽然描写的是宗教题材,但处处都反映出人间苦难社会的影子。唐代宗教壁画中,供养人像则高度发展,世俗生活越来越在宗教壁画中占有较多的成分,连菩萨也象杜甫《丽人行》诗中所描写的妇女一样,丰腴健硕,装束大胆飘逸。盛唐时代肯定现世、重视自我的美学理想同样在宗教艺术中得到充分反映。宋代,则进一步出现俗世味极浓的罗汉像,寺庙中的罗汉像千姿百态,充满现世生活的气息,罗汉像还因此与老百姓的命运连在一起。⑥象贯休所作的罗汉图,“那突目偃眉,张口赤脚的罗汉,充满了现世一般的市民表情,他们不再是高高的台座上不可企及的有超自然能力的神佛,他们事实上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街坊邻居”⑦。在欧洲,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兴起的时候,女神维纳斯的画像则代表了一种新美学思潮的崛起,如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就使女神维纳斯带着文艺复兴初期人间的哀愁忧思和羞怯,踏着海的泡沫,乘着海贝登上欧洲大陆了。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理想代替中世纪禁欲、变态心理的希望之光,威尼斯画家提香笔下的维纳斯则是商人阶层现世享受主义与富足奢侈生活的反映,也是爱与肉欲的现实反映,如他的《乌比诺的维纳斯》,则十足是一位百无聊赖的宫廷贵妇。威尼斯人借对维纳斯的描绘,展示了一幅幅人世间的生活喜剧与爱情故事,那种带有几分野性、放荡、献媚以及挑逗的女神像,已全然失去神的意义,而变成俗世对肉体与爱的官能追求。它剩下的只是一个宗教的外壳了。
在当代西方社会,许多非传统宗教和教派都广泛地使用摇滚乐来布道,并按现代音乐节奏跳现代舞,有时还以电影、幻灯的形式放映以《新约》为题材的影片和幻灯片。美国现代派神学家哈维·考克斯甚至断言,如果教会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应当把游戏成分更多地使用于崇拜的仪式,并为教徒充分放松情感创造更多的条件。⑧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西方当代社会的审美思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西方工业化社会中的宗教心理与社会心理,由于人们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的增大,造成了精神的极度焦虑,人们包括教徒更需要寻找情感的渲泄与释放。这种新的宗教艺术的出现,似乎又回到了宗教艺术最初的意义上了,即追求本能与感官的快感。人的本能追求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渗透到现代宗教艺术中来,其间也透露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对自身存在与生命价值的一种探寻。如同“绿色和平组织”一样,他们对环境与自然的注重,不啻于一种宗教的信仰和崇拜,其主旨仍是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命运。
世俗向宗教的挑战,向宗教的渗透,正是促使宗教艺术摆脱神性的束缚,大踏步迈进美的殿堂的催化剂和推动力。
注释:
①《圣经·创世纪》。
②《洛阳伽蓝记》卷一“景宁寺”条。
③《高憎传·唱导论》。
④唐·赵璘:《因话录》。
⑤清·周际华:《家荫堂汇存从政录》。
⑥在江浙、四川、云南等地区,民间流行这样的风俗,认为进入罗汉堂,随意指一位罗汉为起点,顺右手方向计数,数到与他本人年龄相等的那人数时,所指的那位罗汉就将保佑数数者当年的运气。数数人自然要在这位罗汉面前多烧几炷香。
⑦蒋勋:《美的沉思》,台湾雄狮美术图书公司,第125页。
⑧H·考克斯:《精神的诱惑》,伦敦,1974年,第156~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