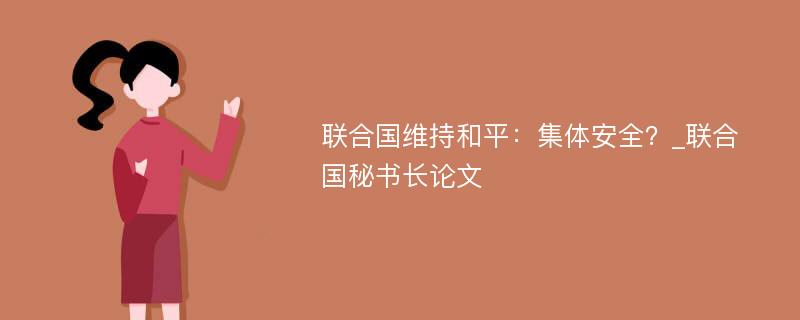
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联合国官方网站统计,自1948年6月联合国监督阿以战争停战协定的“停战监督组织”成立以来,联合国已经在全球开展了60项维持和平行动(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①
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实现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宗旨重要手段的维和行动是一种集体安全。“联合国承担的集体安全行为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军备控制,……另一类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②“联合国维和机制成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行动机制,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庄严承诺”。③ 小约瑟夫·奈也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归于集体安全之列。④ 笔者对此持不同的认识。联合国维和所经历的五种模式及其体现的四大特点均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的差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一、集体安全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是国际社会设想的、 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主要是来自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从而维护每一个国家安全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是国际关系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 for all & all for one)原则的推广。⑤
集体安全与集体防卫(Collective Defense)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成员国均承诺帮助他国抵御外来攻击;被进攻的受害者都预期自己的防卫力量可以得到其他国家力量的补充。尽管如此,就行动意图和模式而言,二者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集体防卫的目的是国家间彼此联合以抵御共同的敌人。而集体安全是一种针对普遍侵略的防卫政策,即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者,无论侵略者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敌人。集体防卫仍属于权力政治的范畴,而集体安全一词已经成为与传统权力政治决裂的一个符号。⑥
集体安全以两条理念为基础。一条是理想主义的思路,认为他国的侵略罪行将激起本国道德上的愤怒,从而拿起武器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者。另一条是现实主义的思路,认为“世界的和平不可分割”,因而如果任何一个侵略者在任何地方都被压倒性的力量所制止和吓阻,那么所有其他潜在的侵略者都将会理解这种警告,并不再制造威胁。⑦
集体安全包含了两个基本原则:威慑原则(Principle of Deterrence)和普遍性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威慑原则指的是, 试图使用武力者将立即遭到一个反侵略国际联盟的反击;普遍性原则指的是,所有国家对侵略者的认识一致,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到反侵略的行动中。⑧ 由此可见集体安全的目的特征在于威慑或制止侵略;手段特征表现为可采取外交、经济、军事制裁,军事制裁时可以使用武力;成员特征表现为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
包韦特指出,集体安全制度必须具备共识、承诺、组织、会员普及和权力分散五大条件。所谓共识,即组织的成员必须对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具有共识,将维持世界和平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所谓承诺,即各国对任何地区、任何时间所发生的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的行为,均承诺依照集体安全的规定予以制裁。所谓组织,即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必须包括中央决策机构,它有权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动用集体安全力量。所谓会员普及,即参与集体安全制度的国家愈多愈好,最好全球国家均参与其中,如果任何重要的国家未能参与其间,则集体安全的力量必然相对减少。所谓权力分散,即各国权力分配如果大致平均,则有利于集体安全的维护;若各国权力分配悬殊,而被制裁的侵略国是超级强国时,则各国“我为人人”的意愿和能力将大为降低,甚至根本不会存在。⑨ 由于现实中上述集体安全的五大条件难以全部具备,因此在设计集体安全制度时,常常不得不迁就国际现实,制订并非完善的规定。
集体安全是对均势可以维持国际和平观念质疑的产物,也是对一战以前国际形势反思的结果。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建议”,其主张建立的国际联盟较全面地体现了集体安全的原则。二战结束前期,在吸取国际联盟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以集体安全为原则,国际社会建立了联合国,以期“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之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行为之破坏,……”⑩ 与国联的集体安全设计中实行“普遍一致”的原则不同,联合国采用了“大国一致”的原则,即仅仅赋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然强调所有成员国共同参与,以集体的力量来维护国际和平。毋庸置疑,联合国是建立在集体安全理念之上的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但是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重要举措之一的联合国维和是否属于集体安全范畴呢?从联合国维和的定义、维和的模式以及维和的特征入手,将其与集体安全进行仔细的比较,所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联合国维和
(一)联合国维和的定义
在联合国出版物《蓝盔——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回顾》中,维持和平行动被定义为“由联合国采取的、旨在帮助维持或恢复冲突地区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但是没有强制力的行动”。(11) 马科拉·格尔丁认为,维和是由“联合国主导的、以帮助控制和解决武装冲突的一种机制”。维和的五条原则分别是:维和行动是联合国采取的行动;维和行动的部署须征得冲突各方的同意;维和人员必须中立、公正;会员国依据自愿原则为维和行动提供人员与设备;维和过程中应遵循最小限度使用武力原则,武器只能用于自卫。(12)
维和是联合国的首创和发展。《联合国宪章》中没有出现“维和”一词。哈马舍尔德称它属于《宪章》“第六章半”,置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传统方法之间,即处于调解和实况调查(第六章)以及诸如禁运和军事干预等更有力的行动(第七章)之间。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上,安理会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联合国大会起着审议和监督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则执行安理会或大会的决议。但在实际的联合国维和过程中,三者的职权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维和行动通常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创建和确定,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中必须有9 个成员国投赞成票,如果5个常任理事国有任何一国对该提案投反对票,提案就不能获得通过。(13) 尽管安理会仍然是权威的机构,但联合国大会曾试图援引“团结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单独授权组织维和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的独立判断和主导行动日益显著,预防外交职能基本上由联合国秘书长包揽。
(二)联合国维和的模式
维和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共经历了五种行动模式,即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第二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
1.宪章制度模式
联合国维和源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它是联合国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独立发展的创新机制。
联合国根据宪章的相关规定,提出了由会员国通过与安理会的特别协议,向联合国提供军队,使之用于制裁破坏和平或侵略的国家的机制。并且,联合国的军事制裁在否决权的限制下不能对付大国,但是只要大国意见一致,足以对付其他国家。
宪章制度模式是最接近于集体安全范畴的维和模式,其主要规定见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但不仅限于该章,还散见于宪章的多个章节与条款。其特点为:第一,确立了集体安全的优越地位。(宪章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款和第五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二,强调安理会的重要作用。(第二条第七款、第一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三,设立军事参谋委员会。(宪章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期望大国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宪章第一零六条)(14)
1948年就巴以冲突而派遣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是联合国部署的第一次维和行动。它与1949年成立的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一道,成为了联合国宪章制度维和模式运行的雏形。但是,由于冷战爆发后大国意见难以一致,这种接近于集体安全范畴的维和模式难以运行。
2.“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
冷战兴起后,美苏两国在全球的竞争与对抗激烈,全球各地的冲突或多或少皆会涉及美苏双方的利益。美国考虑到安理会的行动若对西方有利,必然难逃苏联的否决权。为使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措施不再受制于苏联否决权的束缚,1950年美国主导联合国通过了“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希望以此改变宪章制度模式的维和行动,使之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决议模式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它表面上尊重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要责任,但实际上将冷战时期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交由联合国大会承担。第二,1950决议后的集体安全制度不再强调以大国团结为中心,而以联大中的中小国家所形成的多数会员国为中心。第三,大国不再有免于集体安全制度制裁的特权。大国在大会上没有否决权,无法以它来对抗大会的多数决议。(15)
决议维和模式在朝鲜战争中诞生,也在朝鲜战争持续的阴影下逐渐消失。随着1950年8月苏联重返安理会舞台,并力图阻止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武装行动,以及1955年后大批新会员特别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大的有效控制不断下降,使得该维和模式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
3.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
冷战时期的集体安全制度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促成了联合国“预防外交”思想的产生。联合国不再关注于集体安全的思想,即不再关注确定和惩罚侵略者,(16) 而是创设哈马舍尔德模式的维和行动。1956年,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根据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以往维持和平的经验,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维和的制度设计,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该项新制度主张联合国不能也不宜介入东西双方冲突范围以内的问题;为避免冷战中两大对立集团对地区冲突的介入,应把来自独立国家的军队部署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地带,并为处理冲突潜在根源的外交努力提供时间和喘息余地。
这项新制度便是通称的“维持和平行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s)或第一代维持和平行动,即联合国向发生冲突的地区派遣不具有执行行动权力的军事人员,以协助维持或恢复和平。维持和平行动可分为两类:观察团(Observer Missions)和维持和平部队(Peacekeeping Forces)。(17) 综合而言,该模式的维持和平行动具有下列八项主要原则:同意、合作、非执行行动、自卫、不干涉、自愿、弹性以及维持和平的军队多来自中小国家。
哈马舍尔德模式首次出现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1956年,第一支武装的维持和平部队被派往埃及。通过在交战方武装部队之间部署由联合国指挥的非武装或轻型武装军事人员,此次行动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965年2月,联合国大会建立了“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维持和平”一词开始正式使用。至冷战结束前,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绝大部分属于该模式。该模式的联合国维和既不使用武力以强制达成和平,也不负责和平解决争端。
4.第二代维和模式
冷战后期,联合国安理会因冷战原因只能消极维持和平的情形有所改变。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在某些维和行动中兼采维持和平与解决冲突,从而形成“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Second Generati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与第一代维和模式相同,第二代维和也通常是在实现停火以及冲突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开展行动。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代维和是冲突各方允许联合国部队冻结冲突,联合国只负责监督停火以及分隔交战方等事项,对冲突的解决并无任何实质性措施。第二代维和则是冲突各方已就冲突的解决达成协议,授权联合国部队监督协议的执行,包括协助塑造有利于国内和解的气氛、安排或监督选举以便成立新政府,甚至暂时代行政府的统治权。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通常包括两支或三支不同功能的部队,或是由数个不同部门组成的部队,包括传统维持和平的部队、维持治安的警察部队和监督选举的观察团。
安理会首度尝试混合维持和平与和平解决冲突是针对1980年的阿富汗问题。冷战后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机构行动在许多方面是第二代维和行动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涵盖了第一代维持和平行动的各项功能,也充分展现了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缔造和平与建立和平的功能,它所动用的人力物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反映了冷战后期国际形势对第二代维和行动的巨大影响。
5.第三代维和模式
冷战的结束促成了联合国维和模式的新转变,形成了第三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可以溯至1960年联合国的刚果维和行动,其主要特点是:第一,运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的执行行动(Enforcement Actions)权力, 即不征求冲突有关各方或主权国家的同意,强制执行安理会所交代的任务,强制恢复或重建法律及和平秩序。第二,强制性行动不仅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更多地涉及某些国家因解体或内部种族宗教等分歧而爆发的动乱与内战。第三,维和干预的规模和范围扩大,涉及更多的非军事因素,包括了法治、民政管理、经济发展、人权等内容。为了支持这种复杂的维持和平的更大需求,1992年联合国创建了维持和平行动部(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卢旺达、海地等地区的维和行动均属于第三代维和模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对这些国家或实行武器禁运,或授权以政治方法解决内战,或采取必要措施以执行有关协议。1993年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二期是第三代维和模式的典型代表。联合国在索马里内战既没有实现停火也未征得冲突方同意的情况下,向冲突地区派遣了维和人员。由于缺乏政治意愿的支持、卷入索内战而背离中立性原则、强制性行动明显而不够克制,该行动以失败告终,给联合国维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以上五种联合国维和模式并不只是时间上的推进。同一时期可能出现多种维和模式,同一维和行动也可能涉及多种维和模式。尽管如此,五种维和模式的发展,表明了不同时期联合国对不同的维和模式的偏重。值得关注的是,冷战结束后,第二代及第三代维和模式已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新趋势。
(三)联合国维和的特征
经过半个世纪的演进,联合国维和创造了一种如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所称的“无战斗之敌,无战胜之敌,武器用于自卫,效果靠自愿合作”的特殊军事力量,开创了军人执行和平使命的先例,(18) 体现出“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宽泛性”等四大特性。
第一,中立性。维和部队是“无敌之师”,体现了维和行动的中立性原则。维和行动并没有事先设定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维和强调中立的原则,其目的是防止冲突的再发生,以期创造有利的环境,促进冲突双方接触、谈判、达成和平协定,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冲突。
中立原则在维和行动的实践中确立并得以拓展,具体体现为:联合国一般只有在冲突各方特别是驻在国同意后才能部署和平武力,若强制部署维和部队时,则应强调不介入冲突的派系斗争;维和部队的指挥权由安理会授权秘书长行使,实际指挥权由秘书长委派指挥官行使,指挥官向秘书长负责;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时,应强调公正无私,避免妨害有关各方的权利、主张或立场等;大国或是地域接近或是利益相关的国家,原则上被排除在维和行动之外。(19)
第二,非武力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目的是维持和平但非强求和平。维和旨在为最终的和平创造条件,即在冲突地区出现和平迹象并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维持该环境时,适时采取某种形式的维和行动,为通过其他政治、外交途径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维和承担的角色是缓冲性的,与通过强制的武力行动寻求和平有着本质的区别。
维和强调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原始职能是非作战行动的武装力量,军事观察员不得携带武器,维和部队只携带轻型防御性武器且只能在自卫时使用武力。联合国秘书长申明,“蓝盔人员有权进行自卫并保卫他们负责保护的人”,还强调,“不应把这个新‘理论’解释为把联合国化为战争机器的手段,应该永远把使用武力视为最后手段”。(20) 1995年联合国在索马里二期维和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维和行动未经冲突各方同意,动辄以武力威胁,不够克制,且卷入索内战,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该行动的失败让联合国维和意识到了“中立”与“非武力”的重要意义。
第三,自愿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是由联合国会员国自愿捐助的。维和行动的组建是先依照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的决议,由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维和人员的派遣。一般而言,凡是当事国反对的国家,秘书长不会邀请该国出兵。
参加联合国特派团的高级军官、参谋和军事观察员通常都从会员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借调。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员,都是根据本国政府与联合国谈判达成的条件而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他们仍受本国政府管理。自愿派遣维持和平人员的政府有权决定派遣或撤离维持和平人员,并对费用、纪律和人事问题等负责。会员国出兵并非义务,向联合国派遣维和人员完全是出于本国自愿。目前已有100 个国家自愿先后向联合国派遣了维和人员。
第四,宽泛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具有宽泛性,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涉及一国国内的冲突。维和行动最初是处理国家间冲突的一个手段,但在冷战后期,内战和其他国内武装冲突的扩散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始更多地关注一国的国内冲突。冷战的结束促成了联合国维和的转变,安全理事会依据新的合作精神,建立了更加庞大和更为复杂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其目的是帮助执行国内冲突各方达成全面的和平协定。
此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内容具有宽泛性,涉及政治、军事、民事等多个领域。维和行动初期关注的重点是安全领域,涉及军事因素。冷战后期开始,维和的内容逐渐包括了军事与民事两大职能,法治、行政管理、经济治理、人权发展等问题都被列入维和内容。维和行动还在遏制走私、麻醉品贸易和控制人口贩运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三、联合国维和不是集体安全
联合国维和属于集体安全的范畴吗?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从联合国维和的定义、维和的五种模式以及维和的四大特征来分析,答案却是否定的。
(一)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偏离
联合国官方把维和定义为“由联合国采取的、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但是没有强制力的行动,旨在帮助维持或恢复冲突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该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的内涵相差甚远。其一,维和的方式是“没有强制力的行动”,采取的是非武力的途径。集体安全则特别强调成员国“拿起武器”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者。其二,维和的目的是“帮助维持或恢复冲突地区的和平”,即为解决冲突创造条件,间接而非直接创造和平。集体安全则主要是通过成员国对侵略者的共同反击,直接创造和平或直接威慑潜在侵略者。可见,联合国维和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较大偏离。
(二)维和的模式均不属集体安全范畴
1.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与集体安全
宪章制度模式与“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二者的初始设计最接近于集体安全理念,但在现实的运行过程中,宪章制度模式与集体安全产生了很大的偏差,而“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也中途夭折,未能得到真正的实行。
二战后期大国意见的不一致,使得宪章制度维和模式无法真正开展行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武力迄今未能成立,而军事参谋委员会自1948年后也长期无事可为。类似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的举动,主要体现为1950年联合国出兵朝鲜(此次行动从本质上来说不属于集体安全),以及1991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之后的联合国军事行动。但这二者均属于安理会授权的多国部队行动,而不属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范畴。这两次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措施处理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的行为”,会员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而组成的联合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尽管得到安全理事会同意,但完全由参与的国家控制,而不是由联合国指挥,因此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明显不同,(21) 不属于维和范畴,也未被联合国列入其维持和平行动历程的时间表中。
“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最终也未能得到实施。苏联于1950年8 月重返安理会后,有效地阻止了安理会处理朝战问题。中国开展抗美援朝军事行动后,美国的盟国如英国,中立国如印度,皆不愿支持美国领导的联军深入朝鲜作战。1955年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后,美国的势力在联大成为了少数派。在此情形下,若继续援引“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只会给美国带来事与愿违的利益损害。这个曾由美国提议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的维和模式在朝鲜战争中出笼,也在朝鲜战争持续的阴影下逐渐终结。
2.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维和模式与集体安全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维和模式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得以长时期实行,但由于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与遵循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使得这些模式与集体安全体制相去甚远。
第一代维和模式是依据1956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维和三原则而形成的。这三条原则分别为:第一,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当事国的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第二,维和部队的部署必须得到冲突双方或一方的同意,这是建立和部署联合国维和首要和必备的条件;第三,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以“同意”、“中立”、“非武力”为内涵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成为了第一代维和模式的行动准则。这些原则与集体安全的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
冷战后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多采取第二代、第三代模式。这二者虽然突破了第一代维和模式的一些内容,如第二代模式强调决议的执行以及参与战后的建设,第三代模式出现了不征求与冲突有关的各方或主权国家的同意,强制执行安理会所交代的任务的情况。但是这两种模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得到的成效及教训,都让联合国更加重视“中立原则”与“非武力原则”在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第二代、第三代维和模式也都不属于集体安全的范畴。
(三)维和特性与集体安全存在差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联合国维和行动已与最初的集体安全的设计相距甚远。维和行动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与“宽泛性”四大特性表明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而更接近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就“中立”特性而言,维和的中立原则与集体安全的要求是根本背离的。维和部队是“无敌之师”,事先没有明确的行为体指向,没有设定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维和行动的组成人员来自于与派遣国没有利害冲突的国家。维和行动实行时,强调“不应该偏袒冲突中的一方而反对另一方”,不应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联合国维和“不是用来影响任何内战或内部政治冲突的结果”,并且“不愿意卷入冲突当中”。(22)
相比较而言,集体安全却是“非中立”的,它的针对性和偏向性是明确的。集体安全概念的一个基石即是“全体对付单一”(all against one),(23) 强调要以集体的力量对付侵略,改变当前的力量分布状况。虽然国家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中仍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但因为侵略者对由各国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和平与法律的违反危及(或间接危及)每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因此,集体安全认为每一个国家在保卫每一个被侵略的受害者方面都拥有“国家利益”,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都能联合起来,以绝对的对抗性的优势抗击侵略。(24)
就“非武力”特性而言,联合国维和行动并非强求和平。这与集体安全可以通过强制的武力行动实现和平有本质的区别。维和行动一般由维持和平部队、维持治安的警察部队、监督选举的观察团等共同组成,其中文职官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维和部队的原始职能是非作战的武装力量,武力是其用于自卫或保卫相关人员的最后手段。
维和是禁止使用武力的,而使用武力对于集体安全体系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集体安全制度对付侵略者的手段也多种多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旨在使潜在的侵略者在发动侵略前权衡利弊,使其意识到发动侵略的巨大后果而放弃侵略的打算,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但是,集体安全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共同体成员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本质上是“利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正式联合”。(25) 因此,“集体安全承认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核心,认为增进国际安全的关键在于恰当地管理军事力量”,“一旦侵略者发动侵略行为,使用武力来阻遏、击败侵略者就不可避免”。(26) 由此看来,维和只是“联合国试图但却不能提供集体安全的一种替代物”,(27) 不属于集体安全范畴。
就“自愿”特性而言,维和行动组成人员的自愿性与集体安全制度中抵制侵略的自动性是有区别的。维和人员的组成是会员国自愿提供的,提供国政府有权与联合国协商条件,有权决定派遣或撤离人员。会员国也可不派遣人员参加维和,这不违反任何规定,也不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截至2004年3月31日, 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排名前十位的分别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印度、加纳、尼泊尔、乌拉圭、约旦、肯尼亚、埃塞俄比亚。(28)
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以互助原则为安全基础,自动抵抗侵略是一种义务,这是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或规定履行义务的一种表现。对于承诺奉行集体安全政策的国家而言,将自己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保存本国的军事力量,以平衡那些被视为是对本国或盟国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权力是不允许的。因为在集体安全制度中,对任何国家的攻击被看成是对每一个国家的攻击,即当该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时,其他成员应该对其进行援助,即便它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应这样做。在集体安全中,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即是他助。
就“宽泛”特性而言,冷战后联合国维和更多涉及一国国内冲突,更多涉及除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职能,这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差别。根据联合国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1990年前的1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属于国内冲突的仅为3项; 而在1990年后的4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内冲突达到33项。(29) 冷战前的联合国维和较多履行军事职能,如执行维持停火协议、隔离冲突方军队、监督撤军等任务。冷战后,除了传统的军事职能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职能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政治方面,维和行动有时必须充当临时行政当局,组织或监督大选、协助实行宪法或司法改革;经济方面,维和行动通过修建基础设施、筹集资金等帮助冲突地区进行经济重建;人道主义方面,维和行动通过扫除地雷、协助难民安置、提供食品和医疗等实施人道主义救助;人权方面,维和行动通过对当地机构的执法监督,确保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30)
对比之下,集体安全是以威慑和制止侵略来维护每一国家的安全,因而其根本目标不是针对国内冲突,而主要是针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强调保护成员国免受任何国家的侵害,以此保证对所有侵略者构成威慑,并设定在此过程中对一个或多个实际侵略者的惩罚将会吓阻潜在的侵略者。此外,尽管集体安全可以采取外交、经济或军事制裁等多种手段,但是不可否认,军事制裁是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反侵略手段。
综上所述,联合国维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联合国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较大偏离。在联合国维和的五种模式中,最接近于集体安全制度的宪章制度模式与“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在现实的运行中或出现与集体安全很大的偏差,或中途夭折;长期运行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维和模式也与集体安全大为不同。联合国维和所形成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以及“宽泛性”四大特征,也表明维和已经不属于集体安全概念。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而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注释:
①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情况与数据,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facts.htm,2006—03—16。
②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③ 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④ 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1—174.
⑤ 关于集体安全学术界有诸多定义,主要有:(1)“集体安全指的是所有国家和地区以法律束缚和条约承诺,向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略行为做出制止和反击的反应”。参见Arnold Wolfers,“Collective Defense Versus Collective Security”,in Arnold Wolfers,ed.,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62,pp.181—204;(2)“集体安全是承诺以压倒性的力量构成对侵略者的威慑和打击,并通过联合反对侵略者概念的制度化,创建合作型的国际安全机制。”参见Kenneth Thompson,“Collective Security Reexamin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7,no.3,Sept.1953,pp.753—772。(3)“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维护每一个国家之安全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是国际关系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原则的推广”。参见朱建民:《国际组织新论》,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540页。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沈丁立教授认为,集体安全不只针对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因为当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不能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行为体的时候,该机制也可能针对其外部出现的侵略从而维护体系内每一成员的安全。故本文的集体安全概念综合了朱建民教授和沈丁立教授的观点。
⑥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49、160—162页。
⑦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151页。
⑧ Thomas Cuasck and Richard Stoll,“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tate Survival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1,March 1994,p.36.
⑨ D.W.Bowett,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4th ed.,London:Stevens & Sons Press,1982,pp.125—132.
⑩ 美国新闻处:《联合国宪章(中英对照)》,华盛顿:美国新闻处1945年版,第3页。
(11) The Blue Helmet,2nd ed.,New York,United Nations Press,1990,pp.4—5.
(12) Marrack Gaoulding,“The Evolution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International Affair,vol.69,no.3,1993,pp.452—455.
(13) 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第303页。
(14) 美国新闻处:《联合国宪章(中英对照)》,第3—40页。
(15) 《联合国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之演变》,《(台湾)淡江人文社会学刊》,2000年五十周年校庆特刊,第154页。
(16) 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p.172.
(17) U.N.,Everyone's United Nations,10th ed.,New York:United Nations Press,1986,p.98.
(18) 门洪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创新》,《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2期,第21页。
(19)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340,S/1052,1973,pp.2—3,UN Doc.S/11052/Rev.1,Oct.27,1973.
(20)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可否使用武力?”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faq/q9.htm,2006—03—16。
(21) “联合国其他方面授权的强制执行行动”,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preface/enforce.htm,2006—03—16。
(22) Paul F.Diehl,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64.转引自聂军:《联合国维和与集体安全辨析》,《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30—31页。
(23) Gregory Flynn and David Scheffer,“Limited Collective Security”,Foreign Policy,no.80,Fall 1990,p.78.
(24) 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i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118.
(25) 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4.
(26)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95,pp.45—49.
(27) William J.Durch,“Building on Sand:UN Peacekeeping in the Western Sahar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151.
(28) “联合国行动的35个最大部队派遣国”,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faq/dispatch.htm,2006—03—16。
(29)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text.htm,2006—03—16.
(30) 陆建新:《联合国维和行动:现状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4期,第100页。
标签: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论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