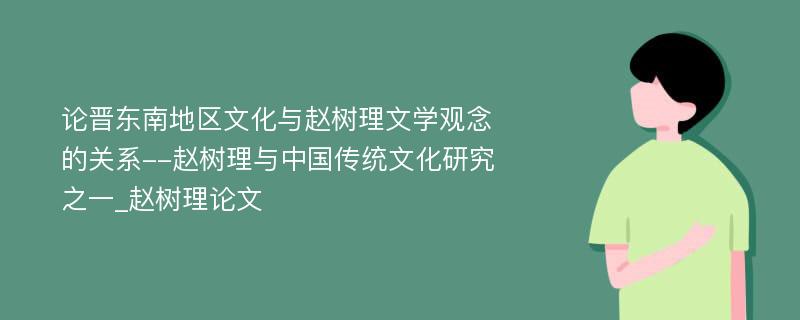
论晋东南地域文化与赵树理文学观念之联系——赵树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赵树理论文,文化与论文,地域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俗共赏
历史文化是一种现实力量,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它无所不在的影响。探寻作家的文学观念与他所置身的文化环境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作家作品,而且对今后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有启示性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孕育发展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且在中华大文化圈内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赵树理一生64年中有57年生活、工作在晋东南地区。晋东南地区以其特有的地理环境、经济模式、政治文化形成了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又别具特点的地域文化,对赵树理的文学观念起着内在的制导作用。
一
从地理环境看,山西自三代时期起就属黄河中游流域一带的中华民族发祥地范围;但它与邻省不同,北有恒山,西有黄河,东南有太行,是一个封闭形的狭长高原。其各组成部分中,晋东南较其它地区又更为闭塞,周边及境内沟壑纵横,遍布崇山峻岭,有“天下之脊”之称。古代所辖潞、泽、沁、辽四州皆在险山急水之中,各县多被阻隔在高山之间。沁水是其中一个较偏僻的山区县,赵树理的家乡尉迟村更是沁水一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偏小山村。所以,如果说山西在地理上处于封闭状态的话,晋东南及赵树理的家乡则更为封闭。
从经济模式看,晋东南进入农耕文明却是很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就与河东、豫北的邻人一同进入农耕文明的行列。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嫘祖养蚕于夏县,距沁水都很近。此后,从夏商直到清末这里一直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历来盛产玉米、谷子、蚕桑等传统农产品,与华北其它省不同,这里的农耕经济是一种小型的、少变化的小农经济。因地处高地,这里遭受不到冀、豫、鲁三省那样的大水灾;因山脊、沟壑土地的水份不易挥发,也很少遭到中原那样赤地千里的旱灾;因很少有毗连的大面积耕地,水地沃土极少,耕地多系山坡上的小片梯田,这里也少有邻省区那样的大地主,多属少有薄土的小农户。这里有丰富的煤、铁、木材等资源,农户一般还兼营采矿、冶炼、纺织等手工业,农耕经济包含着多种经济成份。在贸易上,由于与外省区甚至各县乡之间山水阻隔,各县乡往往自然形成各自的交易市场,农民不需走出本县即可通过集市换取需要的商品。这种农业、手工业和集市小商业交融的自然经济,增强了这种内敛型经济的生命力,但也使晋东南始终未能象邻省区那样发展起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来。稳定沉静的小农宗法社会使这里的农民从远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老井”、“野山”式的生活。北方游牧民族虽也曾南侵到这里,但这里的农民得山大沟深之利,采取的是“灵泉沟”方式——躲到村庄附近的大山里去。所以,这里的人民与外省区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相对就很少。这种状况,使晋东南小农的密度更大,文化上的封闭性更甚。
晋东南虽地处偏僻,经济仅处中下水平,但政治文化方面在封建时代却处于重要地位。三代时期即“属帝都畿内”,离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坂、安邑都很近,离商都殷、周都镐京、洛阳不过数百里。春秋战国时属“五霸”之一晋国和“三晋”之韩、赵,秦时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此后虽朝代更迭,长治、晋城始终为重要州、府所在地。两千余年来,这里重臣名将、大儒辈出,丹朱、微子、赵襄子、廉颇、冯奉山、西门豹、法显、石勒、李隆基、程颢、杜思敬、于谦、吴琠、陈廷敬等或是晋东南人,或在这里有过重要活动。连绵不变的农耕文明和浓重的封建政治文化使这里的农家一般崇奉的格言是:“耕读传家,人人都读书,个个会种田”,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民众的意识深层。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完备而系统,晋东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大部分山区由于相互交往稀少而形成相近血缘和近邻通婚的习俗,一个村庄往往主要由一个或几个同宗大姓组成。这种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更加重了宗法观念的统治。各自分散种田的小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是极有限的,所以又易形成企盼明君清官、英雄豪杰来保护他们的精神要求。差距不大的经济地位也易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晋东南也体现得较为突出,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标准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这里的民众中有普遍影响;苦寒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晋东南人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顽强而富有韧性的生命力,养成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俗、笃实忠厚的道德风尚;少迁徙、集族而居又使人们普遍热恋乡土,进而升华为精忠报国思想;城镇小而稀少,使这里几乎没有市民文化,民间文艺相对较为流行。赵树理就成长于这一文化土壤中。
二
赵树理一生可分为4个阶段:(一)1906年9月到1925年8月在家乡读书务农;(二)1925年9月到1928年4月在长治师范读书;(三)1928年4月到1937年9月在山西各处流浪;(四)1937年9月到1970年9月在解放区、新中国,主要是在晋东南下乡、创作。
第一阶段赵树理生活在沁水乡下,可以说他完全生活在前述晋东南地域文化之中。赵家是村里三大姓之一,赵树理七世祖赵钟恩是清中叶太学生,祖父赵中正笃信儒佛道教,父赵和清通占卜,是个“万宝全”式的自耕农。赵树理出世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根深蒂固的祖父给他起名“赵树礼”,6岁即教读《三圣教道会经》,后不惜破产供他读书,盼望孙子树立圣贤礼教,金榜题名,圆自己未能圆的科举仕进之路。五四运动那年,送他到高小读四书五经,其间入“太阳教”,买到《四书白话解说》,“每日不间断礼读三年”,“以为得了这套资本,就能治国平天下”。可见,在这一阶段,赵树理一方面“饱尝了苦难的乳浆”、“谙熟了农村生活”,“吸收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营养”;[①]另一方面,也深受传统文化消极部分特别是封建礼教的熏陶。前者见诸论述已不少,后者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是赵树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其实,赵树理自己对这一阶段有过清醒而明确的总结:“在这一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理不明事理。”[②]
不少研究者认为赵树理在第二阶段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并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世界观转变之时。这种论断也不甚确切,其根源也在于对晋东南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未予具体审视。系统思维方法研究分析对象时,强调注意系统内各要素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非此即彼的正反两方面。在长治师范读书时,随“五四”浪潮涌入中国的多种文化思想及在晋东南这个偏僻之地仍相当浓厚的传统文化思想交杂在赵树理这个年方20、有着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懵懵懂懂的青年的心中,他一时还摸不清方向。五四运动虽波及了长治,但远未深入到精神文化层次。长治师范“学语文也没有正式课本,老师选的讲义是从《古文辞类纂》上选下来的古文”;[③]“学校偏重于教古文,不能满足有求知欲望的人……所读之书杂得很,可以同时接受互相矛盾的学说,例如对科学和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④]赵树理对自己这一阶段的思想也有中肯的总结:“我的思想虽然有点解放,但旧的体系才垮,新的体系没有形成,主观上虽抱了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出路。其中指导我行动的有三个概念:(一)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信徒);(二)共产主义革命;(三)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不受任何东西支配)。我觉得此三者可以随意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⑤]在20年代中期达到如此认识程度并不奇怪,鲁、郭、茅都有过类似的思想历程,巴、老、曹当时尚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可看出反封建伦理、提倡个性主义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在赵树理思想上却没有掀起波涛。在这一点上,赵树理与鲁、郭、茅等是有差距的。后者都较早地接受了异域文化并先后经过艰难的求索过程,到1928年已基本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特别是在“五四”前后都对封建礼教作了猛烈的批判。也正因为赵树理当时尚未完全“补上这一课”,[⑥]所以到1930年他还认为:“唯物史观家,因为自己头上顶了个‘唯’字,所以硬要说人类的意识形态完全受物质支配。好象说人类还是为了物质才生出来的。你若说人类的心理也能支配生活,他便说你是‘唯心’。其实,‘唯心’二字,除了唯字有点小错外,‘心’(心理作用)的确是人类有的。”[⑦]是年出狱后,地下党曾两次派人动员他重新回到党内,但赵树理都拒绝了。[⑧]到1931年他还很痛快地应允了父亲给他包办的婚姻。所以,不能说赵树理在师范读书时“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做‘社会出路’”,“服膺了无产阶级思想”。[⑨]作为一个20出头、初涉社会的青年,在新思想刚刚传播到封建传统思想十分浓厚的晋东南时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也无损于赵树理后来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作家的光辉形象。但作为一个“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缺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反封建精神和个性主义的哺育,却给他后来的创作埋下了未能向更深更广发展的伏笔。
赵树理研究者一般认为赵树理在第三阶段产生了“朴素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他的作品“属于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创作之列”[⑩]。这一分析大致是不错的,但也有粗疏之处。30年代前期,由于山西特别是晋东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加之“土皇帝”阎锡山推行典型的闭关守土的封建宗法统治,不仅“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化传入晋东南极少,就是殖民文化也很少吹到散布在山间的各县乡。老百姓除了开始少量使用“洋火”、“洋油”、“洋布”等外,几乎看不到什么新的文化现象,绝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山外的国际、国内甚至省城、长治发生的事情,见闻尚不如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阿Q”和“七斤”们。这种普遍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影响赵树理的文学观念。1935年他撰文陈述了他的文艺大众化观点。他认为,当时不应该组织文坛,而应当普及“文摊”。他鄙视上海的文坛,主张多写唱本,群众花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听书、看戏、得到娱乐。[(11)]这一观念显然与“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还没有达到7年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阐述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那样的高度。赵树理是通过自己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中的切身体会而关注低文化的、贫穷的农民的审美趣味的,左翼作家是出于考虑到自己有以先进思想教育群众的重任而倡导老百姓能看得懂的大众化文艺作品的,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同中有异的。[(12)]赵树理未能象叶紫、沙汀、艾芜一样与左翼作家相融合,甚至建国后也与左翼作家较为疏远,其根源正是因为二者成长于不同的文化圈。
晋东南大量涌入现代文化是在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八路军进驻晋东南及牺盟会、决死纵队的建立极大极快地推动了晋东南新文化的建设。赵树理在思想上发生质的变化正是在第四阶段,1937年10月以后他才大量接触到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时他才明确了国家的希望和自己的前途。但这时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已发展到第四时期。毛泽东将“五四”到抗战这一阶段分为四个时期:1919年至1921年为第一时期;1921年至1927年为第二时期;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三时期;1937年以后为第四时期。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五四”的历史功绩:“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第二时期“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第三个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了这个革命,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惨败了”。第四时期是“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13)]这四个时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新文化建设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的文化精髓,对一个革命作家的思想库都有重要的储存价值。将两个系列的四个阶段相对照,可明显看出,赵树理缺乏前三个时期主要是第一个时期的文化熏陶,也正因此形成了他独到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文学价值观念。
抗战期间,解放区、国统区及“孤岛”等不同的政治地域的文化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地处内陆山区的山西各根据地的新文化较前三个时期更充分弘扬了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更体现了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特色。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14)]赵树理前三阶段的经历使他与别的作家比较起来特别适应这一革命,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与左翼作家一样受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养育,却又没有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过份否定传统的影响。养育他的文化沃土不是十里洋场的商埠,也不是庭院深深的北平学府,更不是漾溢着欧洲文明的巴黎,而是晋东南有如太行山一样古老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他不需要像丁玲、艾青们那样作一番文学观念的“改造”。他在徐懋庸等“亭子间”作家眼里是“丑小鸭”,但在革命领导层看来却是“山鹰”。他先后得到了杨献珍、蒲安修、彭德怀等的数次坚定的支持,他如鱼得水,大有用武之地了。他将小说形式返回去又写成评书式故事,他主要通过人物行动表示人物性格,农民习惯接受,这是抗战的需要,也是随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新文学的必然归宿。新文化的阳光雨露加之对农民民间文艺的谙熟,对农民的深知和热爱,使他根植于深厚的晋东南地域文化扎扎实实地成长了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晋东南发动农民抗日,没有新文化在太行山间的普及,他的个人悲剧不会结束,也不会成为名扬中国乃至世界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他是幸运的,成功的,是有独特贡献的。但相反相成,这一优势也给赵树理带来了相当缺憾。闭塞的文化环境,贫寒的小农家庭,使他无缘象鲁、郭、茅、巴、老、曹等一样到京沪等大都市或越洋过海到国际大都市接受更广博的现代文化的熏陶,也难以体会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潮在青年心中掀起的波涛(如巴金),也就对封建礼教缺乏上升到哲学、历史层次的批判(如鲁迅),也难以较多地接触到世界优秀文学的哺育,也就使他难以向更深更广处开掘,难以成为鲁、郭、茅式的“扛鼎”式作家。
这一后果不久就初现端倪。1951年胡乔木批评赵树理“写得东西不大,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并要他“读一些借鉴性作品”,还亲自为他“选定了苏联及其它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求他“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15)]胡乔木看得是准确的,正是要赵树理“补上这一课”。但可惜赵树理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仅一个月后,他“便觉得写作上的根据地不那么容易创造”,[(16)]就又回到了晋东南农村。不久后,还将胡乔木的赠书转赠别人。此后,他的文化根须再未离开这片故土。一个文化扩展、走向辉煌的机会擦肩而过,赵树理继续着他的优势(这是不错的),但却未能弥补自己明显的劣势。赵树理是个不善言辞、不喜抒情的人,但一回到晋东南他就有如神助,话语如流似水,充满了激情。在大会上他忘情地讲:“晋东南地区是我的故乡,是同志们的家乡,……我和她有母子一样的感情。……离得时间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每次回来走走,神经的感应很灵敏,一听音乐,很入耳;一看石头,也开花!”[(17)]赵树理热恋故乡,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的“专一”带来的偏颇。1954年他说,文艺界曾对古典、民间文学遗产“取过消灭的态度”、“幸而”“靠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保存下来”,[(18)]1956年又讲:“‘五四’时代有人(作者注:指‘消灭者’陈独秀)反对传统戏,认为不是艺术”[(19)];1957年又讲:“这笔帐至少应该从‘五四’算起,‘民间文艺’在当时的自然状态下虽然也难免受到一点孔子道统的影响,可是究竟和孔家来往不多”。他说:“自此以后,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新文艺是有进步思想领导的,是生气勃勃的,但可惜也与人民大众无缘——在这方面却和他们打例的正统之‘文’一样。”[(20)]1958年谈到旧戏时说:“总感觉我们赶不上它”,武松、穆桂英“比我们的人物深刻得多”,“小说咱们有,诗歌咱们有,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去学人家的?”“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21)]1964年断言:“评书就是小说!唱词就是诗!说唱大鼓就是词话!相声就是变体喜剧!”[(22)]由赵树理这些似零散实系统的论述可将它们归结为三点:(一)中国文学分为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五四新文学三个传统;(二)五四新文学对前两种传统持消灭态度,在形式上它脱离群众;(三)应以民间文学取代五四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正统。
赵树理深得晋东南地域文化优秀成份的营养,加之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哺育,是一位实事求是、爱民为民、精忠报国、重义轻利的农民化了的优秀知识分子。在艺术上,他深得民间文艺精髓,谙熟农民,农民语言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是古今罕见的农民通俗文学大师。这方面的论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是汗牛充栋,本文不再赘述。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赵树理一生的优秀之作太少了,且大部分集中在40年代,随后则呈下降趋势。以前评论界多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极左”路线,但看来这种论断较为粗疏,其成因与赵树理多年形成的文学观念有关。这里想探讨的是他的文学观念的科学性。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方法从总体上把对象看作系统,认为对象内涵丰富,应分析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层次结构。由此,我们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分析对象,就可发现很难泾渭分明地将其构成要素分为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两个传统,因为二者始终处于相互渗透转化的系统运动之中。《诗经》、古诗、五七言诗、唐传奇、宋词、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等,皆起于民间,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反过来又影响民间文学。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下层人民经常受到中上层统治阶级的多方面影响,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总会通过物质、制度、风俗、精神等各种渠道渗透到整个民间的思想深层;而民间的文化沃土也在不停地孕育、影响着一代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马克思说,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3)]这一论断从古代戏曲、评书、民间故事中能轻易找到许多例证。晋东南是小农比例很高的地区,据收集成册的民间故事及地方剧目看,小农摆脱苦难获得幸福的途径,不是靠明君清官,便是仗豪杰神怪,这正是小农集体无意识的外现。胡风认为,就连民间文艺形式本身也烙有封建意识印记,如“故事化”、“直叙化”等“是在封建农村的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方法的限界”;“看人从生看到死,看事物从发生看到结束,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思想就是它的根源”。[(24)]固然民间文艺并不等同于封建文艺,但胡风的论述也启示我们:封建文化对民间文艺的影响是渗透到整体内容和形式中的,并非“往来不多”。
再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对象分析其各要素的层次结构及功用,也不能断言她对古典文学、民间文学持“消灭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地反对毒害中国人民两千余年的封建礼教,孕育了现代中国第一代革命先锋,其主将正是陈独秀。陈独秀以北大文学院和《新青年》为阵地,集中华之精英,呼号呐喊,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沉睡迷惘的心。但他对民间文学并非取“消灭的态度”。他提出的“三大主义”之一便是“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也是他首先注意到民间文学的重要,组织北大师生搜集整理民歌,出版了数十种民歌集。他主持的北大文学院冲破了只许“经史子集”容身的正统文坛,将本来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小说、戏曲、民歌、故事等抬上了文坛,并由许多名教授在北大开课。正因为他的这些历史功绩,毛泽东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仍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应该说,陈独秀是中国现代革命第一代革命青年的导师,不能因他后来的错误否定他在“五四”时期的先锋作用,不能笼统说他对“古典的”、“民间的”传统持“消灭理论”。从表层看,确有不少新文学作家“对前两种传统”“持消灭态度”。鲁迅说他写小说只靠看了百来篇外国小说,而且劝告青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6)]郭沫若称他受了斯宾诺莎、惠特曼的影响,茅盾受左拉影响,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现代名家都称自己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宣言不等于史实。鲁迅“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27)]茅盾继承旧小说“多动作的描写方法”。即使一向被斥为“文化买办”的胡适写的新诗“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28)]这说明他们是旧、新文化的混血儿。他们之所以宣称对传统深恶痛绝,是因为在当时梦醒的不少“狂人”看来,中国落后,西方先进,为救国就只有“别求新声于异邦”,学习西方的长处,超过它,再不受它的欺侮。在他们看来,传统使中国如此“沉沦”,可取之处简直没有。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传统并不是可以一刀割断的衣襟,它是沉积在每个人心灵深层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随时都会对一个人的心理、行为发挥作用。皮亚杰认为12岁以上的少年的思维能力已超出事物的具体内容,“无需具体事物作为中介了”,[(29)]更何况新文学作家“五四”时期都已在20岁以上?详细分析一番就可看出,新文学作家是关注到民族特色和中国大众的审美情趣的:鲁迅的白描手法、《家》对封建家族礼教习俗的描绘、《子夜》的结构方式、老舍的老北京味儿、闻一多的新格律诗……他们大多采用的是传统的表情达意方式:闰土、林老板、觉新、祥子、周朴园都是典型的中国人,他们的艺术魅力并不比武松、穆桂英差。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克服欧式长句的毛病,注意采用中国式的短句等就是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具体努力。可见,“五四”新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沃土上长出来的,与传统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与人民大众不是对立的,与赵树理的方向是一致的。只能说因为它是新生的,在民族化大众化特别是在农民化方面没有后来的赵树理那么成熟。
以赵树理对文学真谛的执著追求,以他只唯实只唯民的求真精神,以他对农民的深知和热爱,他本能成为一名作品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世界文坛巨匠,可惜因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在给予他许多的同时也使他失去许多,局限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导致他的某些文学价值取向的偏颇,使他没能吸收许多必要的世界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营养,也就使他难以向更深更广处开掘。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注释:
①、⑥、⑨、⑩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一版,第24页、40页、46页。
②、④、⑤、⑦、(15)、(16)《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第255页、256页、5页、378页、335页、389页。
③、(17)、(18)、(19)、(20)、(21)、(22)《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643页、647页、266页、313页、358页、407页、543页。
⑧、(11)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23页、111页。
(12)此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
(13)、(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一版,第659页至663页、6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693页。
(24)胡风《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第261页。
(25)期诺《西行漫记》,第157页。
(26)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2页。
(27)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中流》第十卷第5期。
(28)胡适《〈尝试集〉自序》。
(29)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一版第一章。
标签:赵树理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文艺论文; 农民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