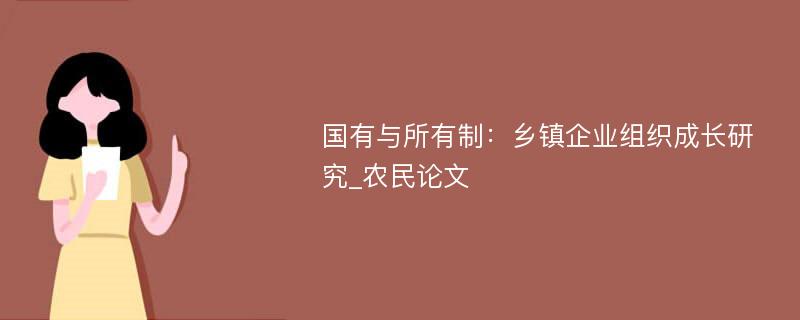
国家和所有权——乡镇企业组织成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所有权论文,组织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放松管制:社队企业出现
国家为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强制建立起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1994)。然而,就在这种体制建立后的1957年初,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就出现了。
建国初期,国家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以集体化的方式强制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其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1、互助组。 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它以一定程度的联合劳动取代完全分散的个体劳动,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它使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职能受到了限制。2、初级社。 初级社一般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民主议定、参加分红,其它生产资料由社统一使用。它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侵蚀了农民所有权。3、高级社。 高级社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归合作集体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的劳动组织形式,集体劳动,产品归合作社集体占有,初级社中的分红也随之消失。它直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4、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在很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制,同时实行集体劳动,由公社统一调配;农民机械地听命于公社的安排和调度,完全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主动性,而统购统销制度与工农业剪刀差的形成,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农村生产二十年徘徊不前。
(一)生产力“暴动”(注:关于生产力“暴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毛泽东针对1954年杀猪宰牛事件的评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暴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430)。王琢和许滨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论》(1995年,经济管理出版社)中用到这个概念,在此并无别义。)
在国家强制地推行集体化的制度安排过程中,由于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多起生产力的“暴动”事件:1、1954年, 正当合作社掀起高潮的时候,长江、淮河地区和河北省遭受了几十年罕见的水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收购任务却未削减。各地为保证完成任务,在收购粮食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吊打现象,并随意加了犯法、自法势力等帽子。广东省因收购粮食而自杀者达111人。 (注:王琢、许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1995,经济管理出版社。)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农村出现大量出售与屠宰牲畜现象,牲畜价格暴跌,农民出勤率下跌。2、1956年,高级社在全国建立之时, 部分农民以自发的退社行为,不接受高级合作社,抑制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变革。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的调查,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注:王琢,许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1995,经济管理出版社。)全国形成一股“退社风”。3、 人民公社导致的共产风无偿剥夺农民财产从根本上挫伤农民积极性,不幸的是人祸与天灾,接踵而至,粮食生产大减产,以至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惨象,城市出现大量的浮肿病。一场以人祸为主的大灾难,再次激发了生产力暴动。农民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抑制公社化:①消极怠工;②公产私分,农村普遍出现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支持下私分财产的风潮。
(二)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的收益和费用结构变化导致政策调整
国家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可以创造任何产权形式,然而同样要付出代价。国家推行集体化的努力,引起制度费用的连年快速上升,并且连年高于国家收益的增长。1958年,国家综合费用指数比上年增长366.82%,高于收益指数增长33.8%。1961年,国家的农村收益指灵敏突然减少了77.4%,只及1952年的70%。(注:周其仁:《中国经济学——1994》,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P23。 )国家收益指数降低到威胁国家生存的最低需要,国家被迫作出调整:1、确定“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体制;2、恢复自留地与家庭副业;3、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同时,调整了农业经济政策,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和农业税的征发率,对农民实行退赔等。
(三)农民谈判地位确立:社队企业出现
1、农民谈判地位确立
国家被迫作出的调整,确立了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和承认家庭副业与自留地的合法地位,加强了农民在与国家契约中的否决权。①农民现在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生活来源,他不再完全依赖集体。②农民对集体不满而减少了的劳动投放,现在不必消极怠工,而可以投入到自己的家庭经营。③农民虽仍不被允许完全退出人民公社,但他可以在体制内部分退出集体,即农民拥有了部分退出权。
2、社队企业出现
国家设立的官员等级制度对乡以下的非正式官员显得激励不足,尤其对生产队的干部更是如此,然而正是这些基层干部控制着农村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初级分配,这些集体经济的监督者就利用这种剩余控制权来分享剩余,并以实际剩余的获得量来平衡自己监管努力的实际供给量,在现实中有两种方式:①消极的形式:以权谋私。集体经济的监管者承担着生产队的管理职能和国家管理的公共职务,国家难以控制这种权力的行使,农民又缺乏制约的能力,因此监管者利用监管权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物的或货币的好处。②积极形式:创办社队企业。面对市场中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的获利机会,广大农民取得了谈判地位之后,必然会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但由于自身力量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集体经济的监管者由于控制着集体积累,并且可以凭借集体的名义取得银行贷款。因而他们有能力提供这种制度。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监管者也可以从社队企业中得到货币收入,因而他们也有动力,社队企业应运而生。
乡镇企业制度建立
生产力的暴动导致国家的成本——收益结构变化,国家作出政策调整,农民拥有了部分退出权,集体监管者拥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社队企业,农民和集体与国家的谈判地位显著提高。然而,这一切都是国家短期政策调整的结果,必然随政策调整而变化,农民要求将这种政策制度化,同时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形式,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出现再次强化了农民的地位,并最终导致乡镇企业制度的确立。
一、土地家庭承包制
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农民面对获利机会进行的一次制度创新。它归初开始于安徽风阳小岗,由于在全国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在全国得到了仿效。土地家庭承包制打破了人民公社全面集中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格局,采用把土地经营权发包给农民的办法,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分户承包经营,冲击了人民公社的土地产权制度。1、 土地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重建了农民家庭的财产所有权。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仍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中,集体已变成了法律的所有权主体,集体作为所有者的经济作用和地位下降了。加上中央对家庭承包制实行长期稳定的政策,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刚化,农民获得了准土地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农民获得了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具备了独立积累家庭私有财产的能力。2、 土地家庭承包制突破了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为农民进行了制度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集体统一经营使集体积累增加,集体更有能力兴办企业;家庭分散经营,使农民在家庭收入出现剩余时为从事非农业提供了资本。
二、乡镇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农民谈判地位的最终确立
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不仅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农民的家庭财产所有权,一方面使得农民拥有了剩余支配权,另一方面使农民在实际中占有了土地,控制了农产品的生产。这样强化了农民的退出权,形成了农民全部退出权。即农民承包经营土地,并实行“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以国家遵守包产到户合约为前提,如果国家单方面破坏合同,就等于授权农民收回上缴承诺。农民不但可以自己携带资源,退出某个农产品品种的生产,转向另一种生产,而且可以转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甚至转向只为家庭消费生产,农民的谈判地位最终确立。
(二)国家行为目标的改变
国家历经多次生产力暴动,使得国家终于清醒的认识到:凭借暴力潜能的职能强制地推行自己的行为目标——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不偿失。生产力一再的被破坏,使国家多次陷入困境,整个社会中不仅产业结构极不合理,而且财政入不敷出,国家综合费用指数远远高于收益增长指数,国家无力追加支出,产生了改变政策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从外部条件来看,随着国际环境趋于和缓,西方各国对我国的制裁也陆续取消,许多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外开放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识到作为时代产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已经失去了生产力的支持,相反,尽快恢复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而毅然决定进行改革。在对农民的关系上,国家从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控制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国家开始接受与农民交易,并进而改变原先集中决策模式而改为分权决策,以降低交易费用,在各地分权决策的基础上,合成中央政策。这使得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中讨价还价,从而最终形成了农民——社区——地方——中央之间的多重谈判。
(三)乡镇政府的行为目标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一方面将地方政府从对农村经济控制的繁忙工作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分权决策的实施,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不再仅仅是能否正确无误地执行中央政策,而增加了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弱,从而官位升迁的正激励促使地方官员有发展本地经济的强大动力。再者,随着国家行为目标的改变,国家承认了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从而在政策调整上,开始向这一方面倾斜。如国家一再缩减计划收购的品种和数量,改传统派购为合同收购,宣布农副产品完成国家收购后可以自由交易,允许私人长途贩运和农民进城经商,国家鼓励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等。这一切都预示着:每公布一条规定,就多了无数的获利机会。面对这些获利机会,地方政府官员必然会利用集体的积累或者凭借集体向银行贷款来发展地方经济。
(四)乡镇企业制度的确立
地方政府改变行为目标之后,产生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大动力。由于农业周期长,见效慢,而政府官员任期有限。因此发展工业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目标。社队企业在农村一定的基础,易于发展,乡(镇)政府一方面通过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为社队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将土地无偿或低价划归社队企业使用,大力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广大农民通过土地家庭承包制重建了家庭财产所有权,收入的不断增长促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同时,国家放松了对农村的管制,巨大的获利机会诱使着广大农民。一些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农民脱颖而出,开办个体、私营企业,从而引起了农村普遍的开办企业的热潮。这样一方面乡(镇)政府开办以社队企业为基础的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农民单个或联户开办私营企业,整个农村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支持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出于与社会博弈被迫放松管制,采取与社会交易的形式,竟然获得如此大的成果,于是,国家改变对新兴产权的态度,主动对新兴产权提供保护。1985年,国家发布了《关于社队企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在文件中将由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集体企业,农民个体或联营建立的企业,全部归纳为乡镇企业,这标志着乡镇企业制度的正式确立。
结语
国家和所有权的矛盾,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分析环境。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对新兴产权的保护必将成为政府职能转换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这不仅会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且必将极大地丰富国家和所有权的理论。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98.0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