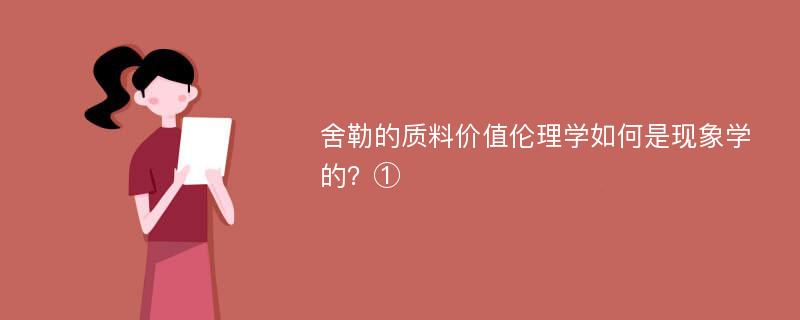
[摘 要]舍勒的现象学思想与其伦理学探究是紧密相连的,然而究竟如何理解其伦理学对于现象学方法的依赖,历来颇多争论。其中涉及三个相对较为集中的问题:首先,舍勒宣称其伦理学是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先天的吗,具有普遍性吗?其次,舍勒的伦理学思考中常常透显出或明或暗的基督宗教思想的背景,其伦理学究竟是现象学的,还是神学的?最后,舍勒的伦理学是在于康德伦理学的对勘中展开的,这一伦理学是如何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的,又是如何发展康德的自律伦理学的?借此三个问题的探究,舍勒的“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可体现为两个部分:现象学的“元伦理学”和现象学的“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是基础,“规范伦理学”则是最终的归宿。
[关键词]质料先天;价值;自律;伦理学;现象学
舍勒在整个早期现象学运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现象学思考首先是与其对伦理学的探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意义上,舍勒首先是个现象学的伦理学家。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一般的质料伦理学和康德的形式伦理学,舍勒发展了自己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但这样一门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如何是现象学的?笔者曾在拙著《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1]中做过尝试性回答。本文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对三个相关问题的补充性讨论。这三个问题是:(1)何为“先天”“质料先天”,以及它们与普遍性的关系;(2)舍勒的伦理学对现象学方法的依赖程度;(3)舍勒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差异。
床式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通过4个微型拉压力传感器检查患者下肢大小腿与康复训练机器人的交互作用力,建立人机交互作用力与关节(髋关节或膝关节)角度偏差的动态关系,其二阶微分方程可表示为:
一、“先天”“质料先天”与普遍性
无论对德国古典哲学还是现象学而言,a priori/Apriori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而在中文语境中,这个词的翻译却呈现出颇为混乱的境况。“先天”是现在比较常用的对a priori/Apriori的翻译,当然也有其他译法,如“验前”“先在”,甚至也有人翻译成“先验”(像王炳文先生翻译胡塞尔著作时的译法)。从义理上来讲,当然需要进一步思考,“验前”“先验”或者“先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不管在康德那里还是在现象学家这里,“先天”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天生”不一样。而之所以有人认为“先天”这个概念翻译得不好、有很大问题,一个很主要的理由是,它很容易和“天生”和“天赋”混淆起来——像王炳文先生所提出的。“先天”这种翻译的的确确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概念的改动、改译和“先验”(transzendental)这个概念的改动和改译其实是一样的,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做很多很细致的论证。有鉴于此,笔者暂时仍采用“先天”的译法。
3)混合臂高空作业车在举升过程中由同1个PLC控制器控制,即伸缩臂、折叠臂和工作斗的三个输入间为互锁关系,提高了工作斗的平稳性和可靠性[3]。
由“先天”衍生出的“质料先天”这个概念是舍勒自己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实它在胡塞尔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而对“先天”“先天现象学”的讨论与重审,自胡塞尔之后就有很多,整个早期第一代现象学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包括在义理方面跟“先天”紧紧相关的“先验”问题。舍勒作为现象学运动的一分子,在胡塞尔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于先天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价值伦理学》的书名就表明,他主要还是在批评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学形式主义,或者说批评形式主义本身。舍勒对形式主义本身的批评最终是回到哪里呢?或者说舍勒最终是借助于什么来批评形式主义的呢?当然是与之相对的“质料主义”。而其核心与突破还是在“先天”这个概念上,即“形式”和“先天”的关系、“质料”和“先天”的关系。
现象学的方法在“价值伦理学”和“情感伦理学”的部分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舍勒在这里诉诸了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即价值感受是意向性感受,这个价值情感行为是具有“意向性”的——“意向性”包括Noesis(“意向行为”)和Noema(“意向对象”)两个成分,“感受”当然是Noesis,这个Noema就是“价值”,在Noesis和Noema之间具有一种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恰恰使“价值”既不同于“实实在在的存在”,同时也不同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这一点也是波尔扎诺对胡塞尔的一个影响,而波尔扎诺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康德批判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和舍勒是一致的,舍勒在1904年——《逻辑研究》刚刚发表之后两三年——就发现了胡塞尔和波尔扎诺之间的内在联系。
神学的和现象学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可能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它们最开始的出发点和最终所诉诸的根据都是不一样的。以神学面貌出现的伦理学不会像舍勒的伦理学这样,而是一开始就会是一个“宣称”:人须得信仰上帝。在那里,“信”是第一位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要以此为基础。
康德区分了“自律”和“他律”,舍勒认为他接受了康德的工作,他跟随康德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归为“他律”之后,他在“自律”的大框架下开展工作,他自己认为他做的工作是比康德更加“自律”的。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六篇最开始的地方认为,康德讲的“自律”(即“理性为自身立法”)最终是一种“法则的律”,即“理律”,康德的“自律”其实还是一种“他律”。
但是“现象学的直观”和非现象学的那些经验、事实相比较,比如康德所讲的这些“范畴”相对于我们一般的认识或科学认识,的确具有它的形式性,实际上也就是具有它的功能性、范畴性、普适性。在此意义上,“质料先天”和“形式先天”是相对性的——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波尔扎诺那里。波尔扎诺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当中重新发现了他,他跟洛采在思想上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波尔扎诺对胡塞尔的核心推动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上:第一,是把“先天”理解为名词,即理解为“对象”;第二是在“形式先天”和“质料先天”的区别上。他提出了“表象自身”“句子自身”等概念。我们任何一个表达,比方说,“我在这里”,都存在着“句子自身”,而这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此外,还有“表象自身”,比方说,“我在这里”中的“我”就是一个表象。核心之处在于,我们如何可以把“句子自身”中的“表象自身”不断的形式化,即可以形式化到什么程度,而这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波尔扎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形式先天”和“质料先天”的关系,他说“先天综合命题”最终其实是靠形式化、替换来谈论的。在《逻辑研究》的“第三研究”中,胡塞尔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跟随波尔扎诺做这样一个工作。
而从波尔扎诺到胡塞尔再到舍勒,他们其实都是把“形式先天”和“质料先天”相对化的。也就是说,“质料先天”不是固定不变的,即并非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实际上,它可以处在生成当中。借助于本质直观的功能化,“质料先天”是可以变化的。这是对“质料先天”和“形式先天”的一个基本解释。舍勒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反对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而且这个形式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康德伦理学。
此外,人们常常也会质疑舍勒的基督徒身份,甚至诟病舍勒思想中的基督教学说的背景。而这就涉及第二个层次,即究竟该如何看待舍勒自己的经验与他宣称的现象学所把握到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到底这些描述有没有“明见性”?
舍勒说的“先天”不跟“普遍性”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一定不是普遍的,而是意味着,先天是“可普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几何学的三角形,在康德意义上或者在胡塞尔意义上,三角形都可以被称为一个“本质”“先天”。而舍勒则可以说,在三角形尚未被谈及之前,这个“先天”也是存在的,然后第一个人提出三角形而别人不接受的时候,它也是先天的,即它不会因为被接受还是不被接受就影响到它是本质的、先天的。正因为它是先天的,所以它一定是“可普遍的”,但这个“可普遍”也不是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舍勒的立场其实没有那么强,比如在他讲的“均衡时代的人”中,他持开放的、多元性的立场。虽然他的确是想要在多元性中间找到一个确定的或者本质的、先天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推而广之。在舍勒看来,这个本质可能会被承认,但是承认它的人却不一定会照着这个本质去做。
江苏省红十字会对于高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应该予以专业上的指导与帮助,积极协助高校,与高校合作,构建江苏省应急救护培训体系。
涉及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主要有如下两个具体的问题。
二、现象学,或神学?
一般而言,研究者不会否认舍勒的价值伦理学有其独到的见地。但是这些分析乃至其在伦理学上的建树,对现象学方法的依赖程度到底怎么样?相较于其他哲学传统,现象学方法的优势何在?其想追问的已经不是,舍勒的讨论到底是不是现象学的,而是:即便是现象学的,那么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优越性。亦即,现象学到底有没有可推荐性。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回答。第一个层次是,舍勒的讨论是不是现象学的,或者他用的现象学方式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舍勒的“价值现象学”与“人格现象学”这两大部分中,现象学的色彩都比较浓厚。在“价值现象学”这部分,它符合胡塞尔所概括出来的现象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我对一个对象的“把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本质”,然后是我对这个对象的把握方式,即它如何被给予我,最后在这种给予的方式和给予的对象之间具有一种相关性。
那么,这个“质料先天”到底相对于什么?是不是还有个质料后天?“质料后天”当然会有,但是舍勒这里,“质料先天”主要还是与“形式先天”对立,首要的还是跟康德的“形式先天”对立。在认识论方面,康德实际上是把感性的形式和知性的形式和“先天”相等同。对此,舍勒最核心的一个评论是,康德把“形式”和“质料”的关系同“先天”和“后天”的关系统一在一起,将形式等同于先天,质料等同于后天。这在伦理学上就体现为“形式”和“质料”“理性”和“感性”的这两对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舍勒要批评的最根本之处。舍勒认为,这两对概念是相切的,即可以画对角线,但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合的。
任何一个首度欣赏桑迪·斯科格兰德摄影作品的人——任何一个从她的装置细节带来的错视画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想要搞明白作品中的金鱼、松鼠、猫狗以及婴儿,也就是那些用纸浆、石膏与聚酯材料制成的雕像,实际上是什么的人——都必然会询问,她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些作品的。也就是说,一旦意识到这些令人惊叹的照片都拍摄自相应的舞台场景,是某种介于事实与虚构、现实与谎言之间的存在时,观众必然会质询她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与艺术方法。
根本上,如果这个源头可以回溯到波尔扎诺的话,胡塞尔与舍勒共同的地方实际上最终就在于他们对康德的反叛上。他们强调以这种现象学的方式或者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来谈论比如“价值”这方面,首先就要关注现象学研究对象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所谓的“行为现象学”,就是Noesis的现象学;第二个方面是“对象的现象学”,舍勒也称之为“现象学的事实”或者“实事的现象学”,面对“实事本身”,这个实事(Sache)就是在“行为”当中揭示Noema的现象学;第三个方面是Noesis和Noema之间的相关性的现象学。舍勒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康德只强调了行为对实事的建构,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所以他认为,康德缩窄了哲学探讨的方式。这是舍勒的现象学特征在质料先天方面的体现。
在人格方面,舍勒的现象学特征体现在哪里呢?主要跟谈论“自身意识”的背景有关系。最关键的是,舍勒对人格自身的认识论方式的谈论,实际上是现象学式的。当然也有人可以反对他,比方说海德堡学派也以这种方式进行谈论。但归根结底,海德堡学派——无论是亨利希还是弗兰克——都受到胡塞尔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现象学的方式对于讨论人格自身被给予的方式是决定性的。
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导致各国的经济体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单纯就经济的发现现状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部门对我国的经济进行了调整,包括出口关税、出口政策、出口商品等方面。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逐渐与周边国家形成友好的合作关系。但在经济贸易往来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动荡时期,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资金比较紧张,在流动资金方面进行控制,导致我国企业的可流动资金过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危机[3]。
现象学揭示出来我们这种意识给予方式里面的机制给出了人格的被给予性的方式,而且可以使得自身意识和自身认识之间的内在冲突更为清晰化。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根本的还在于现象学在人格的维度中所涉及的“时间现象学”这个维度。这个维度主要体现在自胡塞尔以来对“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分析,这是现象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而且也是现象学研究领域中最后且最难的地方。
舍勒一再说,“先天”不等同于“普遍性”,这是他有别于康德之处。完全可能会存在只被一个人把握到的“先天”,而且也有可能存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把握到的“先天”。那么,由之而来的问题是,舍勒所理解的“先天”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如果剥离了“普遍性”,“先天”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考不可能回避掉他自己背后的文化。说舍勒伦理学是现象学的而不是神学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或许有人会说正是因为舍勒有这样的生活经验,舍勒才会说绝对的价值是最高阶的,但关键在于,他不会把这个最高阶等同于耶稣、上帝、穆罕默德或其他的,只要是神圣的价值都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价值的位阶、等级是一种现象学的观念的存在,而耶稣、上帝、穆罕默德等只是观念对象的实在化。
在对康德处理先天问题的方式进行批判之后,舍勒从现象学出发,对“质料先天”进行了思考。而其思考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当中所展开的“立义内容―立义”模式。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当中就谈到这对模式,而且这对模式是用来抵抗康德的建构模式的。借助这个模式,舍勒以“本质直观的功能化”为切入点,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雅致的俗语文”经柯灵先生的锤炼、融化与创造,已达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凭借着“墨磨”的人生阅历,深厚的艺术涵养,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对世事的敏锐洞察力,《墨磨人》在语言上的造诣亦独树一帜。无论是叙事记人,还是议论说理,皆文情并茂,凝练典雅,熔书面口语于一炉,铸文言白话于一体,具有显著的柯氏语言风格。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问题都认为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督教的精神或根子,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回溯到更早的传统。比如“义务”(Pflicht)这个概念,越来越多研究者都认为康德的义务概念源自基督教的传统,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康德可能是因为基督教传统而达到了这一点,但康德也可以完全不借助这一点而从古希腊思想里面获得它:“义务”这个概念在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那里就有了。而西塞罗之所以能够把“伦理学”翻译成“道德哲学”,关键就在于芝诺那里早就有了“义务”这个概念。
那天一脸凄风苦雨的赵仙童回家,看到呆坐在电脑前愁眉不展的砖子,扔了一颗手雷给他:诌不出狗屁就别诌了,弄饭!
舍勒伦理学所关涉的“人格”(Person)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在最开始,“人格”就其本意而言意味着“面具”,而“面具”导致“关系性”的存在,甚至影响了这个词后来一系列的发展——它的一个引申意就是“声穿”,即声音穿过这个面具出来。“声穿”就意味着后来的语言学中的第一、二、三人称。在舞台上演戏,就表明要扮演一个角色。所谓的person,从根本上讲就是指位子、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讲,人自己要来理解你自己,理解你自己的位子或角色。这个问题就跟后来舍勒对人格的理解有关系。西塞罗还进一步指出,这个位子或角色的理解还可以扩展,扩展到人在人生的编剧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关系”问题更复杂,它不单单涉及个人与社会、共同体或总体人格之间的关系。这就彰显出对person这个词翻译的困难之处,它不仅仅指一个人,它也可以指“总体人格”——比方说国家、社会,类似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Sittlichkeit)里的三个成分。所以,不见得一定要从基督教哲学当中寻找舍勒伦理学的根据,其实从西塞罗或斯多亚学派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在舍勒这里,除了上面所说的“关系”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原初的“关系”,即个人跟他自己的关系,这从person这个词的来源上就可以看到。比如,你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扮演安提戈涅,但是落幕之后,你还得作为自己真实地生活。这个“person”/“面具”/“声穿”在最开始的意义上就涵盖了一个内在的不同一性,“人格同一性”是个悖谬的说法。所谓的“人格同一性”指的是,恰恰就是在不断克服原初的不同一性中,才获得了同一性。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人格”思想的诸多方面,而不是说这些思想的源头就只是在基督教的“位格”(Person)或“三位一体”的学说中。
对于毛笔书法作品的法律特征的界定,应该建立在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和美术作品定义的前提下,兼顾我国传统毛笔书法艺术特征进行研究。
从现象学来看,人格最终关涉“时间”问题。舍勒以其现象学的方式给出了对“人格”的整全的晕圈描画。如果说绝对的“时间流”一直在流的话,那么在这个绝对的流上面我们画出来的可能是一个一个点,但这任何的一个点都是有厚度的,都是一个晕圈,都有各个层面的维度在里面。在这方面,“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能够让我们更丰厚一点。
三、舍勒v.s.康德
舍勒以康德为对手,通过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那么,如何理解舍勒对于康德伦理学的批评?这个问题涉及舍勒对康德的批评或理解,还涉及这种理解所带来的效应。
关于舍勒对康德的批评在康德学界造成的影响,有几个代表性的系统研究者。第一个是胡塞尔的学生阿尔弗斯(K.Alphéus),他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完全站在康德的立场上系统地反驳舍勒。第二个人是海德曼(I.Heidemann),1955年他在波恩大学写了一本非常经典的讨论舍勒与康德关系的博士论文。第三个人是生于四川的美国学者布罗瑟(Ph.Blosser),他在20世纪90年AI写作了《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在这三个代表性的研究者中,第一个学者是站在康德立场上,第二个、第三个学者是站在相对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上的。目前英美的康德学界基本上是按照分析哲学的进路在从事研究,康德学界的学者基本上不会认可舍勒对康德的批评。这里面的理由当然是各种各样的。
再比如舍勒自己举的“红”的例子:当我说出“它是红”,“红”本身不会因为一个红绿色盲或者一个盲人而影响“红”本身作为本质而存在。哪怕除了我以外,这个房间里坐的其余人都是红绿色盲,只有我说我直观到“红”,它也不会因为大家都说这不是红而改变“红”的先天性和本质性。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真理”和“多数”的问题了。“本质”不意味着“多数”,而是可普遍的。
首先是关于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这个问题。据笔者的有限阅读经验,对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的解释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席尔普(Paul A.Schlipp)式的,一种是黑格尔式的,一种是舍勒式的。关于舍勒对康德的批评,通常的看法都将黑格尔式的理解和舍勒式的理解混同为一,所以康德学界对舍勒的这种反批评不是很有力度,尽管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或者去深究舍勒究竟说了什么。
而了解舍勒对康德批评的人,以及了解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批评的人,乃至了解从德国的特洛尔奇以后对康德批评的那些人,反过来来维护康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这部书很晚才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的学者知之不详,所以康德原来呈现的面貌是有问题、不全面的。在他们看来,康德的面貌应该更丰满,也可以回应上述这些批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够批驳掉舍勒对康德的批评。
康德在1770年曾做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即约束性(Verbindlichkeit)的“执行原则”和“判断原则”的区分。在“判断原则”上,康德讨论的问题是“意志”(Wille),在“执行原则”上康德用的是Willkür。这个词其实与奥古斯丁关系密切,李明辉先生用刘宗周的概念译成“意念”,现在也有译成“抉意”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讨论了很多Willkür问题,Willkür的形式根据是法权论的,Willkür的质料根据是德性论的。从舍勒所征引的文献来看,舍勒主要针对的还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也涉及一点《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根本上,舍勒对康德的批评集中在Wille的问题上,集中在Wille的约束性的判断原则和Wille的形式和质料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意义上,以康德有“德性论”和以康德有“道德形而上学”这一套理论为理由反驳舍勒对康德的批评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要被质疑的。
康德伦理学不意味着一定是义务伦理学,它也有德性、法权等,它是一整套系统的,但康德伦理学究竟主要是“行动伦理学”还是“行动者伦理学”,这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由于德性伦理学的复苏,英美学界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借助于在康德那里能够发掘出来的德性的维度并回过头来维护康德,以此来对抗亚里士多德主义。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舍勒对康德的批评和康德学界对康德的维护,其实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秩和检验。组内均数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务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
其次是关于“自律伦理学”和“他律伦理学”的问题。舍勒伦理学奠基在作为对象的价值之上,它如何不是一种“他律伦理学”,而是对康德“自律伦理学”的一个发展?
舍勒强调,“本质直观的功能化”是本质直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而同时又是最被人所忽视、没有被人揭示出来的属性。“本质直观的功能化”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是在谈论“形式先天”和“质料先天”的关系上,即在本质直观中,作为“质料”而把握到的“先天”可以被“化”为一个“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功能化”——化作一个“形式”“图式”“范畴”等;另一方面,“本质直观的功能化”张扬了舍勒自己所强调的一种含有相对性的绝对主义,即舍勒自己所称的理性的、客观的,但又带有相对性的这样一种绝对主义。就是说,舍勒一方面反对康德把“形式”和“先天”紧紧等同起来的做法,同时他也反对康德的下列想法,即理性的这种形式是固定的——比如,康德的“范畴”为什么一定是12个的等等。而在舍勒看来,范畴实际上也是“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借助于本质直观的功能化,舍勒实际上也是把“形式”和“质料”之间的关系相对化。简单来讲,所谓的“质料先天”就是作为“本质直观”的“质料”被把握到的那个“先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先天”就是“质料”,但它并不是哪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当然,舍勒也会赞同康德所说的先天形式,比如“时间”“空间”“范畴”等,但是舍勒指出,在本质直观中它们就是作为质料的,同时它们是先天的,即在现象学的直观中被把握到的“质料先天”。
舍勒所讲的“价值”在康德那里的确是有一个区别,在康德那里“价值”只有两种:一种是Preis,用日常语言可以翻译成“价格”,即“市场价值”,另一种是“人格尊严”。康德认可的是后面这种价值,而任何建基于前面那种意义上的价值都是他律。在这个意义上,舍勒所强调的价值可能不会被康德所批判,这可能是两个层面的。但是舍勒意义上的人格自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自律的?是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为自身立法”?当然舍勒不会认可,他甚至强调,康德是一种极端的“去人格化”(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从尼采那里来的)。舍勒所谓的“人格伦理学”最终是一种人格的“生成”“救赎”,是朝向“爱的秩序”的“救赎”。那么,这种“救赎”是不是也要依从于一个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它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
在舍勒看来,“自律”(Auto-nomie)之中的“自”(Auto-)在根本上强调的是一种“自立性”(Selbstständigkeit)。因此,自律作为谓词,其主词或主项就并不是像在康德那里那样是“理性”或“某个作为分有着理性法则性的X的人格”,而毋宁说就是“人格”(Person)本身。舍勒强调,在这里必须区分“双重的自律”:
近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刺激了铜矿山产能不断扩张和铜冶炼技术能力的提升,铜冶炼产能飞速攀升。有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精炼铜年产量从380万t提升至目前的1 015余万吨。目前,较大规模铜冶炼企业主要采用氧气顶吹+PS转炉吹炼、闪速熔炼+PS转炉吹炼以及闪速熔炼+闪速吹炼(简称“双闪”工艺)等火法冶炼工艺组合。
对自身之为善和恶的人格性明察的自律以及对以某种方式作为善和恶而被给予之物的人格性意欲的自律。与前者相对立的是无明察的或盲目的意欲的他律,与后者相对立的是被迫的意欲的他律,它最清楚地包含在所有的意愿感染和暗示中[2](p486)①中译对照原文引自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这里所说的双重自律,实际上是从“人格”的两种不同但却相互关联的意向性活动来区分的:一种是人格性的“道德明察”活动,其意向相关项是“自身之为善和恶”这类道德价值;另一种则是人格性的“道德意欲”活动,与之相关联的是那些善的或恶的事情。这两种人格活动之自律最终无疑都是统摄在“人格自律”之下的。这也是舍勒强调自律首先是人格本身之谓词的原因所在。所谓人格性道德明察之自律意味着对道德价值的“自律地”有明察,而非无明察或盲目,其对立面就是这种无明察的或盲目的意欲之他律;而人格性道德意欲之自律指的则是对那些善的或恶的事情的“自律地”意欲,其对立面是那种被迫的意欲。显然,在舍勒这里,“自律”更多是在“自立性”(Selbstständigkeit)的意义上被使用,它强调一种直接性和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那个偏重“动词”意味的自律在舍勒这里更多可被游移为偏重“副词”意味的词汇。
在康德那里,善与行为的“道德性”(Moraltät)而非“合法性”(Legalität)相关,进而与意志自律相关。比如,康德所举的那个“童叟无欺”的例子,精明的商贩出于对利润的“禀好”(Neigung)而做到公平诚实,他既没有对公平诚实的直接的禀好,更不是出于义务(aus Pflicht)来行事,所以这一行为是无道德价值可言的。只有意志服从其自身所立的法,继而由此意志(或意念,Willkür)决定的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舍勒不会同意这一点。根据他对自律的诠释,康德所说的这个“童叟无欺”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无明察地和被迫地意欲之行为,也就是既非(人格性)道德明察之自律的行为亦非(人格性)道德意欲之自律的行为,但这些并不会影响这个行为本身是善的,具有道德价值,而只是因为它是双重的他律之行为,故不能将这个本身即善的行为之道德价值“善”归派给这个作为“人格”的某人(如精明的商贩)。换言之,借助于这双重自律的区分,我们可以更好地厘清所谓的“行为之善”与“人格之善”。
Development of a 200 ton algae transport vessel for Taihu basin
在依照“人格”的“道德明察”和“道德意欲”这两种不同的意向性活动(舍勒也曾批评康德忽视对此二者的区分)区分双重自律(以及双重他律)之后,舍勒进而明确了自律的“明察”与“意欲”的关系:
完全相即的、自律而直接的对什么是善的明察,必然也设定了对那个作为善的而被把握到的东西的自律意欲;但反过来自律的意欲却并不也共同设定了在它之中作为“善的”而被意指的东西的完全直接的明晰性[2](p490)。
简言之,舍勒这里所强调的是,若我(作为人格)绝然直接地知道什么是善,那也就必定设定我直接自主地意欲这个善的事情,但我直接自主地意欲某个善的事情,却不必然设定我对什么是善有完全直接的明见把握。
舍勒接下去要关注的恰恰就是那种“我直接自主地意欲某个善的事情,却对什么是善没有完全直接把握”的情况,即一种有着“自律的意欲,但并不同时有完全自律的明察”的状况。而这一点正是舍勒与康德争议之所在。
舍勒通过对“顺从”(Gehorsam)这种情况的分析,引出了他的根本关切。所谓“顺从”首先包含有一个“自律的意欲”,我完全直接自主地去意欲“顺从”什么,此处的意欲不是“被迫的”,所以不是“盲从”。但是,也正因为是“顺从”,我其实对我所顺从的这个(异于我的)“什么”之道德价值并无完全明晰的把握,也就是说,“顺从”并不同时包含有一个完全相即的“自律的明察”。在舍勒看来,因为康德没有区分“道德明察”和“道德意欲”,也没有区分这双重的自律,所以康德会将对这个(异于我的)“什么”之“顺从”视为他律,视为一种被迫的意欲。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在于:康德意义上的“自律”概念“不仅将会排斥任何道德的教育和指导,而且也已经排斥一种‘道德顺从’的观念,甚而排斥道德的异己规定的更高形式,即那种通过对由一个明晰的善的人格所给出的纯粹的、善的例子的追随而完成的异己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在舍勒看来,因无视双重的自律的区分,康德会因担心堕入“他律”,而将排斥一切的道德教育、道德顺从乃至于那种对作为价值人格之典范的“榜样”的跟随。而这些道德教育、道德顺从以及所谓的“榜样跟随”,对于舍勒来说,恰恰是其“人格教化”或“人格生成”学说重要部分。而且,它们无疑都可被纳入其“人格自律”说的总体框架之内[3](p253-280)。
总的来看,舍勒总体的倾向是离亚里士多德比离康德更近。但是他对整个伦理学的思考、反思,恰恰又是更为康德式的,即他对整个伦理学的思考是更为现代的,他更多的是基于康德的工作。舍勒所关怀的是:“什么是质料价值伦理学?”正因为是“质料的伦理学”,所以它就要跟一切意义上的“形式伦理学”作斗争,当然包括康德意义上的“形式伦理学”;同时,也因为是“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所以他又要跟一切意义上其他的一般的质料伦理学作斗争,当然包括他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幸福伦理学”(或“德性伦理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主要的敌人,在他自己看来,既是亚里士多德,又是康德。在他看来,他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人格伦理学”)最终是“自律”的,他是跟随着康德把亚里士多德判为“他律伦理学”,之后又在“自律的伦理学”内部跟康德进行竞争,并提出他自己的“人格自律的伦理学”。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舍勒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得到了展示,由此可以对舍勒的伦理学进行一种重构。在笔者的重构下,舍勒的“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层次):一个是“元伦理学”,一个是“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是基础,对“规范伦理学”或者对“人格伦理学”的讨论最终要回溯到“价值的质料先天主义”上去,而“规范伦理学”则是最终的归宿。在归宿的意义上,在舍勒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苏格拉底问题)这样一个最核心问题上,舍勒的伦理学既非康德式的“义务伦理学”,也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而根本上是一种在他自己看来更为根本的“第三条道路”,即“人格伦理学”。
参考文献:
[1]张任之.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Max Scheler.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GW II[M].Bern/München:Francke-Verlag,1980.
[3]张任之.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8.001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8-0005-07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任之(1979—),男,江苏南通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本文源自笔者于2013年6月21日在徐长福教授主持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马哲所会议室)上所做报告的录音整理稿。录音整理由王大帅完成,笔者近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并对录音整理文字稿进行了整合和修订。
责任编辑 罗雨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