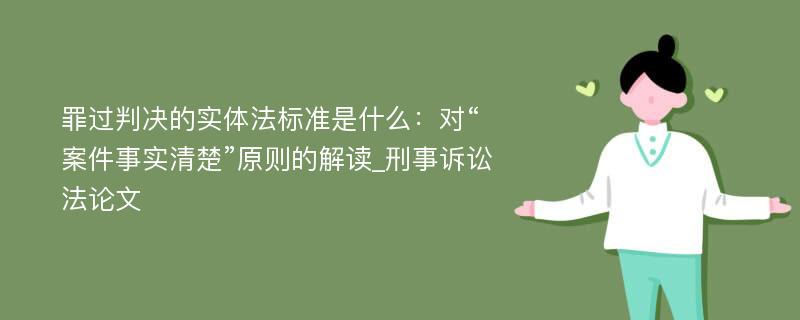
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是什么——“案件事实清楚”原理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体法论文,判决论文,案件论文,理性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罪判决的标准说明的是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基于什么样的标准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学者均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有罪判决的标准。而且,刑事诉讼法学界在分析有罪判决的标准时,注重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读,而对“案件事实清楚”缺乏热情,论述中对于何为“案件事实清楚”往往一笔带过。刑法学者则认为“案件事实清楚”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有学者对其加以关注。所以“案件事实清楚”仍然含混不清。由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其判决既有实体法标准又有程序法标准。那么,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吗?“案件事实清楚”中的“案件事实”包括哪些事实?“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谁清楚?“清楚”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所有案件事实都要“清楚”后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有罪判决?这些均是理论界还没有澄清却又极具实践意义的问题。
一、案件事实清楚: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
(一)刑事诉讼法中有罪判决之实体法标准
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罪判决标准前,有必要明确的是,有罪判决标准实际上就是刑事案件中行为构成犯罪的证明标准。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通过提出证据和进行证明活动,使裁判者对本方待证事实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的程度。①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或自诉方(以下简称控诉方)提出诉讼的目的在于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要达到此诉讼目的控诉方就必须向法院举证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使裁判者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从而作出有罪判决。
从《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的规定出发,“许多同志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程度(即证明标准),应当是证据确实充分”。②也就是说,多数学者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有罪判决的标准。不过,在不同的学者看来,此“证据确实充分”有不同含义。有的学者实际上是从事实和证据两个层面使用“证据确实充分”的,即“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简称。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对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事实和证据的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法定性,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下简称‘确实充分’)成为司法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③而有的学者仅仅是从证据标准的层面使用“证据确实充分”的,即它指纯粹的“证据确实、充分”,不包括“案件事实清楚”的内容。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明的要求,指的是实现查明刑事案件客观真实这一刑事证明任务的具体指标。对此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刑事证明必须达到定案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④
由于刑事证明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刑事证明标准(就有罪证明而言),所以上述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理解上存在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对有罪判决标准理解上的分歧。对于有罪判决标准理解上的这一分歧,笔者认为,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清楚”;二是“证据确实、充分”。其中,前者是事实标准,后者是证据标准。作为有罪判决的事实标准,“案件事实清楚”强调裁判者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应当对于被告人的构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有清楚的把握;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证据确实、充分”要求裁判者在作出有罪判决时认为控诉方在法庭上举出证据的质与量达到了有罪判决要求,即质上要求确实、量上要求充分。所以,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应当包括了事实和证据两方面的要求,相互不可替代。
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事实与证据两个的要求是否均属于实体法范畴在理解上存在分歧。主流观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例如,有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对刑事案件定案时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不是在诉讼一开始就能达到的,也不是对认定有关程序法事实的证明的标准。”⑤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标准既包括了实体法上的证明标准也包括了程序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应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加以理解。我国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意义上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二是程序意义上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⑥两种观点的分歧点在于“证据确实、充分”是实体法标准还是程序法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否亦为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从证明对象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刑事诉讼证明对象一般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⑦刑事诉讼中要证明的程序法事实包括有关回避的事实、有关适用强制措施的事实、有关诉讼期限的事实和其他有关违反诉讼程序的事实。这些事实如果不加以证明,将影响案件的合法、公正处理。而且,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以“证据确实、充分”本身无法排斥关于程序事实方面的证据。
既然这些程序法事实在刑事诉讼中也要求得到证明,那么就必然有证明标准的问题。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是否为“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是从证据的角度对证明提出的要求,如果证据本身不确实、证据量上不充分,证明对象就根本谈不上得到了有效证明。无论是实体法事实还是程序法事实,在证明过程中均要求证明者运用的证据是确实的,并且得到的证据在量上均需充分。所以,“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过程中对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的共同要求。
但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罪判决标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案件事实清楚”和“证据确实、充分”。虽然“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过程对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的共同要求,但这并不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有罪判决的标准就包括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两方面。因为“案件事实清楚”对有罪判决的标准作了限定,即“案件事实”是从实体法事实立场出发的。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清楚”限定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罪判决标准是实体法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多次使用了“案件”这一词。“案件”是指什么?所谓“案件”是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加以解决的各种纠纷或冲突。也就是说,“案件”本身就是一种纠纷或冲突。从案件的性质看,有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刑事诉讼法中所指的“案件”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是指通过刑事诉讼的方式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案件。从事实的角度看,刑事案件就是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害事实。从外延看,刑事案件事实包括何人、何时、在何地、基于何种心理状况、以何种方法、对何对象、实施了何种程度的危害行为。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这些事实均为实体法事实,不包括程序法事实。
所以,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案件事实清楚”是仅仅指实体法事实,而不包括程序法事实。这一理解与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实体法证明标准的观点一致。
(二)现行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之质疑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有罪判决标准是不科学的。其缺陷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表达上的逻辑错误。从证明关系上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手段,⑧即在刑事证明的手段与目的两者的逻辑关系上,刑事证据是手段,案件事实被证明清楚是证明的目的。基于“手段在前、目的在后”这一逻辑关系,有罪判决标准的立法表述就应当为:“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而不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其次,证据标准的必要性不足。现行刑事诉讼法将有罪判决的标准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是将事实标准与证据标准并列作为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有罪判决的标准中事实标准与证据标准应当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例如,有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与“证据确实、充分”密不可分: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前者又必须在后者中得到体现和落实,两者不可偏废。⑨
在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中,事实标准和证据标准是否真的“不可偏废”?如上所述,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看,将案件事实证明清楚是控诉方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达到的证明要求,也即刑事诉讼中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而证据只不过是控诉方达到其证明要求的方式和手段。“证据确实、充分”恰恰是对证据这一手段或方式的质和量的要求。案件事实要被证明清楚当然不可缺少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但这并不说明“证据确实、充分”是有罪判决的标准。实际上,要查清案件事实,刑事诉讼中不但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要有合格的控诉者、裁判者,还要求有合法的程序且刑事诉讼的参与人均依程序而行动,等等。如果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有罪判决的标准,我们是否也应当将“适格的控诉者”、“合格的裁判者”以及“程序合法”等作为有罪判决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立法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理论界也不会给出肯定性的答案。
笔者认为,既然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在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就应当是“犯罪事实清楚”。至于是如何达到“犯罪事实清楚”则是证明过程、证明方法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时,只需规定“犯罪事实清楚”即可,不可将“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其标准的并列内容。
再次,“案件事实”的表达不明确。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表述有罪判决的标准时使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这一短语。这一表述模糊不清,导致了理解上的分歧。虽然由于刑事诉讼法的特定性限定了这里的“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刑事案件的事实,但刑事案件的事实到底是指哪些事实?是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还是证据法事实?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使用“案件事实”这一短语,在该法第96条、第100条和第108条均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一短语。显而易见,“犯罪事实”是指刑事案件的实体法事实,而不包括程序法事实与证据法事实。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37条和第141条使用的也是“犯罪事实”这一短语。从法律用语的一致性上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中的“案件事实”实际上也就是“犯罪事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将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在立法作出修改前,笔者在探讨有罪判决标准时仍然援用“案件事实清楚”这一概念。
二、“案件事实”解读
何为“案件事实”?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认为,“案件事实”是指案件中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事实清楚”,就是要求对涉及犯罪构成和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都应当查清楚。⑩有学者认为,所谓“事实清楚”,是指案件中的待证事实都得到了证明,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对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不要求都查清楚。(11)但也有观点认为,“案件事实”仅指犯罪构成事实,如有学者认为:“事实清楚就是要求犯罪构成的事实清楚,与构成要件的事实无关的其他事实没有查清,不影响定罪。”(12)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的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说明,有罪判决的前提是犯罪事实已经被查清,如果犯罪事实不清就不能作出有罪判决。但作出有罪判决并不意味着裁判者只需查清定罪事实而对量刑事实置之不顾。刑事司法活动总是围绕定罪量刑来进行的。(13)从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看,我国的刑事审判并不采用定罪与量刑分离的模式,法庭审理过程中关于定罪的证据与关于量刑的证据是一并调查的,法院判决时也要求就定罪与量刑问题一并作出判断,而不像英美国家先定罪、后量刑。所以,所谓作为有罪判决前提的“案件事实清楚”应当是指与定罪、量刑的事实都已经查清楚,而非仅仅定罪事实清楚。从刑事审判中有罪判决结果看,有罪判决判决书的结尾部分要从实体上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被告人构成何罪;二是被告人承担什么样的惩罚。前者由定罪事实决定,后者由量刑(14)事实决定。所以,“案件事实”应当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逻辑结构是整个刑法内容的缩影;从刑事案件有罪判决作出的整个过程看,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决定刑罚,完整地反映了办理刑事案件的步骤和过程。(15)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除了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以外,是否存在独立的刑事责任事实?笔者认为,虽然理论上和实践中刑事责任均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但刑事责任并无其独立的事实因素。在刑事审判中,裁判者要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刑事责任的有无问题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刑事责任的大小关及是否惩罚行为人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惩罚犯罪人。刑事责任有无的事实因素与定罪事实重合,刑事责任大小的事实因素与量刑事实重合。既然刑事责任本身没有独立的事实因素,那么在刑事审判中裁判者要查清的事实就只有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
(一)“案件事实”解读之一:定罪事实
1.“定罪事实”与“犯罪事实”辨析
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定罪事实”与“犯罪事实”是经常混用的概念。在阐释“定罪事实”前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略加分析。
什么是“犯罪事实”?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事实仅指犯罪构成事实。例如,有学者认为:“作为司法认定对象的案件事实,并不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而只是与法律适用相关的情况,在定罪活动中,主要是指构成要件的事实。”(16)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事实包括犯罪构成事实和与量刑有关的事实。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犯罪事实,是指发生在犯罪过程中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切事实情况,它包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事实,后者是量刑情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7)第三种观点则将犯罪事实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其中狭义的犯罪事实即犯罪构成事实,而广义的犯罪事实为量刑事实。例如,有学者指出:“从狭义来理解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事实,但从广义来理解犯罪事实则包括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18)
笔者认为,犯罪事实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主客观方面的事实情况和因素,犯罪事实并无广义与狭义之分。刑法学界之所以将犯罪事实作狭义与广义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刑法第61条规定的考虑。刑法该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本条中立法者使用了“犯罪的事实”(即犯罪事实)这一概念,很显然这里的“犯罪的事实”仅指犯罪构成事实。从刑法完善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此处的“犯罪的事实”宜修订为“犯罪构成事实”。通过这一修改,刑法学界在理解“犯罪事实”时就不会出现上述分歧。
什么是“定罪事实”?所谓定罪事实是指与定罪有关的事实,所以要正确理解“定罪事实”其前提就应正确把握“定罪”的定义。我国众多学者都给定罪下了定义。例如,有学者认为,定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进行相互认定的活动。(19)又如,有学者认为,定罪是司法机关依照刑法的规定,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刑事司法活动。(20)上述关于定罪定义的理解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定罪是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罪及构成何罪,而不涉及对行为人量刑的问题。基于定罪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定罪事实”是与确定行为人是否构罪及构成何罪(如果构成犯罪的话)的事实。
从上述分析可知,“犯罪事实”与“定罪事实”之间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定罪事实”只是“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内容。
2.定罪事实:犯罪构成事实
既然“定罪事实”是与确定行为人行为是否构罪以及构成何罪的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在刑事实体法理论中,“定罪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犯罪是否成立,原则上只能以犯罪构成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就充分表明了行为是否包含了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能否成立犯罪,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决定或制约犯罪成立的要件或者因素。”(21)所谓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有机统一”说明犯罪构成是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如何得到证明的,即司法实践中如何通过证明犯罪构成的成立而证明犯罪成立的呢?这又需要借助另一个概念——犯罪构成要件。
(1)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是各种事实整合所形成的整体。在司法实践中证明犯罪成立时只能首先将这一整体分为几个方面,然后对每一部分分别加以证明,最后再从整体的角度看犯罪构成是否决定某罪的成立。正如前苏联学者所言:“犯罪构成只是它的形式,而要适用法律,就必须深刻地了解犯罪构成的内容及其每一个要件。”“我们把犯罪构成的内容理解为组成它的要件之和。要查明犯罪构成的内容,首先就必须确定它的结构,即弄明白其中一般包括要件的哪些类别(种类)。”(22)所以犯罪构成在司法实践中只具有整体观念性的作用,要证明犯罪的成立控诉方必须证明犯罪构成各个部分的事实因素。裁判者也是基于对犯罪构成各组成部分的认定,然后才从整体上确认犯罪成立的。
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同时具备行为才成立犯罪。根据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必须逐一认定犯罪构成的每一个要件的成立,然后从总体上认定某罪犯罪构成的成立,从而作出有罪判决。
不过,现在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刑事司法中裁判者无须查清犯罪客体要件。例如,有学者将犯罪构成要件分为设罪犯罪构成要件与定罪犯罪要件,并认为犯罪客体是设罪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但定罪犯罪构成不应包含犯罪客体要件。其理由在于犯罪客体要件不具可感性、简约性和中立性;犯罪客体隐藏在客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方面的背后且处在高于这些要件的层次上,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而只能通过思维来间接地对它加以把握。在定罪中,我们能够通过也只能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这几个属于现象层面的要件去把握社会关系是否被侵犯。“只能通过”表明犯罪客体对其他要件的依赖,即对其他要件的认定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对犯罪客体的认定;“能够通过”表明其他要件对于定罪已属充足条件无须独立地、专门地认定犯罪客体。(23)更有学者根本上就否认犯罪客体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刑事司法犹如建筑施工,一种行为为什么被认定为犯罪,只需要说明已有的事实材料(包括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是否已符合刑法的实在规定。而传统刑法理论中作为犯罪客体内容的社会关系受到侵犯的事实则是立法者规定某罪背后的根据和理由,这用不着刑事司法工作者越俎代庖地再加以论证和说明。(24)
上述第一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立法论中犯罪客体有其一席之地,而刑事司法中则无须独立地认定犯罪客体;第二种观点则更强调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中不存在犯罪客体要件,更没有必要在刑事司法中加以论证和说明。该两种观点均主张犯罪客体无须在刑事司法中加以查明。这种观点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中的做法一致。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一般不承认犯罪客体的存在,其构成要件以行为为中心,将行为主体以及行为客体(在大陆法系中行为客体实际上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对象)当做原则的要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具体包括:实行行为、结果与危险、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25)
在英美法系中,在讨论犯罪成立与否时,一般不使用大陆法系中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而是使用“犯罪要素”这一概念。从英美法系刑法学著作的表述看,犯罪包括两方面的要素:危害行为和犯意。正如有学者所言:“一般说来,犯罪包括两方面的要素:危害行为(actus reus),即犯罪的物理或外部部分;犯意(mens rea),即犯罪的心理或内在特征。”(26)“通常将犯罪分为两个要素:危害行为和犯意,任何犯罪均可分解为这些因素。例如,谋杀是故意杀害他人的犯罪,谋杀罪的行为是杀人,犯意是故意。”(27)从这些学者的观点看,犯罪成立必须犯罪外部要素(危害行为)和内部要素(犯意)同时存在。犯罪外部因素通常包括行为人的行为、情节和行为导致的后果;而犯罪内部要素则包括目的、明知、疏忽、轻率等情况。
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犯罪成立的实体法标准看,均不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即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的地位。控诉方要证明的只有犯罪的外部要素(客观要素)和内部要素(主观要素)。两大法系在犯罪成立实体法标准上均不考虑社会关系受到侵犯的事实,这是与它们的形式犯罪概念相联系的,因为其犯罪概念强调的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是混合概念(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的结合),在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的同时又突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关系受到侵害的因素纳入到犯罪概念中。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28)所以,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就占有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犯罪成立的确认中就必须查明犯罪客体要件是否成立。
(2)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在我国刑事法理论中,犯罪构成是由四个要件组成的。那么这些犯罪构成要件又分别由哪些因素组成?这涉及另一个概念——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理论界看来,不同的构成要件是由不同的构成要件要素组成的,要确定构成要件首先要确定构成要件要素。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大谷实所言:“构成要件的确定,通过将构成其内容的各个要素抽象出来的方法进行。这些要素就是构成要件要素。”(29)我国学者认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包括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反映具体犯罪事实的因素,它属于构成要件的下位概念,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其犯罪事实必须符合犯罪构成要素,进而与犯罪构成相一致,才能构成犯罪。(30)这说明相对于犯罪构成这一整体系统而言,每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个子系统,在各子系统中还有一系列的因素,正是由这些因素构成了不同的构成要件。证明犯罪构成成立首先就必须证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成立。
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到底有哪些?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都是各有其自身结构的子系统。(31)根据该观点,犯罪构成要件的四个方面均应当有其独立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否则就无法形成各自的“子系统”。但从刑法理论界的论述看,一般认为犯罪主体要件要素包括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自然人主体)、刑事责任能力、身份等;犯罪主观要件要素包括:犯意、目的、动机等;犯罪客观要件要素包括: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等。犯罪客体则具有整体性,因为它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而为危害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虽然可以基于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但社会关系是一个整体,无法再细分出组成要素。
(3)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
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是认定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例如,犯罪客观要件要素中的行为,在刑法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行为可以分化为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方式等内容,这些分化的因素就是诉讼中的基本事实因素。我们在认定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时必须从这些事实因素入手。
虽然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包括犯罪主体要素、犯罪主观要素、犯罪客观要素和犯罪客体要素,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却均可归结为犯罪主体要件要素事实和犯罪客观要件要素事实。这是因为,虽然在刑法学主流观念中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该两类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没有自身独立的事实基础,也就是说犯罪主观要件要素和犯罪客体要件要素的把握只能建立在犯罪主体要件要素和犯罪客观要件要素的基础之上,由它们推导犯罪主观要件要素和犯罪客观要件要素是否充分。
首先,我们来看犯罪主观要件要素的判断。犯罪主观要件要素为犯意、目的和动机,这些要素均为内在于行为人内心的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的评判,裁判者只能基于行为人的行为事实加以推断。正如列宁曾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准来判断个人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个人的活动,——既然这里谈的只是社会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应该加上几个字:个人的社会活动,即社会事实。”(32)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在定罪中,案件事实分为行为事实和心理事实。“心理事实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对于心理事实的认定更为困难,这里存在一个根据客观事实加以推断的问题。”(33)或许有人认为,犯罪人的口供是认定犯罪人主观要件要素的依据。笔者认为,真实的口供虽然会揭露行为人的内心世界,但在司法实践中拒不供认自己实施犯罪时的真实心态的人大量存在,而且即使是真实的口供,如果没有其他客观证据加以印证或补强,亦不能对其犯罪主观方面加以认定。(34)
其次,我们来看犯罪客体要件要素的判断。犯罪客体是指刑法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社会关系无法通过感官感知,只能通过人们的思维来认识。(35)思维和存在是一对哲学范畴,思维以存在为前提是这对范畴的基本内容。虽然社会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人们只能通过对与之相关的事实因素对其加以认识。与犯罪客体相关的事实因素是什么?作为一种思维的抽象,社会关系本身没有事实因素,对社会关系的把握只能借助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有学者认为,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社会关系,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决定的。(36)有学者认为,在认定犯罪客体时,要把危害结果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和犯罪的主观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由于犯罪客体是犯罪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所以只能查清犯罪人的主观罪过的内容,并把它与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确定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37)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虽然取决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犯罪主观要件要素的认定即要借助于犯罪客观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所以在认识犯罪客体要件要素上,我们必须借助于犯罪主体要件要素和犯罪客观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
综上所论,“案件事实”的主要内容即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38)在刑事诉讼中,裁判者应当基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加以判断,这些事实包括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自然人主体)、刑事责任能力、身份等犯罪主体方面的事实因素和行为、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等客观要件方面的事实因素。当然,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作出有罪判决前裁判者要查清的具体事实因素也存在差异。一般认为,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年龄、精神状况、单位主体的法人身份以及危害行为等事实因素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必备事实因素,任何犯罪成立必须以这些事实因素被查清为前提。另外,自然人犯罪的主体身份、犯罪行为的对象、时间、结果、地点、方式等事实因素是某些犯罪的成立要素,这些犯罪的成立前必须查清此类事实因素。
3.否罪事实:排除犯罪性行为事实
控诉方证明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构成事实后,是否说明裁判者可以基于这些事实作出被告人是否构罪的判断呢?从犯罪构成的定义看,既然犯罪构成是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总和,那么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就包含了定罪所需的所有事实,如果控诉方已经证明这些事实符合某罪犯罪构成,裁判者就应当判定行为构成该罪。但刑法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控诉方证明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还不足以确认犯罪,裁判者还必须查清是否具有否罪因素,即是否具有排除犯罪性行为的事实。如果存在否罪因素,则即使控诉方证明的事实符合某罪的构成也不成立该罪。例如,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由法律的规定到与犯罪的诸要素相印证,进而确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在排除了犯罪性阻却事由后,定罪过程即告完成。(39)还有学者认为,从理论逻辑上看,一切侵害行为,在确认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后,并不直接定罪,而是在排除了阻却犯罪性的可能后,才进入定罪程序。在正常的诉讼中,行为的各种因素在被确认符合了犯罪构成要件后,已经说明在此之前没有发现阻却犯罪性的事由,但为慎重起见,再排查一遍是否存在阻却犯罪事由,可以起到避免冤假错案的效果。(40)
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或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例如,有学者认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指外表上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41)还有学者认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是指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在实质上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且大多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42)从现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和排除犯罪性行为理论分析,排除违法性行为理论与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论体系结构中是平等或并列的,不存在前者被后者所包容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阻却责任事由理论虽然与犯罪构成理论密切联系,但并不属于犯罪构成理论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43)既然两者的关系不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平行关系,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对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成立的证明和对于排除犯罪性行为事实不存在的证明就不是同时进行而是存在先后关系的。
但我国犯罪构成是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总和,我国的犯罪构成是实质的犯罪构成理论,而不是大陆法系中的形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存在形式或外表上符合犯罪构成的问题。所以控诉方证明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成立后,裁判者就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而无须查清其他因素。所以,主张符合犯罪构成但又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是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相符的。
显然,犯罪构成理论与排除犯罪性行为理论之间存在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有学者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思路:或许可以认为,如同将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放在犯罪主观要件中研究一样,将正当防卫等表面上符合客观要件的行为放在犯罪客观要件中进行研究,将经被害人的承诺或推定的承诺所实施的表面上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放在犯罪客体要件中进行研究,倒是合适的。(44)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它一方面化解了理论研究中的犯罪构成与排除犯罪性行为理论之间的矛盾,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有罪判决作出前的事实认定问题。从理论上看,将排除犯罪性行为置于犯罪构成理论中研究,符合犯罪构成为实质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立场。从司法实践上看,将排除犯罪性行为的事实糅合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认定中,控诉者证明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成立后裁判者即可作出有罪判决,而无须顾及其他因素。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否罪因素——排除犯罪性行为事实不是控诉方在刑事诉讼中独立证明的因素,在证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成立后就已经完成了排除非犯罪行为任务,裁判者在认定某行为符合某罪犯罪构成后,即应当作出行为构成该罪的判断。
4.“与犯罪有关的事实”分析
有学者认为,“在定罪中,犯罪构成一直起着中心的和主导的作用。”(45)什么是“中心和主导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之外还有些因素与定罪相关?
有观点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犯罪是否成立,原则上只能以犯罪构成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就充分表明了行为是否包含了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能否成立犯罪,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决定或制约犯罪成立的要件或者因素。”(46)这说明只有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才是决定或制约犯罪成立的因素,定罪中只需考虑这些因素,而无须考虑其他任何因素。但刑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定罪量刑根据的事实主要是犯罪事实,但不限于犯罪事实,还包括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事实。(47)该学者认为:“什么是与犯罪有关的事实?笔者认为是指本身不是犯罪事实,但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48)但在列举一系列“与犯罪有关的事实”时,论者仅仅列举了与量刑有关的事实因素,并没有列举出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因素。有学者更是明确地指出:“把定罪仅仅归结为确认某一行为的诸要件与法定犯罪构成的诸要件完全相符,而把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和判断,完全排除在定罪的视野之外,这是不正确的。”(49)言下之意,定罪中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不是定罪的唯一事实,还有其他事实因素,至于还有哪些因素,论者没有言明。
笔者认为,在定罪程序中裁判者所要查清的事实只有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实要查清。其原因在于,犯罪构成是决定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大小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总和,既然是“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总和”,怎么会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之外还有其他决定或影响定罪的因素?
(二)“案件事实”解读之二:量刑事实
从广义上的量刑定义出发,量刑的内容包括:确定是否对被告人适用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何种刑罚及刑度、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等内容。量刑事实就是人民法院在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确定对被告人处理方式和处罚程度时所应当考虑的事实。
1.“量刑情节”与“量刑事实”辨析
与量刑事实相连的一个概念是“量刑情节”,刑法学界一般认为量刑的根据是量刑情节。例如,有学者认为:“定罪的根据是犯罪构成的事实,量刑的根据是量刑情节。司法活动中正是根据量刑情节来确定对被告人判与不判、重判与轻判的。”(50)何谓“情节”?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情节是指事情的变化和经过。(51)这说明情节是对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是一个表达动态意思的词汇。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情节无疑也是由一系列的事实组成的。犯罪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到完成的过程,如果以回顾性的方式重现犯罪经过,也可以使用“情节”这一术语。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虽然也要基于证据重现犯罪发生、发展至完成的经过,但作为定罪或量刑基础的还是静态的、具体的事实。我国学者在界定量刑情节时往往脱离“情节”过程描述性这一特点,而专注于静态的事实。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量刑情节,是指除定罪情节以外的,据以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其基本特征是能够反映出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人身危险性。”(52)“犯罪情节是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时所为行为的各种情况,是组成犯罪事实的基本单位。”(53)既然“量刑情节”的界定中只能对静态事实加以概括、无法体现“情节”动态特性,我们就应当使用“量刑事实”这一术语而不宜使用“量刑情节”这一概念。
2.关于刑法第61条规定的理解
对于量刑中应当考虑哪些事实,刑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刑法第61条规定了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即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但笔者不认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这四个方面是立法者对量刑事实的概括,其原因如下:
首先,这里的“犯罪的事实”是指犯罪构成事实,即作为定罪事实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对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在量刑中的作用,刑法学界理解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在量刑中具有参考价值。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犯罪成立后,刑事诉讼即进入量刑阶段,犯罪构成要件的某些方面,虽然也在量刑中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已不起主导作用了。(54)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不应当在量刑时加以考虑,否则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例如,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在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必须发挥作用,但刑法不能对某一犯罪事实作重复评价,因此,作为认定犯罪构成是否成立的事实,在量刑时就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从而再对处刑轻重产生影响。(55)
笔者认为,既然是定罪事实就不成为量刑事实,否则就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这一点早已成为我国学者的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禁止法条所规定之构成要件要素,在刑罚裁量中再度当做刑罚裁量事实,重加审酌,而作为加重或减轻刑罚之依据。(56)还有学者认为:“对于属于基本罪状内容的情节,在量刑时不得重复考虑。因为刑法在根据基本罪状规定法定刑时,就已经考虑了属于基本罪状内容的情节。易言之,基本法定刑的确定,以基本罪状的综合因素为根据,因此,基本法定刑的确定,已经考虑了属于基本罪状内容的情节。如果在量刑时再次考虑这种情节,则意味着对这种情节进行了重复评价。”(57)
其次,决定“犯罪的性质”的事实也不是量刑事实。所谓犯罪性质是指犯什么罪,即应确定的具体罪名。(58)显然决定行为构成何罪的事实是构成要件要素事实,属于定罪事实的范畴。
再次,决定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的事实有的属于定罪事实,有的则是量刑事实。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事实(但它不决定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全部内容)。行为的危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所以犯罪的成立意味着行为的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的量。任何犯罪的成立在社会危害性上有一个临界点,社会危害性低于临界点行为就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社会危害性达到临界点行为就构成了犯罪,达到临界点的社会危害性的量就是定罪因素,社会危害性超过这个临界点的部分就不再属于定罪的范畴,而属于量刑范畴。所以,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达到临界点的事实就是定罪事实,影响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超过临界点的事实是量刑事实。
3.量刑事实的范围
在量刑中应当考虑哪些事实?笔者认为,量刑事实应当是定罪事实以外的,与行为人自身或其行为直接关联的,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适用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何种刑罚及刑度、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事实。这说明从范围上看,量刑事实首先必须是定罪事实以外的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以外的事实),其次必须与行为人自身或其行为直接关联,再次必须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
在量刑事实中有一类事实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类事实即定罪剩余事实。如前所述,定罪事实是指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因素,构成要件要素事实已经在定罪时被运用,根据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这些事实就不能再作为量刑事实在案件处理中重复评价。但某些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数量范围,或者刑法为某罪的成立规定了可选择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或者行为触犯了几个罪名但只能作为一罪处理时,均存在定罪时无法对全部构成要件要素事实进行评价而出现定罪剩余事实的情形。定罪剩余事实属于量刑事实范畴,这种事实主要出现在数额犯、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和具有可选择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中。
首先,在数额犯中,犯罪数额是犯罪客观要件,只有达到了法定的基本数额,行为才可能构成犯罪。正如有学者所言: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属于犯罪构成的定量标准,其功能在于区分罪与非罪。(59)盗窃罪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根据刑法的规定,盗窃数额较大是盗窃罪成立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数额较大的起点规定为500元至1000元。假设某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为1000元,则此数额是盗窃行为构罪的基本数额。但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所涉及数额往往不会是恰好为1000元,超过基本数额的数额就不属于盗窃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内容,超过基本数额的部分就属于定罪剩余事实,应当作为量刑事实加以考虑。
其次,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行为人一个行为触犯多个罪名,或多个行为触犯多个罪名但以一罪处理。前者是指想象竞合犯,后者是指牵连犯。所谓想象竞合犯,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侵犯数个客体而触犯两个以上罪名的犯罪形态。对于想象竞合犯刑法学界一致认为应当作为一罪处理,只是具体的处理方法有择一重处断和择一重从重处断之分歧。其实无论是哪种具体的处理方式下,有一部分本应当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量刑事实对待。具体而言,行为侵犯两个或两个以上客体时,只有其中一个决定犯罪客体的事实作为构成要件事实在定罪中被运用,决定其他客体的事实则作为量刑事实被运用。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除刑法中明确规定以数罪并罚处理外,牵连犯应择一重处断或择一重从重处断。显然,牵连犯是行为人实施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符合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但由于数额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最后作为一罪处理。也就是说,在牵连犯中,数个犯罪构成事实中只有符合某一个罪的构成事实在定罪中作为定罪事实被运用,其他本为构成要件事实作为定罪剩余事实只能在量刑中加以评价。
再次,针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刑法为某些犯罪的成立规定了可选择的构成要件要素,这种选择要素可能是行为选择、对象选择、结果选择等。在其他构成要件成立的情况下只需具备选择性要素之一,此类犯罪便成立了。但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可能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要素。例如,交通肇事者的肇事行为造成一人死亡或三人重伤,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作为构罪评价的结果要素,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只需造成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两种结果的情况下(如造成一人死亡同时造成三人重伤),只需其中之一作为定罪事实,其余的一个事实就应当作为剩余事实在量刑中加以考虑。
综上所述,定罪剩余事实是构成要件的多余事实,由于这些事实在定罪中无法加以评价,只能作为量刑事实加以评价。我们在确定量刑事实时不能忽略这些事实的存在。
那么,定罪事实如何与定罪剩余事实区分?有学者对此作了原理性划分,即凡是用以充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事实情况,都是定罪情节;定罪剩余的那些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转化为量刑情节。犯罪构成的“起码要求”是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标志。(60)具体到数额犯,定罪事实与定罪剩余事实的区分标准就是构罪标准,即达到构罪标准基本点的数额就是定罪事实,超过这个点的数额就是作为量刑事实的剩余事实。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中重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是定罪事实,轻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是作为量刑事实的定罪剩余事实。
三、“清楚”解读
“案件事实清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何为“案件事实”和何为“清楚”。刑法学界和刑事诉讼法学界均没有直接论及何为“清楚”这一问题,似乎其含义不言自明。其实,“清楚”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里的“清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谁清楚?清楚的程度是什么?哪些案件事实要求“清楚”?
(一)“清楚”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该条使用的是“法院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否说明立法者要求有罪判决作出时裁判者应当清楚案件事实?笔者认为,有罪判决是由法官代表法院作出的,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当然应当清楚案件事实,如果裁判者本身即感觉案件事实不清,当然不能作出有罪判决。但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控辩双方参加诉讼,实践中的情况可能较此复杂。如果诉讼双方和法院均认为某案的事实清楚,裁判者作出有罪判决当无疑义,但当不同诉讼主体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存在理解上的冲突时,如何解决其间的冲突决定着判决的结果。不同诉讼主体之间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的理解冲突主要表现为:控诉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但法院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或控诉方与法院均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但被告方认为案件事实不清。
控诉方与法院对于同一案件事实清楚与否存在理解上的冲突时,剔除案外因素不论,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控诉方与法院所倚立场差异;二是对“案件事实清楚”标准理解不一。
从控诉方所倚立场看,控诉方控诉的目的是追诉犯罪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控诉方只有在认为“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提出控诉。《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公诉案件中,如果控诉方认为案件事实不清,就不可能作出起诉的决定。所以,除非在诉讼过程中辩护方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控诉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否则在诉讼过程中,控诉方必然始终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清楚了。但正如有学者所言:这只是检察机关单方面认定,并不同于审判阶段经控辩双方质证、辩论以后中立裁判者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法律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客观、公正地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但受检察机关的职能以及所处诉讼阶段影响,此时的认定不可避免地带有单方性和偏向性。(61)
导致控诉方与法院对于同一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理解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清楚”标准的确定。如上所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标准之一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所谓“已经查清”当然是指公诉机关(或自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但这里的“已经查清”与有罪判决中的“清楚”是否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那么两者对案件事实清楚的理解就不应当存在分歧,否则就会由于对标准理解的差异导致分歧。从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观点看,一般认为,公诉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应当有差异,两者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学者解释来看,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更为严格,二者之间具有层次性。(62)其层次性表现为提起公诉的标准要低于有罪判决的标准。但从诉讼法规定看,我国提起公诉的标准与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在用语上没有多少差异。所以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未能在我国刑诉法中得到充分体现。(63)有学者则更是明确地指出,在我国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判决有罪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一致的,都可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64)既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标准实质上存在差异,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表达中又没有对两者作出区分,那么,在刑事审判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控诉方与裁判者对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会导致案件事实认定的困难,正如有学者所言:“公、检、法各机关之间经常因为对客观真实产生歧义,乃至互相扯皮、推诿、拖延诉讼时限,个别案件由于证明标准不统一,导致打击不力,形成错案。”(65)
当控诉方与裁判者对于同一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理解上存在分歧时,如何解决两者的分歧?根据裁判终局性原则,对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最终以裁判者的认识为依据。这是否意味着控诉方关于案件事实清楚与否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意义?其实不然。《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地方公诉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法院认为事实不清,公诉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事实不清,可以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虽然经过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自诉人上诉后案件仍由人民法院审理并由后者作出裁判,但抗诉或上诉有可能改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的看法。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诉方和法院均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但被告人(或辩护人)可能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这种理解上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这主要是由被告人(或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的,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被告人为逃避责任往往会千方百计拒绝承认犯罪事实,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也会基于与公诉方不同的视角理解和运用案件中的证据,导致对案件事实清楚与否理解得不一致。当被告人(或辩护人)与法院对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存在分歧时,如何解决这一分歧?《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被告人和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虽然经过被告人上诉后案件仍由人民法院审理并由后者作出裁判,但上诉有可能改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的看法。
综上所述,案件事实清楚的主体应当是作为裁判者的人民法院、作为控诉方的公诉人或自诉人、作为被追诉者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不同的刑事诉讼主体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存在理解上的冲突时,裁判中以人民法院的认识为标准。
(二)“清楚”的标准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清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事物容易让人了解、辨认,如字迹清楚;二是对事物了解很透彻,如头脑清楚;三是了解,如这件事的经过他很清楚。(66)《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哪个层面的“清楚”?这里的“清楚”是指第三种含义,即案件事实清楚是指刑事诉讼主体对案件事实了解、明白。
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刑事诉讼主体是否已经对案件事实了解、明白了呢?这就存在一个清楚的标准问题。对于清楚的标准,刑事诉讼法学界没有直接加以探讨。从已有研究看,刑事诉讼法学界都是研究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问题。如前所述,从另一个角度看,刑事证明标准即有罪判决标准,只要控诉方的证明达到了刑事证明的标准,从实体法的角度看裁判者就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以使裁判者信服、从而作出有利于己方判决的标准。该标准的实质即在于将己方的诉讼主张证明到使裁判者信服的程度。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时裁判者会信服呢?就有罪判决而言,裁判者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了,才会作出有利公诉方的裁判。
“案件事实清楚”本身极为概括、抽象,无法作为司法实践中衡量证明是否达到了证明的程度要求,所以刑事诉讼法学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性的标准,如客观真实标准、法律真实标准。所谓客观真实标准是要求刑事诉讼证明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即“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67)“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68)而法律真实论者则强调刑事诉讼中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真实,只有法律上的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69)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标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有罪判决的具体实体法标准问题,因为何谓“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或“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为了给刑事审判中的裁判者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刑事诉讼法学界回归到“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概念,认为刑事证明的标准即:(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能够排除其他可能性。(70)
笔者在前文中强调我国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是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那么如何衡量裁判者在作出有罪判决前对犯罪事实已经“清楚”了呢?笔者认为,裁判者对犯罪事实“清楚”的标准即排除了合理怀疑。由于有罪判决要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罪、构成何罪、构成一罪还是数罪、构成重罪还是轻罪(如果是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还有可能要弄清犯罪处于何种停止形态)以及其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所以只有当裁判者在这些方面均排除了合理的怀疑,裁判者才可能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清楚。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案件事实“清楚”的标准与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一致,因为其解释中也有排除合理怀疑的成分,只是“证据确实、充分”还有对证据本身可采性、证明力等方面的要求。
既然案件事实“清楚”的标准是裁判者基于刑事证据排除了关于案件事实的合理怀疑,那么排除合理怀疑就成了司法实践中确定案件事实是否“清楚”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的标准,但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就何为“排除合理怀疑”作出立法上的规定,对于是否给该标准下定义存在较大的分歧,已有的关于该标准基本涵义的界定也有较大的差异。(71)不过,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中常引用的说法是《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即“排除合理怀疑”在证据法中意味着对道德确信上充分地满足、彻底地相信;在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意味着那些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的证明力如此之强以至确定被告人有罪。(72)因此,排除合理怀疑是作为理性的人根据证据进行推理,他们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推论。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排除轻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怀疑,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除非这种假设已经有了根据。排除合理怀疑的本质核心在于确定何为合理的怀疑。合理怀疑应当是有理性的裁判者本着道义和良知、基于刑事证据提出的、可以说明理由的怀疑。因此,以下怀疑就不能视为合理怀疑:(1)任意妄想怀疑;(2)过于敏感机巧的怀疑;(3)仅凭臆测的怀疑;(4)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怀疑;(5)于证言无征的怀疑;(6)故为被告解脱以逃避刑事责任的怀疑。(73)
(三)“清楚”的范围
如文章前部分所述,“犯罪事实清楚”标准中,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为公正地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在刑事审判中控诉者应当尽力举证证明犯罪行为的事实,裁判者也应当尽力查清所有的犯罪事实。
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查清所有的犯罪事实?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办案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74)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75)不过,现在多数学者则认为完全重现犯罪事实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案件事实无法查清。(76)有学者则断言:“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根本做不到完全发现或者证明原来客观上发生的事实。”(77)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是对已发生的案件的一种历史性回溯,由于时过境迁、认识手段的局限、诉讼时效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控诉方不可能丝毫不差地重现所有的犯罪事实。这就说明刑事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是案件发生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所有事实。既然刑事诉讼中无法查明所有犯罪事实,那么如何作出刑事判决?学界的通说观点认为,凡是未能查清的事项,都不能认定。当一起案件中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而另一部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较为次要的犯罪事实无法查清时,可以忽略不计或对未能查清的那一部分实行疑罪从无。如果仅据已经查清的部分还不能定罪时,则应对全案实行疑罪从无。(78)该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主要犯罪事实”的概念,只要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就可以作出有罪判决。那么何为“主要犯罪事实”?根据该观点,所谓“主要犯罪事实”就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影响的事实就是次要犯罪事实。
除此“主要犯罪事实”的提法外,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颇为流行的另一个提法是“基本事实”。“基本事实”的提法源于1985年5月彭真同志《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即“一个案件只要有确实的基本证据、基本情节清楚,就可以判”。刑事诉讼法学界将此概括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对于“基本事实”的界定,学理界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基本事实,实际上就是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79)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基本事实即为构成要件事实。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不全面,因为有罪判决中不但要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在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还要解决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单纯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显然无法完全决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有学者认为,基本事实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于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有影响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二是对于确定犯罪性质有影响的事实;三是对于确定法定加重、从重、从轻、减轻和免除刑罚情节有影响的事实;四是对于确定是否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情形有影响的事实。(80)此四方面事实中前两部分事实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因为“对于确定犯罪性质有影响的事实”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第三部分事实属于量刑事实(但其列举的量刑事实并不全面,因为量刑事实并不仅指从严事实和从宽事实,它还包括基准量刑事实)。这些事实均是基本事实的内容。不过,对于该观点中的第四部分事实则应当区别对待。该部分事实中有的属于实体法事实,有的属于诉讼法事实。例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就属于实体法事实,这一事实已经被犯罪构成事实所包容;“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事实也属于实体法事实,该事实已经被量刑事实所包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则属于诉讼法事实。
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基本事实应当是指影响定罪和量刑的事实,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二是此罪与彼罪界限的事实;三是罚与不罚界限的事实;四是此罚与彼罚界限的事实。(81)从内容上看,“基本事实”与案件事实实际上没有区别。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基本事实”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过于绝对,以前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的要求过于全面,以致司法实践中裁判者无所适从。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中的困境,提出了“基本事实”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不是与“案件事实清楚”相对立的标准,也不是对我国有罪判决标准要求降低标准的修正,(82)“基本事实”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中的“案件事实”。所以,“清楚”的案件事实的范围就是“基本事实”,而不是案件事实的全部。
*本文得到了西南政法大学孙长永教授的指导,在此对孙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文章中的错误、疏漏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陈瑞华:“对证明标准问题的一点思考”,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5期。
②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
③龙宗智:“‘确定无疑’——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载《法学》2001年第11期。
④汪建成、刘广三:《刑事证据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⑤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类似观点另参见刘金友主编:《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汪建成、刘广三:《刑事证据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⑥宋博:“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反思”,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⑦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⑧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⑨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页。
⑩崔敏:“刑事证明标准之我见”,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11)张昊:“也论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彭真军:“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2)朱菊银:“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3)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14)从定义上看,量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量刑仅仅指在法定刑范围内裁量决定刑罚;广义的量刑则既包括刑罚的适用也包括免予刑罚惩罚。前者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后者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笔者在文中采用的是广义的量刑概念。
(15)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6)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3页。
(17)赵廷光:“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8)高格:《定罪与量刑》(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9)王勇:《定罪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20)陈兴良:“定罪之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22)[苏]B·H·库德里亚夫采夫:《定罪通论》,李益前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23)夏勇:“定罪犯罪构成与设罪犯罪构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5期。
(24)杨兴培:“再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弊端”,载《法学》1999年第9期。
(25)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13页。
(26)Joshau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New York:Matthew Bender &Company,Inc.2001,p.81.
(27)Nicola Padfield,Criminal Law,Beccles and London:Reed Elsevier (UK) Ltd.,2002,p.21.
(28)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29)[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30)侯国云:《刑法总论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31)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32)《列宁选集》(第1卷),第383页。
(3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3页。
(34)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心态。
(35)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36)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37)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38)应当说明的是,我国刑法学界一般不习惯于使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事实”这一概念,而习惯于使用“定罪情节”。例如,有学者认为,定罪情节就是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不是哪一个事实所能代表的,它是事实的整体,注重的是各种事实整合所形成的整体性,而作为定罪的情节,则注重的是事实的具体性,是各种具体的情节,离开了犯罪构成事实,离开了定罪情节,也就没有犯罪构成。参见李洁:“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9)杨春洗主编:《刑法基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40)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41)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
(42)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43)肖中华:《犯罪构成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19页。
(44)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45)杨春洗主编:《刑法基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46)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47)高格:《定罪与量刑》(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48)高格:《定罪与量刑》(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49)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50)谢玉童:“对量刑原则的再思考”,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2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35页。
(52)黎其武、徐玮:“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
(53)王晨:“量刑情节论”,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
(54)杨春洗主编:《刑法基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55)刘芳等编著:《定罪量刑标准通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56)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57)张明楷:“结果与量刑——结果责任、双重评价、间接处罚之禁止”,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58)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59)刘之雄:“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
(60)赵廷光:“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1)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62)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63)熊秋红:“从英美法看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5期。
(64)田中臣:“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4期。
(65)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32页。
(67)巫宇甦主编:《证据学》,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68)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69)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70)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18页。
(71)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72)Black's Law Dictionary(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p.147.
(73)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67页。
(74)刘金友主编:《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75)张子培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76)崔敏:“刑事证明标准之我见”,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77)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78)崔敏:“刑事证明标准之我见”,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79)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80)刘金友主编:《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81)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82)刘金友主编:《证据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标签:刑事诉讼法论文; 犯罪客体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法律论文; 犯罪主观方面论文; 实体法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量刑情节论文; 程序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