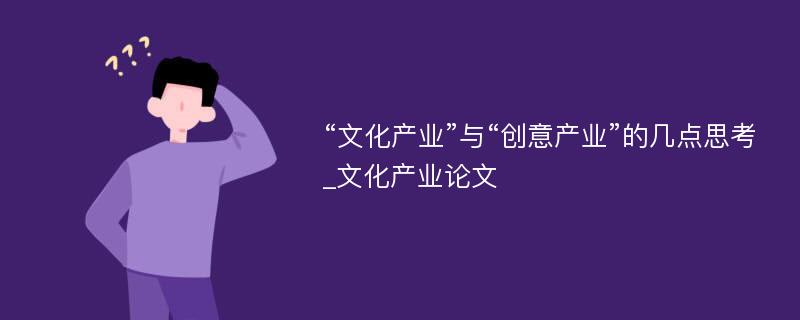
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关于“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文化产业论文,太急论文,根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5-0031-02
“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两个概念的所指大体一致,都包括出版、广告、影视、广播、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建筑、音乐、表演艺术、时尚等。名者实之宾,所以两个概念基本可以互换,即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产业”、“头脑产业”、“意识产业”等,我觉得也无实质性差异。且文化上的诸多概念历来充满争议,一定要在这两个概念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小车不倒只管推”,概念是语言行动的工具,大体能用就行。尤其是考虑到“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只是最近这十来年才在中国盛行,因此就语言和政策的连续性来说,也不一定要以“创意产业”取而代之。
当然,既然是两个概念,总是有区别的。虽然1930年代的“十里洋场”有过发达的文化产业,虽然改革初期文化产业就在中国萌芽生长,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崭露头角并为党、政府正式承认,却是在20世纪末期。即使不考虑政治化时代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仅1980年代以后,文化界对文化产业也从来不是热情拥抱的,党政学各界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疑虑,而且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而“创意产业”的概念一经引进,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就流行开来,甚至讲文化产业,也要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的说法。固然,“文化产业”概念的普及已经为“创意产业”的概念准备了接受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创意产业”在中国语境中不同于“文化产业”的意义。第一,“创意产业”同时包括了研发、设计、数字软件等更为技术性的产业,更多地内在于工业生产、产业部门之中,是在当代社会、科技条件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经济文化化、体验化、人性化的过程,物质生产、实体经济与个性张扬、自由创造逐步会通,具有克服现代经济的“异化”的理想性质,文明人类没有理由反对或抵抗这一过程。而“文化产业”更多是指文化艺术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与经济系统的融合。从近代以来流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三分来说,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当它与经济融合起来而成为一个产业时,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经济理性、市场逻辑对文化心理的殖民,有可能挤压、限制独立个性的自由表达,抑制、妨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因此,接受“文化产业”这个概念需要文化观念的变革,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尊重文化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第二,尽管由英国工党率先提出的“创意产业”概念具有鲜明的政府、政治色彩,是布莱尔改变老工业帝国的“新英国”计划的一部分,但在汉语言中,“创意”更多与个体的自由想象相联系,而“文化”则更多与民族传统、国家体制、政治价值观相联系,因而“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性更为确定。至少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使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在中国比“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更易接受。也因为这两点,“创意产业”更多更好与物质、经济生产相联系,而“文化产业”更多与文化、社会领域相联系。
“创意产业”之所以易于普及并似乎更受到推崇,也在于它比“文化产业”在概念上更多地突出了“创意”和创意的个体。中外对“文化产业”的疑虑甚至批判,在其把文化创造的一次性转换为产业的可“复制”(“再生产”)性。没有复制技术与复制实践就没有文化产业,由此而来的标准化、模式化成为“文化产业”的最大诟病。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文化产业不但体现了资本主义无所不能的整合能力,而且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把对立物系统地组织起来因而导致对立物不可避免地终结的神话暴力。他们之所以把广告、流行音乐、好莱坞、卡通等一言以蔽之地称为“文化产业”而加以批判,不但因为它们是像肥皂和汽车一样的消费品,而且因为它们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制之中而丧失了批判潜能,在服务于资本增值和操纵心灵方面并无不同。显然,批判理论的预设是“文化”与“产业”的二分:前者是与个性自由、否定精神相联系的理想世界,后者是与异化劳动、技术理性相联系的物的领域。文化之成为产业,是统治逻辑的胜利,是个体的终结。批判理论对文化产业的指控,是20世纪上半叶变革社会的希望日益暗淡的现状表达。真实的情况也许是,一方面,当代社会空前强化和提升了统治与操纵的力量、技术和手段,奥威尔笔下“老大哥”早已不再是虚构。另一方面,保护个体自由的各种社会组织空前活跃,社会生活的人性化日益清晰,个性自由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实现空间。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英国文化研究不再视文化产业的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产品在有选择的消费行为和生产性的阅读和阐明行为中被重新定义、重新定型,并改变了其原来的方向,而这一切往往与其生产者的本意或所预见的情况截然相反。这就是说,文化产业确实体现了权力和金钱的意志与逻辑,但公众并非铁板一块地受其摆布;文化产业有其同质性,而受众却是多样的、变异的。文化产业的社会后果,取决于公众与生产商(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之间的谈判和博弈。可见,“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之所以引发诸多议题,重要原因在于“文化”。至少在传统的语境中,“文化”与价值理想、个性追求、真善美体验等难解难分,一旦它成为资本运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权力和金钱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我们又从何处去落实我们的价值关怀、心灵寄托和自由想象呢?无论我们多么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对中国经济建设有多大作用,但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由感来说,我们都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化产业”,我们还需要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还必须有独立于金融体制之外的个性自由表达。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人有多大的可能走出理性化的“铁笼”,摆脱一切都被管理、被操控的命运?客观地说,文化产业没有取消(也不可能取消)个性创造,但其组织化的、体制化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确实对个体、个性在文化领域中的位置和价值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来回应:产业化或许造成文化的异化,但经济活动却因文化的介入而更多地具有自由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比较充分地突显了当代文化的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同样必须警惕文化产业的社会后果。
如此说来,“创意产业”的概念就较为单纯、便捷。“创意”的资源是文化,但“创意”行为本身却不像“文化产业”那样拥有源远流长的理想和规范意义,因为人类生产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少不了创意。影视剧作、媒体广告固需创意,制鞋造帽、空调冰箱也需要创意。因而,使用“创意产业”的概念可以避免诸如民族传统、政治价值、意识形态之类的制约,减少争议、突显核心。当然,不但“创意产业”中的大部分就是文化产业,而且这两个概念也无法完全分开。第一,“文化产业”也需要创意。文化成为产业以复制为前提,但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行动要值得复制、需要复制,在于它内涵高度的创造性和独特的价值体验。一些被用来界定“创意产业”的关键词,如“好奇心”、“想象力”、“灵感”、“理念”、“创新”、“技艺”等,也是文化的内在品格;所谓创意产业的“3T”理论(人才、技术、宽容)也为当代文化生产所必需。古今中外,任何优秀的文化产品、服务和行动都是以个体创造性为特征的。先有创造后有复制,复制是文化产业的下游和低端,没有创造的文化不可能有市场。第二,“创意产业”也需要复制。仅仅一个创意,还不足以成为产业。比如软件、时尚如不能复制,其经济价值又从何而来?甲的创意要为乙所用,必须转化为产品与服务,这就需要“复制”(再生产),孤立的“创意”不可能成为“产业”。创意产业就是“一个好主意变成一桩好生意”。有一、两个“好主意”的人很多,但能做成一桩“好生意”的人却不多,这其间的差别就在于“生意”需要由复制(再生产)而来的产品、服务。
所以,我觉得,“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两个概念都可以用,在文化领域,我们可以多用“文化产业”,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化的同时,注意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多用“创意产业”,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知识与创意已经逐步取代资源与劳动力成为财富创造与经济的主要源泉,从而加快我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这是两个同志式的概念,大体一致而各有侧重,不同使用者、不同情境可以有不同选择,但没有必要煸动它们之间的内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的讨论应当是“‘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而不是“‘文化产业’还是‘创意产业’”。
收稿日期:2009-08-15
标签:文化产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