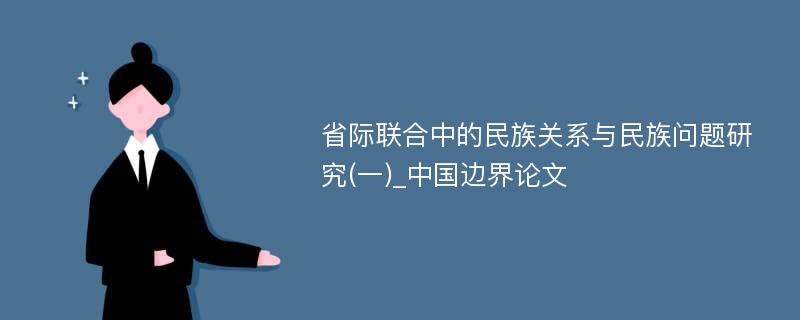
省际结合部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研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2)04-0037-05
省际结合部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单元,它指以省级行政边界为起点向行政区内部横向延展一定宽度所构成的、沿边界纵向延伸的窄带型区域。从行政区划看,边界划分十分清晰,行政隶属关系十分明确;从范围上看,包括若干县及县级市,延伸数百公里及上千公里,远离省级行政中心或经济中心;从自然环境角度看,划分界线一般是以山脉或河流等自然屏障为界,差异较小,更多则体现其整体性特征;从人文生态角度看,省际结合部具有地缘结构、文化习俗、民族传统、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和经济区位的同一性,因而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边界区域,它会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省际结合部仍然是一座未被开发的学术富矿,其自然和人文生态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特征和特性尚待探讨,以及省际结合部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族群利益导向、群体性事件、民族发展战略、小城镇建设、边贸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区域联合与协作等方面值得我们长期的跟踪和研究。
一、关于省际结合部的界定
1.传统边界的定义及其内涵的延展
边界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从普通意义上讲,它是指事物间本质或现象发生变化的标志线或地带。按区域行政、政治实体的级别或层次,区域边界自上而下大致可分为:“国家边界”、“省际边界”、“地方边界”。传统边界的划分方法将边界划分为“自然边界”和“人为边界”。自然边界是以自然要素作为划分的依据,大都是由自然屏障和景观构成,如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人为边界”是以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意识形态、心理、习俗等社会性因素作为依据划分的边界。[1]可以看出,以上两种边界类型是看边界划分的依据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因素,它并没有考察边界形成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从边界的形成过程的角度分析边界的本质,边界同时具有“自然”和“人为”属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有组成社会群体的倾向,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物质利益的因素,参加群体可以获得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一种功利性动机。二是社会心理因素。每个人都有许多社会心理需求,这些需求只有在群体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实现和满足。这类社会需求主要包括安全感、归属感、良好自我形象的维护、荣誉感、自尊的获得、情感的交流以及自我实现等。[2]同时群体的划分也是与空间相联系的,也就是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更倾向于居住和生活在同一地域空间范围内,而空间边界则是群体空间分异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人类群体的社会化本质是空间的。[3]莱芬博尔(Lefebvre)认为,“人类群体划分在本质上是空间的划分,反映出人类倾向于居住和生活在有界的空间愿望,作为与空间划分伴生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是群体分异的标志,也就是说,人类希望并通过划定空间边界来创造属于自己同一群体的领土范围。对人类来说,特定空间被看成是群体成员集合的地域”。[4]可以看出,边界实际上是群体在空间上划分领土的标志,它是群体在空间上对领土具有排他性控制权力的分隔线。
从人类社会空间行为的角度看,边界的产生的划分常常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空间活动带有明显的情感指向,而情感的空间界限就是边界。由于人类具有群体意识并产生对领土空间的情感是一个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化的过程,因此边界的情感属性常常是与民族和民族的形成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特定的血缘集团,如宗族,在特定的区域内其成员随着互相交往的扩大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认识到自己本身的这些共同特征。在这种共同意识的作用下,原先松散的血缘集团——自然共同体,逐渐扩大凝聚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且每个成员都对这个共同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因此,民族的形成既有客观的一面又包含有主体意识的一面,可以认为民族是具有相同血缘,共同的心理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并对这个共同体有着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就像一切实体事物均需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载体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某一特定空间,从空间的角度,这是对共同或相近生活、居住地产生的空间认同与归属感。族群间的团结与联合最初主要源于为抵抗来自外界其他族群,或者说来自外部空间的威胁,这种对内部空间的认同和对外部空间的排斥情感,要求民族内部的趋同和外部的分异,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不同地域占有的民族边界的产生。
2.我国省际结合部概况
我国省际结合部面积巨大,在已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中,陆路边界线总长5.2万公里,分布着84个县(市),占全国总县数的39%。[5]如山东省省际边界地区有日照、临沂等8个市与外省毗邻,占全省17个地级市的47%,土地面积的56%。[6]河南省与周边6个省相邻,共有沿边县(市)43个,占全省县份的36.4%。[7]浙江省与安徽、江西、福建三省交界,自北向南有长兴、苍南等13个县(市),总面积为2.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7.2%。[8]甘肃省现有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其中有12个市州、50个县市区分别与四川、陕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和新疆6省区接壤,省际边界线长9807公里。[9]湖北省边界地区涉及37个县(市、林区)的144个乡镇,国土面积为19418.5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0.4%。[10]
我国省际结合部大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据统计,我国现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共有155个民族自治地方。我国30个自治州中有20个处于省际边界,8个与两省接壤,8个与三省接壤,4个与四省接壤;120个自治县(旗)中有55个处于省际边界,47个与两省接壤,7个与三省接壤,1个与四省接壤。[11]我国呈南北纵向的“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和呈东西横向的“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古氐羌走廊”基本上处在省际结合部地区。[12]西藏、四川、云南三省间的藏彝走廊,从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迁徙与文化交往活动的大舞台。瑶族、侗族主要聚居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地区。鄂湘黔渝四省市交界处的武陵山区,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聚居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30多个少数民族,1300多万人口,占武陵地区总人口的63%。
二、省际结合部的自然生态
1.多以高山大河为自然分界
省际结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其特殊性就表现在它位于我国最大行政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从理论上讲,省际应是经济、信息、人力资源、文化的汇集地带,理应成为省际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等经济要素的流通地带,有着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与潜力;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交界地带人们的观念、民族传统和风俗民情具有融和性,形成互通有无,共生共荣的聚落,建起良好的地缘关系。但是从自然生态环境看,省际结合部一般以高山、大河为自然分界,区位偏僻,交通不便,穷山恶水,远离中心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活质量相对较低。黄河是陕晋、豫鲁的省际边界线;太行山:晋冀鲁豫四省在此接壤;湖北、四川以武陵山、大巴山为界;江西、福建、浙江以武夷山、仙霞岭为界。高山大川,交通不便,地处边远,便形成了有名的贫困山区。我国有名的省际结合部有湘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川黔、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川陕甘等,都是革命根据地。当年革命者正是利用这些山川和交通不便便于隐蔽的环境,在这里进行旷日持久的革命斗争,因此,贫困山区大都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2.交通条件差,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低
按照景观生态学的观点,每一种景观都是由基质、镶块体和廊道构成,其中廊道是景观内部及景观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转化与传输的通道。对于省际结合部而言,廊道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讯、通电、通路及计算机网络等。从目前我国省际结合部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考察,尽管各种廊道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最严重的是边界地区的交通布局的条块分割,自我封锁、自成体系,成为边界地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省际交通条件差的状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境交通路线少。二是过境交通路线质量差。三是边界地区断头路多。省际结合部是各级行政区权力的极限所在,其交通路线的建设难以进入各级政府的视野之中。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甘肃、宁夏、青海十省(市、区)边界地区有453条公路干线,其中只有269条通过边界,而184条在边界地区出现断头,占总数的40.6%。[13]
从我国省际结合部发展现状来看,既有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已达到一定经济水平的地区,如处于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有“金三角”之称的灵宝市,晋煤外运咽喉地带豫、晋交界处的济源市等;也有经济发展刚刚“启动”的地区,如2009年国务院提出的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2012年启动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扶贫攻坚区;更有尚未启动的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边缘性和封闭性,省际结合部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少数民族人口贫困范围面广,其生活质量总体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位于西南地区的滇藏川交接地带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理空间上重合分布的典型地带。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3月发布的“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截至2004年末,该地带有40个国家级贫困县,36.4平方公里面积的400.8万人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别占滇藏川交接地带63个县的63.7%和人口总数的51.9%。①
3.自然生态脆弱
省际结合部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诚然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历史基础与现阶段经济因素、体制等诸多原因,但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是制约省际结合部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我国省际结合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具有被替代概率大、恢复原状机会小、抗干扰能力弱等特性。如甘、青、川交界区域大部分属江河源区,是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大通河、黑水、白水的发源地,也是长江重要支流岷江、白龙江等河流的发源地,各江河干支流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本区的发展,而且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省际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明显恶化,主要问题有:森林资源过度砍伐,覆盖率迅速下降;草地资源过牧导致退化、沙化严重;过度开垦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江河上游的天然林及草地对水循环具有重要的调蓄功能。森林稀疏,植被破坏,导致其涵养水源,调节径流的能力减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旱洪灾害。这不仅对本区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对中下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省际结合部的人文生态
1.N不管地带,社会治安较差
“N不管”地带是一个什么样概念,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定义。我们把“N不管”地带定义为没人管的地方或事情,对事件、人和物没有责任人,无人为事件的结果负责。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事情没有政府机构去管理,甚至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任其发展就叫做“N不管”。“N”在此只是个虚数,正如“三不管”、“四不管”一样,不具体代表一个数目。
我国省际结合部大多处于“N不管”状态,社会治安较差。例如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重庆市秀山县洪安镇交界的地方曾经是远近闻名的“三不管”地带,由于边区三镇行政区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群众矛盾错综复杂。而这一地区插花地比较多,譬如贵州的土地延伸到湖南境内,而上面住的又是重庆人,类似的现象太多,这在客观上给三省市地方政府的管理带来了麻烦,加上边区三镇管理责任不明确,可管可不管的事就没人管,因此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不管”,群众矛盾错综复杂。20世纪90年代到2003年,边区三镇的群众因为土地、山林、道路、水源等纠纷不断,有的纠纷因行政管理不力而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发展为治安案件和恶性刑事案件。由于“三不管”,这一地区成了不法分子的避难所,涉毒、涉赌、涉枪、车匪路霸和偷盗扒窃活动猖獗,治安和刑事案件也一直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群众怨声载道。[14]
2.社会环境相对闭塞,社会系统自成一体
社会的本质就是在组织及组织网络的建构中得到体现的。[15]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民族,它有自身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民族与社会体系的联系,相反,只有将民族置于社会体系当中,才能更为正确的把握它的属性和特征,才能给我们分析民族现象及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位置提供准确的视角和定位。“从社会结构状态着眼,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要素:个体、群体、社会”。[16]它们三者相互区别又密切相连,构成一个动态的结构体系。在省际结合部,传统的乡村秩序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状态,对外经济交往比较单一,人员往来比较固定,外来文化影响有限,社会价值取向比较成熟,人的行为预期较明确,其社会体系自成一体,并起到对内整合的功能。例如,彝族所居住的横断山脉,山谷纵横,构成无数被高山阻隔的小区域,其间交通不便,实际上属于同一族类的许多小集团,分别各自有他们的自称,也被他族看成不同的族群单位。再如,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山寨,仅有8万多哈尼族人,他们散居于全县12个乡两个镇230个村寨,世代相沿形成了渗透于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哈尼族梯田文化,其农耕生产生活过程中用水的独特方式,对森林的深刻崇拜,以及节日庆典、人生礼仪、服饰、歌舞、文学均以梯田为核心,处处体现着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特点。
3.文化教育相对落后,价值观念变迁滞后于外部社会
价值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它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喜好什么、追求什么,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省际结合部历史上由于远离“中心”主流文化而严重封闭,与外界极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辐射和浸润。现实中依然封闭的人文环境,使其文化结构具有严重的封闭性和传统的相对完整性。由于生产力、经济水平的低下,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使边疆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现代意识发育迟缓,民族素质不能得到有效提高,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理性因素,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知识——能力贫困。如川藏滇、湘鄂渝等省际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除赶集之外,一般较少与外界交流,一些老人一辈子未去过几十公里之外的中、小城市,儿童上小学前听不懂一句汉语,大多数村民不知道“小康社会”这个名词。文化的“边缘”定势,使省际结合部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仍旧保持着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民族文化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机制,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他们发展能力的提升。
4.崇尚民间权威,家长制遗风犹存
省际结合部因自然地理条件和行政的板块体制的限制,大多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人的活动基本上缩小在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聚落范围。由于远离国家政治权威,处于行政管理盲区,使得当地的社会秩序不能以社会公认的标准得到正常建立,故而更加崇尚民间权威,社会组织结构中有着家长制和首领制的遗风。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多种社会权威,如属于传统权威的家族权威、道德权威、宗教权威等等,当然,也有政府权威。新中国以前,我国的民族传统社会体系中存在着寨老制、头人制、石牌制、山官制、土司制等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老人统治之外,在省际结合部村寨等各级地域组织中,我国一些民族还普遍采用公众大会的均衡法则。[17]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阶段,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权威逐渐停止了活动。国家政权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中,生产队、村委会等代替了过去的传统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恢复了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习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某些地区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传统权威人物也部分恢复了其在村寨生活中的影响能力,例如在贵州的苗、侗等民族聚居区,寨老又逐渐在村寨生活中发挥作用。[18]应当看到的是,以上的这些现象并不表明寨老、宗族首领、宗教人物等传统社会权威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因素的限制,省际结合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仍有相当部分的村寨处于贫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工作很难给人们带来实惠,其影响和控制力就非常微弱,人们更加尊崇的是村寨中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乡村精英,而不是村里的干部。因此,如何才能解决传统权威影响力淡化和村委会、党支部对村寨控制力不足带来的村寨社会控制问题,引导这些传统社会权威在当代省际结合部现代化建设社会中找到自己的适当地位,这是个值得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深思的问题。
①数据来源:《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