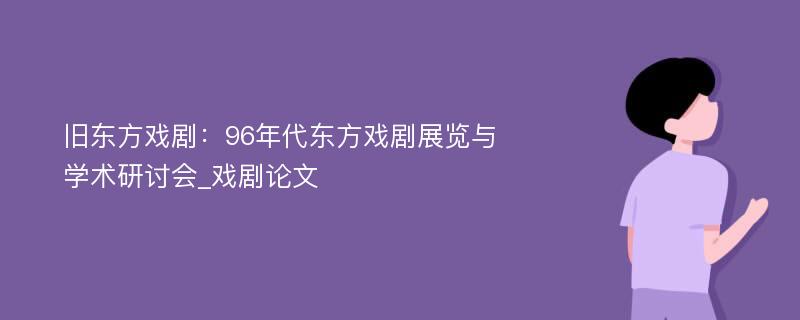
不老的东方戏剧——记’96东方戏剧展暨学术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不老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绿色的5月,春意盎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河北省文化厅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热情支持和赞助的’96东方戏剧展暨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拉开了帷幕。来自中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美国的中外学者和艺术家们相聚在这“天下第一庄”,共同演释、探讨东方戏剧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东方各国的戏剧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此次参加展演的二十多出剧目,制作精致,品种丰富,有日本的狂言、舞踊,印度的卡塔卡里,中国的昆曲、京剧、河北梆子、晋剧、评剧、豫剧、黄梅戏、湘剧……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直接展现了东方戏剧的独特神韵和魅力。
开幕式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献演的是古希腊悲剧《美狄亚》。《美》剧巧妙地引入了古希腊的歌队,那时而超然的叙述、评价,时而变成群众角色和各种道具的造型,别开生面,令人震撼,亦使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剧在演出样式方面的融合与相通。
尤具中国传统戏曲魅力的是三台折子戏专场。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演出的《山西风》、《杀楼》、《凤台关》、《小宴》、《金水桥》,亦文亦武,亦庄亦谐,那激越委婉、热烈豪放的梆子腔,那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翎子、帽翅、髯口、甩发、水袖、稍子等特技,尽展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技艺风采。
给我们带来远古气息的是印度卡塔卡里国际中心的巴拉克里希南先生和什里那特姆先生为我们表演的卡塔卡里。卡塔卡里是印度的古典舞剧,源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印度史诗的剧目明显地存留着印度古老梵剧的遗绪,表现浪漫、幽默、痛苦、勇敢、恐惧、讨厌、吃惊、安静等情感、情绪的面部表情、眼神和手势,弥漫着鲜明的程式化规范和浓郁的宗教色彩。
使我们耳目一新的另一台异国戏剧是日本和泉流派狂言剧团演出的日本狂言剧。“狂言”一词据说源于汉语的“狂言绮语”,意为过分夸大的言辞,用它来作为一种文艺样式的名称,说明它具有诙谐逗趣的特点,它的语言全是通俗的白话,专门表现富有喜剧色彩的生活片断。此次我们观赏的《附子》、《盆景》、《棒缚》这三出戏,最有代表性的是《棒缚》。剧情大意是:酒店伙计太郎和次郎总是在主人一出门就偷酒喝,今天主人心生一计,把太郎的两手缚在他肩上的棒上,次郎见状大笑,也被主人将其双手缚在身后,主人吩咐二人看家,安心出门去了,谁知二人却克服身体不自由的困难又开始喝酒,恰被归来的主人看到:三人相视目瞪口呆。这出戏通俗而滑稽,展现了五百年前日本下层平民的智慧。表演上除保留一些基本的程式化规范外,以生活性动作为主,这使得不懂日语的中国观众也不时为演员的动作所感染,不时开怀大笑。由此使我联想到狂言剧这种通俗性、娱乐性、滑稽性和讽刺性与我国唐代参军戏、宋代滑稽杂剧的相似与相通,亦与我国当代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喜剧小品接近。人们在一天的辛勤工作之余,坐在剧场笑看市井俚俗的人生百态,未尝不是一件赏心乐事。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即是狂言剧具有旺盛生命力而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同时,日本话剧人社带来的若柳派古典舞蹈《花篮》,则以端丽、柔和的艺术风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三出压轴的大戏反映了中国戏曲的新风貌、新活力。河南省小皇后豫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风雨行宫》,是一出揭示皇权扭曲人性的大悲剧,将河南梆子激昂慷慨、委婉跌宕的神韵风彩挥洒尽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红楼梦》不同于以往的《红楼梦》,它更注重作品内在文化意蕴和深邃的时代精神的显现。湖南省湘剧院演出的《白兔记》是长沙湘剧高腔四大名剧之一。改编后的《白兔记》以“打猎”、“回书”为核心,加强了李三娘和咬脐郎的戏,通过情意殷殷的亲情描写而达到互谅互解、合家团圆的结局,全剧演得自然成韵,明白晓畅,真切激昂,生动感人,既展现了传统的道德美,又显示了湘剧高腔的古朴美。
展演只是手段,研讨才是目的,对东方戏剧艺术的学术研讨是此次盛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来自日本、印度、新加坡、美国等国的20多位代表和来自中国的40多位代表,在他们的49篇论文和一系列研讨活动中,围绕着东方戏剧这一内涵丰富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在对东方戏剧历史渊源的探讨中,许多专家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观点,进行了深层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廖奔先生“佛缘东向”的观点显示出了研究者的开阔视野。他认为,根据文化征候进行区分可以看到,印度梵剧文化随着佛教的东渐,在东方造成了两个受其影响的戏剧文化圈,一个是与印度接壤或临水、隶属于印度文化直接传播圈的东南亚诸国,一个是由中国西域导入,经中国文化吐纳氤氲后发散的文化圈,包括朝鲜、日本等。东南亚诸国不仅戏剧题材打有深刻的印度胎痕,在艺术风范上也与梵剧血脉暗通,其舞剧中的舞姿多以手部与臂部繁杂细微的运动程式为主要手段,随时传递出印度戏剧经典《舞论》美学理想的神韵。而中国接受的印度佛教文化则为中国高度发展了的既有文明所过滤,因而中国对梵剧因素的接受也经过了筛选与折射。至于日本经由中国二级输送的佛教文化,已经着染了中国的鲜明特色,而日本戏剧所承接的大唐文化渗透,更是直接由中土的歌舞散乐而来。
讨论中,一些代表对传统戏剧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质疑。著名戏曲理论家曲六乙、流沙等认为,说唱叙述性是东方戏剧的普遍规律,无论是日本的能乐,还是印尼的哇影戏,无论是西藏的八大藏剧,还是傣族的对戏,均是说唱本的叙述体。戏曲就是戏加曲,可以说唱,可以搬演。中国传统戏剧应该包括词话体。古代民间艺人的剧本就从来不讲对话,他们记录的永远是唱词,但他们可以分得清哪里可以有白和动作。而中国从“五四”开始把叙事体和代言体作为戏曲与非戏曲的分野显然是过分武断。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黄竹三亦提出了“泛戏剧形态”的概念,它包括以歌舞表演为主、以假面为主、以说白为主的几种形态,“泛戏剧形态”在戏曲形成之前已长期存在,从整体上导致了中国戏曲的形成,并决定一系列特点,而且在戏曲形成并繁荣后,泛戏剧形态部分亦融入成熟戏曲。因此,将这一形态作为一个整体,去寻找这个“板块”同戏曲之间的渊源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在对东方戏剧的界定上应划一个模糊定义,而叙事、代言亦应该有一个宽泛的地带。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东方戏剧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历史与文化的交合作用将世界戏剧定型为东西两大基本范畴,二者具有不同的传统渊源和艺术发展轨迹,因而亦形成不同的形式规则与美学风范。通过比较戏剧的研究,大家对东方戏剧的性格特质基本取得了共识,认为东方戏剧是一种“明确肯定假定性”的戏剧,它具有舞台手段的综合性,表现技巧的程式性,舞台性格的演员中心性,角色身份的随意转换性,舞台场景的线性流动性,舞台表现的虚实相生性等共同特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苏国荣先生以《宇宙之美人》命题,浪漫而富有哲理地讲述了东方戏剧“一心儿爱好的在天然”的审美形态,与自然相随、游动自如的“飞行思维”,“万物与我为一”的“太一”性程式体系,赞美这种美学品格具有浩瀚的空间意识,充满了宇宙的生命精神。
东方戏剧这些共性特征是对应于西方戏剧的,但由于东方各国人文景观、地域风貌的不同,它的内部仍然具有广泛歧异的内涵构成。例如,印度的卡塔卡里,受其佛教的贯注,其戏剧体验带有浓郁的宗教情绪性,表演技巧上尤擅长以目传情,原始而古朴。日本狂言,因受日本文化影响,其表演气度不仅带有浓重的“武士”风范,而且做表上还具有较大的写实成分。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各地区各岛屿的历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背景基本上相同,这种统一的大文化生态环境决定了能乐、歌舞伎等演出主体和演出形态基本上是单一和完整的戏剧样式,这同中国这种多民族结构、多文化背景而衍生的多形态、多流派的中国戏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分析东方戏剧特质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芝风女士的《初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刘正维教授的《中国戏曲音乐形态的民族性》,日本大学原一平教授的《农村歌舞伎舞台中的演技表现》,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先生的《泰国孔剧》,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殿祺先生的《中国脸谱与日本脸谱》等,从戏剧的音乐、表演、舞台、化妆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各有见地。
代表们不仅对东方戏剧的历史面貌和文化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东方戏剧生存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东方各国传统戏剧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程度不同地呈现出萎缩、困顿的局面,如何保存和发展,如何赢得更多的现代观众,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金芝先生的《戏在变中生》谈的是戏剧的变革问题,他认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前两者虽早生,但就舞台生命而言,亦早逝。中国戏曲在其生命长河中,经险渡危,兴衰更替,不仅始终活在舞台,还繁衍成一个庞大的艺术家族,时至今日,还不断有人咒骂它“该死”、“早衰”、“美死”,但它虽然活得艰难,还是活得很精神。这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生态现象:变而不灭。日本松竹演剧部冈崎哲也先生在《作为现代演剧的日本歌舞伎》中谈及的“新歌舞伎”、“西洋歌舞伎”对西方写实性的借鉴,传统演技和现代舞台结构的融合等议题,也使我们看到了日本戏剧变革的轨迹。再如,江苏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汪人元在《戏曲音乐的现代转换》中涉及的“戏曲音乐应由民间性向专业性转换”,山东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谭源材在《中国戏曲学的发展与戏曲现代化》中强调的要加强对“戏曲社会学”、“戏曲剧目生产学”、“戏曲管理学”、“戏曲教育学”的建设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变革举措。在议论“变革”的同时,大家也提出了“不变”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民坚持认为,改革中有些东西决不能变,那就是程式性、节奏性、剧种个性、声腔多样性、语言与音乐关系等等,变了,也就失去了自我。
在保留传统戏剧文化上大家希望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吴书荫说,日本狂言大约还处于中国戏曲的宋金杂剧阶段,他们的确用了三百年前的“文语”,现代人也听不懂,能留传至今,与经济的有力支持有关。汕头大学教授隗芾结合潮汕地区海洋文化特点,谈到了戏曲的商品属性,他提出要利用广场戏的商业性和民俗性恢复戏剧市场,要还戏于民。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呼吁应成立两种剧团,一是实验型剧团,一是古典国家剧团。国家应有计划地集中优势精力把古典精品搬上舞台,不要让所有的剧团都去为“吃饭”竞争。艺术不能成为纯粹的商品。同时,汉城先生对东方戏剧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我们不要枉自菲薄,我们可以借鉴,但要按照自己的规律改造。中国戏曲的现代戏已趋向成熟。现在到了不是西方主宰世界的时代了,世界戏剧没有东方就不可能发展,未来可能出现世界性的戏剧,亦可能出现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特色的中国戏剧。
在这次交流活动中,我们感受到了各国戏剧工作者对本民族戏剧艺术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感受到了他们为戏剧艺术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由此我们增强了这样的信念:即在东方各国戏剧工作者及各方面人士的努力下,东方戏剧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将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彩,东方戏剧的创新精神也将为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不断增添新的财富。
奋进吧,不老的东方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