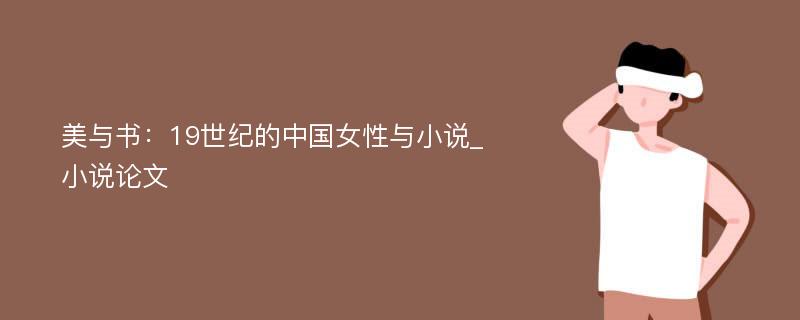
佳丽与书籍:19世纪中国女性与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佳丽论文,中国论文,书籍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1911年清朝覆灭前,中国女性与小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弹词不能不提,但我更关注的是,当时的女性是否阅读或参与了章回小说的写作。这里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她们与之完全没有关系;第二种情况,她们阅读白话小说,但并不参与写作;第三种情况,她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参与创作,不过她们总是设法掩盖这一事实。无论是哪种情况,其中的缘由都与白话小说按古训难登大雅之堂、作者出身鱼龙混杂、小说质量良莠不齐有关,那些遵守闺阁礼数的佳丽们当然不愿被这种文体玷污自己的高贵声誉。 虽然,在中华帝国时代的晚期,女性读写能力和创作的发展,似乎并不是稳步推进的,但明清之际还是出现了三次显而易见的高潮:一是晚明前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一次是晚清。 高潮之间便是低谷。前清之后,保守势力并不鼓励女性从事文学活动。17世纪中期虽然有如王端淑(1621~?)或黄媛介(1618~1685)这样的知名女诗人,与本家以外的女性有很多的诗歌唱和,当然也有与男性友人及其支持者唱和的,但是在18世纪有诗歌传世的女性,则主要是与家庭内部成员发生通信往来。当时大约有两类女性:一是只与家人有诗歌唱和的,再是也与男教师和家庭以外的女性朋友有书信往来的。她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不过在袁枚(1716~1798)和陈文述(1775~1845)的推动下,女性诗歌创作又回归到先前可以与家庭以外人士交流的趋势上。但这一变化却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而再次放缓,农民起义造成巨大破坏,交通、通讯受到阻碍,出版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清朝末年,革新者们接触女性,并鼓动起新一波的女性创作。但是,此时女性的言说方式已发生根本改变,报刊等新兴出版方式的出现,大大削弱了旧体诗歌和旧有联络方式的重要性。 (一) 本文重点谈三次高潮中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经由袁枚和陈文述的讲授和他们的率先支持与带动,其他许多男教师和女性也参与其中。但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极为不同: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袁枚和陈文述率先建构起文学交往网络,不过后续发展并非完全依赖他们。一些女作家开始有自己的师生关系与其他人际关系。她们或得到老师的支持,或与其他女性友人结交,这与晚明前清时极为类似。这些交往有时发端于师生关系,即使其中一方脱离了原来的家庭,这种交往也会延续终身。一般来说,女性作家往往可能通过男教师结识其他女性;也可能经由诗集的付梓刊印,女诗人们的父亲、弟兄或者丈夫通常会将新读物带给各自的女儿、姐妹或妻子。第一和第二时期的差异还与通讯尤其是邮递方式的进步有关。比如,杭州和北京之间的文学女性有着持续稳固的联系。这与17世纪大不相同,那时不同城市的才女大约会不时听说对方的名声,或有某位好心人让她们见上一面,但一旦说再见,那就是永别。但到了19世纪,情况就没有这么严重了。 同时,1792年《红楼梦》的刊行问世,犹如一针强心剂,极大缩短了女性与小说的距离。这样的例子很多,女性常借助于诗词回应《红楼梦》,当然,也有一些通过古文进行的。这样的回应,多来自江南地区的女性,也有一些来自广东、湖南地区,以及满族的贵族群体。例如金逸的诗。金逸是袁枚和钱守璞的弟子,钱又是陈文述的学生。又如熊琏的词,远远早于袁枚弟子们的回应。再如李佩金的词,她是陈文述儿媳王端的女友。此外,还有陈文述弟子周绮的古文等。《红楼梦》中有关结社赛诗活动的描写,很好地佐证了19世纪此类活动的发生。其中最好的例子,是一个女子(香菱)被排斥在此类诗会之外的细节。 但明末清初的女性多不会通过写诗来评价白话小说,这与第二点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对比。然而,当时并非每位女性都完全认同《红楼梦》,有些人甚至是反感小说中那种“女子多才必薄命”的模式。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论述至此,不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18世纪末的女性文化是否存在某些因素,促成了《红楼梦》的诞生?我们作此推测,是因为与此同时弹词《再生缘》的问世——这种两部作品平行诞生的现象,恰恰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还会关注19世纪早期的一些优秀女性,试图了解小说如何进入她们的生活。下述的四位都有作品问世,每一位都在各自的交往圈中颇有影响。有的是因弹词闻名,有的则与章回小说相关。这四位女性,让当时的女士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生动有趣且励志的小说作品。第一位是侯芝(1764~1829)。侯芝虽非出自袁枚或陈文述的门下,但以诗赋扬名于世,并以举止得体娴雅著称,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她在弹词上的成就也很高。弹词通常被视为女性独有的小说体裁,从18世纪末《再生缘》开始,这一艺术形式就在女性中流行,而侯芝可算是弹词创作的一位领军人物。关于她的弹词的影响和传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她声称自己的弹词作品都是被书商挑选看中的。第二,她还声称自己的作品受到几位名媛密友的认同,并将其称赞自己作品的诗歌随书一起刊印。比如当时的名媛骆绮兰和孙云凤,都曾对候芝的弹词作品《锦上花》(1813)大加推崇。 另一位是梁德绳(1771~1847)。她与侯芝一样是位诗人,并以贤德著称,可能也跟书商有过往来。她续补了《再生缘》的结尾,文笔远不如陈端生的原作,若今天读来,肯定会让不少评论家失望。不过尽管如此,她的续作还是很符合当时追求贤德上层女性的口味,读者依然可观。 第三位是王端(1793~1839)。她是梁德绳的外甥女,被梁收养,后又做了陈文述的儿媳妇,可算是同时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并以明诗研究闻名于世。在我们讨论的四位女性中,她是第一位与白话小说而非弹词有关联的女性作家。这种关联或许涵盖了她对《红楼梦》的兴趣,至少她的几位女友都写了与《红楼梦》有关的文字,可惜她自己的文字却没有存留下来。其小说《元明逸史》的诞生本身就具有传奇性。据说该书在交给书商前,曾被她亲手毁掉,是其公公陈文述让世人知道了这本书。不论这本书是小说也好,是通俗史也罢,都表明了女性尝试写作的强烈意愿,以及她们那种莫名的内心压抑。 第四位是恽珠(1771~1833)。她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于1831年问世,是女性诗歌选编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她也因而名闻天下。这部诗集体现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女性的识文断字和渊博的学识与其贤妻良母的身份相辅相成。当时很多人笃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看,恽珠自己是不写小说的,但她写了两组诗来品评《红楼梦》。恰好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是她儿子的好友。因此,这些诗得以出现在高鹗作序的诗集中。1814年《红香馆诗草》刊印问世,其实是恽珠的儿子在未经母亲允许的情况下出版的。这两组诗中一组应和了《红楼梦》中的四首菊花题咏诗,另一组应和了《后红楼梦》(按,《红楼梦》的第一部续作)的四首兰社诗歌。如果不是儿子偷偷将这些诗拿去出版,恽珠的这些作品也不可能流传于世。 因此,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女性与章回小说的关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有了重要的区别。首先,在袁枚和陈文述的倡导下,女性与家庭外成员交往和诗歌应和的模式再次实现了超越,长距离的交往得以延续。其次,重复一下,《红楼梦》在文学舞台上的出现,吸引并激励女诗人从事创作,这种现象是其他小说从未引发的,尽管不少读者并不喜欢小说“红颜薄命”的悲观模式。第三,假如将注意力转移到书商,他们似乎更关注怎样收买和打动弹词潜在女读者的芳心,为此不惜下大力气招募像侯芝和梁德绳这样的名媛作家。这条线索表明当时的女性读者在不断增加,而“贤德女性”是一个重要卖点。女性的认可也说明了小说对她们的吸引力,这种认可可以在1828年弹词的出版和1832年《镜花缘》的出版上体现出来。比如说,钱守璞既评判过《红楼梦》也品评过《镜花缘》,就说明了小说的魅力。第四,这一时期,弹词出现了,逐渐承担起“女性小说”的角色。这一新浪潮大概始于《再生缘》,其创作年代大约和《红楼梦》同一时期。第五,其他类型的女性文学如《国朝闺秀正始集》出版。17世纪虽然也有类似的诗集,但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强调女性贤德和女性学识并行不悖的诗集。与17世纪强调女性才华的同类作品有所不同,恽珠的诗集试图表明,女性如有良好的学养,不仅不会有害于社会,而且还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她为诗集作序,也得到了诸如王端这样社会名媛的认同与应和。第六,像王端这样成就突出的女作家已经显露出对白话小说或者通俗史的创作兴趣,但是她始终没有勇气将其作品出版。 总之,到1830年,女性和小说,尤其是与弹词、白话小说之间的联系已经比17世纪大为接近。小说有恰当的道德立场(弹词通常这样),人们也愿意购买、阅读,就如其他文学作品《正始集》,符合相似的道德标准。《红楼梦》对于读者的魅力并非是道德性的,《红楼梦》抛出了“红颜薄命”的质疑,引起了女性诗人的关注,并获得了很多女性的同情(虽非全部)。 (二) 接着讨论如王端这样的女性小说家,不过参照的中心主要是《红楼梦》的系列续作。清末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仅借用了《红楼梦》的一些人物,却大大改变了主题。如果除去这样的续作,共有十二部作品列入在内,最后一部肯定是女性的作品。该书作者顾春又名顾太清(1799~1877),也是一位词人、剧作家。其《红楼梦影》大约成书于1861年,但直到1877年才得以刊行。顾春在北京的出版商聚珍堂,一向出版汉满双语书籍,不过此时正开始推出有趣的汉文小说。聚珍堂出版了几本与《红楼梦》有关的文本,其中还包括全本《红楼梦》(1876)、长达三十章的《续红楼梦》(1881),还有与《红楼梦》相关的《儿女英雄传》(1878)。比较稳妥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聚珍堂,《红楼梦影》不大可能出版。另外一方面,该小说在完成后过了很久才出版,这说明顾春或她的家人可能并不想顾在世时出版。无论是何种情况,出版商没有宣扬这本续作的作者是女性,而且直到1980年顾春的一些诗歌在日本发现,作者的身份、性别才为当代学者所了解。这些诗作表明,《红楼梦影》的作者是顾春,为其作序的是她的朋友、诗人和文集编撰者沈善宝(1808~1862)。两位女性都用了笔名,这与通常的做法很不一样。这些非同寻常的笔名和出版日期,暗示出顾春不无担心声名受到白话小说的牵累,并试图掩盖其中的关联。顾春的一首诗后附有一个小引:“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姐年尽七十,如何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这段附注说明,顾太清之所以能开展非同寻常的小说创作,闺友的支持和催促是非常重要的。 顾春和沈善宝的友情颇耐人寻味。顾春出生于满族贵族,成年后住在北京,而沈善宝则是杭州人。沈早年家贫,后通过不错的婚配,在丈夫高中进士后,移居北京,得以与顾春相识。顾春和沈善宝互赠大量诗词,这种情谊对于丈夫去世后的顾春尤其重要。她们属于更大的女性诗人群体,这些女诗人常到京城游历,不过即使离开京城回到杭州,仍然保持诗友通信,这其中还有梁德绳的女儿。沈善宝极善于鼓励其他女性作家,显然她的支持对于顾春甚为关键。作为一名女作家,她并不完全认同《红楼梦》。1836年,她曾写诗道:“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其实,她对《镜花缘》还是持积极肯定的看法,有所谓“羡娥眉,有志俱伸”的评语。 大概另一位影响顾春尝试小说创作的是她的丈夫——满族皇子奕绘(1799~1838)。据传,太清虽为奕绘侧室,但两人在文学上相互唱和,是美满的一对。奕绘大概有8种《红楼梦》的续作。虽然奕绘生前未能阅读《红楼梦影》的成书,但是他所藏的续作,却激发了顾春续写《红楼》的兴趣。《红楼梦影》内容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其他续作不同,该作并未复活原作的人物,挽救如过眼云烟的宝黛之情,而是颂扬女性的才华。此外,伴随情节的发展,婴孩的诞生带来了希望,暗示贾家会躲过覆灭的劫难,而湘云之女和宝钗之子最终成婚是这一幸福远景计划的中心。小说中不乏庆典和诗会的场景,其中甚至有顾春在别处的一首诗。除了宝玉最终与心仪的女子失去联系,小说整体上沉浸在欢快的氛围中。率先认定顾春《红楼梦影》作者身份的是学者赵伯陶,在他看来,小说也暗藏着一丝焦虑的弦外之音,隐含着顾春习惯的上层贵族生活并不能长久。 这本小说有好几处令人着迷。首先,它折射出顾春的兴趣爱好。顾显然精通音律,小说中有大量的音乐场景描写,而歌妓是其中一两处的中心。另一有趣之处是其中一处园林的一块石头。正如张菊玲所指,这块石头的现实原型在北大校园之外,顾春可能描写了她临近北京的住所。再者,与顾的诗歌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北京白话方言的利用。此外,小说描写了满族文化在某些场合的细节,虽不能完全称这部小说为自传体,但它的确借用了顾春的生活经历和《红楼梦》已存的结构。此外,小说的“女性”视角也颇为有趣。顾春显然喜欢孩子,拥有丰富的生育分娩知识,这可不是《红楼梦》的特点。而且她对于传统的闺秀文化也了然于胸,小说的一个人物(邢岫烟)割肉孝敬婆婆,这也是《红楼梦》中没有的举动。第三,她对于外部世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贾政奔赴边疆剿灭来敌时,她的细节描述可谓寥寥。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不难想象顾春对于家居生活的兴趣和对男性世界的漠然。不过小说并非自悯自怜,其中的人物积极生活,也找不到一个成天垂泪的黛玉似的人物。恰恰相反,有些角色如史湘云勇敢地面对困境,非常让人敬佩。 也许大家会问:顾春为何写了一部白话小说而非弹词?笔者认为:首先,弹词是一种南方体裁,顾春则是北方人。其次,她显然对北京白话兴趣浓厚,而弹词则是在韵文和非韵文之间跳跃,二者不见得相容。再次,与侯芝相比,顾春不见得是位道德作家。她或许赞同孝顺,认可割肉事亲;但也认可歌妓的优点,这是侯芝的卫道立场很难接受的。相比而言,顾春可能更为温和,她的一些看法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侯芝。因此,如果顾春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续写《红楼梦》对她而言肯定是较为合适的路径。这种情况也说明,女性作家并不满足于弹词是女性唯一的叙事体裁的现状。作为这本小说的女性作者,顾春尤其让我想到下面一个问题,即在《红楼梦》的一系列续作中,是否也有其他的女性创作。 在《红楼梦》的多种续作中,的确有一位作者可能是女性,但此书未能传世,即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或成书于1844年。与王端的《元明逸史》一样,这部女性小说后来或被人为销毁,但因资料太少也不能完全肯定。笔者重点谈除《红楼梦影》以外的11部较完整的现存续作。这其中是否有女性作者呢?如有,又是哪些呢?这11部续作中,已知有些作品是男作家写的,还有几部大肆渲染色情,很难想象是出自高贵端庄的女性之手。这样,剩下的几部或许应该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了,不过仍无确凿的证据。如果不细心研究,《红楼梦》的续作中真没有女作家的身影。 对这些材料还有另一种解读路径。退一步说,即使已知作者是男性,那么《红楼梦》的续作是否体现了女性的影响呢?这可以从两个方向跟进,即有两个方向的回答:一是尚武的,再是居家的。首先看尚武的方向。传统女性作家都钦佩晚明女英雄秦良玉,闺秀文化接受对巾帼英雄的崇拜,即使这些女子都在家里活动。《红楼复梦》是《红楼梦》最初三本续作中的一种,作者姓陈字少海,于1799年付梓刊印。陈的妹妹陈诗雯为其校订作序,这显示了女性才华的渗入。虽然挑头的肯定是男性,但女性也肯定担当着部分作者的角色。就妹妹的序言看,男性读者注意的是小说的哲理超越,而才女们则悲悼女性的不幸命运。如云:“普天才子,作如是之达观;绝世佳人,唤奈何于幽恨。爱由心造,缘岂天悭。斯则情之所钟,即亦梦何妨续。”这部小说与其说具哲理性,不如说更以行动为先导。妹妹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特别之处,在最后十二章作者的身份可能有所改变,宝钗变身为一员女将,率领军队横扫在岭南肆虐的劫匪,这与其他章节的宝钗有天壤之别。这个插曲临近结尾,或许女性的遭遇引起妹妹的极度不满,作者相应地作了某些修改。不管这部分是不是陈少海的妹妹所作,或者提议增加这一情节,它都冲淡了像黛玉这样悲惨角色引发的失望。宝钗一旦成功结束英雄征程,又恢复了她贤妻良母的身份,但她却曾经是男女军团的威猛统帅! 有趣的是,妹妹的这种不满,倒应和了沈善宝1836年的诗作。今天《红楼梦》的正统学者无疑更喜欢原作而非《红楼复梦》,也会嘲笑领军打仗的宝钗属于胡编乱造。但是有证据说明,《红楼梦》里“红颜薄命”主题已令很多女性读者失望,所以,《红楼复梦》才试图让一位才女更积极有为。同样地,顾春的《红楼梦影》也没对才女们施舍怜悯。大家是否发现,佳丽们虽然欣赏《红楼梦》这本小说,但又以某种方式拒斥了曹雪芹“红颜薄命”的主题。《红楼复梦》的出现是否印证了上述抵抗和拒斥的一定存在呢?陈少海让妹妹校订和写序,至少说明他对女性文学才能的尊重。 要讨论的第二本续作是逍遥子的《后红楼梦》,这是《红楼梦》的第一本续作,1796年就已存在,《后红楼梦》在情节上延续了《红楼梦》。而同年仲振奎(1749~1811)开始撰写他的《红楼梦传奇》。恽珠就读过《后红楼梦》并写诗应和,这些前文已作讨论。这本“续补”与《红楼复梦》一样,情节严重偏离原作,林黛玉竟成了一位健康干练、正儿八经的家庭主妇。在她有力的掌控下,宝玉幡然悔悟,参加科举考试且高中进士,成熟地履行各种责任。为了这种转变,小说先是让黛玉复活,让她找到一位失散多年的表兄,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她因而获得了原作中没有的自信、地位和沉着镇定。宝玉拼命讨好黛玉,却未真正得到她的青睐。贾政继续指责宝玉,成为黛玉最强有力的同盟者等等。 至此,虽有恽珠的诗作可作旁证,但是我们仍没有证据能证明小说作者与女性作家有什么联系。而这种关联,或许可以经由仲振奎的两个妹妹仲振宜和仲振宣——这两位女性作家——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后红楼梦》的作者极可能是男性,但是小说似乎更契合上层女性的口味。这本小说中,黛玉的“积极入世”,并非是领军打仗,而是积极整肃家务,她因而摆脱了原作的悲剧性命运。小说描写得也很清楚,女性主人公被想象成艺术评论家,黛玉和宝钗在结尾处交换着对《红楼梦》的看法,并和曹雪芹讨论小说的精巧之处。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与《红楼复梦》中主动积极的宝钗、沈善宝的诗歌和《红楼梦影》中女性对幸福命运的期许是一致的。小说是以曹雪芹母亲的序言开始,这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评论的重要性。 《后红楼梦》影响了其他几部续作,1814年的《红楼圆梦》和1820年的《补红楼梦》则讨论了这部小说。今天的读者会觉得这样的续补情节很荒唐,不过黛玉的积极角色却体现了对“红颜薄命”主题的一种反拨。小说同样认可:女性是值得尊敬的诗人、文学评论家,一定程度的女性才华是社会应当接受的,虽然《红楼梦》的续作没有《镜花缘》那样大胆激进。而且,与《红楼梦影》有些相似,《后红楼梦》似乎对女性化的生活面向,尤其是家政管理,颇感兴趣,而对于男性的职业则比较漠然。这暗示了女作家的参与,虽然作者就是男性。如果女性深入参与到小说写作中,她们又决心隐姓埋名,那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的问题,并作如下回答: 首先,17世纪女性并不开展小说方面的活动,19世纪有些女性评判《红楼梦》。整个19世纪,女性推崇《红楼梦》,但是有些女性排斥其“红颜必薄命”的观点,有些续作是为驳斥这种观点而作,也可能是家中兄弟或亲戚为其姐妹及亲戚所作,或者仅是因为作者非常了解女性的心理和愿望。不过到了19世纪末,顾春切切实实进入了作者的角色。不过在此之前,女性早就充当了小说、包括章回小说评论者的角色,这在第一部续作《后红楼梦》中就清晰地呈现,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最后一本顾春的《红楼梦》续作。 女性的抱负只要不与孝道相抵触,都会得到讴歌颂扬。只要女性从事着崇高的事业,巾帼女杰会被视作才女,一如《红楼复梦》中抗击强盗的宝钗。 当然,对于上述观点的过度强调,会产生对糟糕的文学作品,甚至是滑稽的文学作品的过分肯定。不过这种修订本身,有助于表达当时女性的反应。 如果19世纪确实存在我们鉴别的女性和小说的潮流,则还需要与晚清的“妇女小说”严格界别开来。首先,19世纪早期并未出现专门为女读者创作的大范围的自觉运动,也没有像《红楼梦影》那样公开作者的女性身份。这里讨论的续作包括《红楼梦影》在内,没有一本对于变革有任何兴趣。1904年,王妙如的《女狱花》出版,这可能是晚清最早由女性创作的小说。《红楼梦影》与之不同,并没有灌输民族概念,也未在世界范围内想象中国,没有任何西方影响的印迹。另一个不同是,19世纪的续作仍没有反满情绪。最后一点,《红楼梦影》和其他为其铺垫的续作都是自娱自乐,而非倡导某种变革。这些小说都是在《红楼梦》的联想范围内运转,而且多是基于传统闺秀文化的理念。当家庭或战场上出现坚强的女人时,这些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叛离了原作。但是这些小说似乎未对根本性变革寄托希望,如19世纪末渐起的西式教育和放脚运动。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本土发展,与晚清潮流并不连贯,随着清末反满话语占据上风,这种趋势中断了,最终被替代、被遗忘。虽然早期的发展起于家居内部,与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关系,但很可能为晚清事态发展有所铺垫,比如女性爱国便能从军,这样的关联与清末的状况没什么不同。 正如一开始所说,从现存的证据中很难觅回讨论的整个潜流。它的不可见是因为一种文化禁忌,导致女性和章回小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间隔区,这种文化潮流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走到尽头。标签:小说论文; 红楼梦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陈文述论文; 读书论文; 陈文论文; 镜花缘论文; 曹雪芹论文; 沈善宝论文; 诗歌论文; 红楼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