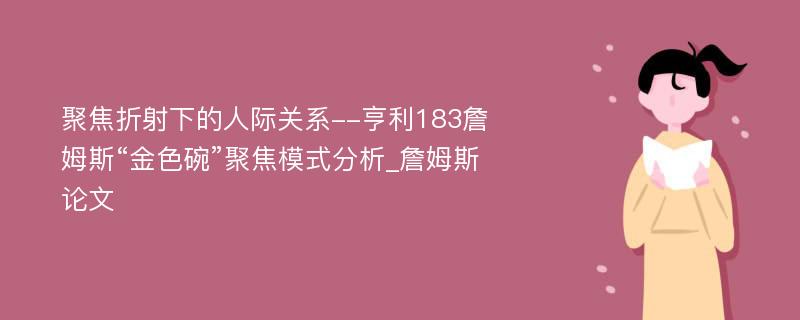
聚焦折射下的人际关系——亨利#183;詹姆斯《金碗》聚焦模式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亨利论文,人际关系论文,模式论文,金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金碗》是亨利·詹姆斯最后一部长篇巨著,从内容上看,小说呈一明一暗、一主一辅两条叙事脉络:明线/主线围绕维尔维父女二人的婚姻。女儿麦琪自幼丧母,与父亲亚当相依为伴,父女情深。在阿辛汉姆夫妇的撮合下,麦琪与意大利青年亚美利戈结婚。为了不使父亲感到寂寞,麦琪把自己当年的同学夏洛特作为婚姻对象介绍给父亲。隐含在婚姻主题之下的一条辅线是亚美利戈与夏洛特之间的恋情。通过阿辛汉姆夫妇间的对话,我们得知,夏洛特与亚美利戈曾深深相恋,只是因为贫困而未能结婚;她之所以嫁给亚当,除了摆脱窘迫的经济困境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接近亚美利戈。
批评家们从叙事分析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评论时,大都注意到了该小说在运用人物视点方面的独特技巧,通常都认为该小说只存在两个意识中心,即小说前半部分用亚美利戈作为意识中心,后半部分用麦琪作为意识中心。克罗克(Dorothea Krook)和塞尔斯(Sallie Sears)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克罗克说:“该小说中只有两个意识中心,亚美利戈是第一卷的意识中心,麦琪是第二卷的意识中心,这两个意识中心在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紧密相连”(注:Dorothea Krook,The Ordeal of Consciousness in Henry Ja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236.);塞尔斯认为该小说的聚焦模式是“两双眼睛注视着同一个事件”(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73.)。批评家们所关注的重点,用现代叙事学的术语表述,就是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观察故事事件?”(注:Ge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Ithi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186.)而实际上,只要读者能够直接通过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该人物的眼光就构成叙事视角。因此,在小说《金碗》里,内聚集人物还应该包括直接参与故事的亚当和夏洛特,以及主要以观察者身份出现、处于故事边缘地位的凡尼·阿辛汉姆夫妇。霍兰德(Laurence Holland)甚至认为,那位出售金碗的店主也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观察者,(注:Laurence Holland,The Experience of Vision:Essays On the Craft of Henry Jam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pp.345-346.)不过,由于本文主要探讨该小说中的三位人物(麦琪、夏洛特和亚美利戈)以及两个主要人物意识中心的意识形态,所以,本文仅限于讨论亚美利戈和麦琪的视角。
与詹姆斯运用单个意识中心刻画人物意识的作品相比(如《一位贵妇人的画像》、《专使》和《美国人》),《金碗》中多个人物意识中心使该小说在展示人物意识活动方面产生出一种多向度和立体感。可以说,从运用单个人物意识中心转为使用多个人物意识中心的转变,意味着詹姆斯的小说从描写事件对个人产生的心理意义转到了刻画个人在面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意识的交流和冲突。当然,詹姆斯的这一手法并不是在小说《金碗》里一蹴而就的。在这之前的两部作品,如《悲剧的缪斯》和《鸽翼》,都以一个以上的人物视点使故事世界中的人物关系呈现一种动态。不过,在人物视点的运用上,与这两部作品不同的是,《金碗》中的两个主要聚焦者亚美利戈和麦琪是一对形式上互为一体(夫妻关系)而实质上互相对立(守住秘密与发现秘密的意识争斗)的聚焦者。这样的两个聚焦人物为整个叙事作品带来了一种由矛盾和对立形成的张力。
不少批评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物意识中心在整部作品结构中的排列:两个主要聚焦人物,一前一后,显得既连贯又对称。但批评家们对于这两个聚焦人物表现出的不同意识形态却很少涉及,有的认为运用这两个意识中心“表示了詹姆斯在意识深层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注:Tony Tanner,London Magazine,1961.1,p.42.)也有的认为该技巧“符合詹姆斯艺术思维中的对称结构”;(注:J.A.Ward,The Search For Form: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Henty James's Fic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7,p.203.)还有的认为“是为了使小说呈开放式”(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73.)。这些评述自然各有道理,但总的来说,这些看似不同的结论大都与詹姆斯本人的解释大体吻合。詹姆斯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始终通过亚美利戈的眼光和意识观察故事事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则由麦琪完成这一功能。”(注:"Preface To The Golden Bowl",The Art of the Novel,Critical Prefaces by Henry James,ed.R.P.Blackmur,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4,p.329.)实际上,如果注意一下该故事中的一隐一明两条叙事线索,我们就不难发现:小说的前半部分以亚美利戈为意识中心,这既是为了描述他与麦琪结婚这一显性结构中的情节,也是为了表现他与夏洛特在婚后进一步发展的情人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亚美利戈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处于意识的中心,所以,他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主人公,而且在与夏洛特和麦琪两个人物的关系中还以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体出现;小说的后半部分以麦琪为意识中心人物,其主要目的在于表现她从被蒙在鼓里到逐渐明白夏洛特与亚美利戈之间真实关系的过程。但是,詹姆斯在作品形式上对两个人物视点的划分,只是解释了技巧在形式上的作用。而叙事视角作为构成故事的一部分和表现故事的手段,在表述人物关系时,远不像作品形式本身那样井然有序,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总是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让我们先通过亚美利戈的视角来观察他与夏洛特的关系。
一、亚美利戈与夏洛特
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模式中,当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被持续用作意识中心/内聚焦人物时,常常意味着与他/她有关的其他人物的视觉被排除在外;而当人物受到知觉限制的时候,该人物在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就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在《金碗》的前半部分,麦琪就处于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不利处境。但当小说在后半部分转用麦琪的视角和意识描述故事时,夏洛特与亚美利戈就处于被观察的地位,这种转换人物视角的手法虽然与詹姆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展现人物意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使利益相关的人物在观察与被观察的地位转换中呈现出与人物知觉、权力相关的地位变换。从阅读过程看,读者既能观察到意识中心人物的视觉内容,又能通过该人物的眼光对聚焦对象进行观察。而当聚焦对象转成聚焦者(人物意识中心)时,通过内聚焦人物的内省活动,我们又可以看到该人物的意识活动,由聚焦者变换引起读者的认同态度也是动态的:我们总是先通过一个聚焦人物的眼光观察另一个人物,而当原先被作为聚焦对象的人物转换成为聚焦者时,我们又通过他/她的眼光对原来的观察者进行反观察。单从转换聚焦人物眼光的技巧看,整个过程的确如塞尔斯所说的那样,在小说《金碗》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人物视点,这一现象使我们在阅读时无法与任何一方认同”。(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73.)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金碗》中,理应涉及四个人物主体意识的故事在前后两个部分里都只有一个意识中心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故事的前半部分还是在后半部分,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只能通过两个聚焦人物观察到夏洛特和亚当的意识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夏洛特和亚当自始至终都是被观察的对象,但是,相对于亚美利戈和麦琪两个意识中心而言,他俩的视点和意识无疑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而在聚焦范围中所占份额最少的是夏洛特。较持续地用夏洛特的视角进行描述的仅限于第一卷中的第14章和第18章,除此以外,只是零星地分布在对其他人物的描述中。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在亚美利戈还是在麦琪的聚焦中,夏洛特基本上都是被观察对象,我们对她的了解仅限于聚焦者对她外貌的观察;由于聚焦者强烈的主观性和观察者眼中渗透出的偏见,我们所见的观察者眼里的聚焦对象夏洛特,与其说是该对象本身的戏剧展现,倒不如说是聚焦者充满自身意识的眼光折射出来的形象。聚焦者的眼光就像是一面滤色镜,使聚焦对象蒙上了一层与观察者内心意识密切相关的情感和心理色彩。因此,读者所见到的聚焦对象实为聚焦者对于对象的主观描述。也就是说,用内聚焦模式展示人物内心意识使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形成最大限度的距离,从而实现由戏剧化带来的真实性。但由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被观察的人物的真实面貌,这种真实性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幻像。请看一段夏洛特刚出场时亚美利戈对她的观察:
看见她外套的袖子滑到手腕上,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那袖子里飘逸的双臂,是那么圆润,又是那么洁净、修长。他熟悉她那双细细的小手,他熟悉那手上的纤纤十指,还有那指甲的形状和颜色,他熟悉她转身时那异常优美的体态和身段,而他最熟悉的还是她那纤细而富有弹性的腰肢,那是花开正盛的花枝,好像长长的、鼓鼓的丝质钱包,里面装满了金币。这时她还没有转过身来,可他却好像已经在手心里把这一切都掂量了一下,甚至已经听到了那金币相碰的叮当声。(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36.)
这是一段典型的内聚焦模式描述,单从视觉方面看,聚焦者亚美利戈对于夏洛特的观察虽然仅限于她的服饰(外套袖子滑到了手腕上),但大量的“心理叙述”(Psychonarration)(注:Dorrit Cohn,Transparent Minds:Narrative Modes for Press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1.),尤其是重复出现的“他熟悉”(he knew that)的句子结构,不仅体现了故事外叙述者对于内聚焦人物心理意识的充分把握,还把重点从对聚焦对象外部的“客观”描述转向了聚焦对象在聚焦者眼里的意义转化:从叙述话语层面看,叙述者井然有序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叙述者与聚焦者分属于“说”和“看”两个不同实体,但两个比喻——“花开正盛的花枝”和“丝质钱包”——的运用,让我们看到观察眼光在观察想象的作用下,把观察对象转换为与观察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客观对应物。从眼前之人联想到想象之物的意识过程之所以形成连贯,主要原因来自聚焦者业已形成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物视角的功能不仅是我们观察故事事件的“窗口”,而且也是展示观察者本人内心、构成故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在分析詹姆斯小说反复强调的视觉意义时指出,聚焦者的观察过程是一个从视觉-预知觉(pre-cognition)到知觉,最终把视觉纳入自身的价值系统的过程。(注:Seymour Chatman,The Later Style of Henry James,Oxford:Blackwell,1972,pp.15-30.)查特曼所谓的“预知觉”阶段是指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沉思过程,它是观察者丰富意识形态的必要阶段,但并不“直接依赖于感官”。(注:Seymour Chatman,The Later Style of Henry James,Oxford:Blackwell,1972,pp.15.)也就是说,用于表现这一观察的动词虽然也指涉感官动作,例如“看到”,但重点却在于强调这一行为的结果在观察者意识中的主观反应。在上面提到的场景中,我们首先看到,当夏洛特出现在亚美利戈的视觉世界里时,她被转化为代表女性美丽的“花枝”;接着,当他对这种美丽进行“掂量”的时候,她又被“物化”(reified)为“丝质钱包”。从“人”到“物”再到金钱的意识转变过程,是一个眼光对观察对象从外观凝视(gaze)反射(reflexive)到观察者内心意识的内化(internalized)过程。两个比喻的并列使用暗示着存在于亚美利戈的意识形态里的一个思维等式:夏洛特=美女=金钱。这个等式包含着亚美利戈意识流程中的一个逻辑转换:如果A=B,B=C,那么,A=C。即:夏洛特
是美女,美女即金钱,那么夏洛特就是金钱。
从聚焦模式来看,亚美利戈眼光的主观性来自于他的内聚焦。也就是说,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和故事内的观察者,他的眼光是有限的、不可靠的。但这种对人物主观性的强调正好符合詹姆斯所要表现的心理现实主义:外部事件对于个体经验的影响和个人对于事件的价值判断。如果纯粹从知觉层面(perceptual facet)上讲,亚美利戈看到的仅仅是夏洛特“外套的袖子滑到了手腕上”,其余的“观察”基本上是通过聚焦者的想象(“他仿佛…”),而与聚焦者想象穿插进行的是聚焦者通过内省(introspective)展示的回忆(“他熟悉…”)。这一内省加回忆的手法使我们不仅了解亚美利戈与夏洛特之间亲密的过去,而且还暗示着亚美利戈在观察麦琪时也是受同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在上面引用的那段描述中,当亚美利戈的眼光落在夏洛特的手腕上,并且用他的想象之眼对夏洛特的双臂、双手、手指、腰肢进行细致“观察”时,叙述话语所要强调的是夏洛特在亚美利戈眼里十分突出的生理性别。这种眼光,加上亚美利戈强烈的金钱意识,使得夏洛特仿佛“被再次包装”,其最终目的是使女性“在男人之间进行交换”。(注:Luce Irigarar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New French Feminisms:An Anthology,ed.Marks and de Courtivron,Harvester,Wheatsheaf,1981,p.105.)在亚美利戈眼里,夏洛特仅仅是个待价而沽的尤物,而他之所以不能通过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婚姻——来拥有这个尤物,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但对于此时的他来说,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她进行观察、想象。
然而,当夏洛特终于嫁给了亚当,终于能接近亚美利戈时,她显得颇为主动的姿态着实让亚美利戈感到“骇然”。(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p.217.)请看下面一段描述:
尽管这位女子只是一晃就过去了,可是,王子,从他站的角度看,就在那一瞬间,已经认出了她是谁。这使他有好一会儿直楞楞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6.)
接着,我们得知,夏洛特的突然出现,使亚美利戈觉得她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鬼魅,他骇然地看着这个鬼魅,好像它随时都会扑过来”。(注:Henry James,The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6.)然而,他们只要一在一起,她就好像火箭霹雳,呼的一下就从形式窜到了内容,她站在那里看着他,毫不掩饰地问:“好了,亲爱的,下面我们干什么?”(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7.)
这是夏洛特在一个雨夜趁麦琪不在家时径直去找亚美利戈的情景。虽然我们站在亚美利戈的视点观察夏洛特,但由于叙述者首先对夏洛特进行了静态描述,然后再通过亚美利戈的眼光对她进行动态描述,所以,这一技巧造成的视觉效果是:亚美利戈无意中站在窗前,夏洛特闯入了他的视野。当我们把这一看似寻常的聚焦场景收入两者的关系中考虑时,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在亚美利戈的意识里,夏洛特像是有意闯入的一种破坏力量;原本在叙述层面呈主动地位的聚焦者在读者意识中反而成了一个被动者。这在逻辑上显得有悖常理,但却非常符合亚美利戈眼光背后的意识:在他与夏洛特的关系中,自己是个受到诱惑的被动者。
一般来说,聚焦分析通常关心的问题是“谁的眼光在观察”,但如果仅仅考虑这一问题,就很容易忽略聚焦者与聚焦对象之间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和关系。在上面这个例子中,虽然叙事话语在形式上要强调的是观察者的视觉内容,但同时也暗示着聚焦人物的眼光如何受到聚焦人物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左右。通过亚美利戈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亚美利戈对于夏洛特的主动欲望,但他却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值得同情的被诱惑者。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通过亚美利戈的视点看到的仅仅是亚美利戈眼里的夏洛特,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中,我们看到,夏洛特的欲望被外化为她的主动行为,由于叙述在表现这种主动行为时采用的聚焦位置是从亚美利戈的立场对她进行描写,用拉康的话来说,夏洛特的这种主动性则呈现出她“希望被喜欢的欲望”(the desireto be desired)。(注:Ja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New York:Norton,1988,p.276.)与夏洛特这种只能通过“被喜欢”来表述主体欲望的方式相比,亚美利戈实质上是个主动者。但由于我们只能站在亚美利戈的视角位置等待夏洛特闯入“镜头”,加上心理描写——“使他有好一会儿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语中运用的被动语态,使夏洛特在视觉效果上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诱惑者的形象。即便是在表现亚美利戈对于夏洛特的欲望时,聚焦所表现出的亚美利戈依然是个被诱惑者。请看第22章中的一段描写:
她那从灰色的旧窗户里朝他投来的久久的凝视,她那帽子的戴法、领结的颜色、凝固的笑容,似乎有某种东西使他猛醒,他突然意识到,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可以依赖她。大好时光,如怒放之花,何不信手将它摘来。(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61.)
在这一场景中,虽然夏洛特被描述成观察者,但是,叙事话语着重强调的则是亚美利戈对于夏洛特的注视的主观阐释。动词“摘”(pluck)虽然表示了亚美利戈的主动行为,但紧接其后的宾语——无生命的人称代词“它”(it),在使人联想到花朵的同时也使得亚美利戈的主动行为显得轻描淡写,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亚美利戈在他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所充当的主动和暴力角色。从亚美利戈突出夏洛特的女性身体到把她比作无生命的花朵,从装着金币的钱包到可以轻易采摘的花朵,这一心理运作正好对应于亚美利戈从一开始就视她为婚姻市场上供人挑选的被动者的意识。通过亚美利戈的眼睛,我们也可看到,夏洛特的期待——想在婚姻中寻找一份安定,又企图在与亚美利戈重修旧好的情爱中找回她丢失的女性主体——纯粹是一个幻想,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像一个物品从亚美利戈的怀抱重新转归由亚当收藏。
二、麦琪与亚美利戈
努恩(Fernr Nuhn)曾说,如果将《金碗》后半部分的故事从夏洛特的视点进行改 写,那么,麦琪的形象就会变成“可怕的恶婆娘”。(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92.)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两点:其一,作为在利益上相互对立的两位女性,麦琪与夏洛特,在形象方面也被塑造成一种对立;其二,麦琪作为小说后半部分的意识中心,由于其充分展示的意识,不仅使她在故事中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而且使得有关她的话语成为一个具有连贯意义的力量。小说的后半部分自始至终着眼于描述麦琪的视觉和意识进程,代表麦琪的斗争成为叙事中心。麦琪从小说前半部分被蒙在鼓里的处境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中心,其象征意义之一,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排斥他人话语的方式排除威胁自身权力的力量”。(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he Discourse onLanguage,Harper Colophon Books,Harper & Row,1972,p.216.)但是,颇具反讽色彩的是,我们看到,麦琪采用了一种被动的策略——沉默,这又使得原本作为对立形象的两位女性在本质上都从属于另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对立结构,即:男性=主动,女性=被动。
以往批评家们在评论麦琪这一聚焦人物时,也注意到了她为争取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如沃德(J.A.Ward)、塞尔斯、马西森(F.O.Matthiessen)和杜匹(F.W.Dupee)等。但他们常常认为,麦琪与亚美利戈的意识形成一种对抗,即,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总是通过亚美利戈观察麦琪;在后半部分,我们总是通过麦琪观察亚美利戈。但实际上,两个聚焦者在整个叙述结构空间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对等。全书共两卷42章,第一卷占24章,第二卷占18章。而第一卷并不是一直从亚美利戈的视点进行描述,例如第9章大部分是从麦琪的视点进行描述,其余均属于亚当的视点;而第14章和第18章基本上是夏洛特的视点。在小说的第二卷里,所有的章节基本上均从麦琪这的视角对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进行观察。但是,单凭麦琪在叙述空间中所占的相对优势,并不能说明麦琪在与亚美利戈的关系中处于一个具有同等权力象征的主体地位。一般来说,对一个内聚焦人物内在心理视域的延伸,常常会有效地影响读者对于该人物的了解和同情;而该人物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眼光,也会相应地干预读者对聚焦对象的判断。因此,塞尔斯认为,该小说中有“两双眼睛同时关注一个事件,使两个意识形成一种对立”,使读者“无法认同于其中的任何一方”,(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73.)依照塞尔斯的说法,亚美利戈与麦琪两个视点是一种互为对应的关系;在第一卷中,亚美利戈(聚焦者)观察麦琪(聚焦对象);在第二卷中,麦琪(聚焦者)观察亚美利戈(聚焦对象)。而实际上,在第一卷亚美利戈聚焦中,只有在第一章(观察麦琪)和第二章(与凡妮的谈话)中亚美利戈观察和思考的中心才是麦琪,在其余与亚美利戈聚焦有关的几章里,他的观察对象还涉及到亚当、夏洛特和凡妮;在第二卷中,麦琪除了在第36章中对围坐在一起玩牌的阿辛汉姆夫妇、夏洛特和亚美利戈进行观察外,其他大部分都表现了她在独处时的一种内省(introspection)和沉默。她在沉思和想象中把自己移位(transfer)到一个想象和直觉的世界中“观察”亚美利戈和夏洛特。当亚美利戈出现在麦琪的意识中时,麦琪反而使自己从属于亚美利戈的意识:
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崇拜他,喜爱他,他的英俊、聪明和魅力都是他恰到好处地逐渐向她展示的。(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2.)
当她把视角投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时,她觉得:
即便是有朝一日他酗酒、殴打她,或者是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反正不管问题有多严重,只要一想到他身上具有的那种对她来说不可抗拒的魅力,就足以使她觉得自己有多爱他。(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2.)
在这两段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代词“她”和“他”。虽然亚美利戈并没有真正出现在麦琪的视线中,但是不断重复的“他”表明亚美利戈在麦琪的意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一个被“崇拜”、被“爱”的对象。由于没有相应的语境证明麦琪强调的“英俊”和“魅力”与亚美利戈的精神世界有何种联系,我们只能认为,“英俊”和“魅力”仅仅是麦琪在想象的视觉(vision)中描述亚美利戈的外貌。与小说前半部分亚美利戈的聚焦不同的是,麦琪对于亚美利戈的观察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她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的。另外,在这段文字中,尽管在语言形式上“她”是代表主体的主语,但“他向她展示”一语,以及“不可抗拒”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麦琪虽然在形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她与另一位女主角夏洛特一样,也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她不仅要考虑到丈夫的尊严,还要为父亲的利益着想。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当她意识到亚美利戈与夏洛特的真实关系时,她依然以沉默的方式与这种关系抗衡,并且只能凭直觉在想象中观察、揣摩这种关系的进展。而她的主要聚焦对象也常常不是亚美利戈,而是夏洛特。因此,当夏洛特和亚美利戈同时作为聚焦对象呈现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时,她带有强烈的道德谴责意味的眼光直接指向夏洛特。从这一点讲,将夏洛特的行为转化为道德无意识的直接人物并不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也不是詹姆斯,而是聚焦者麦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发生在第36章中的一幕。通过麦琪的眼光,我们看到阿辛汉姆夫妇、夏洛特和亚美利戈四人在玩牌;麦琪在高大、明净的窗户旁边一边踱步,一边观察夏洛特;她觉得“像是有一只野兽马上就要扑向她,咬住她的喉管”;(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3,p.472.)不一会儿后,她仿佛听到了“笼子的栏杆正在被砸破,那只轻捷、漂亮、浑身闪亮的野兽已经钻出了笼子,在外面逍遥自在”;(注:Henry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72.)她觉得“她(夏洛特)就是那只野兽,费尽力气钻出了笼子。”(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74.)“她看到那只野兽已经从金属笼子里边把笼子的门捅破,野兽已经在笼子外自由自在。”(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505.)
在这一场景中,我们看到,麦琪的视觉与意识、现实与想象已经融为一体。虽然她的确看到了现实中的夏洛特,但真正现实意义上的观察对麦琪来说已不再重要。正如诗歌中的“移情”作用一样,当麦琪得知自己的丈夫与继母的真实关系后,出现在麦琪视觉中的夏洛特立即被她的道德意识所联想的意象(野兽)覆盖了。与亚美利戈的眼光一样,麦琪的思维中也出现了一个等式:夏洛特=野兽。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在麦琪的意识中,以至于当麦琪在想象中感觉到父亲正在帮她解决难题时,她也用同样的意象描述这一感受:她父亲“那双插在口袋里的手中捏着一根丝绸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紧紧地系着她(夏洛特)的脖子”。(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3,p.508.)值得一提的是,麦琪在意识中对夏洛特进行道德批判时全无责怪亚美利戈之意,而这与我们在前面有关她的那段内心独白形成了她立场、态度上的一致。
与麦琪一贯性的思想意识相对应,亚美利戈在对麦琪进行观察时也表现出他在视觉与思想意识之间形成的一贯性:
他(亚美利戈)看了她(麦琪)一会儿——他明白她在自己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像,在她那个美丽的世界里,她就是其中最美丽的东西之一。(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9.)
如果我们把这段聚焦描写与亚美利戈观察夏洛特时的情景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亚美利戈在这儿依然是聚焦者(“他看了她一会儿”),但叙述话语却省略了他对于聚焦对象的外观描述,转而用“总结性的心理叙述”(注:Dorrit Cohn,Transparent Minds:Narrative Modes for Press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1978,p.41.)对聚焦者本人进行心理描写。里蒙·凯南在界定叙事聚焦时,把聚焦分为知觉、心理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内容。(注: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 and New Youk:Methuen,1983,pp.77-82.)在上面这段聚焦中,叙述对于知觉方面信息的省略为的是突出聚焦者的心理和意识活动。通过叙述者对人物意识的转述,我们看到,麦琪在亚美利戈眼里转化为“最美丽的东西”(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如果对照一下亚美利戈对夏洛特和麦琪的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聚焦者本人在观察两位女子时眼光中蕴含着同一价值体系。用另一人物凡妮的话来表示,有两样东西占据了亚美利戈的意识中心:“一是一位可人的(beautiful)女子,二是一笔可观的(beautiful)财产”。(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394.)对于亚美利戈来说,这两者都是他想要的东西(things)。
只要把亚美利戈和麦琪对于夏洛特的观察进行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一种在形式上十分相似的思维风格:亚美利戈对于夏洛特的观察是把眼前具体的人抽象为金钱(物化为钱包);麦琪则把夏洛特转化为具有强烈道德寓意的动物(野兽)。从整个心理过程看,前者所经历的意识过程是从具体(夏洛特)到抽象(夏洛特的交换价值)再到具体(被占有的夏洛特);后者也是从具体(夏洛特)到抽象(诱惑)再到具体(野兽)。但当聚焦者的眼光从对聚焦对象的外部观察内化为聚焦者本人的心理意识时,叙事文本在读者不经意间悄悄掩盖了第二个环节:亚美利戈眼里夏洛特的交换价值以及麦琪眼里夏洛特的诱惑。这样,无论我们通过亚美利戈的聚焦还是通过麦琪的聚焦,我们都只能看到,在亚美利戈与夏洛特的关系中,亚美利戈是受引诱的被动者。因此,麦琪尽管“感觉到自己身处困境,但她觉得这种时候要想保持尊严,全凭如何处理这事”。(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45.)小说第二卷放弃麦琪对事件和人物的外部观察,转而持续描写聚焦者本人的意识和直觉,这一技巧正好符合麦琪所采取的沉默策略。于是,麦琪在第二卷中作为意识中心所占的叙述空间越大,她的沉默和被动就显得越是漫长而沉重,麦琪的沉默,虽然是她采取的策略,但也是迫于亚美利戈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和父亲的利益的无奈之举;既是为了亚美利戈的“尊严”(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p.45.)和“一只没有瑕疵和裂缝的金碗”,(注:Henry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56.)也是为了她父亲,因为“父亲之所以结婚,也是为了我——全是为了我”。(注:Henry James,The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24.)显然,麦琪的沉默是她为维护父亲的利益和丈夫的尊严下意识采取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这种放弃自我与夏洛特为亚美利戈牺牲自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夏洛特的主动和麦琪的沉默都紧扣着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象征主题——那只带有裂缝、里边是玻璃,但外表镀着黄金的镀金碗——一种以父名构建的美丽而残酷的形式。麦琪的权力,除了沉默,还是沉默。所以,当凡妮惊叹于她的沉默并问她究竟为了什么时,麦琪的回答只能是模棱两可的:
“为了爱,我什么都能忍。”
凡妮有些迟疑地问:“是为了你父亲?”
“为了爱,”麦琪重复了一遍。
凡妮直愣愣地看了她一会儿。接着问:
“为了你丈夫?”
“为了爱,”麦琪又重复了一遍。(注:Henry James,The Golden Bow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384.)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说《金碗》中,聚焦问题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问题,两个人物意识中心也不仅仅是构成形式上的对称。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两个聚焦人物,则不难发现眼光折射的人物意识形态对于眼光的操纵作用。因此,在讨论聚焦问题时,仅仅关心“是通过谁的眼睛观看”是不够的。就《金碗》中的两个主要聚焦者而言,当我们考虑到两个聚焦者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对象的观察以及眼光蕴含的性别、主体和金钱意识时,我们的认同态度绝对不是如塞尔斯说的那样:“或者无法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就是等同于双方”。(注:Sallie Sears,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73.)也许J.希里斯·米勒的观点是可以借鉴的。米勒认为,阅读是一种代表道德的行为,;一个叙事文本,除了它自身形式上的东西以外,“还表述了某种意识形态”。(注:J.Hills 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8.)小说《金碗》也不例外。两个主要人物意识中心的运用,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它们互相对立,虽然使我们无法与其中的任何一方发生认同,但是互为对立的结构为我们提供了对两种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的可能。
